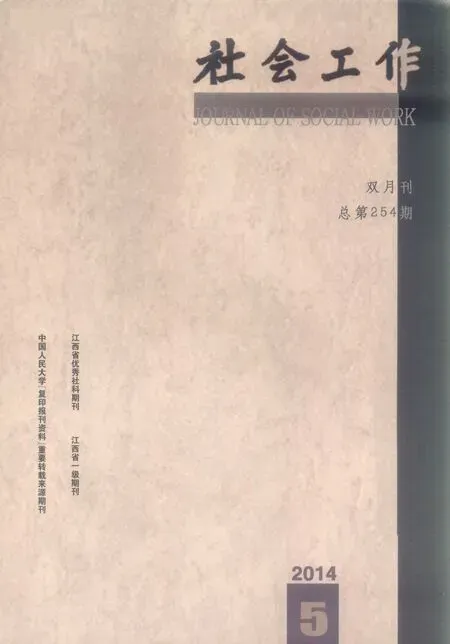对男性受暴者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的经验与反思
2014-04-09蔡宜庭
蔡宜庭
对男性受暴者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的经验与反思
蔡宜庭
当大众将焦点关注在婚姻里的受暴妇女(70.67%)时,也开始有部分的男性婚暴被害人(27.86%),逐渐透过社政、警政、卫政等管道求助。现今在婚暴相关领域之研究,多是将男性定位为婚暴中的加害人,并关注婚暴妇女的服务需求与心路历程。本研究的目的,即是透过实务工作者回观与反思过去与男性婚暴被害人工作经验,进而探讨工作者是如何看待所服务的个案,以及工作者自身所持有的价值观,并探讨工作者的价值观在服务输送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本研究将采取质性研究之深度访谈法,并使用立意抽样,汇集四位实务工作者之访谈内容进行分析。
男性受害者 婚姻暴力 工作经验
蔡宜庭,台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硕士生。
一、前 言
因本研究之主题是建立在对男性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的经验上,故引发笔者回想在生命经验中出现过的“男性们”,以及与他们的互动经验。笔者在家中排行老大,后面还接续著有两位弟弟,一家共五口人。在家中,男性虽然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然而他们(包括笔者的父亲)却较常是沉默且甚少表达意见(也可能是被家里的少数女性给剥夺了),家中大部分的决定多是母亲做主。或许是小时候父母亲忙于家计,又嘱托笔者要帮忙照顾、管教两位弟弟,因此直到笔者正式与“性别刻板”、“女性主义”等概念接触时,感到有些陌生与不适应。在笔者的生命经验里,男性(指笔者的两位弟弟)才是需要被管教的,女性(指母亲)的权力与地位是与男性(指我父亲)相当的,女性并非是男性的附属品。
家庭是个人社会化过程的最初场域,然而到了求学阶段后,学校成为第二个影响个人成长很深的场所,不仅是课业上的学习还包括人际上的交往。可能是受到在女校待了六年,以及大学时主修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系所(此类系所修读的女性多于男性)等影响,因此在笔者的人际相处经验中,很遗憾的还是与女性互动的经验占多数,在与男性互动时会感到有些退缩与不自在,直到开始交了男友后才对于男性有不同面貌(男性也有成熟的、体贴的、较强势的一面)的理解,但也很遗憾因为参考的“样本数”不够,而也不足以描绘男性群体的样貌。在逐步社会化的过程中,随着对女性主义议题的关注,笔者一方面瞭解到女性遭受男性的压迫与种种不公平的对待,但对男性亦有”疼惜”之感,尽管男性在表面上享有很多“优势”,然而这些优势的背后也隐藏著华人文化对于男性的深厚期许,这也未尝不是对男性的另一种压迫。
笔者的生命经验(缺少与成年陌生男性接触的经验)或多或少影响了后来在工作上接触到男性且受暴的个案时的工作态度,而这些受暴男性们的“故事”在我的内心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原来,在当今认为男性是宰制女性的社会里面,男性亦有可能出现受暴的情形,进而引发出构思本研究的雏形。男性在生理上相对于女性是占优势的,因此从政策立法到实务上的服务输送,在面对与处理男性受暴的问题上常常受到忽略。简言之,一位男性若和外人诉说自己遭受妻子的施暴,比一位女性向外人诉说遭丈夫施暴的被取信程度还低,此外,其求助的目的还可能会被人怀疑,使得男性受暴时向外求助意愿更加退缩。
二、研究动机与目的
过去有关婚姻暴力①“家庭暴力防治法”2007年对家庭成员的定义做了修改放宽,此放宽让“家暴防治法”不仅是异性恋者可以使用,也将同性恋者在亲密关系中人身安全上的需求纳入服务范围内,因此在学界里也开始有人使用“亲密关系暴力、伴侣暴力”来取代“婚姻暴力’,研究者也较倾向于采用前者的说法,然碍于本文有意强调在婚姻关系中之男性受暴者的处境,故思量一番后仍采用后者。的研究多半将研究的焦点放在受暴的女性以及男性为加害者的角色上,对于受暴男性的关注可谓是相当少。婚姻暴力议题多是以受暴的女性为叙事主体,尽管这些研究也承认有潜在的男性受暴个案,然而多数的研究还是从数据来解释女性在婚姻中受暴仍占多数且处境弱势,因而呼吁要将资源放在弱势且受暴的女性上。这些即为在开始工作前对婚姻暴力的想像。
因毕业后笔者曾在N市的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以下简称N市家防中心)从事兼职追踪通报单的工作,该工作经验打破了过去对家庭暴力受暴者多为女性的想像,根据对实际接触个案的统计,男性受暴个案也占了将近一半的比例。犹记得刚开始追踪通报单的时候,总会盯着通报单的内容仔细研究一番,这种情形尤其是在追踪男性受暴个案上,且因担心被个案拒绝而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沙盘推演,对于电话会谈里个案的言词、语调都非常地戒慎恐惧,且很怕被“识破”。笔者的这种心理状况在面对女性受暴个案时则不会发生,通常是研究完通报单之后便立即拿起电话进行追案。因此在工作进度上,男性的个案很明显地总被拖到很久才完成追案,且会因为男性个案的基本资料及状况差异而有不同程度的“拖延”。例如,在面对30-65岁之间,学历程度研究所(含)以上,或是从事专门技术工作(如律师)等类型的男性个案时,总会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样类型的男性应该不会需要社会工作者的协助。
因此,本研究是从研究者的工作经验与反思出发,并与现从事相同工作性质的其他社会工作员进行访谈,企图探讨社会工作员在面对男性受暴个案时的工作态度与自我反思,并就现行的政策与实务工作状况提出个人的回馈与建议。
三、研究背景与文献探讨
(一)研究背景:N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与兼职社会工作员之现况说明
因本研究之背景脉络与N市家防中心有密切的相关,故研究者认为有必要将此脉络交代清楚,以便瞭解研究者的工作内容、性质,有助于对于本研究之发想与展演有更贴近的瞭解。根据“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法律规定,各县市皆须要设置一专门受理家庭暴力暨性侵害相关业务之单位,故在该县市所发生的家暴或性侵害事件一经相关责任通报单位知悉后,便须在24小时内进行通报,通报后便由该县市之家防中心提供后续相关的服务。
以N市家防中心为例,该中心内部之组织编制,有主任、秘书,以及接案组、儿少保护组(内部称辖区)、成人保护组(指委外之妇女保护服务的单位)、性侵害保护扶助组,以及其它间接服务类型的组别(如教育宣导组、综合规划组等)。该中心在家庭暴力案件类型上,乃是依照受暴者与施暴者之间的关系来界定暴力案件的类型,其类型共有:儿少保护、女性婚暴并儿少保护、女性婚暴、男性婚暴、老人保护、其他家虐。其中,因为儿少保护与女性婚暴之通报案量过高,遂将女性婚暴之案件委托由民间的社会福利机构来承接,提供受暴妇女后续的服务,然各机构每月仍有派案之上限,故当月超过上限之女性婚暴案件亦会交由接案组的兼职社会工作员负责追踪,若经追踪后评估需要开案,则可再派案到该辖区负责承接女性婚暴之社会福利单位提供后续的服务。
研究者过去曾应征N市家防中心的兼职社会工作员,从组织编制来说,兼职社会工作员是隶属于接案组之下,由接案组之督导负责管理。其工作内容为负责追踪通报单,在一个完整的家暴服务历程的光谱上,属于初步且短期的关怀追踪;其负责追踪的案件类型包括:男性婚暴、目睹儿童、老人保护、其他家虐;其职责在于厘清个案之受暴状况、瞭解个案与支持系统的连结、提供个案所需之服务资讯,并依据其受暴后之人身安全状况、危险程度与后续的服务需求来评估开案(即后续长期的处遇服务)与否。
(二)文献探讨:男性在婚姻关系中的受暴
对于男性受暴个案值得被关注的重要性,魏楚珍(2002)的研究曾提出以下的看法:尽管在婚姻暴力中,男性受暴的机会与受伤害的严重程度远比女性要低得多,但是此类”轻微”的攻击可能会引发后续的问题,例如,假设社会上仍然存在一种潜规则是,赋予男性能够管教他们妻子的权力,则对男性施暴的女性可能会引起男性的报复;亦有研究发现,来自妻子轻微的暴力,会增加来自丈夫严重攻击的比例。此外,在男性或女性单方面的施暴,亦或是男女双方互殴的暴力冲突等场合,目睹儿童可能会产生许多问题或受到心理伤害,影响儿童的行为、情绪、社会功能、智力或学业、身体上的伤害与阻碍等。因此,不论是约会的男女、同居伴侣或已婚/离婚后的夫妻彼此都不能以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在道德本质上的错误。因而在社会政策与临床服务上,皆不能忽略男性个案受暴的问题。
在表面上,婚姻中的男性总是比女性更具攻击性,魏楚珍(2002)认为,此乃是因为情境的定义狭窄与限制,以及发生时间与地点的隐私性,难以被察觉与注意,有关精神上的虐待更是难以被具体定义之缘故。然而从魏楚珍(2002)所整理的国外针对家庭冲突调查的文献可发现,男性与女性都会攻击伴侣,且超过三分之二的研究发现女性攻击(12.4%)的机率略微高于男性攻击(12.2%)。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女性其实像男性一样,使用与她们性别角色较为一致的方式,表达直接的攻击(魏楚珍,2002)。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乃是采用质性研究的面对面访谈法,使用立意抽样选取访谈对象,选取与研究者一样有服务男性受暴者工作经验的人员为主要对象,并于邀请前说明本研究之动机与目的,在获得受访者同意进入本研究后,于进入访谈前亦先取得受访者之录音意愿征得受访者的同意进行访谈录音,并将誊打完成之逐字稿与受访者再次澄清以确认无误会受访者所陈述之内容并将誊写打印完成的逐字稿交给受访者再次澄清,以确认不会误会受访者所陈述之内容,最终经过受访者同意后开始分析并撰写本研究。访谈大纲最初是从研究者自身的工作经验反思出发,于2013年1月16日完成第一次访谈与完成逐字稿后,略做修正并增减想要继续探讨的议题,并于2013年1月17日、1月22日、1月23日三日完成与社会工作员的访谈,总共汇集四名访谈者的访谈资料。
四、资料分析
(一)受访者之基本介绍
四位受访者中有一位是男性,其余三位皆是女性,年龄皆在30岁以下,其中有两位受访者有在家暴领域实习的经验,另外两位则是有儿童与家庭或医疗领域实习的经验。此外,四位受访者皆是毕业于社会工作学系,其中有两位目前是一边兼职一边修读研究所。四位受访者的共同点为,从事兼职工作乃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四位受访者从事兼职工作最长的有将近两年,最短的则是五个月。最后,四位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来应征兼职工作时,是抱持着希望能累积一些实务工作的经验,且部分的受访者亦有在规划参加“国考”或是研究所等考试。
(二)与男性受暴个案一起工作
社会工作员在接到有男性受暴的个案时,对于女性单方面施暴的状况仍感到很特殊,对于男性受暴个案的自我保护能力产生质疑,亦认为其求助的目的可能是与和另一伴在资源上较劲的意味有关,感觉受暴后真正需要协助的男性占少数,这与女性受暴个案工作有很大的不同。
“东方人的文化还是觉得说男生是属于比较强势的,当然会怀疑说,你的力量比较大,或是你可能都在外面工作,你知道的东西比较多,为什么你还会被这样子?心中会有这样的怀疑。”(受访者R)
“男婚,特别有一些反而会是加害人,因为我觉得毕竟刻版印象就是会觉得说男生本来就是保护自己的能力会比较好,力气也是比女生大…在评估上不够客观…其实他说不定真的是有一些困难,有时候太太也是因为曾有社工介入造成较会善用一些资源去压迫个案…或是如果太太想离婚或者争取监护权可能就会去激怒个案,太太可能言语暴力,那个案就是以肢体暴力的方式回应,这样也是有可能……也有听过说个案就是遇到太太没事就录音的状况。”(受访者O)
“我觉得最大的冲击可能是来自于,女性纯粹是一个加害人的角色的时候。因为新闻还有一些资讯都会一直形塑说,婚姻暴力是男性对女性的施暴…男性纯粹受暴的状况因为太特别了,不同于我们过去想像的形态。其实真的存在,可又很难解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受访者Q)
“通报单进来的受暴者分两种:一种就是想要,因为他妻子有用这个资源,他也想用这个资源;另外一种是,他确实就是属于婚姻中比较弱势的那一方。但是第二种,这种比较弱势的这种是少数啦”(受访者R)
然而亦有受访者提到,社会工作员在面对相同严重程度的受暴状况下,个案的性别会影响到社会工作员决定案件被追踪的优先顺序,其中也隐含着社会工作员自身的性别刻板概念。
“假设一个男性去打破一个女性的头的时候,会觉得很严重。但如果今天是一个女性打破一个男性的头的时候,相对来说,好像甚至会想说,是不是东西太硬?不会想到说,就结果来说,两个人都是伤到头,都是属于高危险的受暴。我想在现实中处理的话,一个可能会是很急的案,可是另一个可能就会被摆到次要的。那我相信他一定会是需要更前面的顺序去追,可是就没有人可以跟女性被打这件事情平起平坐”(受访者Q)
在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中,强调社会工作员与个案之间的互相信任,然而当社会工作员面对男性受暴个案时,在建立关系上难以自然地建立起信任关系,且过程中经常会一再的检验、追问细节,以确认该男性受暴个案是否为纯粹的受暴,亦或是“案情不单纯”的状况。
“看了他以前可能有一些施暴的经历之后一定会多少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的训练就是…要相信他们讲的话,我们是跟他们工作的”(受访者R)
“遇到男婚的时候,多少会想到就是其实是女婚并男婚,会觉得真的是女生单一的去施暴吗?还是其实是两方的拉扯…多少会去预设男生是相对人,甚至会觉得那个拉扯好像是淡化了一些什么东西,多少都会有这样的探究。”(受访者Q)
“还是要相信他讲的话,我都是这样子想…报告当然呈现就是客观的东西…但是在评估的地方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我真的质疑他说是不是只是想要获得这个资源。”(受访者R)
社会工作员在接触男性受暴个案时,整理出男性受暴个案在面临受暴后的服务需求可能以法律上的服务需求(如保护令细节、离婚诉讼、争取子女监护权等)较多,对于情绪支持或是人身安全计划的讨论需求则是较少,但也会碰到男性受暴个案对于自己的需求并不明确、厘清困难的情形。此外,社会工作员亦会面临到既有的资源无法满足男性受暴个案的需求之情况。
“男性他们的想法是比较目标,任务取向。那其实我们谈的时候也多少是就当次事件,他后续要怎麽去处理来处理。只有一部分的男性会愿意去讨论对于当次事件的情绪。”(受访者Q)
“男生主要都是在法律上的问题,因为如果真的说到安全的话,男生基本上的确会有比较多的能力可以保护自己…男生就是比较多在问有关保护令的详细的细节,或者是离婚争取监护权的状况。”(受访者O)
“其时我刚开始是相信他的…就是怎么都没办法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一直被打,但是还是会觉得有些疑点,就是你都可以工作而且你们也都分居了,那太太就是可以这样子随意进来你的家里嘛?那既然都分居了,为什么不离婚…但是他就是一直觉得还有机会可以…他也一直说他受不了他太太,可是他还是想要继续维系。但我觉得其实这跟很多女性受暴的状况很像,就是受不了被这样对待,可是还是没准备好离开。”(受访者O)
“家暴中心一开始会成立本来就是因为女性主义,所以一开始本来就是服务女性啊…可以提供给男生的就是比较少,像女生可以庇护,可男生没有办法庇护。我其实也有遇过男生就是想要跟我问庇护的事情,他觉得他有需要,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跟他说有游民中心,你要不要去住一下…还有便宜的旅馆,那也是他自己本身要有钱。”(受访者O)
社会工作员在服务过程中若觉察到个案过去曾是施暴者的身份时,所采取的因应方式可能会与受暴男性开始产生心理上的距离,意指不太会针对案主的感受给予正向的支持,此外,在资讯的提供上,也是比较被动给予的方式,亦会透过法律上的约束强调对暴力的谴责态度,以较委婉的方式规劝其对妻子的施暴行为。
“知道他其实是相对人…当然难免会有,可能站在个案这一方的想法会比较少一点,会变得比较有距离,的确是会发生。”(受访者Q)
“举例来说,他想要采取一个法律途径,那如果我知道他是相对人的话,可能就不会愿意跟他说那么多,会请他去问律师之类的,那还是会提供他一些法律咨询的资源。”(受访者Q)
“我通常会看旧案,如果过去其实就是加害人的角色,在资讯提供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完整。例如很简单求助管道,就是只提供他“113”而已,不会跟他讲我们中心的电话。”(受访者O)
“表面上是跟他说使用暴力以暴制暴自己也会受伤,但是其实一方面是在提醒他说,不要对他的家人使用暴力这样。”(受访者R)
此外,针对研究者自身的经验,刚开始在面对男性受暴个案之会谈上的障碍状况,经访谈四位受访者后,认为此乃是研究者个人的经验。在其他四位受访者的经验中,在与个案电话会谈前的恐惧与焦虑多半是来自于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度不足、害怕与陌生人交谈等情形所致,并无特别针对个案的性别而有差异。
“跟陌生人讲话的时候我是还满焦虑的,但是会发觉说,经过这四个月以来越来越能比较自在的能跟案主工作还有会谈,比较能够在他们情绪高涨或是她们也很焦虑的时候,先把他们情绪稳定下来,然后再跟他们做一些沟通。就是最大的进步。”(受访者R)
“记得我当时觉得比较慌的是,他有问我保护令的东西,因为我那时候对保护令还不是很熟悉,但是他又问得很详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和旁边的社工使一下眼色,然后他就赶快写给我,我就赶快跟他讲这样子。”(受访者O)
五、小 结
婚姻暴力最隐弊的地方在于,事发的当下可能仅有夫妻双方在场,而夫妻之间的互动状况、沟通模式也很难在初次电话关怀时即能充分理解,并评估夫妻之间是否有权力控制的议题,甚至外人与夫妻双方当事人对于当次暴力冲突也有着不同的认定。常可见到的是,外人在一旁十分挂心与担忧,然而个案反觉得外人太夸张,这并没有什么;而这个外人又更加不瞭解这到底是淡化受暴的事实亦或仅仅是单一偶发的暴力冲突。这之间的差距与微妙的细节确实需要实务经验上的累积,才能在个案有开放讨论的意愿下,社会工作员透过更深入的厘清始能做出正确的评估。
在实际接触到及过去所认知的,与女性遭受男性施暴的婚姻暴力概念有所差异的男性受暴个案时,对于如何与男性一起工作,尤其是在讨论婚姻暴力的议题时,确实是面临到一些挑战,一方面对于真实的状况感到十分的特殊与难以理解,另一方面又担心不断的追问会伤害到男性尊严。此外,根据笔者自身的工作经验,男性在婚姻关系中受暴的状况与女性受暴的状况之明显差异在于,其中涉及权力控制的议题甚少,且在实务上也很少质疑拒绝协助男性的适当性(林等译,2004),甚至亦会怀疑其求助的目的与动机不纯,一经发现其过去曾有施暴或潜在施暴的状况时,便会与个案保持更大的距离,在资讯的提供上也会基于避免“疑似相对人”知道太多而有所保留或消极回应,故对于厘清男性受暴个案的真实面貌以及建立信任的专业关系确实有一定难度,也深感未来对于男性研究之深入探讨以作为实务经验上之整理的必要性。
本研究主要发想自研究者自身的工作经验与反思,在即将挥别将近两年的工作单位,转而投入研究所课业之际,藉由此次课程机会将这些经验做出粗浅整理与论述,对研究者而言有所助益,也算是一短暂工作经验的结晶。期望后续在男性受暴的议题上能将其受暴历程、受暴后的身心状况以及婚姻概况等因素也纳入考量,以增进对于男性受暴个案之理解。
[1]王行,1996,《回家的路也太长——“男性研究”两年杂感》,《妇女与两性研究通讯》第41期。
[2]王行,2002,《“男”对“作品”的回应》,《应用心理研究》第16期。
[3]魏楚珍,2002,《房门内的故事——我看异性恋男人在亲密关系中的“受虐”》,台北:东吴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硕士论文。
[4]Lena Dominelli,2004,《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林青璇、赵小瑜等译,台北:五南。(原著出版于2002年)
编辑/杨恪鉴
C916
A
1672-4828(2014)05-0088-07
10.3969/j.issn.1672-4828.2014.05.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