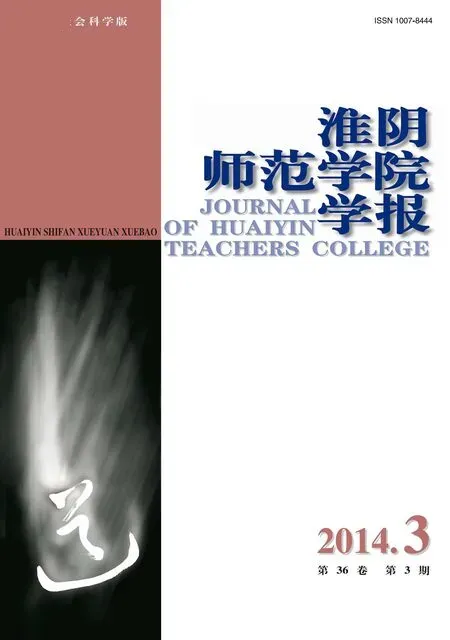主持人语: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的源头是民歌。
2014-04-08周玉波
传统民歌发展史上有这样几个经典性的标本,并且带有各自独具特色的时代印记。一是《诗经》,学界共识是《国风》中大部分篇什是其时流行的民歌,蓬勃的生命力至今令人景仰。二是两汉乐府,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秉性为后世叙事性韵文的创作树立了标杆。三是明清民歌。李梦阳的“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说,为明代民歌的兴起作了理论上的储备,李开先、袁宏道、冯梦龙等人则是以编撰、鼓吹民歌的实践,为《挂枝儿》《劈破玉》等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成就了“我明一绝”(卓珂月语,见陈宏绪《寒夜录》)的奇妙景观。清代乾隆以后,民歌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南北交汇,城乡交汇,雅俗交汇,民歌时调与曲艺(戏曲)交汇,使得有清一代民歌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传播方式多样,接受人群遍及各阶层,清代亦因此成为民歌发展史上一个集大成的时期。逮及近代,黄遵宪“天地之至文”(《与郎山论诗书》)的民歌观,与李梦阳的“真诗”说相去未远,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歌谣征集、整理与研究热潮,则成为文化革命与启蒙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传统民歌的发展历程大致如上所述,民歌与文学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在文人文学占据正统地位,即文学发展进入规范化的轨道之后,相对原生态的民歌已经难以进入主流文学的领地,民歌扮演的只能是配角,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登上前台,与主角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互动——梁实秋说,在最重辞藻规律的时候,歌谣愈显得朴素活泼,可予当时作家一个新鲜的刺激(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第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当代无文字,里巷有真诗”(《袁宏道集笺校》卷二《李子髯》),以“真诗”对应“文字”,就是“刺激”的最为生动的例证。
历史是由受教育之文雅阶层书写的,向来代表主流社会的观点,治文学、文化者则服务、服从于此一阶层与社会,会有意无意地忽略彼岸风景,是以在文学研究领域,除《诗经》享有尊崇待遇外,作为配角的其他各代各类民歌始终难以摆脱通房之嫌。
由周作人、刘半农、胡适等人发起的歌谣运动,改变了这一状态,其参与者多,影响亦大,价值与意义,世人多有论述,且简要归纳为如下两点:
其一,拓展传统学术研究疆域。歌谣运动的早期倡导、参与者,均为正统学术圈中人物,有着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范围。对他们而言,乡土气息浓厚的民间歌谣的介入,有着双重意义。一是这些歌谣是来自现实的鲜活的东西,因而有着强烈的冲击力;二是这些歌谣中蕴含丰赡,为人们从文学、历史、语言、民俗、社会学等角度切入提供了多种可能,而这恰恰是新兴学科初创期必须具有的原动力。
其二,颠覆传统学术研究理念。歌谣运动颠覆国人固有的学术研究理念。国人向以为文章乃不朽大业,经国盛事,民间制作则不然。如顾颉刚先生,原以为歌谣是低级的东西,不值得理会。受歌谣征集运动影响,顾先生的观点有很大改变,“对于一切的民间文艺有了比较平等的眼光”(顾颉刚:《吴歌·吴歌小史·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版),因而积极参与其中,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歌谣运动参与者们深入生活、重视田野之做法,也成为歌谣运动本身取得的重要成就。
与歌谣运动参与者的做法不同,郑振铎等人对民歌的整理与研究,遵循的仍然是传统治学路数。郑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在文学演进的整体框架内,观照历代民歌的生命历程,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但是受时代与条件的局限,在研究方法与资料挖掘上,《中国俗文学史》以及相近时代的其他著述(胡怀琛《中国歌谣研究》、朱自清《中国歌谣》等),均存在一定的缺憾,如资料长编的特征较为明显,郑先生甚至将不同戏曲选集中收录的民歌混为一谈(详见拙著《明代民歌研究》第十二章《弥足珍贵的历史遗存》,凤凰出版社2005年8月版)。
傅芸子、傅惜华、关德栋等人在具体民歌作品(集)的挖掘、介绍与评介上用力尤多,《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曲艺论丛》《曲艺论集》,还有关先生、赵景深先生为《明清民歌时调集》所作的长序,至今仍然是明清民歌研究领域的奠基性文献。
文学研究只是民歌研究的一途,如钟敬文即认为其“致力于民俗学的工作,是从搜集民间文艺作品开始的”,虽然“当时考察所用的观点,主要是文艺学的”,但20世纪20年代后期,钟先生即“不但对民俗学范围的注意逐渐延伸了,而且对于这门学科本身及相关学科的知识也在不断地扩充”,于是就形成了“把民俗当作文化现象的初步观点”(钟敬文:《民俗文化学
梗概与兴起》第2页,中华书局1996年11月版)。前说胡适、刘半农、周作人诸公,他们关注民歌的重点,均不在文学,而是在调查、研究与改良社会。
此一现象似乎说明,经过漫长曲折的繁衍生息,民歌的职能实现了回归——从源头看,孔子“兴观群怨”说本非专门针对文学而言,何况还有后来“观风俗、知薄厚”(《汉书·艺文志》)的明确定位。至此,历经数千年的艰难跋涉,民歌完成了“华丽转身”,其本体意义、价值和外在之研究行为悄然“复位”。私心以为,至此可以讨论一下民歌学的问题了。
此前有人说歌谣学,然其立足点是民俗学,是在民俗学框架下说歌谣的种种,如歌谣分类、传播、整理与研究,等等,与我心目中的民歌学理念稍有距离。最主要的区别,是研究路径有异,对研究主体定位亦不同。我之所谓民歌学,是摆脱现行学科分类的限制,将全部民歌活动当作一个自发的过程,将民歌搜集、整理与研究当作一个自洽、自在的完整体系。换言之,民歌学的理论基础是民歌本位论,研究路径是循民歌活动轨迹,探究其发生、发展的规律,了解其在社会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及所起作用。如《诗经》,向来的研究模式是人类学、民俗学、文学、历史学著述等均从其中寻求素材,寻求观念支撑,《诗经》被割裂肢解,被“各取所需”。在民歌学视野中,以上学科对《诗经》的引用与解析,均成为《诗经》的延伸与具体应用,人类学中的《诗经》、民俗学中的《诗经》、文学中的《诗经》、历史学中的《诗经》,变而为《诗经》中的人类学、《诗经》中的民俗学、《诗经》中的文学、《诗经》中的历史学。视角转换,效果不同,经此转换,《诗经》的内容、价值得到整体展示,人们对经典的印象亦由此前的局部、附庸变而为系统、独立。个案如斯,整体尤是——可以想象,依此理念而成的《中国民歌发展史》,将是何种气派。
要而言之,民歌研究可以属于任一范畴,但是借助对民歌运行轨迹的大致描述,有心者似可尝试创设有特色的本土民歌学体系,其内容包括民歌发生学研究、传播与接受研究、类型研究、内容研究、音乐研究、地域研究、演变研究、功用研究等。
或曰“民歌学”云云,类同梦呓。
那么回到民歌研究本身,确实仍须从头、从细部做起。如我做明代民歌研究,方法上向前辈学者如郑振铎、傅惜华等先生学习,着重点是民歌与其时文学新思潮的关系,顺及民歌的内容、价值(道德评价)、特色等,转囿宽松,并可避免因固执偏颇而受累;做清代民歌研究,关注的是民歌的生态链,是其与其他艺术种类如曲艺(戏曲)的相互影响,同时亦细究诸多文献的流布情况;做喜歌研究,着力点是考查喜歌与婚俗的共生状态,是在传统礼制与国人生活习性的背景下了解喜歌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形——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回到原点,即做好基本文献的爬梳工作。
此所谓着眼长远,立足当下。愿同好者携手,借助淮阴师范学院学报“民歌研究”这一园地,享受“立足当下”的乐趣,开启彼此共同的逐梦、圆梦之旅。
主持人:周玉波,江苏邮电报社主任编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