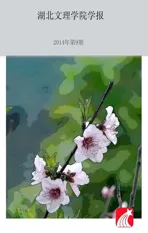宋玉遗迹传说田野调查报告(四)
——湖北应城蒲骚遗址与宋玉行迹调查报告
2014-04-08刘刚,王梦,关杰
刘 刚,王 梦,关 杰
(湖北文理学院 宋玉研究中心,湖北 襄阳 441053)
湖北文理学院宋玉研究中心宋玉遗迹传说调查小组于2013年10月8日抵达湖北省应城市,对古蒲骚遗址与宋玉在应城的行迹作了田野调查,返校后又根据调查所得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兹报告如下:
一、宋玉确到过蒲骚
据文献记载,宋玉曾到过蒲骚。为详尽的说明问题,兹将相关文献依时代次序引列如下:
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二十四《人道部·故交》“重见故人”条载:
景差至蒲骚,见宋玉曰:“不意重见故人,慰此去国恋恋之心。昨到梦泽,喜见楚山之碧,眼力顿明;今又会故人,闭心目足矣。”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六《人品》“喜会故人”条载:
景差至蒲骚,见宋玉曰:“不意重见故人,慰此去国恋恋之心。昨到梦泽,喜见楚山之碧,眼力顿明;今又会故人,开心目足矣。”
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二十《人伦三》载:
景差至蒲骚,见宋玉曰:“不意重见故人,慰此去国恋恋之心。昨到梦泽,喜见楚山之碧,眼力顿明;今又会故人,闭心目足矣。”(《列士传》)
明周圣楷《楚宝》卷十五《文苑·景差》载:
景差,楚同姓也,与宋玉同师事屈原。尝至蒲骚,见宋玉曰:“不意重见故人,慰此去国恋恋之心。昨到梦泽,喜见楚山之碧,眼力顿明;今又会故人,闲心目足矣。”屈原死,赋《大招》一篇。
清陈诗《湖北旧闻录》卷三十四《文献一·景差》载:
景差至蒲骚,见宋玉曰:“不意重见故人,慰此去国恋恋之心。昨到梦泽,喜见楚山之碧,眼力顿明;今又会故人,间心目足矣。”(《列士传》)
以上自宋至清五种文献所记基本相同,至于《山堂肆考》之“开心目足矣”、《楚宝》之“闲心目足矣”、《湖北旧闻录》之“间心目足矣”中“開”、“閒”、“間”均为转写传抄中因与“閉”形近而讹,而《古今事文类聚》与《广博物志》作“闭心目足矣”,切合文意,不误。这五种文献所载宋玉事,当同出于一书,《广博物志》、《湖北旧闻录》本注言出自《列士传》,即为五种文献引事之原典。此外,清李可寀等《雍正应城县志》卷七《古迹》,清赓音布等《光绪德安府志》卷三《地理志·古迹》,清罗缃、陈豪等《光绪应城县志》卷十《人物·流寓》亦载此事。或云引自《列士传》,或云引自《楚纪》,考明廖道南《楚纪》所载宋玉、唐勒、景差事,并无宋玉在蒲骚遇景差之内容,恐方志所引为另一本《楚纪》。《光绪应城县志》卷一《舆地志·沿革》于“(应城)战国时属楚。宋玉在蒲骚,景差被放至蒲骚,见玉曰:‘不意重见故人,慰此去国恋恋之心。’”一语下,自注说:“《楚纪》引《列士传》。”可见,方志转引之《楚纪》所载宋玉在蒲骚事亦出自《列士传》。《隋书·经籍志》言“《列士传》二卷,刘向撰。”今是书已佚,考之古文献中引录的《列士传》轶文,笔法、风格及写作旨趣与诸书所引宋玉在蒲骚事相类,可以判定宋玉在蒲骚事确出自西汉刘向所撰之《列士传》。这就是说,宋玉在蒲骚事是可以征信的。关于这一点,也可以在宋玉的作品中得到佐证,如《小言赋》说楚襄王赐宋玉以云梦之田,就与蒲骚有关(参见下文)。同时也与秦占领楚郢都(今湖北荆州北之纪南城)后,楚襄王迁都陈郢(今河南淮阳),收复江南十五邑拒秦,又用黄歇计“复与秦平”,而后直至楚襄王卒,秦与楚无战事的历史背景相吻合[1]。因为,一度被秦人攻占云梦东部重为楚国所有,秦与楚关系缓和且无有战事,宋玉随楚襄王去云梦一带才能成为可能。
二、应城蒲骚调查与考辨
除传世的宋玉作品外,汉代文献中记录宋玉行迹的资料极少,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只有此则与《汉书·地理志》所记的宋玉在寿春事,因而弥足珍贵。这一则资料以及对这则资料所涉地名与事件的深入考辨,很可能对宋玉及其作品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古蒲骚在今湖北省应城市境内。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江南道·鄂州》载:
应城县:本汉安陆县地,宋(指南朝宋)于此置应城县。
故浮城县,在县西北三十五里,即古蒲骚城也。《左传》“莫敖狃于蒲骚之役”,“郧人军于蒲骚”,是也。后魏于此置浮城县,隋废。
自《元和郡县志》这一认定而后,历代地理类文献和该地志书均未有异辞,仅是在距离里程表述方面略有出入。清李可寀等《雍正应城县志》卷一《沿革志》描述应城设县之始时说:
应城属《禹贡》荆州之域,历夏及商未有著名,入周春秋称蒲骚地。《左氏传》“郧人军于蒲骚”,又“屈瑕败郧师于蒲骚”,杜氏注:蒲骚,郧邑也。
南朝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析江夏置安陆郡,始徙江夏治夏口,而以安陆县为安陆郡治。析安陆县东境置孝昌县,北境置安蛮县,南境置应城县,并属安陆郡。应城为县自此始。(本注:县名应城,或云当时以为此地应作城,故名。或云岡阜周环隐隐如城,故名。未知孰是。)
清罗缃、陈豪等《光绪应城县志》卷七《名迹·城址》综合历代考辨指定古蒲骚遗址时说:
蒲骚故城,一名蒲骚垒,一名蒲骚台,在今县西北三十里,崎山团古城畈。居民常于耕作时拾败瓦零砖残戈断戟,古色斑驳。离城址三里曰沈家湖,今没为平畴,故老谓即古城之池也。
故浮城县,在县西北三十五里,即古蒲骚城也。《左传》“莫敖狃于蒲骚之役”,“郧人军于蒲骚”,是也。后魏于此置浮城县,隋废。(本注《元和志》)《郡国志》云,吉阳县东有蒲骚城,今谓之浮城,即《左传》所谓“郧人军于蒲骚”是也。(本注《舆地纪胜》)(又注:按《元和郡县志》,吉阳县本汉安陆县地,梁于此置平阳县,西魏改为京池县,隋大业二年改为吉阳县。在今汉阳府孝感县北。)《旧志》云,治西浮城县,西魏置。考《魏书·地形志》治境未尝置浮城也,今治北三十里有浮城畈,俗称故城畈。(本注《肇域志》)《一统志》并谓蒲骚城今在治北三十里,方隅相同,岂昔人称其地为蒲骚,后讹为浮城,亦慕容步摇之类与?
明周良《蒲骚台》诗:古垒荒凉望眼迷,断碑无字草离离。牧童不管兴亡事,一曲升平笛里吹。国朝程大中《蒲骚故城》诗:初日照寒溪,远风落深树。漠漠故城阴,隐隐苍苔路。郧人昔军此,州蓼纷相聚。抗楚亦何愚,要盟毋乃误。群鸟散惊弦,安能复回顾。空闻宋玉悲,讵解莫敖怒。往迹已苍凉,游人自来去。举琖对秋天,黯然立风露。
综合《光绪应城县志》所记,古蒲骚,南北朝西魏称之为浮城,后俗称浮城畈、故城畈,地处应城西北,明人曾在此地见过断碑,清人曾在此地拾得败瓦零砖残戈断戟,言之凿凿。据悉,应城治所自南朝宋建县以来,虽在20世纪由县改制为市,但地址从未迁徙。又北朝西魏在今应城境内曾置浮城县,但县治与南朝宋所置应城县治并不在一处。因此以应城市区为参照,古地志关于西魏所置之浮城亦即先秦之蒲骚的空间方位描写是非常清楚的:方位是应城市区西北,距离为三十五或三十华里,清光绪年间的地名是属于崎山团所辖的浮城畈。然而由于崎山团和浮城畈这两个地名在近代已经不复存在,古蒲骚的所在便成为了待解之谜。在2007年出版的《应城名胜》一书中,李怡南所撰《蒲骚故城遗址》一文认为,蒲骚遗址在今应城地区田店、巡检、杨河之间[2]。这三个地点均在应城市北:田店在西北,位于与京山县交界处,距市区约20公里;杨河在东北,位于与安陆市交界处,距市区约25公里;巡检在正北,距市区约15公里;三个地点呈钝角三角形分布,而田店与杨河又相距约20公里。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难以令人满意。为此,在应城调查时,我们采访了《应城名胜》一书的主编原应城市政协主席朱木森先生。他认为:一是蒲骚本无城垣遗址,可能有军事工事,所以叫蒲骚垒;二是蒲骚本为周代卿大夫封国,受郧国保护,相当于郧国的附属国,李文所言是其封地范围;三是蒲骚之役是一场大战,范围很大,因而其遗址不应限于某一点。朱先生所说有一定的根据,即在20世纪文物考古普查时,在这个地方确实没有发现古城遗址,但现今没有考古发现不等于其地古时不曾存在。我们认为《蒲骚故城遗址》的表述是不符合古代地理以治所为标识的学术规范,按学理即便是卿大夫的封国也当有其治所,即便其治所没有城垣也不能否认治所的存在。因此,寻找蒲骚的治所还是非常必要的。
其实,古代地理文献与该地志书所说的“蒲骚故城”、“故浮城县”就是指其治所而言,而不是封地范围,或县域范围。于是,我们按照已知的故浮城即古蒲骚城、古蒲骚城后讹为故浮城、清末仍有浮城畈的线索,进一步考索浮城畈的具体位置。清罗缃、陈豪等《光绪应城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在描述富水流经时说:
(富水)又东南流,至应城西为西河。西河至走马滩东经田店、王店、李家渡、严家渡、彭家畈,又十里至浮城畈、团山渡。渡为京、潜往来要道,邑人宋成美设义渡于此。(据采访补)西河至浮城畈,又二十里过宋家坡、三吉堰,港水注之。港自崎山发源,东南曲折至何家冲约七里泛为三吉堰,又五里经晏家桥,又十一里至严家濑,经龙潭龙坑,旧传有龙蛰此,故名,又二里至宋家坡入河。
这段描述是光绪年间县志编纂者根据实地采访撰写的,可信度极高。描述说:“东经田店、王店、李家渡、严家渡、彭家畈,又十里至浮城畈、团山渡。”“又二十里过宋家坡、三吉堰,港水注之。”这就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具体的坐标与里程依据。其中田店、王店、严家渡(今名严家河)、宋家坡等四个地名在《应城市全图》中还能找到,以严家渡“又十里至浮城畈、团山渡”的指示,按图向东检索,地图上标示的今名是“何家塆”,而由此再向东检索就是“又二十里”的宋家坡,相距里程也与县志描述基本相符。在采访65岁的朱木森先生时,他曾经谈到了团山渡,他说团山渡是个很古的渡口,从河边到坡堤上曾有360级石阶,这是他亲眼所见;石阶在1958年大跃进时被破坏,这是他曾经经历的事情;在团山渡一带曾出土一件珍贵的青铜文物提梁卣,他曾被邀参与文物鉴定,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此件文物证明此地历史久远,为春秋时蒲骚故地。我们在团山村田野调查时,又特意询问过两位村民,他们都说在团山村委会北面不太远的富水河边就是团山渡。而何家塆就在团山正北二三公里处,团山渡应当就在其附近。虽因道路太窄、岡阜路面又凸凹不平,出租车难以通行,司机也不愿前往,我们终未能抵达团山渡,但是对于团山村西临燕子山水库、东临黄毛水库、东北接近李咀水库、有岡阜南北向横亘、蜿蜒迤逦的地形地貌,还是有了身临其境的了解。找到了团山渡,也就等于找到了浮城畈,因为县志描述富水流经时是团山渡与浮城畈并提的,说明二者距离不会太远。又据清李可寀等《雍正应城县志》卷二《乡户志·村市》载:
城西北:巡检司十五里,团山庙二十里,浮城畈二十里(两处“二十里”当是“三十里”之误),车埠头三十里,马家店三十五里。
按这一描述,团山与浮城几乎就在一地,但为何要分别表述呢?又考《光绪应城县志》卷一《舆地志·乡镇》,在其介绍以“团”为县属下级行政区的描述中方知,应城“西向为团十六”,十五“曰团山”;“北向为团十五”,七“曰崎山”。原来团山渡隶属团山团,浮城畈隶属崎山团,虽地理位置相同,但属于不同的“团”管辖,所以要分别表述。再查《光绪应城县志》卷首《县境经纬图》,崎山、团山之间隔有西河(即今大富水),崎山在河之北,团山在河之南。这就是说团山渡与浮城畈隔河相对,隶属崎山团的浮城畈在河北,而隶属团山团的团山渡在河南,故而描述时方位、里程相同。据此,我们可以判定,古团山渡在今何家塆附近,而浮城畈就在古团山渡的对岸,也就是说古蒲骚治所遗址就在古团山渡对面的大富水(亦称西河)之北岸。遗憾的是,一则由于交通工具的限制;二则由于我们在田野调查时还不能完全确定古蒲骚遗址的准确地点,虽近在咫尺,但未能亲临。惋惜之余,我们下决心找时间重访应城市团山村团山古渡与其对岸的浮城畈,以了却一桩心愿。然而,我们更为期待的是,对于古蒲骚的考古发现与考古文物的证明。
三、宋玉到蒲骚的原因与相关问题
考定古蒲骚遗址,对于宋玉及其作品的研究关系重大。我们知道,宋玉的故乡在湖北宜城市,他入仕以后一直在朝中为楚王的文学侍从,当随为秦人所逼迫的楚国朝廷不断迁徙,路线当是由陈郢而至巨阳(今安徽太和北),再由巨阳而至寿郢(今安徽寿县东南)[1]。为什么他曾在一段时间里逗留于蒲骚呢?甚或《光绪应城县志》强调说:“宋玉,楚人,屈原弟子。隽才辩给,善属文,事楚襄王为大夫。尝侨居蒲骚。”这就不禁让人自然地联想到宋玉《小言赋》中提到的“赐以云梦之田”的问题,以及《讽赋》中提到的其“休归”时因路途颇远而“仆饥马瘦”的问题。
《小言赋》说,宋玉“小言”倍得襄王赏识,被“赐以云梦之田”,明确交待了所赐之田的范围在云梦之内。而位于今应城市西北的古蒲骚,恰在古楚云梦田猎区中,这当不是巧合,而是说明宋玉之《大言赋》、《小言赋》确有源于史实的“缘事而发”的创作动因,也说明刘向《列士传》所记亦有其整理文献时所见的史实依据,否则二者不会如此契合。因此可以推断,宋玉所得的襄王赐予的“云梦之田”,就是古之蒲骚,或在蒲骚境内。其实,早在唐代,大诗人李白就认为应城地区有宋玉获赏的云梦之田,他的《安州应城玉女汤作》一诗说:
神女没幽境,汤池流大川。阴阳结炎炭,造化开灵泉。地底烁朱火,沙傍歊素烟。沸珠跃明月,皎镜函空天。气浮兰芳满,色涨桃花然。精览万殊入,潜行七泽连。愈疾功莫尚,变盈道乃全。濯缨气清泚,晞髪弄潺湲。散下楚王国,分浇宋玉田。可以奉巡幸,奈何隔穷偏。独随朝宗水,赴海输微涓。
李白所咏之汤池,今仍水源充沛,被辟为汤池旅游度假区,然而汤池并不在古蒲骚境内,而在其西南约25公里左右的汤池镇。《雍正应城县志》说汤池“南流为汤池港,入五龙河”。五龙河亦南流“入三台湖”。可见,汤池水是不能“分浇宋玉田”的,但诗歌创作可以夸张、想象,超跃时空而为之。据《李白年谱》,李白曾居安陆十年[注]清王履谦等《道光安陆县志》卷三十一《寓贤》引宋薛仲邕《李白年谱》:李白“还息云梦,故相国许圉师家以孙女妻之,遂留安陆者十年。”《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1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对安陆与其周边地区的历史典故与民间传说当非常了解,他在诗中提到应城的宋玉田,自当有他的根据。有了李白诗的佐证,古蒲骚有宋玉田的推断就更加具有可信度了。这就是为什么宋玉曾到古蒲骚的原因所在。
然而须要说明的是,《光绪应城县志》说宋玉“尝侨居蒲骚”,可能有托名贤圣而光耀地方的嫌疑,与事实尚有出入。楚襄王赐宋玉以云梦之田,后世简称为“赐田”,并作为典故被古之文人墨客广泛使用。赐田,就是赏田,《礼记》郑注说:“赏田者,赏赐之田也。”按先秦礼制,为官者的俸禄是以田来兑现的,宋卫湜《礼记集说》言:“三公则受百里之地,六卿则受七十里之地,大夫则受五十里之地,而元士三等,亦视附庸而受田。夫田者,禄之所自出;而居官之禄,即田也。”宋玉仕楚当自有其“禄之所自出”的禄田,《周礼》“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以此言之,宋玉之禄田,当在楚都城近郊。而赐田是襄王的额外赏赐,亦即《礼记集说》所说的“禄外之田也”,这种赏田按理当在远郊,然宋玉所得之赐田,是襄王游“阳云之台”时即兴而赐,即在襄王所游的云梦之地,距离楚都可以用“遥远”形容之。因而宋玉是不会常年定居在他的赐田的,也就是说宋玉不会定居于蒲骚。退一步说,宋玉会不会经常到他在蒲骚的赐田,也是个难以确定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说宋玉“尝侨居蒲骚”,是不准确的;如果说宋玉在楚襄王朝借休假之机,曾去蒲骚打理赐田的相关事宜,或许更接近事实。
宋玉的《讽赋》就谈到了休假的事情,《讽赋》先说“楚襄王时,宋玉休归。唐勒谗之”,接着又说“玉休还”对唐勒所谗“出爱主人之女”事进行了一番辩解。这里说的就是一次休假中发生的事情。古代休假有多种情况,《渊鉴类函》载:(休假)“书记所称曰休归,亦曰休急、休澣、取急、请急,又有长假、并假。”《讽赋》谈的“休归”,当是一次长假。文中交待宋玉走了一天的路,“仆饥马瘦”,途中还需住宿驿站,若是到“近郊”的禄田,大概不会如此,若是去远离都城的蒲骚赐田,就合乎逻辑了。其实,从楚都(宋玉作《讽赋》时的楚都当在陈郢,即今河南淮阳)到蒲骚尚不止一天的路程,以乘马车计,恐怕也要走上五六天。而官员请长假须要国君亲批,汉律有“予告”“赐告”之称,即是因请长假须皇帝批准而得名。“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者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所以说告长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宋玉在楚襄王朝近十年间[2],能获准两三次长假就当算做幸事了,岂能长时间地“侨居”于此!这又是宋玉“尝侨居蒲骚”说不准确的一个证明。
还有一个须要说明的事,也很重要。清罗缃、陈豪等《光绪应城县志》卷十《人物·流寓》说:“(宋玉)尝侨居蒲骚。闵其师屈原忠而被放,作《九辩》以述志。”《县志》如此说,从介绍宋玉其人、其事、其代表作的角度讲,并无错误,而其错误在于交待有失明确,给读《县志》者造成了误解,让人以为宋玉的《九辩》是在古之蒲骚、今之应城所作。《应城名胜》一书中李怡南的《宋玉蒲骚著<九辩>》一文就受到了《县志》的误导。《九辩》是宋玉晚年之作,其作品中有“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驰”、“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无处”可证;宋玉作《九辩》时,由于秦人的东进,他已失去了所有,无官、无家、无田,作品中“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去乡离家兮来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可证;宋玉晚年不可能在蒲骚,《史记·楚世家》载“考烈王元年(公元前262年),纳州于秦以平”,州在今湖北沔阳县东南,属古云梦的东部。这说明由于楚考烈王的进献,秦国已拥有了整个云梦,即楚襄王当年收复的江南十五邑,当然也包括宋玉的蒲骚赐田,业已纳入了秦国的版图。宋玉自然不会在那里甘心做亡国之臣;作《九辩》时的宋玉当在寿郢(今安徽寿县),《汉书·地理志》说:“粤既并吴,后六世为楚所灭。后秦击楚,徙寿春,至于为秦所灭。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按《汉书·地理志》体例,凡在某地区提及某人,其人一定在那一地区生活过。这便是宋玉晚年在寿春的证据。因此说,宋玉作《九辩》是在失职之后的寿郢,而不可能在古之蒲骚、今之应城。与蒲骚相关的宋玉作品,从其传世的作品分析,当为《大言赋》、《小言赋》、《高唐赋》、《神女赋》、《讽赋》五篇。当时宋玉随楚襄王游云梦,作《大言赋》、《小言赋》后,得到了蒲骚的赐田,这是与蒲骚有直接关系者。游赏而后,宋玉追忆楚襄王于云梦祠神女事,作了《高唐赋》、《神女赋》;后又因休归去蒲骚赐田引来唐勒的谗言,为自我辩解,作了《讽赋》;此外,如果《舞赋》是宋玉所作,那么也应是创作于楚襄王游云梦之际。这些是与蒲骚颇有些许关联者。
学术研究是严肃的,且不可为了某种利益驱使而牵强立论,附会演说,从而混淆视听。
参考文献:
[1] 刘 刚.宋玉辞赋考论[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
[2] 朱木森.应城名胜[M].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