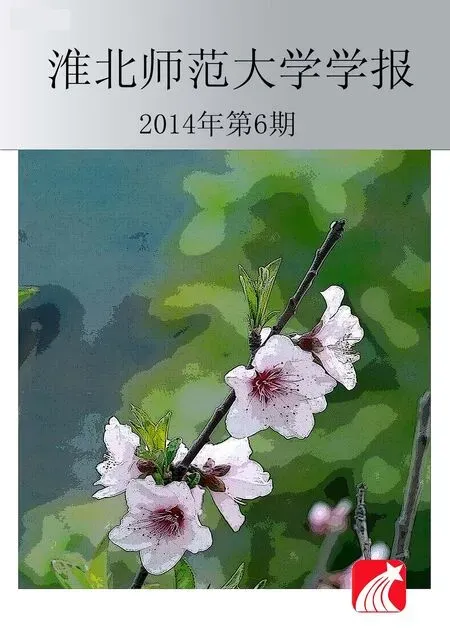从《谢氏诗序》看欧阳修的女性诗学思想
2014-04-08邱瑰华
邱瑰华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一
《谢氏诗序》是欧阳修为友人谢伯初之妹谢希孟的诗集所作的序,载于《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三中。文曰:
天圣七年,予始游京师,得吾友谢景山。景山少以进士中甲科,以善歌诗知名。其后,予于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为景山母夫人之墓铭,言夫人好学通经,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于瓯闽数千里之外,负其艺于大众之中,一贾而售,遂以名知于人者,繄其母之贤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许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为诗百余篇,然后又知景山之母不独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余遗其女也。景山尝学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隐约深厚,守礼而不自放,有古幽闲淑女之风,非特妇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尝从今世贤豪者游,故得闻于当时;而希孟不幸为女子,莫自章显于世。昔卫庄姜、许穆夫人,录于仲尼而列之《国风》。今有杰然巨人能轻重时人而取信后世者,一为希孟重之,其不泯没矣。予固力不足者,复何为哉,复何为哉!希孟嫁进士陈安国,卒时年二十四①宋周必大刻《欧阳文忠公集》、近人张元济主编《四部丛刊》本的《欧阳文忠公集》皆作“卒时年三十四”,见李逸安点校《谢氏诗序》注释[六],《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三,第609页。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年三十三而死”。。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峡州夷陵县令欧阳修序。[1]卷四十三,608
此序作于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八月,即欧阳修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的第二年。此前一年,范仲淹由于直言谏事忤宰相而落职,欧阳修为之鸣不平,亦遭贬。据胡柯编《欧阳修年谱》知,景祐四年(1037)三月,欧阳修“谒告至许昌,娶薛简肃公奎女。是夏,叔父都官卒。九月还夷陵”[1]2599。其间,时任许州法曹的谢伯初将其妹谢希孟所作的百余首诗出示给欧阳修。欧阳修欣赏谢希孟之诗,感叹其声名之不显,遂为之作序。
谢伯初,字景山,晋江(今福建泉州)人。生卒年不详,主要生活于北宋仁宗(1010-1063)时期。天圣二年(1024)进士。天圣七年(1029),始与二十三岁的欧阳修交往。时欧阳修“始游京师”,而他已“以善歌诗知名”“以名知于人”。景祐四年(1037)夏,他把自己所作诗文寄与欧阳修,得到欧阳修的称赏,认为他的诗文能取法古人,雄健俊逸,非时贤所能及。欧阳修《与谢景山书》中云:“昨送马人还,得所示书并《古瓦砚歌》一轴,近著诗文又三轴,不胜欣喜。景山留滞州县,行年四十,独能异其少时隽逸之气,就于法度,根蒂前古,作为文章,一下其笔,遂高于人。乃知驵骏之马奔星覆驾,及节之銮和以驾五辂,而行于大道,则非常马之所及也。”[1]卷六十九,1003此后又三十五年,欧阳修仍熟记此事并能诵其诗,而他却仕途偃蹇,功名不显,不知所终,所作诗文也散佚殆尽。《六一诗话》中云:“闽人有谢伯初者,字景山,当天圣、景祐之间,以诗知名。余谪夷陵时,景山方为许州法曹,以长韵见寄,颇多佳句,……景山诗颇多,如‘自种黄花添野景,旋移高竹听秋声’,‘园林换叶梅初熟,池馆无人燕学飞’之类,皆无愧於唐诸贤。而仕宦不偶,终以困穷而卒。其诗今已不见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诗,逮今三十五年矣,余犹能诵之。盖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诗沦弃亦可惜,因录于此。”[1]卷一百二十八,1955-1956《全宋诗》中仅收其《寄欧阳永叔谪夷陵》《许昌公宇书怀呈欧阳永叔韩子华王介甫》二诗及“园林换叶梅初熟,池馆无人燕学飞。”“多情未老已白发,野思到春如乱云”两联残句[2]卷三,2023。
谢伯初妹谢希孟,进士陈安国(河南温县人)之妻,秉母教,能诗,惜其年不永,二十四卒。著有诗集二卷,见于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女郎谢希孟集》二卷。闽人谢景山之妹,嫁陈安国,年三十三而死。其诗甚可观。欧阳公为之序,言‘有古淑女幽闲之风雅,非特妇人之言也’。”[3]欧阳修所见她的百余首诗及陈振孙所著录的《女郎谢希孟集》二卷,早已散落殆尽,今仅存《樱桃》《咏芍药》诗二首以及《朱槿》《踯躅》《牡丹》《凌霄》《蔷薇》《曼陀罗花》《蝴蝶花》等七首诗的残句[2]卷三,2025。
二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其《六一诗话》及《梅圣俞诗集序》之诗歌批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其女性诗学思想则更直接地体现在《谢氏诗序》中,主要有三:
其一,宣扬母教之功。《谢氏诗序》虽为谢希孟诗集作序,但也表彰了另一位女性——谢家兄妹之母吕氏:“予于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为景山母夫人之墓铭,言夫人好学通经,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于瓯闽数千里之外,负其艺于大众之中,一贾而售,遂以名知于人者,繄其母之贤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许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为诗百余篇,然后又知景山之母不独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余遗其女也。”在欧阳修看来,谢母具有三方面的品德:一是通经,有学识;二是贤淑,有德行;三是课读,有师仪。正是这些品德成就了谢氏兄妹之名。
中国传统社会重视家庭教育,母亲课读与教养子女厥功甚伟。孟母三迁,择邻而居,广为流传,成为佳话。欧阳修本人成名,也得自母教:他四岁丧父,家贫无纸笔可资书写,无书籍可供诵读,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其写字,借书以课读。他在《泷冈阡表》中写道:“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1]卷二十五,393男性除了母教,还有学校、师友可供读书问学,然而,处于从属地位的女子,其才学之获得只能有赖于家庭教育,且更多地是来自于母亲的言传身教。因而,欧阳修宣扬母教之功,意义匪浅。
其二,推赏“隐约深厚”的诗风。所谓“隐约深厚”,是指以《诗经》为代表的传统诗歌美学风貌,其特点是含蓄婉约,温柔敦厚。而要具有这样的诗风,其为人须“守礼而不自放,有古幽闲淑女之风”。所谓“古幽闲淑女”,即以卫庄姜、许穆夫人为代表,她们皆为古代美艳绝伦而又兼具贤淑懿德、风雅多才的女子,所作诗歌“录于仲尼而列之《国风》”。据《毛诗》,“《绿衣》,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4]卷三,80“《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4]卷三,87“《终风》,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也。”[4]卷三,90“《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4]卷四,161卫庄姜、许穆夫人的诗缠绵悱恻,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欧阳修称赏谢希孟的诗言而有礼,言而有法,含蓄婉约,格高调雅,不失温柔敦厚之旨,正与卫庄姜、许穆夫人等“古幽闲淑女”的诗风一致。
其三,哀叹女子诗文“莫自章显于世”。《谢氏诗序》中,欧阳修把谢氏兄妹二人的诗风、诗名进行了对比,指出谢希孟的女子身份是其诗名不能彰显于世的根本原因:“然景山尝从今世贤豪者游,故得闻于当时;而希孟不幸为女子,莫自章显于世。”谢希孟因不幸为女子,只能闭锁闺中,没有社会交往生活,不能“从今世贤豪者游”,虽有诗才,其名便不能自我彰显。既然女性不能自我传播诗名,便只有依凭像孔子那样的“杰然巨人能轻重时人而取信后世者”,为其传播而不至泯没。但如孔子那样的“杰然巨人能轻重时人而取信后世者”,且又不废女子吟咏者,普世间又有几人?欧阳修对谢希孟的慨叹,在整个传统社会都具有普遍意义。
三
诗文集序跋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其内容包罗万象,有重要的历史、文学、地理、宗教及社会文化等价值。为诗文集题写序跋,是中国文人的传统;而为古代女性诗集作序者,欧阳修可称滥觞。欧阳修集大学者、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地位于一身,故而《谢氏诗序》对后世女性的诗文创作及其诗文集序跋的写作也就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和意义。
第一,开启了文人为女性诗文集撰写序跋的风气。中国古代女性诗文作者寥若晨星,至唐宋时稍有增多,然而有诗集传世者,亦仅薛涛、鱼玄机、李清照、朱淑真等数人。随着明清女性文学繁荣,大量女性别集出现,许多女性及其家人或欲以文传人,或欲以人传文,请求亲朋故交为其家族中女性诗文集作序,其中不乏名宦显贵、诗文大家、著名学者。袁枚、王士禄、沈德潜、钱澄之、翁方纲、阮元、洪亮吉、况周颐、俞樾、王闿运、吴汝纶等纷纷为女性诗文集题写序跋,成为风气。袁枚是其中最为用心、为女性诗文集题写序跋最多见者之一。他曾为清代的云间(今属上海市)女诗人廖云锦的《仙霞阁诗草》[5]、昭文(今江苏常熟)女诗人席佩兰的《长真阁集》[6]、汉军旗人女诗人杨琼华的《绿窗吟草》[7]、仁和(今浙江杭州)女诗人张瑶瑛的《绣墨斋偶吟》[8]、钱塘(今浙江杭州)女诗人徐裕馨的《兰韫诗草》[9]、常熟(今属江苏)女诗人屈秉筠的《韫玉楼集》[10]、上元(今江苏南京)女诗人骆绮兰的《听秋轩诗集》[11]、其妹袁棠的《绣余吟草》作序[12]。欧阳修的《谢氏诗序》写作无疑开了风气之先。
第二,对传统女性的诗文创作有着积极的意义。由于传统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受着“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不宜为诗”“内言不出于阃”等观念的束缚,女子多不作诗,偶一为之亦多毁弃,不使传世。至清时,女性诗文创作虽然繁盛,但许多女子的家教仍常以是为训,学人也多秉持此见。章学诚作《妇学》抵斥袁枚对女子为文的赏识和支持,可见一斑。欧阳修歌颂母教,激赏和宣传女子诗作,并为之鸣不平,对后世女子创作自然有着鼓励意义。如清初钱澄之为桐城(今属安徽省安庆市)潘江(字蜀藻)母吴坤元的《松声阁集》题跋曰:“余尝见欧阳公为谢景山女弟希孟诗序,言景山母夫人好学通经,自教其子,不独成其子之名,又以其余遗其女也。然景山母氏诗不传,徒因景山与希孟而知其母氏之决能诗,若太君自有诗传世,不必藉蜀藻传者也。或曰诗非女子所宜,《小雅》云:‘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女德如是而已。’然古所谓教于公宫者三月,其日教以言,言非文耶!卫庄姜、许穆夫人皆德女也,皆能诗,其诗皆为圣人所录,则圣人之不禁女子之为诗也,审矣。”[13]
第三,为后世女性诗文集序跋写作者提供了有力的论语依据。《谢氏诗序》中的论语常常为后世女性诗文集序跋写作者所引用。如明文渊阁大学士费宏为其岳母当涂(今属安徽省马鞍山市)女诗人邹赛贞的《士斋集》作序曰:“昔欧阳子序谢氏希孟之诗,而叹其不幸为女子,莫能彰显于世。由孺人观之,岂不信哉?虽然玉气如虹,剑光射斗,物之奇者,亦岂能閟且匿之?兹集卒赖傅侯以传,而不至于氓没,则又幸矣!”[14]又如清赵棻为江苏武进女诗人刘荫的《梦蟾楼遗稿》作序曰:“其(刘荫)辞之工拙,未知视世之立言者何如,而勤而不怨、婉而多风,得诗人旨焉。昔欧阳文忠公序谢希孟诗,谓其‘隐约深厚,守礼而不自放,有古幽闲淑女之风。’我于夫人诗亦云。”[15]
[1][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2]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陈子展.诗经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5][清]廖云锦.仙霞阁诗草[M]∥张应时,辑.书三味楼丛书.上海图书馆藏清刻本.
[6][清]席佩兰.长真阁集[M].北京图书馆藏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
[7][清]杨琼华.绿窗吟草[M].上海图书馆藏清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
[8][清]汪启淑,辑.撷芳集[M].上海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十九年飞鸿堂刻本.
[9][清]徐裕馨.兰韫诗草[M].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本.
[10][清]屈秉筠.韫玉楼集[M].上海图书馆藏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本.
[11][清]骆绮兰.听秋轩诗集[M].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年(1797)刻本.
[12][清]袁枚.袁枚全集[M].王英志,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20-21.
[13][清]吴坤元.松声阁集[M].安徽图书馆藏民国重刊本.
[14][明]邹赛贞.士斋集[M].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年(1542)刻本.
[15][清]刘荫.梦蟾楼遗稿[M]∥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初编.合肥:黄山书社,2008:821-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