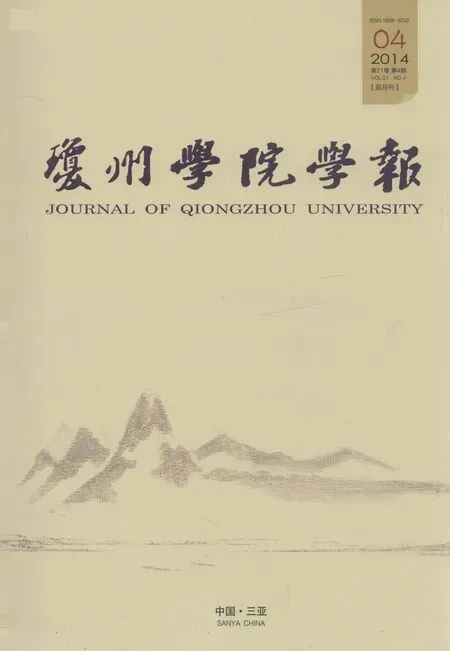嵇康与卢梭自然教育思想之比较
2014-04-07余咏梅
余咏梅
(琼州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海南 三亚572022)
嵇康(公元223 -262年),字叔夜,谯郡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人,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教育思想家。嵇康的教育思想主要是主张越名教、任自然,“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声无哀乐论》)[1]109。“越名教”即反对儒家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在教育上,是反对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中心教材的仁义礼智教育。“任自然”即要脱离“名教”的束缚,让受教育者的个性自然发展。①参见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 -353 页。嵇康的《难自然好学论》标志着中国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诞生,他是中国第一位系统论述自然主义教育的思想家。卢梭(1712 -1778),18 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西方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卢梭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归于自然”。他所理解的自然,在教育上,是指儿童的天性,他的“自然教育”就是教育要顺应儿童天性发展的自然历程。这个理论第一次把儿童放在教育的中心位置,确立了真正的自然教育体系,使自然教育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改变。尽管嵇康和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其生活的时代、地域不同,又各具特点。
一、嵇康、卢梭自然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之比较
魏晋时期,以司马氏为代表的士族大地主阶级与曹魏为代表的庶族中小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斗争激烈。司马氏为纂夺皇位,在教育方面,大力提倡“名教”,以其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嵇康由于与曹魏有姻亲关系,政治立场上与司马政权处于敌对状态;他本人又“生性疏懒”“不涉经学”“又读老庄,重增其放”(《与山巨源绝交书》)[1]272,无荣进之心,爱好自然,向往“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与山巨源绝交书》)[1]275的生活,认为司马氏“刑本惩暴,今以胁贤”(《太师箴》)[1]197,如此利用礼教,是亵渎了礼教,但又无计可施,故而反对“名教”,斥之为“芜秽”“臭腐”,认为“名教”破坏和压抑了人性的自然发展。他赞美古代简易无为的原始社会“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声无哀乐论》)[1]109,没有人为的教育,一切顺其自然,人的品质是最完美的。针对儒家“名教”,他提出“任自然”的教育主张。
18 世纪的法国,封建制度日益腐朽,资产阶级、广大人民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天主教会和封建统治者相互配合,实行严酷的思想钳制,极力扼杀进步的思想和科学文化。处于社会底层的卢梭,亲身感受到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屈辱,看到人民遭受的痛苦和不幸,认为腐败的社会使人堕落,并对儿童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的手里,就全变坏”[2]1。卢梭的许多著作都在攻击法国专制的反动政府和残害人们思想的教会。在教育上主要是针对天主教会控制的腐朽的封建经院主义教育戕害人性、违反自然而提出了反封建的一切顺应自然,“归于自然”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
嵇康和卢梭都是在反对当时政府和占统治地位的反人性思想的背景下,在批判传统教育漠视儿童身心发展的基础上阐述他们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二、嵇康、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内容及方法
(一)理论基础
嵇康与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依据的理论基础大相径庭。嵇康以“元气自然论”为理论基础,主要继承了老庄的自然无为思想,但又摆脱了老庄的权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1]134,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元气自然变化的结果;“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太师箴》)[1]195,太素分化成阴阳、天地,进而育化出万物和人类。他认为这种自然的东西是最美好的,体现在教育上,注重自然任性,主张教育要从儿童的自然本性出发,让其个性自由发展。
在认识论上,卢梭是一位感觉论者,他把感觉经验作为认识的基础和知识的来源,“进入人类心灵的知识以感觉为门户,所以人类最初的理性,是由感觉经验而得的理性”[3]。人的理性通过观念获得,而观念依靠感觉而生,所以感觉经验对人的理性的发展十分重要,感觉作为人的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的自然本性,所以要发展儿童天性,应从培养儿童的感觉经验着手。
嵇康和卢梭教育理论依据的哲学基础有所不相同,一个以“元气自然论”为基础,一个注重感觉经验,但他们在教育上的落脚点都是要从儿童的自然本性出发,让其天性得到自由发展。
(二)教育目的
教育是培养人的,古今中外,各阶级及其教育家在培养什么人才方面都有自己的教育目的。中国先秦各家学派皆有自己的理想人格,但其内涵不甚相同。儒家的教育目的就是把士培养成理想人才—能够博施于民而济众、修已以安百姓的“圣人”。嵇康作为魏晋时期一个著名的玄学家,对儒家“名教”教育培养出来的“士”进行了剖析,认为“士”“积学明经”只是为了追逐自己的私利,是一些“有矜忤之害”“矫饰之言”,以及“匿情矜吝”者,这种人“故能成其私之体,而丧其自然之质”(《释私论》)[1]126,实在是一些至恶的小人,而非真正的“圣人”,应该“兼而弃之”,统统抛弃。进而他提出自己的教育目的,要求培养“至人”。所谓“至人”就是通过“任自然”的教育培养起来的理想人物,是“文明在中,见素表璞,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于古今,涤情荡欲”(《卜疑》)[1]39的人,是完全超脱了现实中“声色”“名利”的桎梏,身心自然和谐发展的人。
卢梭在《爱弥尔》中明确提出应以培养“自然人”为教育目的。卢梭的“自然人”,并非自然状态中的原始人,而是一个摆脱了封建社会约束和封建文化腐蚀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新型人物,是社会状态中的自然人,其实也就是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具有公民品格的人。爱弥尔就是这种“自然人”的化身,“长得体态均匀,身心两健,……他富有感情,富有理智,心地十分的仁慈和善良,他有很好的品德,有很好的审美能力,即爱美又乐于为善,他具有许多有用的本领……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去,都不愁没有面包”。[2]609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嵇康认为现实中儒家“名教”培养的“士”与儒家理想中的“圣人”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提出要培养“至人”这种超凡脱俗内心自由和谐的人。卢梭要培养的“自然人”是针对欧洲封建教育培养王孙公子和达官贵人的教育目的提出来的,他认为本来依照社会的自然进程,人类可以日臻完善,逐步达到幸福境界,但封建社会摧残了人的主权,人的天赋的自由被践踏,使人得不到自由和谐的发展。与嵇康的“至人”一样,“自然人”也是摆脱了传统教育的束缚,身心和谐发展的人。
(三)教育作用
许多儒家学者从维护“名教”立场出发,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爱好儒家“名教”是符合人类本性的。嵇康则认为,所谓“仁义名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人为创造出来的,“及至人不存,大道凌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其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难自然好学论》)[1]143。主张采取“任自然”的态度,即顺各人的个性自然发展,不必进行人为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教育。他把一切文化教育都看作是违反自然的东西,否定教育的作用。但作进一步分析发现,他实际上没有全部否定教育的作用,从《家诫》一文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人无志,非人也”(《家戒》)[1]304,他把立志教育摆在重要位置。其次他重视教育子弟培养仁义礼让等道德品质;他还主张教育子弟要敬远长吏,不受人请托,不要打听别人的私事。这些都说明他反对的只是儒家“名教”对人的身心控制和约束,并没有全部否定教育的作用,他认为人是需要教育的,在教育中要适当诱导和控制,不能任其自流。
卢梭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善良的,那些违背儿童天性的教育,“扼杀了他的天性”,使他们成为“没有味、没有香气的早熟的果子”。另一方面,他认为教育导致人与人的差别,在塑造人的品性、改变恶劣环境对人的影响方面起着决定的作用,“我们在出生时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时需要的东西,全都是教育赐给我们”[2]3。由此所见,卢梭提倡的自然教育,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而是主张教育要顺应儿童的天性,使其自然发展。
嵇康和卢梭对教育在人身上所起的作用方面的认识大致相同,都没有否定教育在培养人中的积极作用,反对的只是那些传统的违反自然、违背儿童天性的教育。
(四)教育内容
嵇康和卢梭都质疑当时社会的教育内容,提出自己的主张。魏晋时期,社会动乱,阶级矛盾尖锐,儒家提倡遵守名分和立德扬名的道德哲学受到全面挑战,无法维持其“独尊”地位。嵇康认为,儒学“立六经以为准,仰仁义以为主,以规矩为宣冕,以讲诲为哺乳,由其涂则通,乖其路则滞”,并以“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难自然好学论》)[1]143的看法是错误的,儒家“名教”的仁义礼智,并非人性固有,而是戕贼人性的东西。他从人性的观点出发,提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观。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其然”(《难自然好学论》)[1]143。主张从欲而反对抑引,以为这样才能“全性”“养真”。他把“自然养生论”作为“任自然”的教育内容,对于如何保养身体提出顺应自然的主张,提出要“戒智”与“戒欲”,认为纵智嗜欲绝“非道之正”,而是道之“偏”,会使身体受到摧残,不能保持健康。要做到“戒智”“戒欲”,根本在于知足。知足者,即使“被褐啜菽”,也会感到自然而自得,“不足者虽养以天下,委以万物,犹未惬然”(《答难养生论》)[1]59。
18 世纪的欧洲,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在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教学内容空洞而脱离实际,只注重学习神学课程和人文课程,总是把小孩子当大人看待,要求学习一些不切实际的书本知识,不利于儿童的全面发展,不能培养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自然人”。卢梭认为人的精力有限,只能在恰当的时候学习恰当的内容。他根据人的自然发展进程及各个时期生理、心理发展的特点,规定各个阶段的教育内容。出生到二岁,多给孩子们以真正的自由,注重体育,促进身体的健康发展;二岁到十二岁,特别注重感官教育,使其获得丰富的感觉经验;十二岁到十五岁期间,应该学习有用的知识以及进行劳动教育;十五岁到二十岁,施之以道德教育,培养善良的爱人的感情和思想。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到二十岁时就成长为一个完美的、具有公民品格的全面发展的自然人。
(五)教育原则方法
从“任自然”的教育原则方法方面来说,嵇康主张“无措”,他说“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释私论》)[1]120。“无措乎是非”,即泯灭是非之义,“无措乎是非”是达到“行不违乎道”的方法或工夫。所以,“无措”是体道及实现至人理想的工夫,“它要求对学生进行教育时,不要人为地分辨是非,应因势利导,顺乎自然,让学生个性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自由地发展。”[4]嵇康的“无措”之论,直接来自于庄子“不谴是非”说,不过庄子的“不谴是非”说主要在追求至人的境界,嵇康的无措论,则是在瓦解名教社会所依据的是非标准。
卢梭在对传统教育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培养自然人的一套教育原则和方法,这些方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遵循“自然”。他的自然教育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学必须符合儿童身心自然发展水平,根据儿童的年龄采取不同的方法。因为卢梭认为传统的教育,只是主观地设想儿童的未来,不考虑儿童的现在,不考虑儿童现在的生活、儿童的能力、他的天性,要儿童学习一些他们不能理解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他们可能一生都用不上。为纠正时弊,卢梭认为教育要顺儿童之自然本性,按儿童的年龄、兴趣、需要、能力之特点,引导儿童在实际活动中合乎自然地获得知识,发展个性,否则就会培养出一些对社会无用的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①参见[法]卢梭《爱弥儿—论教育》(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1 页。
第二,在活动中学习。卢梭主张让儿童在生活中、从各种活动中进行学习,通过观察获得直接经验,主动地学习。卢梭认为感觉经验是理性发展的凭借,教学给儿童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所以要以行动去教育青年,让他们在经验中学习那些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再者道德观念也是在活动中形成的,要通过观察去了解社会,通过行为的练习来培养善良的道德观念。
第三,给儿童充分的自由,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实现儿童个性的充分发展。遵循自然的教育必然是自由的教育,卢梭反对压抑儿童天性、束缚儿童自由,他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自由是人的首要的自然权利,自然的教育必须保护儿童善良的天性,一切教育措施都不应超出儿童的需要和能力,要先让他的性格的种子自由自在地表现出来,在详细了解儿童的基础上,对他的个性发展给予正确指导,使他合乎自然的发展。
嵇康和卢梭的教育原则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反对压抑儿童天性,认为教育应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规律,循序渐进,教育措施不应超出儿童的能力和需要,而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使其个性得到充分发展。
三、嵇康、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对当代的启发意义
嵇康和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强调要尊重儿童的自然和自由,非常重视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进程,认为教育的一切措施都应依据儿童身心发展特点,让其个性得到自然发展,这种观点不仅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仍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正确认识全面发展观
人的全面发展始终是教育追求的理想,全面发展包括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的发展。自然教育就是要使人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然而我们传统的教育—应试教育却严重违反了人的成长规律,一味地向学生灌输知识,通过各种考试增加一些知识和技能,把学生培养成统一规格的教育产品,置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于不顾,严重破坏了人的内在自然。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必须改变满堂灌的应试教育方式,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儿童的独立个性、完善人格,使其成为新时代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
(二)承认学生的主体地位
把学生放在主体参与学习过程的本位上。自然教育的主体思想是要顺应人的天性发展,把人看成是自然主体,强调学生的自主发展。而目前仍有人认为儿童的天性是破坏性的,对儿童要严加管教,主张采取强制管理、灌输矫正的方式来教育儿童,儿童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按照父母和老师的规定的道路走下去,这种教育方式使学生的个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损伤。在教学中,必须承认学生学习主体的地位,充分发挥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其主动参与学习过程。
(三)教育教学活动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
嵇康和卢梭都认为对学生进行教育时,应因势利导,让学生个性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自由地发展,把儿童当成儿童来对待。而我们现在的社会却总是把儿童当作成人,不管他的接受能力就强行灌输一些成年人才应该知道的东西,这样不仅无助于孩子的发育成长,反而会扭曲孩子的心灵,造成其身心畸形发展。儿童的身心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量变到质变的连续不断地发展过程,并且不同的年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不同的个性存在差异。因此,我们的教育,必须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注意到学生身心发展的顺序性、阶段性和个别差异性,按儿童的接受能力、自然进程实施教育,促进他们身心发展,不断提高他们身心发展水平。
[1]夏明钊.嵇康集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法]卢梭.爱弥尔[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3]滕大春.卢梭教育思想述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96.
[4]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二[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