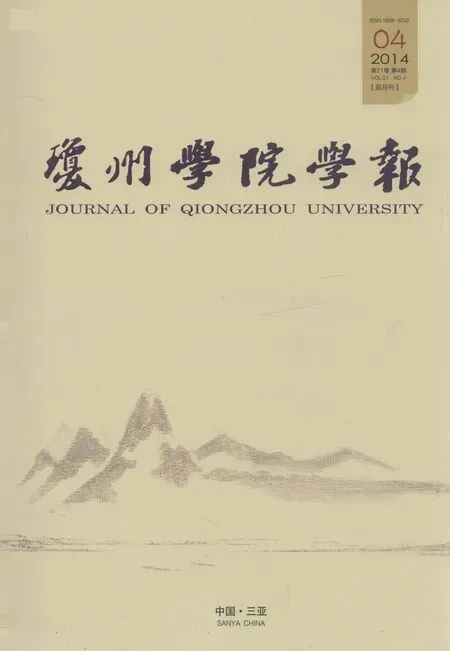一种哲学智慧的诠释:如何通向本体的澄明之境
2014-04-07任祥伟
任祥伟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730070)
《周易略例·明彖》中,魏晋玄学家王弼曾提出“物无妄然,必由其理”[1]的说法。这也就是说,事物的存在是以其内在的原因为支撑的,否则世界上绝不可能存在无缘无故的事物。诚然,有些事物可以去设想它的成立和存在,但是它自身却根本不能存在。并非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有些事物根本就没有其存在的理由。例如,“永动机”不符合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方形的圆”不符合几何的逻辑规则,因此二者都缺乏存在的内在理由,从而无法获得自身的存在。
作为“在者”,每一个可能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相应理由,那么,把这个问题上升到超验性的高度,追问整个普遍性的世界万物何以存在?这种“求本溯源”式的问题所探求的乃是“在”本身,而非“在者”。这种始源性的问题目的就是追问“在者”之“在”,问题也就从“在者”过渡到了“在”本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本体论问题。怎么样去领会本体的意蕴,从而走向于本体的澄明之境?这无疑需要一种哲学智慧的诠释,而这种诠释只有在对“在”和“在者”的划界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剖析的基础之上才是可能的。
一、“在”与“在者”的划界与发展
从思想史上来看,“在”(being)与“在者”(beings)的区别和分野,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划分问题。在中国哲学中,《老子》中就提出“道”的划界问题,亦即“道可道,非常道”。在这里,否定词“非”就把“道”划分为可言说之“道”和不可言说之“道”。《易传》中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提法也是此等划界的表现,如此等等。在西方哲学中,表现出“在”与“在者”划界问题的则有巴门尼德的存在(being)说、亚里士多德提出“作为存在的存在”。直到现代的海德格尔认为“在”与“在者”的划界,乃是一种“本体论的区分”(ontological difference)等。这些都是论述的“在”与“在者”的划界问题。
亚里士多德把追问第一原因的学问(亦即形而上学)称之为“第一哲学”。他指出:“存在着一种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就自身而言依存于它们的东西的科学。”[2]84而且“我们应当把握的是作为存在之最初原因。”[2]84亚氏在这里提到了“作为存在的存在”,包含两个存在。其中的第一个存在,所指的是具体的存在物,亦即“在者”,而第二个“存在”则是指一般的普遍的存在,亦即存在自身。故亚氏“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提出,实际上就标志着“在者”与“在”的自觉划界。
随后实体概念的引入更是把追问“在者”之“在”的问题推向了研究的高潮和巅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原始意义上存在不是某物,而是单纯的存在,只能是实体”[2]153。可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体就成了“作为存在的存在”的代名词。后来的斯宾诺莎又对实体范畴进行了新的拓展。他认为“宇宙间只有一个实体,而且这个实体是绝对无限的”[3]14而且“实体”又是自因的,“自因(causa Sui),我理解为这样的东西,它的本质(essentia)即包含存在(existentia),或者它的本性只能设想为存在着。”[3]3黑格尔在谈到斯宾诺莎的自因概念时,说道:“自因这个概念就是真正的无限性”。[4]108
对于斯宾诺莎实体范畴的绝对性和无限性,黑格尔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却不满意斯宾诺莎实体范畴缺乏展开性和能动性。对于斯宾诺莎的实体,黑格尔批评道:“这是一种死板的、没有运动的看法。”[4]103在黑格尔看来,“实体”应当是具有能动性的,只有展开自我的辩证运动方能真正完成自身。所以黑格尔提出了赋有能动性的“主体”概念,他认为:“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唯其如此,它是单一的东西的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则又是这种漠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5]11由此可见,黑格尔正是借助于“主体”这个概念本身带有的能动性,即自我否定、自我展开的特性来进一步诠释实体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体和主体在意义上是等价的,即“实体既是主体”。这里的“主体”和“实体”一样都是一个绝对的本体论概念,都是为了表述那种“在者”之“在”的。此后,黑格尔又引入了真理的概念。他指出:“真理是全体。但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到完满的那种本质。”[5]12可见,真理又是一个被黑格尔用来诠释实体的范畴,真理的本真内涵就是对实体的彻底地展开和绝对地完成。以上也就是黑格尔对“在者”之“在”的一个探究方式和过程。
从巴门尼德的“存在”到亚里士多德的“作为存在的存在”,通过对“在者”与“在”的划界,哲学终于确立了自己的专门领域,即那种追问“在者”之“在”的形而上学领域。而且“在者”与“在”划界之后,斯宾诺莎、黑格尔等通过对实体的研究进一步把“在者”之“在”的问题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哲学”与“科学”的分野
试着追问“哲学”和“科学”分野的根据,追其源头正是得益于“在”与“在者”的划界。从视角和语境上来说,“在者”是科学的研究对象,而哲学研究所要把握的则是“在”本身。由于“在”与“在者”的这一划分,使对“在”的把握和研究脱离出来,呈现在人们的思考领域内,这样才凸显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视域,从而使哲学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
人总是有着一种去解释或诠释事物的文化本能和偏好。这必然为科学的诞生埋下了伏笔。人类作为拥有发达大脑和聪明智慧的高级动物,每每遇到各色各样的事物时,总是有着一种去解释和阐明的冲动,以求给出事物存在之理由为目的;如若不然,感到困惑的人们就像原始森林中的旅行者迷劳动路那样惶惶不可终日,或者像处在太空中的人因失重而无所依靠一般。对于“在者”,科学作为一种恰当的把握方式是十分必要的。科学的作用就在于对一切可能的事物(即“在者”)进行研究和剖析,从而使尽可能多的事物为人类所用。
海德格尔指出:“在者本身显现为因果之网中的现实的东西。”[6]92所以,归根结底处在因果联系中的“在者”(即现实的事物)必然地带有相对性和有限性。那么,建立在“在者”基础上的科学也自然是如此了。对于“在者”的把握和捕捉,只有在特定的因果关系的坐标中才是可能的。罗素指出:“科学家应当寻求因果律这条格言,如同采集蘑菇的人应当寻找蘑菇这种格言一样明白清楚。”[7]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十分推崇因果关系,他认为一个新的因果联系的发现比获得波斯国的王位还要高兴。由于德谟克利特痴迷于“经验的观察”,以致“不满足于哲学,便投入实证知识的怀抱”[8]。以历史上看,西方那悠久的科学主义传统正是“对于实证知识的偏爱”这一取向所生成和造就的。可见,对“在者”的“把握”正是体现为以因果诠释模式为特征的科学。这种科学主义传统也正是造成海德格尔所谓“在的遗忘”的根本原因。对于科学的局限性,雅斯贝尔斯指出:“科学的事实知识并不是存在知识。科学知识是特殊的,是关涉一定对象而不关涉存在本身的。”[6]158对于科学来说,只有“有”“在者”才能够当作对象被设置。科学知识只能把握的是“有”而非“无”,这也正是科学的特殊性之所在。最后,雅斯贝尔斯说道:“任何被认识了的存在,都不是存在本身。”[6]163海德格尔也指出:“在一切科学中,当我们探索其最根本的旨趣的时候,我们是和在者本身打交道。”[9]343海德格尔认为,科学使人们仅仅同“在者”打交道,这是正确的看法。在海德格尔看来,科学只能捕捉到“在者”,是永远也无法捉到“在”的,因为“在”本身就如“无”一样,而“‘无’既不是一个对象,也根本不是一个在者”[9]353。
与科学不同,哲学把握的是“在”本身,换言之,可以把追问“在者”之“在”的学问称之为哲学。虽然在形式上,哲学对于“在”的把握带有解释的性质;但是在问题域上,已经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转变为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科学观念是经验性质的,“哲学绝不能以科学观念的尺度来衡量”[9]359,只有在形而上学的超验层面上把握哲学才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形而上学就是超出在者之上的追问,以求返回来对这样的在者整体获得理解”[9]356。如果抛开形而上学,而使哲学投向科学的怀抱,那么哲学也就不是哲学了。雅斯贝尔斯也说:“对存在的阐明则指向哲学的世界方向,指向形而上学。”[10]27“在”本身不可能是构成知识论所把握的东西,这是因为“在”本身拥有着绝对性和无限性,从而是无法被对象化的。所以雅斯贝尔斯说,“任何被认识为对象的存在物都不是存在”[10]26。对此,海德格尔也指出“‘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11]5。
三、只有“人”才能发出对“在”的“追问”
作为大自然和万物的一员,“人”注定是一种“在者”,而且是最为特殊的“在者”。海德格尔曾提出著名的“此在”的说法。即人就是“此在”(即Dasein,也译为“亲在”)。为何人是最为特殊的“在者”呢?那就在于:在整个宇宙万物之中,只有人才能追问“在者”之“在”。海德格尔说:“对‘在’的领悟本身就是‘亲在’的‘在’的规定。这个‘亲在’在‘在者状态’上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乃本体论地‘在’。”[9]361因此,对“在”的把握只能采取本体论式的把握方式。在海氏眼里,“此在”之“在”本身乃是“在者”之“在”的敞开和彰显,或者毋宁说“此在”以其在着的方式昭示和召唤着“在”,从而使“在者”之“在”得以澄明。
海德格尔还认为,对人的存在来说,哲学构成了人的宿命,或者说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动物。这是因为“只消我们存在,我们就总是已经处于形而上学中的”[9]359。只要“人”还存在,只要人还以“人”的方式存在,那么人就始终处于形而上学之中。可见,哲学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须臾不可离的。值得注意的是:以科学探究的方式是无法诠释“在”的,“在”只有通过“人”的“此在”的方式进行彰显。
此外,中国的先哲也认为唯有人才能发出对“在”的追问,而且只有通过“我”(吾心、灵明等)才能澄明和昭显“在者”之“在”。诚如冯契先生就言:“孟子认为,一个人能够‘尽心’‘思诚’,就可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2]庄子在《齐物论》中也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3]84。显然孟子和庄子在这里已经提出了只有“人”才能追问“在者”之“在”的问题。在以往,我们把此类说法解读为:在实有层面上,“我”决定了世界万物的存在。因而这类说法被定性为主观唯心主义,显然这是错误的解读。实际上这种说法只是想表明:万物存在的理由只能由“我”(即作为“此在”的“人”)才能给出,或者说只有“我”才能追问万物存在的理由。陆九渊曾指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宇宙”[14],没有哪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会认为陆九渊指的是整个宇宙都装在了“我”的“心脏”里了。其实,陆九渊之意乃是:唯有通过“吾心”,方可去彰显和澄明宇宙万物赖以存在的内在理由。这里所谓的“心不是一块血肉”[15]107,陆九渊进一步说:“万物森然与方寸之中,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13]292在《传习录》中,王阳明则借“灵明”比喻“吾心”,所谓“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15]95。而且“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15]110。这就更加印证了“吾心”对于本体的彰显和澄明,因此只有从作为“此在”的人出发才是可能的。由此可见,在王阳明那里,只有从灵明(即吾心)出发,只有从拥有灵明的人出发,才可以去体会宇宙万物的“在”。这也就说明了只有“人”才能发出对“在”的“追问”。显然,中国先哲同海德格尔在思维层面上是有着内在的亲近性的。
四、“不能设问”与“必须设问”之间的矛盾
海德格尔把“在”比作“无”来阐释,他说:“我们自始就把‘无’定位某种如此如此‘在着’的东西——作为一个在者。但‘无’却恰恰与在者截然不同。追问‘无’——问‘无’是什么以及如何是——就把所问的东西变成了它的反面。”[9]345这就昭显出了本体论的一个始源性的悖论:本体论试图消解掉的规定恰恰隐含在本体论的追问及其讨论方式赖以确立的前提之中。其实,本体论的确立本身就意味着确立一种认知姿态,因为本体论作为一种探究方式,它必须设问、追问。然而,对“在”本身的领悟必须以逃离知识论的樊篱为其前提,因为“在”本身是本体论层面上的。可见,对“在”的追问,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不能设问与必须设问之间的矛盾”。
正是因为我们像追问“在者”那样去追问“在”,“在”本身从而就被遮蔽了,“在”也就沦为“在者”了。究竟为什么在者在?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写道,意义就在于“此一追问是只消在者存在着就要为在者寻求根据。寻求根据,就是说:奠基,追溯到根据处”[16]。但是,每当我们对“在者”之“在”进行提问的时候,不论这个问题是关于什么方面的(比如性质、用途亦或根据),我们就已经把“在”当成一个“在者”来设定和看待了,这也就造成了海氏所谓的”在的遗忘”了,从而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知识论提问方式的窠臼,也就无法走向本体的澄明之境了。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对“在的遗忘”的批评,主要针对的就是拉图以来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家用追问“在者”的方式去追问“在”本身,而并不是针对古希腊哲学家对“在”与“在者”的划界的。前一种情况之所以受海德格尔的批判,是由于这种以知识论的方式和态度去设置“在”,从而遮蔽了“在”对“在者”所固有的超越意义,使之成为一个对象性的规定,进而沦为“在者”。“在”是绝对的、不可定义的。不论设问“什么是本体和本原?”亦或者“什么是存在和绝对?”,这种把握方式都走向了同样的误区。一旦我们提问“在”为何物时,就已经提前预设了“在”是可定义的了,就已经产生内在的悖论了。所以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存在是什么,换言之,实体是什么,不论在古老的过去、现在、以至永远的将来,都是个不断追寻总得不到答案的问题。”[2]153对于“存在”亦或者是“实体”的追问总得不到答案,主要就是由于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和悖论。其一,“存在”与时间性无缘了,从而变成一完成之物。对此,海德格尔指出,“时间”乃是“使对‘存在’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悟得以可能的境域”[11]1。其二,“存在”沦为了人的一身外之物且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因此,生存论问题就成为知识论问题,“存在”就变成了知识的对象了,这也正是导致海德格尔所谓的“在的遗忘”之根本原因。
既然采用追问“在者”的方式来追问“在”本身会导致内在的悖论和矛盾,那么“在”该如何才能得到昭示和澄明呢?哲学的使命就在于使“在者”向“在”本身的提升和过度得以澄明。而哲学的这一使命也算是对人的“拯救”。因为人一出生就不得不面对“在者”。这种被抛入了一种经验的存在之中的情形使得“人当下总是已经而且只执着于在者”[6]103。只是通过哲学的途径才能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完成对人的“拯救”。自觉地澄清并解除哲学追问在者之在的提问方式上的遮蔽之处乃是通往哲学之路的首要前提。也许中国的先哲给出了很好的启示。老子曾所谓“上善若水”“复归于婴儿”等提法在语言层面上的高明之处在于:使语言由指称义转向象征义,从而避免了那种指称性的陈述,而代之以象征性和隐喻性的暗示,由此决定了文本就由理解的对象变成了领悟的契机。这种转换使人们有可能通过语言及其所指代的相对性和有限性,来领悟和洞见本体的绝对性和无限性,从而超越知识论提问方式的羁绊。
五、马克思借助于“实践”来通达和澄明本体之境
常言所谓“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在哲学层面相对于“说”,“行”往往被赋予了更大的本质和信任,一个人只有通过“行”才能成就自己本真存在的过程和凸显人的本真性。而这个意义上的“行”,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实践。如果说海德格尔是运用“回到事情本身”的现象学方法来体认和显现“本体”或者“存在”的话,那么马克思则是借助于作为本体范畴的实践来澄明和通达本体之境的。马克思并不是借助于象征义或者比喻义的语言修辞来体认本体,而是运用现实的对象性的物质生产活动(亦即实践)来生成和显现不可言说的“本体”或“存在”。而这里的实践俨然已经是一个本体的范畴了。
那么实践是何以成为一个本体范畴的呢?这是由于马克思的实践特性所决定的。马克思的实践本身具有原初性和生成性的本体论特征。首先,在其逻辑顺序的建构上,实践是最原始的范畴。实践在逻辑顺序上先于主—客二元分裂,体现着原初性、始源性的特点。这是因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在理解并阐释任何对象时,始终保持着实践维度的优先性,即把实践作为观察、思索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思维现象的基础和出发点。”[17]其次,实践总是生成性的。最为典型的就是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论述:“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8]马克思认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19]。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一切事物和历史都是实践所塑造和生成的。而这种生成性实践的作用就在于“人无法选择人本身所面临的既定的客观前提,但是正是借助于实践的生成性特质,人所面对的既定前提在实践的生成中被消解和重构了”[20]19,因此生成性的实践就变成了创造性的实践。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实践的生成性是无限的,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无限的生成。正是由于实践范畴本身的“原初性”和“生成性”,才铸就了实践作为本体的可能性和合法性,而这样一个实践范畴在马克思那里是在人的存在的意义上谈论的,表现了马克思在人学立场上的生存论视域。
实践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最始源性、本真性的基础。这里的实践不仅仅是人的一种属性,而是包含着人及其存在本身,乃至历史的全部可能性和秘密。实践在这里包含着一切可能的规定性,但它是潜在意义上的、是预设性的,是有待完成的整体、“大全”和“一”。因而,马克思对问题的态度往往诉诸于历史的无限生成和发展之中,对于“存在”或“本体”的体认问题也是如此。他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1]66。恩格斯也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21]650而历史又是被实践所生成和造就的,一切“在”与“在者”的问题,尤其是对“在”的澄明问题都融入到了实践和历史的无限生成之中,马克思正是通过这样的“实践”范畴去通达和澄明了本体之境,而这也有效的避免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在的遗忘”。可见,马克思哲学也正是基于人类实践本性和人类思维本性的本体论追求。
[1][三国魏]王弼.周易略例[M]//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9:591.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Ⅶ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3][荷]斯宾诺莎.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 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5][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6]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存在主义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7][英]罗素.宗教与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6.
[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01
[9]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著作选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0][德]雅斯贝尔斯.论真理[J].哲学译丛,1984(4):25 -31.
[1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87.
[12]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80 -181.
[13]丁祯彦,臧宏.中国哲学史教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4][宋]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273.
[15][明]王守仁.阳明传习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6][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
[17]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5 -366.
[18][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2.
[19][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4.
[20]任祥伟.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多重维度分析[J].宜春学院学报,2014(5):16 -19.
[2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