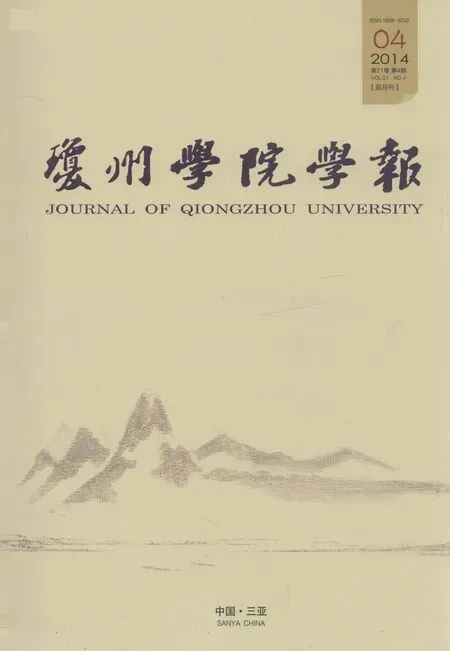论“古诗”类五言诗及乐府诗在传播中的变异
2014-04-07王立
王 立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亚洲研究系,加拿大 温哥华V6T1Z2)
宇文所安的《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和木斋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是两本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的五言诗研究专著。笔者以为,不仅他们详细的论证、严密的逻辑推理、所得出的突破性的结论值得重视,他们从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多种可能性入手的研究角度亦需被关注。本文拟在二位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文本传播的角度入手,对《古诗十九首》及相类古诗作品略作探讨。
一、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多种可能性
宇文所安在其书之序言中写到:“‘西方’学者和东亚学者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也即将文本当作其创作时刻的本来状态对待。但在理解早期诗歌中没有比这个更加误导的观念了:早期诗歌是一个存在于复制状态中并通过复制而为我们所接受的诗歌系统。知道和传播诗歌的人、表演诗歌的乐师以及后代的抄写者和文学选集的编者都会对他们进行复制。而在复制的时候,所有这些人都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动文本。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改动的痕迹常常十分明显,诗歌的扩张和缩短都有较大的自由度。”[1]21-22“诗歌的流传过程中,文本、最终决定文类体裁和次文类体裁归属的标题、作者署名等都有可能有变化。”[1]8而较之文本在传播中被更改,作者署名在流传中的变动更容易产生混乱,很多学者已指出了这个问题。如《玉台新咏》中所录早期五言诗歌的署名:《团扇诗》被署名班婕妤、秦嘉与徐淑的赠答诗之署名、《同声歌》被署名张衡、《饮马长城窟行》被署名蔡邕、《羽林郎》被署名辛延年、《董娇娆》被署名宋子侯等,都被宇文所安等人所否定。①宇文所安推测“秦嘉的诗很有可能是专门为该集而作的”,而木斋在其专著《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中已证实此确系伪造。对于这些诗歌的署名问题,其他学者也有相类见解,逯钦立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编录《团扇诗》时即否定了署名班婕妤②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 版。;木斋在其《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一书中利用专章论证所谓秦嘉和徐淑的赠答诗为后人托名之作①见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而叶嘉莹在《谈古诗十九首时代问题》中对徐陵编辑《玉台新咏》的态度和书中所录诗歌署名可信度的评判是:“其轻率与不负责之态度已可想见,因此其提名枚乘之说(指《古诗十九首》中的八首,笔者按)也就使人觉得不可采信了。”[3]99徐陵在编纂《玉台新咏》时混入伪作,篡改作者署名便是诗歌流传过程中受到人为影响而发生重大变化的典型例证。
正是意识到诗歌传播中的多种被改变的可能性,木斋在《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中大量征引史料,指出曹叡对曹植作品的删改和剔除,产生了《古诗十九首》及一些同类“无名古诗”:“曹植在参加元会的当年死去,曹叡随后在景初二年下诏对曹植文集进行重新撰录,曹植和甄后之间有关联的主要诗作(被删除)以及连带删除曹植其他的一些优秀的五言诗作,并将这些被重新撰录、整理之后的文集‘副藏内外’,以便作权威版本。而根据《晋书》记载,曹志分明说自己家中有曹植生前‘手所作目录’,说明朝廷整理的曹植全集与家藏的‘手所作目录’是不同的版本。而朝廷之所以将这些整理过的版本不仅仅收藏于宫中,还要使之流行于‘外’,正是希望这些删除的诗作永远消失。为了达到使这些涉及植、甄隐情的诗作永远与其本事无关、与曹氏家族无关,将这些诗作分别派发到枚乘、傅毅、班婕妤等两汉诗人名下,而曹植、曹彪兄弟的唱和之作则被依附到所谓的苏李诗。……那些被删除的曹植(可能还有曹彪、甄后)之作只能靠口耳相传流传下来。……因此,在西晋陆机的时代,从曹植文集中剔除出来的这些诗作就已经失去了作者署名。”[2]264-265
其实传播中的种种变更常见于古代的各种文字作品。如钟嵘的《诗品》中与“古诗”作者署名相关的一句“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吕德申在《钟嵘诗品校译》标明:“吟窗本、格致本无‘旧’字。‘曹王’,冯舒《诗纪匡谬》、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三)引作‘陈王’。”[4]63现代印刷版本中往往将“曹王”写作“曹、王”,“曹王”虽可解为“陈王”,但“曹、王”和“陈王”则差别大矣。
二、“古诗五十九首”和“古诗”
至晚在陆机时,已有人注意到这批失作者名或冒其他作者之名的五言诗的存在。这批诗作当时被统称为“古诗”。吕德申在《钟嵘诗品校译》中根据《世说新语》中王孝伯与其弟的对话得出结论“说明晋时已有‘古诗’的称谓”[4]64。宇文所安就同条材料分析认为:“使用‘古诗’一词并且确信别人会明白其确切所指。”。[1]36木斋引倪其心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古诗十九首”条目为证,认为“十九首等‘古诗’是在魏末晋初才开始流传的”[2]6。曹旭《诗品集注》中亦有“古诗:齐梁时对汉魏无名氏五言诗的总称。”[5]10总之,在陆机时代已有一批以后世所谓的《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无作者名或冒作者名的五言诗存在,以其出众魅力为彼时文人所重。《诗品》中关于这批诗作的记述为:“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1]17宇文所安据此推断出:“在六世纪初,有一个收录了五十九首无名‘古诗’的集子的存在。从钟嵘的措辞可以看出,陆机所拟的十四首位于这一组诗的开头。”[1]41陆机拟作的“十四首”又可能是“十二首”[5]77,则集中所收古诗为五十七首。无论五十九或五十七,或者更多、更少的数字,能够确知的是彼时有这么一批古诗的存在。那么,这批古诗可能包括哪些呢?
许文雨的《钟嵘诗品讲疏》中所举历代学者对这批古诗所含的诗作推断为:《古诗十九首》②“陆机所拟十四首古诗,除《兰若生朝阳》一首外,其余都包括在‘古诗十九首’内。”见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3 页。宇文所安指出,其中《拟东城一何高》所拟为《东城高且长》,但作为题目的首句显然不同,说明《文选》编纂时所见文本已不同于陆机拟诗时所见文本(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17 页)。此亦为文本流传时的变更所致。《兰若生朝阳》①《文选》中陆机诗题目为《拟兰若生朝阳》(第971 页),《玉台新咏笺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中归为枚乘名下的诗为《兰若生春阳》(第20 页),逯钦立所收亦同(第335 页)。参见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三十七》,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0 页。《橘柚垂华实》《上山采蘼芜》《四座且莫喧》《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十五从军征》《新树兰蕙葩》《步出城东门》《采葵莫伤根》《甘瓜抱苦蒂》《青青陵中草》、《长歌行》《鸡鸣高树颠》《相逢行》《伤歌行》《羽林郎》《董娇娆》、《飞鹄行》《艳歌行》《饮马长城窟行》《古八变歌》《艳歌行》《陌上桑》(艳歌罗敷行)二十四首。②参见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成都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3 -36 页。
另外,根据前文所述的宇文所安对《玉台新咏》中《团扇诗》(《怨歌行》)等几首古诗作者署名的质疑,及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对《同声歌》署名张衡的不确定的论证,不妨将《团扇诗》和《同声歌》归入这批无作者署名五言诗。而所谓苏李诗的署名,更是素来被学者否定,又苏李诗与《古诗十九首》在用韵、语法、语汇等相类,如李泽厚所说二者“风格极为接近”[7],故可将这二十一首③参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6 页。《文选》所录“苏李诗”为七首。纳入。《宋书·乐志》中同为“古词”的《白头吟》也可归属此类④参见[南朝齐]沈约《宋书》,中华书局,2005 版,第413 页。。罗根泽对托名的现象总结为“至古辞或失名之作嫁名汉人者,则以歌词所咏为某人,或事类某人,遂谓为某人之作。所以《白头吟》嫁名卓文君,《怨歌行》嫁名班姬,《河梁诗》嫁名苏李。”[8]57《塘上行》沈约在《宋书》中记为曹操的作品,而多有文献指出其为甄后作品⑤参见陆侃如《乐府古辞考》,商务印书馆,1926 版,第103 页。,故亦可收入此类。
《乐府诗集》中列为古辞的有近八十首,其中五言类为三十四首,其中风格与这批早期五言诗歌相类、还可暂补入的有“横吹曲辞”中《紫骝马》⑥参见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二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1 页。;“相和歌辞”中《长歌行》除“青青园中葵”外的另两首⑦参见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三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5 页。、《君子行》⑧参见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三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7 页。《豫章行》⑨参见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三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3 页。《长安有狭斜行》⑩参见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三十五》,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71 页。《陇西行》⑪《步出夏门行》⑫参见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三十七》,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3 页。《折杨柳行》⑬参见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三十七》,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6 页。《怨诗行》⑭参见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四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05 页。;“杂曲歌辞”中《焦仲卿妻》⑮参见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七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7 页。《枯鱼过河泣》⑯参见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七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1 页。《离歌》⑰参见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八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2 页。等13 首。
由此,数量则远多于五十九。搜罗列举“十九首”以外的其他诗作的目的有二:一是展示诗作流传中的可能性——因为流传中的不确定性而使原本是“同批”或“同集”的诗作分裂,演绎出不同的身份,继而误导后代学者的研究和判断;更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呈现“十九首”及同批诗作的“原始面貌”——它们是五十九首或者其他某个数量的由于某些原因而失作者名的诗作。虽不能确定具体的诗作名称,但根据“十九首”和苏李诗的水准可以推断,这批诗作的创作年代跨度不大,作者非平庸之辈,而是有极高的诗歌创作水准。这批诗作可能最初藏于宫中——陆机和钟嵘都可能是藉由直接或间接接触宫中藏书得以发现它们⑱参见俞士铃.《陆机<拟古诗>十四首考》,载《古典文献研究》,2004年,总第7 期,第275 -280 页;[美]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0 页。。“我们知道洛阳的手抄本在南渡时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带到了建康”[1]66,那么这批作者不确定的诗歌能被带去建康,除随机的可能性之外,还可能是由于这批诗歌为宫廷所重。
另外,这些诗作,尤其是“十九首”,目前流传的顺序确切地说是《文选》选编的顺序。近一步扩大化设想,甚至可以说,所谓的“十九首”可能亦是由《文选》而来,倘若当初选的是其他某个数量的诗作、或是这批诗中另外的某些诗作,那么“十九首”将是不同的面貌。正如叶嘉莹所说:“则当时钟嵘所见的古诗至少当有五十九首之多,而《昭明文选》则选录了其中十九首编为一组。”[3]97如此以来,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便不能仅局限于十九首文本本身,而应以大局的观念重新审视建安、魏晋南北朝流传的无作者名或作者署名被严重质疑的五言诗作。
三、乐府和古诗
这批诗歌的创作主题颇为相似。宇文所安认为这些早期的诗歌创作主题很有限:“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列出有限的一套主题,而这些主题可以涵括(可能是)创作于三世纪末之前的绝大部分五言诗,还有相当一部分杂言诗和四言诗。”[1]18并从游仙、死亡、宴会等主题角度论述。木斋总结建安诗歌有不同于前世各代的三大主题游宴、女性、山水景物,以此论证“十九首”发生时期。如对女性主题,木斋指出:“其中的写作方法显示了由简单地使用女性题材,到更为深入的使用女性视角来写作的渐变过程。”[2]149宇文所安和木斋对游宴诗都有专章论述。如此重视游宴诗,不仅因为游宴主题是这些作品的重要主题,如“曹植始终所表现的场景一定有音乐存在”[1]152,更是因为二位学者都确知“乐府”的宫廷地位,即后世流传的乐府皆为宫廷歌词——而宴会是这些宫廷歌曲演唱的重要场所。
宇文所安认为:“那些表面上看来出自‘民间’的无名歌词现在备受珍惜,以前可能曾用于非正式场合的宫廷演奏,是出于保存的欲望而被收集起来的材料的一部分。无论这些无名乐府中的某些篇什是否真的来自‘民间’,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它们是作为一代代的宫廷传统而保存下来的。”[1]33
木斋指出:“首先是关于汉初所谓‘贵族乐府’的问题。‘乐府’的本意,就是宫廷专门管理宫廷音乐的机构,而并非一般贵族家庭可享用。是故此类乐府诗,应该称之为‘宫廷乐府诗’。其次,萧涤非先生称‘武帝迄东汉中叶,为民间乐府时期’,笔者对此深表怀疑。所谓乐府,本意自然是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其歌诗皆为配乐之歌诗,……何以就能出现民间的乐府诗?‘民间乐府’古人并无这一说法,民间可以有民谣,民谣不应等同于乐府,可以称之为歌谣、民歌等皆可。”[2]41
曹魏时期的公宴提供了乐府演出的机会,有利于五言诗的兴发——清商乐的主要歌辞形式是五言诗,故五言诗的兴发和曹操大兴清商乐有密切关系,而清商乐又是建安思想领域通脱解放和游宴活动的结果。①参见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9 -80 页。清商乐的特点是加入金石乐器,金石乐器和秦汉流行的丝竹乐器配合,使得音乐旋律和表现手法更丰满;而且清商乐的制辞方式是“撰诗合乐”;清商乐的曲调悲凉,符合秦汉以来士人以悲音为美的观念。②参见王立《论清商乐对五言诗及词体起源的两大促动》,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6 期,第148 -153 页。清商乐作为曹操提倡的“新乐”,以其丰富、动听的旋律,为世人所好的音乐风格得以流行,而其“撰诗合乐”的制辞要求促动了新的歌辞的创制。如此清商乐通过在公宴中的流行而促动了五言诗的发展。
汉魏时期的文化教育尚不普及,乐人多出于乐户,其文化匮乏。乐工所歌之词,除采集民歌改编和本人创作,更主要是依靠文人创作。宫廷乐会中,对于演出作品的要求应该比较高,一般的民间谚谣恐难登大雅之堂,频繁的宴会要求可供演出的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因此,宫廷乐会中的作品主要靠文人创作。换言之,曹操大兴清商乐和宴饮活动后,歌宴中文士即席创作应是五言歌辞的主要来源方式。王瑶对当时情景的描述为:“操、丕、植三人都是领导当时风气的人物,而所谓建安诸子,也完全是曹氏父子的幕僚和羽翼。他们凭借着政治上的领袖地位和文学的卓越才能,大胆地运用着新体乐府,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而且当时所有的著名文士,几乎皆收罗在他们幕下,风云所会,公宴唱和,才歌咏出了慷慨苍凉的人生调子,放出了文学史的奇葩。”[10]212
在清商乐兴盛的背景下,“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高唱”[6];原本多用于歌辞的五言在士人间普及,遂有“曹操的作品皆为乐府歌诗,曹丕和建安七子(孔融早死除外)的五言诗也备清商乐歌诗”[2]80。由此可知,早期文人五言诗歌大多为乐府的清商乐歌辞。相应的,这批诗歌中亦有不少被记录为乐府歌辞。如《鸡鸣高树颠》《飞鹄行》《白头吟》《塘上行》《陌上桑》(艳歌罗敷行)见于《宋书?乐志》①参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10 -413 页。,《饮马长城窟行》《伤歌行》《长歌行》《怨歌行》(《团扇诗》)见于《文选?乐府》②参见萧统《文选》,李善,注,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866 -867 页。,《乐府诗集》收《冉冉生孤竹》《驱车上东门》③“‘十九首’中其他作品亦被认为是乐府歌辞。”参见张清钟《古诗十九首集说赏析与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26 页。《十五从军征》等④参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0、332、336 页。;《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收《上山采蘼芜》《四座且莫喧》《去者日以疏》《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等为古乐府⑤参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4、332、333 页。;《北堂书钞》收《青青陵上柏》等为古辞⑥参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0 页。;《明月皎夜光》在《文选》李善注中为古乐府⑦参见萧统《文选》,李善,注,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848 页。马茂元更认为:“古诗和乐府除了在音乐意义上有所区别而外,实际是二而一的东西。”[11]
结合前文所述可以推断,包括“十九首”在内的这批早期文人的无作者署名或假托作者署名的五言诗作能跟随宫廷南迁,可能是由于它们属于彼时宫廷常用乐府歌辞。
四、创作中的共性
作为宴会上的即席创作的合乐歌辞,这些歌辞有许多创作手法上的相似性。因为作者既要在仓促间作辞合乐,又需达到一定审美的要求、满足听众的喜好,难免会框套彼时常用的感情基调、套语、流行的体裁,以使其被普遍接纳。这些诗歌的主要作者都属于上层士大夫阶层,因此作品中“时代的差异多于个体的差异”[10]32,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很雷同。
它们的感情基调是悲哀的。叶嘉莹对“十九首”的感情特征的总结为:“《古诗十九首》所写的感情基本上有三类:离别的感情、失意的感情、忧虑人生无常的感情。我以为,这三类感情都是人生最基本的感情,或者也可以叫作人类感情的“基型”或“共相”。因为,古往今来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有生离或死别的经历;每一个人都会因物质或精神上的不满足而感到失意;每一个人都对人生的无常怀有恐惧和忧虑之心。”[3]66
隋树森也说“十九首”的主要思想是“悲观、厌世、愤虐的思想,要求刹那间之快乐于醇酒膏粱中之主义,这种不得已而要尽量享乐的办法,都是乱世之音的表现”[12]。这些思想感情的特质,在这批诗歌中也同样存在。因为正如李泽厚指出,这类直抒胸臆,深发感喟,突出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是从建安到晋宋整个时代的感情基调。⑧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147 -148 页。
它们的审美风格和审美目的相似:“作为清商乐的倡导者和奠基人,曹操将自己的文艺审美观融入了清商乐和文人乐府诗之中,慷慨悲越成为清商乐和建安五言诗(包括文人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共同的审美特征。”[2]76“曹操的乐府诗也好,建安十六年之后的游宴诗也好,都与音乐和演唱有关,与娱乐有关,这就是诗歌的目的得以脱离开政治教化,开始与审美的愉悦相关,而‘一诗止于一时一事’,诗作主题的缩小,就使诗歌得以走向更为细腻、生动的境界。”[2]128
这些诗歌拥有许多相近的语汇。这些早期诗歌拥有一套“共享材料”——“组成诗歌‘共享材料’的一系列主题、话题和程序句在整个三世纪而且直到西晋末期都一直作为诗歌创作的背景而存在。”[1]152木斋书中专章论述了曹丕诗歌、曹植诗歌与“十九首”中的相似语句及曹植诗歌与“苏李诗歌”的相似语句;⑨参见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 -157 页。宇文所安不仅在文本语句细节的中多次对比,并附录铃木修次在《汉魏诗研究》中统计的“人生苦短”类诗句。①参见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79 -381 页。它们之间呈现出片段的相似性。宇文所安从早期诗歌的创作实践方面将这些相似性归结为:“话题、主题和主题的组合。有些主题组合是拼合独立的片段”[1]107;及创作套语的使用,“即兴创作有些传统套语”[1]159。这类创作中的共性使得阅读这些诗作往往带给人的感受是“似曾相识”。
五、传播中的变动
而当相似性非常明显时,十分相似的作品体现出的便是差异性——主体相同的诗作有不同“版本”出现。如宇文所安参考前人成果指出,“十九首”中《生年不满百》的部分诗句和《西门行》重复②参见宇文所安著《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三联书店,2012年版,214 页。罗根泽认为,《西门行》是按照《生年不满百》增加字句改成的。参见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5 页。,且同收录于《乐府诗集》的两首《西门行》“虽然使用了同样的材料,却有明显的被删改和添加的部分。”[1]216对同篇诗作的差异,宇文所安认为是“不同的文本保存渠道所具有的成规方面的区别”[1]32-33,探讨歌辞和诗作孰为原作无意义、也不符合实际情形;但《乐府诗集》中有“本辞”之辨、陆侃如在《乐府古辞考》中也有本辞的说法,如认为《乐府诗集》中《长安有狭斜行》是《相逢行》的“本辞”[9]102。罗根泽亦承认乐工对文人诗词的改动③罗根泽将乐府分类为入乐类和不入乐:入乐类又分歌者修改后的民间歌谣或文人诗赋、歌者自制歌词、及后世仿效者所作歌辞;不入乐类即后世仿效者单纯作的诗。从此分类方法正是对乐人在传播过程中对诗作的改变的承认。罗根泽著《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 页。。笔者赞同陆侃如、罗根泽的歌辞、本辞的说法,认为对这批诗歌来说,先有文人所写诗作,交付乐工演出和传播时会被改动。
《乐府诗集》中对一些相和歌辞特别标出魏乐所奏、晋乐所奏和魏晋乐所奏。其中只魏乐所奏的4首④参见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二十七,曹操《度关山》、《蒿里》、《对酒》,卷三十曹丕《短歌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而魏晋乐所奏的最多,有27 首⑤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二十六曹操《气出唱》三首,曹操《精列》,古辞《江南》(江南可采莲);卷二十七古辞《东光》,曹丕《十五》;卷二十八古辞《鸡鸣》(鸡鸣高树颠),古辞《乌生》,古辞《平陵东》,古辞《陌上桑》(艳歌罗敷行);卷二十九古辞《王子乔》;卷三十六曹操《秋胡行》两首,古辞《善哉行》,曹操《善哉行》,曹丕《善哉行》四首,曹叡《善哉行》两首,古辞《折杨柳》,曹丕《折杨柳》,曹操《卻东西门行》;卷三十七曹操《步出夏门行》,曹叡《步出夏门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晋乐所奏数量次之,有26 首⑥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二十六古辞《楚辞钞》,曹操《楚辞钞》,曹丕《楚辞钞》;卷二十九石崇《大雅吟》,石崇《王明君》,石崇《楚妃叹》;卷三十曹操《短歌行》二首;卷三十二曹丕《燕歌行》两首;卷三十三曹操《苦寒行》;卷三十四古辞《豫章曲》,古辞《相逢行》;卷三十五曹操《塘上行》(被疑为甄氏作);卷三十七古辞《西门行》,古辞《东门行》;卷三十九曹植《野田黄雀行》,古辞《雁门太守行》,古辞《艳歌何尝行》(飞鹄行),曹丕《艳歌何尝行》,曹丕《煌煌京洛行》;卷四十曹叡《棹歌行》;卷四十一“楚调曲”《白头吟》,曹植《怨歌行》(明月照高楼);卷四十二曹植《怨歌行》(为君既不易);卷四十三古辞《满歌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从统计来看,这批诗作中的《鸡鸣高树颠》《折扬柳行》《陌上桑》(艳歌罗敷行)在魏晋时都有演出。而《豫章曲》《相逢行》《塘上行》《白头吟》《艳歌何尝行》(飞鹄行)仅标晋乐所奏,但曹植却有拟《豫章曲》⑦《乐府解题》曰曹植拟豫章为穷达。参见郭茂倩《乐府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4 页。。这些记载,基本印证了木斋所论的《陌上桑》等一向所说的汉乐府民歌并非汉乐府的论断。罗根泽认为《相逢行》和《鸡鸣高树颠》《长安有狭斜行》为同题之作,孰为前后难以分辨,有可能是流行中的变体。《塘上行》《白头吟》既为嫁名他人的古辞⑧参见见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 版。,则先前就是演出作品;因此《豫章曲》《相逢行》《塘上行》《白头吟》应是传播过程中失去记载,或失去所配音乐,到晋朝后又重新配乐演出。《艳歌何尝行》(飞鹄行)的情况比较复杂,罗根泽认为“先为语句不齐之歌,至徐陵选《玉台》时,则渐变为纯粹五言矣。”且怀疑曹丕《临高台》中后一段有可能为“古辞错附”[8]38-39——“古辞错附”就是典型的作品在流传中被变更⑨根据下文分析,整段歌辞“错附”也可能是乐工为了延长歌曲长度有意为之,被记录在歌辞集中而流传下来。。
《乐府诗集》中仅有“晋乐所奏”中列出9 组歌辞和本辞的变化:卷三十曹操《短歌行》,卷三十二曹丕《燕歌行》,卷三十三曹操《苦寒行》,卷三十五署名《塘上行》,卷三十七中古辞《西门行》、古辞《东门行》,卷三十九曹植《野田黄雀行》,卷四十一古辞《白头吟》,卷四十三古辞《满歌行》。
对《塘上行》和《白头吟》歌辞、本辞变化分析如下:《塘上行》的歌辞比本辞加入重复的语句,如重复“蒲生我池中”“莫用豪贤故”;改变歌辞,如将“莫若妾自知”改为“莫能缕自知”;在句子前加补充性词语,如在“夜夜愁不寐”前加“今悉”;连续加入若干句,如“倍恩者苦枯,倍恩者苦枯,蹶船常苦没,教君安息定,慎莫致仓卒。念与君一共离别,亦当何时,共坐复相对”;改变句尾词,改“脩脩”为“萧萧”;改成常用套语,如将“从君致独乐”改为“今日乐相乐”。《白头吟》的歌辞和本辞之间的变化也很明显:歌辞中加入“平生共城中,何尝斗酒会”“郭东亦有樵,郭西亦有樵,两樵相推与,无亲为谁骄”“如马啖萁,川上高士嬉”;改“男儿重义气”为“男儿欲相知”;加入演出结尾的吉祥套语“今日相对乐,延年万岁期”。
两组的改动都很明显,改动的方式也相类:重复某句话,加入连续的句群(有可能是从其他歌辞中直接抄录),变化结尾的词,最后加入结束的吉祥套语。这些改动都很简单、直接,没有对本意的改变,所加入的句群无甚实际意思、非必须,是为了符合曲子的长度或演唱时临时要求的长度。这些变化应是歌者根据演唱实际需要而来。这些变化被保存下来,是因为无论《宋书·乐志》《古今乐录》或其他的歌辞辑录本“并不为读者‘选’诗,它旨在保存了宫廷音乐的材料,既包括祭祀文本也包括世俗文本。《乐志》弥足珍贵,因为它保存了来自表演传统的文本,连同文本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表演的痕迹一起保留了下来,没有使文本去适应公元五世纪或六世纪‘诗’的观念”[1]67。
从上述两组对比中如此雷同的改变的方法中可见,歌者对本辞的改变似乎是必须的。本辞的创作毕竟不能完全吻合乐谱的歌唱需要,比如长度、韵律方面,所以歌者需要根据演唱的要求重复现有歌辞,或增加句子。那么,当时的乐府歌辞记录应分为“歌辞集”和“本辞集”。而所见的被保留的“歌辞”的原始文献是“歌辞集”,而那些没有明显改动痕迹的作品的原始文献为“本辞集”。乐工文化水平低,演出的节目往往靠口口相传,因此以清晰可见的文字形式被保留的“歌辞集”不多。①参见杜亚雄、秦德祥《中国乐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40 -341 页。而那些著名的文人在酒宴上即席创作的诗作应被记录在“本辞集”中供乐工选用。相应的,现在流传下来的诗作必然有歌辞、本辞的区别。
有此意识后,在分析文本时应注意传播中的变动。传播中的变动分为有意的改动和无意的改动。有意的改动就是上文所说的乐人在演出时对歌辞修改。如对曹丕的《大墙上蒿行》,宇文所安的评论为:“这首诗与其说是为了配合现存的乐曲而作,更可能是围绕一个标准主题自由即兴创作再上配乐曲,歌手加入了特别引以为豪的宝剑和华冠的描写。”[1]230无意的改动是指乐人在口口相传时或抄工在抄写歌辞时因为误会而导致一些歌篇混淆,如前文所说的“古辞错附”可能即是传播中的无心之误。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研究“古诗”类早期文人五言诗时,不能仅局限在“十九首”或“苏李诗”等,而应扩大视野,将风格相类的无作者署名或作者署名不确的早期文人五言诗作时都纳入研究范围。同时,在分析文本时,应立足于其本质为歌辞这一点,对创作中的共性和传播中的变动予以充分考虑,并具有歌辞、本辞之别的意识,不需深陷于一些与主旨无关的内容的考量。
[1][美]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M].北京:三联书店,2012.
[2]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4]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5]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0,77.
[6][南朝梁]钟嵘.诗品[M].古直,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3.
[7]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47.
[8]罗根泽.乐府文学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9]陆侃如.乐府古辞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
[10]王瑶.中古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11]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2.
[12]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