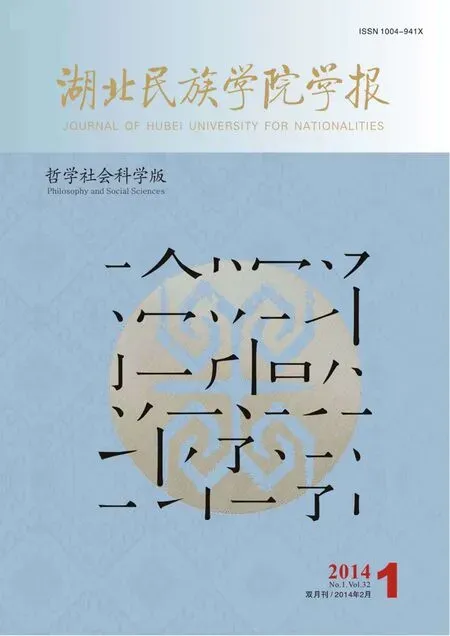跨文化体系下的预科汉字课程教育研究
2014-04-06张孟晋韩瑞芳
张孟晋,韩瑞芳
(东北师范大学留学生教育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曾有中国学生在课堂上问及,为何要给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设汉字课。是否应该设置?其深浅度应该为多少?这些问题似乎少有教师想过。许是因对外汉语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心理学已让教师们疲于应付,遂把尖酸难懂的文字学束之高阁;许是文字学家们不屑于为如呀呀学语的幼儿一般的留学生讲解深奥的汉字知识,总之,对外汉语学界内的汉字教学颇落后于国内文字学之研究,乏善可陈。可汉字又为汉语教学中无法绕过的一个结点,预科教师为在限制时间内完成更多教学内容,汉字往往要求死记硬背,这也是预科部汉字难教难学之缘故。如何在跨文化前提下进行汉语汉字教学,自以下三点可寻到突破口。
一、“以词代字”教学,还是“以字代词”
自古以来,“字”即为汉语的基础单位之一,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古时,“字”更似现代所阐述“词”之作用,而现代所谈之“词”被定义为句子的基本单位,故国内的汉语教学皆从字入手,以词带字,形成“词(字)→句→文”之学习模式,其缘由亦可明了了。
国内对外汉语教材之编写和教学方式大体以“以词代字”为基本,即通过讲词的方法带出汉字之教学内容。实践证明“以词代字”会出现以下情况:
1.“以词代字”即拆词以讲字,从词到字为单一裂解过程,字为此顺序方向的最后一个环节,之后并无其他内容用以延续教学。而细化至字及汉字词时,部首往往仅标示其本源义,而引申义和假借义却无法展示。
举例来说,“北方”一词可裂解为“北”和“方”二字。“北”,甲骨文写作,本义指两个人背对背,义为“背面”、相反,也是“背”之本字。但于战争中与众将士前进方向相反则为“逃跑”之义,例如“追亡逐北,伏尸百万。”[1]都逃跑了即为“失败”之义,例如“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2]古时人们的房屋皆为面南而背北,故由相反之面产生“北面”之义。此三者实为引申而来,非“北”之本义。段玉裁所举“朋”、“来”之例也是同理。现代汉语中于“北”之本义已有些差距,即便是引申义“败北”也保留甚少,相反“北方”之引申义大行其道,若国际汉语教师不掌握字源理论,是无法在对外汉语课堂上给留学生解释清楚的。
陈五云说:“汉字记录汉语,在应用时,不可能每个字都按照造字的本义去记录语词。事实上,只要汉字一进入交际场合,它所记录的绝大多数都非造字的本义。”[4]教师说不清,学生听不懂,汉字学习仍然是死记硬背。
2.汉字“模块化”效应虽加强了学生头脑中双音节间之联系,但学生却无法将两字拆开后再另外与其他字自由重组,对现代汉语中“字”构“词”之语言构型模式很难理解透彻,此必将影响其日后构词的自由度。
仍以“北方”为例,学生之模块化记忆往往仅限制于“北”与“方”的组合,但“北”与“面、边、部、国、海、风、纬、美”等之组合形式,学生即便见到往往也难以形成词间内在联系,搭配成词。“南、西、东、上、下、左、右、前、后”与“方”也如是一样。
法国白乐桑先生曾提出的“以汉字为本位”观点,不仅反映出一位外国学者眼中的汉字状况,更暗示了非汉语文化圈对学习汉字的倾向。“字”与“词”的本位之争于学界已有一段时间,对外汉语学界内已广泛接受白乐桑先生的“字本位”理论。首先,区分白乐桑先生与徐通锵先生的两个“字本位”很重要,前者仅仅被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为一种汉字教学应用手段;而徐先生之理论则是一种语言研究方法。两者虽名相仿,而用不相同,不可相提并论。另外,白乐桑先生“字本位”之优势不言自明,将“以词代字”反向为之的“以字代词”即可层层步进:双音节词、多音节词、成语、俗语……皆为其结果,程度甚深;且同一字可对应含此字之不同义之数个词,是为一对多之“字构词”模式,范围甚广。徐通锵先生提出的“字→辞→块→读→句”[5]亦是此种道理,其深与广皆优于“以词代字”,应用也必然更为广泛。
二、形声字构字发音的问题
形声字是一种为方便记忆而人为组合部件的文字形态。从汉字发展史便能窥其一斑:在商周文字阶段,形声字只在其文字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到了战国时期便增至一半了;许慎的《说文》中已有八成。1952年,教育部颁布的2000常用字中,有74%为形声字。种种现象表明,形声字占汉字总数之大半,得其者即可得汉字。可以形声字为例却又发现漫长的历史改变了很多汉语字词的发音,留学生在试图总结形声字规律时又常常遇到例外,造成记忆困扰。
“韵部的稳定性较差。……一切音变都是向临近的发音部位转移,一步步向前走,或一步步向后走,或是一步步高化或低化,绝不越级跳跃。”[6]王力先生的意思是包含元音的韵部往往因时间、地域及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渐移。元音的发音是更多受到口型及舌位的影响,不若辅音声母还涉及送气问题,所以相比较起来这种渐移更易发生。
1.清代学者钱大昕提出两条声母演变规则: (1)古无轻唇音。钱大昕发现上古时期并没有轻唇音(唇齿音)f,只有重唇音(双唇音)b、p、m,轻唇音是后来从重唇音中派生出来的。例如:
①非(f,轻唇)——悲(b,重唇)、辈(b,重唇)、裴(p,重唇)、徘(p,重唇)
②方(f,轻唇)——祊(b,重唇)、旁(p,重唇)、彷(p,重唇)
(m即明母,多从微母——w中演化而来,例“氓”——“亡”)
(2)古无舌上音。《切韵》系统的舌上音“知、彻、澄”,演化为现代汉语的zh、ch、sh;舌头音“端、透、定”,演化为现代汉语的d、t。依照钱大昕的发现,这两组声母在上古本来是一个音位,或者“知、彻、澄”是从“端、透、定”分化出来的。
舌上音→舌头音
③是(sh,舌上)——题(t,舌头)、提(t,舌头)、堤(d,舌头)
④尚(sh,舌上)——堂(t,舌头)、躺(t,舌头)、党(d,舌头)
舌头音→舌上音
⑤多(d,舌头)——侈(ch,舌上)、哆(ch,舌上)、奓(zh,舌上)
⑥童(t,舌头)——憧(ch,舌上)、幢(ch,舌上)、撞(zh,舌上)
2.“清乾隆年间(十八世纪),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作者写了一部《团音正考》(1743),才区别了团音和尖音。”⑦尖团字乃为一种古音孑遗。乾嘉学者们归纳整理发现,现代汉语普通话中j、q、x来自古时g、k、h(牙音“见、溪、群、晓、匣”一组),并一一对应。例如:
⑦工(g)——江(j);更——[kəŋ,55],[tɕi,55];街——[tɕiε,55],[kæi,55](东北方言)
⑧快(k)——缺(q);考(k)——巧(q);壳——[k‘ɣ,35],[tɕ‘iαu,51]
⑨害(h)——辖、瞎(x);咸(x)——喊(h);鞋——[ɕiε,35],[xæi,35〛(四川方言)[8]
若国际汉语教师能够掌握f——b、p,m——w,zh、ch、sh——t、d,g——j,k——q,h——x等声母变化规律,总结出形声字变化发展图表,不仅对扩大留学生的词汇量有巨大帮助,对留学生的形声字字形掌握也有很大好处。
三、如何连接汉语词之“音”“义”
有一非洲裔学生曾困惑于“HSK”的含义,他觉得自己得考HSK,遂称其为“黑色考”。而当教师问及若不为非洲裔学生考试时该如何解释,他亦给出了幽默的答案:亚洲学生是“黄色考”,中东的学生是“褐色考”,非洲学生是“黑色考”,其他学生是“花色考”……我们可以发现不同颜色均以相同声母[x]为基础,依此类推,大量相似之词均有相似之声母:甭、别、不、罢、没、莫——[p];非、弗、否——[f];河、湖、海——[x];拿、捏、挪——[n]……
此非孤例,上古声母中以唇音有关的字母多与否定有关,以上面唇音一组为例,其几乎囊括了古今汉语所有的否定词。用双唇紧闭表示否定,应该来自于汉语的原始形态。而唇齿音[v]及零声母词(无、未等)亦是从上古的双唇音分化得来,皆可表示否定。尖团音中的z、c、s演变成了三个近指代词兹、此、斯。
或许我们可以如此假设:汉语中,语言使用者在潜意识中赋予了“声母”较多的义,人在受到“声母”刺激的同时即在头脑中产生了对特定义群的限定,这种限定并不明确和细致,只起到总领源词词义(有且只有数个之多)的大方向和指导词义孳乳的作用,于发音上则不明显;相对而言,“韵”中以自然形式包含的义较少,其功能更多地出现在圆润发音和细化词义上——于义群大类中分化出详细的发音与分支词义。但由于历史上诗词歌赋对于格律的追求,“韵”的使用被无限放大,以至于如“声母”一般产生了“同韵义群”。此种人为因素参杂、元音之变化受时间、地域等诸多方面影响,并不能轻易寻出一条线索为留学生之用,不似声母,故不列入本文讨论范畴之内。
齐佩瑢先生的《训诂学概论》[9]和孙常叙先生的《汉语词汇》[10]均曾以明母——声母[m]为例论述基点以讨论声母含义问题。愚试以四小类来阐述两位先生之观点:
1.[m]声存在着模糊不清、黑、遥远等类似之义。
例如:
暮——指日落的傍晚。声符“莫”本义亦指傍晚,后也引伸出“无,没有”之义,“莫须有”便也源自于此。由“莫”作为声符的字大多亦包含有空旷、虚无之义,冷漠、漠不关心即表示心意虚无,无法让人感受到。
煤、墨——其声母均为[m],表示黑色。东北方言中称墨[mi,51]斗鱼,墨[mi,51]镜,河南口语称墨[mei,35]镜,虽韵母发生变化,但其声母亦未改,可见人们于潜意识中“义”对于声母的需求。
漫漫、茫茫、莽莽、蒙蒙、淼淼——也有茫远、广大、模糊不清之义。
昧——其声母[m]与其形符“日”皆为细化出“不明亮”和“人糊涂”之义服务。与之相对的“寐”则凸显出“宀”,即在房屋中处于迷糊睡梦,而“梦”亦指人不清醒的状态。
民——甲骨文作“”,即以锐物刺瞎眼目,指当时为避免抓捕来之战俘奴隶逃亡,便刺瞎其双目,以便于役使。遂“民”之本义应为“盲之奴隶”,其声母不仅与“盲”相同,义亦同源。
某,为不明说之人。懵,指昏昧无知之态。谩,为蒙蔽真实之言语。迷,义为迷失行路。“蒙”作形容词时义为迷糊,眼发黑。所有相似之义皆来自声母[m]。
庙——廟,“广”表示房屋,“朝”作声旁。“朝”为定母宵部,义为早晨;“廟”为明母宵部,供奉祖先之所在。虽韵相同,但声母不同,所以意义上并没有联系。
魔——是一种人类无法理解的事物,取[m]声应在一定程度上跟模糊不清有关。那么作为鬼的一种,“魅”亦好理解了。
2.[m]声蕴含的黑、看不清之义往往由覆盖引起,所以其另一分支义为:覆盖、闭合。
例如:
埋——土覆盖于上,同“薶”,音同[mæi,35]。同理,“霾”亦可知其为烟雾、灰尘覆盖于空中。
面——段注曰“顏前也。……顏前者謂自此而前則爲目,爲鼻,爲目下,爲頰之閒,乃正鄉人者。”即目光所覆盖之人脸处。毛、眉即面上之遮盖物,目则为被覆盖之物。此毛发类丰富则称“茂”。貌,外貌。膜,覆盖之薄皮。瞑,闭眼。刮风天我们也会“眯”眼,而睡觉亦称“眠”。瞒、蒙为动词时义为掩盖事实。瞄,视线集中覆盖于所观察之物,亦可释为结合。而摹、描、锚、铆,也属同类。
帽、冕——本为“冒”,覆盖于头上。“冒”字现有透出之义,如“明”为光线透出夜幕,“萌”为草木透出土地,“芒”为可突出之尖刺物。
灭(滅)——以水盖火,尽头。没[mo,51],段注曰“没者全入於水”封于水下。抹[mo,214],从手末声,涂敷。沫,段注曰“一曰沫也。沫謂水泡。”覆盖于水面的水泡。霉,生成菌丝状覆盖物。磨[mo,51],一盘压盖另一盘。迈,跨过并含覆盖之义。
幕——《说文》曰“帷在上曰幕,覆食案亦曰幕。”即桌布。墓,即土盖。幔,幕也。幂,义为盖巾,当下数学中于乘方之用亦源自重复覆盖。墁,涂饰,覆盖之义明显。
扪——手按压覆盖。抿,即抹,亦有嘴紧闭之义。闷,因封闭而愤懑。而“门”之关闭义也一目了然了。“秘”为不公开,“密”,闭也。
以钱易物即为“买”,以物易钱即为“卖”,买、卖虽为相反,但皆有替换覆盖之义,遂贸即含有“买”“卖”两种行为。
“满”即无法再进入,充实其内似覆盖于外。弥、每、忙、麻等此类表示内部充满之义之词皆从[m]声。
3.[m]声由“遥远”的事物在视觉中较小衍生出另一个分支义:“小”。
例如:
尛,同“麽”,义为细小。蔑,亦为细微之义,例如扬雄《法言·学行》中曰: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藐,本义即指小,幼稚。就连“米”也有小而密实之义。
秒,禾芒也;麥,芒束之谷,均释为细小。
4.[m]声从黑、茫远、模糊等义又可以再分支出一义:没有。
没——本身也是[m]做声母。粤语中的句末疑问语气词“冇”[mɑu,214]即为此义,例如“吃饭冇?”默,没有声音。谜,没有答案。泯,灭也,即表尽头,没有。免,即免除,如免税、免职、免疫、免进皆为此用法。
此外,还有一些词虽以[m]为声母,但仅为小义群,例如含有迟缓、堕怠、滞止之义的词“慢”“磨”(“磨叽”与“墨迹”就是一组同源词,另“磨叨”亦属此用法)等,此处便不多赘言了。
绵长的历史改变汉语声母的语音面貌,仅凭语音学无法完全解释汉语的音义结合问题,故需引入音韵学知识来辅佐证明。
此处我们需要清楚,音韵学之“声”与汉语拼音中之“声母”并不相同,但二者于“声”含“义”之功能却较相似。留学生的母语多为以词根词缀区分含义及词性的字母系语言,其对包含含义的词首词根发音非常敏感,而词首词根多为辅音字母或元辅音字母组合,这一点与汉语拼音及音韵学中的“声母”形式非常相似。
当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看到单词“patch”(补丁)时,他们首先接收到的信息是“p”(扁、平、片),头脑中会反映出pad(垫子)、pan(平底锅)、paper (纸)、page(页)、pizza(披萨饼)、piece(片)、palm (手掌)、peace(和平)、people(平民)……与之不同的是“match”一词,“m”所包含的意义是山、男性、配合及比赛,例如mountain(山)、man(男人)、male(雄性)、mate(队友)、match(比赛、像比赛队员一样排列整齐的火柴)……所以即使“patch”与“match”有四个字母一样,甚至排列顺序都没变的情况下,意义仍然是一点联系都没有。如果预科汉语教师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相似优势,为学生整理出“声母含义图谱”,使学生记住“声母含义群”即可在潜意识中建立起汉语之语音——含义构型模式,这对留学生大量扩充汉语词汇量,意义非凡。
[1] 韩非子·五蠹[M].
[2] 贾谊.过秦论[M].
[3]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M].
[4] 陈五云.“字无引申义,词无假借义”说[M].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4).
[5] 徐通锵.语言论[M].北京: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30.
[6] 王力.汉语语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30.
[7] 王力.汉语音韵[M].北京:中华书局,1980:79.
[8] 周有光.汉字声旁读音便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12.
[9] 齐佩瑢.训诂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4:70.
[10] 孙常叙.汉语词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