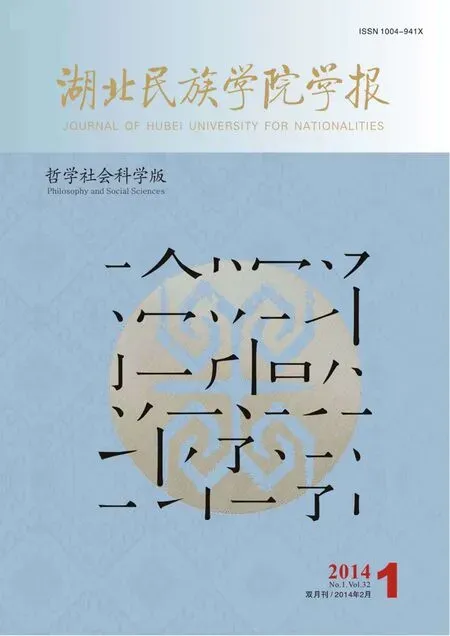论民主革命时期艾思奇对文化民族性的重建
2014-04-06梁文冒
梁文冒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文化是文明的载体。文化民族性往往凝结着一个民族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在比较封闭的社会形态或者共同体里,文化民族性的作用还得不到彰显。越是在开放的社会里,文化民族性越显得重要。也就是说,文化民族性是相比较而言的,在比较中才能不断显现出不同民族文化的优劣,才能体现出一种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独特个性和气质。自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渐次深入,中华民族的文化民族性和文化的时代性、世界性、阶级性相伴生。几乎所有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家都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民族性的出路做出过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文化人,比如艾思奇等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文化民族性的界定及其重要意义
(一)文化民族性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民族性
所谓文化民族性,是一种民族的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性。它是文化结构中相对稳定的组成部分,表现在文化的基本精神、思维方式、表现形式、价值取向等方面。
中华民族历经长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佛教等为主的独特文化,具有自己的文化民族性。中华民族的文化民族性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或政治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它不是指中华民族中某个具体民族的文化,而是指整个华夏儿女普遍具有的文化特性。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延续力和内在的包容会通精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华文化是儒家一统下的多元文化,是求稳务实的农业文化,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民族性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从基本精神上来说,中华文化是一种忧患意识、儒道互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文化,从思维方式上来说,中华文化是一种注重整体性思维、直觉思维、类比思维、辩证思维、中和思维的文化,从价值取向上来说,中华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重视群体、注重人伦、重公抑私、重义轻利、崇尚气节、天人合一、均等大同的文化。
文化民族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长久保存下去并保持完整性的重要保证。这种丰富和发展不是在封闭、孤立的状态中进行着,而是在开放的世界中不断和其他文化产生碰撞并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从而内化为自身的文化过程中实现着,它反过来又成为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它必须是与其他文化的特性兼容的和谐共处的,而不至于发展成为一种文明的冲突。它是一种宽容的文化,而不是排斥他者的文化,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的文化。它也不是民粹主义的,而必须是为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
(二)文化民族性在现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以至于戴震不得不想着“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和李大钊喊出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口号,由此引起了中西方文化论争趋向白热化。文化论争的实质是文化民族性已不能完全满足中华民族自身发展需要,西方文化开始挑战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当时的一些思想家认为,文化民族性非但不能成为促进中国发展的动力,反而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绊脚石。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攻击,甚至连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一些优秀的民族特性也一起批判,以至于当时被国民党贴上传统文化破坏者的标签。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人才开始意识到它对于民族抗战的重要意义,重新审视文化民族性。其中比较突出的人物就有艾思奇。艾思奇从文化民族性如何满足现实需要出发,对文化民族性进行批判继承。这种批判继承也直接促使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形成。
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文化民族性问题已经解决,或者说它是个不言自明的东西。而事实上,只要民族国家存在,文化民族性就需要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文化民族性本质上是文化各个类型的特性如何满足其价值主体需要的问题。人的需要是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发展的,在不同的时代,各种文化会面临着不一样的境遇,其价值主体必须根据自身需要做出文化选择。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民族性问题不是不存在了,而是变得更加突出。全球化对于文化的危险在于容易走向民族虚无主义或复古主义两个极端。民族虚无主义表现在西方文化仍然在世界上占据着强势地位,掌握着话语权。在西方文化的入侵下,民族话语处于碎片化状态,难以进行有效的整合,只能被动地应对。作为对全球化的一种有意识地对抗,复古主义趁势崛起,成为继五四后的又一次逆流。复古主义不但不能发展文化民族性,反而容易给文化民族性贴上落后的标签,使一部分人脱离于现代思维和现代生活方式,不利于文化民族性自身的革新。因此,只要民族国家存在,就会存在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就会存在发展文化民族性的问题。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发展文化民族性就更显重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文化民族性可以促进本民族自身文化的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实现本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强化国民意识,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对文化民族性的态度,反映着文化的走向和社会动向。弘扬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可以重启新一轮改革。重拾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追求大同的社会理想,可以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中华民族的文化民族性必须得到强化而不是被弱化。
二、艾思奇对中华民族文化民族性的基本看法
要了解艾思奇对文化民族性的认识,首先就要懂得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艾思奇认为,中国文化有着资本主义的雏形,是不稳固的封建社会的存续,是非常庞杂而又极不平衡的。这就决定了他对文化民族性主要采取的是批判继承的方法。
(一)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农业社会
艾思奇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宗族制度为纽带的。他在《家族》里提到:“这种宗族制度,正是封建割据制度的基础,中国的封建制度,就是以宗族制度为构成原素的。”[1]658艾思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经济上加以解释这种以宗族制度为纽带的社会形态,并由此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着重论述的是东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制度,李大钊和陈独秀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际需要把重点放在对儒家伦理的揭示和批判上,艾思奇则对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制度文化进行整体性揭示。他对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论述较少,而更侧重于现实思想文化斗争的直接的需要,有简单化的倾向。虽然如此,正像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艾思奇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性,并由此展开了对中国文化其他方面的批判。
(二)天下为公的社会价值取向
艾思奇认为中国自古就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他指出:“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2]683艾思奇在这里直接继承了陈伯达的观点。陈伯达认为孙中山和谭嗣同、康有为都对“大同”思想有所发挥。这显示出他们理论上的默契。但他们刚开始并没有将中国的大同社会理想和共产主义社会做区分。这或许是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但也说明了当时他们理论修养上的不成熟。
而到了写《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时艾思奇已经做了明确辨析。在此文中,艾思奇指出,孔子、老子、康有为、孙中山都有大同世界理想,然而不相同。康有为没有脱离半封建的改良的主张,希望与封建势力妥协来实现,而孙中山的理想包含革命的民主主义因素。同样,老子的大同理想也与孙中山的不一样。老子的理想是不能超过封建的社会秩序的范畴,是对原始的自然经济的憧憬,与包含着近代民主主义内容的孙中山的理想有本质的不同。通过对艾思奇有关中国大同社会前后不同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也是不断发展进步的。
(三)愚忠的封建伦理
在艾思奇看来,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和基本文化精神是一种愚忠思想。这突出表现在他对中国旧戏里所谓英雄人物和蒋介石的“诚”的思想的批判上。
艾思奇对封建社会里刚健有为的精神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在《中国戏剧与武生》里把中国古代英雄人物刚直不阿的气概看做忠君的奴隶道德。他说薛仁贵的道德是一种“忠仆”的道德,薛仁贵式的人物是“奴隶底英雄”,而“武生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的人品之最高峰”。艾思奇否定封建社会的基本精神是想提醒人们不要沉湎于封建意识里,要对它进行现代改造。
艾思奇对蒋介石思想的批判是响应了王明在《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中发出的“共产党员用灵巧的方法去揭破法西斯蒂撞骗宣传”的号召。王明在该文中指出,蒋介石和蓝衣社社员利用落后的、古代的孔孟学说、道教、佛教等等来愚弄人民。蒋介石把“诚”的思想作为“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提出来。艾思奇指出,蒋介石宣扬的“诚”的思想完全是“唯心论哲学”。他把蒋介石的“诚”的唯心论哲学和宗教联系起来,指出“诚”字在中国的运用,常被当做是一个迷信的符号,只是要求民众“诚心诚意”地遵守欺骗愚民的道德。
(四)消极落后的中和思想
激发艾思奇对中和思想进行批判的直接原因是1930年共产国际发的一个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文件。这是一个反对党内对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进行调和的政治文件。艾思奇无疑是贯彻了这个文件的精神,从思想上对调和论进行清算,所以对调和论的思想基础——中和思想进行批判。
艾思奇首先展开对中国历来存在的中庸思想的批判。他把中庸思想仅仅限定在事物存在的原理层面,而防止其进入价值原理领域。在价值领域,他把中庸思想看作一种观念论,认为它是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他指出历来被看作善的中庸思想并不是善,善是有前进性革命性的发展的东西。他还认为阎锡山的“中”的哲学的基础,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执两用中”的“权”术。“中”的哲学思想是当时山西的统治者根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和经验在新的形式上把传统的儒家中庸思想给系统化而已。到了1945年,新华社、薄一波、续范亭、陈伯达也对阎锡山进行批判。但陈伯达等人着重用事实来反驳阎锡山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而艾思奇则批判阎锡山的思想基础——“中”的哲学。可以说各有侧重,互有分工。
三、艾思奇关于文化民族性的建设路径
艾思奇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他留学日本期间接触了河上肇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回国后在上海和延安专门从事文化工作。参加新启蒙运动,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他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而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文化民族性。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为契机,推动文化民族性发展。
(一)以共产主义道德取代封建专制伦理
王明在《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中指责蒋介石把孙中山的学说给曲解了,要求共产党员做反蒋介石及其蓝衣社的思想斗争。作为响应王明这个号召的一部分,艾思奇相继发表了《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共产主义者与道德》、《家族》、《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改善家庭关系,建设新家庭》等文。
在这些文章中,艾思奇批判以家族制度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及其道德,提出建立以新型家庭关系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及其道德。在《共产主义者与道德》中,艾思奇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认为道德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共产主义者必定在吸收旧道德合理部分的基础上建设新的道德。艾思奇反对把封建道德当作永恒不变的绝对的道德律令,认为旧的经济基础解体了,建立在旧经济基础之上的旧道德也要随之瓦解。但旧道德不是随着旧经济基础马上消失,它具有相对稳定性,是个逐渐衰落的过程。而且旧道德中也含有普适的部分,这些普适的部分会随着社会发展和新经济基础的诞生吸收新的内容。共产主义者并不是要漠视一切旧道德,而是要吸收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切优秀的道德品质,要提高、发展和改造旧道德中精华的部分。如果说艾思奇在《共产主义者与道德》中只是对旧道德批判继承,那么在《家族》和《改善家庭关系,建设新家庭》中则对作为共产主义道德基础的新型家庭关系进行系统构建了。艾思奇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下的家族制度,是旧的一夫一妻制的消灭,而代之以真正合理的一夫一妻制。马克思主义对于家族问题的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人类的家族制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把中国的旧家族形式理想化,并企图以它为基础,来解决中国目前的道德文化以及革命问题,那是错误的、违背时代的思想。随着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开始出现新的民主的家庭关系,艾思奇及时提出了要继承“五四”以来反抗旧家庭的传统,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家庭关系,废除旧的家长专制制度。
(二)以唯物辩证法代替传统的中和思维
在文本中虽然没有找到艾思奇直接论述用唯物辩证法取代传统中和思维的地位,但从他对唯物辩证法的热心宣传和对儒家思想方法的猛烈批判来看,艾思奇显然是想用唯物辩证法来取代他认为的消极落后的中和思维。
伍启元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中介绍了五四时期被广泛传播的“唯物的辩证法”,并提到河上肇的《河上肇经济学研究》。艾思奇正是在留学日本的时候接触河上肇的唯物辩证法,并将唯物辩证法作为自己后来从事文化工作的方法论基础。在新启蒙运动期间,艾思奇和陈伯达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宣传唯物辩证法。艾思奇把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新哲学”提出来。他在对儒家封建的哲学思想复归进行解剖后说:“中国哲学的新时代”[2]118,“是在1927年后掩蔽了全思想界的唯物辩证法思潮出现时又显露了头角。”[2]118为了宣传唯物辩证法,他还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辩证法唯物论的理论根据。他在《哲学“研究提纲”》中指出,中国的墨子、老子等就是自然发生的辩证法唯物论的代表。他说:“自然发生的辩证法唯物论是人类哲学史上的最初派别,如希腊的初期哲学,中国的老子、墨子等。”[1]552
在积极宣传唯物辩证法的同时,艾思奇并没有忘记对其他反动的落后的思想方法的批判,尤其是对儒家中和思想的批判。这种宣传和批判是思想文化战线斗争的两个方面。除了指出阎锡山的“中”的哲学是包裹着新外衣的儒家的中庸之道外,艾思奇还把它和唯生论一样看作和一定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愚民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是要抬高封建统治者的个人权威,把统治者及其他们要人们奉为信条的封建伦理神圣化、绝对化。阎锡山的“中”的封建哲学是僵死的不运动的,必然滑向神秘主义和观念论的错误。和蒋介石的“诚”的哲学思想一样,“中”的哲学也是统治者用来欺骗麻痹人民的思想工具。
(三)以文化的大众化带动中华文化民族性发展
艾思奇非常重视文化大众化对文化民族性的带动作用。他在总结抗战时期延安文化界取得的成就时虽然把文化民族性视为文化大众化的工具,但客观上有利于民族性的发展,比如对连环图画的运用问题上。他在统计陕甘宁边区大众文化的发展情况时就有民族性的内容,并强调旧戏剧、旧小说值得发展。艾思奇把民族性融入大众化之中实际上是想把民族性扎根于现实土壤,而不是让它成为纯粹观念性的东西。针对叶青反对读经,主张读外国书,艾思奇主张读什么书“要针对着现实社会的问题上的需要”。他在《大众哲学》中强调,要改善中国的文化,必须“以前进民众的需要为标准”。他还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点是抛弃了一切优秀的传统,特别是抛弃了中国大众的优秀文化传统。在谈到旧形式的利用问题时他也强调文艺要是民族的,而且要是大多数民众所接受的。这是要通过文化大众化来传播文化民族性。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文化民族性结合起来,是自觉地担负起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发展文化民族性的双重文化使命。
和艾思奇文化大众化、民族化思想相呼应,中共中央1939年5月31日通过的《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到,要注意宣传工作的大众化和民族化,要符合中华民族的特点,尤其注意对于旧的戏剧和歌咏等的运用,力争使各种宣传品变得生动活泼,易于被大众所接受。正是在吸收艾思奇关于文化大众化与民族性关系思想的基础上,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提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要正确地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
(四)以文化先进性推进中华文化民族性进步
艾思奇继承了戊戌以来批判旧学传播新学的新传统,只是理论的出发点和其他人不再一样。他不再像胡适等人以西方的经验论和逻辑学为思想武器,而是以五四以来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艾思奇否定封建社会的英雄人物式的奴隶道德,但他并没有否定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他是在揭示封建的文化民族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逐渐解体后文化秩序的打破,力图摧毁旧的文化民族性的历史惰性力,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现代文化民族性。在艾思奇看来,文化的先进性内在地蕴藏于民族性之中,先进性离不开民族性,民族性必须紧随着时代发展,作为文化先进性的载体。他认为文化民族性的发展集中表现在鲁迅身上,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文化民族性的先进方向。他指出:“通过文艺,他向中国人民传播他在政治上、历史上、哲学上、文艺上等等方面的革命观点,传播着他的改造民族精神,改造中国文化和社会意识的新思想。”[3]177
[1]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