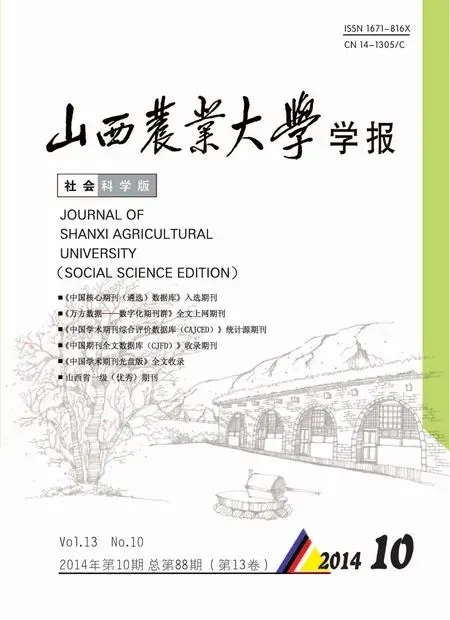自然法学派的法律发现观及启示
2014-04-05张志文
张志文
(山东交通学院 交通法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357)
自然法学派的法律发现观及启示
张志文
(山东交通学院 交通法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357)
在自然法学看来,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法律只能加以发现,不可以以人为的方式进行创造。这种发现法律的观点显然是基于立法的视角。在法学实践品性的观照下,这种法律发现观已然失去了“市场”。不过,司法视角下的法律发现观依然没有放弃对“理性”的追逐。
自然法学派;法律发现;法律方法;司法
言及法律发现,历史法学的“法律系发现的,并非制定”的观点,曾被无数学者所提及和引用。历史法学将法律的生命安置在活生生的历史之中,民族精神可谓法律本质体现之所在。而发轫时间早于历史法学的自然法学认为,“法律只能加以发现,不可以人为的方式来加以创造”。只不过发现法律的场域非历史,而是“由人的理性去发现有权威的命题或自然法,所谓的法典编撰不过是透过人的理性去发现的自然法,将之书写下来而已。”[1]自然法理论也是一种有关制定法律的理论,它以永恒和普世价值的存在为标尺评价、衡量已有法律中的内容。“法律中的旧内容应当接受这个理想的检验并通过修正以使它们符合这一理想;如果它们无法与这一理想相符合,那么就应当予以否弃。如果存在着需要填补的空白,那么就应当依据这一理想方案进行填补。”[2]那么,自然法学派是如何利用理性去发现法律的,以及这种发现法律的做法对当下司法实践又具有哪些意义。此乃本文的问题意识所在,也是笔者行文的落脚点。
一、背景: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回溯
正如梅因所说,“如果自然法没有成为古代世界中一种普遍的信念,这就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了。”[3]应该说,在整个西方法学领域,自然法学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影响和推动了西方法律、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从自然法的演变轨迹来看,它的发展大体经过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早期阶段、中世纪的基督神学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古典自然法阶段以及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现代自然法阶段。出于论证主题的限制,在这一部分中,笔者拟对自然法发展的前三个阶段进行阐述。原因在于,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然法思想是在与分析实证法学观点“斗争”交锋之后的产物,虽说仍然保留着古典自然法思想的核心,但是在对待法律发现问题上,显然没有古典自然法时期那般的“坚持”。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奠定了自然法的基础,确定了自然法的基本精神。古希腊的圣哲先贤们从世界的同一性出发,认为作为世界一部分的人有着与自然界同一的规律。在自然界有自然规律,而人类社会的规律则是自然法。只有以自然法为基础的人类法律才是正义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皆为这种观点的丰富做出了努力。而至古罗马时期,西塞罗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承继古希腊法学思想的基础,并使之系统化、罗马化。后人也正是从西塞罗的作品中透视出了自然法的思想。然而,古罗马时期的法学阶层更多侧重的是法律实践,而较少从事诸如正义、法律等抽象理论的探讨。
到了中世纪,由于西欧实行的是神权和王权、教会和国家的二元统治,这时包括法律在内的人文科学都成为了神学的附庸和婢女。可是,中世纪的思想家在神学思想的统治下,仍然对自然法思想进行着发展和延续。只不过自然法的思想更多是包含在了教会的教义中。这时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人物,如奥古斯丁,“把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西塞罗的‘自然正义’、‘自然法’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形成一整套为神学服务的理论体系。”概言之,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成为了神学统治的工具。
自然法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应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17世纪到19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在文艺复兴的推动下,在对中世纪神学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观念与自然法学结合在了一起,使自然法更加世俗化。自然法中的神学因素被抛弃,国家取代了教会,人的理性取代了神的意志,从人的本性而不是神的观念中寻找自然法的本源。人的理性成为了自然法思想的出发点。
综上所述,自然法学是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以理性主义为核心,以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自然法为理论根据的法学流派。应该说,在自然法的发展过程中,理性观念的论证始终占据着主流,而对理性的认识在不同的阶段也表现各异。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法是奠基在自然理性的基础之上,即言之,自然法的存在根据为自然规律或自然本性。自然之法是唯一的非人定之法,但也是现实社会中的正确之法,[4]通过自然的正义、道德、事物的本质等价值来确定法律的有效性和适用标准,对他们来说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吻合的正确的理性。[5]这一时期,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的贡献下,也包括西塞罗的努力,“把法律引向基于人类理性引导的对人与物的正确‘自然’秩序的认识”。[5]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强调,法律是理性的命令,法律是公道和正义的标志。亚里斯多德主张,“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的(永久)的制度。”西塞罗认为,“法律乃是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它允许做应该做的事情,禁止相反的行为。当这种理性确立于人的心智并得到实现,便是法律。”
中世纪的自然法则由“自然”理性转向了“神”的理性,而神法的地位高于自然法。也就是说,“自然法是永恒的上帝律法在人的意识中的复现,永恒法存在于神的智慧的理智里,只要人的理智能把握这种永恒法,人就会意识到它是自然法。”[4]在这里,自然法成为了神法的从属;而人类对“人法”的塑造则依赖于上帝理性的获取。所以,阿奎那认为,“人的理性来源另一个根据,从本原意义上讲,人的理性来自于神的理性、是对上帝的理性的分享;而上帝的理性表现为宇宙秩序和神法”。[6]在这时期,“通过塑造神之理性来取代自然理性的先验性和最高原则性地位,使自然之理性从神之理性的绝对永恒性和抽象性中解放出来,成为神之理性和人之理性的过渡和联系的中介,为古代的自然法从片面地关注自然本质及规律过渡到对人定法的关注奠定坚实的基础。”[7]
而行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神法的权威性遭到了颠覆。“法律的来源和权威基础并不来自于上帝,正确之法不是由上帝决定,而来自于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的本性。”[8]与前两个阶段将自然法的本质归结为自然规律或神的意志不同,人的本性成为它的来源。于是,神之理性消失了,而人之理性得到了阐扬。所以说,理性不仅成为了认识正确之法的根据,也成为了正确之法的源泉。因此,如果要发现“正确之法”,首先要探寻人的“本性”,然后按照逻辑推导出人的“自然的”权利和义务。[4]可见,法律存在的根据既非道德也非神权,而是人的理性。从人的理性中发现法律成为了这一时期学者们论证的重点。
总之,在理性智慧的关照下,法律摆脱了其客观规律和神权意志的本质,转向了人的自然权利和义务。在这里,对法律发现的诠释,明显是从法律如何表达,也即立法者的角度来进行的。
二、操作:理性的主导与法律的发现
在完成了对自然法学演变轨迹和理性思想的交代之后,接下来需要说明的就是学者们如何在理性思想的主导下发现法律的。经历了16世纪血雨腥风的宗教战争之后,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自然法学逐渐褪去了神学的外衣。人类开始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而更加相信自己的理解力。与此相伴,与神学、哲学分道扬镳的自然法思想渐次由法学家来研究并主导。于是,“‘自然’秩序观的‘理性’论证也应运而生”。
欧洲近代自然法学派的奠基人之一格老秀斯认为,根源于人的本性的自然法不在具有宗教的基因而是理性的体现,实在法或制定法应与自然法相契合。他说“自然法是正确理性的命令,它在宣示一个行为是否合乎伦理,是否合乎理智的及合群性的本性,”,并说“自然法为众人均同意的制定法。”[9]国家所制定的规范人类生活的国内法抑或藏匿于国与国之间的制定法,皆源自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仍是出于体现理性的自然法原则。按照格老秀斯的主张,国家立法者的立法活动也就是从社会生活中发现彰显理性精神的规范,将之公之于众以规范人类生活。无论是国内法或市民法还是国际法或万民法均可从人的意志中探寻其渊源。对人的理性的笃信是格氏法律发现观的特色所在。对于所发现之法律是否符合自然法原则,他为我们指出了两种方法以解验证之需。即“演绎证明法在于表明某事是否必然符合理性或社会性;归纳证明法在于断定某事是否符合那种被认为是所有各国或所有文明发达之国所遵循的自然法——即使这种断定并不具有绝对的把握性,至少也具有极大地可能性。”[10]
与格老秀斯将人定义为天生就具有在社会中和平共处的能力,简言之“合群性”不同,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是从人的自私自利、充满残暴、邪恶的本性出发建构法学体系。正是基于人类自私贪婪的本性,使得自然状态之下的社会生活笼罩在你争我抢、尔虞我诈的战争失序状态之中。理性的人们总结了诸多的具体规定,比如每个人都必须放弃根据其本性为所欲为的权利,[10]使人性得到收敛以及在自然状态中无法得到满足的情感归于顺畅。“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实为霍布斯自然法思想的经典总结和永恒体现。为此,人们之间订立契约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与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象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11]“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霍布斯认为,国家产生之前,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法就是公道、正义、感恩以及根据它们所产生的道德,“只是使人们倾向于和平与服从的本质,而不是正式的法律”;之后,自然法成为了实际的法律,成了国家的命令,成了民约法。在霍布斯看来,“民约法和自然法并不是不同种类的法律,而是法律的不同部分,其中以文字载明的部分成为民约法,而没有载明的部分则成为自然法”。民约法的制定目的就是限制和剥脱人们的天赋自由,使他们互不侵害而互相协助。可见,利维坦的出现使立法权集中在了主权者的手中,国家的理性和命令成为了法律的主宰。换言之,从国家统治者的智慧中发现不违背理性的法律以确保人类从纷争不断的状态进入和谐共处的时代。“法律决不能违反理性,以及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不在于其文字也就是不在于其每一部分的结构如何,而在于其是否符合于立法者的意向这是我们的法律家所同意的。……构成法律的便不是法官的慎虑或低级法官的智慧,而是我们这位人造的人——国家的理性和命令”。[11]
格老秀斯撬开了束缚在自然法理论上的宗教枷锁并使其回归于人的本性,将发现制定法的渊源放置在人的理性之中;霍布斯以失序的自然状态理论为突破口,论证了“伟大利维坦的诞生”,它的命令就是法律,从理性和命令中发现法律。透过上述学者观点的分析,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自然法得以实施的最终保障应当主要从统治者的智慧和自律中发现法律。发现法律的脚步并没有止于此。凸显制定法中天赋人权不可侵犯的自由的自然法思想,成为该学派继续发展的主要特色。对自由的确保以及建立在权力分立基础上的立法权的行使权限的制约,也成为了这一时期亟待解决的课题。
英国经验主义的鼻祖洛克是在假设政治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非霍布斯认为的“失序”而是“和平”状态的基础上,认为自然法是理性的表述同时也是规范人类生活永恒的规范。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然而,这种状态的性质是自由而非放任,原因在于“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12]自然法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保全个人的同时不要伤害他人。不过,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由于缺少确定的、规定了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裁断纠纷的尺度,以及个人虽有惩罚违反自然法行为者而充当自己案件裁判者等不足,所以,人们自愿让渡部分自然权利组成社会和国家以至于他们可以和平和安全的享受自己的财产,“而达到这个目的的重大工具和手段是那个社会所指定的法律”。在制定法和自然法的关系上,洛克主张自然法是所有的人、立法者以及其他人的永恒的规范,“他们所制定的用来规范其他人的行动的法则,以及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行动,都必须符合于自然法、即上帝的意志,而自然法也就是上帝的意志的一种宣告,并且,既然基本的自然法是为了保护人类,凡是与它相违背的人类的制裁都不会是正确或有效的”。[12]在人类自由的保障方面,除了对立法权权能的限制外,执法权和行政权也被限制在人们羽翼的保护之下。如若发生独裁或专断,人们可以罢免或更换无视委托关系的立法机关或者通过抵抗或革命的方式反对行政机关的行为,如此,人们在“反对压迫性的和否定了自然法的实在法的过程中维护自然法”。[10]可见,仅是规定立法者发现体现自然法理性的制定法对洛克来说难以放心的下,故而将立法者通过的法律交由政府的行政部门予以实施和执行,使两种权力依次由不同的机构来操作,这种观点体现了洛克的良苦用心。从自然法中发现理性的制定法始终成为该时期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而这些所要维护的宗旨无怪乎是权利的保障,只不过学者为解决此问题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迥异。
至此,在法律发现与自然法理性关系问题上,制定法是对自然法思想的表白而非另寻他处的喃喃自语,即自然法是立法者发现法律的场所及渊源所在。近代自然法理论在刚刚完善之时也暗含着某种危机。法国思想家卢梭不仅在对自然法的论述上与其前辈出现了分歧,而且自然法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也遭到了驱逐。在自然状态的性质定位上,无论是霍布斯主张的“战争”状态还是洛克力主的和平状态,他们均都认为“在发现人应该遵从的自然法时都离不开人的理性”。从自然法中发现规制人类生活的制定法也即水到渠成,制定法成为自然法的复制品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自然法理性的崇拜在卢梭理论体系中的定位显然没有市场。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之中的人类,没有正义、非正义和善恶观念,只存在着两条先于“理性”的原理:“一是对于自身的安舒和保护关心,二是对同类遭受不幸或痛苦的怜悯”。理性发展的最终结果是窒息人的天性,扼杀人的自爱心和怜悯心。规制人类生活的行为规则不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了而只得另寻他法。从体现理性的自然法中发现行为规则的做法在这里行不通了。“纵使人们能说出自然法是什么,人们也并不会因此便能更好地了解国家法是什么”。[13]自然法和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勾连在卢梭这里已经完全脱节了,制定法不再是理性自然法的具体化,是“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的结合体,即“社会条件的结合”。与霍布斯所认为的法律是“统治者的命令”的主张不同,卢梭指出法律是“公意的行为”,或“共同意志的确定行为”,是人们根据共同意志而制定的。法律不在仅停留在体现理性自然法层面上的意义表达,转而强调法律的感情因素,如自然法源于人的感情:自保和怜悯,人定法则是人的主观意志。
总之,在理性观念主导下的古典自然法学时期,上帝已经得不到人们的信任。作为法律之前提的宗教基点,也被抛弃了。理性法学者相信,法律背后存在终极价值,如正义的观念,或先验的上位律令,如契约必须被遵守。从这些价值或律令中,就可纯演绎地推导出一切具体的法律律令,而不用考虑时空情况和经验的实际。唯有如此,“人们方能坚信自然法在一切时代对所有的人普遍有效。”所以,这时的法律发现是从终极价值或上位概念中去发现具体的法律规范。向社会输出的是规则,而非具体的判决。显然,这种法律发现是基于“立法”立场的。
当然,遵照古典自然法学的“绝对主义”和唯理性的逻辑路径,实证的法律来自绝对的法伦理,而具体的法律判决又可从实证的法律中推导出来。读者可能会质疑,这难道不是“司法”立场的法律发现?之所以如此强调“立法”立场,乃是因为,从法学演变轨迹来看,法律方法的兴起主要缘于概念法学与自由法学之争。在这之前的阶段,法学要么借力哲学去开启端绪,如古希腊时期,要么被宗教“挟持”,如中世纪,或者凭借理性获得“新生”。所以,这时的主要任务显然是基于法是什么等元问题的思考,至于“法能够用来干什么”尚未成为论证的重点。
三、反思:司法中理性发现法律的期待
已如上述,自然法学派的法律发现观可以概述为,法律是理性的体现,理性为衡量制定法之标尺。它所谋求的乃是从理性或事物的本性中去发现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非历史的普适性的法律。除了国家制定的实在法之外,还存在一种凌驾于实在法之上的超法律的体现人类理性的自然法,这种观点贯穿于近代自然法学派的演变历程。立法者不能任意创造实定法而侧重根据人的理性可以发现出普遍适用的法律。总之,“一句话,相信个人理性发现正义规则的能力,这是一种远离偶然性根植于自然理性秩序之中的正义”。
显然,自然法的这种重视理性的做法,继承了古希腊时期的基因。建立于理性基础之上的自然法,同建立在神学基础之上的自然法形成了呼应。欧洲首次以“宗教改革的方式”打破了宗教的垄断地位。法律将自己的根基摆脱了神学的束缚,转向了世俗化。这种世俗化的“始作俑者”是“伊比利亚半岛自然法学派”。[14]正如叶士朋所言,“自然法中的伊利比亚半岛学派对欧洲法学思想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理性主义、契约论及其他近代法的学派均从这里找到它们的原理。”[14]该学派的形成受阿奎那的影响较大。阿奎那对前人自然法理论的局限有着敏锐的感觉。所以,他主张,“对自然秩序发现并不源于神圣理念的直接观照,也不源于一种抽象的追求,而是源于一种对事实的观察,是我们的经验的有限而不完善的结果”。另外,伊利比亚半岛学派又掺入了许多人文主义的文化成果。所以,这一学派的观点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法的世俗化;二是法根植于人的理性。“个人理性被推崇为法的渊源,成为镌刻着永恒的法律原理的‘第一法典’”。三是法的逻辑化。采用逻辑演绎的方法,既可从法的理性原理中,推导出内容精确、永恒不变的法律规则。以上三点为自然法学派法律发现观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然而,虽说理性被视为法律规则的渊源,但是自然法学派还是在从哪里发现法律这一问题的认定上出现了分歧。比如卢梭将发现法律的场所界定在了人们的“公意”之中,使得从自然法中发现法律的做法戛然而止。自然法和实定法两分的方式是以任意的假设为前提。透过人的理性能够设计出普遍有效的法律制度的全部细节。由此,法学走出了桎梏其发展的神权政治学说的阴影。那种“上帝主宰一切,一切归结为上帝,人法必须服从神法”的法律思想究竟无法抗衡人类理性的力量。这样以来打通了横亘在人类理性和实定法之间的隔阂。古典自然法学派所主张的法律发现,为我们诠释“立法”立场的“法律发现”做了恰当的注脚。然而,这种发现法律的方式也有其内在的隐忧,即对理性的盲从发挥到了极致。虽然后来的卢梭以“公意”和多数决定取代了理性,但是对理性的绝对盲从仍不失为古典自然法发现法律的多数派。这样建立在理念基础之上的法律发现的方式,又忽视了历史实践和社会实际的重要性。历史法学派的法律发现观就是在披露自然法学派不足和缺点的基础上产生的。
其实,自然法学中的上述“隐忧”,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端倪。那时,由于在法的认知上的不同,自然法思维就分裂为两种门径。[15]“一种门径导致自然法纯粹成了用于辩护和解释的工具,并促成了一门哲理法学。这门哲理法学为既定的实在法规范体系提供了各种似是而非的论证理由,并被看作是对理想自然法所作的权威展示,而在理论上,所有实在法仅仅是这种自然法的宣示。”另一种自然法思维也遵循实在法是宣示性的主张,只不过“法律规范并不是对理想道德规范的宣示,而是对习俗的宣示”。由于习俗蕴育于文明社会的经验之中,故而发现的法律,不应是用于道德说教的理想准则,毋应为体现民族精神的大众习俗。
总之,在自然法学看来,法律只不过是“上帝的侍者”或“自然的奴仆”,或仅为“理性的附庸”。所以,这一学派认为,法律是被发现的,但其内容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可是,在法律实践品性的要求下,负载人文精神的抽象价值总是显得有些捉摸不透,难以把握。于是,对它的质疑与批判纷至沓来。虽然我们对自然法学的法律发现观所显露的幼稚与天真进行了无情的嘲笑与讽刺,但是不容否定的是,正是由于对理性的推崇才有了后来的法律法典化,以及对法律的实证化分析。再者,法律发现这个时下更多是从司法角度诠释的术语,也有过存在于立法立场的经历。这也同时说明,法律这个本来在其起源之处就被定义为定纷止争的工具,在经历过了中世纪的神学对它的“绑架”,文艺复兴之后的理性对它的“解放”,概念法学的将其“法典化”,以及社会法学对它所实施的“消解”与“重构”等种种曲折之后,又回到了它的起点。所以,法律发现“立场”的变迁,一则说明了人们对法律概念认识要摆脱静态、抽象层面的分析,转向从具体的实践中去彰显它的丰富内涵;二则在司法的场域中发现法律时,更应有对“理性”的重新认识,和由此所延伸出规则的坚守。毕竟,由“立法”立场所发现出来的法律,有着出于响应某种价值的可能,可以宏观。但是,“司法”立场发现的法律,与诉讼两造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这也就要求法官更加的“理性”和谨慎。
[1]杨日然.法理学[M].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232.
[2][美]罗斯科·庞德著.邓正来译.法律史解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9.
[3][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3.
[4][德]阿图尔·考夫曼,哈斯默尔著.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68,70,79.
[5][德]魏德士著.丁晓春,吴越译.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95,191.
[6]西方法律思想史编写组.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02.
[7]王新举,申永贞.论现代西方主流法学流派对理性的解读[J].广西社会科学,2012,12(3):113.
[8][德]科殷著.林荣远译.法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3.
[9]李钟声.法理学大纲[M].台湾:三民书局,2005:77.
[10][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45,52,62.
[11][英]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31-132,209-201.
[12][英]洛克著.叶启芳,翟菊农译.政府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
[13][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5-46.
[14] [葡]叶士朋著.吕平义,苏健译.欧洲法学史导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54,150.
[15][美]罗斯科·庞德著.陈林林译.法律与道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0-23.
TheViewandEnlightenmentoftheNaturalLawSchoolinLegalFinding
ZHANG Zhi-wen
(ResearchCenterofTrafficLaw,ShandongJiaotongUniversity,JinanShandong250357,China)
In the view of natural law school, the law is the embodiment of reason. Law can only be found, not be created artificially. This point of view of finding law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practice character, this view has lost its market. However, the reason is still chased by the legal fin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judicial.
The natural law school;The legal finding;Legal method;The judicial
2014-05-19
张志文(1980-),男(汉),山东临清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法学理论、法律方法论方面的研究。
D90
A
1671-816X(2014)10-0993-06
(编辑:佘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