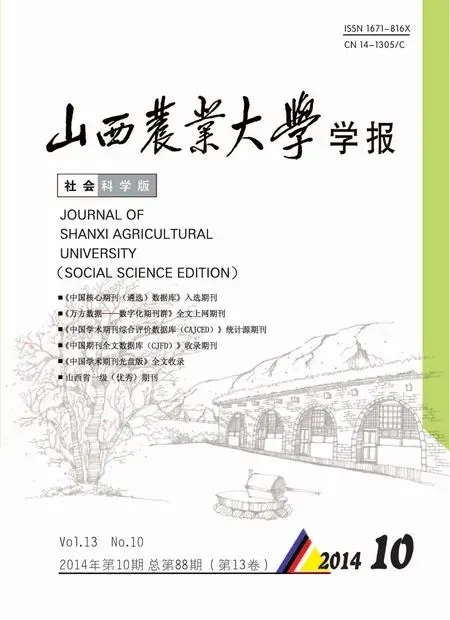社会法治国下的国家形象与国家任务
2014-04-05吴逸越
吴逸越
(中国政法大学 比较法学研究院,北京 100088)
社会法治国下的国家形象与国家任务
吴逸越
(中国政法大学 比较法学研究院,北京 100088)
社会法治国是法治国原则和社会国原则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主要强调国家对人民的积极给付义务。通过梳理社会法治国的发展历程,回顾国家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不同形象、任务及其不完善之处,从而推导出国家在社会法治国的框架下应当具有的新任务,即社会分配和社会发展两个面向。参照中国的现实,当从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国家任务的完成两方面进行着手,完成社会法治国对国家的要求。
社会法治国;国家形象;国家任务
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民主与社会的联邦国家。第28条第1款规定,各州宪法制度必须符合基本法的共和、民主、社会的法治国原则。这两个条文将“社会国”原则确立为德国基本法的一项“国家目标条款”。而“法治国”则起源更早,最初出现时是人民为了对抗君主专制制度而提出的一个口号,与“人治”相对应。1798年,德国著名哲学家普拉西杜斯(J.W.Placidus)首次提出了法治国(Die Rechts-Staats-Lehre)的概念。法治国原则贯穿于德国基本法的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原则。
法治国与社会国作为德国基本法的两项基本原则,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各种力量的作用与博弈,最终形成了社会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德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任务也在不断变化。所谓国家形象,即人民以及国家自身对国家的构想与定位;而国家任务,则是国家的法定职责,是制度层面的要求。
社会法治国由于其漫长的发展历程而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如果脱离这段复杂的发展历程而单独看待这样一种成熟的发展境界,则难以理解其巨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我国的发展也没有太大的借鉴价值。鉴于此,本文先回顾德国从自由法治国、形式法治国到社会法治国的演进过程,分析前两个时期国家作用的不足与完善,通过历史进程的前后对比来勾勒出社会法治国下的国家形象与国家任务。
一、从自由法治国、形式法治国到社会法治国
1798年,普拉西杜斯在其著作《国家学说》中首次提出了法治国(Die Rechts-Staats-Lehre)的概念,其认为:国家首要的、根本的目的在于保证公民的权利和自由。[1]法治国原则的德文写法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渐被固定为Rechtsstaat,这与普拉西杜斯的写法差别并不太大。但是,在德国的实践中却出现了完全不同于原先设想的状况,法治国的发展脉络也经历了从最初偏离目标到逐步回归的过程。
(一)自由法治国
自由法治国是法治国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被塑造成一种消极不作为的形象,其任务被限定为维护社会治安,而不得干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自由。人民有权利自由活动,自由经营,自由竞争。此时的法律虽然规定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但是由于国家处在被动的地位上,因而人民权利的实现并不能得到国家的保障。
放任自由的社会生活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人民表面上的行动自由掩盖了实质上的不自由:社会上弱者的意志受到强者的绑架而无法真实表达,无法真正自由行事,其利益也得不到真正的保护。因此,由于国家的消极被动,自由法治国时期的法律所规定的人民的充分的自由权利实际上是缺乏保障的空头支票,思想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二)形式法治国
这一阶段的法治国倾向于形式化。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对法治国作出了最完整的形式论解释,因此成为形式法治国理论的最重要代表。他认为,“法治国的概念不是指国家的目标和内容,而只是指国家实现目标和内容的形式与方法。”[1]由此可见,法治国的含义在施塔尔这里完全被改写了,法律沦为工具,法治国沦为实现目的的形式。德国行政法的创始人奥托?迈耶(Otto Mayer)对形式法治国理论的构建与完善更是功不可没。他提出,“法治国的所有作用都是以法律的形式决定的”[2]以及“法治国就是经过理性规范的行政法国家”。[2]
我们不排除形式法治国在限制国家机关行为的任意性和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时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形式法治国过分钟爱形式与程序,而忽视了法律条文背后的价值追求。实际上,法律条文对国家行为的各种程序和形式上的限制都只是一种方式与途径,其目的在于防止国家公权力的肆意扩张,其最终落脚点还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而如果将形式作为最终目标,而忽略实质内容,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特别是行政机关在行为时,将“依法行政”作为终极的目标追求,而完全忽略了法律外衣下所保护的人民的充分的自由权利。此时的法治国原则就像是一个贴有标签的空瓶子,而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装进不同的液体。纳粹时期的德国在形式上仍然保持了法治国的面貌,但是其所作所为却与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背道而驰,这也充分说明了形式法治国的弊端,其对人民权利的保护是空洞而容易异化的。
(三)社会法治国
回顾自由法治国和形式法治国,我们发现,两者都背离了普拉西杜斯当初所塑造的国家形象。他提出“法治国”原则时为国家设定的目标是保证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无论是自由法治国对人民的自由放任,还是形式法治国对国家机关行为合法性的严格要求,都不能说涵盖了这一目标的全部范畴,甚至连其主体部分也并未完全包括。保证人民的权利与自由,不仅要求国家不侵害人民的权利,还要求国家积极作为,使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以真正实现。
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法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法治国与社会国的关系问题。“简单的说,社会国就是致力于或应该致力于社会任务的国家。”[3]在法治国原则的大框架下,社会国原则演变成为社会法治国。这使国家重新走向积极:通过积极作为的方式介入人民的社会生活,提供物质资料的给付,为人民实现自身权利提供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才逐渐形成今日的社会法治国的样貌。
二、自由法治国和形式法治国下的国家
在英美国家的“法治”(rule of law)概念中,只有法的统治,不牵涉国家;而在德国的“法治国”(Rechtsstaat)概念中,一直有“国家”(Staat)概念的存在。这是德国独特的国家历史背景的产物,因而,国家在德国的法治发展路径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自由法治国来源于“夜警国家”,[4]其保持着消极中立的幕后形象,对公民社会保持克制,不加干预,奉行无为而治。其主要任务在于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秩序。可见,此时国家的任务比较单一,范围非常狭窄,而且负担的主要是不作为的消极义务,以便让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幸福。但是,随后到来的工业革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遗留下诸多的社会问题,人们之间贫富、强弱分化日益严重,弱者的利益受到侵害。而由于国家保持消极中立的态度,便也无法调节社会矛盾,保护弱者的利益。
在形式法治国中,极其重视国家行为的形式与程序。人们期望国家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也因此而进行了制度上的设计,要求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外观。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纳粹教训也说明,国家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可能会披着法律的外衣,进行许多对人民非常不利的措施,因而光有合法性的外观是远远不够的。
在自由法治国和形式法治国中,国家均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与市民社会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划分。实际上,此时的人民也处在被动的地位上,即他们无法主动要求国家对自己进行给付或者是要求国家帮助自己实现权利,而只有在受到国家的侵害时才能被动地要求国家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或者赔偿损失,人民幸福的实现只能依靠自身。此时便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国家与人民双方均处在被动的地位上。进一步说,即国家与人民尽可能地互不干涉,希望能明确地划清相互之间的界限,撇清相互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禁要质疑:此时的国家究竟有多大价值?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何在?这与社会契约的理论以及国家的根本价值是相背离的。法国大革命的先驱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曾指出,“由于每个人都是把自己奉献给全体而不是奉献给任何一个个人,由于每个人都能从其他结合者那里得到与他转让的权利相同的权利,所以每个人都得到了他失去的东西的等价物,并获得了更多的保护其所有物的力量。[5]而在自由法治国和形式法治国中,人民无法从国家那里得到相应的等价物,更不用说更多的力量,而只能要求国家对自己的利益不加侵害。这明显是一种互相不对等的状况。这与法治国的概念提出之初,普拉西杜斯所提出的“国家首要的也是根本的目的在于保证公民的权利和自由”[1]也是不相符合的。日本学者大木雅夫教授在分析了德国自由法治国和形式法治国的弊端后,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机关的任务不只是自由放任和保护,而是必须在国民生活各个领域中积极发挥并干涉计划、分配和形成成功的境界。”[6]
三、社会法治国下的国家
相比而言,社会法治国下国家的形象与任务均发生了变化。其主要的就是国家要积极地予以给付,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在行政法的范围内,这就是给付行政的概念了。正如康德拉?黑塞(Konard Hesse)教授所说,“现代行政已经突破和超越了‘侵害型行政’这种传统的范围,更多地发展成了一种‘给付型行政’。它承担了涵盖广泛的计划性的行为、社会救济与社会保障的义务。”[7]
台湾学者许育典将社会国的内涵划分为社会形成、社会安全和社会正义三个方面。[3]目前我国关于社会法治国下国家的任务的讨论也主要限于对人的基本生存问题的保障,突出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要求国家为他们提供一个符合基本人性尊严的生存条件。[8]但是,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面向。诚然,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是最迫切需要保护的对象,但是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弱势群体以外的其他绝大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应该只是社会法治国下国家任务的一个面向,而国家的任务还应该包括一个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的面向,以保证整个社会有更高的发展。
当然,国家不可能对每一个公民的所有个人幸福负责。幸福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对一部分人来说幸福的事,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可能就是枷锁。因此,国家不可能按照统一的标准打造出每个人相同的幸福生活。但是,有一些领域虽然已经超出了保障基本生活的范围,却也是每一个公民都需要的,如基本教育、医疗保障、环境保护等。国家可以在这些方面推进全社会的共同进步。因此,笔者将社会法治国下国家的任务分为社会分配和社会发展两个层面。
(一)社会分配
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保证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拥有符合人性尊严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这是社会分配的内涵,也是社会法治国下国家任务的最低限度。此时的国家,有义务积极地介入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不断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帮扶,以消除自由市场所带来的弊端;有义务通过建立各种设施与机构来保障社会的安全,以及弱势群体在陷入困境时可以通过这些业已建成的社会救助机构得到援助,以实现符合人性尊严地生活;有义务通过国家权力的杠杆,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分化,保障底层人民生活、医疗、教育等方面,同时通过税收的杠杆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从而调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社会发展
以上关于社会分配的种种措施都是社会财富的各种不同的分配方式。简单的说,就是将钱从一边口袋拿到另一边口袋。并没有在总体上提升国家的实力,从而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由于国家的积极给付义务直接地加重了国家的负担,而国家的财政能力是有限的,只能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落实社会法治国原则赋予国家的任务。因此,德国在落实社会国原则的时候非常谨慎,小心翼翼地界定国家积极给付的范围,防止国家承受过大的财政压力。
在这样一种条件下,需要提防一个危险:那就是国家的积极给付可能会沦为一个口号,得不到实质的落实。国家可能会以经济实力尚未达到相应水平、财政能力有限等理由来拒绝进行积极的国家给付。如果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那社会法治国则又倒退到了自由法治国时的情景:国家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充分的权利,但是无法保证实施,仅有形式,缺乏实质内容。因而,国家积极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对公民进行积极给付的能力等一系列活动也应该是实现公民社会基本权的应有之义,是社会法治国下国家的一项新的重要任务。
根据台湾学者翁岳生的表述,“行政是追求利益的国家作用。行政乃实现国家目的之一切国家作用,而所谓国家目的者,具体言之,即指公共利益或公共福祉而言,是以,追求公益可谓是行政的一项重要特征。”[9]可见,行政机关负有发展国家实力,提高经济水平的责任。从此处看来,即为履行社会发展的任务。
此时出现一个问题。社会法治国下赋予人民社会基本权,“与公民居于消极地位的自由权不同,社会基本权是公民居于积极地位,要求国家为积极给付的权利,是基本权的积极面向。”[10]而传统的自由基本权则是一种消极权利,二者之间必可避免地会出现一种紧张的关系。“社会基本权要求国家采取积极的经济干预措施,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国家对政治、社会的高度控制,侵犯私人自治领域,为权力‘假借社会正义、群体自由之名目,行剥夺个人自由之实’留下可乘之机。”[11]此时,为避免这一危险,必须将社会法治国下国家的积极作为范围限定为某些不太关系公民自我个性发展并且市民社会自身无法有效调节和完善的领域,如基本教育、医疗保障、社会救济、环境保护等。
四、我国法治观念下的国家形象与国家任务
反观中国,虽然没有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但是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各有明确的职责划分。而由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职责较为明确和固定,在此,笔者将以行政机关作为研究问题的切入点,从社会法治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行政现状。在中国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行政诉讼唯一审查的要素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行政复议审查的要素也仅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无论合法性还是合理性,都只是将人们放在被动的地位上,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有没有对人民的利益造成积极的侵害。这样的行政法实践,显然已经不符合现代的国家形象。在我国的行政法学领域中,对给付行政已经相当强调,而且德国的社会法治国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模仿的范本。因此,行政实践也当实现“从‘依法律行政’到‘法治行政’的转变”。[12]笔者认为,在社会法治国下,我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国家任务的完成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的塑造包含了人民对国家职能履行的要求与期待。现在我国人民对国家的期待绝对不只限于希望国家保持消极克制或者要求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外观,而是在应对社会贫富严重分化、自然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方面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希望国家能够积极作用,发挥行政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有学者在国家法治形象的塑造方面提出了“善治政府”,要求“公共治理更多协商、更少强制,更多参与、更少命令,强调规制方式的柔性化和非强制化。”[13]善治政府要求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更多的互动,决策时更多地民主协商,这也体现了实质正义的理论,有助于塑造亲民的国家形象。
(二)国家任务
国家任务即国家的法定职责,是其在制度层面上的固化。在我国的法律中,并没有规定国家的社会给付等义务,但是我国的国家机关已经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这实际上就是社会法治国范畴下的社会给付。而且我国政府还在强调要进一步发展经济,使更多的人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可见,他们也正在社会发展层面上进行努力。既然这样的行为已经做出,人民已经从中得到了利益,那么就不应该让其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而应在法律中将其规定下来。社会给付不仅仅是国家机关的政绩,更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这样以立法督促行政,将减小国家机关行为的随意性,提高其效率与成果。
五、结语
德国法治国的发展历程向我国展示了一条法治发展的经典路径,那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必须从消极逐渐走向积极,积极进行给付,积极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条件。然而,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历史阶段的局限性是无法逃脱与忽略的现实困境。德国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实现了从自由法治国到社会法治国的转变,而我国的法治建设才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因此,我们无法跳出现实的局限,要求中国的现状与德国经过了一百多年发展并且已经高度成熟的社会法治国相媲美。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法治发展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避免其犯过的错误、走过的弯路,向着社会法治国的正确方向迈进。
[1]郑永流.法治四章:英德渊源、国际标准和中国问题[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83,102,83.
[2][德]奥托·迈耶著.刘飞译.德国行政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61.
[3]许育典.宪法[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1:75, 77-78.
[4]赵宏.社会国与公民的社会基本权——基本权利在社会国下的拓展与限定[J].比较法研究,2010(5):17-30.
[5][法]卢梭著.李平沤译.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9.
[6][日]大木雅夫著.华夏,战宪斌译.东西方的法观念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5.
[7][德]康拉德·黑塞著.李辉译.联邦德国宪法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66-167.
[8]龙晟.社会国的宪法意义[J].环球法律评论,2010(3):47-58.
[9]翁岳生.行政法(上册)[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14-15.
[10]Sachs. Grundgesetz Kommentar[M]. München: C. H. Beck, 2009: 743.
[11]徐振东.社会基本权理论体系的建构[J].法律科学,2006(3):22-37.
[12]赵宏.法治与行政——德国行政法在法治国背景下的展开[J].行政法学研究,2007(2):128-134.
[13]韩春晖.从行政国家到法治政府——我国行政法中的国家形象研究[J].中国法学,2010(6):61-76.
NationalImagesandNationalMissionsunderSocialStateofRuleofLaw
WU Yi-yue
(CollegeofComparativeLaw,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Beijing100088,China)
Social state of rule of law is the produ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rinciple of rule of law and the principle of social state, whose main emphasis is on the national positive obligation to the people. By combing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tate of rule of law, the paper recalls the different images, tasks and imperfections of countries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to derive new national tasks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social state of rule of law, namely social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concludes it is necessary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state of rule of law to the countries in 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images and accomplishing the national missions by referring to China's reality.
Social state of rule of law; National images; National missions
2014-06-14
吴逸越(1991-),男(汉),安徽六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德比较法方面的研究。
D911
A
1671-816X(2014)10-0978-05
(编辑:佘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