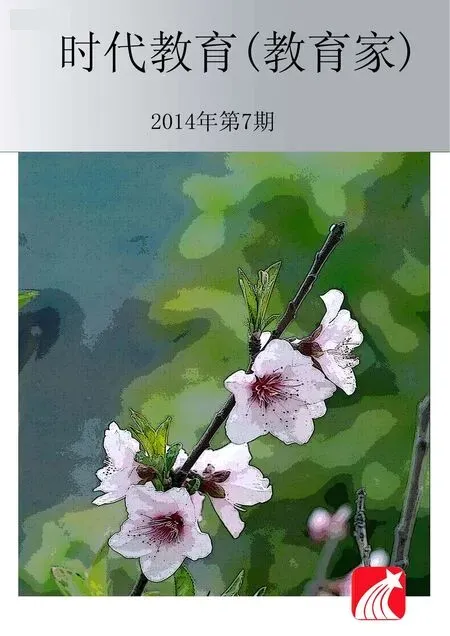叶开:自编教材,对抗语文
2014-04-04撰文李星言摄影陈征
撰文_李星言 摄影_陈征
叶开:自编教材,对抗语文
撰文_李星言 摄影_陈征

2011年,有感于现行语文教材脱离当代文学创作的现状,《收获》杂志副编审,倡导语文教学改革的叶开出版《对抗语文》。紧接着,他决定为中小学生编一套语文教材。不久前,这套名为《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出版。叶开编教材,力图打破业内“教材是严肃的、不是随便谁都可以编写的”这样的固化思想,将一直以来被“陌生化”、“神秘化”、“艰深化”的语文教材编写变成一项光明而坦荡的事业。他将自己比作“一块砖头”,希望“把一些豪杰从水里砸出来”,让更多的人关注语文、关注教育。
他的探索引起了一些争论,誉者称其为“中国语文教育的改革者”,毁者却称其“不懂语文”。
从“考霸”到语文教师
叶开出生在广东的一个小县城,童年时他上树掏鸟蛋,下海捉小鱼,在乡村中学读书,经常几门课加一块也没超过100分。这事在同学中并不稀奇,混到毕业直接打工的大有人在。
但叶开碰到了一位“活宝”语文老师。老师姓吴,不太“安分”,上个世纪70年代就偷偷弄了部卡车跑运输,生意没做起来,便又回来教书,很有点特立独行的做派。得知叶开考砸了,他破天荒地把叶开叫来,一本正经地问他:“你去过县城吗?喜欢吗?”,叶开点点头,去过,挺好玩。
“那你去过湛江市吗?”叶开想了想,去过一次,车很多。
“那你去过广州吗?”叶开摇摇头。吴老师笑笑,夸张地比划了一下:“我去过广州,满街的山珍海味,还有漂亮的姑娘们!”
再问,“你去过北京吗?”叶开摇摇头。
吴老师笑意更深,“我也没去过,特别想去,可是年纪大了,没机会了。”说罢,正色相告:“你好好读书,一定要考上大学,到更大的天地去看看。”
或许是少年的斗志被激发,或许是对世界的好奇被唤醒,很多年后,叶开坦言,自己正是被吴老师的这句话改变了一生。
“父母开通,买了四大名著连环画,我的阅读很早,虽然与当下的孩子阅读无法相比,但是与同龄人相比,我的阅读比他们超前,在之后的学习当中,我从来不做作业,因为有大量的阅读积累,再加学会了一些应试技巧,考试对我而言易如反掌。”
一努力,就考了全班第一;一努力,就成了高中补习班里的佼佼者,谁都不清楚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农村娃成为“考霸”,但叶开心里知道,他离这个世界越来越近。
一转眼就到了高考时节,“当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很厉害,报考志愿时我看招生海报,先被一个乐呵呵的老头吸引,他是中文系钱谷融教授,接着被另一个人吸引了,他是王建磐教授。海报介绍说他原是福建一个小木工,没上大学本科,自学了高等数学直接考取数学系硕士研究生。我一看‘哇哇’得不得了,这是屌丝奋斗成大神的鲜活偶像啊!”
于是,叶开成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一员。
1991年大学毕业时,叶开原本已经定了回湛江医学院基础部教语文。那年6月,他一直崇拜的作家马原来到了上海,在作家格非宿舍里聊天时,当得知叶开毕业后去向时,马原当即说“你热爱写作,必须留上海,你随便找个地方吧!”
又是一句话改变命运,叶开决心留下来。那时分配已经结束,只剩偏远的、位于闵行区的上海电机专科学校基础部还有个名额。
回忆起那段并不快乐的日子,叶开笑了,“很多人质疑我没当过语文老师却总是质疑语文教育,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正儿八经当过几年语文老师。”
当时,在工科学校当语文老师,让踌躇满志的叶开自觉“比创可贴还没用”,他瞧不上教材,常常把书一丢,用自己的方式为学生讲课,每每博得学生满堂彩,成绩也不错。
但他的狂傲和革新也引来了质疑, 1994年,他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结束了短暂的教师生涯。
回忆往昔,叶开自认当年的自己确实年少气盛,但他并不后悔,甚至觉得如今的学生往往少了这份血性。“年少就应该气盛,要是年纪轻轻就老于世故,那不就成了早衰?心要开阔点,想着世界,别总想着买车买房混吃等死。”
育儿:阅读经典才是学习语文的关键
叶开与太太都是华东师大的文学博士,可以说是真正的“学霸”,是“考试一流人才”,但在他看来,考试其实是人生中的次要能力,是一种低级技能,它只能说明你在学校很成功,并不意味着你在社会上同样很厉害。从自己的经验来看,就语文学习而言,大量阅读经典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才是最根本的。
因为自己的这些人生体验,叶开将之用在了女儿身上,“别的父母在教孩子认字的时候,我教孩子大量有效的阅读,别的家长在炫耀孩子认识汉字的数量的时候,我的孩子已经能够阅读大部头的小说了”。
女儿在幼儿园阶段从来没有学过字,也几乎不报各种兴趣班,周末与节假日都是带着孩子满世界游玩。“幼儿阶段,保持孩子空一点的内心很重要,所以,我这个阶段会推荐多读一些幻想类作品,多读一些动物小说,让孩子的想象力与思维能够打开,能够感受到语言的节奏,养成独立思考能力、表达能力与写作能力。”叶开强调,要顺应孩子的思维,适当地引导,“我觉得培养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比培养一个超人更重要。”
可女儿入学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叶开发现,由太太辅导三年级女儿做的语文作业,第二天拿回家后,上面经常红红地一大片叉,乔乔觉得挺委屈。
在学到《智烧敌舰》时,题目要求她回答三国时期最足智多谋的人是谁。因为刚看完《三国演义》彩图本,乔乔自信地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孔明和庞统”。这个答案也得到了妈妈的认可。没想到标准答案是“诸葛亮”,语文老师说,在小学阶段答案只能写诸葛亮或周瑜,写孔明也算错。
这是叶开第一次被孩子的语文教育刺痛。
这阶段,写作文成了语文课上的重头戏,同学们开始读“优秀作文选”,可乔乔看也不想看。语文课本也让她“一点都不喜欢”。她更不喜欢的是书包里的教辅书《一课一练》,这占据了她课后很多时间。
为此,叶开拿起乔乔的语文课本,试图弄清问题所在。结果一打开课本,他发现一些不说“真话”的作家的作品,不仅进了女儿的教材,“而且还要背诵”。更糟糕的是,一些原本是经典的作品,到了教材里被改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他正冒火,转身却发现乔乔抱着《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目不转睛地读着。为了考验女儿,他刻意跟乔乔聊起《哈利·波特》和四大名著彩图本,结果发现里面很多故事和细节,乔乔记得特别清楚。
“这说明她不是胡乱读,是真读懂了,女儿的阅读理解完全没问题。”
叶开把乔乔的几本语文教材全都仔细看了一遍。2008年11月,他写了第一篇批判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文章《语文的物化》。在文章中他写道:“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入了很多与花草树木有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作者不是欣赏鲜花自身的美丽,而是在鲜花这个符号上寻找道德寓意。”
这些“火药味儿很浓”的文章发表了两期后,一位语文特级教师就打电话给晓苏,质问道:“哪儿来一个疯子在这儿胡说八道?”
当时9岁的乔乔看了爸爸的文章,咯咯直笑。“我们都不喜欢语文课本。他写得太好玩了。”她评价道。
暑假时,叶开给女儿启动了“倒垃圾”计划,“孩子在学校学了半个学期的语文,肚子里装的都是垃圾,我们利用假期给她倒出来。”
“倒垃圾”的方法,则是给孩子买经典作品阅读。在意识到孩子语文教材中的问题后,叶开给女儿买了一个四层的书架,书架上多了《哈利·波特与密室》等《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续集,也有了《窗边的小豆豆》、《唐诗三百首》等名著。
而这也成为促发叶开编写《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的最直接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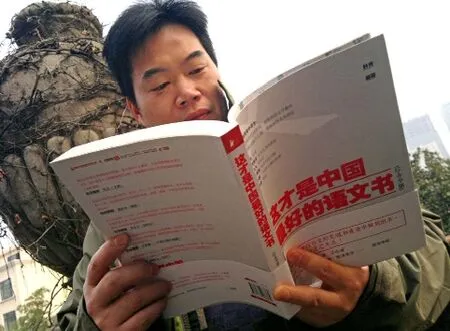
“夫物芸芸,复归其根。”这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叶开很喜欢。在他看来,对孩子的教育就像这句话所表达的一样,要回归到生命的本源,尽力去呵护孩子的本真。
在孩子12岁之前,与识字、背书等能力相比,叶开更重视好奇心、想象力的培养。不过最近两年,随着女儿阅历的丰富,叶开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对还有一年就要面临中考的女儿开玩笑:“人生就是妥协的过程,凭借多年丰富、有效的阅读,再掌握一点应试技巧,你只要在语文考试上稍微出卖一点灵魂,应付语文考试几乎可以说居高临下,势如破竹。”
80后父母有更敏锐的思考
早在《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启动之前,叶开写作了《对抗语文》,努力推动语文教育改革。
在叶开看来,即便现在的教材有了一定意义上的“分流”,出现了“北师大版”、“吉教版”、“苏教版”、“沪教版”,等等,但这样的分流非但摆脱不了“人教版”所形成的固定形式,还有很多“假大空”和“可笑”的文章夹杂在其中。
令叶开不解的是,有很多很优秀的爱国主义文章,没有被收进教科书中,“比如我的书中收录的巴金先生的《西湖》,写了与西湖有关的英雄,岳飞、秋瑾……这难道不是爱国主义吗?这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维护,是对外族侵略的抗争,这都是爱国。”
除了对文章的选取不满,叶开还对某些版本教材编写者的编辑水平提出了质疑,“像沪教版语文教材里一篇名为《带刺的朋友》的文章,本来想表达主人公与刺猬之间的感情,在经过上海语文教材编写者的低级删改之后,一些必要的细节没有了,文章也变得不合理了。”
经过多年对中小学教育的观察,叶开发现,80后伴随网络长大的父母在对待子女教育方面,呈现出与父辈不同的特点。他们更有敏锐的思考,也对传统的教育有一些不认同的地方,这反过来触动了他们寻找新可能性的内心冲动。这让叶开感到欣慰,这让他看到了中国教育“变好”的可能。
让语文教材闪现人性光辉
在《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中,叶开精心选入了众多中国作家以及外国作家的优秀作品,并在每篇文章后面专门写了段赏析解读的小文。
该书共有四册,此次出版的是“当代小说”分册和综合分册,前者适合初中高年级和高中生,后者是为小学高年级学生和初中生编撰。
“当代小说”分册分为“学校”、“时代”、“人物”、“历史”、“少年”、“科幻”六个部分,选入王安忆、苏童、余华等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
综合分册分为“幻想”、“文学变形记”、“动物”、“人与事”四个部分,选入巴金、梁实秋、王小波等作家的作品,以及卡夫卡、E.B.怀特、宫泽贤治等外国作家作品。
此外,与现行语文教材的编写方式不同,这套书的体例比较特别,而这也是叶开认为整个构思过程中最下功夫的地方,“采取了一种进阶阅读与写作的指导”。
以小说分册为例,每篇文章前,有详细的作家介绍及精短的阅读提示;正文中则采取了类似批注的形式,不时插入分析,提请读者注意此处的精彩用词、人物塑造手法、情节叙述等的阅读引导;文章结束后,则会有一两千字的整体分析思考与发散性提问,引导读者体会如何在写作中留有适当的想象空间,学会处理“戏剧化”场景,尝试运用精妙的比喻,掌握平实的叙事基调,学会在思辨中进行思考。最后,还辅以“延伸阅读”板块,推荐作家的其他经典作品作为扩展阅读。
叶开表示:“只要文字不错,言之有理,都可以进入我的选材范围。”

暑假时,叶开给女儿启动了“倒垃圾”计划,“孩子在学校学了半个学期的语文,肚子里装的都是垃圾,我们利用假期给她倒出来。”
在刚刚编好尚未出版的散文分册里,叶开甚至选入了一篇网文《孙悟空的师父到底是谁》。《宇宙尽头的餐馆》等好几篇课文甚至是叶开还在上初中的女儿帮着选出的,“女儿太喜欢马文和蛙星机器人的聊天大战了,把文章指给我看,我看了捧腹大笑也很喜欢,就选入了”。叶开还在新书中选入了四篇名家中篇小说,这在传统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里也从未有过,“从来没规定说课本不能选中篇小说”。
叶开觉得,孩子在“学习的黄金时代”中只读到现行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太遗憾了,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本书,让孩子知道教材之外还有更多更杰出的作品与更大的世界,这些作品充满着“人性”、“人道主义”的光辉,贴近普通人的生活与灵魂,容易引发共鸣。
叶开说:“中国的语文教材有自己的发行体系,我并不奢望我的书能进入孩子们每天的课堂,但我希望有更多教授、作家跟我一样,试着独立为孩子们写写语文书。我认为,现在的很多课文承担着政治教化之类的作用,完全脱离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现实,极大误导了学生。”
在他看来,编这套语文书的最大目标不是“打击”现行语文教育模式,而是给有心的家长和有反思精神的语文教师提供一种新的选择,一个不同的视角。
2012年,杭州语文名师、越读馆创办人郭初阳在上海师大举办的活动上第一次见到叶开。郭初阳认为,语文老师或多或少带有一些谨小慎微的匠气,而叶开则有一种大开大豁的天然本真,文学的核心是自由、是自然,叶开散发着一种自然而蓬勃向上的力量。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语文老师杨林柯也已关注到叶开博客中对语文教育的批判,认为他说得很到位。
叶开喜欢发一些有关语文教育的微博,让这些一线教师关注讨论。在杨林柯看来,叶开通过这种方式也参与了语文教师的成长,让教师们分享他的思考与智慧。杨林柯认为,叶开所做的许多事情对中国教育非常有价值,希望有更多的叶开来参与语文教育教学。“叶开和我的教育理念一致,就是希望通过阅读提升语文素养,而非通过糟糕的语文训练题。我觉得这一点抓住了根本。”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语文老师樊阳认为,现行语文教材中不乏一些二、三流作家“不痛不痒的小散文”,质量不高、意义不大,有些比较有思想有追求的语文老师索性直接略过,而叶开选择的篇目就比较有意义、有趣味,文字优美,阅读面更广泛。 “书中的文学名篇部分学生开始接触时可能会有阅读困难,需老师引导,但部分老师可能都不知道宫泽贤治是谁,也就无法理解作者选篇的目的,所以这套书的推出也有助于促使语文老师提高自身素养。”
“现在的家长都是70后甚至80后,不少人愿意让孩子尝试这些语文教育的新形式,这和以前50后、60后的家长不同。”郭初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