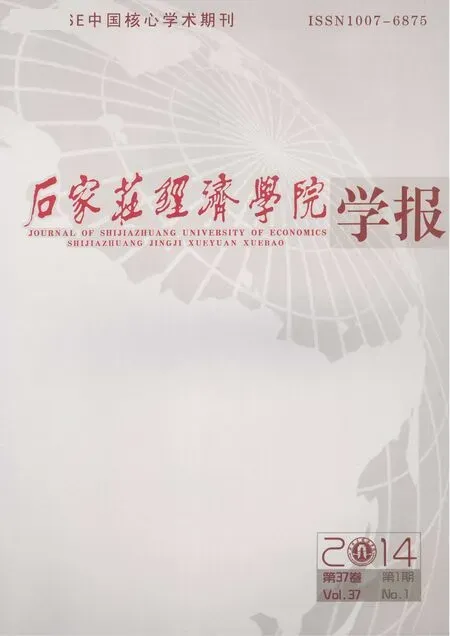从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中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2014-04-04陶征
陶 征
(青岛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山东 青岛 266000 )
从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中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陶 征
(青岛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山东 青岛 266000 )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很多人认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导致了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逻辑矛盾,我们之所以从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中去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去解释和解决这一逻辑矛盾。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逻辑矛盾;抽象;具体;价值
一、马克思理论体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逻辑矛盾的提出
马克思在建立劳动价值论时指出,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里他也坚决地排斥“需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但当他对社会生产的比例关系进行解释时又不得不引入需求这一因素,这就导致了马克思理论体系上一个显著的逻辑矛盾。一方面坚决地否定需求对价值决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解释社会大生产中的价值决定问题,又不得不引入需求、竞争等因素。既然否定需求与价值的关系,为何在这里又引入?许多理论工作者要么局限于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忽视了价格理论的发展;要么试图丰富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内涵,将需求与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联系起来,这不仅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反而会使问题复杂化。对于局限于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人,他们认为两种含义是同一的,不存在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决定也仅认为是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起作用,但这种观点只能回答供求均衡条件下的价值决定问题,当供求不一致时,它就无法解释此问题。因为在供大于求的状态时,社会生产就会产生过剩的产品,而这种过剩的产品是不被社会所吸纳的。对于试图丰富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人,都想通过丰富其内涵来解决这一内在矛盾,他们认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统一于商品生产和交换上的,并且共同对价值决定起作用,后者对价值决定起主导作用,表现为价格随着供求的变换而有所变动。当供大于求时,价格就会下降,反之亦然。这种上下波动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实现变动之前,价值究竟怎样决定?在实现变动之后,生产条件也会发生变动,这时它们对价值决定的影响肯定也会变化。所以无论是“同一论”还是“统一论”都不能合理地解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更不能很好地去解决这种内在的逻辑矛盾。为此当代很多学者提出“交换价值论”,樊纲先生首先在《“苏联范式”批判》[1]中明确指出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导致马克思理论体系严重的逻辑矛盾,但他同时提出自己的观点即以“交换价值论”为支点对其矛盾缺陷进行修复,他认为“有了‘交换价值理论’,马克思没有必要提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这一理论出发,劳动决定价值,需求决定使用价值,而价值和使用价值二者一起决定的是价格即交换价值,而不是决定价值本身。劳动价值论本身根本不需要混同于‘需求决定价值’的理论,同时劳动价值论也完全可以同需求决定价格的价格理论并行不悖。因为价值并不等于价格,价值是为生产一物所付出的劳动,而价格只是一种物的交换比例,在它当中包含着劳动的交换比例。”[1]这里樊纲先生所指出的“交换价值论”是以交换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价格来解释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价格与价值的区别所在”[2],但是这一理论仅试图通过强化价格的作用来解释价值的决定问题是需待商榷的。樊纲先生虽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但他并没有详尽的指出什么样的劳动决定价值,对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也没有针对性的进行区别分析,实际上非生产性劳动是否创造价值至今还是颇具争议的。这里所讲的需求决定使用价值也太过片面,因为使用价值是指商品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即商品的有用性,它强调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反映的是一种自然属性,而不能简单理解为需求就完全决定使用价值,这样“交换价值论”也不能很好的来解释和解决这一问题。上述几种解释之所以解决不了这一逻辑矛盾是因为他们都忽视了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本质关系,所以只有揭示出它们的内在含义与本质联系,才能更好地去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
二、从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中去解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逻辑矛盾
抽象与具体,是《资本论》逻辑中一对十分重要的范畴,它也是辩证思维的高级形式,对辩证思维而言,这包括两个过程即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和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探寻它们的含义不仅有利于理解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更有利于加深我们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的理解。首先我们来看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怎么描述的。
引文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3]
引文二:“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和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相互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4]
引文三:“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需要只有这么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5]
引文四:“商品价值的性质,即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一般来说在市场价格的形式上,进一步说,就是在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6]
上述四段引文,分别被有关学者列为马克思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几种解释,多年来理论界也都将第一种解释称作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第二、三、四种解释称作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认为: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不是分析某个单一商品价值决定问题也不是分析某种商品价值决定,而是表达和说明作为思维抽象的商品及其价值决定问题,是在说明商品价值决定的本质规定和科学内涵。所以这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就是指价值决定的这个“抽象规定”,也就是说这里它是指一个抽象的“时间一般”。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指各个特殊领域的商品之间比例关系及其价值的调节问题,是根据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在确定了“时间一般”之后,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具体化之后的一个概念。从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方法论中去来看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两组概念的本质关系。
1.从本体论来看,客观的一切事物都是抽象方面和具体方面的辩证统一,它们都是一切事物所具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抽象和具体的辩证统一。我们应该看到,抽象的、一般的方面是客观上存在的,所以在认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不仅要把它从具体的、个别之中抽象出来,同时也要将供求、竞争等因素加入进去,从而使之具体化。
首先从它的抽象方面来看,此条件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马克思在考察“资本的生产过程”时提出来的,并且尚未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进行考察(这里也舍弃了竞争、供求等因素的影响),这里也是在假定生产条件或者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提出的。引文一中明确指出“是在现有的正常生产条件和现有的平均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条件下的生产,这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默认为商品的生产总量恰好满足商品的需求总量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考察资本的生产、流通和再生产时候都是假定商品是按照价值出售的,若是商品是按照其价值出售那就意味着商品能实现其价值,也就是说商品是供需一致的。
其次从具体方面来看,此条件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时提出的,这里也考虑到了竞争、供求等因素。从引文二和引文三中可以得知,马克思此时的论述无非想说明一点,那就是只有当全部产品按照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才能卖出去。各种商品都按照社会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进行生产时,才能实现其价值,但若是这个比例破坏了,商品不按照需要的比例量来进行生产,这时虽然在这个商品的总产品生产中体现了一定条件下的为生产这个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但总的来说,商品的一部分已经不能被社会所吸纳,成为剩余或者过多的了,产品的一部分也没有了用处,所以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么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从引文四我们得知,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不是某个生产者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与市场供求相一致前提下的一个概念。这里的供求一致与引文二、引文三中所讲的按照比例分配生产实际上是一回事。所以,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非一个是从抽象的劳动时间一般,一个是从具体的劳动时间个别来进行解释。我们把它们看成两种含义是不准确的,这都是对抽象与具体辩证关系的不理解,都是对马克思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不理解。
2.从认识论来看,从抽象到具体是认识论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们这里不能仅将两组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成两种静态的、相互区别的概念,当然也不能完全将其等同于同一种概念,而是应该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或者可以这样理解“从前一个认识阶段中通过分析揭示出来的抽象的即简单的、片面的、贫乏的规定性,通过综合复制,再现出认识对象的整体,在这里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抽象的和具体的两组概念是同一逻辑认识发展的两个不同层次和阶段的关系。”[7]从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三个阶段中来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第一阶段:“商品直接以劳动力为基础的交换。在此阶段商品交换还具有偶然性,在其交换过程中是按照这些商品的劳动时间作为一种交换尺度来决定其交换间的比例关系。”[8]
第二阶段:“商品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换。在此阶段商品以价值为基础进行交换,其核心就是一般等价物向金属货币的过渡。马克思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称之为‘商品的惊险跳跃’,同时这一过渡也掩盖了商品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商品交换也不再是偶然现象,对生产者而言他们也是按照其社会上一定的需求条件来进行生产的,所以这时候货币已经成为决定性的价值尺度。”[9]
第三阶段:“商品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交换。生产价格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但是生产价格这个概念产生之后就掩盖了价值的本质,市场价格也不再按照商品的价值上下波动而是转变成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10]
从抽象方面来看,马克思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论述,正是对商品生产和交换本质的概括,它是撇开了一切体现不同发展阶段的非本质的特点。马克思指出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尽管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千差万别,但在这里它是作为同一人的劳动来看待的,每一个劳动力与其他劳动力一样从质上讲都是同一人类劳动。我们抽象出等质的劳动来对商品生产进行本质上的规定,这就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过程,是从个别归纳出来的一般。
从具体方面来看,商品交换的三个阶段正是马克思从具体的角度去分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通过对几个阶段历史的、具体的考察,我们发现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当从第一阶段上升到第三阶段时,我们的考察也从以劳动力为基础的交换上升到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阶段,而这些阶段的特点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般在这些阶段上分别呈现出来的不同特点,这是一个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个别。
综上所述,《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论述是着眼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它们实际上具有内在本质联系,是一种由抽象到具体、一般到个别的关系,两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我们从抽象和具体的辩证角度去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对我们解决马克思理论体系逻辑矛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前面中提到的“同一论”、“统一论”以及“交换价值论”之所以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逻辑矛盾,是因为他们都是孤立的、片面的去强调某一方的作用,更或者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来补充和解释,但当通过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思维去理解它时,我们发现它是一种动态的、全面的含义,这里没有刻意强调某一方的作用,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发展的概念来进行研究,这就解释了马克思理论体系不仅没有逻辑矛盾,反而更体现了它的与时俱进。
三、逻辑矛盾解决的现实意义
通过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分析,得知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际上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过程的全社会内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的问题,这也是部门之间平均化的结果。承认社会需要对价值本身有影响,但并不意味着承认了“需求决定论”是正确的,我们也不否认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但这里还必须继续推进。其实按照马克思的逻辑,他并没有把价值决定问题限制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为什么这么理解呢?按照马克思严密的逻辑体系和辩证的叙述方法,他在论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最初阶段上实际上是默认供求平衡的并将供求抽象掉,为的就是纯粹的理论分析,在这里他考察的也是单个商品价值决定而非总产品的价值决定。后来他所提出的按照社会一定比例分配生产实际上是在最初阶段的基础上将需求因素拿回来,拿回来的过程就是具体化的过程,这不仅是本体论概念的一种推进更是认识论上的一个新的阶段。所以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发展,这样我们就很好地解释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中的这一逻辑矛盾。当我们理清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的时候,也就能正确的理解它们与决定价值的关系,即前者决定市场价值,后者制约价值的实现程度。
正确理解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本质,这对于指导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当前经济的发展也更多的依赖市场的调节作用,市场调节作为一种“无形的手”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简单的市场运行来看,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按照价值规律来运行,通过调节供需关系,使商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交换,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整个国家的运行来看,我们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和适当干预来保持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合理。一方面按照马克思的“价值决定理论”,价值是在供求平衡条件下处在中等生产条件和中等劳动强度下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就要求我们为提高商品的价值,就应该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的生产条件。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的“价值实现理论”,价值是一个在全社会范围内按照比例分配劳动时间的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个小孩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11]这就要求我们为满足各种需求必须把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到不同生产上。所以只有真正搞清楚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内在含义,才能理清它们与价值决定的关系,同时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理论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发展。
〔1〕 郭京龙,李翠玲.聚焦劳动价值论在中国理论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114,115.
〔2〕 樊纲.苏联范式批判[J].经济研究,1995(10):70-80.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2.
〔4〕〔5〕〔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16,717,716.
〔7〕 刘烔忠.资本论方法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220.
〔8〕〔9〕〔10〕 丛松日.从方法论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J].江苏社会科学,1991(2):18-19.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8.
(责任编辑 吴 星)
Understand the Necessary Labor-time of Society Based on Abstract and Concrete Dialectics
TAO Zheng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000)
Necessary labor time of society is a critical concept in the viewpoint of Marxist labor value theory. Most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second sense causes the logical contradiction in Maxism theory system. For the sake of the better explanation and settlement of this contradiction, we will make out the conception of social necessary labor time in dialectics of abstraction and concretion.
necessary labor time of society; logical paradox; abstract; concrete; value
2013-10-16
陶征(1988—),男,山东新泰人,青岛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C970
A
1007-6875(2014)01-01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