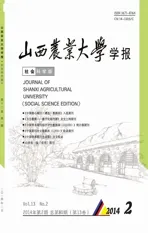论黄顺元小说的叙述视角
——以韩国作家黃顺元的短篇小说为例
2014-04-04李桂娥
李桂娥
(鲁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山东烟台 264025)
论黄顺元小说的叙述视角
——以韩国作家黃顺元的短篇小说为例
李桂娥
(鲁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山东烟台 264025)
韩国作家黄顺元小说叙述视角的转换,给小说带来独特性的同时,也让小说获得了丰富多彩的叙事效果。从叙述学立场出发,以叙述视角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究黃顺元小说中叙述视角的灵活应用及巧妙转换。
小说;叙述视角;转换
一
纵观黄顺元的小说,以第三人称为主的叙述视角在作品数量上占大多数,这也是传统叙事小说普遍采用的叙事形式。所谓的 “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即叙述者直接使用第三人称代词 “他或她”,采用旁观者的口吻叙述作品内容的小说。这类在语言学上被称为 “后续性信号”的人称代词,运用在叙述视角转换的文本中,却成了一种缺乏先行名词的 “非后续性后续信号”。[3]也就是说,这类作品的叙述者往往并不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而是作家赋予无限特权的 “代言人”。它可以洞悉过去,亦可以预知未来;可以表达自有想法,亦可以随意评判别人;可以自由的穿越时空,也可以深入灵魂挖掘内心隐藏的秘密……总之,这位叙述者在作品中 “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用罗朗巴特的话来说就是 “叙事者既在人物之内又在人物之外,知道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但又从不与其中的任何一个认同”。[4]这种叙述特点反映在黄顺元的作品中比如有 《黄老人》、《偏远山村的狗》、《鹤》、《山村里的孩子》、《沼泽》、《距离的副词》、《做缸的老人》、《酒》、《抽一支烟的时间》、《我们俩的时光》、《阵雨》、《温馨的碎片》、《稻草人》、《雁》、《树荫》、《芦苇》、《海螺》、《有钢琴的秋天》、《配角》、《山》、《迷失的人们》等;其中,《山村里的孩子》这部作品的内容是:奶奶给孙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寒冷冬夜里,一个贫困山村的孩子缠着奶奶讲故事,于是奶奶讲道:从前,有一个小伙子因被一狐狸精女人迷惑而身体渐趋虚弱,所幸的是小伙子后来听私塾先生的话吃下一颗珍珠而终免一死。孩子听完之后发誓自己绝不会被这样的女子迷惑。后来的一天,孩子却梦见一如花似玉的女子向他走来,于是孩子在万分情急之下寻找珍珠,这时梦醒了……显然,作品中这个故事是奶奶 “一手”创造出来的。首先,奶奶全权负责了故事的发生、发展乃至结果,而故事的可信度、可靠程度在这里已经不是重点。其次,在作品中出现过的几个叙述人物中,叙述的焦点自始至终落在奶奶身上,奶奶就是 “全能讲述者”,包括文中对她的所见、所为、所说的描写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其他人物 (比如孙子以及故事中的小伙子,狐狸精,美丽的女子等)都是作为奶奶的衬托人物出现的。
也许,正是由于第三人称叙述过于的 “全知全能”,给这些作品的叙述者以及作品的接受者造成了一定的被动和无奈,这也正是这种叙述方法的遗憾和缺陷之处。正如冯·麦特尔·艾姆斯所说的:“一般的方法是这样:无所不知的作者不断地插入到故事中来,告诉读者知道的东西。这种过程的不真实性,往往破坏了故事的幻觉。除非作者本人的风格极为有趣,否则他的介入是不受欢迎的。(《小说美学》))”。因为在作品中只有作者这么一个 “全知全能者”,接受者的参与、幻想、推理、判断和欣赏能力在这里也成了无望的期待。因此,这种传统的叙述方式受到当代国内外众多评论家的质疑也在所难免。
二
在文学的历时坐标上,“叙述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叙述的主流而高居文学作品首位。但是在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这一主流地位却发生了撼动。语言变异包括叙述视角的“玩转”,逐渐成为 “小说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支持的文学语境中的艺术探险”。[5]这其中的小说家,自然包括孜孜不倦追求与贡献的黄顺元。在洞悉到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的局限后,他又在叙述文本中进行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尝试。这里的叙述文本,“并不是指读者在实际阅读中接触的物质文本,而是读者在阅读经验中体验到的文本。”[6]在此,我们暂且把它称为 “体验文本”。在此文本中,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即故事中的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叙述视角因此而移入作品内部,成为内在式焦点叙述。在这种叙述视角观照下的叙述者不仅可以参与事件过程,还可以离开作品环境向读者进行描述和评价。在黄顺元的作品中,这种类型的作品并不少见,比如 《自然》、《圣诞快乐》、《杂技师》、《习俗》、《我故乡的人们》、《全部荣誉》、《黑暗中的刻版画》、《惭愧》等均是采用了此类叙述方式。这些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来作为小说的叙述视角,和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相比,某种程度上可以缩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对引起写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共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笔调上也显得格外亲切。但不可否认的是,依靠中心人物的眼睛嘴巴来观看并叙述周围一切的模式,完全颠覆了被动沉浸于故事中的一贯传统方式。如此一来,接受者就必须调动起所有存储的知识、经验和想像力来进行推理、判断与评价,以此让自己最大限度的融入故事中。这也是运用这种叙述方式进行叙述的优势所在。毋庸置疑,这种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的叙述方式直接影响了近现代一批侧重于主观心理描写的小说。
小说 《黑暗中的刻板画》是这样叙述的:这是 “我”在避难地大邱经历的一件事。搬到大邱的当天晚上,主人热情地问候 “我”并准备好了酒桌招呼 “我”一同畅饮。他把话题转到了打猎上。他看起来像一个职业猎手,他只要一看妻子的眼神就可以洞察四方。原来他在大邱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猎人,六年前,他听说喝抱子的血对怀孕的身体有利,所以为了让妻子喝到抱子的血,他和妻子一块出去打猎,第二天抓到了抱子并且把抱子的血给妻子喝了。但是,当猎人豁开了抱子的肚子才发现抱子已经怀孕,看到这,妻子不禁呕吐起来,把刚刚喝过的血全部吐了出来。那天晚上妻子便流产了,这之后妻子虽然多次怀孕,但是每次都流产,流产后的妻子劝说丈夫不要打猎,但是丈夫不听他的话,所以妻子把打猎的工具全部藏了起来。此时,他向 “我”炫耀“妻子明明什么都知道却又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他这样对我说。瞬时 “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幅在黑暗里寻找藏小盒子地方的中年汉子形象的版画……物质文本中的这些语言纯正、清新,诚如李形奇所评论的那样:“句子都具有抒情性,简洁而不繁琐,不仅充满了极为浓烈的抒情气息,而且充分体现了国语美的高峰。”[7]这种语言模式堪称为韩国现代文学语言的 “范式”语言。
在叙述中,小说的叙述者 “我”同时又是所讲故事中的一员。叙述者 “我”不仅充分讲述了文本人物 “我”在场时发生的一切,甚至细腻到“我”的内心活动以及心理变化,这样既能使故事情境变得真切可信,也无形中拉近了作者和读者的情感距离。但是,这种限知叙述视角只能描述 “我”存在的场景,而其他 “我”没有亲自出想的场景就无从描述了。这亦是作品使用第一人称叙述的缺憾所在。
三
其实,小说叙述视角的转换,往往是与叙述人称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叙述人称的变化往往带动着叙述者和叙述视角的变化。在尝试了全知叙述视角和限知第三人称视角的写作之后,黄顺元悟出终难摆脱单一叙述视角之局限,于是 “采取多视角的叙事,在同一部作品中采用多重的叙述视角,加强了作品叙事的立体维度”。[8]他采用人称交叠法,在第一人称叙述和在第三人称、第一人称甚至第二人称的交替变换中,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叙述视角转换情况。在人称转换中,不同的叙述者和角色人物承担者,形成了作品叙述视角的不同形态。这种交叠形态反映在小说中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便是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交叉叙事的作品,如 《黄鼠狼图》这部作品就交织使用这种叙事方式进行叙事:我和万珠在同一屋檐下长大,拥有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在一个寒冷冬日的晚上,万珠的舅舅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这个平淡无奇的故事却让我和万珠更想去了解外面广阔的世界:万珠的舅舅在蒙古时,曾经逗留在一蒙古人家里,偶然地碰到了一个日本人,他们和主人在一起闲聊,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狗叫声,主人说: “这是因为黄鼠狼来了”,黄鼠狼不知受到了什么刺激像疯子似的跑着,日本人为了抓黄鼠狼而跑了出去,但却遭到了黄鼠狼的攻击……
在这些文本叙述中,叙述人称慢慢地由第一人称的 “我”向第三人称 “万珠的舅舅”转变,这样在文本中就产生了叙述者身份的转变与替换:作品在以第一人称 “我”叙述时,作品叙述的主要人物是 “我”的所见所闻;而在第三人称叙述者叙述的故事中,作品叙述的主要人物又变成了 “万珠的舅舅”讲述的故事。也就是说,叙述者身份的变化,在作品中叙述的主要人物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当然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其他文本。此外,在叙述 “我”的童年生活时,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对往事加以追忆;而在叙述万珠舅舅在蒙古的奇特经历时,则采用了第三人称叙事者的全知叙事视角进行叙述。因此,在这类作品的叙事中,不仅叙述人称以及叙述者发生了变化,而且叙述主要对象的变化,也会形成另一种叙述者视角与人物视角的转换。
总之,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如果一味的模仿前人的小说模式而创作,无疑会成为 “存在的缺席”。[9]
所以这就要求作家以异于他人的理解和方式重建文学语言和文学秩序。黄顺元之所以能摘得 “短篇小说之王”的桂冠,不仅仅是因为他对人物心理的细致观察和重点描摹,更重要的在于他用“简洁的句子和客观性叙述方法是黄顺元小说问题的特征之一,而正是这种特点是其艺术构造更加趋于完美的主要原因。”[10]这种 “客观性的叙述方法”就是指叙述人称以及叙述视角的变化。的确,作为一个成熟而优秀的作家,他在建构一部新作品之时,定然会首先选择并恰当运用一个合适的叙述视角,这既决定了其小说叙事走向,也是其异于他人、选择 “怎样叙述”的一个标志之物。可以说,黄顺元在小说叙述视角转换方面的大胆尝试与探索,不仅影响了韩国小说形式上的变化,对韩国现代小说的创作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胡亚敏.叙述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9.
[2]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
[3]罗钢.叙述视角的转换及其语言信号[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1):27-35.
[4]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88.
[5]肖莉.小说叙述语言变异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3.
[6]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
[7]李形奇.黄顺元文学全集[M].韩国:三中堂,1973:376.
[8]陈慧娟.论新时期小说叙述视角的转换[J].江淮论坛,2006(8):163-167.
[9]肖莉.小说叙述语言变异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9.
[10]权英民.小说的美学之一:黄顺元的文体[M].韩国:文学与志成社,1965:158.
(编辑:佘小宁)
On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of Huang Shunyuan's Fiction——A Case Study on Huang Shun-yuan's Short Story
LI Gui-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Ludong University,Yantai Shandong 264025,China)
Huang Shun-yuan is a Korean writer.The conversion of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creates a unique world and a varied effect in his fiction.From the point of narratology,this paper,taking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as the starting point,further studies the flexible application and ingenio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Fiction;Narrative perspective;Conversion
I106.4
A
1671-816X(2014)02-0171-03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小说语言属于一种 “话语”。但这种 “话语”并不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表达的真实语言,而是作家为了建构自己的小说世界、传递作品内容、影响并濡染接受者的一种工具和载体。在写作中,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接受者正确理解并适当评价作品,作家除了运用各种方式交代清楚时间、地点、背景以及有关人物外,还必须注意叙事人称或者叙述视角的恰当选择。因此叙事视角和人称的选择成为表达作品意义和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
叙述视角是叙述者或作者在叙述过程中观察故事的角度。角度不同,叙述内容和叙述结构也就不同,所以叙述视角的重要支配性不言而喻。难怪小说理论家路伯克曾说:“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观察点问题——叙述者所站的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支配。”[1]在小说的叙述世界里,黄顺元对叙述策略以及叙述视角的探索,一直走在同时代韩国作家的前列,正如雅各布森(R.Jakobson)在“文体学研讨会”上建议的那样 “……文学研究者对语言学问题不予关心,对语言学方法也一窍不通,他们就显然过时落伍了”。[2]
叙述视角也称叙述聚焦,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同样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的人物观察就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小说的叙述视角有两层含义,一是叙述者的叙述视角,也就是作者的叙述视角;一是人物的叙述视角,即小说中人物的叙述视角。前者,主要表现为人称的变化,即第一、二、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后者,就是小说中从某一人物角度看人看事。在此,笔者仅仅以前者为理论依据分析韩国作家黄顺元的 “短篇小说”,从人称叙述视角的变化梳理作品中叙述故事的层化并进一步探析作品的叙述深度。
2013-10-22
李桂娥 (1975-),女 (汉),山东栖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