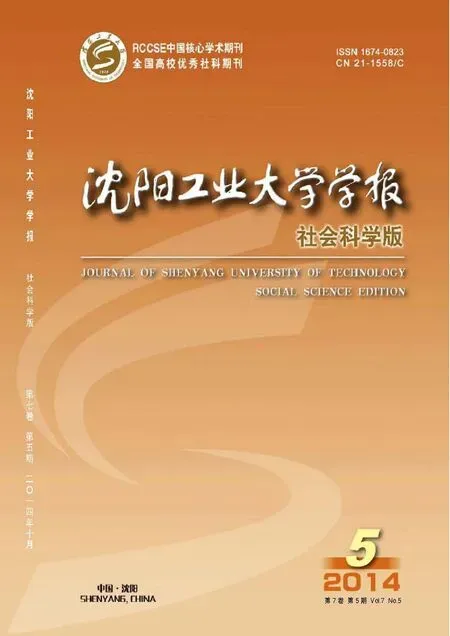戊戌维新派宪法思想概论*
2014-04-03杨凡
杨 凡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81)
戊戌维新派宪法思想概论*
杨 凡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81)
从“进化论”与“三世说”理论、“民约”与“民权”理念、“分权”与“集权”思想以及“立宪”与“法治”主张四个方面探讨晚清戊戌维新派的主要宪法思想,力图从制度设计与制度实践的差距中探索制度生成的历史逻辑,并由此揭示民主精神与共和制度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关系。
戊戌维新; 维新派; 宪法; 立宪; 民主精神; 共和制度; 民约; 民权; 法治
从实践经验层面来看,我国并不缺乏“源远流长”的宪法学说史和宪法制度史。“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不是说过‘我们不能够说中国有一种宪法’吗?哲人此言是言过其实还是中肯论断?”[1]22但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传统法律在近百年中经历了三次极其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是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在列强逼迫下,为了重建国家主权而大规模移植西方法律,几乎完全抛弃了传统法律。……第三次是改革时期,再次全盘引进西方法律,既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现代革命法律传统,也再一次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法律;‘现代’被等同于西方,中国传统被等同于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需要的‘前现代’或非现代。”[2]1由此,本文择我国宪法之历史进行研究,并期望由此有所借鉴。
一、研究缘起
反映到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理论的建构上,可清楚地看到,由于其深受西方学术研究范式的型塑,以致从概念到逻辑、从义理到方法几乎均已西化。一方面,学术研究得以更为明确而具体地开展;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很多有价值的传统学术材料被排除在现代形式主义法学的研究体系之外,使得我们难以甚至无法“慎终追远”那些宝贵的制度文明遗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现有的法学理论认知工具都是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那么,运用这些工具来探讨中国社会的现实法治问题就必然遭遇主观逻辑衔接上的困难。但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尽管在旧中国宪法发展中脱离宪法理性的制度与文本所占的比重比较大,但就整体学术脉络而言,不同时代学者们所提供的宪法学知识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学术关联性,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3]65我们不该对任何学术遗产心存偏见甚至先见,历史更不是“分段的生死”,而是一种内在的自我扬弃与自体更新,这在中国的易学中又叫“相磨相荡”、“相反相成”。就制度的形成与流变而言,近代以来的一系列革故鼎新,其实“改革的动力早在原体制内部就产生了”[4]6。那么,研究那些制度生成和演化的内生性变量,对于把握历史性的当下的制度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同光时期”,作为抱定“君宪救国”思想的戊戌维新派,如果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其在历史中的定位与功绩,可谓上承洋务运动的“制器”遗风,下启近现代以来各种“变法”的大幕。正如张晋藩教授所言:“百日维新虽然是短命的,但却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追求君主立宪的一次实践,这是维新派与早期改良派的主要区别。至于康有为提出的建立以宪法为基石的法律体系的主张,无疑是中国近代宪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5]32作为宪政的两大基石,“民主”与“共和”古已有之,然“共和”之于中国从来都只是王权之下的“贵族共和”,而那种所谓的“成汤,代夏做民主”式的“民主”则恰恰等同于“主民”而已。那么,此番所说的“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便在于中国人第一次真正在学理和制度的双重层面上,通过削皇权而重民权的努力试图扭转、至少是推动一种于中国历史而言新的共和体制。尽管民权离民主还很遥远,也尽管这种走向共和的努力遭致后人的白眼相向,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努力渐渐实现着古老中国千百年来的最高政治伦理——大同世界。历史交给我们的是智慧和宽容,而宽容恰恰是宪法的核心精神。如此,则整理这段国故于“再造文明”而言确实具有永久的现实意义或现实的永久意义。
二、维新派宪法思想概要
客观地讲,尽管戊戌维新变法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至少就其当世而论,支撑其宪法制度构想的宪法思想不可谓不丰富,而包容其宪法思想的宪法制度设想亦不可谓幼稚。就其宪法思想而言,择其大要可概括为“进化论”与“三世说”理论、“民约”与“民权”理念、“分权”与“集权”思想以及“立宪”与“法治”主张。
1.“进化论”与“三世说”
人心思变,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和时代的人们不自信与自信的来由。只因人们对变化之态度的不同而使得深处变化中的人们采取了不一样的应对变化的行为,与此同时形成了各种各样有关“变化”的学理。当时之世,东衰西盛。在中国人看来那是故国不堪回首的离乱时世,但西方学者却无不自豪而自负地说道:“三百年前爆发了工业革命,摧毁了古老的社会,创建了一个全新的第二次浪潮文明。它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制度,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把一切事物集中组织起来,形成世界有史以来最有力量、最有向心力、最有扩张性的社会制度。”[6]5这所谓“集中组织起来”进而“形成最有扩张性的社会制度”不仅摧毁了“天朝大国”的美梦,也斩断了中华文明对有关世界变化规律的一贯理解,即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内变”和“渐变”观念已不可能再适应这个“被扩大”了的“天下”。于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轰击之下,曾经留学英国的严复以一个中国传统士子的自尊与自强选译了英国人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一书的部分导言和讲稿的前半部分,并用一种中国式的家国天下的观念将该译著的书名意译为《天演论》。
该书实际上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政论文。作者认为万物均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变化,“物竞”就是生物间的“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生物就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进化演进的。联系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的状况,作者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指出再不变法将循优胜劣败之公例而亡国亡种。《天演论》揭示的这一思想,结合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及西方哲学思想,使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如获至宝,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客观地讲,《进化论与伦理学》以及《天演论》的出现源于西方世界工业化浪潮的激荡震撼。从此意义上来说,《天演论》的诞生乃是中国历史由被动到主动地纳入世界现代化轨迹中的肇始性著作。同时更可以说,《天演论》乃是从中国传统经义哲学的最高层面来反思、撼动那“千古犹行的秦法政”。其对戊戌维新派宪法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否认的根本性影响。向来目空一切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书,并认为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如果说《天演论》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揭示了另外一种有关世界变化的本源性“法则”,那么公羊学的“三世说”则为康有为应对这种变化的具体型范及方法提供了最为利锐的理论武器,并为其主张和领导下的一系列宪政实践活动提供了最高的和最基本的思想纲领。如其在《上清帝第一书》中说到:“夫治国之有法,犹治病之有方也,病变则方亦变。若病已变而仍用旧方,可以增疾。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危国。故当今世而主守旧法者,不独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圣治世之意也。”[7]58由此可见,此所谓的“时既变”乃指时代主题,甚至是时代“主体”之变;而所谓的“治世”亦不过是假托“列祖列宗”名下的三世因果。
康有为关于变化与变法的历史政治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以其大弟子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诸君。如同《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所说:“光绪十六年……八月梁启超来学。……吾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义。……既而告以尧舜三代之文明,皆孔子所托。又告以大地界中三世,后此大同之世,复有三统。”[8]123梁启超更是直言不讳:“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9]57
2.“民约”与“民权”
宪法是讨论协商之下的产物,但不是唯一的产物,因此,谁参与了协商讨论实际上决定了对这一产物是否为宪法的判断。“宪法”一词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典籍当中并不鲜见,如《尚书·说命》中所言:“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又如《管子·七法》中所言:“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再如《墨子·非命上》所说:“是故古之圣王,发宪出令,设以为赏罚以劝沮暴。”但是,古之“宪法”的概念含义与近现代以来宪法理念的奥义大相径庭。中国古代的所谓“宪法”其实等同于“皇纲”之下的“宪制”,是一种标榜皇权至上的统治纲领,是“一定国是”的一言堂式的产物。即使在“立宪”的过程中存在协商与妥协,最多也只是一种“贵族共和制”下的商妥,是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专政的合法性认证。因此,这种“门开半边”甚至是谋划于内室、强行于率土中的“宪法”因为缺乏对普罗大众的尊重和关注而不能为“历史创造者”的人们所永远尊戴,终将被历史的大浪淘走。
“大学之道在亲民。”又诚如马基雅维利在其名著《君主论》当中所揭示的两种不同的君主一样,人们更愿意接受那种使人心生亲近之感的君父,而不是那种令人心存敬畏的君王。可以说,整个维新派的变法理念可以用“君主立宪”四字来概括。对于拥护“君主”的军机章京们而言,这是一个“开明专制”的政治伦理。而回归到“立宪”之争的核心关节上,这实际上又是一个“与谁谋”的问题。维新派与此之前洋务派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将这个“谁”开放给了更为广泛且更为底层的社会民众,呼唤当朝统治者给予更广泛的民众以一定的个人权利,甚至是政治性权利,也因此使得中国自古以来的所谓“宪法”第一次有了“民约”的内涵。这个“民”未必都是草民,但因为有了对“民”的重新定位,才使得传统的政治制度有了“德不孤,必有邻”的政治品德。也因此自下而上的维新变法运动,使传统中国的“使民”政治开始真正转向认可并尊重“民权”的大道,民主化的进程也随之渐进展开,而“共和”的含义也开始在中国发生了质的变化。
就其对“民”重新定位与定义而言,显然是有了“民权”观念的初步觉醒才能有“民约”在制度上的新追求,观诸维新派的宪法理论建构,也不难发现西方民权观念对诸君们的深刻影响。当然客观地讲,尽管身为维新派领袖的康有为本人很早就从制度建构设想的层面对实现“民权”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但其对“民权”思想的理解还是比较保留的,如在1895年2月的“公车上书”中,康君便建议光绪皇帝设立所谓的“议郎”制度,即由士民推举“议郎”,而“凡内外革新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7]207由此可见,康君只将这项重要的政治权利开放给“士人”阶层,而未曾及于普罗大众。这也是他始终强调“实君共和”而在后来与其学生梁启超分道扬镳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管其思想局限性如何,正如有学者断言的那样:“戊戌一幕之所以惊人,不仅要求君主变法,而且要求与君主分权,即所谓‘民权’。”[10]72
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他在变法之前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民权”与制度革新的关系。在其1896年撰写的《古议院考》中,倡言“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政分,则事易就。”[11]32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的梁启超更是在痛定思痛中进一步发展了他个人的“民权”理论。在其1899年发表的《爱国论》中,梁君更是从“爱国”的角度阐发了“民权”与“国权”即“国家主权”的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12]73在此,他已不再满足于抽象的、甚至是虚化的政治国家的概念,而开始将国家看作一个“族群共同体”,由此也完成了一种从“朕即国家”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概念转型。尽管梁本人曾明确表示:“各国改革之业,其主动力者恒在中等社会”。“中等社会者何?则宦而未达者,学而未仕者,商而致小康者皆是也。”也就是说,梁君所谓的“民”似乎也只局限于有产阶层,但我们需看到,社会是一个流动的阶层集合体,今之有产者必是昨之贫贱者。纵观梁君一生的学术思想,还有“开民智”的重要主张。那么,梁君此处对“民权”的界定与其说是一种限制,不如说是一种引导和鼓励,即引导有产者参政议政,鼓励无产者兴业受教,以备他日参与之需。如此则即使是从其思想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而论,其所倡导的“民权”理念亦比康、谭诸君更具开放性和前瞻性。
3.“分权”与“集权”
既然维新派已开始将“国权”视作“君权”与“民权”的结合体,那么在现实的改革层面寻求“分权”的理论支持也就成为必然。诚如上文中所论到的以康梁诸君为代表的维新派在他们变法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都对权力与权利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但如何切入具体制度层面的建构则不是能够从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中找到依托的。也就是说,要实现从制度学理到制度实践的质的飞跃则必须“采泰西之所长”。康有为在其变法前后都曾对三权分立学说做过特别的推荐与说明,如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7]214在维新变法期间,他从“实君共和”的角度再次声明了三权分立的重要性:“盖自三权鼎立之说法,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7]339对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的详细介绍,梁启超在其《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一文中也有过比较宪法学意义上的精辟论述。梁君以为:“自1778年美国独立,建新政体,置大统领及国务大臣,以任行政;置上下两议院,以任立法;置独立法院,以任司法;三者各行其权,不相侵压,于是三权鼎立之制,遂遍于世界。今所号称文明国者,其国家枢机之组织,或小有异同,然皆不离三权范围之意,政术进步,而内乱几乎息矣,造此福者谁乎,孟德斯鸠也。”并进一步对其制度运行的客观逻辑进行了阐发:“然居其职者,往往越职,此亦人之常情,而古今之通弊也。故设官分职,各司其事,必使互相牵制,不致互相侵越。于是孟氏遂创为三权分立之说,曰立法权,曰行政权,曰司法权,均宜分立,不能相混,此孟氏所创也。”[13]18-2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戊戌时期的维新派自始至终坚持中央集权式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为将传统中国“宗法宏观一体化”的帝王专制制度转变为“国法宏观一体化”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注入了一支强心剂。有学者总结康君坚持中央集权的理由为:“(1)只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面对中国当前的困难;(2)中央政府不受地域分裂压力的牵制,才能确保人民在宪法上的权利不受侵害;(3)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完全控制国家的财政、军事与司法,中国永不能变成现代文明国家;(4)一个强大有力的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完全地实行人民的意志。”[14]33-36笔者认为,康君的这一看法有其敏锐的历史眼光与中肯的地方特色。就“集权”与“专制”的关系而言,笔者并不认为在二者之间可以绝对地划一等号。“集权”只是一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原则或模式,其所对应的概念乃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而“专制”则表明一种权力运行上的主体性思维,与“民主”相悖反。如此,则“集权”与否同“专制”与否在政治实践逻辑上并不能自洽。也因此,维新派一方面主张在整个国家权力机关内部应实行分权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则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原则上坚持中央集权。“分权”与“集权”这对看似非此即彼的矛盾在戊戌变法的语境中获得了双赢。至于如何强化中央集权,康君则认为应从废除行省入手。“康有为早在1907年就发表《废省论》,公开抨击行省制,于1910年又发表《裁行省议》,指出行省面积太大,总督巡抚拥有过分的权力,会引起严重的行政问题。”[15]49总而言之,在处理中央跟地方的权力关系上,维新派坚持“加强县级政权机构建设;减少县以上机构的层级,地方机构只设道、县两级,取消省、府(州),这样可以尽快下情上达、上令下传;设立制度局,改变君主专制的局面,建立君主立宪的体制。”[16]200
4.“立宪”与“法治”
所谓“立宪”通常有两种含义的解读,一是指包括宪法典在内的宪法文件的制定;二是指宪法制度的推动实行,亦即宪政活动的正式开启。前文所论或为宪政活动的思想准备,或为宪政活动的制度规划,其宪政之实质内涵已在维新变法的前后渐次具备,此处所论乃是戊戌诸君致力于制定宪法文本的主张。“康有为曾经奉旨在总理衙门回答王公大臣对于变法事宜的询问,这个经历使他深感骤议开国会一事不可能取得王公大臣们的认可,因而被迫在应诏而上的《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仿日本明治维新之例,‘开制度局而定宪法’。”[5]48但维新派有关制定宪法的主张不待制度上的施行,便随戊戌变法的失败而胎死腹中。
值得特别介绍的是,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新千年之交的1900年撰写了《立宪法议》一文,全文以制定宪法为核心,系统而详实地给出了自己对于中国立宪具体步骤的看法:“其一、首请皇上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其二、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带领通晓英法德日语言文字之随员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须有学识,不徒解方言者。并许随时向各国聘请通人以为参赞,以一年差满回国(又此次所派考察宪法之重臣随员宜并各种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类,皆悉心考究)。次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宫中,草定宪法,随时进呈御览。次四、各国宪法之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使国民咸知其来由,亦得增长学识,以为献替之助。次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皆得辩难讨论。或著书,或登新闻纸,或演说,或上书于立法局,逐条析辩。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次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11]153-154应该看到梁君此文影响之深,实为清末预备立宪活动之张本,甚至其“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亦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启发了民国时期有关“训政”的行宪思想。正因如此,才有学者评价:“‘戊戌变法’的失败是中国立宪努力的第一次重大挫折。”[17]89尽管失败,但它毕竟是古老中国预构现代民族国家甚至民主国家的第一次努力的失败。
难能可贵的是,维新派在主张“立宪”的同时,还对型塑一国“法治”有过比较深入而系统的探讨。康有为在与王公大臣廷辩于总理衙门之时就明确提出:“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在其《上清帝第六书》中更是明确提出:“今宜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则、舶则、讼律、军律、国际公法,西人皆极详明,既不能闭关绝市,则通商交际,势不能不概予通行。然既无律法,吏民无所率从,必致更滋百弊。且各种新法,皆我所夙无,而事势所宜,可补我所未备。故宜有专司,采定各律以定率从。”[7]215而在其第五次上书之时,康君便已主张“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7]207即以宪法之“名”以定“公法”、“私法”之“分”。所谓“名”是指逻辑体例,“分”是指分界疆域。梁启超则从批判荀子的“治人”理论入手来揭露中国自古以来人治传统的弊病:“荀卿有治人无治法一言,误尽天下,遂使吾中华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11]297从此断言中可以看到,梁君所谓的“法治”已经初步具备了“法治国家”的两种预设形态:从国家、人民、法律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梁君眼中的“法”必高于国家和人民,这无疑是一种“法律至上”的思想;从“依法治国”的制度功用角度,又可以看出梁君所谓的“法治国家”必包括作为政治国家权力层面的“国家法权”的重构以及作为社会公民权利层面的“个人责任”的担当,而这种对“个人责任”的强调必与“个人权利”相伴随。也就是说,这种重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主义法治”无疑也是将“个人权利”开放给更多的社会大众。
三、维新派实践其宪法思想的经验与教训
诸如某些历史学家的观察一样,“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与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18]168考其《孔子改制考》及《孟子微》等书中的义理,更可见那种“实用道德主义”对这一中国传统学人的深刻影响。例如,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他自叙到:“读王制选士、造士、俊士之法,则世卿之制为孔子所削,而选举之制为孔子所创,昭昭然矣。选举者,孔子之制也。”[19]238甚至乃引《春秋繁露·楚庄王》篇中的义理来为改制“正名”以求妥协于帝后臣工:“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19]199而在《孟子微》一书中,康有为更是将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归结为对孔子人本思想的制度性继承,如其所言:“此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权、开议院之制。盖今之立宪体,君民共主法也……以国者国人公共之物,当与民公任之也。孔子之为《洪范》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是也’;尧之师锡众曰:‘盘庚之命,众至庭’。皆是民权共政之体,孔子创立,而孟子述之。”[20]209-210
客观地讲,维新派的这些做法可谓用心良苦,其与“托古改制”的传统政治权谋并无二致,那种期盼自身能与帝后心心相印的做法确也是朝夕研习帝王之学的那一代学人所不得不沿袭运用的“伎俩”,所谓“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客观地说,这种“以术致道”下的政治权谋有其无奈,也有其合理性。但作为“身在此山中”的政治家,如何“委曲求全”以成“反手而治”?则鲜有成其功者。正如书生意气的“康党”们,既不能“吾道一以贯之”,更不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廷辩朝堂却以“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员”开罪满朝亲贵。泄私愤还是倡公义?是人事?是天命?《左传》有言:“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君不君,臣不臣”几成专制王朝的幽暗命运,戊戌六君亦难逃此劫。由此可见,“人治”的思想与制度实在太过微妙,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执中守道”难矣,靠此幽暗微妙的权术手腕来推动变法改制,身败名裂者十有八九,如此看来则六君宿命又与秦商鞅、明居正几无二致。
由此当比观“洋务派”与“维新派”两家革故鼎新的主张,为什么后者终未能从国家制度重构的层面超越前者?更比之于同是依靠渐进改良却获得了巨大成功的英国“光荣革命”,为什么在彼时的中国就不能成功地实现“旧瓶装新酒”?诚如有学者所言,就其实践历史的意义而言,现代宪政活动的开启所要追问的乃是“如何从传统的旧制度中开辟出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21]18如此重大任务的完成,又“涉及一个现代国家之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the state)与现代公民之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the individual)的双重主权之建构问题。”[21]19而我们所看到的以上两家,均无法从此双向层面同时建功立业。所谓帝国胸中的“吾国吾民”,说白了仍旧是“家天下”式的役民之制,是那种“云在青天水在瓶”式的“金瓯永固”,是那种将普罗大众排除在共和之外的君主与满贵族和汉官僚三者之间的共和,总之是将民主排除在外的共和。
所谓“制度者,智慧和机运之联合产儿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22]524我们当然不能苛责于前人的智慧,更无法去臆测某种历史的机缘,只能说“共和”的大厦因为没有建构在“民主”的基石之上,则难免中心摇摇。也可以说,在滑向近现代的历史河流时,无论我们如何高推共和制度的圣境,没有民主的提纲挈领,则现代共和制度的擎划终究只能是纸上谈兵。而民主的程度与真实性又确乎决定了共和大厦的坚实性。由此,“君主共和”与“民主共和”间的不同意义也就在历史的背景下真实地映现出异常殊远的现实逻辑与价值。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撇开个人政治道德而用理性的思维来诘难此后的那一系列政治闹剧,诸如袁氏称帝和张勋复辟。还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理由自信并相信“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确实是在历史的等待中生成的,确实是在人民的期盼中诞生的。
[1] 陈端洪.宪治与主权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 黄宗智.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3] 韩大元.中国宪法学:20世纪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 [C]//张庆福.宪政论丛.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4]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 张晋藩.中国宪法史 [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6]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M].朱志焱,潘琪,张焱,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
[7] 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 [M].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
[8] 康有为.戊戌变法:第4册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 [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 [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11]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上 [M].李华兴,吴嘉勋,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 [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 [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辛向阳.百年博弈: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100年 [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15]熊文钊.大国地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宪政研究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6]辛向阳.大国诸侯: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结 [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
[17]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 [M].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18]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9]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0]彭明,程啸.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1]高全喜.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论现时代的政法与其他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22]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M].长沙:岳麓书社,1999.
GeneralityofconstitutionalthoughtofReformMovementof1898
YANG Fan
(Law School,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The main constitutional thought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discussed from four respects such as the theories about Evolution and Three-epoch Doctrine, the concept of Civil Convention and Civil Rights, the thought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and the proposition of Constitutionalism and Constitutionality.The historical logic of institution generating is explored from the gap between institution design and practice, so as to reveal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and the republic institu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reformers;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ism; spirit of democracy; republic institution; civil convention; civil rights; constitutionality
2014-06-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AFX010)。
基金项目: 杨 凡(1982-),男,湖南益阳人,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宪法等方面的研究。
* 本文已于2014-09-23 11∶15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 网络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40923.1115.003.html
10.7688/j.issn.1674-0823.2014.05.03
D 911.01
A
1674-0823(2014)05-0402-06
(责任编辑:郭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