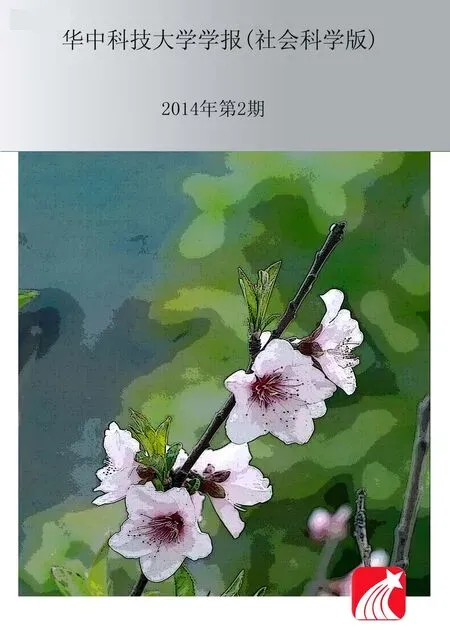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与孔子论“射”
——德性伦理的理性逻辑与情感逻辑
2014-04-01李超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李超,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211189
随着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中西方传统德性伦理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以下简称亚氏)和孔子德性伦理学的比较研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愈演愈烈。尽管两者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减轻了儒学证明自己哲学性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也消弭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同时也让那些复兴亚氏德性伦理学的当代英美伦理学了解到,儒学(本文特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作为原汁原味的中国德性伦理学,其博大精深不仅可与亚氏相媲美,亦可为德性伦理学的复兴提供理论支持和资源帮助。亚氏与孔子作为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在很多方面具有相通性,但最具特色与共同点的则是中庸思想与德性论。笔者通过对比分析亚氏和孔子论“射”来说明中庸,阐明中庸德性在二人伦理思想体系中的不同地位,进而指出两人论“射”的不同目的和不同价值指向,说明两人论述中庸德性的不同理论预设,深度挖掘二人德性伦理的逻辑路径,从而说明中西两种不同德性论传统的内在逻辑。
一、射箭模型与中庸德性
以“射”为例来论述中庸德性,亚氏和孔子最具代表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两者(亚氏和孔子)都在解释德性本质的时候遵循着射箭术的模式(model of archery)。”[1]131虽然两者都承认中庸是一种德性,但中庸思想在二者思想体系中的含义与地位却大不相同。
亚氏在其伦理学中谈到射箭的地方并不多,但“射箭的技艺是亚里士多德建立中庸学说时的模型。”[1]140因为“像射手有一个目标帮助他一样,更能帮助我们命中正确的东西”[2]1094a25。亚氏论“射”就是要说明命中中庸就如同箭手命中正确的目标。射箭太上或太下、过左或过右都不会命中目标,因为目标只有一个,正确的目标就是箭靶的中间。此即亚氏论“射”所关注的射箭之理——中庸的道理。也就是说,射箭之理是亚氏谈论伦理德性所要遵循的原理。
中庸德性在亚氏看来,一是存在于过与不及的中间;二是适当的。所谓“中间”即是两种恶、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德性虽然与存在着过度、不及、中庸的感情和实践相关,但以求取中庸为目的。所谓“适当的”就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感受这些感情,就既是中庸的又是最好的。这也就是德性的品质。”[2]1106b21-23即中庸对于德性是本质性的,正如亚氏在总结德性的定义时所说的那样:“德性是一种能做出选择的品质。这种品质在于一种中庸状态,而中庸状态是相对于我们而言的,是由理性所规定的。而理性则是由有实践智慧的人所界定的,它是两种恶之间的中道;这两种恶一是过度,一是不足。”[2]1107a1-4也就是说,德性是一种中庸状态,而中庸就是德性品质。需要声明的是,亚氏谈论中庸时所言及的德性乃是伦理德性,而非理智德性。
以中庸来界定德性是亚氏德性伦理学的特色,但其中庸学说却又很遗憾地为西方哲学史或伦理学史上的大师所否定①对亚氏中庸学说进行否定的人有:称中庸学说为“毫无深刻的识见”的黑格尔;认为中庸学说“发挥得很巧妙,却并不那么成功”的罗素等人。。特别是当代德性论的代表麦金太尔,他指出:“这个学说(中庸学说)最终显得充其量不过展示了不同程度的有用性,而对于德性的特征,却几乎没有揭示出在逻辑上必然的东西。”[3]103我们知道,“中庸”、“幸福”等范畴的引入正是亚氏伦理学区别于前人特别是柏拉图之处,正如大卫·福莱所言:“事实上中庸之道代表亚里士多德很重要的伦理学发现。……中庸之道总的说来为亚里士多德提供了一个确定的体系,以此讨论德与恶的问题,并使之体系化。”[4]143-144而宗白华曾就亚氏的中庸思想指出:“中庸之德并不是庸俗一流,并不是依违两可、苟且的折中,乃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毅力、综合的意志,力求取法乎上、圆满地实现个性中的一切而得和谐。所以中庸是‘善的极峰’,而不是善与恶的中间物。”[5]70这也是对中庸学说的一种肯定。
所以,离开中庸而奢谈亚氏伦理学中的德性是不切实际的,更是荒诞的。中庸思想也并非像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说的是“他(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中最著名的但却最没用的部分之一”[6]36。著名显而易见,“最没用”却是对亚氏中庸思想的一种错误理解或贬低。倘若真像乔纳逊·巴恩斯(Jonathan Barnes)所说的,亚氏对《尼各马可伦理学》进行修订时定会将德性是一种中庸的观点删掉,那么,亚氏德性伦理学也定会因此而逊色很多。事实上,中庸不仅是种德性,更重要的它还是德性目标与德性标准。若删掉亚氏的中庸观点,那么亚氏伦理学中的德性思想必然会较现在大为失色。
考究孔子论“射”的思想不能仅局限于《论语》一书,应以“四书”、“六经”等为文本依据。古者以射观德,“射者,所以观盛德也。”(《礼记·射义》)因此,孔子论“射”关注的是射箭之德——中庸的德性。“德”字早在甲骨文、金文中就已存在,但“德”的观念在先秦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天德、祖宗之德;二是源自于礼的规范的制度之德;三是精神品行之德,此即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德”[7]。孔子论“射”所关注之“德”主要第二、第三阶段的“德”,亦即他所关注的是射箭之制度、规范、礼仪和“发而不中”乃“反求诸己”的心得体会与精神品德。在孔子看来,射箭之德的最高表现是中庸,“中庸其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
孔子曾以“过犹不及”与“狂狷”释“中庸”,朱熹注解“过犹不及”时说:“道以中庸为至。贤知之过,虽若胜于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则一也。尹氏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夫过与不及,均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故圣人之教,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于中道而已。’”(《朱子集注·论语集注·先进》)“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獧乎!狂者进取,獧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孟子·尽心下》)余纪元认为:“射箭术的比喻可以从儒家的‘中—和’结构那儿找到。”[1]138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中和”即是“中庸”。中庸之道亦即君子之道,故“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礼记·中庸》)。《礼记·射义》记载:“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对此亦有类似表达:“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此即以“射”观“德”,且“德”为中庸之德。
但是,仅从“中—和”结构来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不仅不够深刻,而且也不全面。在儒家思想中,“中—和”结构可以解释“中庸之道”的“中道”、“中行”、“中和”、“中正”②例如,“不得中道而与之”《孟子·尽心下》;“不得中行而与之”《论语·子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位乎天立,以中正也”《周易·彖·需》等文献。等表达方式,但并未表达出“时中”的内涵,也未传递出“当其可之谓时”(《礼记·学记》)的意蕴①孔子重“时”的表达可见:“物其有矣,维其时矣”《诗经·小雅·鱼丽》;“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不违农时”、“无失其时”《孟子·梁惠王上》;“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上》;“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荀子·修身》;“以时顺修”《荀子·王制》;“事时制明而用足”《荀子·君道》;“善时者霸,……霸者敬时”《荀子·强国》;“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荀子·天论》;“礼,时为大”《礼记·礼器》等语句。。《礼记·中庸》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尚书·召诰》亦有言:“其自时中乂”。《易·蒙·彖传》:“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它们均旨在强调一个“时”字。“时”与某种常规、成见相对举,而与“权”、“宜”(义)、“损益”诸概念相通,是“庸”之方策,亦是“中”之精义所在。孟子关于“嫂溺援之以手”(《孟子·离娄上》)的事例就很好地说明了“时中”之意。故程子说:“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朱子集注·孟子集注·序说》)因此,理解中庸应从“中—和—时”这个三而一、一而三的结构来理解。
先秦儒家将中庸视为一种极高明的“天人合一”境界,并提升到本体论的境界,即“诚”的境界。“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礼记·中庸》)由“尽己之性”到“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最后达于“赞天地化育”,与“天地参”的“天人合一”境界,正是中庸之道的真谛。它是一种以入世为意向的道德进取,是各层次伦理的贯通与和谐。这种典型的具有东方韵味的文化特色与今天的生态伦理可谓是不谋而合。
总之,在亚氏和孔子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射箭模型与中庸德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一关系中亦可探得两人论“射”的善与礼的不同目的和幸福与和谐的不同价值指向。
二、“射”的目的及其价值指向
在亚氏看来,论“射”是为了说明伦理德性是种中庸状态,命中目标就要遵从射箭之理,命中德性就要遵从中庸之道。有伦理德性必是合乎中庸,而中庸是人们追求的善目的。故与其说中庸是种德,不如说是善。善的最终价值指向是最高善——幸福。而在孔子看来,论“射”意在说明中庸之德虽为至德,但行为只有合于礼才算有德,而合乎中庸即是合于礼,中庸不过是礼的表现而已。故与其说中庸是种德,不如说是礼。礼的最终价值指向是“和为贵”——和谐。
亚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一开始就宣称,每种技艺、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2]1094a1-2。射箭活动亦不例外,它所命中靶心的目的是善事物,而德性所命中中庸的目的也是善事物。善事物分为两种:一些是自身即善的事物,一些是作为它们的手段而是善的事物,即那些因其自身的缘故而为我们所追求的善事物是因为属于一个单独的形式而被称做善的,而其他任何产生或保持着这些善或阻止着它们的对立物的善事物,都是因作为它们的手段而被称为善的。廖申白先生指出,作为单纯的手段善的事物往往是因为我们的需要而成为善,当需要满足后它就不再是善。因其自身之故和既因其他事物之故又因其自身之故而被我们追求的目的善则都是对我们显得是善,是更为终极性的善。也就是说,善的自身的、根本的性质由这种目的性的而不是手段性的善规定[8]xx-xxi。
因此,亚氏认为在目的王国中显然存在着一个以最高善为终极目的的目的,而关于这种最高善的知识对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它像射手总有一个目标要瞄准一样,更能帮助我们命中正确的东西。像箭手需要明白他的目标一样,“我们就应当至少概略地弄清楚这个最高善是什么。”[2]1094a26在亚氏看来,最高善是某种完善的东西,而最完善的东西就是那些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这样的事物就是幸福。“幸福是所有善事物中最值得欲求的、不可与其他善事物并列的东西”,并且“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2]1097b17-21
在亚氏看来,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惟有在其实现活动中才能展现他的存在。作为人生的最终价值指向,幸福是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实现活动。人在活动中所追求的外在的善、身体的善及灵魂的善等善的事物,只有灵魂的善才是最恰当意义上的、最真实的善。因此,人的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实现活动,即灵魂的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这里的德性不仅是指伦理德性,更重要的则是指理智德性。在伦理德性的意义上,亚氏说幸福可以通过德性或某种学习或训练而获得,这种幸福在亚氏的伦理理论中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幸福,但也是一种属人的幸福。而在理智德性的意义上,亚氏认为沉思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是一种比人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因为沉思是最高等的、本性的最好部分的实现活动;它最为连续和持久;沉思能够带来更大的、纯净而又持久的快乐;沉思中含有最多的自足,即最为自足;沉思活动是惟一因其自身之故而被人们喜爱的活动,即自身即是目的;人在沉思中能够找到自足、闲暇、无劳顿及享福祉的人的其他特性等,即含有最多的闲暇。也因此之故,亚氏总结说,幸福就在于沉思,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2]1177a20-1178a8。即是说,幸福就是人生所要命中的最高善,也是所有善事物的最终价值指向。
与亚氏不同,孔子论“射”关注射箭之德背后的礼仪,射者要遵循射礼,目的是礼。“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礼记·射义》)“射”在《论语》中出现的并不多,第一次就彰显了论“射”的目的。“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这里所谓的“射”,不仅指射箭比赛,更重要的是指射箭之礼——乡射礼、大射仪。此外,孔子还说:“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朱熹注曰:“射不主皮,乡射礼文。为力不同科,孔子解礼之意如此也。”[9]因此,凡是不合“礼”的都应当禁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强调“礼”是孔子论“射”的目的所在。
从孔子思想体系的整体上说,“礼”比“仁”的层次更高。在《论语》中,孔子论“礼”常以具体的礼学范畴,特别是“仁”来表达。“仁”的内涵极其丰富,包含了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原则,还构成了人的主观心理因素。“复礼”为“为仁”的内容和方向所确立的观念是:“礼”为第一位而“仁”为第二位,即“礼者仁之实也”[10]43。“仁”不过是让“礼”获得更大的伦理性和道德意蕴,并使其重新获得内在生命支柱,“仁”提升了“礼”的内在价值,使其直接与人性深处最深厚的根本相沟通,故“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核心地位①在孔子以前言及“仁”的文献并不多,谈“礼”的却相当多:从孔子“吾从周”(《论语·八佾》)的志向可知,其所“从周”者就是周礼;孔子于“礼崩乐坏”之世毕生所为是“克己复礼”,孔子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只有在周礼的规范下,春秋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才能被遏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僭礼行为才能被杜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社会秩序才能建立;在《论语》的记载中,孔子忍无可忍的就是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礼行为;当弟子“林放问礼之本”时,孔子夸赞是“大哉问”(《论语·八佾》)。因此,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
不仅《论语》所言皆礼,且“六经”亦通于“礼”。《礼记·曲礼》有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故君子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礼记·礼器》)“礼”于人于国都是非常重要的。从国家角度说,“礼,国之干也。”(《左传·僖公十一年》)孔子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经解》)而对于个人来说,“礼”乃立身之本。“礼,人之干也。”(《左传·昭公七年》)故“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鉴于此,甚至断言:“无礼必亡!”(《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如钱穆先生所深刻分析的:“因治掌故以明礼,习礼文以致用,固当时之学问然,即孔子所以见重于时者,亦惟在其知礼。”[11]5-6因此,《论语》中的“礼”具有极强的伦理道德的特征。“周公‘制礼作乐’,实现了其由宗教性向政治性、伦理性的一大转变;孔子继衰世而起,‘援仁入礼’,完成了其由政治性向伦理性的完全转化。自此以降,‘礼’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其向外‘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向内‘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使全社会通过‘礼’构成一上下贯通、涵浑蕴藉之伦理整体。”[12]这一伦理整体的价值指向是和谐。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为天下之大本,寓意和谐,即是说,“礼”的价值指向是和谐,而中庸作为“礼”的表现也当以“和为贵”。“和谐是中庸的精髓,中庸和谐的精神是中国伦理最高精神,而天人合一则是这种精神的最高价值与最高精神指向,它是中国伦理的整体精神形态。”[13]39尤能体现这种中庸和谐精神的是孔子所言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这种“不纲”、“不射宿”的行为,与其说是出自“仁人之本心”(朱熹语),不如说是一种时中、制中之礼,是中庸之道,是一种和谐。孔子这种向大自然有限度地索取体现的正是人与天、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与境界。“所谓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是为人的道德行为,尤其是道德修养设立了一个永远也无法达到的‘极高远’的最高境界与最后归宿,它要求人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德性涵育万物,最后与天合一。”[14]257这一点是亚氏所不能匹及的。
总之,亚氏论“射”目的在善,价值指向是幸福;孔子论“射”目的在礼,价值指向是和谐。为何两人论述相同的事情而目的不同、价值指向也不同呢?其原因在于,二人思想体系的理论预设和逻辑出发点是不同的。
三、善与礼的理论预设与逻辑出发点
灵魂说是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是人性和神性、人论和神论的交汇地。它虽非亚氏首提,但却为其所用。他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中明确地将灵魂说置于第一重要的位置,他说:“所有的知识都是应受尊重和珍视的。就知识的精确性,或就知识的对象崇高和奇妙而言,有的知识更值得尊重且更有价值。就这两方面来说,我们有理由把研究灵魂的学问置于首位。众所周知,关于灵魂的知识对于真理的推进,尤其是对自然的理解有着巨大的贡献,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灵魂是动物生命的本原。”[15]402a1-9
关于灵魂的学说是亚氏自然哲学、形而上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本体论还是知识论都与灵魂学说有关。亚氏的灵魂说还与他的政治学、伦理学等实践学科密切相关,这些研究人的生存、行为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以灵魂说为基础的。研究灵魂对于理解亚氏伦理学有很大的帮助,亚氏曾明确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去研究灵魂。他认为,我们所要研究的德性是人的德性,不论是人的善还是人的幸福,都和灵魂有关,幸福也是灵魂的现实活动。我们的生活不是靠任何其他的东西,而是靠灵魂。德性就在灵魂中,也正是由于灵魂的德性,我们才生活得美好。
亚氏认为,灵魂是作为质料、形式以及质料与形式的结合三种意义上的本体。质料是潜能,形式是现实。“灵魂就是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躯体的头等现实性。”[15]412a25灵魂是有生命躯体是其所是的本质,它是原理意义上、定义意义上的本体。“灵魂在最首要的意义上乃是我们赖以生存、感觉和思维的东西,所以,灵魂是定义或形式,而非质料或基质。”[15]414a12-15亚氏将灵魂分为无理性的部分和有理性的部分,而无理性的部分又分为两部分,一是造成营养和生长的部分,即植物性的部分,这种能力是所有生物共有的;另一部分是在某种意义上分有理性的部分,即欲望的部分,这种能力是动物性的感觉。灵魂中有理性的部分即心灵部分,心灵是指灵魂用来进行思维和判断的部分,也就是“理性灵魂”。根据亚氏的观点,灵魂具有消化生长、欲求、感知、运动的能力以及理性的能力,惟有理性能力为人的灵魂所独有,人的功能就在于灵魂的理性能力。
功能论证是亚氏伦理学的重要方法,虽非亚氏的原创,却也有其特色。亚氏通过功能论证表明,幸福的生活是理性生活,是理性灵魂体现德性的活动。功能是一物之为一物的特征,是事物之所是该事物的本质——本是。依此,人的功能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亚氏看来,只要一物功能实现得好——卓越,此物就具有德性。人之所以具有德性也是因为其功能实现得好,亚氏认为理性乃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植物的功能所在。“人的功能是灵魂的一种合乎理性的实现活动与实践,而一个好人的功能就是良好地、高尚(高贵)地完善这种活动。”[2]1098a13-15以理性诠释德性是西方文化的传统。亚氏认为德性的区分同灵魂的划分是相应的,可分为伦理德性(非理性部分听从理性而分有理性)和理智德性(具有理性)。“每种德性都既使得它是其德性的那事物的状态好,又使得那事物的功能发挥得好。……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处于好的状态,又使得他很好地发挥人的功能的品质。”[2]1106a15-20“德性是一种能做出选择的品质。这种品质在于一种中庸状态,而中庸状态是相对于我们而言的,是由理性所规定的。”[2]1107a1-4
不论是灵魂划分还是德性区分,都是以人的灵魂中存在理性为前提。亚氏论“射”关注的是射箭之理——中庸的道理,目的在于善。善的最终目的是最高善,其价值指向是幸福。人的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实现活动,善和幸福都是和灵魂相关的,善就是功能实现卓越,人的善就是从整体上把握并规定源于自然之欲望的理性实现其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亦即具有德性,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在于理性。也就是说,灵魂是亚氏伦理理论的理论预设,理性是其逻辑出发点。
我们再转向孔子。礼的价值指向是和谐,这种和谐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即是“诚”的境界。“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记·中庸》)孔子论“礼”的理论预设是天道。然而,“天道”与“礼”之间并没有天然的联系,二者之间需要有贯通的中介——情感。正是基于人对天道之敬的情感,天道下贯而为人道,并在人类社会集中体现为礼。
“天道”即“人道”,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方式和道德准则,“天道”、“人道”也只是一个“道”。中国先秦儒家和郭店竹简原典儒学一再强调,“道始于情”,“道由情出”,“礼,比本于天”,且“礼始于情”,“发乎情止乎礼义”。由此可以得出关于“道”、“礼”、“情”的这样一个圆圈式而非直线性的关系图(图一)。
“1”所表达的是:道即天道与人道,天道是礼的理论预设,礼是人道在人类社会的集中体现。“2”所表达的是:“礼生于情”,亦可治情。“3”所表达的是:“道始于情”,此“道”一般是指“人道”。“情”作为某种根本或出发点,是人道甚至天道之所生发。总之,由此图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尤其是先秦儒家是非常重视情感的,并将其作为生活的本根实在。
孔子论“礼”时谈到,“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礼记·礼运》)这就把“礼”的理论预设建立在当时最高的哲学范畴——天道之上,使礼具有最神圣的地位,并成为宇宙间固有的一种客观存在。“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礼,必本与天。”(《礼记·礼运》)而《礼记·礼器》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也者,理智不易者也。”(《礼记·乐记》)因此,“从‘道’的角度看,《礼记》事实上是把‘礼’定义为客观不变的道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反映。”[16]279
在孔子看来,“礼”是人与禽兽之别的标准。“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论语·为政》有言:“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此处的“敬”就是指“礼”。这种人禽之别的“礼”在儒家的丧礼中描述得最为明显,可以体现出“礼”之缘情而作的内涵。“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记·檀弓上》记载:“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即丧礼要以出于哀戚的真实情感为本。其次,从“礼”的起源看,“礼”表现的是对祖先或上帝的崇敬、对未知事物的敬畏,凸显出“敬”的心理情感,有“敬神如神在”的心理虔敬。诚如孟子所言:“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这种“敬”的情感要贯穿于人之生与死的全部,所谓“敬始慎终”(《荀子·礼论》)。否则,“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即是说,“敬”的情感必须借“礼”来体现,“礼”的法则必须赖“敬”而推行。“敬”与“礼”不过是互为表里的二位一体的关系。牟宗三先生指出:“在中国思想中,天命、天道乃通过忧患意识所生的‘敬’而步步下贯,贯注到人的身上,便作为人的主体。”[17]18
“敬”不仅是“礼”,更是“情”。孔子所言之“礼”当是出于人的情感,以情为本。礼出于情亦可治情。《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即情感表现为中和就是礼,就是德。这种情感表现中和的德性与礼,在《尚书·皋陶谟》中表现尤为突出:“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
总之,在“道”、“礼”、“情”的关系图中,我们可以直观看到孔子的德性伦理是一种“情本体”(李泽厚语)的伦理思想。“礼”在孔子看来就是情感表现中和,“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者也。”(《郭店竹简·语丛一》)“礼生于情。”(《郭店竹简·语丛二》)礼是人道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表现,而人道是由天道下贯而成的,“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郭店竹简·性自命出》)在郭店竹简所体现的“天—命—性—情—道—教”的中国哲学逻辑中,也并没有“理”的存在。在儒家看来,这里的“情”就是以生理血缘关系的亲情为基础的,即是基于生理血缘的“孝—仁”为核心的伦常情感。正如樊浩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文化一开始就选择了情感的道路而拒绝向纯粹理性方面发展。……情感是家庭生活的绝对标准,血缘关系的绝对逻辑,而家族血缘又是情感培养的母胎,这种双向的运动及其相互作用导致了情感在文化价值系统中的绝对意义。”[13]13所以说,孔子的德性伦理学是以天道为理论预设,而以情感为逻辑出发点的。
综上所述,亚氏论“射”的路径是:射箭—中庸之理—德性—善—幸福—灵魂—理性;而孔子论“射”的路径是:射箭—中庸之德—德性—礼—和谐—天道—情感。由此两个路径可以发现:中西两种不同的传统德性伦理学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与传统习惯。当今正面临着德性伦理学复兴的时代潮流,那么,是西方亚氏理性主义德性伦理学在复兴运动中更具生命力和始源性,还是中国的孔子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在复兴运动中更具推动力和普遍性,抑或是真正的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在于两种德性伦理学的相资相用?我们拭目以待。
[1](美)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林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载《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美)A.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美)大卫·福莱:《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宗白华:《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Bernard Williams.Ethics of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7]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 期。
[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八佾》,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王夫之:《周易外传·贲》(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11]钱穆:《国学概论》,台湾: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
[12]陈续前:《礼——从周公到孔子》,载《孔子研究》2009年第4 期。
[13]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樊浩:《文化撞击与文化战略》,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载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6]勾承益:《先秦礼学》,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版。
[17]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