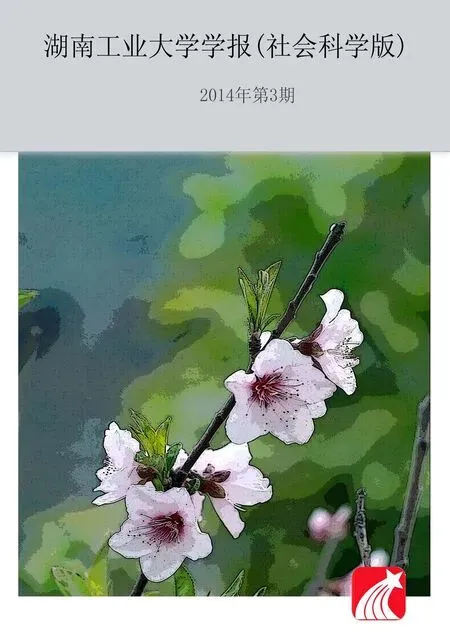石头精神:忧郁中沉思
——论吴投文的诗歌
2014-04-01孙德喜
孙德喜
(扬州大学 文学院,浙江 扬州 225002)
2003年,吴投文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土地的家谱》[1],3年后,他在北京汉语诗歌资料馆帮助下又出版了另一本诗集《忧郁的石头》。随后,他一直活跃在诗坛上。他的诗情喷涌而出,一发而不可收,他的诗作连续被收入《2007中国新诗年鉴》《2008—2009中国诗歌双年巡礼》《2012-2013中国年度诗典》《新世纪诗典》《中国当代短诗300首》《中国当代汉诗年鉴》(2012卷)等各种诗集,从而引起了一些诗歌评论家的关注。最近,他和诗人朱立坤联合出版了诗集《中年生活》[2]。这十来年间,吴投文的诗歌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石头精神和深沉的忧郁贯穿始终,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值得关注和探讨。
古今中外,许许多多诗人诗作氤氲着忧郁和感伤,从两三千年前的屈原到鲍照、曹植、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再到现代的徐志摩、戴望舒、艾青;从古希腊的荷马到莎士比亚、济慈、里尔克……都在诗作中流露出忧郁的情绪。吴投文和这些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一样,在忧郁中投入诗歌创作。吴投文诗歌中的忧郁已经引起学者的注意。王士强认为:“吴投文其人其诗都有一种忧郁的气质,这种忧郁并不是外在、鲜明的,但却一直存在,是一种内在的、隐而不彰的底色。”[3]不过,王士强的所言只是阐述诗人创作的“非学院化”的一个铺垫。吴广平在《诗人的孤独——读吴投文的诗集〈忧郁的石头〉》[4]中将吴投文的忧郁与孤独联系起来进行探讨,也很有意义。笔者认为,为深化吴投文诗歌的研究,这个问题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吴投文的诗沉重而厚实,赤裸的,就像石头一样。石头从来不会随波逐流,倒是经常受到波浪的冲击和磨练;石头是质朴的,非常率真,随性而为。虽然诗人没有像贾平凹那样多次精心描摹他心中的石头,一再展现石头意象,但是石头精神蕴涵其中。吴投文诗作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哈罗”系列。诗中的“哈罗”从形态上讲不过是一条常常为人们所瞧不起的狗,然而在吴投文的笔下,这不只是一条狗,而是一位行为哲学家,它以自己的毫无矫饰的直率的行为阐释着一种哲学、一种思想或者说一种观念。古希腊哲学大师认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然而,哈罗的看法却完全相反:“人总是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这看上去似乎是与哲学大师的辩驳,实际上不过是一次解构。因为,哈罗并没有对他的哲学作理论上的推演,也没有引经据典地摆开论战的姿态,而是通过具有嘲谑性的“抬起腿撒尿”和“吞吃地上的一堆屎”来表达的,而就在这时,与哈罗形成对话的“我”就在距其“三米远的地方”。此时的这个“我”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而是一个在场的对话者,因为,只有“我”从哈罗的行为中解读出了其哲学观念。哈罗另一个哲学思想表达的是对人的看法,它觉得:“人是错误的动物”,原因是“人总是离开自己的本质而生活”。哈罗是通过它与一条母狗的公开的性交来“发表”自己看法的。当时,人是作为旁观者出现在哈罗性交的场所的,人们虽然看到哈罗的行为,但是并不真正地理解,只是可怜地看热闹,脸上还露出几分不怀好意的微笑。而当哈罗号召性地“大声叫道: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现场的旁观者似乎感到羞愧,于是“争先恐后离去”。对于哈罗,人们并不理解其存在的意义,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问它的主人是谁,把它至多视为人的宠物,根本没有意识到它就是它自己的主人。当“我”告诉人们这一点的时候,竟然引起人们的“哈哈一笑”——把哈罗当作是“野狗”了。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具有人的优越感的人们原来是这样愚蠢。吴投文的另一首诗《我在路上碰见一只狗》虽然没有被列入“哈罗”系列,然而表达的是与“哈罗”系列一样的思想内涵。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就以“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莎士比亚语)自居,制造出令人陶醉和飘飘然的神话,总喜欢以高居一切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内心充满着作为人的优越感。然而,现实的存在并非如此。诗中的“我”在路上碰见了一只狗,总以为自己与它有着“本质的区别”,因而在“往前走”的时候,有意“与狗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显示出人与狗的不同。但是,当这条狗遇到另一条狗时,两条狗居然那么亲密无间,彻底摧毁了人自大的神话,让“我”这个自以为高贵的人“感到孤独”。然而当“我”想加入狗的行列时,却又“无法脱下自己的面具”。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裸奔的女人》,这个“裸奔的女人”“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雪白,明亮,像一朵奔跑的火焰”。对于这个女人,满街的人除了带着邪意目光的看客之外,就是试图阻止其“裸奔”的警察,只有抒情主人公理解其“裸奔的”意义,并且产生了与其一道奔跑的冲动。问题是“这只是一瞬间的意念”而已,最终没有付诸行动,因为他同样“无法脱下自己的面具”。
从吴投文的这些诗作来看,他所崇尚的是率真的本性,或者说就是毫无遮掩与装饰的赤裸裸的天性。这种天性与其说是人的本性,倒不如说是石头的天性。我们知道山里的石头就是无遮无掩的,从来就不知道乔装打扮自己,天然的石头论其形状可以说是千奇百怪、形态各异,正如著名作家贾平凹所说:“最是那方方圆圆的石头生得一任儿自在,满山遍坡的,或者立着,或者倚着,仄,斜,蹲,卧,各有各的形象,纯以天行,极拙极拙了。”[5]有些石头给人的印象甚至是比较丑陋的,面貌有些狰狞。然而,石头就是石头,从来都是实实在在,决不卖弄、作秀和显耀,而且耐得住孤独和寂寞。吴投文将自己的第二本诗集命名为《忧郁的石头》,其寓意大概就在这里。然而,在现代社会里,由于各种原因所致,许多人失去了率真的本性。不少人用贵重的化妆品与华丽的服饰装扮自己,其结果却是在浮躁、虚荣和欲望的改写下,反而失去了原来本真的自我。为了生存的需要,我们在人群中不得不戴上厚重的面具,总是以各种方式把自己的真实的情感和内心的欲望隐藏得很深很深。在社会各种潜规则的作用下,我们被扭曲了灵魂,变得十分可怜。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吴投文所推崇的石头精神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在石头精神的反衬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显得非常的不完整,是支离破碎的,是虚假的,是出了严重问题的。《不完整的世界》描述了出了问题的现实世界,诗中写道:“这世界/不能说是完整的了/它曾经也肯定是不完整的,但现在更加不完整了。”这看起来只是诗人“在上班的路上”“冒出了这个奇怪的念头”,其实是有充分的现实根据的:“一个同事出走了”;“一个同事离婚了”;“还有一个同事进了监狱”……作为他自己又如何呢?他“已经厌倦了生活”,于是产生了放逐自己的念头——“想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走走”。面对着如此的现实世界,怀有理想主义情绪的诗人怎么能不感到厌倦呢?或者说他的厌倦是由于他无法适应这个现实的世界。现实世界的不完整让他感到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难以忍受。然而,问题并不完全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他的出走仅仅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他最终没有放逐自己,他还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他还是要在这个不完整的世界里呆着。他想出走而最终没有出走,给他带来了尴尬——人们认为他病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这种尴尬表明:抒情主人公陷入了孤独的境地,他看出了这个世界的问题,他想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没有人理解他。他的这种情形使得他就像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样,是一个十分孤独的清醒者。然而,他的思想大于行动的特性,使他始终无法解决与现实的不完整的世界的冲突,因而他就像18世纪欧洲的许多浪漫主义诗人一样“忧郁”。《忧郁的石头》表达的就是诗人内心深处的累积至深的忧郁。
其实,这个世界岂止是不完整,简直就是一个病态的甚至是罪恶的世界。《去年冬天的雪》《阿香的夜晚》《我在大街上走着》《阿宫山》《诗歌执照》《寻找诗人》等诗作都展示了现实世界的丑恶。阿香本来是山村里一个像雪花一样纯真的少女,她怀着对现代生活的憧憬到深圳去闯荡,结果沦落风尘,被迫卖淫。当年那个“扎着羊角辫”,“口含一朵雪花/手折一枝梅”的阿香(《去年冬天的雪》)现在变成了“一天要重复很多次”“匆忙中拉上了裤子”(《阿香的夜晚》)的动作的卖淫女。是谁将天使变成魔鬼?是阿香自己吗?显然,不是阿香本人的堕落,而是这个荒唐的世界。《我在大街上走着》中的“我”遇到的卖淫、乞讨和斗殴都是这个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就一向为人们所崇敬的诗坛来说,现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诗歌执照》以夸张和嘲谑的笔调,道出了诗人的尴尬处境:且不说“李鬼太多”闹得诗坛乌烟瘴气,搅得诗坛“一锅混(浑)水”,特别是作为权力象征的主编大人更是“头昏眼花”,尸位素餐。这种现实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诗人“死去的”时代,现实中许多所谓的“诗人”其实都只是徒有虚名,“他们红着眼睛/在人群中寻找一枚分币,或者更多的分币”;有的所谓“诗人”看上去像模像样,实际上往往是“骑着一匹哈巴狗回家,迈着诗歌的步伐”;还有一些“诗人”“远离痛苦与黑暗的中心/远离真实与生命,沿着一枚口香糖溜达”(《寻找诗人》)……然而,真正的敢于正视现实、拼着热血和生命呐喊与高歌的“佩剑诗人”却又到哪里去寻找呢?如果仅此而已,我们就可能将吴投文定位于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将他的诗作判定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其实,当读到他更多的诗作时,我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判断过于简单化,也显得非常草率,没有认识到吴投文写作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我们从他的诗作看到:他笔下的现实就像在世俗文化的洪水冲击之下泥沙泛起、浮叶漂流的河道,恰在此时,有一块石头任凭洪水冲击而岿然不动,它总是以沉思的姿态面对着身边的一切。
吴投文所崇尚的生命的本真、对人的神话的解构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很容易让人想到战国时代行吟于楚湘泽畔的屈原,这位中国最早的伟大的杰出诗人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他的“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浊唯我独清”(《渔父》)。吴投文的诗确实让人看到屈原的身影,给人以强烈的愤世嫉俗之感。自古以来,确实有为数可观的诗人总是在怀才不遇和愤世嫉俗之间徘徊吟唱,哪怕就是像曹操这样的旷世豪杰有时也免不了愤世嫉俗,更不用说那些平生不得志的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本文并不打算就此展开论述,只是想说,怀才不遇和愤世嫉俗的背后多少隐藏着作家和诗人的几分自恋以及主体与客体难以沟通与和解的矛盾。问题是吴投文并非简单地继承前人的衣钵,一味地自恋与自怨,他是在批判人的高傲而偏执的同时,寻求人的本真之所在。而他所追求的人的本真可以说是他对于生命本质的理解和感悟。长期以来,吴投文孜孜不倦地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去研究文学大师沈从文,这无疑大大地推动了他对于人的生命哲学的深沉思考。这种理性的思考积淀于心,久而久之便潜移默化地转移到诗歌创作中来,使得他的诗作显示出深厚的现代主义思想内涵。因此,如果将吴投文仅仅视为一个愤世嫉俗者或者自恋主义者,显然是误解了他。更确切地说,吴投文是一个思想者,忧郁只是他的一种神态,一种目光中包含着的东西,思考才是他的本质。
作为思想者的吴投文,并不停留于对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思考,他更感兴趣的是某些关于社会和人性本质的哲学思辨。所以,他的思辨多少给人以凌空蹈虚之感。最具典型性的是《白马》一诗,吴投文似乎探讨的是名与实的问题:作为事物名称的“白马”和作为人名的“白马”究竟具有什么关系?《鱼》《零,或者圆圈》同样是关于名与实的思辨。这种名与实的问题实在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实在是非常深奥,而吴投文却思考得有滋有味,而且融化于诗的形象和语言中。像这样的哲学性思考,我们在他的《一根羽毛》《饮者》《世界》《在黑暗中》《打开一个盲目的梦》《刀》《对一只老鼠我真该告诉它点什么》《怀疑,或者梦呓》等等都可以体会到某种深沉的意味,其中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意蕴让我们回味无穷。这已不是我们简单地用“深刻”能够概括的。所以,吴投文的这些诗不能不叫人佩服,正如他在《寻找诗人》中所说的“我真该向你脱帽致敬”。
在吴投文对于人的生命的思考中,除了哲学以外,人们还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某种宗教思想的存在。就他的石头精神而言,石头的那种返朴归真的理念与道家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此同时,佛教和基督教的某些思想观念在他的笔下时有所现。《墓地》就蕴涵着佛教的某种精神意韵。《欲望与拯救》《无题·我企图在一场噩梦中》中基督教的意味比较浓厚。在吴投文的这些浸润着宗教思想与文化的诗作中,最让笔者感动的就是《最后的祈祷》。笔者之所以深受感动,并不是说这首诗演绎了何种宗教哲学或者图解了什么宗教教义,而是吴投文深入宗教之后又跳出宗教的一次思想升华。在这首诗中,诗人面对着人生的罪孽和世界的罪恶,揭示的是人性中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致命的弱点,进而以基督的精神作“最后的祈祷”,然而这里的祈祷已不同于基督教的那种向上帝的祈祷,因为在诗人这里,上帝也同样是有罪的,同样需要忏悔、改过。因为上帝与魔鬼相互纠缠在一起,以致难以分开。这就需要每个人以极大的勇气在祈祷、忏悔、改过中获得新生,使每个人消除与他人的隔阂和矛盾而“结合在一起”。写于新近的《一个人的影子》也是颇具宗教意味的作品。这首诗虽然没有突出某一具体的宗教色彩,但是其中无疑蕴涵着极其深厚的宗教精神。诗中由“我”“影子”“旅途”“远方”和“身体”等因素构成一个对话场,探询的既可以说是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也可以说是精神的归宿,给人以无限的遐思。
吴投文是石头,具有石头的质朴和率真,这在他的诗歌语言上同样有所表现。中国的白话诗自其诞生之后,其在语言上的探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最初的白话诗人受西方语言的影响,他们的诗歌语言固然适应了诗体大解放的要求,但是显得比较散淡,欧化色彩较重;随后的新月诗派与现代诗派的诗人矫枉过正,推崇的是“戴着镣铐跳舞”,追求格律、雅致和象征,诗歌语言走向贵族化;稍后兴起的红色诗歌在大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过于极端地强调大众化,使得诗歌语言变得淡而无味,其文化内涵日趋浅显。到了新时期之初,朦胧诗浮出地表,在语言上对于50-70年代诗歌语言开始拨乱反正,在典雅中追求深刻,诗歌语言显得新奇诡谲;后来的“后新诗潮”又对朦胧诗的语言表示厌恶,开始追求语言的口语化,并且以后现代的和平民的姿态解构诗坛上的深刻,展示的是语言的平实。正是在这个时候,吴投文开始闯荡诗歌王国,他的少年的热情似乎一开始就与“后新诗潮”一拍即合,他非常乐意以纯粹的口语创作诗歌。不过,随着他诗歌创作不断走向成熟,吴投文不再跟在“后新诗潮”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努力探索自己诗歌的言说方式,到了2 000年的时候,吴投文的诗歌语言在石头精神的浸润之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就在《看性病门诊的女人》《老张的情人》《公汽上的孕妇》和《裸奔的女人》等诗作中,诗人使用的是生活中的叙述语言,而且这种陈述是以现在进行时的时态出现的,给人以一种在场感,很容易将读者带入到诗歌的情境中去。然而单纯地强调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如果不注意思想内涵,就可能令诗作的语言变得轻飘飘的,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那么,如何让口语式的语言显得厚重沉实?吴投文的诗歌语言给我们提供了比较成功的范例。他的“哈罗”系列以及《刀》《桃花开了》等诗作的语言看似每一句都很清淡,但是诗人在现场的口语化的叙述中建构起新的语义场,进而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和思考的空间,因而其诗的语言给人以一种透亮的澄澈感,不是那种一览无余的透明,而是澄澈而又深不见底。所以,读到他的这些诗作,读者自会感到他的诗歌语言并不华丽、高雅,而是以大白话的形态出现,显得非常朴实,内蕴深厚,就像石头一样。
吴投文在他的《忧郁的石头》一诗中写道:“它知道自己/不过是一块石头,不过是在河岸仰望天空/它的痛苦与呻吟,无法被流水带走”。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诗人的精神和灵魂的自画像,或者说它是吴投文诗歌最恰当也最准确的注脚。如果能够抓住这把钥匙,就可以顺利地走进吴投文的诗歌世界,解开其诗歌王国的密码,与其展开精神上的对话。
[1] 吴投文.土地的家谱[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2] 吴投文.中年生活[M].香港:银河出版社,2013.
[3] 王士强.学院诗人的非学院化写作——以吴投文为例[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6-19.
[4] 吴广平.诗人的孤独——读吴投文的诗集《忧郁的石头》[J].艺海,2010(12):111-112.
[5] 贾平凹.贾平凹散文自选集[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