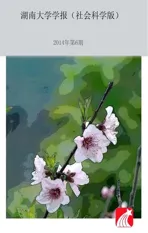被忽视的晚清诗文拓荒者——论胡先骕之诗文评*
2014-03-31付洁
付 洁
(山东大学 文 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 南 250100)
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际,胡先骕在《学衡》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表达自己政治、文化见解的文章,如《文学之标准》、《评尝试集》、《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论批评家之责任》、《说今日教育之危机》等,体现了他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他以《学衡》等杂志为阵地,反对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的白话文运动,进而对当时的政治、教育、文化情况皆有所批评。同时,他亦发表了多篇关于清人诗词集的评论①,当属第一批对晚清诗歌做详细、深入研究的作品。保守主义的文化观决定了胡先骕是传统诗文的阐释者、继承者,而对晚清诗歌的开山性研究,又决定了其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到今日仍有不可超越的地位。在古代诗歌的研究中,晚清诗歌研究属于起步较晚的一个领域,大量优秀的诗歌至今仍未获得足够的关注,而对少量研究著作的研究,更乏人问津,这种情况亦导致胡先骕的拓荒之功迟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1925年之后,胡先骕在《东南论衡》、《独立评论》、《青鹤》、《国立中正大学校刊》、《观察》等刊物,都陆续发表过人文领域的文章,但或许是因为他的文化观念有所改变,或许是他与胡适的私交转为密切,又或许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让胡先骕将注意力慢慢转移到其他方面,总之这些文章中已基本不再涉及新旧文学之争,除1926年的《评亡友王然父思斋遗稿》外,亦再无评论诗词集的专文问世。
一 新人文主义和儒家传统思想相融合的文化观
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庵,江西人,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主攻植物分类学,一生成果颇丰,为国际植物命名委员会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一级研究员。同时,他又是南社成员,《学衡》杂志主要撰稿人,新人文主义学派的信徒,其诗集由钱钟书代为编订成《忏庵诗稿》。
胡先骕3岁受训启蒙,5岁读完《论语》,6岁识字万余,10岁赴南昌府应童子试,12岁得沈曾植赏识,入南昌府洪都中学,15岁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曾受教于林纾。少年时期的勤奋攻读和名师授受为胡先骕打下了坚实的儒家传统文化基础,故其文评中对古代诗文的论析皆能切中肯綮,有较强说服力。
1913年2月,19岁的胡先骕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攻读森林植物学。留美期间,胡先骕曾参与创办《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在专业领域取得了优异成绩,于1916年获农学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留学时期认识了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大师白璧德,曾得以“面谒先生,亲承教诲”[1]。白璧德对中国传统文化,如孔孟老庄等,都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其学说中“节制”、“道德责任感”、“中正”等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有天然契合之处。胡先骕一经接触,便引为知己,成为白氏学说的信徒。《学衡》第2期《评尝试集(续)》一文中,胡先骕将白璧德的学说称为“人文主义”①为区分15、16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文主义,白氏的学说通常被称为新人文主义,但白璧德本人并不认同这一称呼,《学衡》在大多数的文章中,也选用的是“人文主义”一词。,第3期又刊登了胡先骕所译的《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人文主义这一名称,自此为《学衡》同仁沿用。虽其后胡先骕较少从事翻译白氏学说的工作,但却终生服膺新人文主义,许多观点与白璧德一脉相承。
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融会贯通,形成了胡先骕保守主义的文化观。他的很多观点,很难区分究竟是来源于儒家传统思想还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比如对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的态度,胡先骕不反对浪漫或写实的手法,但却反对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认为这是对浪漫或写实手法的过度运用,前者不切实际且逃避道德责任,后者则将人类与禽兽等列而论,都应当被批判。表面看来,对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的指责,与白璧德一向之主张极为相似。但进一步分析时,便可发现胡先骕批判的出发点是其违背了文学的中正原则,这与儒家的中庸思想又若合符契。
胡先骕终生以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这也与新人文主义者对道德的极高诉求是一致的。他抑制感情的放纵,讲求理性与克制。这不仅体现在他克己复礼的人生观中,也体现在他保守正统的文学观中。胡先骕屡次强调适度、中正,认为出色的诗作必然具备这两点。比如他不反对雕琢,却反对因雕琢而伤气;不反对以俗语俗字入诗,但反对俗语俗字过多;非不能写艳词丽句,但定要含蓄隐晦。他对文学的要求为“不趋极端,不为矜世骇俗之论”[2](P42),“无一时之狂热”,“不必务求花样翻新也”[2](P43),与其为人处世的标准十分一致。胡先骕虽宗法宋诗,但却极欣赏诗有唐风的张之洞,一方面固然是被其政治品格折服,另一方面则因为“文襄学术以平正通达为旨归”[3](P122),这也正是胡先骕所追求的。
二 温柔敦厚、含蓄传统的评论原则
胡先骕对诗文的品评,以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为基本原则,同时又继承古代诗歌的传统,重视诗之浑化、韵味、理境、意趣等特色,并强调通过摹效前人优秀之作来获取入门途径。
胡先骕用“君子之德”来要求诗文之品格,以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为旨归。他对刘光第之诗评价甚高,但刘光第诗中有大量刺时之作,胡先骕认为“失之过怨”、“皆怨而毒,大非臣子所宜出者”,甚至直言“以此贾祸,亦有自取之道”[4](P122)。可见对诗文立意中正、感情节制的看重。更明显体现这种标准的,是胡先骕对金和之诗的厌恶。他不但著专文驳斥金诗,且在多篇文章中大加批评,认为其不合臣子之德。如“吾以为金氏之诗,岂但轻薄,直是刻毒”[5](P117);“其气格之凡猥,韵味之寡薄,明眼人自能辨之”[6](P119);“此市井儇薄少年,利口伤人之习,非士君子所宜效也”[6](P120);“但知讪笑,且语气时近轻薄也”[6](P121);“虽备极轻薄刻毒之能事,而无一至诚惨怛之语”[6](P124),痛加批评,毫无赞赏之情。胡先骕又举例比较,证明金和之讽喻诗缺乏真挚之情,故又不同于杜甫之新乐府。金和才丰而性躁,极擅七古,偃蹇的人生经历使得其诗以讥讽反语为特色,这种遇不平之事必欲吐之方快的性格成就了金和,也使得其诗缺少沉郁深刻的一面。金和之诗多有戾气,实为一大弊病②金诗历来备受争议,对其的评价趋向两个极端,梁启超、胡适、陈衍评价最高,钱仲联、汪国垣等相对中肯平和,徐英、胡先骕则将金诗批判得体无完肤。徐英对金和的指责多集中于词句韵律方面,胡先骕的指责则多集中于思想方面。。胡先骕一再强调“修辞立其诚”,认为感情是否真挚重于韵律是否谨严。金和之诗缺乏中正深沉的情感底蕴,违背了怨而不怒的传统文学道德,故虽“才气横溢、言词犀利、诚有过人之长”[6](P126),却终不能成为一代大家。应当指出的是,胡先骕对金和的批评,实际上反映出了胡先骕文化观的相对独立性。对才华横溢之奸臣小人,只要作品在传统的伦理道德范围内,胡先骕定能慧眼识珠,大加称赞。反之,如果诗文本身之思想情感超越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则即使此人为人处世无甚瑕疵,亦必不为胡先骕所喜。
除为文之德恪守温柔敦厚外,胡先骕对各种文学体裁地位的认识也比较保守。首先,胡先骕认为体裁不同,写法便不同,比如诗文有明确区别,“文重理智,诗重感情,重感情则不妨引用俗语,此诗中用俗语较多之故”[5](P125-126)。所以像胡适这种分不清是散文还是诗的作品,胡先骕认为不应提倡。同时,胡先骕又认为诗高于其他体裁,即使在古体诗内部,格调之高低也不相同。“中国诗以五言古诗为高格、诗最佳之题材。而七言古、五七言律绝与词曲为其辅”[7](P118)。再者,词曲又高于杂剧,“词曲之格较弹词剧本为高,此吾人所承认者”[7](P112)。近代的戏曲改良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戏曲之地位有了极大提升,被视为改造社会和国民性的武器。但胡先骕并不赞同这些改变,仍坚持传统的观念,划归戏曲为最末等。
而小说在胡先骕眼中,与杂剧一样,地位最低,“小说杂剧在吾国不成庄重之文学,此与欧西诸邦积习有异者也。至金人瑞始以水浒西厢与史记庄骚并称,甘冒士林之大不韪”[2](P19)。胡先骕认为各体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低等体裁可以模仿高等体裁的写法,反之则不行,更不能将两种有高下之别的体裁并列而论。所以他反对金圣叹将水浒西厢与史记庄骚并称。又如评论金和之诗时,胡先骕亦曾言“夫以温柔敦厚为教之诗,乃得力于儒林外史,其品格之卑下可想矣”[5](P117)。以写小说之法写诗,在胡先骕看来十分荒谬。
胡先骕对诗文传统的看重还表现在他多次强调“摹效”的重要性。他认为古人作诗,十有八九皆从摹效前人之作始。要继承文化传统,自然不能抛开古人规则,所以他极力反对胡适论诗八大主张中的“不摹效古人”一条。胡先骕认为摹效与创造并不矛盾。首先,必须摹效古人作诗的技法,这与雕刻、书法、音乐等艺术一样,不学基本之技法,则是弃前人心血于不顾,是回归草昧时代。技巧纯熟,方能随心所欲的表达感情与思想。其次,关于诗之思想,因为个人性情不同、人事变迁等多种因素,诗之内涵不可能完全等同,故无需担心摹效导致诗歌面目千篇一律。摹效是学诗的基石,有了这块基石,加以自己的勤奋和才力,则可渐入佳境。没有这块基石,则找不到学诗的门径,又何谈成就之大小?
可见,胡先骕所谓的摹效是继承之意,绝非照抄剽窃。摹效的目的,在于获得正确的入门之法,心中有所得后,方另立门户,别开一格。韩白黄陈皆学杜,但被称颂千载,原因正在于他们学杜而不囿于杜,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实际上提倡不摹效古人的胡适,其《尝试集》相当大一部分,仍是脱胎于古体诗。仅就单纯的语句模仿而言,亦比比皆是,如“父母生我该有用”(《赠朱经农》)[8],语义类于“天生我才必有用”,“弃我去者,二十五年,不可重来”(《沁园春·二十五岁生日自寿》),语义类于“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但美感却皆远逊之,这恐怕亦是胡适八不主义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
总之,淹贯中西的学术背景,让胡先骕能够客观地看待近代文学革命的许多问题。他既不同于一味守旧的顽固派,亦不同于将传统全部抛开不要的激进派。他提倡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但也主张改革,创造新的文学样式,同时他又不遗余力地将国外的文化历史与现状介绍给国人,使之有所比较与借鉴。胡先骕提倡的文学之路是对是错固无定论,但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他的选择是冷静的、经过慎重思索的,相对于顽固派或激进派那种狂热的态度,无疑更为可取。
三 旧式诗话和新式文评相融合的评论方法
胡先骕的诗文评论继承了传统诗话“论诗而及事”、“论诗而及辞”①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指出古代诗话大略可分为“论诗而及事”、“论诗而及辞”两种,以单篇形式问世的胡先骕诗文评,实际上杂糅了这两种特色。关于章学诚对诗话的分类,可见章学诚著,叶瑛校注的《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559页.的鲜明特色,善于从自己的视角入手解读历史,同时亦重视系统性和理论性。文中对古代诗词的发展脉络有大量提纲挈领式的梳理,并运用古代诗学“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批评方法,将诗文结合评论对象的生平经历与所处时代综合分析,加以议论、描写、抒情等各种笔法,可谓学术性、理论性、趣味性并存。同时,胡先骕又大量援引西方诗文及评论家之语,加入中西对比,评中国文学亦评外国文学,论述对象亦不再局限于诗,而扩展到其它文学体式及现象,显示出胡先骕开拓的文化视野与扎实的理论功底。可以说胡先骕的诗文评融合了传统诗话和近现代文学评论两种体式,表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批评风格,其批评方法值得关注。
(一)评诗亦评史。胡先骕十分看重诗文的存史之功和教化作用,看重记录的真实性和议论的切中时弊。他在评论中有意记载了大量史实,对清季一段历史,叙之尤夥,使诗话不仅评诗,亦兼评人评事评史,即具有所谓“历史之眼光”[9](P42)。
《读张文襄广雅堂诗》一文中,胡先骕以张之洞为主线,概述了自文襄殿试高中,至最后眼见国事无救、呕血而死的几十年间,与之有关的几件大事。涉及到张佩纶、宝廷、李鸿藻、翁同龢等清季名臣,将南北帝后党争、戊戌之变等事件勾画轮廓,剖析史实,对张之洞与梁启超之间的一段公案论之尤详。胡先骕虽意在以此段笔墨赞扬张之洞对清室和国家的拳拳忠心,以及支持改良维新的超前眼光,但在客观上却保存了许多正史未载之史实。
涉及此段历史的还有《评陈仁先苍虬阁诗存》和《评赵尧生香宋词》两篇。前文不再围绕某一人物,而是宏观的分析了清季二十年的历史情境,从帝后党之争起,至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兴,再至庚子之祸、宣统年间亲贵弄权,最后袁世凯觊觎帝位,清室终而覆灭。胡先骕否定了清亡于慈禧的说法,毫不讳饰戊戌党人尚欠深思的诸多举动,条分缕析清王朝逐渐走向灭亡的过程。后文在此基础上,又重点突出袁世凯的乱国之罪,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了解那个风云变幻的复杂年代。
胡先骕多次指出戊戌党人对变法操之过急,未能先深谋细虑而后行事,“维新”之“新”徒有其表,且对时政的思索不够透彻与实际。其变革之勇气固然可嘉,但这场条件不够成熟、计划不够完备的 运动,“实为一种 浪漫运动”[5](P120)。即使侥幸成功,虽庚子事变可免于爆发,中国的前途也未必能扭转乾坤,“故谓戊戌变法成,必有利于清室末造者,殆亦过当之论也”[10(P119)],“戊戌党人之誉,要为言过其实,故戊戌政变即使成功,是否为中国之福,尚未可知”[2](P26),后世对其寄予的希望实际上超越了它所能达到的成就。胡先骕对历史有自己的深入思考和独特看法,认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成熟条件是改革成功所必需的,戊戌变法的失败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成熟条件。在《论批评家之责任》、《评陈仁先苍虬阁诗存》等文章中,胡先骕都将戊戌变法与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类比而谈,认为这两次改革皆属于时机未到,故而前者注定失败,后者之新法即使再完善再超前,对国家来讲,“亦视为虐政也”[9](P43),同样没有出路。
胡先骕反对孤立的看待文学现象,尤其在“有清末季文人,与政局多有密切关系”[11](P110)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每篇文评都涉及到评论对象的品德性情和生平遭遇,充分考虑了社会现实对人的影响,这既是知人论世,亦是以个体反观历史,突显了文学作品的厚重度,有助于后人之理解。他品评人物时不为条框所限,能结合史实以意逆志,揣摩人物的心态历程,尤其不会单纯凭借诗人的政治抉择做高下之分。如俞恪士在清朝历任甘肃藩台、学台、厘捐总局局长、南京水师学堂督办等职务,民国时亦出任官职,似有身事两朝之嫌。但胡先骕却能够谅解俞恪士之做法,认为其在清朝“未受特达之知,自不必以遗黎自居”[12](P122),甚至认为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比之樊增祥、易顺鼎等人借名士之衔,奔走猎食、沉迷酒色更值得赞赏。胡先骕在《评俞恪士觚庵诗存》中将清季之文人分为五类:第一类是顽固守旧派。第二类是清流士人,清亡后以遗老自居。胡先骕极力称赞的赵尧生便属此类。第三类是如俞恪士等赞成维新人士。第四类是革命激进派。第五类是上文所提到的樊增祥、易顺鼎等假名士。胡先骕对其中第二、三、四类文人皆能持公允无偏见之态度,这与他提倡批评家应能“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9](P41)是相吻合的。
(二)比较定位法。胡先骕在介绍诗文之风格时,最常用的是比较定位法,通过比较来确定诗人个性,以及其诗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之地位。
第一种比较法是探寻研究对象的取法与宗尚,用古人之风格来定位其面貌。优秀的作者多不局限于单一之面貌,摹效时也必定转益多师,且因为其能够杂糅多种特色,方成一代名手,故胡先骕惯常以两位风格完全不同的前人来定位今人。此种方法是古人评诗较为常用的一种手法。胡先骕秉承宋诗派诗论之遗风,对诗歌的偏好、品评方式与陈衍、陈散原等人有相似之处,但他更擅长在差异冲突中定位,突出诗人风骨与面貌、精神与语言的内在对立和统一。
如胡先骕称阮大铖之诗“禀王孟之精神,副以黄陈之手段”[13](P122),便是指其诗统合了模山范水的内容,超脱尘世的感情,雕琢字句的手法这三大方面,糅和成独有之风格,令人耳目一新,能够出奇制胜,成为“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13](P118)。又如,对朱祖谋的评价,胡先骕称其“敛稼轩之豪情,就梦窗之轨范,遂兼二家之长,而别开一境界”[11](P108),便将其词作言语意向的密丽深婉和感情的豪放激越非常准确的概括出来。更为难得的是,朱祖谋又有大量作品,非辛吴二者所能局限,是取法于此而高于此,故能成为晚清四大词家之首,被胡先骕许为词界“有清一代之冠”[11](P111)。
对自己最为推重的诗人郑珍,胡先骕在《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文中,将郑诗的风格概括为“以苏韩为骨,元白为面目”[5](P116),“盖以苏黄韩杜之风骨,而饰以元白之面目”[14](P109),“以黄陈之手段,傅以元白之面目”[13](P122)。郑诗以俗语俗字入诗,且善写平凡生活,能够化庸俗为生动。但同时,郑诗之笔力矫健雄浑,又非元白所能比,这正得益于宋诗派以苏黄杜韩为尚。胡先骕对宋诗派诸位大家一向称许有加,对郑珍之评价又居于诸家之首,直言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14](P108)。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否为平情之论自然见仁见智,但可见郑诗十分合于胡先骕之喜好。细究之,原因大概有三方面,其一,郑诗之风格或平易或奇奡,句式或散或骈,但皆遵循法度,收放有据,善汲取前人之长,正是胡先骕指出的作诗由摹效入手而自成一体。其二,郑珍天性纯挚中正,其诗尤胜在感情真切。集子中有大量描写父母兄弟朋友妻儿之作,皆深于言情,感人至深,合于胡先骕提倡的“修辞立其诚”。其三,郑珍一生困顿偃蹇,但却始终恪守儒家之道,尤其是中年以后,立身行事,端重自持。他强调诗品与人品的一致性,这恰与胡先骕乃至整个新人文主义学派对道和文的双重诉求相吻合。可以说从人品到诗风,郑珍都符合胡先骕所推崇的标准,也就难怪胡先骕评价甚高。
第二种方法则是将诗人在同一派别内比较,胡先骕对阮大铖之评价,亦兼用了这种手法。胡先骕指出自周秦始,中国之诗歌可分为人文与自然两派。如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苏轼、黄庭坚、郑珍、郑孝胥等人之诗,皆属人文一派。他们的诗歌是入世的,内容上多为国家盛衰、百姓疾苦,重人事伦理。而自然派之诗中则充满了出世之思,对功名利禄皆淡漠处之,陶渊明、谢灵运、韦应物、柳宗元、贾岛、姚合、林逋、赵师秀等人属于此派。①胡先骕的这种划分方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将诗人直接划为某派便欠妥,因为胡文所举的绝大多数诗人,皆是两类题材均有涉及。其次,胡先骕将屈原推为自然派之鼻祖,也不合适。但胡先骕的观点对中国诗歌分类的探讨,还是有意义的。中国古代对诗歌的分类过细过杂,动辄几十种,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近现代的文论家又长期将诗歌简单分为叙事和抒情两大类,现在多数学者都认同诗歌大致可分为叙事、抒情、哲理、写景四类。可以说对其中写景类的重视,胡先骕在将近100年前就已经做到了。从所推许之人和诗歌风格来看,胡先骕认为阮大铖应属于自然一派,但在自然派中亦能别具一格,有自己的高超之处,因其能够做到“窥自然之秘藏,为绝诣之冥赏”[13](P120)。余者如王维、储光羲等人,即其代表作,也仍然“静胜有余,玄鹜不足”[13](P120)。玄在佛教或者道教中皆谓不可言说的妙理,鹜有追求之意。以追求玄妙为评定诗歌之准则,可见胡先骕对自然派诗歌超尘脱俗之思的极高要求。而这种“玄”之色彩,正是阮大铖擅长,其余自然派诗作所缺乏的。阮大铖在佛法研究方面较有造诣,一方面是家族渊源,郑雷指出:“大铖生父阮以巽赋性恬淡,“奉持佛法至恭至谨”,阮大铖可能受其父影响而学佛。”[15](P99)另一方面,明代统治者倡导三教合一,佛教在明代发展迅速,南京、北京等地皆有多次盛大的法会,刊刻佛经,广修寺庙,佛事活动频繁举行。社会氛围如此,阮大铖自然或多或少受到影响。胡先骕言阮大铖“崇拜自然如宗教”[13](P120),其诗“非精研内典确有心得之人不能道,王右丞尚有不逮”[13](P122),对阮诗的这种特色甚为赏识,用“空灵”、“超脱物象”、“别具神理”、“天机完整”等词来形容,可以说抓住了阮诗的最大特色。胡先骕极爱阮大铖之诗,认为在写景一派中,阮诗远胜于王孟韦柳诸贤之作,实为此派之集大成者,故其对他人写景之作的评价,也常以阮诗为标准,如称赞刘光第之诗“极似阮石巢,置之咏怀堂诗中,可乱楮叶”[4](P119)。但自古以来以人废言之习俗,使阮大铖之诗长期无人问津,直到清末,才有章太炎、陈三立等人为其正名,实为诗界一大憾事。历史上如孙觌、严嵩、赵文华、马士英等人,亦皆是品行不端但极有才华,胡先骕提出应将文人之品性与其作品之优劣区分而论,方能避免更多文化悲剧的诞生。
第三种方法为中西比较,这种对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近代国门大开,西学盛行,中西文化碰撞之产物。虽不为胡文独具,却为胡先骕极为擅长之处。胡先骕文章里的中西比较,可谓着眼点高且说服力强,有宏观的现象对比,也有具体的作家或作品对比。胡先骕对西方文化堪称精通,大量作家与作品皆能信手拈来,与中国之作品排列举例。他曾将中国之五七言诗与欧洲之meter(格律诗)类比,将卢梭与老庄类比,将林纾译作与英国文学家John Florio所译法国人文主义作家Montaigne之文集类比,认为二者之伟大皆在于能成功地进行创造性之翻译。
胡先骕更曾屡次将桐城派与法国文学类比,认为二者的共同点在于“不为浮诞夸张之语,不为溢美溢恶之评。一字一句,珠两恰称,不逾其分”[5](P106)。针对后人常批评桐城派之文空洞无物的现象,胡先骕认为实非桐城派之弊,而由于当世学术思想不发达而致。19世纪初英国之诗坛,情况与此极为相似,虽人才辈出,但因无充实思想,故而成就有限。桐城派大盛于清,其时一方面文网极密,文人惮于在文中品评时政,另一方面天下相对安宁,又尚未全面接触外来思想,自然实质性的内容相对缺乏。这也正是后来世变时移,曾国藩方能抓住契机,重振桐城派的原因。
四 不可忽视的开创之功
晚清至近代,诗话品目繁多,但胡先骕的文评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以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和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为例,此二部都属于彼时较具代表性的作品。但梁氏将大量篇幅用于选录作品,所选之作也皆以“新诗”为标准。胡先骕则以论诗为主,录诗为辅,在选取评价对象时,刨除了为“诗界革命”服务的目的,无疑更为客观公正。同时,囿于时代等因素的限制,梁氏的西学理论相对薄弱,在中西融贯方面,远逊于胡先骕。而汪辟疆之文,因属于游戏之作,故在诗作背景、诗人生平、理论阐释等方面都过于简略,范围虽广,但论述皆点到为止,缺乏更深层次的剖析。仅就这些方面而言,胡先骕的诗评要优于梁汪二人为代表的一批晚清诗歌研究之作。
胡先骕虽不刻意求新,但因独具慧眼,故擅发掘别人未识之佳作,每篇文评皆能指出评议对象最独特的优势,且不以惯常之看法妄加于人,常有“翻案”之论。如《评朱古微强村乐府》一文中,胡先骕批评世人将张炎评价吴文英的话断章取义,认为张炎“七宝楼台”之语是一时兴到之言。世人只以此为口实诋梦窗,却选择性的忽略了张炎对吴文英的诸多赞美倾羡之语,实为可哀可叹之事。
又如,自清社屋而民国始,“人咸羞言清季,而尤恶称满人”[3](P119),胡先骕针对这种情形,提出要客观看待历史文化,认为“有清一代学术文物之盛,远迈元明,上追唐宋”[3](P119),盛赞清代学术文化之繁荣,对时人的偏颇观念有矫正意义。胡先骕在《论批评家之责任》一文中,指出如要研究中国文学,除经史子外,还应浏览古代名家之集,在这个名单中,清人或晚清遗老占了近三分之一。胡先骕的文评,亦主要针对这个群体。他在1947年的手稿《四十年来北京之旧诗人》中曾言:“晚清末季,诗学甚为发达,大家名家辈出。民国四十年来作旧诗之诗人半系晚清遗老,半系后起之秀,但后者是宗派蕲向,实与清末之老辈诗人相同。”[16](P470)凡此种种,可见在胡先骕心中,清代诗词在历史上占有何等重要之地位。
对阮大铖之诗,胡先骕乃是做系统研究的第一人。如前所述,虽清末民初,章太炎、陈三立、柳诒徵、陈寅恪等人对阮诗皆有褒奖之语,王泊沆尤为喜爱,甚至曾手抄阮集并作跋语,但这些评论都限于零星半点,未有专门之研究。胡先骕在王伯沆处得阅阮诗[17](P330),并于1922年在《学衡》发表《读阮大铖咏怀堂诗集》,将阮诗做了系统的全面分析,对其五言写景诗称赞有加,指出其思想之高妙与语言之精湛,但篇末亦不讳言其余诗体的无甚可观,以及因其“天性不足”而使诗歌缺乏人伦情感这一缺憾。胡先骕的这篇文评可以称得上是阮大铖诗歌研究的奠基之作,后人的研究多以此为基础。
胡先骕的《评赵尧生香宋词》,亦是第一篇专文研究赵熙词的著作。赵熙之作,《平等阁诗话》、《石遗室诗话》、《忍古楼词话》等都有提及,但或集中于其诗,或仅聊聊数语,总之皆限于漫谈式的点评。胡先骕之文从赵词的思想感情到选词用语一一论列,系统而深入地分析了赵熙之词,对骨肉分离、江山易代引发的沉挚之痛深为体谅,更着力赞扬词中流露出的忠君之情。后世之研究颇受胡文影响,如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曾言《香宋词》“似从自然界的灵悟中得来。他的描写景物之作淡朴自然,真是又多又好”[18](P39),无疑参考了胡先骕评香宋词时,指出古今中外摹写自然之名作“咸从自然界之灵悟中得来”[19]的说法。
胡先骕对刘光第的诗歌评析同样具有开创意义。刘光第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人们对他的研究历来多局限在政治方面,其《介白堂诗集》获得的关注少之又少,胡先骕直言刘光第之诗“不但为六家之冠,近世亦鲜有能过之者”[4](P116),并用较长篇幅着重分析了其纪游写景之作,认为此种题材是集中精髓所在,仅凭此已可独步千古,“在中国三千年所为诗中别开生面”[4](P122),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除写景诗之外,胡先骕认为介白堂中描述兄弟父子家庭伦理之情的篇章,亦大有可观,能以本色挚情动人,诚属佳作。
除此之外,胡先骕对俞明震(字恪士)、陈曾寿(字仁先)、王浩(字然父)、文廷式(字道希)等人的专文研究皆属于开先河之作。这些诗词集在胡先骕之前或无人问津,或仅在诗话词话中以寥寥数语提及,缺乏深入的整理和研究。胡先骕融合古代诗学和新式文学评论的手法,对这些清代诗词集做了详尽而客观的批评,几乎篇篇都对后人的研究起到向导性的作用,在近代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重要的影响。[20]
五 殊途同归的二胡之争
要评价胡先骕在近代文学中的地位,无法绕开的是他与胡适之间的一场文白之争。胡先骕初识胡适,尚引为同调中人,但随着胡适白话文学观的形成,二人的分歧越来越大。1917年,《新青年》刊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求对仗、不避俗语俗字八条。陈独秀在此文后加入解读,认为“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21](P31),可以说正式确立了新文化运动的实质——白话文运动。1919年,胡先骕发表于《南京高等师范日刊》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上)由《东方杂志》转载,文中称自己“素怀改良文学之志,且与胡适之君之意见,多所符合”[22](P169),只含蓄暗示胡适之文过于偏激,指出文言分离的优点,以及白话无法代替文言的数点理由,算是二胡初次之交锋。1920年,《尝试集》出版,作为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出版,一经问世便引起极大轰动。胡先骕终于按耐不住,于1922年、1923年连续发表长文《评尝试集》、《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认为胡适不懂传统文学之价值,妄议文学革命,对桐城派、梁启超、章炳麟等的评价皆存在谬误。胡先骕详谈了中国古诗之句法、体裁、音节、韵律、用典、俗字、模仿等问题,引经据典,将胡适所谓的“八不主义”一一反驳,认为“中国文言与白话之别,非古今之别,而雅俗之别也”[5](P128),且白话运动以来,“从未产生一种出类拔萃之作品”[5](P129),可见白话文根本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强行推广白话文,只能阻碍文学的发展。至于胡适的白话诗,胡先骕认为简直不可称为诗,他嘲笑胡适“但能作白话 而不能作诗”[7](P130),直言《尝试集》之价值仅在于昭示新诗之路不通,以此启迪后贤另寻他法。这两篇文章的措辞与以前相比,明显更为尖刻激烈,时而夹杂对胡适的讽刺之语。
在今日看来,胡适之诗的确不能被称为白话诗中的杰作,毕竟诗之意象选择、语言之错落有致,还是相当重要的,应遵循一定规律。《尝试集》在这些方面尚欠美感。有一些诗,如“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朋友篇·寄怡荪,经农》),“做诗的兴味,大半靠朋友”(《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觐庄》),音节尚不对称,即使是打油诗和民间小调,恐亦不取。另外,口语入诗的情况,有时有点过了,如“要脸吗”、“别讨厌了”(《双十节的鬼歌》)之类的句子,比比皆是。但是,胡适之诗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如《小诗》、《梦与诗》、《关不住了》等篇,都清新隽永,别有趣味。应该说,胡诗的主要贡献在于大胆的摸索和尝试,这种摸索尝试,对我们探讨文学之死活究竟来源于形式还是内容,十分有意义,不应完全否定。
但是,对于胡先骕的批评,胡适却无丝毫回应,这似乎又给予了胡先骕冷静的时间,没有再撰写新的批评文章。两人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诸多方面往来颇多,交往转为密切,胡先骕也停止为《学衡》写稿。这场二胡之争,终而不了了之。
综合新文化运动中立场不同的两方来看,胡先骕与胡适其实都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不同于初创期的,应尽快为中国找寻一条合适的文化发展之路,只是他们选择的方向有所差别,胡适的主张更彻底、更极端。二胡之争,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甚多,胡先骕以及《学衡》甚至算不上强有力的一员,因为他们并不反对新文学,反而与其殊途同归。
只是,或许是因为太急于要维护文言,维护旧文化,胡先骕有时候不免急躁,反倒走入了死角,他曾说“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之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之文字之今古为死活”[7](P125),“诗之功用,在能表现美感与情韵,初不在文言白话之别”[7](P129)。此言未尝没有道理,但是他期望别人用这种中正的眼光来看待文言,自己却做不到以同样的态度看待白话,看待新文化运动,而是早早的便给白话文判了死刑,一味的认为胡适必然失败,断定“胡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鲁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症耳”[7](P125)。涵养如胡先骕,竟也忍不住妄下断言,诅咒胡适之作。这便将本与新文化运动不对立的他,推到了对立面上。反观历史,倒也很难说清这是时代使然,还是胡先骕本身的性格使然,或许兼而有之吧。
胡先骕一再强调道德节制的重要性,呼吁青年学子万不可盲从所谓的世界潮流,而应谨守儒家的旧道德。他视精神上的节制与修身养性,超越于物质,认为前者才是社会的根基,他对社会现象及历史发展的最终推动力的认识,稍欠深思。这样的思想观念,使得胡先骕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选择了加入《学衡》的阵营。但说他保守固然可以,却不得不承认他的很多预言,其实也已实现,比如他坚信古体诗有恒久的生命力。就今天诗坛的情形来看,虽然白话诗已成为新诗的主要形式,但胡适断言的死文学——古诗与律诗,却仍未退出历史舞台。胡适晚年甚至放弃了白话诗,而专写古体诗,这恐怕也是早年处于论争中的二胡,都始料未及的。
百年已过,世事苍茫,新旧文化之争尘埃落定,对错难以评说。当我们重新审视这场论辩,唯一毫无争议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前途进行的思索和倾注的心血。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抱着同样崇高的理想,在这个历史的岔路口上进行了艰难的抉择。《学衡》与胡先骕都是这个抉择中有重要意义,却被一度忽视的环节。这种落差,值得我们深思。
[1] 吴宓.悼白璧德先生[N].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12-25(11).
[2] 胡先骕.文学之标准[J].学衡,1924,(31):10-44.
[3] 胡先骕.读张文襄广雅堂诗[J].学衡,1923,(14):115-125.
[4] 胡先骕.评刘裴村介白堂诗集[J].学衡,1924,(34):116-123.
[5] 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J].学衡,1924,(18):104-129.
[6] 胡先骕.评金亚匏秋蟪吟馆诗[J].学衡,1922,(8):118-127.
[7] 胡先骕.评尝试集[J].学衡,1922,(1):108-130.
[8] 胡适之诗,尝试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9] 胡先骕.论批评家之责任[J].学衡,1922,(3):36-49.
[10]胡先骕.评陈仁先苍虬阁诗存[J].学衡,1924,(25):112-123.
[11]胡先骕.评朱古微疆村乐府[J].学衡,1922,(10):102-111.
[12]胡先骕.评俞恪士觚庵诗存[J].学衡,1922,(11):116-123.
[13]胡先骕.读阮大铖咏怀堂诗集[J].学衡,1922,(6):118-125.
[14]胡先骕.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J].学衡,1922,(7):118-126.
[15]郑雷.阮大铖丛考(上)[J].华侨大学学报.2004,(1):93-101.
[16]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胡先骕文存[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
[17]黄侃.黄延祖重辑.黄侃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8]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后三十年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9]胡先骕.评赵尧生香宋词[J].学衡,1922,(4):118-126.
[20]胡建次.民国时期以来传统词学中的词境论[J].中国文学研究,2013,(4):76-79.
[21]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7,二卷五号:21-31.
[22]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上)[J].东方杂志,1919,十六卷三号:169-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