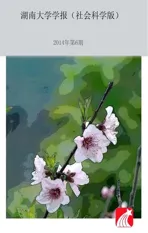怨诗楚调考论*
2014-03-31廖春艳
廖春艳
(1.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2.湖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晋陶渊明有《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五言诗一首,沈约《宋书·乐志》载曹植乐府诗《明月》一首,题为“楚调怨诗”。怨诗楚调究竟为何?怨诗何以与楚调相结合,而不与齐、赵之讴相和?怨诗楚调的特色是什么?这便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 怨诗楚调的形成与衍变
怨诗楚调初见于乐府之相和歌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一辑录了《相和歌辞·楚调曲》,并曰:“楚调曲有《白头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东武琵琶吟行》《怨诗行》。”[1](P599)另外《楚调曲》还辑有《怨诗》《怨歌行》《怨歌行朝时篇》《长门怨》《阿娇怨》《婕妤怨》《蛾眉怨》《玉阶怨》《宫怨》《杂怨》等多种以怨为主题的楚调歌诗。而据郭茂倩所载,古辞只有一首,即《怨诗行》“天德悠且长”一篇,汉代歌诗也仅班婕妤《怨歌行》一首。又据《乐府诗集·怨诗行》下所附的解题,其中也只提到《怨诗行》与《怨歌行》。由此可见,“怨诗楚调”初指音乐上属于“楚调曲”的《怨诗行》及《怨歌行》,而后逐渐扩衍为指向悲怨主题的一类歌诗。
郭茂倩在《乐府诗集·怨诗行》题下附有一段详细的解题:
《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献楚怀王,王使乐正子治之,曰:‘非玉。’刖其右足。平王立,复献之,又以为欺,刖其左足。平王死,子立,复献之,乃抱玉而哭,继之以血,荆山为之崩。王使剖之,果有宝。乃封和为陵阳侯。辞不受而作怨歌焉。”班婕妤《怨诗行》序曰:“汉成帝班婕妤失宠,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乃作怨诗以自伤,托辞于纨扇云。”《乐府解题》曰:“古词云:‘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言周公推心辅政,二叔流言,致有雷雨拔木之变……”[1](P610)
由上述材料可知,怨诗楚调形成的源头有三:其一是卞和献玉蒙冤而作“怨歌”,形成于战国时期;其二是班婕妤失宠于汉成帝而作“怨诗”,形成于西汉时期;其三是周公推心辅政而遭谮,形成于周成王时期。那怨诗楚调究竟形成于西周、战国还是西汉,抑或是其他年代?
周公旦遭谮而有“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的诗句,《技录》、《乐录》、《乐府解题》皆以为古辞,而《艺文类聚》乐部论乐、真西山《文章正宗》以及郭茂倩《乐府诗集》都题为曹植作。[1](P617)笔者认为,这大概是因为曹植《怨歌行》篇首援用了这两句古辞残句,从而造成这层迷雾,而《怨歌行》歌诗并无确凿证据证明非曹植所作。那有此两句诗的古辞成于何时?可以确认的是,它并非产生于西周时期,也无法产生于春秋战国,最有可能产生于汉代,尤其是东汉。因为汉以前诗歌以四言与楚辞为体,五言诗歌孕育于汉初迄武帝时期,发生于武帝迄宣帝时,流行于元成迄东汉初,成熟于东汉中叶迄建安时期。[2](P19~24)另外《晋书·乐志》也云:“凡乐章古辞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故此诗大致成于汉世。因缺全文参照,其类似于《戚夫人歌》之杂言中夹五言也未尝不可。故含此两句的古辞至少应为武帝时作品,若为完整五言诗则更在此之后了。
《琴操》载卞和蒙冤而作《怨诗行》,《乐府诗集》中录有本辞:
天德悠且长,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几时,奄若风吹烛。嘉宾难再遇,人命不可续。齐度游四方,各系太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1](P610)
此就内容而言是伤生叹逝,劝人及时行乐,完全与卞和献玉之事无关,自当不为战国时所作。视其体为整饬的五言,且诗风古朴,质木无文,篇幅又较武帝时《江南曲》①从沈约《宋书·乐志》、郭茂倩《乐府诗集》、郑樵《通志·乐略》所辑来看,《江南》在“相和曲”中向来列在第一首,萧涤非据此以之为正声,认为此诗当为传世五言乐府之最古者,“殆武帝时所采吴楚歌诗。”笔者以之为是。详见《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21、62页.长许多,当为元成迄东汉初歌诗,抑或更后。
班婕妤《怨歌行》“新裂”一篇,由于班固《汉书·孝成班婕妤》只录班婕妤自伤赋一篇而未录此诗,因而自刘勰起,班婕妤之作者身份多见疑于后代。笔者认为单以班固《汉书》未录此诗就否定班婕妤之作者身份,理由不足以服人。因为五言歌诗于当时而言乃为民间小道,尚未成文学正统,所谓“辞人遗翰,莫见五言”[3](P140),故而正史不载实属正常;而从身份地位、行为心理、遭际命运来看,班婕妤与《怨歌行》所示极为吻合。因此若无确切证据证明此诗为他人所作,则不应否定班婕妤之作者身份。今以其本事年份及其完整五言句式而论,最早当成于成帝迄东汉初。
综上所述,以《怨诗行》、《怨歌行》等为代表的最初之怨诗当产生于武帝以后,甚至是东汉时期。而楚调当汉初就有。汉高祖为楚人,曾作楚歌《大风歌》。《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4](P389~393)此应为汉乐 府 之 开 端。《汉 书 · 礼 乐 志》载“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5](P1043)又《唐书·乐志》云:“楚调者,汉房中乐也。”[1](P376)可见楚调汉初即已盛行。用楚调而歌的“怨诗楚调”当产生于武帝以后,大致在元帝迄东汉时期。
怨诗楚调的形成当是人们依据卞和、班婕妤与周公的经历,深感其痛,发而为文,以抒发其怨情而产生的。上文已述,《怨诗行》本辞非周公所作,亦与卞和无关,后人之所以将二人本事引入,固然是崇古之心使然,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展现其冤之深、其怨之重。《琴操》有载:“平王死,子立,复献之,乃抱玉而哭,继之以血,荆山为之崩。”[1](P610)《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载:“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4](P1522)泣血而哭,山崩地裂,秋禾尽偃,狂风拔木,其冤足可动人心魄,其怨足可撼动上苍,将他们引入即能更贴切地突出“怨”的主题,概述人生之一大怨——志不得伸,忠不得明。而班婕妤的《怨歌行》,则是现身说法地展现了人生的另一大怨——情不得守,恩不得长。在此之后,人们又陆续引入陈皇后阿娇、戚夫人等悲剧人物以表达类似于婕妤的怨情。怨诗篇目题名增多,由本事衍生出《班婕妤》、《长门怨》、《婕妤怨》、《长信怨》、《阿娇怨》,由典型意象衍生出新题《玉阶怨》、《明月照高楼》、《蛾眉怨》,另有总括题名《宫怨》、《杂怨》等,亦为《怨诗行》、《怨歌行》之衍生。至魏晋南北朝迄唐,形成了一组很特别的以着重表达思妇宫人忠臣之怨情的楚调类歌诗,据《乐府诗集》所载,凡录108首。
二 怨诗楚调的独特内容与艺术手法
怨诗楚调歌诗之共同特点即以“怨”为主题,《相和歌辞·楚调曲》中所录怨诗108首无一例外。即便是南朝陈张正见之“新丰妖冶地,游侠竞骄奢”一首,看似徒呈富贵奢靡之景,实则承继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以季伦家富贵豪奢为典,怨刺时人纸醉金迷,引发隆盛如斯而今不再的生命迁逝之感,抒发广义上的命运之怨。总括而论,怨诗楚调的题材类型主要分为三类,即如上文所言的由卞和、周公本事引发的蒙冤屈志之怨,由班婕妤、陈皇后等本事引发的相思被弃之怨,以及由“天德悠且长,人命一何促”古辞所引发的伤生叹命之怨。
相较而言,抒发情不得守、恩不得长的相思被弃之怨的歌诗占三类之中的大多数。这些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宫怨诗,一类是闺怨诗。怨诗楚调宫怨诗多集中于《怨歌行》、《班婕妤》、《婕妤怨》、《长信怨》、《长门怨》、《阿娇怨》等题名,多以班婕妤、阿娇本事为依托,陈宫妃遭弃之悲,发君恩凉薄之怨。闺怨诗多集中于《怨诗行》、《怨诗》、《明月照高楼》、《杂怨》几个题名,盖以曹植《怨诗行》“明月照高楼”一篇为首,多陈离别相思之苦,亦杂弃妇伤情之怨。唯有北周庾信的《怨歌行》与晋傅玄的《怨歌行朝时篇》较为特殊,前者抒发别乡之怨,后者抒发悼亡之思。
伤生叹命之怨,自古辞《怨诗行》之叹逝开始,晋梅陶、魏阮瑀承其绪,至陶潜主题一改为人生多艰之感叹,南朝沈约《怨歌行》也持有同感,到唐代孟郊《杂怨》,以三首之多抒发人生短暂、人生多艰、人生不定之复杂怨情。
而第三类蒙冤屈志之怨篇目较少。曹植《怨歌行》为其主要代表。该诗吟咏本事怨情的同时,亦抒发的是自己见疑屈志的冤屈。值得注意的是,梁朝王叔英妻沈氏《班婕妤》援谗入诗,立标新意,所谓“宠移终不恨,谗枉太无情”,唐代长孙左辅《宫怨》与翁绶所作的《婕妤怨》亦将婕妤被弃归因于“谗谤”,所谓“盛衰倾夺欲何如,娇爱翻悲逐佞谀”、“谗谤潜来起百忧,朝承恩宠暮仇雠”,这都是将班婕妤与周公、卞和之本事相联通的结果,亦是在怨诗楚调总体语境下的综合立意。
由此可以看出,怨诗楚调主要抒发的是人之怨情,总括一个“怨”字,重在一个“情”字。这也构成怨诗楚调与其他楚调曲辞的重要区别。《相和歌辞·楚调曲》中录有其他的楚调曲歌诗,比如《白头吟》、《决绝词》、《泰山吟》、《梁甫吟》、《泰山梁甫吟》、《东武吟行》等,虽然这些歌诗也甚为悲怆,甚至与怨诗之主题有大部分重叠,比如《白头吟》多叹相思恩薄,《梁甫吟》多叹生命流逝,《东武吟行》则多咏人世沉浮、时移世易、人情凉薄,但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有迹可循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整体而言,两者侧重的表达方式不同。其他楚调曲歌诗情中带理,多阐发人生感悟,揭以人生真言,而怨诗则重在抒情,多陈内心情感,展现心境悲苦。比如同为怨君恩薄的作品,张籍的《白头吟》与长孙左辅的《宫怨》皆以宫妃前之荣宠与后之悲戚相对比,然前者悲伤之余得出“人心回互自无穷,眼前好恶那能定”的人生哲理,后者则用独开独闭之门、苍苔满覆之地、满箱的前舞衣、泪渍的凉玉枕来烘托主人公孤独悲凄的心境与难以言喻的怨情。同是写被弃女子,梁简文帝《怨歌行》主要借由秋风、寒霜、阶上青苔、路径杂草等衰败冷清的意象来烘托气氛,展现女子内心之哀怨;而李白的《白头吟》虽也叙写了“落花辞条归故林”的被弃情感,但更注重对人生意识、认识的表达,诗中发出“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的悲叹。而此种人生感悟、人生真言在其他楚调曲歌诗中俯拾皆是,比如“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白头吟》古辞)、“人情贱恩旧,世路逐衰兴”(鲍照《白头吟》)、“谗新恩易尽,情去宠难终”(张正见《白头吟》)、“但感久相思,何暇暂相悦”(元稹《决绝词》)、“履信多愆期,思顺焉足凭”(陆机《梁甫吟》)、“时世一朝异,孤绩谁复论”(鲍照《东武吟行》)、“财力犹可倚,不惭世上雄”(李白《东武吟》)。就连内容与句法几乎都一样的两首歌诗——《怨诗行》古辞与沈约《东武吟行》,皆以叹惜生命荣华徂谢为旨,然后者之“天德深且旷,人世贱而浮”比之于前者“天德悠且长,人命一何促”的表达,无疑更具判断,更理性些,更接近于人生真言。
另外,其他楚调曲歌诗相比于怨诗楚调还更多地运用了叙事手段,这也使作为理的人生认识、感悟的表达更为水到渠成。比如《白头吟》本辞,即从良人有两意之事写起,而后表达决绝之意,至篇末自然引出对男人的论断:“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又如鲍照《白头吟》,在叙写“申黜褒女进,班去赵姬升。周王日沦惑,汉帝益嗟称”这些事实之后,发出“心赏固难恃,貌恭岂易凭”的由衷感叹。笔者统计,八首《白头吟》中用叙事者有七,五首《梁甫吟》中有三,四首《东武吟行》(包括《东武吟》)中亦有三。总括而言,怨诗多展现,而其他楚调曲多叙写。
其二,两者对本事的运用与倚重不同。上文怨诗题材分类的论述中已极为明显地透露出一个重要事实,即怨诗楚调各题名的形成、发展,题材类型的形成都得力于卞和、周公、班婕妤、阿娇的本事的支撑与传播。比如班婕妤作《怨歌行》以后,傅玄、简文帝、江淹、沈约、虞世南、李白等人都作《怨歌行》,或直咏本事,或以此本事为典代人作怨辞;而后陆机、崔湜等新作《班婕妤》、《婕妤怨》等题名,多为本事伤情,或叹君恩凉薄。《长门怨》、《阿娇怨》《玉阶怨》、《蛾眉怨》亦由本事渐次发展而来。108首怨诗,直咏本事的多达五十多篇,另外很多篇章虽非直咏本事,但亦借用了与本事有关的典型意象为典故表达怨情,这些典型意象包括纨扇、长信、后园舆、长门、昭阳殿、金屋、歌舞衣、相如赋等。笔者对歌咏本事或明显有本事痕迹的歌诗以及以与本事有关的典型意象为典故的歌诗进行统计,108首怨诗中有75首,约占70%。那些无本事或无本事典故的歌诗多出自《怨诗行》、《怨诗》、《杂怨》,这与古辞《怨诗行》诗文中的本事体现不甚分明有关,它的无特指性也就造成了题材的发散性。总括而言,怨诗楚调是以本事为依托,紧紧围绕本事之哀情间或向外发散而表述怨情的一组歌诗。
相比而言,其他楚调曲歌诗有的虽也有本事支撑,比如卓文君本事之于《白头吟》、《决绝词》,曾子本事之于《梁甫吟》,但其本事的运用与怨诗楚调是有差别的。统观郭茂倩所载《白头吟》8首,《反白头吟》1首,《决绝词》3首,《梁甫吟》5首,《泰山梁甫行》1首,凡18首诗歌中除了《白头吟》古辞之外,无一首咏叹本事,以本事为典的也仅李白《白头吟》两首。所有这些诗歌的主题也比较分散,比如鲍照与张正见的《白头吟》咏忠直遭谗,刘希夷则伤逝年华,李白、张籍叹思妇见弃,而到白居易《反白头吟》则转变为不囿当前怨憎的劝诫。这与楚调怨诗中直咏本事或借本事典故、意象抒发同类怨情的写法是大相径庭的。而另两个题名《泰山吟》、《东武吟行》则根本无本事支撑。
三 怨诗楚调的音乐特色
怨诗楚调是乐府歌诗,“而要想准确把握乐府诗的特点,必须进入到音乐研究的层面”[6](P69)。怨诗楚调的音乐特色大致可以从楚声、相和歌、楚调曲三个方面由远而近地来具体考察。
楚调为楚声当确定无疑。楚声乃指“配合先秦楚歌演唱的楚国地方音乐,用来进行徒歌的、楚地所特有的吟唱韵律和格调”。[7](P183)楚声也即南音、南风。《左传·成公九年》载“使与之琴,操南音”。杜预注:“南音,楚声。”[8](P702~703)《左传·襄公十八年》载“南风不竞,多死声。”[8](P947)《楚辞·招魂》中曰:“宫庭震惊,发《激楚》些。”洪兴祖《楚辞补注》引文颖曰:“其乐浞迅哀切也。”[9](P211)而朱熹《楚辞集注》则注为“高张急节之奏”。[10](P142)可见先秦楚歌具有节奏急促、声音哀切的特点。近人陈思苓认为,屈原时期的楚国声乐有六大特征:其一是古乐之遗,其二是神巫之歌,其三是凄清之调,其四是和歌之声,其五是糜曼之曲,其六是郑卫之风。当时的楚声使用丝竹之器、清声之律,其音高而激,其韵清而秀,其调哀而伤,音乐上的基本风格是悲怨凄美,哀婉动人。作为徒歌的吟唱韵律及格调,我们从《离骚》、《九辩》等篇幅较长的楚辞作品可以探知:内容怀乡忧国、失志不平,音律格调上愤激感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云:“《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歔欷;又三复之,涕泪俱下,情事欲绝。”[11](P31)综合来看,不管是楚歌还是楚声的吟唱韵律都以悲怨哀切为特点,此亦当为楚调之特点。
怨诗楚调属《乐府诗集·相和歌辞》。“相和在先秦与汉初本是一种泛称,凡是人与人或者人与乐器相配合的演唱都叫做‘相和’。”[12](P198)郭茂倩在《相和歌辞一》解题中指出:
《宋书·乐志》曰:“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其后晋荀勖又采旧辞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三调歌诗,即沈约所谓“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1](P376)
可见怨诗楚调是一种由人持节而歌,丝竹演奏的乐曲。郭茂倩《相和六引》解题云:“《古今乐录》曰:‘张永《技录》相和有四引……凡相和,其器有笙、笛、节歌、琴、瑟、琵琶、筝七种。’”[1](P377)《礼记·乐记》曰:“丝声哀……竹声滥。”[13](P1019)《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曰:“丝竹之凄唳。”“哀”、“滥”、“凄唳”,说的便是丝竹乐器演奏的特点,也是相和五调的总体特点。从《乐府诗集》所录的诸曲调所用的乐器看,平调曲无节加筑,清调曲加篪共八种乐器,瑟调曲与楚调曲所用乐器与上述七种完全相同,可见张永所谓各调当以楚调、瑟调为基准,而楚调由楚声而来,其琴、瑟多发危苦之音。阮籍《乐论》载“桓帝闻楚琴,凄怆伤心,倚房而悲”[14](P99)。故而相和各曲调都带有哀伤的风格,后世清商乐之风格可作旁证。由上文引述可知,清商调是晋荀勖采相和调并汉魏旧曲施用于世而成的,可见清商曲承相和歌之风格无疑。而世传清商乐皆哀婉悲怨,杜甫有《秋笛》诗曰“清商欲尽奏,奏苦血沾衣”,可见一斑。
怨诗楚调属《相和歌辞》楚调曲。郭茂倩《相和歌辞·楚调曲》之解题云: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楚调曲……其器有笙、笛弄、节、琴、筝、琵琶、瑟七种。”张永录云:“未歌之前,有一部弦,又在弄后,又有但曲七曲:《广陵散》《黄老弹飞引》《大胡笳鸣》《小胡笳鸣》《鹍鸡游弦》《流楚》《窈窕》,并琴、筝、笙、筑之曲,王录所无也。”[1](P599)
《宋书·乐志》曰:“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15](P603)可见相和曲包括楚调曲是从最早的仅有人声相和的“但歌”发展而来,楚调但歌当然用楚声,之后并入琴、筝、笙、瑟等乐器演奏。可见演奏场中持节而歌者用楚声,和者也用楚声,楚调曲之表演核心——演唱为楚声,乐曲无疑带有楚声清切哀伤的特点。张永指出楚调曲歌者未歌之前有一部弦,又在弄后。这是演奏程序的记录。弦,即弦乐,指琴、瑟、琵琶、筝等的演奏;弄,本意即为音乐演奏,但在相和歌诸曲中则是指区别于弦乐的管乐器如笙、笛等的演奏。“部”字含义颇多争议,据逯钦立、王小盾、赵敏俐等考证,“部”当作弦乐器演奏的遍数解。[12](P214)由此我们可知怨诗楚调的音乐演奏概貌:首先是管乐器演奏,之后由弦乐器演奏一遍,(平调曲为八遍,清调曲五遍,瑟调曲七遍),之后才是歌者的歌唱。
综上可见,楚调,是以清切哀伤的楚声为歌,以哀凄悲怨的丝竹之乐演奏,带有固定表演程序的曲调。它总体风格上的凄怨之色与怨诗的被弃之哀、被谗之悲、生命短暂多艰之叹形成高度契合,因而动人心魄,感人至深。自汉以后,历代大家多有怨诗之作,这种音乐与情感上的高度契合是其重要原因。
怨诗楚调作为歌诗,它“有辞、有声”[1](P376),其辞多被弃、离别、遭谗、迁逝之怨,其声清切凄唳,悲怨感人。但东晋以后,楚调衰微。《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一》解题云:“清乐者,九代之遗声。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并汉魏已来旧曲。其辞皆古调及魏三祖所作。自晋朝播迁,其音分散。”[1](P638)相和三调即平、清、瑟三调,楚调已未列入。有学者考察,楚调可能并入瑟调[16](P202),然即便如此,也“遭梁、陈亡乱,存者盖寡”[1](P638)。怨诗楚调演奏慢慢失传,但其辞却屡有作者。及至唐代,盛世文化兴隆,时人尤尚诗文,多有依旧题造新诗者,然这些诗作基本已不能入乐。楚调怨诗此时也就不再是歌诗,而成为一种纯供阅读吟诵的非音乐性诗歌,白居易《怨诗》、李白《怨歌行》等均属此类。
另一方面,在由入乐至非入乐的发展过程中,怨诗楚调以其强大的本事支撑,极为集中的主题表达,至为分明的风格特色而逐渐地发展为“哀怨”风格的指称。后人提及楚调往往与怨、恨交织在一起。比如顾况《王郎中妓席五咏·筝》“秦声楚调怨无穷,陇水胡笳咽复通”,卢仝《感秋别怨》“霜秋自断魂,楚调怨离分”,黄庭坚《次韵叔原会寂照房》“风雨思齐诗,草木怨楚调”,以及他的《代书》“孤臣发楚调,倾国怨胡笳”等,莫不如此,以致“怨诗楚调”渐次成为抒写怨情的一个专门题类。
[1]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 (梁)刘勰著,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4]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 吴相洲.关于建构乐府学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2006,(3):65-71.
[7] 郭建勋.楚辞与中国古代韵文[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8]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9]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宋)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1](明)王世贞.艺苑卮言[M].济南:齐鲁书社,1992.
[12]赵敏俐.汉代乐府制度与诗歌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3](清)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 (晋)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5](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6]龙建国.楚调考论[J].江西社会科学,2011,(8):198-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