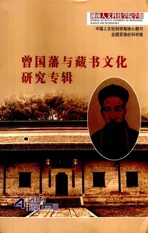曾国藩与晚清社会风气的流变
2014-03-31朱耀斌
朱耀斌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政治与法律系,湖南 娄底417000)
在晚清中兴这一历史语境下看,湘军的横空出世及在其影响下军营、伦理、吏治等方面为之一变的社会风气无疑为晚清的天空涂抹了一幕流年残照。曾国藩以湘军为组织载体,以程朱理学为圭臬,满怀保守主义色彩的救世情怀来引领一班“正人”,实现澄清天下的大任,确在晚清糜烂的社会罅隙中吹进了一股别样的清风,但也无法逆转或阻止晚清深重的社会危机的爆发。辩证地看,晚清社会风气的流变是以外激型碰撞为历史起点,但终是以内生型增长为内在根据的,即晚清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渐进式变迁终是解释这一变局的根本凭藉。因为湘军史在晚清史学研究中的枢纽地位,研究晚清社会风气的流变自然要从源头上探究,其中最基本的线索就是晚清湘军的肇兴使晚清的社会风气流变带有浓厚的个人和组织色彩,最终诱变为晚清乃至民国时期的一个特殊的政治胎记。本文略述一二,以求教于方家。
一 激扬家声——齐家与治国
曾氏家风以耕读、孝悌为核心理念,以“自拔流俗、进德修业、陶铸世风”为宗旨,将家规与治军、治吏以及转移社会风气结合起来,使咸同时期的风气没有完全衰败,完成了拯时救世的大任。
曾国藩出身耕读之家,要求曾氏家人和自己以修身进德为至要,凸显了曾氏耕读家风的文化图谱。曾氏家风以耕读治家、勤俭持家、孝友传家为基本内涵,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品格与遗传基因。在一定意义上说,曾国藩的吏治和军旅生涯鲜明地体现了曾氏家风的价值原则与伦理精神。曾国藩曾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致诸弟的信中说过,但愿诸弟及儿辈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贯穿其中的就是曾国藩修身齐家思想之要,这对于曾氏家族的影响颇为深远。就近而言,曾国藩家族数人因此而驰骋沙场以救世卫道;就远而言,曾氏家族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家族陋习。站在传统文化的道德至高点来看,“内圣”才是“外王”之根本。
在曾国藩的吏治和军旅生涯中随处可见其家风痕印。从湘军的组建来看,曾国藩创建的是一支具有鲜明理学色彩的军队。无论是训早操还是晚间军营读书声相传,遑论湘军统帅以儒家书生领山农的时代景观,恰如曾国藩希望家族尽出读书明理之君子一样,湘军集团是以“澄清天下”为文化使命和政治情怀的。同治二年十二月,曾国藩在给侄子纪瑞的信中说,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他毕生以勤俭自矜,服官20 年却不曾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曾国藩一生尤其戒惧月盈则亏之道,最怕后辈染上骄、奢、逸的毛病。
曾国藩以家规训营规,要求湘军将帅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所以,在湘军中形成了统帅率先示范、躬身营务的习惯,大凡战前都养成了察看地形的勤劳风俗,以惩戒湘军中的骄矜之气。湘军行军与作战中也养成了挖壕沟、扎硬寨、打死仗的行伍之风。孝悌和家是曾氏齐家的最高伦理准则,关系着家庭关系的长幼之序与朋辈之道。在曾国藩看来,天下官宦之家大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能延续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曾国藩自己终身躬行孝悌,无论是对父母还是兄弟子侄,都体现其崇高的道德风范。在湘军体系中,曾国藩尤其强调湘军内部的伦理秩序,所谓“湘军尊上而知礼”呈现了晚清湘军内部维系的精神纽带,意谓湘军内部通行尊卑有序的伦理原则,于国家而言,报效国家和忠诚天下是最高的伦理要求,这也是湘军最终能在完成镇压太平天国之后自己全身而退的一个重要原因。湘军内部虽然发生过几次分裂,但就湘军集团而言,在以曾国藩为中心的道德权威下湘系集团的各个成员和组织包括湘军幕府都能维系湘军利益大局,与朝廷形成了整体性的博弈格局,确保了湘军的生存空间与利益空间。
二 陶铸世风——以士风领世风
曾国藩以理学为圭臬,注重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之学。从士林风气来看,道光中叶以来的朝士风气专尚浮华。曾国藩早在居京期间就直指崇尚浮华、疏谈国事的士风,一反士子中工于小楷、巧设律诗的考据之风。任直隶总督期间,曾国藩发《劝学示直隶士子》,似乎在扩张湘学版图,实是改良燕赵之风,振兴北学。北学自康熙中叶开始衰落,莲池书院亦一落千丈。1868 年(同治七年),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伊始就力主改革莲池书院教学模式,直指北学软肋,强调以“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等四者为文化图谱,以改良燕赵之风。表面上看是曾国藩力图扩展湘学版图,实则是通过大力整饬书院,搜罗人才,发挥士风对于世风的引领作用。所以,曾国藩尤其注重人才至上,力倡引用一班“正人”,一改士林中的功利之风。曾国藩幕府为晚清人才之渊薮。曾国藩曾对胡林翼说:“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1]在清朝封闭的文化环境中,曾国藩为西学东渐打开了方便之门,推动了晚清洋务运动的开展,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推动洋务发展,曾国藩认为:“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章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才录用。”[2]这为开清季洋务之先声奠定了组织基础,开阔了世人眼界。
从湘军风貌来看,曾国藩以书生领山农为组织架构,以宗法文化为纽带依托,突出“忠义血性”的政治品格,通过“培养正人”以收“转移风气”之效。这些政治品格代表了晚清湘军的最高准则:第一要才堪治兵,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功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缺一不可。湘军军纪如禁鸦片、禁扰民、禁赌博、禁奸淫、禁异服、禁结盟拜会等被广喻士卒,赏罚严明。所以湘军严格的军纪与晚清朝廷经制兵的“败不相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反差,军营风气为之一变。
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则带有根本性的改革精神。从吏治弊端来看,曾国藩大胆针砭官场中琐碎、虚饰和骄矜之风。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曾国藩针对吏治弊端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滑机巧,逍遥自得。”[3]这种不溺于文辞而痛陈时弊的文化反思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直指吏治腐败的根源在于“用人一端耳”。曾国藩在1850-1852年间先后上奏议事。1850 年,其《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1851 年,上呈《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犯颜直谏君王“每察于小节”、虚文矫饰和“富威自专”之过。1852 年,上呈《备陈民间疾苦疏》,指出惟民心涣散为患甚大,强调钱贱银贵、盗贼增生、冤狱太多是破坏王朝民心根基的三大弊端。京官办事有“退缩”和“琐属”的通病,而外官办事则有“敷衍”和“颟预”的陋习,最终诱发民变。因此要清除民变的“乱源”,除了采取军事镇压政策以外,还必须从整饬吏治和挽回民心入手。于是曾氏坚持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收拾人心,以缓和“乱民四起”的社会矛盾。
曾国藩在掌管江南各省及直隶时,即对吏治进行整饬。他提出吏治要有一定的制度和法规。他亲自拟制《劝诫规则》16 条,作为官吏们廉洁尽职的标准。16 条包括劝诫州县、劝诫委员、劝诫绅士、劝诫营官等各4 条,可作为“好官”的座右铭。曾国藩在任直隶总督仅月余之时,就深感直隶官府“风气甚坏”,尤其在讼案方面问题多多。曾国藩从清理诉讼入手,整饬吏治,亲撰《直隶清讼十条》,要求通省大小衙门公文宜速,州县需躬亲六事,不得尽信幕友丁书,禁止滥传滥押头门悬牌示众,并且严饬州县、臬司收理公牍案件时,必须亲为审谳,按月呈报,不得积压。曾国藩重视吏治,激浊扬清,“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宦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变”[4],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
三 迁善改过——道德改造
曾国藩极为认同“性本善”的伦理假设,强调道德改造对于完善自我的重要意义。曾氏家风也历来强调道德修养的原则,体现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版图的厚重感。曾国藩以道德改造为路径,以仁礼忠信为治军之本,以“忠义血性”为选拔标准,以“勤恕廉明”为行动准则,对湘军的组建和湘军幕府的治理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构建了湘军左右相连、上下有序的伦理秩序,维系了湘系集团的统一。正因为曾国藩一直强调湘军以及湘军中枢——湘军幕府对于朝廷政治权威合法性的认可与极力维护,他始终没有走上历史惯性的拥兵自立的军阀割据道路,这应该归根于他对于晚清湘军体系的道德改造政策。曾国藩正是凭借其对湘军体系的道德权威而勉力维持着晚清的政治稳定,以收转移世风之效。
在曾国藩的道德改造图谱中,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也是廉洁的重要保证。他尝言道:“吾忝为相将,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当守此等简朴宅风,亦惜福之道也。”[5]而在官场生涯中,天下至诚则是曾国藩追求的道义制高点。曾国藩曾经对初入幕府而年少轻狂的门生李鸿章说:“此处所尚,惟有一诚字而已。”此则道出了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
曾国藩组建湘军坚持“以忠诚为天下倡”。他在选择幕僚时首先强调“忠”,其次“尚才”。有史料说,曾国藩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湘军幕僚之于曾国藩,湘军统帅之于晚清朝廷,都是以“忠”作为评判标准的。在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曾国藩借助于湘军这一载体,广修湘军昭忠祠、忠义祠及个人专祠,以大力弘扬忠孝节义的社会风气。对于湘军烈士的祭祀,既肯定了湘军历史的合法性,又激发了湘军集团为忠义而战的伦理精神,旨在“以慰忠魄而维风华”[6]。
在如何实行道德改造的途径上,曾国藩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突出了终身学习的理念,对于当时“心妄用,功杂效”空谈性命的学风不啻是一剂良药。在曾国藩看来,人改过方能成为贤人。曾国藩认为,唯有读书才能改变人的气质:“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7]而“多觅榜样”则是保全天命之性的最好方法,“做好人,做好官,做好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8]。道德践履则是曾国藩倡导师法古代圣贤的具体方法。
中国是在没有完全剪断原始宗法血缘关系的脐带的前提下进入文明社会的,蕴含在宗法关系中的社会伦理文化的传承需要历史长河中个别历史人物来担当。曾国藩以其个人特殊的人格魅力在内忧外患的晚清时空带领一班“正人”,改变了咸丰以后的社会风气。但社会风气的衰变毕竟存在其内在的演变逻辑与规律,曾国藩创建湘军所造成的晚清权力的全面下移与曾国藩等所倡导的伦理原则形成了事实上的悖离,最终造成了晚清更为深重的政治危机。
[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二)[M].长沙:岳麓书社,1987:617.
[2]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M].长沙:岳麓书社,1985:2.
[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一)[M].长沙:岳麓书社,1994:225.
[4]薛福成.庸庵文编:卷1[M].光绪石印本:32.
[5]马道宗.冰鉴[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102.
[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二)[M].长沙:岳麓书社,1987:1197.
[7]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6:67.
[8]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