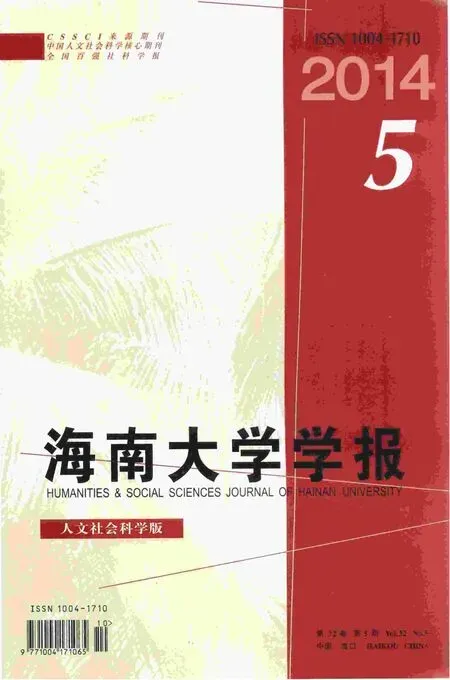“本质”的透视———海德格尔与实存主义的殊异考辨①
2014-03-31郭熙明
郭熙明
(海南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海南 海口570228)
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实存主义②“实存主义”是对Existentialisme(法语)、Existentialism(英语)、Existentialismus(德语)的翻译,在当今汉语学界,这几个西文更广为人知的译名是“存在主义”;关于该词译名的辨析,可参见孙周兴《本质与实存——西方形而上学的实存哲学路线》,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 期,页71-2;实际上,我国早在20 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引进“实存主义”初期,就有学者专门撰文辨析该词译法,见刘乃辰《存在主义乎?抑实存主义乎?》,载于《读书》1983年第12 期,第135 页。为了行文统一,笔者将在正文里把中文旧译的“存在主义”均调整为“实存主义”,而在注释中则保留原译者的译法以示对原译者感谢。于20 世纪首先在欧洲声名鹊起,随后愈演愈烈而成为席卷全球的思想运动。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与法国哲学家萨特密切相关:两次世界大战暴露出的人性丑恶及其带给人类的痛苦创伤,几乎是人们生活中浓郁的阴云,沉重压抑的气氛让人渴望积极乐观思想的疗治;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下,萨特通过《恶心》和《存在与虚无》表达出的实存主义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抨击为“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面对批评,1944年12月19日,萨特在《行动》杂志上公开发表《关于实存主义的几点说明》③1945年6月8日,这篇短文在《行动》杂志上再度发表,由此可见其影响力。[1]首次做出回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萨特先后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法国巴黎的“现在俱乐部”公开发布《实存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2]7的演讲,再度做出回应。通过两次回应,萨特成功地将实存主义解释为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哲学,由于重新解释过的实存主义切合于战后普遍存在的“人生之心境情调”④对笔者而言,“人生之心境情调”这一表述,特别来自于陈家琪的同名文章《人生之心境情调》,载于《读书》2002年第9 期,第133 页。,萨特的实存主义迅速成为遍及西方的思想和社会运动⑤以上内容根据两部著作整理而成:伊森·克莱因伯格的《存在的一代——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1927—1961》,陈颖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201 页;高宣扬的《萨特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年,第158-168 页。。
在萨特关于实存主义的两次答辩状中,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都身陷其中:由于海德格尔在二战中担任过纳粹德国官方任命的弗莱堡大学校长这一政治事件的公开,实存主义面临着“以德国纳粹哲学家海德格尔为师”的“指责”,第一次答辩时,萨特并没有否认实存主义与海德格尔的师承关系,而是一方面通过区分作为纳粹的海德格尔和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为实存主义辩护,另一方面冒着触犯众怒的危险从作为个人可能存在的“害怕”、“野心”或“随波逐流”的心理状态出发,为海德格尔的纳粹行为进行“同情的理解”:
海德格尔在成为纳粹之前就早已是一位哲学家了。他赞同希特勒主义是出于害怕,也许是出于野心,但随波逐流是肯定无疑的,他干的的确不漂亮,这我同意,然而仅仅这一点就足以驳倒你们的出色推论,你们说“海德格尔是国家社会党党员,所以他的哲学必然是纳粹党的哲学”。事实并非如此,海德格尔没有骨气,这才是真相。可是你们敢由此得出结论说,他的哲学就是对怯懦行为的辩护词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人有时达不到其著作的高度吗?[1]
第二次答辩时,萨特把自己与海德格尔都看作“无神论实存主义”的“代表人之一”⑥萨特对海德格尔作出“无神论”评价的时候,海德格尔作于1936年的《哲学论稿》(全集65 卷)仍在秘藏状态,其中的篇章“最后的神”(Der letzte Gott)应当知者寥寥;然而,当海德格尔接受《明镜》周刊的采访以“只还有一个神能救渡我们”的标题1976年刊行于世,萨特的这一评价当不攻自破;不过,海德格尔思考中的神,终究是一个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参见:张志扬的《偶在论谱系》“后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94 页;刘小枫选编的《海德格尔式的现代神学》,孙周兴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中“期待上帝的思”,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55 页。[2]6-8。显然,萨特的“知性真诚”让他无法回避实存主义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关联。毫无疑问,二战之后,萨特对海德格尔的思想辩护,在政治上给处于风口浪尖的海德格尔提供了很大程度的帮助,但是,它造成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实事”与实存主义长期的纠缠不清——至今,海德格尔仍然常常被看作实存主义的“代表人之一”。
根据美国学者克莱因伯格《存在的一代》[3]中材料丰富的分析,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最初的接受史被分为三个阶段:1932年,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共同的学生列维纳斯在法国发表《马丁·海德格尔与存在论》一文,拉开了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传播的序幕,尽管这篇文章涉及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但是其解读方向遵循由笛卡尔开创至胡塞尔达到顶峰的近代“主体主义”哲学传统。因此,通过科耶夫的黑格尔化,当法国思想界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第一轮解读在萨特的实存主义中结束时,海德格尔哲学已经被误读成与法国人笛卡尔引发的“主体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人道主义”了。1945年11月23日,让·波夫雷在巴黎金鸡咖啡馆偶遇让-米歇尔·帕尔米耶,得知他的朋友即将离开巴黎去弗莱堡,波夫雷匆匆写就一封短信托帕尔米耶带给海德格尔,这给了海德格尔陈述自己哲学志向并辨析它与萨特实存哲学之间殊异的机会,于是有了海德格尔于1946年秋天写给波夫雷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这封信次年在法国的公开发表激发了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第二轮解读,法国思想界因此注意到海德格尔从《存在与时间》中的基础本体论到思考存在历史的“语言转向”,海德格尔哲学于是带着它所有的异质性和陌生性回到法国,它对作为主体的自我进行的批判以及“语言转向”,直接促发了结构主义于20 世纪50年代在法国的兴起,同时拉开了海德格尔与萨特实存主义、法国哲学与笛卡尔主义的思想距离。第二轮解读扭转了第一轮“误读”海德格尔的局面,在以海德格尔自己的语言为基础理解海德格尔的虔敬追随中,法国思想虽然“还原”了海德格尔哲学,但仍然停留在注解海德格尔阶段,只有在以布朗肖“对灾难的书写”以及列维纳斯关注“他者”为代表的第三轮解读中,法国思想才开始在实质性地批判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础上,为人类的伦理和政治议题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通过以上简要概括,能够明显看到:克莱因伯格对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最初的接受史划分出的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误读”、“还原”和“创造”,这似乎在有意识套用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逻辑;同时,对于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最初的接受史,克莱因伯格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到“海德格尔纳粹事件”的限制。尽管看起来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位美国学者对法国思想接受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出色研究,仍然能够给予人启示:法国思想界对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接纳,一开始就不是盲目被动地跟随,而是从发源于笛卡尔的“主体主义”这一让法国人引以为傲的思想传统出发⑦张志扬多次强调过笛卡尔不等于“笛卡尔主义”(亦即“主体主义”),哲学史上的“主体主义”实际上形成于莱布尼兹,笛卡尔本人在《第一哲学沉思录》的“第三个沉思”中“知性真诚”地保留了“我”的“先天的时间缺口”,亦即“我”的“生存时间”中可以直观的“死的根性”。因而,如果没有“上帝”的担保,笛卡尔的“我”根本无法跨越成持存在场、永恒现存、绝对同一的“主体”。可参见张志扬《形而上学的巴别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第二章“主体之辨”,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3-200 页;张志扬《有意指的“意识”与无意指的“存在”》,见于道里书院论坛网,http://daoli.getbbs.com/post/topic.aspx?tid=200655。,积极主动地疗治“法国学院哲学的严重危机”,无论“误读”还是“还原”,法国思想始终都没有放弃为人类伦理和政治处境做出自己独特贡献的理想目标⑧关于法国哲学的独特气质,直接受到张志扬《检讨三代学人学术积累传承的前提》一文的启发,见于爱思想论坛网,http://www. aisixiang.com/data/48300.html。。
在20 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萨特的实存主义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先后被引入汉语学界;更早在20 世纪60年代,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就曾经被熊伟先生译成了中文⑨熊伟先生的这篇译文名为《论人道主义》,1963年被编入《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存在主义哲学》“内部发行”,1982年被编入《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首次公开出版;《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的新译见于2000年公开出版的《路标》,出自熊伟先生的“学生”孙周兴;2004年,《论人道主义》被编入《熊译海德格尔》,纳入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再度公开出版—20世纪40年代后期,熊伟先生恰在同济大学执教!对于笔者等后学而言,海德格尔这篇书信的中译和出版过程及其带出的时间跨度,既体现着这个民族传统的师生温情,又见证着新中国由自立走向自强的艰难历史。;然而时至今日,汉语学界混淆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与萨特实存主义的现象仍在持续,从萨特实存主义理解并遮蔽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力量依然不小。因此,本文选取萨特和海德格尔均使用过的“本质”一词,以透视并尝试考辨萨特实存主义和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殊异。
一、“实存先于本质”: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与柏拉图的“理念”
“实存先于本质”是萨特实存主义的标志性口号,对这个命题,萨特自己这样解释:
实存先于本质的意思指什么呢?意思就是说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如果人在实存主义者眼中是不能下定义的,那是因为在一开头人是什么都说不上的……人性是没有的,因为没有上帝提供一个人的概念……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实存主义的第一原则。[2]8
这段话透露出关于实存主义的几个要点:首先,萨特的“实存”特指人⑩相应于“实存主义”,“实存”是对existentia(拉丁语)、Existenz(德语)、Existence(英、法语)的翻译,这个词在哲学史上并不一定特指人。参见孙周兴《本质与实存——西方形而上学的实存哲学路线》,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 期,第71 页。克莱因伯格指出,萨特用“实存”来特指人与海德格尔的Dasein 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科尔班用法语réalité-humaine(人的实存)来翻译Dasein 之后,参见克莱因伯格《存在的一代》,陈颖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159 页。,因而萨特的实存主义是一种人生哲学(实践哲学);其次,萨特认为自己和海德格尔都是“无神论实存主义者”,他在有意拉开自己的实存主义与神学的思想距离;第三,“概念”、“下定义”显然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传统;第四,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实存先于本质”显然在反驳柏拉图以来的“本质主义”哲学传统。然而,麻烦在于:这几点之间相互牵扯关联,如果不能逐条理清,又如何可以给萨特实存主义在哲学史上一个合理的思想定位呢?
在《关于实存主义的几点说明》短文中,萨特对实存与本质做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区分,并在这个基础上给实存主义定位:
用哲学术语来说,一切对象都具有本质和实存。所谓本质就是属性中恒常因素之总和,而所谓实存,指的是世界上某种确实的在场。许多人相信,先有本质,然后才有实存……实存主义却相反,主张在人那里,也只有在人那里,实存先于本质。[1]
这番话至少提醒人们,就哲学史而言,萨特的实存主义仍然处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争辩中。因此,首先弄清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区分,应当是理解萨特实存主义的恰切进路。在介绍柏拉图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如是说:
苏格拉底……在这些伦理问题中寻求普遍性,并且第一个把思想专注在定义上。柏拉图接受了他的教导,但是主张把它不是应用于可感觉的事物,而是应用于另外一类实在,理由是永远变动的感性事物不能有一般定义,于是,他把这另一类的事物叫做理念。他说所有可感觉的事物都是根据这些理念来命名的,并且都依赖于与这些理念的关系,因为许多存在的东西由于分有“形式”就获得了它们具有的同一个名称。[4]
这段话十分重要,它在相当大程度上确定了传统哲学史对柏拉图的定位,而且,其中的关键词与萨特对“实存先于本质”的界定非常契合,可以从中带出对柏拉图本质主义的素描:由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引发“真理”和“意见”纷争,经过普罗塔戈拉、高尔吉亚、克拉底鲁等智者们用“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怀疑诡辩之后,使柏拉图不得不承接苏格拉底以完成“拯救现象”的重任;对苏格拉底开启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方式,柏拉图将注意力转到“下定义”,于是在“可感觉的事物”之外设定“理念”,理念具有“普遍性”因而可以“命名”具体个别的“可感觉的事物”,“可感觉的事物”只有在“分有”具“普遍性”的“理念”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让自身存在的“根据”。沿着这个思路继续下去,柏拉图的“理念”自然而然要走到“最具普遍性”的理念“至善”,就逻辑而言,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为“归纳”,这似乎暗合于洞喻中的囚徒由洞穴内上升到洞穴外;“至善”因而拥有普遍、永恒、先验的确定性,由于获得了对如洞穴外太阳般“至善”的惊鸿一瞥,凭借对“至善”理念的分有和回忆,“可感觉的事物”既获得存在论上的合理性而成为真实的存在,又在认识论上拥有了相应的确定性而成为可靠的真理,这似乎暗合于洞喻中的囚徒由洞穴外再度下降到洞穴内。在这一上一下的运动中,传统哲学的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位一体”得以实现。正如太阳在柏拉图洞喻中处于中心和绝对的高位一样,“至善”在柏拉图的“理念”中也处于中心和绝对的高位,柏拉图因此奠定了传统哲学以太阳为中心和高位的“白色神话”——拥有普遍、永恒、先验确定性的“至善”,尽管看上去像是基于经验地从一上一下的逻辑运动中推理而出,实际上则是被柏拉图像虔敬太阳神一样先验接纳和信奉的,就像世间万物离不开太阳一样。与之相应,柏拉图对分有和回忆的强调,是从逻辑上对演绎的先验设定。但由此造成理念世界的混乱,特别是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分离,则成了柏拉图致命的阿基里斯之踵。
柏拉图先验设定“至善”以及演绎在逻辑上优势地位的做法,激起他“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耿直学生亚里士多德的不满。于是,为了拆穿柏拉图“理念”世界的虚妄,亚里士多德采取了反其道而行的做法。
亚里士多德对“实体”给予过看上去不同的说明:在《范畴篇》第五章,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第一实体与第二实体,前者是具体个别的“这一个”,它“是那既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例如某一个个别的人或某匹马”[5]12;后者则是内涵比具体个别更抽象但外延比具体个别更丰富的属和种,“在第二性的意义之下作为属而包含着第一性实体的那些东西也被称为实体,还有那些作为种而包含着属的东西也被称为实体”[5]12,比如相对于“个别的人(如张三)”的“人”这个“属”和“动物”这个“种”。第一实体在语法中只能做主词,通过系词“是”的连接被宾词“种”和“属”定义,但一个合理的定义必定要体现出种加属差,如“张三是好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种逻辑思路是基于具体个别经验的归纳,亚里士多德要借此继续“拯救现象”⑪由此可见,“实存先于本质”的发明者,恐怕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这一个”、黑格尔的“感性确定性”、海德格尔的“Dasein”、萨特的“实存”,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密切的关联。。
于是,现象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第一实体”,“本质”则成为用来说明并依附于“第一实体”的“属性”,“本质”的地位仅仅被局限于说明“第一实体”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亚里士多德因此改变柏拉图集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位一体”于一身的“理念”“本质”,但“本质”依然拥有普遍、永恒的确定性,“本质”因而拥有了先验的地位。本质与作为个体的“第一实体”之间的关系,是形式与质料的关系。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则明确地说到了存在的三类实体,分别是可毁灭的可感实体、永恒的可感实体以及永恒的不运动的可分离的不可感的实体;物理学研究前两类实体,形而上学则研究最后一种实体,形而上学之所以比物理学要高,因为它研究的是“第一实体”。然而,这作为“永恒的不运动的可分离的不可感的实体”的“第一实体”,并非可以沿着归纳逻辑一步一步推理而出,归纳逻辑对动静生灭无效,于是,亚里士多德引“四因”中“动力因”和“目的因”补归纳逻辑之不足⑫黑格尔后来干脆把“目的因”置入逻辑内部,改亚里士多德归纳逻辑为辩证逻辑,以让作为“感性确定性”的“这一个”在有目的的运动进程中将自己整个变成“神”。然而,黑格尔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让归纳逻辑同时成为演绎逻辑,将“个别是一般”的逻辑随时颠倒为“一般是个别”,尽管这一点未必会得到亚里士多德认同。参见张志扬《偶在论谱系》第八节“亚里士多德实体——成为主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3 页。,“潜能”和“现实”是“动力因”和“目的因”的另一表述;“永恒的不运动的可分离的不可感的实体”的“第一实体”因而是“不动的动力因”的“神”,作为“第一实体”的“神”和具体个别的“这一个”之间的差异通过“目的因”得到了说明——“神”与具体个别的“这一个”之间有着自然目的论的等级秩序;如此,《形而上学》作为“神”的“第一实体”与《范畴篇》作为具体个别的“第一实体”的天壤之别被亚里士多德“目的”先行的精心策划所遮蔽;亚里士多德用他对自然目的论的等级秩序的信奉,重新同一了《范畴篇》被割裂的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位一体”。
于是,亚里士多德“第一实体”从“这一个”到“神”,就像柏拉图洞喻由洞穴内到洞穴外一样,它同样是被亚里士多德自己的“目的”先行设定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对确定的“第一实体”的寻求因而同柏拉图一样,均基于对“确定”的神学式信奉,与合乎逻辑的理性论证无关⑬这部分对亚里士多德“实体”的论述,同时参考了聂敏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功能主义和自然目的论》,但在取义的向度上与他有根本不同;参见聂敏里《存在与实体》“代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6 页。。。
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差别仅仅体现在各人为自己设定的起点,而在对“普遍、永恒、先验确定性”的需求上,二人则如一个铜板的两面谁都离不开谁,于是,西方哲学史上的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在纷争中双剑合璧地开拓着形而上学道路。
真正“把形而上学带到边缘”的是海德格尔。
二、“本质的本质性”:海德格尔对“实体”与“理念”的古希腊还原
以《存在与时间》为界,海德格尔的思想存在着早期和中晚期的“转向”,如果有保留地接受这一说法⑭“转向”不意味着海德格尔思想的断裂,而是说:转向之后的海德格尔,在“返回步伐”中越来越真实地“切近”存在—思想的实事,那么,1936—1942年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做过的6 次尼采专题讲座,则在这次“转向”中起了重要作用。克莱因伯格曾言:
从《存在与时间》的出版到《人道主义书信》的出版期间,海德格尔哲学还进一步远离了传统形而上学。他已经从强调《存在与时间》的基础存在论——这与实存主义紧密相连——转向了对存在历史的研究。[4]384
由于这6 次讲座是海德格尔对“柏拉图—尼采”的形而上学历史的重要清理,可以把它看作是海德格尔“转向对存在历史的研究”的关键步骤。
在《欧洲虚无主义》的讲座中,为了“把形而上学带到边缘”,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实体”和柏拉图“理念”进行了重新解释,在松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敞开更切近存在本质的古希腊初始经验。先看看海德格尔对“柏拉图—尼采”的形而上学历史的说明:
“形而上学”这个名称所命名的无非是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知识,而存在者的存在是由先验性来标识的,并且被柏拉图把握为理念。所以,随着柏拉图把存在解释为理念,形而上学就开始了。在全部后继时代里,形而上学烙印了西方哲学的本质。自柏拉图直到尼采,西方哲学的历史就是形而上学的历史。。⑮略有改动,着重号为作者添加。[6]852
“存在者之存在”(Sein des Seienden)这一表述,由于德语语法中的“魔鬼第二格”,实际上有两种不同含义:当第二格为“主语第二格”时,应为“存在者底存在”,“存在者”是主语;当第二格为“宾语第二格”时,应为“存在者的存在”,“存在”是主语;因而造成“存在者之存在”这一表述有两种不同理解方向,由于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与形而上学都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思考,弄清这个短语中的“魔鬼第二格”,就能清楚明了地看出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差异;海德格尔多次谈及,形而上学虽然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思考,但却是把“存在”当作“存在者”来看待,显然,形而上学所取的理解方向应为“存在者之存在”的“主语第二格”,存在者在形而上学的思考中毫无疑问地处于中心(主语)地位;海德格尔自己的存在哲学,不满于形而上学“存在者”对“存在”李代桃僵的做法,因而要在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思考中恢复“存在”的中心(主语)地位,无疑,他所选取的理解方向是“宾语第二格”⑯笔者对德语“魔鬼第二格”的清醒认识,主要来自于张志扬,可参见《是同一与差异之争,还是其他——评德法之争形而上学对奠基之裂隙的指涉》,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 期,第11 页。海德格尔在自己的行文中,对德语“魔鬼第二格”十分清醒,参《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载于《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67 页;笔者此处对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与形而上学对这个短语理解方向的区分,在海德格尔自己的文字中亦得到证实,参《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载于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34 页。。
如前所述,柏拉图的“理念”被看作是存在的“本质”,一切具体个别的“存在者”只有分有“理念”才能获得“存在”的合理性和真实性,然而,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由此呈现出与“现象世界”相对应的“理念存在者”,因而,柏拉图才在追求普遍、永恒、先验的确定性中将“理念世界”建立在“至善”这一“最高理念”的“本质”基础上。显然,柏拉图的“理念”既是“存在者存在”的根据、本质,同时又是“存在者”,如此的理解思路便是从“主语第二格”理解“存在者之存在”。
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这种理解“存在者之存在”的方式,是追问“这是什么”中的“什么”、“本质”的形而上学问题方向,亦即“本质主义”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则代表着形而上学的另一问题方向,即追问存在者“如何存在”并把结果导向“如此”的“这一个”,“如此存在”因而“指示着特殊个体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实情”,这存在者的“如何-如此”,“即是拉丁文的实存(existentia)的本来意义”,难怪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最终导向作为神学的形而上学或者具有神学指向的形而上学,亦即“实存主义”形而上学[7]。然而,这两种形而上学的共同点在于,力图通过确定某个独特的“在场者”遮蔽存在者与存在“非同一差异”中的“裂隙”,并以这个“在场者”为基础建立存在者与存在“同一”的形而上学巴别塔。
为了拆解柏拉图“理念”和亚里士多德“实体”中的形而上学,对应存在者与存在的存在论差异,海德格尔区分了名词性的“在场者”和动词性的“在场状态”,并且在从“宾语第二格”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过程中,力图恢复被形而上学奠定的“始基”及建立其上的“巴别塔”所遮蔽的存在者与存在“非同一差异”,还原存在在显隐相关中运作生成的生成“本源”。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存在意味着在场状态,即:进入无蔽域之中的持存者的在场状态”[6]848,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持存者”理解为某个能够始终在场的东西即“在场者”,他们就看不到与“在场者”密切相关的“持存者的在场状态”,甚至看到了也会因为对生成运作的存在“本源”之不确定的恐惧害怕而宁愿躲藏在自欺欺人的“始基”和“巴别塔”享受安逸的确定。
因此,就柏拉图的“本质”而言,它是确定的、永恒的;经过海德格尔所进行的古希腊还原而出的“本质”,实际为“本质的本质性”,它始终在存在者与存在的差异之间经受“不确定/确定”、“无/有”悖论式的生成运作——“本质的本质性”,总会因无而有地“解蔽”同时又由有返无地“遮蔽”,这种既显现又隐匿才是始终“在着”而又不终止其在于“某个具体在者”的“存在”奥秘、奥妙,凭借对它的悉心领悟和聆听,才可能让西方人从形而上学“迷途”返回存在的近旁“依于本源而居”⑰不能理解这存在“本源”的显/隐、解蔽/遮蔽、扭身而去的召唤之“双重性”,只能将海德格尔特别是其中后期的殚思竭虑,当作无聊的玄言或“让人诗意发昏”的昏话轻易打发掉。。
三、代结:奠基的“始基”,抑或本源的“裂隙”
很久以前,就有传言哲学是对“始基”的寻求,哲学家因而总是在“始基是X”的问题进路中,不断发明又推翻各种不同的“X”——从泰勒斯的水、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笛卡尔—莱布尼茨的“主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直到胡塞尔的“纯粹意识”,而传言中的哲学实际是形而上学,一部历时几千年的形而上学史中不断重复上演的奠基、精心构建方法体系、筑造巴别塔随后又眼睁睁目睹巴别塔倒掉的惨剧,在此不断重复过程中仍然不能让人惊觉而恍然大悟奠基不牢、方法体系不良、巴别塔不固,其实是形而上学家自设的迷误,形而上学的执迷和疯狂已经让人类在技术化和物化时代面临随时毁灭自身的悲惨处境,确定的东西反倒让人类未来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自以为可以像神一样支配自然的人类受到越来越可怕的支配——这一切多么讽刺,但的确已不再是耸人听闻的“盛世危言”。
海德格尔的“返回步伐”已经先行于人们地到达本源的“裂隙”,但他深知人们同在一个星球,于是扭身告诉人们:
在返回步伐中从差异之为差异的被遗忘状态而来追思这种作为解蔽着的袭来与自行庇护着的到达的分解的差异……只要我们思及解蔽和庇护,思及过渡(超越)和到达(在场),我们在这种关于分解的道说中就已经使曾在者达乎词语了。更有甚者,通过这种深入到作为其本质郊区的分解中的对存在与存在者差异的探讨,也许就有某种自始至终贯通存在之命运的一般东西显露出来。⑱这里同样需要尤其注意:解蔽着的袭来与自行庇护着的到达、存在与存在者差异区分化运作的分解中的“双重性”。[8]
但海德格尔仍然不忘告诫人们这有多难。
究竟有多难,一位老者已经用他几十年的艰难跋涉真实经历过,有他一路黑暗中夜行的文字为证。
[1]萨特.关于存在主义的几点说明[J].潘培庆,译.法国研究,1986(2):26-29.
[2]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伊森·克莱因伯格.存在的一代——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1927—1961[M].陈颖,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李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32-33.
[5]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M].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6]海德格尔.尼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7]孙周兴.本质与实存——西方形而上学的实存哲学路线[J].中国社会科学,2004(6):71-81.
[8]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孙周兴,译.[M]∥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