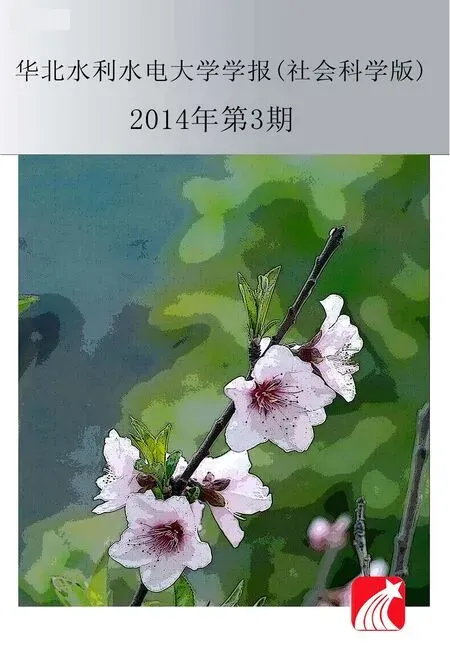波涛和雷雨中的觉醒与幻灭——《觉醒》与《雷雨》女主人公之比较研究
2014-03-31温松峰
温松峰
(郑州轻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在1899出版了她的代表作《觉醒》,为读者刻画了一个违背妇道、追求个性自由和人格完整的妇女形象。她最后的悲剧也揭示了传统父权社会道德对女性的残忍迫害。1933年,中国有部话剧也刻画了一个追求解放、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女性,即曹禺的《雷雨》。尽管生活年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雷雨》中的繁漪和《觉醒》中的艾德娜一样,都拒绝了传统给予她们的角色,为此她们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她们生活的时代父权思想极度严重,她们超越时代的思想和行为注定了她们的悲剧。父权文化要求女性“顺从、贞洁、有爱心、对家庭有奉献精神,有了这些,女性才可能获得幸福”[1](P373),结婚前顺从父亲或其他男性家长,婚后听从丈夫的安排,全力支持丈夫,有子女后要悉心照顾子女。女性要“耐心等待男人的救赎,将婚姻视为对良好的品行的唯一奖励”[2](P87)。两个女主人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抗父权社会,反抗传统社会道德。她们的反抗既相似,也有不同之处,但都让我们看到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与戕害。
一、艾德娜的觉醒和悲剧结局
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父权文化氛围很浓,女性仍然被局限在家庭。女性一生的身份都建立在其与男性的关系之上。婚姻是女性的生活目标,女性要照顾丈夫和孩子,忠于家庭。在路易斯安那,即《觉醒》中的故事发生地,女性甚至不能单独上街,更别说发展自我,追求解放与独立。“离开了丈夫的女性就没有自己的身份,她们不能拥有财产,她们的一生只能和丈夫联系起来。”[3](P205)浓厚的父权文化夺去了女性独立的创造主体身份,将生儿育女、照顾家人规定为女性的天职。正如小说一开始所描绘的失去自我的女性形象一样,“她们就是这样的女人:钟爱孩子,崇敬丈夫,认为抹杀自己个人的存在,并且长出翅膀变成救苦救难的天使,是一种神圣的权利”[4](P5)。
艾德娜在觉醒之前也是个没有自我的女性,恪守女性的社会角色,忍受没有爱情的婚姻。她像丈夫一件颇有价值的私人财产一样被欣赏着,“也许还可以以一定的尊严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下去,而永远关闭掉通向浪漫和梦想的王国之门”[4](P11)。她没有过多的行动自由,只是打扮好自己,取悦丈夫,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她还要为丈夫装点门面——每周二下午她都要精心打扮一番,招待来访的客人,直到深夜。在家中,丈夫是至高无上的,可以常常夜不归宿,赌博,和其他女人鬼混。
在外人看来,艾德娜有个幸福的家庭,但她不满足于现状,总是有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让她隐约感到痛苦的压抑感”,这使她内心非常孤独。迫于传统的压力,艾德娜只有把这种痛苦深埋在心里,做一个别人眼中的贤妻良母。也正是这种痛苦驱使她觉醒,开始慢慢释放自己,连她父亲都对她丈夫说“你对她太宽容了”[4](P112)。29岁生日宴会对艾德娜来说非常有意义,这一天她容光焕发,充满活力与自信,开始刻意拒绝做“贤妻良母”,试图打破外部世界的限制。她一直以为自己学不会游泳,在格兰德岛她发现自己可以学会。游泳还唤醒了她对独立自由的渴望,让她第一次感受到激情,看到生活的光芒。学会游泳是艾德娜觉醒的标志,使她意识到父权文化的禁锢。因此,她决定逃离丈夫的支配,拒绝接受丈夫的发号施令。“我要呆在外面,我不想进去,也不打算进去,以后不要再这样跟我讲话,否则我是不会回答的。”[4](P74)这件看似琐碎的事是艾德娜“第一次正面抗议他们的婚姻所默许的前提,即丈夫的权威”[5](P78)。此后,她开始刻意拒绝之前的角色,如把婚戒丢到地上,并用脚踩。婚姻在她眼中成了“世界上最令人惋惜的事情”[4](P101)。后来,她索性搬出了家,住进了“鸽子屋”,不再出席丈夫的会客日,很少做家务,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绘画上。丈夫、家庭、孩子已经不再是她的全部生活。
随着思想的觉醒,艾德娜的女性意识也开始苏醒。作为一个浪漫的、爱幻想的女性,她拒绝被物化为男性欲望的客体,试图作一名自由独立的女性。因此,她开始按个人意愿选择情侣,体验全新的、充满激情的生活,有了两段离经叛道的婚外情,逃离了丈夫的束缚。但父权社会传统是艾德娜所无法逃脱的。最终,她的爱人罗伯特也无法理解,离她而去,她又堕入了残酷的现实。脱离了丈夫和孩子的艾德娜无法切断与孩子之间的伦理纽带,更无法摆脱来自社会各方的道德制约。所以,艾德娜来到让她觉醒的地方,在大海温柔的拥抱中,赤裸着缓缓走入大海,游向远方,直到精疲力竭。她用生命换得了解脱、自由和独立,永远地逃离了孤独。
二、繁漪的觉醒和悲剧结局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多数女性也被浓厚的父权文化所约束。丈夫在家中的权威和蛮横使家庭缺乏应有的温情和夫妻之间的关爱,妻子与丈夫之间只有服从和被服从的关系。受“五四运动”所倡导的女性解放思想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女性也像艾德娜一样,不满于无爱的婚姻和冷漠的家庭,试图摆脱父权文化的约束,争取自由和爱情。《雷雨》中的繁漪就是这样,她和艾德娜一样,有着自由的思想,却受困于无爱的婚姻,被长期禁锢在周公馆,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她的丈夫周朴园大她二十岁,封建思想十分严重,视她为个人财产,习惯性地命令、斥责家人。因此,繁漪的精神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过着寂寞乏味的生活。在死气沉沉的周公馆里,繁漪逐渐失去了她原有的活力,“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6](P61)。
繁漪是一位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作为旧式女性,繁漪上过私塾,具有旧式女人的文弱和忍让等特点。但她所受的新式教育使她比一般的旧式女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使她具备了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的能力。新式教育解放了她的个性,使她无法安于“三从四德”所为之规定的命运。但作为周朴园的妻子,繁漪得不到一个妻子应有的尊重,没有爱情,没有自由。她要服从丈夫的命令,被他以“病”为借口隔离在闷热的楼上,被逼喝药。尽管不愿意也不喜欢周朴园霸道的作风,但繁漪还是选择压抑自己服从丈夫来化解家庭危机。继子周萍的到来唤醒了她对爱情的向往,她不顾人伦道德,爱上了继子,从这种“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畸形关系中得到些许精神慰藉和情感满足[6](P61)。但他的移情别恋让繁漪再次陷入痛苦之中,于是她开始疯狂地反抗、报复,最终毁灭了别人,也毁灭了自己。
繁漪有一定的独立意识,但还不足以使她摆脱旧式的家庭、放弃养尊处优的生活去追求新的幸福。周朴园家庭至上的观念和专制主义折磨着她,使她的生存理想与现实相悖,在空虚和痛苦中煎熬了十八年,磨钝她的感观。在这样的牢笼中,繁漪慢慢变成了一个活死人,正如她跟周冲所说的,“我忍了多少年了,我在这个死地方,监狱似的周公馆,陪着一个阎王十八年了,可我的心并没有死”[6](P162)。繁漪所渴望的只是一个普通人应该有的温暖和自由,但是周朴园紧紧地把她困在自己编织的牢笼中,把她变成了他的附属品。虽然在物质上她应有尽有,但却只能把自己的追求局限在家庭内。周萍的出现并以平等的身份向她吐露心声,使她感到温暖,唤醒了她对生活的憧憬,因此她把爱情倾注到了她不该爱也无法给予其真正爱情的继子身上。当周萍回归传统伦理的框架后,后悔并抽身这段畸恋,繁漪开始一步步逼迫自己和他人走向悲剧的结局。
三、结语
尽管艾德娜和繁漪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但她们都是生活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她们都将这样的社会文化不同程度地内化了,但是深受压抑的她们仍然渴望独立自由的生活。繁漪与艾德娜相同,都是因为某一个男性人物的出现而觉醒,进而反抗压抑的父权文化,最终都是因为无效的反抗而选择自我毁灭。对于艾德娜来说,她是在与罗伯特在大海里学习游泳的时候觉醒的,大海使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激情,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是大海唤醒了她的心灵,并使她反思生活。艾德娜觉醒了,深刻意识到婚姻和家庭对她的禁锢。于是她反叛社会道德,去追求真正的爱情,按自己的意愿去寻找伴侣,坦率地说出了对罗伯特的爱。美国十九世纪的社会道德对这种行为是不宽容的,所以更表现出艾德娜的勇气,但同时艾德娜也是注定要遭到社会抛弃的,就连爱她的罗伯特也没有勇气去面对。既不愿意再次回归桎梏灵魂的家庭,又无相爱的人与其一道,陷入困境的艾德娜无路可走,最终选择大海,用自己的生命换得灵魂的自由。她选择死亡并非是逃避社会,而是用牺牲自己来反抗社会。繁漪是因周萍的出现而觉醒,选择一条注定是不归路的方式反抗传统。这种畸形的反抗方式也正是她与艾德娜的不同之处。艾德娜更多的是因为爱惜自己而反抗,但繁漪的反抗是近乎自虐式的。曹禺说:“繁漪是个最令人怜悯的女人,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勤的马,毫不犹豫地踏着艰难的走道,她抓住周萍不放手,想重新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这条路也引向了死亡。”[6](P3)另外,艾德娜的自我毁灭是清醒之后的选择,而繁漪的毁灭是无助的仓皇决定,也牺牲了其他的人。总之,她们二人都是父权社会中女性悲剧生活的缩影,她们的悲剧使我们看到,父权文化统治下的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道路的艰难。尽管艾德娜和繁漪觉醒了,但从父权文化桎梏之下解脱后,发现自己仍是走投无路的。因此,要解决女性的生存困境,就要打破传统的霸权式父权文化,建立更加多元化、灵活、宽容的社会文化,使女性能够拥有更多的自主和选择权,进而真正实现性别平等。
[1][美]Welter,Barbara.“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1820-1860.”Family in Transition[C].10thed.Eds.Arlen S.Skolnick& Jerome H.Skolnick.New York:Longman,1999.
[2][美]Tyson,Lois.Critical Theory Today[M].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Inc.,1999.
[3][美]Walker,A.Nancy.Kate Chopin:A Literary Life[M].Hampshire:Palgrave,2001.
[4][美]Chopin,Kate.The Awakening[M].文忠强,贾淑勤,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5][美]Christ,P.Carol.“Spiritual Liberation,Social Defeat:Kate Chopin”in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C].Vol.14.Ed.Hall,K.Sharon.Detroit:Gale Research Company,1981.
[6]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