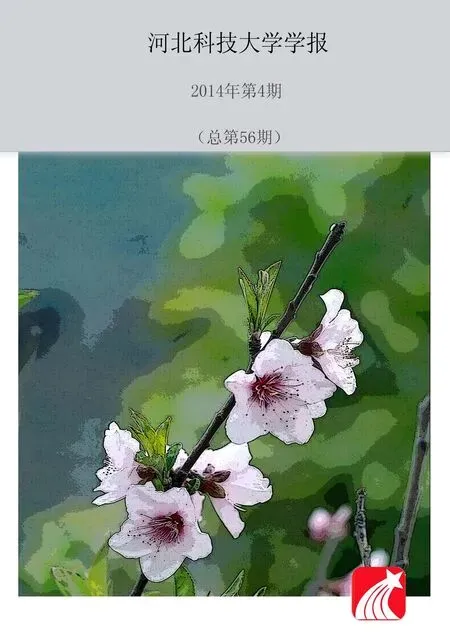论《狼图腾》的“嫁接性”叙事
2014-03-30李致
李 致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狼图腾》(以下简称《狼》书)作者在文学叙事方面具备的表现力和创造力令人震撼。小说围绕着草原上人与狼以及草原之间内在的生命联系展开描写和思索,其独特别致的叙事给文坛和读者带来震惊,其“嫁接性”的叙事也为很多评论家所诟病,但笔者认为《狼》书的叙事价值恰恰是它独特的“嫁接性”文体。作者在小说结构上大胆突破,采用主体叙事+“理性探掘”的结构,将传统小说的形象性叙述和学术论文的逻辑论证相结合,用生动的形象、鲜活的生活场景和语言演绎作者的观点。这在当现代文学中是较为罕见的。
一、借助“狼性性格”塑造叙事信念
姜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谈小说文体,“我认为这既是‘一部充满哲学、人性色彩的论文’,又是一部充满了形象、性格、血肉、故事、情感、想象、虚构、细节、冲突、激荡奔放等等文学元素的长篇小说。”[1]这说明作者运用这种“嫁接性”叙事策略是一种自觉主动的选择。小说之所以吸引读者的首先还在于小说中的主体叙事部分,这部分为读者呈现了鲜活的草原世界和生命体验。
小说叙事强化陈阵的主观感受和体验,而淡化情节。小说开场是陈阵在毕力格老人带领下近距离观摩狼围捕黄羊,中间插叙了陈阵孤身陷入狼群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激发出陈阵观察狼、研究狼的欲望;随着与狼(包括狼的故事与传说)的深入接触,陈阵对狼和狼性、“狼图腾”的兴趣愈发浓厚。这种兴趣强烈地吸引了陈阵,强烈到让他冒天下之大不韪,亲自养了一只小狼。小说从第十章开始转入对小狼个体的描写和观察,作者通过陈阵养小狼的线索,穿插着关于人与狼的点点滴滴,包括人与人、人与狼、人性与狼性、草原精神与信仰、原始天鹅湖的发现和死亡、游牧文化与汉文化的对比、草原上无处不在的“狼图腾”信仰、小狼之死等等。陈阵通过与小狼的朝夕相处,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草原精神与信仰。我们无法从小说中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情节线,唯一称得上小说线索的也就是小说人物陈阵在草原的生活经历。这是一种反情节化的叙事策略——淡化了情节,而强化了陈阵的体验和感受,引导读者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射到陈阵的内心世界。《狼》书这种叙事策略,曾招来一些批评。李建军命名该小说的叙事为“假言叙事”,批评小说的情节缺乏因果关联:“《狼图腾》采择的显然不是写实性的写作路径,而是一种依据理念和假想展开的虚拟性叙事策略。……我将他的这种奇特的叙事命名为‘假言叙事’。这是一种极其消极的叙事模式。它把缺乏可靠性的事象和冲突,当作推动情节展开和发展的动力;把虚假、可疑的或然性质的判断,当作得出真实、深刻的实然性质的结论的根据和前提。但是,由于作者的猜测通常基源于一种偏见甚至谬见,由于它的情节的因果链条之间缺乏充分的逻辑关联,因此,造成一种极其虚假而混乱的叙事效果,给人一种诡诞而荒唐的阅读印象。”[2](P41)这意见尽管更多的是批评者道德意识俯视导致的“偏见甚至谬见”,但敏锐而正确地抓住了小说在情节方面的特点。《狼》书缺乏一个强烈集中的矛盾冲突作为情节发展动力,知青陈阵等人在草原生活的经历就成为结构小说的唯一线索。人与狼构成了“看”与“被看”的关系:对于陈阵而言,狼是“被看”的对象,对于读者而言,陈阵和狼都是“被看”的对象。这样的叙事策略就将“狼图腾”的寓意最大程度地“间离”给读者。
通过这样的叙事策略,小说叙事主体部分用宏大叙事的手法展示了草原上各种生物之间的生存形态,演绎了草原上的狼、人、马、羊、獭等这些“小命”与“草原大命”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联系,描写和塑造了草原上被作者称作“狼图腾”的强大精神力量,揭示了这种精神力量影响下美丽的额仑草原及诸多草原生命别样的生命形态和生存法则。小说开篇即一个壮观开阔的场景:陈阵跟随毕力格老人观摩草原狼群围剿黄羊,中间插叙了陈阵孤身陷入狼群智退狼王的故事,场面紧张而充满悬念。之后,小说即以陈阵的视角观察和描写草原狼,写草原人爱狼、恨狼、怕狼、杀狼、图腾狼的复杂心态,尤其是通过养小狼得以近距离地观察狼之后,更全面深刻地展示了狼的智慧、狡猾、凶狠,野性难驯,富有团队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精神特点。陈阵在日常草原生活中通过与草原智者毕力格老人以及其他草原人的接触,在对草原狼用心观察和思考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狼图腾”精神是草原文明乃至人类的核心,是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源头和动力。
“狼图腾”精神更是通过“狼性性格”的塑造完成。《狼》书作者用他在草原生活的独特经验和瑰丽的想象力塑造了令人震撼的“狼性性格”。为了凸显“狼图腾”精神,作者在“草原逻辑”这一前提下来描写狼:“狼图腾是什么?狼图腾是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当万的强大精神力量。狼图腾是捍卫草原大命的图腾,天下从来都是大命管小命,天命管人命。天地没命了,人的小命还活个什么命!要是真正敬拜狼图腾,就要站在天地、自然、草原的大命这一边,就是剩下一条狼也得斗下去。”[3](P189)这样就等于是有了一个过滤器,“狼性”中有助于塑造和展示“狼性性格”的成分便被保留下来,而无助于甚至有害于性格塑造的部分便被过滤掉。小说中的草原狼与人(草原人和北京知青)之间形成了互动,启示主人公陈阵思考和探索“草原逻辑”。陈阵第一次从一大群金毛灿灿、杀气腾腾的蒙古狼群中死里逃生之后,便产生了接近狼、观察狼和研究狼的强烈欲望。在这种欲望的驱遣和草原智者毕力格老人的启发下,陈阵逐渐深刻地理解了“狼”,理解了“草原逻辑”。作者用“草原逻辑”辉映着“狼图腾”精神的光芒,同时也在悄悄地滤除狼性中“凶残”等负面成分:极力消除读者将“狼性性格”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的潜在可能。在小说第六章,陈阵面对狼群屠马的血腥场面时,“他在狼性中看到了法西斯、看到了日本鬼子。陈阵体内涌出强烈的生理反应:恶心、愤怒,想吐、想骂、想杀狼。他又一次当着毕力格老人的面脱口而出:这群马死得真是太惨了,狼太可恶太可恨了!比法西斯,比日本鬼子还可恶可恨。真该千刀万剐!”立即遭到了毕力格老人的驳斥:“日本鬼子的法西斯,是从日本人自个儿的骨子里冒出来的,不是从狼那儿学来的。”[3](P56)在草原生态链中,狼是最重要的一环,人、狼、食草动物、草之间因狼的存在而保持了理想的平衡状态。凶残的狼维护了草原的美丽和生命,是草原的守护神:“草原太复杂,事事一环套一环,狼是个大环,跟草原上哪个环都套着,弄坏了这个大环,草原牧业就维持不下去。狼对草原对牧业的好处数也数不清,总的来说,应该是功大于过吧。”[3](P151)从这一视角而言,作者是在呼吁一种和谐自然生态,认为草原人的“狼”图腾崇拜最符合生态平衡的需要,草原上(蒙古人)信奉“天兽人草合一”,远比华夏文明中的“天人合一”,更深刻更有价值。
二、理性阐释显逻辑严密之思想美
主体叙事和“理性探掘”两部分相得益彰,使得小说寓理于情,在情理交融中完成作者对“狼图腾”精神的塑造和烘托。在主体叙事部分,作者借知青陈阵和杨克等人的对话和思考将关于“狼图腾”的观点穿插在人与狼的故事中,实际上已经完成对小说主旨的传达。但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意犹未尽更是大胆地加上一章“理性探掘:关于狼图腾的讲座和对话”,进一步对“狼图腾”精神进行了酣畅淋漓的阐释和规范,并用“狼图腾”精神重新梳理和审视中国文化。小说的这种结构为很多批评家所诟病,认为“《狼图腾》的主体部分是优秀的。但是,赘在后面的《理性探掘:关于狼图腾的讲座和对话》却比较糟糕。”“理性探掘部分的理论实际上与主体形象部分的形象并不融洽,甚至可以说理性探掘部分有时恰好在消解主体部分的思想。”[4](P6)这种判断有其道理,但并不完全准确。从某些角度看,后面理性探掘部分确有将小说概念化的嫌疑;不过从小说理念的统一性和叙事效果的可控性角度看,作者通过强化叙事者的议论强化作者的价值观无疑地是一种正确的策略。我们不妨用W·C·布斯的小说修辞理论来分析一下《狼》书“理性探掘”部分对整个小说叙事的意义。布斯认为,在小说叙事中“作者的声音从未沉默”[5](P63),关键是作者通过什么样的技巧将他的声音传达给读者并得到认同。布斯将布洛的审美距离概念引入小说分析并提出小说距离控制的概念,认为小说叙事技巧的本质就是处理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叙述者、其他人物和读者之间往往存在道德、情感、价值、理智等方面的差距,最理想的叙事效果就是随着叙事的展开和完成,读者最终接受了作者的信念和规范。《狼》书叙事的主体部分,作者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由很多形象和思想元素构成的形象体系,生态元素、文化元素、民族性批判等诸多元素共同丰富和演绎着“狼图腾”精神;“理性探掘”部分则引导和强化了读者从多义性的形象体系中认同和接受作者的信念和价值观,是作者完成“狼图腾”精神塑造的最后一块拼图。
雷达先生在分析小说叙事特点时曾用“边缘性和嫁接性”来概括:“关于《狼图腾》的文学性,不宜用常规要求,它确乎有点小说不像小说,纪实不像纪实,带有边缘性和嫁接性。”[4](P5)不过,雷达先生并未就小说的“边缘性和嫁接性”特征及其叙事效果深入阐释。事实上,“嫁接性”是小说叙事的特点,更是小说作者有意为之的叙事策略。它关系着小说美学世界的成功建构和小说主旨的成功表达,也关系着小说作者更深刻的文化使命的传达和实现。“嫁接性”首先来源于“理性探掘”部分的存在。
“理性探掘”部分的讲座是在人物性格允许的范围内完成的,也有助于提升人物作为具有独立人格和理性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内涵。《狼》书作者选择第三人称(陈阵)限知叙事的策略,通过强化叙事者陈阵的经验和思考来实现他的叙事目的。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中心人物,人和狼都是作者叙事展示的对象,是“狼图腾”精神的承载者和体现者,谁都称不上是绝对中心形象。如何在人与狼与草原的演绎故事中离间出“草原逻辑”以及“狼图腾”精神,叙述角度和叙事代言人的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而且,在这样一部叙事中掺入大量理性议论的小说中,叙事时刻都有坠入教条说理的泥潭而引起读者反感的危险。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叙事代言人就显得异常关键。最理想的叙事代言人既要能够参与事件的发展,引导读者进入特定的叙事情景产生情感共鸣;同时又能跳出叙事进程引导读者开展理性思维。小说中,场面和事件的叙述以及作者叙事信念的塑造都是通过陈阵来完成的。作为叙述者陈阵既是事件的参与者又是事件的旁观者,他构成小说叙事的最佳支点。作者精心设置了人物的身份和形象,因而非常轻易地就赢得了读者的信任:一个被流放到额仑草原的汉族知青,出身于汉族高知家庭,不盲从政治运动,不苟且逢迎权贵,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求知欲、理性思维精神和独立人格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富有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理的执拗和勇气。这样的形象很容易为现代读者所认同。陈阵的形象是在小说叙事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知的,因此读者与陈阵之间的价值、审美和信念等方面的距离在叙事时空中也被逐渐缩小。《狼》书叙事线索是陈阵、杨克等汉族知青与草原原住民(包括人与狼等生物)的接触和观察,其间穿插了大量生活场景的鲜活片段和陈阵关于“狼性”的思考。作者正是利用读者对叙述者的认同而将“草原逻辑”和“狼图腾”精神的全新观念推到前台。小说叙事主体部分完成后,读者已经完全接纳了陈阵关于“狼图腾”的看法,因而再推出“理性探掘”就显得顺理成章,读者读来如面对一个睿智的学者的讲座,乐思想的锋芒而忘其冗长,享理性的深度而忘其艰涩。
“狼图腾”精神的真正指向是国民性批判,姜戎以“狼图腾”精神体系为参照系,反复批判和反省汉民族软弱的民族性。小说结尾处,作者借杨克与陈阵的对话表达了自己创作小说的终极目的:“我考察研究近30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病根,寻找中国的出路。现在找到了中国这条五千多年的老病根,就可以对症下药,把握民族的命运。”[3](P401)小说作者在谈到《狼》书创作动机时也曾做过类似的表述。①小说以草原狼为载体多方展示了“狼图腾” 精神强悍、智慧、尊严、顽强、团队意识、崇尚自由独立等内涵,它是草原民族的精神底蕴,曾铸就强大的草原帝国,曾诞生过成吉思汗和康熙们。作者在描写和展示草原人强大的精神信仰的同时,也找到了汉民族性格病态的根源所在:农耕民族的“羊性”所致,医治的药方就是“狼图腾”。长期的农耕生活让汉民族丧失了作为人性中的顽强勇猛和开拓进取的成分,变得越来越软弱和任人宰割。“狼图腾”精神这面镜子,让读者惊觉汉民族的性格缺陷,也清楚地发现了民族性格健康发展的进路。
小说由于主体叙事部分的文学含混性而导致其主题的多义性,容易令读者将小说作为生态文学误读;而 “理性探掘”部分的存在,使我们确证那些将《狼》书当作生态文学来阐释的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单向度读解,它与叙事主体部分交相辉映显示出逻辑严密之思想美。
三、结语
小说这种“嫁接性”叙事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审美规范,因而引起很多文学批评者的诘难。从小说艺术探索的角度看,文学研究应该给这种“嫁接性”小说写作多几分包容之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乏作家因在叙事文体方面不合常规而受到责难的例子。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因其敢于真诚大胆地袒露“性苦闷”和伤感情绪而曾广受责难;汪静之的诗歌《蕙的风》也曾受到很多道德家的“淫书”诬蔑;鲁迅《呐喊》《彷徨》曾获成仿吾除《不周山》外其他作品皆“浅薄”“庸俗”之作的批评,甚至鲁迅开创的“杂文”这一文体的合法性直到现在还在受着一些研究者的非难和质疑。然而,它们都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这些都已经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公案,它们为文学发展所做的艰难探索和贡献以及当初所受种种非难都已经铭刻历史。文学批评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为未来的文学发展寻找方向和动力,因此,它需要关注任何可能给文学发展带来契机的叙事实验和探索。就这个层面看,笔者相信《狼》书因其叙事上的大胆突破和探索,它终将在未来的文学史上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无论它的叙事是否完美。《狼》书叙事的价值也值得研究者去关注和肯定。
《狼》书作者用令人耳目一新的叙事策略塑造了“狼图腾”精神,从而打破了人们心目中传统的“狼”形象,并用“狼图腾”的精神重新梳理了中华文明史。这就颠覆了汉民族文化中心的观念,“一位作者试图用新的标准重新评价所有价值,或超出这种或那种思想规范到达全新的领域,或暂时把所有价值搁置不用,而不仅是把一种公认的思想规范抬高到另一种之上时,人们便可以预料到,会有更精心制作的修辞。”[5](P203)的确,《狼》书的“修辞”技巧和策略足够精心。作者在文学叙事方面具备的表现力和创造力令人震撼,小说围绕着草原上人与狼以及草原之间内在的生命联系展开描写和思索,其独特别致的叙事给文坛和读者带来震惊,引起很多评论家对小说叙事价值和意义的关注。笔者认为《狼》书的叙事价值恰恰是它独特的叙事文体。
注释:
①姜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这样表述小说的创作动机:“越是真实、深刻地了解狼的精神,我就越是感到汉民族的性格缺陷的严重性。我只是在‘中原大地’的农耕土壤上,竖立了一个具有可比性的参照系,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本民族的弱性。”参见姜戎的《我的“狼书”一定战胜“羊书”》,《新京报》2004年4月25日A23版。
参考文献:
[1]姜 戎.我的“狼书”一定战胜“羊书”[N].新京报,2004-04-25(A23).
[2]李建军.是珍珠,还是豌豆?——评《狼图腾》[J].文艺争鸣,2005,(2).
[3]姜 戎.狼图腾[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4]雷 达.《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欲望与理性的博奕[J].小说评论,2005,(4).
[5][美]W.C.布斯.华 明,胡晓苏,周 宪,译.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