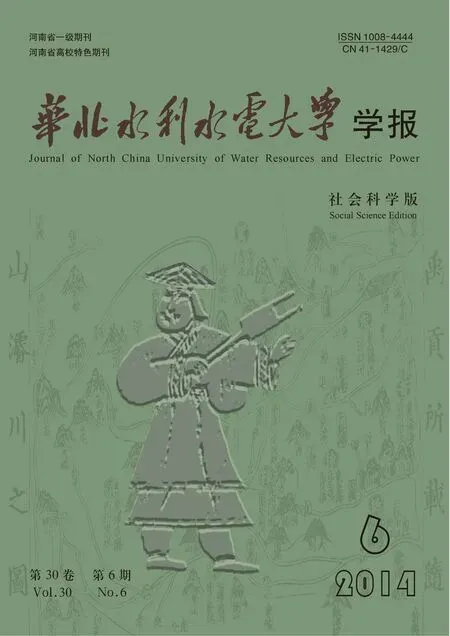邝丽莎历史小说中的中国意象
2014-03-30孙冬苗
孙冬苗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邝丽莎历史小说中的中国意象
孙冬苗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美国华裔作家邝丽莎以中国在美国的代言人自居,认为自己笔下的中国是真实可信的。然而,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出发对邝丽莎的历史小说进行文本解读和分析,不难发现邝丽莎笔下的中国呈现两种意象:西方话语体系下的“野蛮中国”和“竹幕”之后的“红色中国”。 此外,邝丽莎笔下的中国人依然笼罩在“他者”面纱之下。可见,邝丽莎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并不具有代表意义。
邝丽莎;“野蛮中国”;“红色中国”;他者
邝丽莎在美国华裔文学界是一位独树一帜的作家。大多数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华裔作家如汤亭亭、赵健秀、任碧莲等,其作品多纠结于华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这一弱势少数民族的特有情节,较少涉及中国。然而,仅有八分之一中国血统、外貌几乎没有任何中国人特征的邝丽莎,坚持自己的华裔身份,致力于挖掘被遗忘、被埋没的历史来书写中国人的故事。如《雪花与秘扇》以19世纪的中国湖南瑶族村寨为背景,通过讲述一对老同姐妹雪花和百合的故事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的女书文化。而《恋爱中的牡丹》则将故事背景设定在17世纪的中国杭州,讲述了一个文艺少女因相思病而亡的故事。在《上海女孩》中,邝丽莎将该书的主人公珍珠和梅置于1937年至1957年这一历史语境之中,迫使她们历经日本侵华战争、天使岛移民审讯和坦白运动等历史磨难。小说《乔伊的梦想》是《上海女孩》的续篇,讲述了珍珠和梅的女儿乔伊返回中国寻找生父和在安徽农村结婚生女的人生经历,天真而又倔强的乔伊却因大跃进运动和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尝尽了人生的苦难。
在访谈中,邝丽莎一再强调自己的中国血统,表示愿意成为中美两种文化沟通的桥梁。正如她本人所说:“我不完全属于美国,也不完全属于中国,这样的背景对我写作很有帮助,我笔下的中国和美籍华裔的生活经历,对中国人来说是真实的,同时也能被美国人和其他的西方文化所接受。”[1]邝丽莎希望用写作来还原历史尤其是那些对西方人来说鲜为人知的中国历史,从而消除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她说:“写作就是我最好的方式来宣传中国以及中国文化。”[2]那么,仅有八分之一中国血统的邝丽莎能否成为中国在美国的代言人?邝丽莎对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呈现是否具有真实性?其作品中的中国元素是否带有东方主义的烙印?笔者拟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对上述四部小说进行文本解读,对上述问题一一答复。
一、西方话语体系下的“野蛮中国”
邝丽莎在《南方日报》的访谈中还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写作目的:“我希望读者从我的书中感受到的是,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共同拥有的生活经历—— 恋爱、结婚、生子、死亡,以及人类普遍的情感体验—— 爱、恨、贪婪、嫉妒等等。这些是彼此相通的,而不同的部分在于特定的风俗传统和文化。”[3]诚然,中国风俗传统和文化的确是邝丽莎小说中的亮点,也是美国读者喜爱她的作品的重要因素。笔者最近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查阅了读者对邝丽莎作品《雪花与秘扇》的最新50个评价,除去仅仅表述对作者和其作品喜爱的13个评价,余下的37个评价中有33个明确表明他们通过该书了解到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但是,当具体谈及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时,他们无一例外地提及“小脚”“包办婚姻”“迷信”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陋习。
在《雪花和秘扇》中,作者用了二十余页,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以女主角百合的口吻详细讲述了缠足的痛苦过程。在《恋爱中的牡丹》中,虽没有关于缠足的独立章节,主人公牡丹却多次强调缠足是贵族女孩的一种特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然而,在西方人眼中,小脚却是一个神秘的、东方式的色欲文化的所在,如在《恋爱中的牡丹》中,牡丹就发现吴人在性爱过程中最喜欢“把谈则穿着丝质红色绣花鞋的小脚捧在手中,感受它们的精巧、芳香,体味她的痛苦带给他的愉悦”[4](P214);百合的丈夫对于小脚也有着相似的喜好,“我的双足让我的丈夫心驰神迷,即便是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最私密最亲热的时刻”[5](P30)。同样的,小脚也是裹足女性最为私密之处。然而在《上海女孩》和《乔伊的梦想》中,日本人对珍珠母亲的暴行和青龙村村民对 “坏分子”地主婆雍的批斗都始于解开其裹脚布将其变形的脚展示在众人面前,最终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她们的死亡。作者对小脚一再渲染,直至把小脚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顺应了读者对小脚的猎奇心理,迎合了西方对“野蛮”中国的想象。
中国的十二生肖是一个独特的民俗文化。在小说中,邝丽莎不断提及每个主要人物的属相,把属相置于一个神秘而又重要的位置。在百合家中,“爸爸总是容易担惊受怕——典型的属兔”[5](P14),属猴的母亲则机敏灵巧。当王媒婆到他们家时,“父亲说些客套话,声音几乎听不见”[5](P15),母亲则相当镇定,“她深黑的眼珠子里潜藏着缜密的心思……一种类同于男人般的野心,从她的皮肤里焕发出来了”。在珍珠看来,妹妹梅的性格和行为都源于属相。“属羊的人时髦,有艺术感”[6](P8),因此“每当导演的镜头想捕捉到一张天真无邪的面孔时,梅总能把乔伊安排在最合适的角度”[6](P183);“属羊的人往往只关心自己,只顾着自己的快乐”[6](P8),所以梅把女儿乔伊和丈夫弗恩丢给姐姐照顾,自己“在好莱坞,参加派对,寻欢作乐,和那些男人为所欲为”[6](P280)。从上述来看,邝丽莎显然没有准确理解中国的生肖文化,因而她只看到其中一些诡异而又晦涩的元素,然而这些元素恰恰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他者”中国的阅读期待,让他们从中获得了东方主义的快感。
众所周知,作家的创作无法脱离其成长的客观环境。在美国长大的邝丽莎也未能摆脱主流文化的东方主义话语对中国的固有想象,不可避免地戴着有色眼镜有选择性地、片面地展现中国文化。除小脚和生肖外,邝丽莎的小说中与西方的“野蛮”中国想象相符的还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以及拜奉鬼神和祖先的迷信思想等。对于以人本主义文明、基督教文明和法治文明为三大支柱的西方世界而言,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那种对女性身心的摧残、子女对父母的惟命是从和人们对鬼神的敬畏等,是如此的怪诞和匪夷所思,也正是其落后、愚昧和野蛮的具体体现。
二、“竹幕”之后的“红色中国”
“红色中国”是西方社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一种带有政治倾向性的称谓。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诸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客观上造成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隔绝,中国更是被西方蔑称为“竹幕”,意指封锁国境,使人民无法知晓国外消息,外人亦无从得其内情。“竹幕”的隔绝使中国愈加神秘,理所当然地被西方诸国视为敌人,继续被“妖魔化”了。在《乔伊的梦想》中,邝丽莎继续了这一“妖魔化”的进程,正如美国权威书评网站Bookpage所言:“作为一个完美的历史小说家,邝丽莎讲述了大跃进时代的中国社会之真实状况,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有趣而又令人恐怖的新世界。”[7](P27)
这个“有趣而又令人恐怖的新世界”在小说中具体体现在作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妖魔化描述。在邝丽莎的笔下,红色中国的最高领袖毛主席就是一个类似于成吉思汗的暴君,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乔伊与李志革见面之初,李志革正是由于毛主席对他的不满被迫离开上海前往安徽省青龙村进行自我改造。在评选全国艺术大赛最佳作品时,身为评委之一的李志革在评选画作时对乔伊说:“评选规则都是毛主席的意思。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他想让获奖的作品,不要让他丢面子。如果他丢面子了,许多人就要遭罪了。”[8](P164)乔伊曾听人说“毛主席一讲话就停不下来,不愿听到不同的意见”[8](P166)。在乔伊和李志革与毛主席会面时,乔伊亲证了传言。毛主席一个人滔滔不绝,还数次打断李志革的答话,直至工作人员提醒他该走了,他还意犹未尽,说“我们以后再聊”[8](P169)。
邝丽莎善于把小说中的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强调历史对人物命运的影响。由于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随后的大饥荒是对毛泽东时代攻击的主要目标,在《乔伊的梦想》中,邝丽莎把乔伊回到中国的时间设定为1957年,迫使其亲身经历了大跃进和随后的大饥荒。为全面展现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状况,邝丽莎还赋予乔伊特殊的社会身份——知名画家的女儿和农民的妻子。作为知名画家的女儿,乔伊有幸随父亲参加一些宴会,品尝了精美的中国菜——“猴脑、狮子头、燕窝羹、鱼翅、海参”——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他者”化的饮食习惯无疑强化了中国人怪异、野蛮的“他者”形象[8](P170)。作为农民的妻子,乔伊亲历了大跃进和随后的大饥荒。大跃进时期,大队干部莱为了提高小麦的产量,提出了密植的方法,在本应播18斤种子的一亩田中播了40到50斤种子。可想而知,夏收的季节村民们几乎颗粒无收,加上秋季的蝗灾,饥荒的年代到来了。在饥荒岁月,乔伊的公婆以及婆家弟妹们相继饿死,乔伊一家也奄奄一息。
的确,邝丽莎对中国历史的描述是基本准确的,但她对新中国欣欣向荣的一面视而不见,似乎只关注社会的阴暗面,如村民们在批斗地主遗孀时的疯狂与残忍、饥馑岁月人性的沦丧和高度政治化引发的非理性癫狂。在书中,邝丽莎还杜撰出一些荒诞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如在乔伊和珍珠进入中国时,边防警察没收了她们的胸罩,因为“胸罩是西方腐化生活的标志”[8](P67);归国的科学家必须签字认同“中国的月亮比西方的月亮大”[8](P89);李志革关于如何区分领导干部的级别的言论更是让人无法忍俊,“普通领导胸前的口袋上只装一支钢笔,装两支笔的领导级别更高一些,最重要的领导在口袋上装好几支笔”[8](P161-162)。显然,邝丽莎对中国的描写或许有其真实的一面,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疑印证了西方世界对红色中国的“妖魔化”想象: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公民没有民主、自由可言,人权得不到保障。
三、“他者”面纱下的中国人
东方相对于西方所具有的某种差异性和神秘性,使其长期被作为西方确立自我和验证自我的“他者”。同样地,东方人也被作为西方人认识自我的“他者”。美国的东方主义传承了欧洲的衣钵,将东方肢解后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趣味重新组合,完成了语言文化上的殖民过程。在此过程中,华人男性或被妖魔化,或被女性化;华人女性形象则充分体现了白人男性征服少数族裔的欲望和幻想,或为充满诱惑的妖女,或为等待救赎的天使——美丽纯洁但又无助。上述模式化的华人“他者”形象也同样出现在邝丽莎的作品中。
《恋爱中的牡丹》中的牡丹正是这样一个集天使和妖女于一身的“他者”。牡丹是一个典型的东方美女,有着“丝绸一般顺滑的黑发,柳叶一般细长的眼睛,牡丹花瓣一般淡粉色的双颊”[5](P4)。牡丹还是一个温顺的少女,从不在人前大声说话,也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想法,最终却因包办婚姻绝食而亡。美丽、温顺却又楚楚可怜的牡丹,似乎在等待白人骑士的救赎,无疑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东方女性的想象。牡丹死后成了孤魂野鬼,鬼魂所具有的超能力使牡丹不再无助,失去的爱情更是激发了她身上邪恶的一面。为取悦丈夫,她控制了他续娶的妻子谈则的意念和身体。她通过谈则的身体享受与丈夫的鱼水之欢,却丝毫不顾及谈则的意愿,“我随时随地地使用谈则的身体,毫无愧疚和痛惜之情”,“即使她很疲倦、很害怕、很害羞,我还是要强迫使用她的身体”[5](P214)。最终,谈则不堪折磨而亡。在《雪花和秘扇》中,小脚女子雪花和百合奉“父母之命”嫁给了不爱的丈夫,互相扶持走过了婚后艰难的岁月,然而雪花与百合之间类似于同性恋般缠绵真挚的情感,如用手指在彼此的裸体和隐私部位书写女书文字,却印证了西方读者心目中视华人为异己化的“他者”。
美国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国家,然而邝丽莎作品中的华人男性,几乎没有英雄,只有反英雄。牡丹的祖父就是这样一个自私、怯懦的人。在扬州大屠杀时,他要求妻子为保护自己和儿子做出牺牲,最后妻子被清军刺死,而他和儿子躲在妻子身下逃得一死。雪花的父亲“天性胆小怯懦”[4](P108),抽大烟败光了家产。家道中落的雪花嫁给了一个粗俗、市侩的屠夫,他支持妻子与百合的交往,仅仅是“因为每次雪花都会满载着食物、书籍和金钱而归”[4](P183)。珍珠和梅的父亲则是一个赌徒,赌输后把女儿卖给他人为妻,更让妻女心寒的是,他在战争爆发时独自逃亡,致使珍珠和母亲被日本人强暴。珍珠和梅爱上了同一个人——Z.G.,然而Z.G.却是一个毫无责任感且优柔寡断的人。当珍珠因不愿接受父亲包办的婚姻向他表白时,他却平静地说:“你应该嫁给这个男人,听上去你们很般配。你要对你父亲尽孝。”[6](P29)Z.G.与梅发生了性关系,却在面对爱情的抉择时选择了逃避。乔伊的丈夫冯涛则是个十足的投机主义者,他与乔伊结婚是希望通过她改变自己的命运。当阴谋未能得逞,他不仅对乔伊极为冷淡,也不关爱两个人的女儿。在大饥荒的年代,他甚至还打算与他人易子而食。显而易见,上文中或邪恶、或懦弱的华人男性无疑符合了美国主流文化对华人的思维定式。
四、结语
在众多美国华裔作家中,邝丽莎是为数不多的以中国和中国历史为写作背景的作家。在不同的访谈中,邝丽莎多次强调自己八分之一的华人血统和她在唐人街度过的童年岁月,还有她为创作多次前往中国的调研和大量文献资料的查阅,来印证其作品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的确,邝丽莎是一个勤勉的作家,她的每一部作品从构思到出版都历经数年。为确保其作品的“真实性”,邝丽莎在创作的过程中多次前往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甚至前往湖南拜访最后一个会女书的老人。但是她从未在中国长期生活和居住,仅凭在中国的一点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和相关史料的查阅而写出的中国题材小说,误读和隔膜是不可避免的。
德国当代哲学家、美学家伽达默尔曾说过:“所有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在阅读过程中才可能完成。”[9](P215)可见,读者才是文学活动的中心,读者的消费意向也就是作家的创作方向,作家自然而然地会从史料中发掘吸引读者的素材来加工成赢得市场的故事。在西方话语中,中国是野蛮、落后、愚昧的,是作为西方的对立面出现的。因此,中国异于西方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必然引起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兴趣,成为其丑化中国、殖民中国的客观依据。作为一名畅销书作家, 邝丽莎在创作时必然会考虑读者的阅读喜好,有选择地呈现中国,用大量的笔墨夸张地描述中国传统文化之糟粕、红色中国之神秘,再次印证了中国和中国文化依然是用于验证西方文明的“他者”。于是,处于美国强势语境中的作家个体,邝丽莎不由得为主流社会的东方主义话语牵引,讲述了一个又一个西方视阙下的中国故事,虽部分地呈现了历史,却百分百虚构了故事。所以,在中国历史中寻觅东方奇观的美国作家邝丽莎至多是一位对中国抱有善意的美国人,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在美国的代言人。
[1] 张羽. 美国篇:邝丽莎——续写华人记忆[EB/OL]. http://news.sina.com.cn/s/2011-02-10/144521933339.shtml,2011.
[2] 卢俊. 中国情结与女性故事——美国华裔作家邝丽莎访谈 [J]. 当代外国文学,2012(3).
[3] 郭珊.《雪花秘扇》掀动神秘“女书文化”热潮[EB/OL]. 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11-07/10/content_22958030_2.htm.
[4] Lisa See. Peony in Love[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07.
[5] 邝丽莎. 雪花与秘密的扇子[M]. 忻元洁,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6] 邝丽莎. 上海女孩[M]. 谢春波,译. 北京:京华出版社,2010.
[7] Praise for Dreams of Joy[Z]. Dreams of Joy[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8] Lisa See. Dreams of Joy[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9]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责任编辑:王菊芹)
TheImagesofChinainLisaSee’sHistoricalNovels
SUN Dong-miao
(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NorthChinaUniversityofWaterResourcesandElectricPower,Zhengzhou450046,China)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Lisa See regards herself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in America and states that China in her novels is real, even to Chinese. The paper queries her statement and points out the two images of China in her novels, that is, Uncivilized China and Red China. Besides, Chinese in her novels still turn out to be “the self”. Clearly, Lisa See’s novels, with China as its background, are not representative.
Lisa See; Uncivilized China; Red China; the Self
2014-07-03
201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生代美国华裔作家邝丽莎的作品研究》(2014-qn-412)阶段性成果
孙冬苗(1976—),女,河南尉氏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
I207
: A
: 1008—4444(2014)06—012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