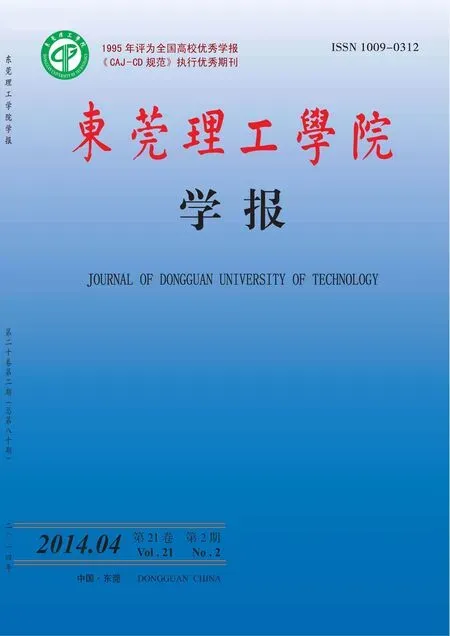司法确认之申请主体适格问题刍议
——以民事诉讼法(2012修订)第194条为切入点
2014-03-30李晓琼
李晓琼
(广东财经大学 法学院,广州 510320)
司法确认之申请主体适格问题刍议
——以民事诉讼法(2012修订)第194条为切入点
李晓琼
(广东财经大学 法学院,广州 510320)
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以基本法律的形式将非诉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纳入我国民事诉讼程序,赋予了当事人双方基于调解协议在规定时限内可向法院提起司法确认,以使其具有强制执行力。然而只能由当事人双方共同向法院提出申请这一规定的弊端明显:存在逻辑悖论、纠纷解决效率下降以及难以体现司法确认程序的优越性。为此,构建由一方当事人单独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程序是使我国司法确认制度得以有效运作的路径,而这一路径有赖于建立相应的异议制度、细化不予确认的范围以及构建司法确认纠错机制。
单独申请;纠错机制;司法确认;非诉调解协议
非诉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发端于甘肃省定西法院系统的实践,定型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2009年7月24日,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2011年1月1日施行,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中得到了部分的肯定和体现,并于《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2011年3月30日施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中有较为详细的规定,最后被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民诉法)规定为特别程序。本文拟以新民诉法第194条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非诉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申请主体的适格问题。
一、关于“双方共同申请”的评述
新民诉法第194条规定: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依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该规定明确了司法确认程序的启动必须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向主持调解的机构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亦即,任何单方当事人无权启动该程序。
(一)关于支持者观点的评析
针对“双方共同申请”的规定,支持者主要有如下观点[1-3]:第一,非诉程序的选择适用应当以自愿为基础,否则将侵害一方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他们认为一方当事人可启动司法确认程序意味着另一方当事人将要被迫使用司法确认程序确定双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因而势必会损害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第二,调解应以自觉履行为目标而非通过公权力进行强制,因此立法不应该鼓励将所有调解协议都确认而应当有所限制,司法确认的门槛宜高不宜低。第三,申请司法确认将给双方当事人带来可能遭受强制执行的不利益,故而只有双方合意忍受此种不利益才能启动司法确认。
对于第一种观点,非诉程序是否必然经由当事人双方合意选择适用?根据新民诉法第77条的规定,司法确认程序适用特别程序的规定,当然属于非诉程序范畴。然而“从所有的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的启动方面来看,当事人双方合意启动程序的规定尚不存在,即使是非讼程序也没有先例。”[4]换言之,非诉程序均由一方当事人提起并不曾被否认,并且学界对此也未曾质疑其必将损害对方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因此,将“非诉程序应当以自愿为基础”作为支撑“双方当事人共同提起”的论据无疑是站不住脚的。“尊重意思自治”所要求的应当是在合意达成之时是完全基于自愿以及在确认时对于合意真实性的审查以及构建相应的救济程序,它不可能也不应当要求当事人对司法程序选择必须以合意做出。正如当债权人启动督促程序时,我们不会认为其侵害了债务人的程序选择权一样,反之,债务人对支付令提出异议并提起确认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的确认之诉,我们也绝不会说其侵权。
对于第二种观点,我们认为降低司法确认门槛并不与鼓励“自觉履行”相悖。在实务中,调解协议做出之后无非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其一,双方当事人信守合约精神自觉履行调解协议;其二,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反悔不履行调解协议约定的义务。前者,当事人双方的履行完全基于“自愿”而无需依赖于司法确认所赋予的“强制执行力”,反之,只有在后一情况下,司法确认程序才能显现出其保障协议得以履行的功能。换言之,司法确认程序的意义在于规制和监督调解协议的履行,而不在于鼓励所有的调解协议均要通过司法确认程序方能履行。再者,降低司法确认的门槛也并不妨碍当事人双方的“自觉履行”。设想一下,若明知双方均能信守合约精神、自愿履行协议,当事人何苦要申请司法确认程序?退一步讲,哪怕该调解协议经过司法确认而具有强制执行力也并不会妨碍当事人对约定义务的自觉履行。可见,进入司法确认程序的门槛的高低与合同履行的自觉自愿不存在必然联系。
对于第三种观点,只有在经过双方当事人同意承受这种“可能的不利益”的情况下方能启动的论断,看似尊重双方当事人的处分权,实质上却对无故“反悔”而损害对方当事人的违约方提供了保护盾。我们必须明确调解协议对于双方当事人具有当然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类似于合同又强于合同。但是,与违约责任保障合同的依约履行所不同的是,对于民事调解协议,若非通过司法确认程序赋予强制执行力,实无任何法律责任规制“反悔”行为。如前所述,当事人遭受强制执行的不利益是缘于其未能诚实履行约定的义务,换言之,若其依约履行了义务,这种“不利益”产生的几率将为零。反之若其无故反悔,除非对其强制执行,对方当事人将会面临协议约定利益落空的不利益。前者的不利益产生于恶意违约行为,而后者的不利益产生于诚实信守合约的行为,二者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如果立法为了保护缘于恶意的不利益而将信守承诺的一方置于不利益的境地中,实有本末倒置之嫌。
(二)“双方共同申请”的弊端
不可否认,若双方当事人能达成合意,共同申请司法确认的确是两全其美,既体现了立法对于私权的尊重又保证了民事调解的实效性。然而,从实践角度上看,这种“两全其美”的构想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将启动主体局限于当事人双方使得司法确认制度进入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即若当事人双方均有意履行协议,申请司法确认则显得毫无必要;若一方或双方有反悔心理,申请确认的合意则没有达成的可能[5]。“当事人申请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主要理由无外乎有两种:该协议效力都不明确和防止以后反悔。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以相互信任为前提基础,如果丧失了这个基础,他们也难以达成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的一致意愿。”[6]换言之,实践中当事人对是否申请司法确认往往难以达成合意。从另一方面看调解达成的前提往往是以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作出让步为基础的,协议的一方或双方难免会有利益损失,在心理上加大了合意达成的难度。
第二,若将提起司法确认的主体范围局限于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不利于发挥非诉程序提高司法效率的作用。司法确认程序的目的在于保证调解协议履行以解决民事纠纷。根据第194条的规定,若当事人双方不共同向法院提出申请,则司法确认程序不能启动,因此,除非当事人双方自愿依协议履行,否则只能诉诸法庭。至此,前面所经过的调解程序将全无意义,法院的审查必须重新开始,不但无法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反而增加了司法成本,拖延了解决纠纷的时间。
第三,共同启动的司法确认程序无法体现出其相对于公证程序的优越性。[6]虽然我国《公证法》没有明确将民事调解协议纳入公证对象范畴,但是基于对民事调解协议的“合意属性”的考量,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民事调解协议并不是不可公证的,并且公证程序不受申请期限的限制,在实现诉调对接,保证协议的履行方面并不逊于司法确认程序。当然,有人可能会指出司法确认程序是免费的,而公证程序的费用通常比较高昂。但是,若仅有费用上的优势将不足以成为另设司法确认制度的理由。因为,费用问题可以通过完善公证制度得以解决,如减少对非诉调解协议进行公证的费用等。
二、单方申请司法确认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基于上文的分析,将申请司法确认的主体局限于“当事人双方”的规定使得司法确认程序实现诉调对接,保障民事调解协议履行的功能大打折扣。因此,笔者认为,启动司法确认的主体应当由双方当事人扩大到单独一方当事人,在立法上应当明确一方当事人可单独申请司法确认。
(一)必要性分析
从程序的实效性出发,司法确认程序的启动主体应当是一方当事人。“只有允许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都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程序,才能够极大地发挥司法对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监督,有利于诉讼和非诉讼机制的有力衔接。进而最大可能地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在解决纠纷,维护社会和谐方面的功能和作用。”[7]一方面,单独一方当事人可申请启动司法确认程序可以成功避开“双方申请”所产生的“逻辑上的悖论”。它既改变了“进入司法确认程序都有履行的合意基础,而有反悔意图的被不受约束”的现状,又降低了司法确认程序的门槛,为更多有可能不被履行的调解协议开启进入司法确认程序的大门。另一方面,“司法确认首先是为了解决民事合同性质的调解或和解协议效力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及为了解决人民法院‘诉讼爆炸’现象所创造的替代性功能补充机制,它既有助于实现非诉讼程序与诉讼程序无缝对接的社会需求,也有助于降低当事人权益维护的司法成本,提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和社会公信力。”[8]若要实现上述目标,则要求司法确认程序赋予更多效力不确定的调解协议(尤其是当事人有反悔可能的协议)强制执行力,确保协议的有效履行以解决纠纷。
从程序的特殊性出发,司法确认程序的启动主体也应当是一方当事人。只有允许一方当事人启动才能体现出司法确认程序在实现“诉调无缝对接”方面的优越性。如前文所述,若只允许当事人共同申请,司法确认程序无法体现出其相对于公证程序的优越性,甚至没有足够的论据作为该程序设立的必要性依据。反之,若允许当事人一方单独申请启动司法确认程序以求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司法确认程序将更多存有反悔可能的调解协议纳入其中以保障其被履行。而这些调解协议正是由于当事人的一方或双方缺乏履行的意愿往往无法达成合意申请公证的。因此,司法确认程序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可行性分析
我们应当肯定的是允许当事人一方单独申请启动司法确认程序并不损害“私法自治”。如上所述,“尊重意思自治”所要求的应当是当事人在合意达成之时是完全基于自愿的,法院在确认时对于合意真实性进行全面审查以及通过立法构建相应的救济程序,而不是要求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需要通过合意作出。再者,《人民调解法》第3条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调解民间纠纷。“此处的自愿含有两层意思:表层含义是自己行为,即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参与人民调解活动以及参与的内容和行为方式等;深层含义乃自己责任,即当事人要对自己参与人民调解活动所达成的结果承担责任。”[5]换言之,当事人双方在达成调解协议的同时已经对履行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达成合意。而对于申请司法确认程序可能带来的强制执行也早在调解协议达成之时已经被双方当事人所接受。因此,在调解协议达成之后,由一方当事人启动司法确认程序并无损于合意。
综上所述,将司法确认的适格主体规定为一方当事人而非双方当事人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因此,我们应当对民事诉讼法作进一步修改,在立法上明确一方当事人可单独申请司法确认,同时构建与之相配套的制度。
三、单方申请司法确认的制度构建
(一)明确一方当事人可单独申请司法确认
如上所述,“双方共同申请”的弊端显而易见,甚至导致司法确认制度的功能大打折扣;而无论从必要性还是可行性上看,单方申请司法确认有其合理性。因此,笔者建议针对新民诉法第194条规定可修改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依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有权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从而,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将一方当事人规定为申请司法确认程序的适格主体,在调解协议生效后可单独向人民法院提出司法确认申请。
(二)赋予对方当事人异议权
司法确认程序可由一方当事人单独申请。但是,由于司法确认的效力是使得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在将来的某一天可以被强制执行。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司法确认程序不可随意启动,而应当有所限制,但这种限制不应当是对申请的限制而应当是对受理的限制。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在立法明确单方申请司法确认的合法性之后,在第194条中增设第二款,赋予对方当事人相应的异议权。该异议期的规定无需太长,建议5日。若其在异议期内不提出书面异议则视为其默示同意申请启动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反之,若其行使异议权,则应当在异议书里提出异议的理由。异议成立的理由应当不同于法院不予确认的范围,因为异议权阻挡的是司法确认程序的受理而非确认裁定。笔者建议该理由包括:调解协议违背其自由意志和情势变更。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撤销申请;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异议,启动司法确认程序。
(三)细化司法确认程序不予确认的范围
除了在受理阶段赋予对方当事人异议权外,为了进一步防止一方当事人对司法确认程序的滥用有损协议双方的利益,还应当对民事诉讼法作进一步修改,细化司法确认程序不予确认的范围。《若干规定》的规定,不予确认的调解协议主要有:涉及身份关系的、不属于法院主管范围的、违反自愿原则的、调解协议内容违法的。虽然《若干规定》对司法确认不予确认的范围作了相关规定,但仍无法消除一方当事人滥用司法确认程序的可能。“根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则,违反公序良俗或专属于其他机关登记管辖的不能进行司法确认,这一原则值得借鉴。”[9]此外,不予确认的范围还应包括:(1)不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2)属于诉讼契约的内容(如人民调解协议中约定纠纷解决方式或者诉讼程序的选择等部分内容),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确认。由于上述两者均不具有给付性质,不属于可强制执行的范畴,因而应当排除在确认程序的范围之外。
(四)建立司法确认纠错机制
我国新民诉法将司法确认程序定位为特别程序,使得司法确认程序将实行一审终审,不允许当事人上诉,也不可能再审。然而,“在非讼事件程序中,法院是采用决定的行使做出裁判,而且在裁判后,法院如果发现存在不当,还可以作出撤销的变更”[10]。笔者认为在承认单方可申请司法确认之后,对于司法确认程序也应当给予法院纠错的权力。在标的物被强制执行之前,若法院发现其作出的确认裁定存在明显错误,法院有撤销其作出的确认裁定的权力。另外,一旦进入执行程序则应当允许被执行人通过执行异议对其权利进行救济;另一方面,当申请司法确认程序提出异议的当事人异议被驳回时,应当允许其对驳回裁定提起上诉。
上述制度的构建,一方面,通过明确一方当事人的主体适格地位能够有效地促使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效力得以确认,有效地遏制调解协议的反悔率,强化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督促当事人积极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从而提升司法确认制度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通过相关制度的构建也尊重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防止公权力强制当事人履行违背自由意志且无需承担之义务。
[1] 刘敏.论诉讼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J].江海学刊,2011(4):142-148.
[2] 范愉.诉讼与非诉讼程序衔接的若干问题: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切入点[J].法律适用,2011(9):30-34.
[3] 洪冬英.论调解协议效力的司法审查[J].法学家,2012(2):111-120.
[4] 唐力.非讼民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若干问题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38、39条[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3):105-111.
[5] 刘显鹏.合意为本: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之应然基调[J].法学评论,2013(2):128-134.
[6] 郭志远.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实施问题研究[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12(2):181-189.
[7] 张永进.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思考:以《人民调解法》为蓝本[J].法治论坛,2010(4):239-246.
[8] 姚小林.司法确认的诉调对接试验及其法治完善[J].法治研究,2010(8):98-101.
[9] 胡晓霞.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疑难问题研究:以人民调解协议变更、撤销及无效认定为视角[J].政治与法律,2013(3):148-154.
[10] 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M].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3-15.
The Qualification of Applicant of the Judicial Confirmation:Some Reflections on the 194th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2012 Revision)
Ll Xiao-qiong
(School of Law,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angzhou 510320,China)
The amendments to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in 2012 bring judicial confirmation system of non-litigation mediation agreement into our civil procedure.It warranted both parties can put forward the judicial confirmation to the court within the prescribed time limit,if both of them want to make the mediation agreement enforceable.However,there are obvious drawbacks to this provision,such as it brings a logical paradox,lower efficiency and it is difficult to reflect the superiority of the judicial confirmation process.The path whereby our judicial confirmation system can operate effectively is to permit a separate party to apply for judicial confirmation of the mediation agreement procedure.Furthermore,it is of great necessity to establish the objection system,to refine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judicial confirmation system and to construct error correction mechanism of judicial confirmation.
separate applicant;error correcting mechanism;judicial confirmation;non litigation mediation agreement
D915.2
A
1009-0312(2014)02-0033-05
2013-12-14
李晓琼(1989—),女,广东潮州人,硕士生,主要从事法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