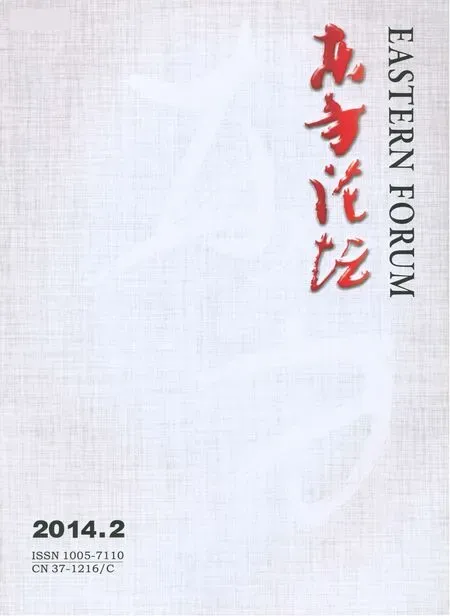张舜徽的雅学理论研究
2014-03-29窦秀艳何和平
窦秀艳 何和平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张舜徽的雅学理论研究
窦秀艳 何和平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张舜徽小学功底深厚,于《说文》学有皇皇巨著《说文解字约注》,而关于雅学、声韵的研究却分散于其经史子集四部著作之中。通过对其20余部著作的研读,可发现张舜徽对雅学理论的建树:关于撰写时代和撰人问题,他认为《尔雅》是汉初经师经生们对古代传注的总汇,并非出自周公之手;关于性质问题,他认为《尔雅》是“汇集群经传注中训诂名物分类纂录而成”的,是我国最早的类书;关于分篇问题,他认为《尔雅》中有《叙》篇,此《叙》篇在《汉志》20篇之中,是传《尔雅》学者所为;关于邵晋涵《尔雅正义》和郝懿行《尔雅义疏》的得失问题,他总体上是尊邵抑郝。此外,张舜徽还提出了今后雅学发展规划,指明了雅学的发展路径。
张舜徽; 《尔雅》学;理论研究
张舜徽(1911-1992)是我国上个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精于版本、目录、校勘、声韵、文字之学,经史子集四部兼治,一生笔耕不辍,有《清人文集别录》《郑学丛书》《中国文献学》《说文解字约注》等二十四部著作,计八百万字。张舜徽出身于书香世家,家富藏书,其父小岩先生“一生讲究朴学,不尚浮华”,是他的启蒙老师,重视培养他小学根基,自他幼年起,就传授他《尔雅》《说文》之学,常常教导他“读书以训诂为本,欲明训诂,此后可读段注《说文》、郝疏《尔雅》、王氏《经义述闻》三书”。[1](P71)按照小岩先生指引的路子,在打下了文字学功底后,就转攻雅学,自郝懿行《尔雅义疏》入手,参以邵晋涵《尔雅正义》。先生后来回忆说:“余早岁治《尔雅》,始读郝氏《义疏》,继观邵氏《正义》。”[2](P465)张舜徽十七岁时便读完了郝氏《尔雅义疏》,并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了《尔雅义疏跋》一文,该文初步运用《说文》对《尔雅郝疏》进行了一些考订。张舜徽研读《尔雅》,心得颇多,遗憾的是并未裒辑成册。他关于《尔雅》的诸多论述散见于其文集著述之中,涉及了《尔雅》的时代和撰人、《尔雅》的性质、《尔雅》的篇数、《尔雅》的功用等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解。其《说文解字约注》《清人笔记条辨》等著述,广泛征引《尔雅》,多有创见。张舜徽又广辑郑玄笺注,条分缕析,纂辑成《郑雅》一书,填补了郑学研究空白,亦雅学之功臣。张舜徽的雅学成就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对其有关雅学理论方面的论说作以简单评说。
一、关于《尔雅》性质的论说
对《尔雅》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历来看法不同。有的认为《尔雅》是解经之作,或主要是训释儒家经典的;有的认为《尔雅》是一部训诂书,即训诂专书(工具书、专著)或训诂汇编;有的认为《尔雅》是百科全书;有的认为《尔雅》是一部字典;有的认为《尔雅》 是一部词典(辞典);有的认为《尔雅》是一本教科书;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考察角度、方法、标准不同。也正是因为如此,许多人对《尔雅》性质的认识不是单一的。对此,张舜徽认为:
(一)《尔雅》是古代传注的总汇,是为经学服务的专书
过去有不少学者,认为《尔雅》是我国最早的字书。其实,这部书包罗极广,是古代传注的总汇,是汉初学者综合经师们说经的许多解释,排比类次而成。它是专为研究经学服务的,不能算是字书。[1](P34)
《尔雅》一书,虽列入《十三经》,其实乃汉初学者裒集经师传注而成,为训诂之渊薮。[3](P1103)
自传注既兴,而后有训诂之学。《尔雅》一书,乃汉初经生裒录众家传注而成。后人以其可取以解经,故附之群经之后耳。[4](P40)
这分明是汉初学者汇集群经传注中训诂名物分类纂录而成,所以内容绝大部分是解经的。[5](P36-37)
在这些论述里,张舜徽多次论及了《尔雅》的性质问题,他否定了《尔雅》是我国最早的字书之说,认为《尔雅》汇集了汉初经师、经生的解释,是古代传注的总汇,是为经学服务的专书,“故附群经之后”。张舜徽从《尔雅》的编纂目的、主要内容方面,对《尔雅》的性质做了客观的认定,与上个世纪一些语言学家的观点相比,更具有概括性、代表性。如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认为:“《尔雅》一书,为西汉以前古书训诂之总汇。”[6](P16)王力《中国语言学史》认为:“《尔雅》实际上是一种故训汇编。”[7](P11)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认为:“《尔雅》是一部训诂汇编”,“是我国古代训诂学的第一部专著。”[8](P73,P83)冯浩菲师明确提出,《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训诂工具书”。[9](P29)张舜徽此说实质就是《尔雅》是故训资料的汇编,是一部训诂专书。
(二)《尔雅》是我国最早的类书
类书之起,当溯源于《尔雅》。将训诂名物分十九类以统括之,悉取材于汉以上传注,实即最早类书也。[4](P228)
类书之起,昉于明分部类,据物标目,盖必推《尔雅》为最先。[10](P392)
首三篇专释故训,《释亲》以下十六篇,则详备六亲九族之礼,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远而天地山川,近而宫室器用,庶物毕载,人事悉显。总括万殊,而皆以类相从,因物为号,盖类书之始也。[11](P318)
中国历史上类书的出现,一般都认为始于魏文帝时的《皇览》,这是不确切的。如果从“考镜源流”的角度去谈问题,这种书籍的出现,自当溯源于《尔雅》。……这部书凡十九篇,有解说字义的,头三篇《释诂》 《释言》《释训》便是;有谈亲属关系的,《释亲》便是;有记房屋器用的,《释宫》 《释器》《释乐》 便是;有记自然现象的,《释天》 《释地》《释丘》 《释山》《释水》便是;有录生物品名的,《释草》 《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便是。这分明是汉初学者汇集群经传注中训诂名物分类纂录而成,所以内容绝大部分是解经的。分类登载,有条不紊,此非类书而何?谈到中国的类书,应该从《尔雅》算起。至于由最高统治者组织人力,编纂类书,以供自己阅览,那才是从魏文帝时的《皇览》开始的。[5](P36-37)
张舜徽在四部著述中从体例入手,层层深入地论证了《尔雅》是我国最早的类书,首先抓住了类书“明分部类,据物标目”的特点与《尔雅》“庶物毕载,人事悉显,总括万殊,而皆以类相从”“分类登载,有条不紊”的特点相符,明确地提出《尔雅》 是我国最早的类书的观点。在 《清人文集别录》中,张舜徽反驳了马国翰提出的最早的类书是“周《月令》”的观点。张舜徽认为“国翰此言,乃由乎不明古书体例而致谬戾耳”。[10](P392)张舜徽所论述的关键点是《尔雅》与类书的体例相通,都是“类聚群分”。张舜徽关于《尔雅》是我国最早的类书之说,也是我国关于类书起源的学说之一。此种提法有反对者,也有同志者,如刘叶秋在《类书简说》中认为“大约最后完成于汉代经学家之手”,“《尔雅》实开后代类书之先河”。[12](P8)
我们认为,类书是摘录、汇集古籍中的典章制度、诗赋文章、丽词骈语,或其它事物典故等资料原文,将其依类或按韵编排,以供寻检、征引的一种资料性工具书。《尔雅》虽然汇辑了先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诸多语料,并采取了分类编排的体式,但严格说来,它显然不具备类书这种工具书的特征,后世类书承袭了雅书类聚群分的方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与其把它当作第一部类书,倒不如视为类书的滥觞更适当。
二、关于《尔雅》成书时代及撰人的论说
(一)《尔雅》成书于汉初,是“汉初学者”裒集经师传注而成,“实不出于一手,不成于一时”
张舜徽认为:
《尔雅》……是汉初学者综合经师们说经的许多解释,排比类次而成。[1](P34)
《尔雅》一书,虽列入《十三经》,其实乃汉初学者裒集经师传注而成,为训诂之渊薮。[3](P1103)
《尔雅》一书,乃汉初经生裒录众家传注而成。[4](P40)
按《尔雅》一书,盖汉初经生所纂辑,所以疏通故训、辨识名物,以资说经者也。[11](P57)
按《尔雅》一书,盖汉初经生所纂。……实不出于一手,不成于一时。[11](P318)
关于《尔雅》的作者、成书时代,自汉至隋唐,学者大多数认为《尔雅》或周公作、或孔子及其门弟子传人作;至宋代,学者们才开始提出《尔雅》是秦汉间说《诗》者纂辑《诗》训诂而成。近代学者或认为“汉代经师解释《六经》训诂的汇集”①如罗常培说:“《尔雅》的著者,虽然有人伪托得很古,实际上它只是汉代经师解释《六经》训诂的汇集。”详见周祖谟《方言校笺》(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页。,或认为“大抵西汉经生,缀辑旧文,递相增益”②如胡朴安在《中国训诂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5页)中说:“《尔雅》不专为释《诗》而作,亦不专为释经而作。大抵西汉经生,缀辑旧文,递相增益。”,或认为“孔门后学、西汉经生笺释群书,好事者乃分类辑录之耳”③如蒋伯潜说:“《尔雅》……孔门后学、西汉经生笺释群书,好事者乃分类辑录之耳。”详见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重印本)第五编第八章。。与诸家相比,张舜徽所论更加明确、具体,把时间定在“汉初”,撰人为经师、经生,即儒家学者、传承人,也就是说《尔雅》“不出于一手,不成于一时”,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也是先生那个时代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此说既是张舜徽融会贯通众家之长,也是他多年躬耕实践,深邃思考所得。从时间上看,汉初百废待兴的帝国迫切需要这样一部搁置纷争、规范统一的教材,只有统一的王朝才有能力整合专家学者修订完善这样一部著作。于是,在汉代立国20余年之后的汉文帝时期《尔雅》就成为了学习教育课程。《尔雅》的出现不始于汉代,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最后完成于汉代。从编者看,不论是先秦还是汉初,儒家学者一直是社会学术的中坚力量,因此,《尔雅》在汉初短时间内修订完成,是由饱读诗书的经师、经生们根据专长、分工协作编定也是可能的。
(二)批驳了张揖《尔雅》周公作说
“《尔雅》周公作说”,是关于《尔雅》撰人问题的主要学说之一。最早见于三国魏人张揖的《上〈广雅〉表》,六朝颜之推、陈隋陆德明、宋陆佃、清邵晋涵、王念孙、钱大昕等均主此说,可见此说影响之深远。张舜徽反对此说,他对张揖提出“周公作说”的心理进行了剖析:
魏世张揖因《尔雅》旧例,博采汉儒笺注及《三苍》《说文》诸书以增广之,名曰《广雅》。深恐其书不为时人所重,乃推尊《尔雅》,谓为周公、孔子遗书,以明己之学所自出。此犹言《易》卦者,必托名于伏羲;言《本草》者,必托名于神农;言医经者,必托名于黄帝;言礼制者,必托名于周公;言六经者,必托名于孔子。莫不高远其所从来,以自取重于世。[4](P40)
此乃后人托古之陋习,不足信也。[2](P465)
而张揖目为周公之书,此与郑玄谓《孝经》为孔子所造,用意正同。盖郑玄注述旧典,揖埤广雅训,皆欲推尊本书以自重,故不得不高远其所从来耳。[11](P318-319)
张舜徽道出了张揖“《尔雅》周公作说”的真实目的,为了取重时人,高远其书之所从来,这是古人著书之通病。张舜徽此说实发前人所未发,从魏晋至清代,如陆德明、邵晋涵、王念孙等视“周公作说”为圭臬,即使反对者也未有什么高论,张先生此说确为的论,给我们的启示颇多。首先,张揖提出周公作说,是对东汉郑玄提出《尔雅》孔门所作说的反动。曹魏学界以王朗、王肃父子最为显赫,他们的著作被列入官学,成为世人学习的教材,而王肃是反郑玄的,对郑玄的学说一一反驳,甚至不惜用伪造经书的手段与郑玄一派对抗。张揖与王氏父子同殿称臣,提出《尔雅》周公作说可避免与王肃父子的摩擦。其次,也与张揖所处的曹魏时代政治学术环境密切相关。有汉以来特别重视礼法,至东汉,礼教对人心的束缚越来越严重,而礼教与忠君密不可分。曹氏三代为汉世朝臣,曹操加九锡、封魏王,终于没有代汉,不能说没受此因素影响,曹丕代汉是依据古礼禅让而成的。在统治者尊礼、崇礼的大背景下,张揖提出周公制礼、作《尔雅》一篇以释礼之说来迎合统治者,同时也为自己的广续《尔雅》之作《广雅》抬高身价也是可能的。此后主张周公作说者代不乏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各个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不排除对圣人崇拜的文化心理。
三、关于《尔雅》篇数的论说
(一)《尔雅》有《叙》篇
《汉书·艺文志》著录《尔雅》三卷二十篇,汉唐以来通行本均为三卷十九篇。对所逸的一篇究竟为何篇,说法不一。大致有三种:《尔雅》有《叙》篇,《释诂》分两篇,《尔雅》有《释礼》篇。
张舜徽赞同《尔雅》有《叙》篇之说,所依据的是孔颖达《毛诗·关雎正义》的材料以及古书著录通例,但张舜徽进一步提出了《尔雅》之《叙》篇,为传《尔雅》之学者所作之说,《汉志》著录《尔雅》二十篇中包括《叙》篇,同时否定了清翟灏《尔雅》有《释礼》 篇、孙志祖《释诂》分二篇之说。①翟灏《尔雅补郭》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85册第611页):“祭名与讲武、旌旗三章俱非天类,而系于《释天》,邢氏强为之说,义殊不了。愚谓:古《尔雅》当更有《释礼》一篇与《释乐》篇相随,此三篇乃《释礼》文之残缺失次者耳。《汉志》尔雅二十篇,今惟十九,所少或即此篇。”孙次舟《尔雅篇数考》(载华北日报《图书周刊》1936年1月13日第63期):“《汉志》作二十篇者,盖以《释诂》作二篇也。”他认为:
按《毛诗正义》开卷诠释“诂训传”三字,便引《尔雅·叙》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则《尔雅》本有《叙》篇,唐人犹及见之。顾《叙》篇之文,非出于撰集《尔雅》者之手,乃传其学者所为,斯固古书通例也。《诗》《书》之《序》,其前驱也。考今文《尚书》,伏生所授,初止二十八篇,而《史》《汉》俱称“伏生以二十九篇教于齐鲁之间”。其一篇,乃百篇之《序》也。《汉志》云:“《诗》,经二十八卷。齐、鲁、韩三家。”又云:“《毛诗》二十九卷。”毛视三家多一卷,乃《诗序》也。然则《汉志》著录《尔雅》二十篇,亦包括《叙》篇在内无疑。翟氏以为有《释礼》篇,孙氏以为《释诂》当分上下,皆臆测之辞,不足据也。②清汪士铎《悔翁笔记》(《清人笔记条辨》第262页)卷三“《汉志》尔雅二十篇”条下云:“今十九篇。翟晴江以为当有《释礼》篇,今《释乐》之祭名、讲武、旌旗,即其中残缺之文。孙志祖以为《释诂》当分上下篇。近人以《关雎》正义引《尔雅叙》篇为一篇。”[11](P262)
张舜徽之论与清陆尧春不谋而合,但要详于陆氏。③陆尧春《尔雅序篇说》:“《尔雅》之有序篇,犹《周易》之有序卦、《尚书》之百篇序、《诗》之大小序也。”详见《尔雅诂林叙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页。
我们也认为《尔雅》有《叙》篇,张舜徽的《汉志》《尔雅》二十篇包括《叙》篇之说对我们很有启发。班固《汉书·艺文志》承自刘歆《七略》,因此著录《尔雅》三卷二十篇应始于刘歆。刘歆是西汉后期著名学者,领校群书,整理篇次,又有《尔雅注》,惜其未传,《七略》所载必不误矣,则《叙》篇在《七略》时就已经存在。张舜徽提出《叙》篇“为传《尔雅》之学者所为”,并未确指某氏,然从其所类比《诗》《书》之序看,《尔雅》之叙不会太晚,他启发了我们思考的方向。由此我们推论,该《叙》篇,或为刘向、刘歆父子所作,或刘歆以前之犍为文学等治雅者所为,前者或更为可信。刘向每校一书,写就叙录,叙述学术源流,附原书上奏,此《叙》篇或即叙录之文,因其单行,后来淹没不传。至孔颖达撰《毛诗正义》,此叙录或残存,或是湮灭,孔氏或是转引他书,不得而知。且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并未提及此叙篇。其次, 《尔雅》 郭注、张揖 《广雅》、陆德明《尔雅音义》、唐开成石经等《释诂》均为一篇,《释诂》分上下二篇自邢昺作疏时始,而邢疏以后的明正德本、闽本、毛本、影宋蜀大字本等,《释诂》还保留一篇之旧式,所以“《释诂》 旧分两篇”之说有待商榷。再次,魏张揖著《广雅》,篇次一依《尔雅》,无《释礼》篇;且张揖认为周公作《尔雅》以释礼,则《尔雅》也必无《释礼》篇。[13](P24-27)
(二)叔孙通撰集《礼记》遗文增入《尔雅》
清臧庸在《拜经日记》卷二中,据张揖《上〈广雅〉表》有“叔孙通撰置《礼记》”一语,认为《大戴礼记》中有《尔雅》数篇,为叔孙氏所取入。④详见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第166页:“《公羊·宣十二年》注:‘礼,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疏云:‘《释水》文也。’考何邵公引《尔雅·释水》而称礼者,魏张揖《上广雅表》言《尔雅》秦叔孙通撰置《礼记》,此盖汉初之事。《大戴礼记》中,当有《尔雅》数篇为叔孙氏所取入。故班孟坚《白虎通》引《尔雅·释亲》文,称为《礼·亲属记》;应仲远《风俗通·声音篇》引《释乐》‘大者谓之产,其中谓之仲,小者谓之箹’为《礼·乐记》。则《礼记》中之有《尔雅》,信矣。或疑《汉·艺文志》礼家不及叔孙通,张氏之言,恐未得实,盖未考之班氏诸书也。”梁启超赞同臧氏之说,但也没有提出有利的证据。张舜徽则说:
所谓“撰置《礼记》”一语,谓撰集古《礼记》遗文置之《尔雅》中也。下文所云“或言叔孙通所补”,即指此耳。细审上下文意,至为明白。何、班、应三家之书所引用者,皆有关礼制之文。叔孙通虽已自《礼记》中取之以增入《尔雅》,然在汉世,盖犹有单篇别行之本,分题《乐记》 《亲属记》 诸目者。故引用时,仍标原书,而不云出自《尔雅》也。臧氏自信太过,漫加论断,误矣。其后陈寿祺又从而和之,载其说于《左海经辨》卷上、《大小戴礼记考》,亦失之疏略而未暇审思也。[11](P166)
张舜徽根据张揖《上〈广雅〉表》中 “或言叔孙通所补”之语及古书称引通例,认为是叔孙通取《礼记》之《乐记》《亲属记》之文增入《尔雅》,与臧氏之说正相反。由于《月记》《亲属记》在汉初单行,人们引用时仍标此两篇之名,而不表明引自《尔雅》,这是臧氏误解的根源。
四、关于郝懿行《尔雅义疏》与邵晋涵《尔雅正义》评说
邵晋涵《尔雅正义》与郝懿行《尔雅义疏》是清代两部最重要的《尔雅》研究著作,二者都是为疏通《尔雅》经注、笺补邢疏而作,所以学界往往把邵氏《正义》与郝氏《义疏》相提并论,但对二书的价值认识不一。多数人认为郝书优于邵书,也有人认为二书各有千秋,难分伯仲。张舜徽奠定小学基础时,就是先学习郝氏《义疏》,然后又专研了邵氏《正义》,对二书的得失有深入的认识。
张舜徽自十七岁便攻读郝氏《尔雅义疏》,并作了一些考订工作。后来,他向初学者推荐学习书目时,于“字义”类,首推《尔雅义疏》。[3](P1103)虽然如此,张舜徽还是认为郝氏《义疏》逊于邵氏《正义》,原因有三。首先,郝懿行“才仅中人,而志学稍晚,又无记诵之功,故虽汲汲终身,所造仍不能极乎高远。置之乾嘉诸儒之班,亦只能居中下之科耳”。[14](P276)其次,郝氏“对音韵之理不甚了了”“疏于音理,虽欲明诂训同、近、通、转之故,而其道莫由”。[14](P276)因此《尔雅义疏》无法达到完美的程度。张舜徽在《扬州学记·阮元》中说:“郝懿行是阮元在嘉庆四年总裁会试时所录取的门生,后来便根据阮元这些指示来作《尔雅义疏》。①阮元《与宋定之论尔雅书》:“窃谓注《尔雅》者,非若足下之深通乎声音文字之本原不能,何也?为其转注假借本有大经大纬之部居,而初、哉、首、基,其偶见之迹也。山、水、器、乐、草、木、虫、鱼诸篇,亦无不以声音为本,特后人不尽知耳。”详见《清代扬州学记》第144页。可惜郝氏对音韵之理不甚了了,所以《尔雅义疏》的写成,仍然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15](P301)这些认识皆是张舜徽躬耕实践、对郝《疏》的细致扒梳得来的。张舜徽曾把王念孙的《尔雅郝疏勘误》与《尔雅义疏》对校,“知懿行之所以扞格不通者,多在声而不在韵。自来治古音者,详于叠韵,而忽于双声。段玉裁、王念孙虽各自定古韵部目,然其阐明训诂,往往不言韵而言声。盖声音在文字之先,而韵部乃后世所定。如云训诂必通声音,则古声类之学,不可不讲。王氏《广雅疏证》,所以高出《尔雅义疏》者,正在此耳”。[10](P276)第三,张舜徽指出,郝懿行在撰述《尔雅义疏》时并未亲自从经籍中检引例证,而是间接征引《经籍纂诂》,有失严谨,从而降低了《尔雅义疏》的学术性。郝懿行《尔雅义疏》初名《尔雅略义》,比较简略。后阮元《经籍纂诂》成,便大肆采集《经籍纂诂》之文补充《义疏》,遂成二十卷言皇皇巨著。张舜徽认为:
其倚赖是书,可以想见。当王氏为《广雅疏证》时,《纂诂》之书,犹未编出。凡所征引,悉本原书,别择精研,语多心得。懿行之说以不逮高邮者,亦即坐此。两家之书可覆按也。……盖其始事,但欲以简略成书,其后有《经籍纂诂》供其采猎,遂不免失之繁冗。观是集卷二《再奉云台论尔雅书》,已谓购得《经籍纂诂》一书,绝无检书之劳,而有引书之乐云云。[10](P276)
张舜徽从郝氏才智、功底、治学方法等方面作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令人信服,也对我辈后学有谆谆教导之意。
张舜徽在研习《尔雅义疏》的同时,也攻读邵氏《尔雅正义》,他尤其服膺邵氏之学问,对邵氏《正义》偏爱有加:“清乾嘉时,邵晋涵撰《尔雅正义》,在郝《疏》前,其书甚精,可与郝《疏》并行。”[3](P1103)关于邵氏《正义》的成就,他认为,邵晋涵《尔雅正义》不但对清代雅学、训诂学的发展有开启之功,而且也开创了清代学者为群经作新疏的风气:“这是清代学者对群经作新疏的开始。从此以后,才有各种新的经疏陆续出现。邵晋涵在这方面,可算是开了一个头。”[14](P186)其次,张舜徽还认为邵氏《尔雅正义》义例谨严、博征约取:
晋涵经史之学,根柢深厚。余早岁读其所为《尔雅正义》,弥服其义例谨严,文章尔雅,穆然有唐人《正义》遗风,远非郝懿行所能逮。[10](P227)
他在博征之中,力求守约。自谓此书苦心不难博证,而难于别择之中能割所爱耳。乃外人竟有病其略者,斯事所以难言。邵氏在撰《尔雅正义》的过程中,能实行“博征约取”的原则,不尚繁征,力求简要,这却是他的绝大本领。全书精要,便即在此。……结合我早年学习《尔雅》的经验,先看郝氏《义疏》,后看邵氏《正义》,也感到邵书义例谨严,文章尔雅,在简约中确能说明问题,非郝疏所能及。[14](P186)
对于学界“邵不如郝”的观点,张舜徽不护其短。如梁启超说:“郝氏绝无新发明,其内容袭邵氏之旧十六七,实不应别撰一书。《义疏》之作,剿说掠美,百辞莫辨。我主张公道,不能不取邵弃郝。”[14](P186)张舜徽认为梁氏这一评断,是很公正的,并说:“就大体言,郝不如邵。”[4](P41)“邵书善矣,第草创之初,虑犹有罅漏;又其成书甚早,后出之义转多。”[2](P465)也就是说,邵书虽有草创之功,难免有罅漏;邵书成书早,后出转精,郝书自然有独到之处。
五、有关雅学理论拾零
(一)规划雅学今后发展
张舜徽对今后雅学的发展也作了规划,即编订丛书、丛编。
首先,要编订《九雅全书》。张舜徽年轻时就开始筹划雅体汇编,冠其室名“九雅”以明志,并说:
明人尝合刻《尔雅》《小尔雅》《释名》《博雅》(即《广雅》)、《埤雅》,为《五雅全书》,而不知取《方言》以代《埤雅》,此明人之陋也。……益之以陈奂《诗毛传义类》、朱骏声《说雅》合为七种。后于罗氏《玉简斋丛书》中见钱坫所纂《异语》十九篇,仍用《尔雅》体例。自称补《方言》所未及,自魏晋以下不著录。其用心之勤,可与群雅相辅而行,因撰疏证以表章之。迨晚岁写定《郑雅》既成,因并入上列诸种,合《九雅》,欲合刊《九雅全书》,以便学者。有此一编,则魏晋以上之训诂,悉在是矣。九雅者,《尔雅》《小尔雅》《广雅》《方言》《释名》《毛诗传义类》《说雅》《异语》《郑雅》也。若夫前人纂录魏晋以下训诂之书,如程先甲之《选雅》、俞樾之《韵雅》,则皆等诸自鄶可也。[4](P41)
这里所谓《九雅》,从纂集方式看都是“雅体”。后来,张舜徽也曾谈及修纂《九雅》的计划,在此计划中《集雅》代替了《异语》,并交代了《九雅》合刻的原因:
按《尔雅》一书,盖汉初经生所纂辑,所以疏通故训、辨识名物,以资说经者也。故其书与群经传注相表里,且有直引经句而为之诠释者。其后《小尔雅》《广雅》,亦同斯体。要其取材,皆采之传注。论其功用,轻重略等,固未容轩轾于其间。刘熙《释名》,原本郑学,依声训字,创通大例,实为训诂之学辟一新径。……余旧有志合《尔雅》《小尔雅》《广雅》《方言》《释名》、陈氏《毛传义类》、①张舜徽《郑学丛著·郑雅自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余年十九治毛郑《诗》。读陈氏《毛诗传疏》,病其胶固。而独喜其所为《毛传义类》,檃栝有条例,与《尔雅》相表里。”朱氏《说雅》 及余所纂《郑雅》《集雅》(集汉人何休、高诱、赵岐注家注义)汇刊为《九雅》。早岁尝以九雅名其堂,斯于必偿斯愿。怀此有年,未克有济。果能成此汇编,非特视《五雅》为闳博,即考核名物训诂,不俟旁求矣。[11](P57)
其次,编纂《翼雅丛编》。关于编纂目的,据张舜徽在《爱晚庐随笔》“翼雅丛编”中称:“自来治雅学者,每苦古代名物器服制度难明。余谓清儒好为专篇以类释之,实多精湛之作,足以羽翼雅学,为用甚弘。尝记其作者、篇名及见于何书,思合刊为《翼雅丛编》而竟未成。今录其目如次。”[4](P47)张舜徽一共列举了四十八篇,这四十八篇“倘能汇刊行世,信有助于究绎雅学”。张舜徽规划的《九雅全书》《翼雅丛编》虽然未实现,但这种宏大的设想却与21世纪的古籍整理发展方向吻合,相信这两部丛书定有出版之日。上个世纪末由湖北大学编纂的《尔雅诂林》问世,共有六册,一千多万字,“汇百家众注于一体”,庶几可以告慰先生。
(二)提出今后治雅途径
张舜徽认为《尔雅》是纂辑传注而成,基于此,他提出了治雅的基本途径——博通传注:“《尔雅》既由纂辑传注而成,推之《小尔雅》《广雅》,皆同此例。故治雅学者,必博通传注。传注明而后《尔雅》明,《尔雅》明而后训诂之学始可得而理。传注者,训诂之渊薮也。如欲为训诂之学,必沈研而精熟之。”[4](P40-41)
《尔雅》收词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主,尤其与《诗》《书》经传的关系最为密切。张舜徽称:“按群经各自为体,则所以通之之术亦各不同。惟有古文《尚书》,应读《尔雅》,解古今语而可知,故治《书》必本《雅》训。”[11](P30)同样,治《诗》、治《礼》没有《尔雅》,亦扞格不通。如何博通传注,先生已经为我们开辟了道路,提供了资粮。郑玄是汉末经学大师,遍注群经,对儒家文化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张舜徽少年时期就矢志整理郑玄注文,成《郑笺义类》《三礼郑注义类》《郑氏佚注义类》,思合此数种,纂为《郑雅》十九篇,后四十年不遑纂集,晚而“发愿重理旧业,以竟前功”,[15](P125)先生摘录郑氏注文,按《尔雅》十九篇之序成《郑雅》一书,“此编训诂名物之繁赜,倍蓰于《毛传》《尔雅》《说文》。苟能贯通郑学,则群经莫不迎刃而解。斯一编也,不第六艺之钤键,抑亦考古之渊薮矣。”[15](P126)
《尔雅》解释词汇意义,《说文》分析字形、探讨文字本义,《广韵》明语音,三者是传统小学三大基石,精通三者,方能解决诸经中的疑难问题。因此,张舜徽称:“按字学不外形、声、义三者。据形系联者,《说文》也;据声系联者,《广韵》也;据义系联者,《尔雅》也。故三书为治字学之纲领。”[11](P297)
(三)阐明《尔雅》与史志关系
最早把《尔雅》与史书之志联系在一起的,是南宋史学家郑樵。他在《通志总序》中说:
志之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余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16]
通过志、表的难写以及一些志书“详于浮言,略于事实”的弊端,郑樵抛砖引玉,为其《通志·二十略》作铺垫。《通志·二十略》最大的特点是类例分明和知识广博,其分类思想追摹《尔雅》。如郑樵在其《尔雅注序》中盛赞《尔雅》经纬六经的功能说:“大道失而后有六经,六经失而后有《尔雅》,《尔雅》失而后有笺注。《尔雅》与笺注俱奔走六经者也,但《尔雅》 逸,笺注劳。《尔雅》者,约六经而归《尔雅》,故逸。笺注者,散《尔雅》以投六经,故劳。”郑樵认为,《尔雅》体例“约六经而归”,类例分明,纲举目张,故逸;他的《二十略》的划分正是受《尔雅》“约而归”思想的影响,总“百代之宪章”,统括世间万物。《二十略》“总天下之大学术”,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学科的知识,其中的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都是郑樵独创,可说与《尔雅》十九篇同样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郑樵认为,《二十略》于史书亦属于志体,而追溯志体的形成,盖“志之大原,起于《尔雅》”。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则以为:
郑氏《通志》乃云志之大源出于《尔雅》,其说非也。然郑氏之说,亦不无所见。盖训诂名物,传注支流。史家之道,实通乎经。列传可拟左氏之经纬,则诸志自可比乎《尔雅》之类释矣。然如郑氏之指,必欲举六书、七音、昆虫、草木之属,侪乎礼、乐、刑、政之间,自属一家之言,不可为史家一定之法。刘知几欲增方言、方物二志,则转似有得《尔雅》之义者。[17](P11,P115)
章氏认为郑氏把志体起源归于《尔雅》是不对的,但史书与经书密切相关,从来源上把诸志与《尔雅》相比未尝不可。章氏又认为刘知几所欲增方言、方物二志“转似有得《尔雅》之义”,还是侧重其与《尔雅》内容相关而言。
与章学诚的异议相比,张舜徽对郑樵“志之大原出《尔雅》”之说是认同的,在《清人笔记条辨·乙卯札记》中不但赞同郑樵之说,并把志书各篇与《尔雅》十九篇对号,他说:
按《尔雅》有《释天》,即后世《天文志》之权舆;有《释水》,即《河渠书》之权舆;有《释宫》《释器》《释乐》,即《礼乐志》之权舆。夹漈谓志之大源出于《尔雅》,其说是也。《尔雅》又有《释诂》《释言》《释训》以明文字声音之理;又释艸木、鸟兽、虫鱼,以广天地万物之名。其所包罗至博,故夹漈亦沿其例而欲举六书、七音、昆虫、草木之属悉纳诸通史之中。盖文字有古今之异,语言有方音之变,昆虫、草木亦随地域而有不同,则史家悉加甄录,以与礼乐刑政并列于书、志之中,亦何不可。刘知几欲增方言、方物二志,即此意也。惟兹事体大,非有高识如夹漈者,固未敢创斯义例耳。观夫《二十略》之为书,可以知其规制弘阔为不可及也。[11](P115)
张舜微认为,郑樵发凡起例,以《尔雅》为规模法度,创制《二十略》,在编纂体例、内容涵盖、事类划分上均突破以往史书志体框架,“规制弘阔”,“包罗至博”,这样高识之大家古今一人而已。
关于张舜徽先生的雅学成就本文只涉及了冰山一角,比如《说文解字约注》征引《尔雅》上千例,《清人笔记条辩》《异语考证》中也广引《尔雅》,还有很多征引散见于其他著述之中,把这些雅学材料辑佚出来,按《尔雅》二十篇之序排比,将是一部分量颇重的《尔雅》疏证著作,其成就当不下于《说文约注》;诸如,《尔雅释亲答问》《郑雅》《小尔雅补释》《释疾》等皆可以专题研究;另外,张舜徽先生关于雅学与经学、文字学、声韵学之比较研究有待深入。总之,本文对张舜徽先生的雅学理论研究还是比较粗浅的,有些解读与先生本旨或有距离,我们只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抛砖引玉,促进学人对其雅学成就的深入研究。同时,对张舜徽先生这样的大家的雅学成就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也是当代雅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
[1] 张舜徽.讱庵学术讲论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 张舜徽.霜红轩杂著[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 张舜徽.旧学辑存[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 [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 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7]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8] 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9] 冯浩菲.中国训诂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10]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1] 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2] 刘叶秋.类书简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3] 窦秀艳.中国雅学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4.
[14] 张舜徽.清儒学记[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5] 张舜徽.郑学丛著[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6] 郑樵.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邓实编.风雨楼丛书[M].清宣统三年(1911)神州国光社铅印本.
责任编辑:潘文竹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Erya by Zhang Shunhui
DOU Xiu-yan HE He-ping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Zhang Shunhui's studies on Erya and rhymes are seen in four of his books. As for the compiler and his era, he maintained that Erya was compiled by teachers and disciples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not by the Duke of Zhou. As its nature, he held that it was the earliest book compiled according to categories of things in China. He also discussed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wo books respectively written by Shao Jinhan and Hao Yixing, commending the former and depreciating the latter. Besides, he also pointed out the roadmap of future studies on Erya.
Zhang Shunhui; studies on Erya; theoretic study
G256
A
1005-7110(2014)02-0074-08
2013-07-31
窦秀艳(1968-),女,吉林白城人,蒙古族,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献整理、汉语史研究;何和平(1989-),男,江西宜春人,青岛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