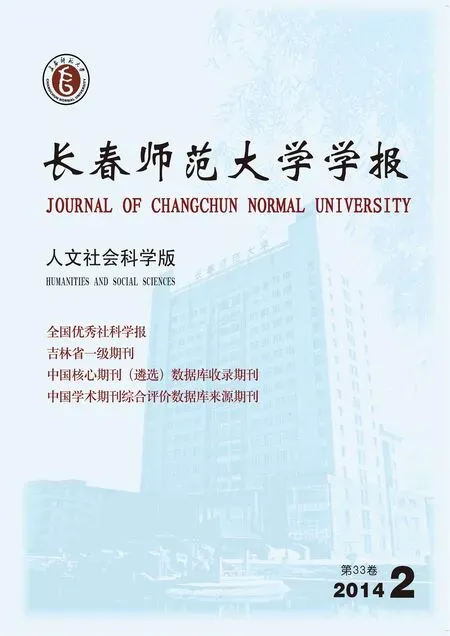《呼啸山庄》杨苡译本的修辞解析
2014-03-29陈丹霞
陈丹霞
(闽江学院 外语系,福建 福州 350108)
《呼啸山庄》杨苡译本的修辞解析
陈丹霞
(闽江学院 外语系,福建 福州 350108)
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呼啸山庄》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国内有众多的翻译版本。本文通过肯尼思·伯克的修辞理论中的“象征手段”、“认同”、“辞屏”等来重新解读《呼啸山庄》的杨苡译本,以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理解杨苡之翻译行为、目的以及效果的角度。
《呼啸山庄》;翻译;象征手段;认同;辞屏
英国十九世纪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的作品《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奠定了她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此书叙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和复仇的故事:希刺克厉夫在收养他的家庭里遭受了嘲弄和辱骂,经历了与庄园小姐凯瑟琳·恩萧爱情的失落和毁灭,长大后采取了一系列疯狂的报复行为:害死了心爱的凯瑟琳,虐待成为他妻子的伊莎贝拉·林惇,夺取凯瑟琳哥哥辛德雷·恩萧的财产,折磨辛德雷的儿子哈里顿·恩萧,甚至强迫埃德加·林惇的女儿凯蒂嫁给他病殃殃的儿子,最终自己也在孤寂和狂乱中死去。而哈里顿·恩萧和凯蒂,终是化恨为爱,开始了他们的甜蜜生活。
《呼啸山庄》出版不久后曾遭到许多谴责和非议,时至今日某些主题仍存在着论争。但无需置疑的是,艾米莉·勃朗特和她的《呼啸山庄》持续吸引着广大读者和学者的关注。国外对于艾米莉和《呼啸山庄》的研究长盛不衰。西蒙·马斯登(Simon Marsden)将艾米莉置于十九世纪神学历史的框架内,指出《呼啸山庄》的叙事包涵了圣经阐释学[1]。丹尼斯·布卢姆菲尔德(Dennis Bloomfield)则分析了艾米莉如何通过疾病、伤害和死亡的隐喻引导和推动情节的发展从而使其读者了解其中的人物性格特征[2]。自文本引进中国后,《呼啸山庄》在国内已有多种译本,梁实秋、杨苡、方平、宋兆霖等都以或偏重直译或偏重意译的方式翻译过该书。同时,众多的学者采用哲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伦理、社会学、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作者、文本、读者进行了深度解读,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如张福勇、李小敬通过解析《呼啸山庄》的情节、结构,对蕴含的时间哲学进行了探讨[3]。也有一些学者从译文、译者的角度着手进行研究,例如刘佳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及女性话语在译本里的应用和体现进行了分析[4];范立彬、王海云对几种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人称照应衔接手段[5];蔡明灯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分析译者对原文的操纵和改写[6]。但即使存在涉及修辞方面的解析,也多是停留在辞格或者风格的层面,缺乏从修辞的角度加以全面深化的阐述。本文希冀借助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解释力的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的修辞理论来解析杨苡及其翻译的《呼啸山庄》文本,以期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理解杨苡翻译行为、目的以及效果的角度。
一、象征手段与认同
肯尼思·伯克在论述修辞的特征时,阐明修辞是“植根于语言本身的一个基要功能中”,“是作为一种诱发天生对象征敏感的人类互相合作的象征手段的语言运用”[7]43。在同一书中,他明确指出,“只有当我们能够讲另外一个人的话,在言辞、姿势、声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做到和他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同于这个人的言谈方式时,我们才能说得动他。”[8]也可以这么说,劝说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受众对说者的认同。这对翻译活动也是同样适用的。译本只有取得受众的认同,才可以影响受众,达到翻译的效果。
Wuthering Heights的译介进入中国可以溯源至20世纪的30年代。早期的版本包括1930年上海华通书局发行的伍光建译本《狭路冤家》,194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梁实秋译本《咆哮山庄》,1949年上海正风书局发行的罗塞译本《魂归离恨天》以及1956年上海平明出版社发行的杨苡译本《呼啸山庄》。
杨苡的《呼啸山庄》汉译本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决定了外国文学翻译偏向于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而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覃志峰谈到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中国读者对《呼啸山庄》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认同人物的个性解放思想和爱情追求,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另一方面,受左倾政治的感染,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个人主义的代表,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担心青少年读者受其不良影响”[9]54。针对当时社会的受众需求,考虑到《呼啸山庄》的成书年代(约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杨苡选择了较为中规中矩的翻译方式,没有古文的艰深晦涩,没有今文的随意随性。语词、句式、结构等各种象征手段的选用,都尽可能地向原文传达的意境靠拢,显示译者的抉择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原著风格。例如,对于原文第十章中这样的描写“for very soon after you pass the chapel, ……the sough that runs from the marshes joins a beck which follows the bend of the glen”,杨苡译为“因为你过了教堂不久,……从旷野里吹来的飒飒微风,正吹动着一条弯弯曲曲顺着狭谷流去的小溪”[10]89,无论是句式,还是选词,都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原文风格。另外,译文中对一些西方的寓言或者宗教方面的人物或术语作了注释,方便受众理解。例如,杨苡对“His saints”当中的His特地作出为何将其大写的注解如下,“祂—He,指‘神’而言。对上帝(神)表示尊敬,故将第一个字母大写。在中国,教徒言及上帝往往写‘祂’”[10]22。她不只是将“Paul”、“Peter”等人名简单地译为“保罗”、“彼得”,而是译出之后,加上注释,指出他们都是“耶稣的使徒”[10]99。在翻译“a dog in the manger”时亦注明此“引自《伊索寓言》,指已不能享用而又不肯与人的鄙夫,即心术不正者”[10]97。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样的译法满足了受众对英美文学以及英美文化的微妙心理,容易取得受众的认同,容易被读者接受。不过较为遗憾的是,尽管如此,《呼啸山庄》的这个译本还是没能安然渡过后来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
二、辞屏与动机
伯克用“辞屏”(terministic screen)来解释人类运用的象征手段。伯克提出每一个词汇或者术语即使被人们认为是“现实的反射”(a reflection of reality),但由于词汇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定是“现实的选择”(a selection of reality),因此某种程度上它是“现实的折射”(a deflection of reality)[11]45。正因为有这样的功能特点,“才使得目的和动机能够在象征行动中得到体现和实现”[12]339。在译者的翻译活动中,有两个方面最能体现这样的特点。一是在译者阅读原文,揣摩原文语义时,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正是受到源语词汇的辞屏作用;二是在译者翻译原文,选择译入语词时,面临源语对应的译入语存在多种译法,译者的抉择背后则是他们翻译活动的修辞动机和预期目的。
杨苡的译本也处处映照着“辞屏”的作用。如何在译文中展现情仇的演绎,如何在译文中体现爱恨的交织?比如,她的译本中使用了正式的词汇“哀恸”、“毒辣”而非“悲痛”、“坏心眼儿”来分别翻译“lamentation”和“malevolence”,用“仆人”而非“小厮”来翻译“lad”。再如第九章中辛德雷的一句话“……Damn it! I don’t want to be troubled with more sickness here. What took you into the rain?”[13]79杨苡译为:“……倒霉!我可不愿这儿再有人生病添麻烦,你干吗到雨里去呢?[10]83”杨苡将“damn it”译为“倒霉”而非“他妈的”这样的国骂,每一次的选择都隐含着杨苡作为译者的“选择”和“折射”的修辞动机,最后必然造成受众阅读该译本时所产生的心理印象与阅读该书其它译本的差异,影响着受众对艾米莉和《呼啸山庄》的看法和态度。通过这样的“辞屏”分析,可以说,杨苡的译本有效地秉承了艾米莉《呼啸山庄》原文的修辞场,注意到“原文和源语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并没有“按照译入语的兴趣和需要”随意地拆分译出语文化“模块”,避免了“对源语文化及其成员集体作出具有误导性的表述”[14]16。
三、结语
正如刘亚猛在总结当代哲辩思想家对“言”和“力”之间“难解难分的关系”时所作出的论述,“虽然词语本身并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和能力,但是它们一旦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中得到应用,产生实际效用,也就是说,一旦从语言层面上升到修辞层面,就成为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12]29。现在,全球化的大潮中,翻译必然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沟通手段,不断在具体的形势和语境中得到使用。吴文安、朱刚针对全球化趋势下“处在弱势文化中的中国译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阐明译者“应该具备明确的民主政治意识,对翻译过程进行自我控制,既要以吸收和借鉴外国语言和文化为己任,又要保护民族语言和文化,维护民族身份”[15]。这时,翻译过程中译者以受众为中心、加强修辞思考、关注译文话语的潜在修辞效果、修辞地选择话语的必要性越发彰显[16]。当然,翻译活动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杨苡的译本也并非尽善尽美。
[1]Marsden, Simon.‘Vain are the Thousand Creeds’: Wuthering Heights, the Bible and Liberal Protestantism[J]. Literature and Theology,2006(3):236-250.
[2]Bloomfield, Dennis.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Sickness and Death in Wuthering Heights[J]. Bronte Studies,2011(3):289-298.
[3]张福勇,李小敬.浅析《呼啸山庄》的时间哲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6):40-42.
[4]刘佳.女性话语在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中的应用—从女性主义翻译角度[D].济南:山东大学,2010.
[5]范立彬,王海云.《呼啸山庄》及其三个中译本人称照应衔接手段对比研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7(6):36-38.
[6]蔡明灯. 从《呼啸山庄》的两个译本看译者主体性对原文的改写[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0(6):368-369.
[7]Burke, Kenneth. A Rhetoric of Motive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
[8]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京:三联书店,2004.
[9]覃志峰.论《呼啸山庄》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和被接受[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12(4):52-55.
[10]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M].杨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11]Burke, Kenneth. 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12]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13]Bronte, Emily. Wuthering Height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
[14]刘亚猛.从“忠实于源文本”到“对源语文化负责”:也谈翻译规范的重构[J].中国翻译,2006(6):11-16.
[15]吴文安,朱刚.翻译策略的语境和方向[J].外国文学评论,2006(2):90-99.
[16]陈小慰.论译文话语的修辞力量[J].中国外语,2011(3):95-98.
The Rhetorical Analysis on Yang Yi’s Translation ofWutheringHeights
CHEN Dan-xia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of Minjiang University,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a)
Emily Bronte’sWutheringHeights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re have been many translation versions in China. The paper hopes to offe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Yang Yi’s translation action, purpose and effect by reinterpreting Yang Yi’s translation in the rhetorical framework proposed by Kenneth Burke with some key concepts such as symbolic means, identification and terministic screen.
WutheringHeights; translation; symbolic means; identification; terministic screen
2013-12-04
陈丹霞(1981- ),女,福建福州人,闽江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从事修辞学、英美文学研究。
H315.9
A
2095-7602(2014)02-007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