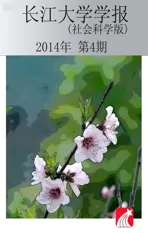《牡丹亭》梦境意义探微
2014-03-26章芳
章芳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因一曲《牡丹亭》而扬名天下。剧中的杜丽娘感梦伤怀,竟至香消玉殒。而更让人惊异的是亡故三年后的她居然因为梦中情人的召唤而起死回生,从而演绎了“生生死死为情多”的旷世爱情传奇。如此怪诞的情节皆因情生,全由梦起,难怪汤显祖不无得意,“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可见《牡丹亭》的梦境描写确有可探之处,它不仅使全剧呈现出真幻交织的艺术意境,更是作者表达其思想主张及人性观念的委婉策略。
一、欲求宣泄之依托
《牡丹亭》创作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这是一个重个体、崇自我、主体意识高涨的特殊时期。在思想领域,程朱理学虽然一统天下,但王学左派的出现已经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李贽、颜山农、罗汝芳等心学家高倡人情物欲,标榜自然人性,为提高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和哲学支撑。汤显祖虽然不是心学家,但他深受心学人物的影响,对他们的思想颇为认同,并以具体的艺术实践来推崇他们的学术观念和思想主张。
被汤显祖称之为“吾所敬爱之学西方之道者也”的达观禅师在《皮孟鹿门子回答》中指出:“情之有者理必无,理之有者情必无”,强调的是“情”与“理”的对立。汤显祖则进一步阐释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段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生。谛视久之,并理亦无,世界身器,且奈之何。”在汤显祖看来,无情则无理,“如果忽视情感欲求,道德的存在也就缺乏意义。压制人类自然的情感欲求,必然导致伦理道德的崩溃坍塌。要维持秩序纲常的正常运转,就必须顺应人之合理欲求。”而不能视其为洪水猛兽。所以在《牡丹亭》中,汤显祖就让春情萌动的杜丽娘在梦中尽情地释放源于她内心最原始、最自然、最真实的本能,让她在与柳梦梅的云雨欢幸中大胆宣泄着怀春少女汹涌不息、奔流不止的自然情欲。而《牡丹亭题记》中“梦中之情,何必非真”的辩护则向世人宣告了杜丽娘自然情欲的纯粹真实与合情合理。这个美丽的春梦就是杜丽娘的求情示爱之梦,实际上就是性梦。它是杜丽娘自身情欲的直接显现,更是她情欲焦灼、压抑的大胆宣泄。尽管现实中的杜丽娘悲叹自己青春虚度,个人才貌被埋没,但境遇悲惨,苦闷彷徨的她,既没有青梅竹马的爱侣,也没有一见钟情的际遇,甚至连一诉衷肠的对象也没有,她只能将自己的爱寄寓梦中。杜丽娘找不到释放饥渴,排除煎熬的可能,梦就成了她敞开胸怀的最佳场所,于是她做起了白日梦。只因为情难己抑,欲难自制。
梦是人的潜意识的表达,是人的愿望的达成。杜丽娘在梦中与柳梦梅“共成云雨”,实际上是她生理本能被现实伦常礼法所钳制的集中爆发。所谓“梦由心生,情自性起”,梦中之人,梦中之事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不会遇见,不会发生,但其中寄寓的情感却是真实可信的。
二、个性解放之途径
如果说《牡丹亭》只是表现了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那么它是难以“几令《西厢》减价”的。作者把杜、柳之间的爱情当作个性解放运动的一个缩影来展示,把反封建的主题和要求个性解放的旨意结合到一起,使作品上升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同时也大大超越了以往剧作把爱情描写仅仅停留在反对父母之命,批判封建礼教的狭隘层面上,显示出在新的时代思潮中的进步光华。《牡丹亭》既是一部自由之爱的恋曲,也是一首鼓吹青春觉醒的颂歌。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杜丽娘处境艰难,禁锢重重,她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展示自己的青春。尽管她惋惜“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尽管她哀怨“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可冰冷、残酷、狭窄、死寂的生存环境不容许她越雷池半步。然而游园之后的她由思春而感梦,由感梦而生情,终于在梦境中幽会了意中人,“现实中解决不了的困惑、幽怨和涌动着的春情,只能在梦中靠五彩的如意世界来体贴关怀。如是则有可人意的俊书生手持柳枝来拨云化雨,又有花神来保护现场,待其情得意满后,则以一片落花惊醒香魂,将美妙幽香的仪式感渲染到极致。”尽管剧作对二人欢会时“千般爱惜,万种温存”作了极力渲染,充分肯定了作为人的本性的男女之情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但作品并没有止步于情爱故事,而是借男女之情来演绎和阐释青春之美、人性之真,从而表达了青年男女对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向往与追慕。
三、情理调和之手段
汤显祖认为只有既宣扬了社会道德规范,又展示了个体自我需求的戏剧才是最有效的案头之曲与场上之作,才能真正发挥“至情”之用。汤显祖一方面希望人的心性情志可以自由流露随意而为,一方面又指望它们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可,并且还能有助于伦常教化的传达。然而在当时的现实中情与理水火不容,作者的理想遭遇了残酷现实的抵制,于是在《牡丹亭》中汤显祖就巧妙地借助梦境来实现情与理的调和与折中。或者说梦境描写成为了汤显祖兼顾社会道德规范和个体自我欲求的策略。对于杜丽娘心中蕴含的“情”与“理”的对立、冲突,《牡丹亭》没有在现实人世中予以展现,而是把它放置于一个超越人世的幻境中进行凸显,作者借助这个异于世俗社会的情境来展现杜丽娘追求理想的全部至情力量。也正因为杜丽娘的这种至情没有在现实环境中与“理”进行至深至烈的冲突。所以“至情”的前行一旦从幻境转向现实,就显出彷徨与迷惘。最后,那在现实中铸就的根深蒂固的“理”意念又于内心深处泛起。杜丽娘由鬼魂还生后,当柳梦梅催促成亲时,她却以“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推脱,之前那个为了追求理想而不顾生死也要冲击“理”的杜丽娘,此刻居然一本正经地担当起封建伦常的维护者了。杜丽娘在幻境与现实间的巨大反差让我们依稀看见她脖颈上晃动的精神枷锁和前行身影中的拘泥步态。《牡丹亭》以杜丽娘还魂后的谨慎强调身为鬼魂幽欢的反常,以杜丽娘返阳后的崇礼暗示她与柳梦梅幽媾的悖礼,由此表明“梦中痴缠”、“鬼魂幽会”的大胆热烈是不合世俗社会的礼义规范的。杜丽娘的前后不一实际上是汤显祖思想观念的矛盾反映。
汤显祖反对的是虚伪残酷、僵化刻板的理,而非正常的、合理的道德规范,因为后者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协调人际关系还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不能废弃。所以在梦中的杜丽娘可以率性而为,任意而作,不受羁绊。可是一旦回到现实,她就必须恪守妇道,谨遵闺范。还魂后的杜丽娘在面对柳梦梅的再度求欢时,就以“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来拒绝,这不是杜丽娘的矫情之语,而是她作为活生生的人必须遵守的礼法。可见梦中的杜丽娘是汤显祖“情”的展示,是他对人的自然欲求的肯定;而现实中的她则代表了作者“理”之所在。这样“梦中欢会”便与后来的“鬼魂幽媾”以及“奉旨成婚”一起构成了调和情理冲突的策略与技巧。
由此可见,在汤显祖的人性观里,情和理既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同源的一面。当他痛感现实社会中天理禁锢和扼杀人情的时候,当他的个性意识在心灵中翻滚奔突的时候,他就着重强调情与理的对立和冲突,并以艺术的激情把这种对立和冲突推到了势不两立的极端;而当他为了捍卫情的合理性、正义性和纯洁性的时候,当以人伦为人的本性的传统人性观支配着他的思想的时候,他则着重声明了情与理的统一和同源,情即是理,理在情中。面对这种两难的处境,汤显祖选择了技巧性的艺术探索和策略性的高明处理,而“丽娘之梦”的设置则帮助作者成功地避免了是非曲直的哲学演绎和逻辑推理,由此获得了更具人性化和人情味的关注。
总之《牡丹亭》以其深刻的思想意蕴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而家传户诵,而“丽娘之梦”则是使汤显祖扬名天下、《牡丹亭》流芳百世之肯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