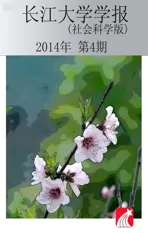中国古典文论的生态意蕴解读
2014-03-26宋坚
宋坚
(钦州学院 中文与传媒学院,广西 钦州 535000)
中国古典文论博大精深,不仅包藏宇宙万有,而且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理念,体现了东方民族的生命哲学和生存智慧,彰显了华夏民族特有的艺术精神。因此,在建构当代生态文艺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向西方的生态批评借鉴理论资源,吸收生态学科的前沿成果,还要汲取我们祖先留下的经典文论中的生态智慧。为此,有必要溯本寻源,对浩如烟海的古典文论所包含的丰富的生态意蕴进行解读,以便拿来为我们今天所用。
一、崇尚自然的生态审美观
中国古典文论中,普遍以自然万物为喻体,来论述艺术美感与人类的生命感应问题。从儒家经典《易经》提出的“生生之德”,到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提出的“天地大美”;从陆机的《文赋》提出的“物感说”,刘勰提出的“神思说”,到王国维提出的“境界”说,都包含着丰厚的生态审美意蕴。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都是你中有我,互摄互融的和谐统一关系。古典文论汲取了这种生态伦理观,体现了生生不息的生态情怀。
儒家文艺思想从诞生之时起,就以“亲民仁爱”为核心价值观,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念,有着“泛爱众而亲仁”的生态思想,以“仁者爱山,智者乐水”作为君子人格的象征,注重涵养“乐山乐水”的山水情怀。所有这些,都融入了中国古典文论的整体思想之中。儒家最早经典之一的《易经》曰:“生生之谓易。”《易经》认为,天地之大德为“生生之德”,天地之间阴阳互荡,涵养万物,生机勃勃。这是何等繁盛的生态景象。因此,天地万物在古人看来,是有灵性的统一体,天、地、人三者构成了生机互摄的生态关系。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便要不断地去领会生生不息的大千世界,尊重自然,感悟天启,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的相亲共融的互动关系。而文人圣哲则通过寄情山水、寄兴感怀来抒发性灵,这就是为什么文论家在论文之前,先领悟天地之道,通过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来把握万物荣衰的节律,最后以天地之道来观照为文之道的主要原因。
这种“比德”说以及“万物有灵”观,体现了先民“敬天爱人”的生态思想。《易经》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强调了仁人君子须有大地的厚重,才能承载万物。文德也是如此,文如其人强调了文品恰似人品,是人格的写照。人品高尚,胸怀坦荡,文风自然浩荡。古君子为文,先要做人,不仅要培养天地一样的博大情怀,还要追求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因此,古代文论往往从自然万象所呈现的生态景象中获得感悟:“天清地旷,浩乎茫茫,皆我友也。如太空无言,照人心目,辄增玄妙,此禅友也;夕风怒号,击竹碎荷,败叶飕飕,助我悲啸,此豪友也;眉月一弯,悄然步庭外,影珊珊如欲语,清光投我怀抱,此闺中友也;墙根寒蛩,啾啾草露中,如一部清商乐,佐西窗闲话,此言愁友也。审是天地自然良友,悉集堂中,莫乐此矣。”[1](P26)古人从自然之道中逐渐感悟文章之道,为文者在感悟自然万象的过程中,陶冶性情,荡涤灵魂,物我之间始终是彼此融合,两情相悦的。人以其主体精神投注客体,自然风物以其节奏音韵启迪人的才思,构成物我合一的移情和交融关系。“山鸟山花吾友于”体现了这种和谐关系。对此,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并驱矣!”这种物与我的高度浑融,构成了优美的诗意境界,表达了诗人浓浓的生态情怀。人的情感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如此的水乳交融,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古代文人在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中涵咏性情,不为物喜,不以己忧,面对纷呈多彩的世界而悠然自得,坐观庭前花开花落,闲看天上云卷云舒,纵浪大化,一任自然。刘勰说:“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2](P35)古人以博大的心胸悦纳万物,在赠答往还中见证了人生的诗意。人与自然的互相感应,山水景物在人心中的诗意生成,都在人与自然的深度交流中完成。这些生态文艺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艺观,使其具有浓郁的生态情怀。
二、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
中国古代文论历来就有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天人合一,即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与万物相亲共融,并最终达到和的境界。这个和的境界,讲究的就是杂多的统一,在相辅相成中进入和谐一致,均衡发展的极佳状态。[3]天人合一是中国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历代文人圣哲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它遵循的是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原则,体现了自然界生物多元共生的生态特性。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持这种观点,如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说,董仲舒的“天人相类”、“天人感应”说,王阳明的“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说,等等。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中庸》曰:“和也者,天地之大道也。”荀子的《天论》篇中说:“万物各得其和而生。”《淮南子·天训篇》也说:“阴阳和合而万物生。”[4](P87)这都是最早的关于天人合一的观点。在这方面,儒道的观点是一致的。道家以道法自然为宗旨,倡言“和以天倪”,提出了“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生态和谐观,包含着天人合一的辩证统一思想。道家所说的天人合一,主要是指向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庄子称之为“天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与阴同德,动与阳同波;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谓之天乐”。[5](P63)为此,庄子所追求的,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共来往的大境界。儒道互补糅合而成的天人合一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的主导思想。古代文论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认为天地有心,万物有灵,天人感应,心物互渗;反映到文艺思想上,则认为文章为天地之精英,刚柔之发端,应契合天人谐和的思想。以此为出发点,中国的文艺思想倡导以天地为心,与自然万物并存,敬畏生命,感悟生活,反身而诚,追求内心的充实与精神超越,将钟爱之情挥洒于山海之间,使得自然风物皆著上我之色彩,创造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
从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出发,古代文论对鱼跃鸢飞的勃勃生机景象十分向往,对万物生命是如此的眷念与执着,以至于把文学的审美气韵当作生生不息的宇宙万有来看待,出现了人化自然或者文学生命化的倾向。《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云从龙,风从虎,归凤求凰,天理之然也。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文学正是应和着自然界的生机韵律和节奏而作的。如“充塞大千无不韵,妙舍幽致岂能分”,“常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五灯会元》卷11《风穴延沼禅师》)。这种诗意都是应和自然万有,瞬间获得的自由灵动的审美感悟。这种人与自然的相证互摄,构成了生机互发的和谐之境,把握住了文学与生生不息的大千世界血肉相连的真谛所在,体现了“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物我合一”的诗性智慧和生态意蕴,使人觉得文学和自然生态一样,是多么地富于生机与活力的灵性之物。白居易曾经强调人文在融通天地万物时所起的作用:
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6](P229)
在白居易的文学观中,包含了天地与人文相互谐和的思想。因为文章乃天地氤氲之气的自然流荡,故而感人心,调阴阳,通灵府。文学艺术依循“生生”的节律,使人的精神进入“太和”的“高致”之境。人在这种境界中,实现了生命意识与艺术精神的完美结合,体验到自然生命向精神自由的超越,达到生命精神与宇宙本体的统一,最终进入天人合一的浑融之境。
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篇着重论述了为文之道首要的是尊重“自然之道”,具有很深的生态意蕴。其曰: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刘勰认为,文章(学)是应和自然万象的华彩和音韵而诞生的。山河大地,日月辉映;山川草木,禽鸟和鸣,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人参赞天地之化育,感应大千世界的绮丽和韵律而挥笔成文,这正是文学之道合乎自然之道的表现,因而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正说明了人类文化的起源,是肇始于宇宙生命大化的流行;文章之感人至深,是因为它符合自然生生之道的缘故。
三、“缘情说”与“物感说”的生态内涵
情之为物,絪缊化生。《易》曰:“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生物界之所以鱼跃鸢飞,生机勃勃,就是因为絪缊之情化生的结果。中国文论依循自然万物的生态机理,提出了著名的“缘情说”与“物感说”。它们把人情与物态、世情与物情和自然的生态原理融合在一起,体现了人与万物之间的氤氲之情的高度融合,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内涵。为此,中国文学成为主情的文学,注重情感的丰厚和气韵的流荡,这和西方文学所倡导的理性分析和心理分析是有着明显的界线的。中国文论最早倡导“性情论”的,是《毛诗序》所提出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什么叫诗歌?先秦文论说:诗言志,歌抒情;抒情言志,乃为歌诗。也就是说,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最好形式,所以古代文人纵情山水,寄兴感怀,就是为了达到借景抒情、借诗言志的目的,从而进入与自然万物融合为一的人生境界。古人感于风物,吟咏性情,皆是有感而发,力避无病呻吟之作,既符合天地人文之间同声相应的原则,也是符合艺术的创作规律的。
魏晋时代的陆机提出的“缘情说”具有划时代意义。“诗缘情”不仅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文化传统,而且第一次揭示了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肯定了情是诗歌生命力的美感表现,把诗歌作为抒发个人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受的载体。“缘情说”第一次突破了儒家诗论中诗教和事功的目的论,充分肯定了诗歌创作中个人情怀的自由抒发,使得魏晋风度以个性张扬的方式表现出来,标志着文学与审美的自觉时代的到来。陆机的《文赋》有多处论述到情感,如“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以及“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翁翁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这种诗情的生发,和周围的自然景物是如此的和谐统一,内在思想感情的显豁与外在物态形象的明晰总是交错在一起,构成了生机互动的文思才情。其中的“六情”指的是人类的喜、怒、哀、乐等主体情感。陆机认为,如果缺乏外部景物的激发,人的“六情”就会处于停滞状态,创作的玄妙精神活动也就无法展开。受陆机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许多文论家都十分推崇这种思想。钟嵘《诗品》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无成。莫不察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7](P126)他们不再从诗教伦理的角度来规范诗之情,而是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待情在诗歌中的作用,并以“情文”、“情采”作为文学美感的重要标志。
风起于青萍之末,才洒于山海之间。万水千山总是情,讲起人间艺术,怎一个情字了得。受“缘情说”的影响,唐朝诗人白居易提出了“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的情感文学论(《与元九书》);明朝思想家李贽提出了“童心说”,并且告诉我们,情以其“厥初生人,絪缊化物,乃为物始,乃为造端,乃是问学之第一义”[8](P187),说明了文学情感所具有的生态机能;后来袁宏道提出了“性灵说”,认为文章须“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自己胸中流出,不肯下笔”;明朝文学家汤显祖提出了“至情说”。他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9](P1050)汤显祖认为“人生有情”。这种生死至情,最终成就了他的临川四梦,其中的《牡丹亭·游园惊梦》一章堪称经典,重新诠释了中国文学所说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让人荡气回肠。由“言情说”的文学理论学说,诞生了惊天动地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气韵流荡,感情充沛,可歌可泣,具有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
“物感说”是中国文论中的又一个重要观念。它根源于我国先民对万物之间生命感应、心物相通的一种理解。《易》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人与自然之间是心物互渗,相互感应的。人心与天地万物间精神的生机互荡,构成了心物两融、身与物化的和谐关系。陆机在《文赋》里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他认为,正是物侯的四时变化和生生不息的大千世界,激发了人们的人生情怀,因此,敏感的诗人才不得不借助于笔墨,以抒发人生的情怀。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物感”是心物互渗、相互感应的结果。人参赞化育,含英咀华,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关注。之所以“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因为人心受到客观景物和季侯变换的影响,触景生情,所以才生发出抒情言志的创作欲望,以写天地文章来达到浇我心中块垒的作用。
“物感说”作为古代文论观,蕴含着生机互发、生命共感的生态意蕴。中国哲学素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始终把人的生存与周围的自然景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哲学思想认为,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心与物态密不可分;生命界中阴阳交合,天人感应,化生万物,才造就了和谐共生的活泼泼的生机景象。它消解了西方哲学中二元对立带来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共荣互存的和谐情景。这是中国艺术追求的至境,所以中国艺术思想中十分注重创造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深邃意境。这种心物互融之境,相当于王国维说的“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触物而感,欣然动情,融心于物,心物便处于交感互构的双向运动之中,达至心物互契、相互谐和之境。辛弃疾的《贺新郎》写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诗人与青山之间彼此相悦,惺惺相惜,相互爱慕。两者之间是相契互摄的关系,充满了谐和共感的生命意识。
刘勰的《文心雕龙》对客观景物给人心的召感作用作了深入的论述,认为“微虫犹能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心物感应,本属天然。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写道:“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诗人沐浴自然风物的熏染,应和四时景物的变化,往往心潮澎湃,引发无穷联想,于是诗兴勃发,奏清风明月之曲,谱阳春白雪之章,传达生命共感的景象。刘勰接着说: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
诗人感应万物,逸兴湍飞,浮想联翩,流连忘返于迷人的景色,依依不舍地吟咏心中的兴味,极尽生动的表现手法,精心描摹万事万物,做到随物赋性,形神兼备,活灵活现,创造了情景交融、气韵流荡的艺术画面。
心与物是和谐共生的,灵感的火花,正是在心物的感应中迸发出来的。以心物感应说为基础的中国艺术,是一种具有动态生命感的有机活动,其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文论家钟嵘对中国文论所做的最大贡献,正是提出了具有生态意蕴的“物感说”。其在《诗品·序》中曰: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寒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
魏晋南北朝是人的生命觉醒与审美自觉的时代,钟嵘的《诗品》继承了前人“物感说”的理论成果,提出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的重大命题,把“物感说”提高到人类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高度。正是由于气动引发物感,才使得诗人的创作动机瞬间生成,从而吟咏性情,形诸笔墨,写出惊天动地的璀璨篇章。由于艺术创作肇于自然,艺术情思也感发于自然。因为人正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也是一气贯通的。因此,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是一对生机互发、彼此感应的关系。汉末至魏晋时期的文学之所以具有为世称道的建安风骨,就是因为那时候的文学家在感物的过程中,融入了自然的气息和人的生命意识,并创造了混融一体的艺术画面,具有特殊的审美意义。所以,风格上有着建安风骨的文章,大都显得刚健峭拔,具有清新活泼的生命力。在这里,钟嵘特别以气来说明物动,强调了气动与物感的相互共振,使之充满了一种氤氲化生的动态生命感。
四、结语
多年来,学界多次呼吁中国文论的改革和创新,以挽救文学理论于学科危机之中。当代文论的最大症结,在于理论体系的僵化、灰色、教条和玄虚,在于内容的枯燥,缺乏文艺精神应有的灵动和生命意义,尤其在生态关怀和人文精神方面,存在严重的缺失。对此,笔者曾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个人的见解。窃以为,中国的古代文论和儒道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山水的亲密关系,具有当代文论少有的生态意识和生态原则,表现了东方民族特有的生存智慧。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中包涵的心与物游的浑融思想,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与物为春的畅神情怀,都标志着古代文论蕴涵着生态艺术的合理基因。因此,在建构当代文艺学时,首先必须借鉴传统文化的生态思想资源,这是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艺理论时,最值得借鉴的思想理论资源。[3]
随着全球生存危机的加深,随着理论创新不断出现的一些瓶颈问题,西方思想家深感西方现代文明的衰落。为从根本上拯救濒临危险的地球生态,为了彻底解决人类的精神危机问题,他们都一致将目光投向遥远而神秘的东方——中国,希望通过东方的古老文明拯救人类危难于水火中,尤其重视中国古典文论中蕴含的丰富的生存智慧。像黑格尔、罗素、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思想家,在建构他们的理论体系时,都明显地受到了中国道家的文艺思想和艺术精神的影响。因此,本民族的文艺工作者,必须重视中国本民族传统文化根基上生长出来的一片新绿,对中国古典文论的生态意蕴,做到合理的借鉴和应用。
对古典文论合理的借鉴和应用,意味着对古典文论的现代化转换。这就意味着要做到中西合璧,古今融通,求同存异,从而解决传承、融合、发展和创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让古典文论汇入到现代化的理论和文化洪流之中,在交流融汇中获得新生,使其成为一种融古今为一炉,保持民族特色,融通中西的新质的文艺理论体系。这无疑是疗救当代文论长期疲软问题,并使其走出徘徊不前的低谷的唯一良方。
参考文献:
[1]叶鐄.散花庵丛语[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2]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宋坚.生态文艺的绿色之维——生态文艺学的理论建构与应用[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4]刘安.淮南子[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5]曹础基.庄子[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6]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7]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8]李贽.李贽文集(第七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9]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第3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