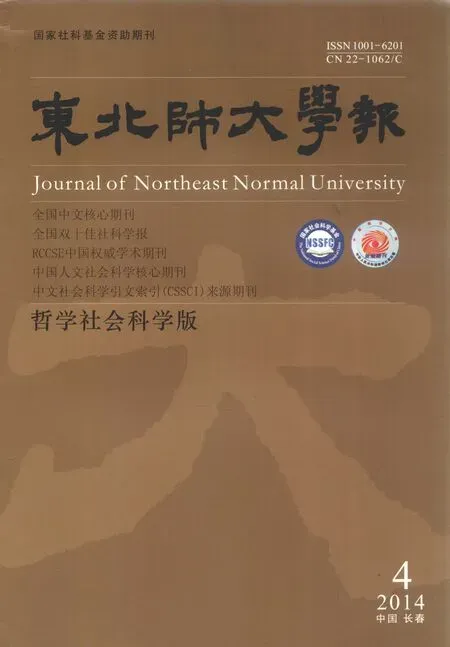组织边界扭曲:原因及其识别
2014-03-24于尚艳付才辉
于尚艳,付才辉
仔细观察大量的经验现象和研究,发现两种与TCE相悖的情况非常普遍:按TCE的预测,低专用性的交易本该采取“市场式治理结构”,但却出现了“企业式治理结构”;高专用性的交易本该采取“企业式治理结构”,但却出现了“市场式治理结构”。简言之,本该“外包(buy)”的却“自制(make)”了、本该“自制”的却“外包”了。对于这一相悖的现象,支持TCE的文献(尤其是经验研究)将其视为大样本中的不显著事件忽略掉了;反对TCE的文献(尤其企业边界的能力理论)借机从根本上就否认了其理论。若正视这一相悖的现象,并承认TCE作为一个理论基准是正确的,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极为要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扭曲了在TCE看来是最优的交易治理结构?换言之,组织的边界为什么会被扭曲?
有学者认为上述与TCE预测相悖的现象源于TCE所隐含的分析对象是出资人控制的企业而非代理人控制的企业。但他们的研究看似解释了“原本该‘外包’的却‘自制’了”,却不能解释“原本该‘自制’的却‘外包’了”这一相同性质的相悖现象。本文认为,保护专用性租金免受敲竹杠的治理合约若由代理人来设计的话就可能扭曲对委托人来讲是最优的治理合约。
一、问题的性质:异质的互联合约
商业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常见的经济情景:老板(委托人)委托经理(代理人)去向供应商、经销商、雇员以及投资者等采购、销售、雇佣、融资带有专用性的原材料、商品、劳动力、资本等。由于原材料等采购标的存在专用性,经理需要设计治理合约来防范交易对手敲竹杠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信息不对称,老板也需要设计激励合约来克服经理的道德风险。
一个交易生成一张合约,交易之间的互动就会导致合约之间的互联,合约之间的互联可能会改变各自合约的内容,也即改变了博弈的结构[1-2]。
前面情景中问题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异质合约之间的互联:股东和经理之间交易形成的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激励合约;经理与供应商之间的交易形成的是保护专用性租金防止敲竹杠的治理合约。同质的互联合约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分析,但遗憾的是,不完全合同与完全合同之间的互联问题尚未得到关注。现实中存在与TCE相悖的现象意味着异质的互联合约可能会产生冲突,这不同于同质的互联合约能产生“以合约治理合约”的功效。
二、委托人设计的治理合约
这里,将治理合约定义为“保护专用性租金防止敲竹杠的微观制度安排”。采购商获得的专用性租金是其采取了保护措施以防患供应商敲竹杠的结果[3]。按标准假定,所获得的专用性租金份额是租金保护措施的增函数且边际功效递减。由此可以得到治理结构的简要形式。
要获得特定控制必须对专用性投资及其产生的专用性租金做出明确规定,也即改善合约的信息结构,但得为之耗费信息费用。要获得剩余控制必须耗费治理费用,在标的产权结构不明晰的情况下甚至可能需要动用私人暴力和社会资本来获得剩余控制。信息费用与治理费用之和等于交易费用。按标准假定,交易费用是治理合约结构的增函数且边际交易费用递增。
这里,暗含的假定是交易双方在交易期间的认知理性以及交易的复杂性相对稳定,因此就可以用治理合约设计的交易费用(信息费用与治理费用之和)及其收益(保护的专用性租金)之间的权衡来内生解释治理合约的结构(特定控制与剩余控制)。
那么,委托人如何设计治理合约?
采购商通过治理合约的设计能够主动控制专用性租金的获取但得为之付出交易费用,其面临的问题是一个不带约束的优化问题。根据基本假定,在理论上可以得到治理合约结构的内点解、设计治理合约的交易费用、采购商获得的专用性投资产生的专用性租金的份额和专用性水平。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治理合约安排对效率的改进不是普遍的,其依赖于缔约的信息空间与权力结构。信息空间影响治理合约设计中的特定控制及其边际信息费用;权力结构影响治理合约设计中的剩余控制及其边际治理费用。采购商在较差的信息空间与权力结构中缔约所耗费的高额边际交易费用会严重阻碍治理合约对专用性水平的效率改进。然而,信息空间与权力结构的好坏又取决于交易制度环境的差异。
最优治理合约设计的基本原则即治理合约的契约替代率必须等于特定控制与剩余控制边际交易费用的比率,否则可以调整治理合约的结构来节约交易费用。
三、代理人设计的治理合约
采购商若委托一个代理人来与供应商交易,此时由代理人来设计与供应商交易的治理合约会产生什么后果?对此的研究思路是,先将治理合约设置成科斯式的“make or buy”经典二元离散分布,然后再用内生专用性的思维将其拓展到连续的情况。在前者的情况下,得到的结论是:当代理人的行动选择及其绩效是可观察和可证实时,委托人给代理人的报酬可以直接依代理人的行动而定,从而激励相容约束成为多余,由代理人来设计与供应商的治理合约不会存在扭曲;当代理人的行动不可观察时(信息不对称),激励合约不能够依存于代理人的行动选择。给定依存于行动绩效的激励合约,代理人会选择其行动来最大化其收益:在不对称信息下由风险厌恶的代理人来设计与供应商交易的治理合约可能就会扭曲对委托人而言是最优的治理合约选择。换言之,对委托人来讲原本该选择“自制”的代理人却选择了“外包”、原本该“外包”的却选择了“自制”。
“自制—外包”是治理合约经典的科斯式二元划分,本文认为,在不对称信息下由风险厌恶的代理人来选择治理合约的话就可能扭曲对委托人来讲是最优的治理行为选择。这一结论的新奇之处有三点:第一,其链接了不完全合同(治理合约)与完全合同(激励合约)在互联合约中的关系,这一点被已有文献忽视了;第二,异质的互联合约可能会产生效率损失,这一点不同于已有文献中同质的互联合约会带来效率改进的观点;第三,组织(企业)的边界由代理人设计的话就可能会被扭曲。
基于“自制—外包”的二元比较分析尽管在理论上能够说明问题,但不具有可操作性,其会陷入科斯当年所面临的“引而不用”的尴尬境地。在基本假设中可以看到在“自制—外包”两个治理合约分布的极端状态下,专用性水平都相同且处于社会最优水平,唯一的决策依据是各自交易费用的直接比较,即选择费用相对较小的形式。姑且不论交易费用能否准确测量,事实上这种直接比较不成立:未被选中的治理合约的交易费用根本无法被观察到。而用内生专用性的思维可以识别代理人设计的治理合约可能存在的扭曲。
用内生专用性的思维将其拓展到连续的情况。若委托人能够观察到代理人的行动时,委托人可以通过激励合约控制代理人的行动,也即代理人的激励相容约束不起作用,此时委托人的最优化决策实际上是一个帕累托最优的激励合约:代理人获得的固定薪酬等于保留工资加上行动的成本,代理人不承担风险是因为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最优的行动水平出现在行动的边际期望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处。
若委托人不能够观察到代理人的行动时,给定激励合约,代理人会选择能够最大化其确定性等价收益的行动。对比两种情况可发现:在不对称信息下由风险厌恶的代理人来设计与供应商交易的治理合约扭曲了对委托人来讲是最优的治理合约选择。显然,行动本身委托人不可观察,也就无法测度,由此也带来了委托人的期望收益或代理人的行动绩效损失。这再一次从委托人收益的角度表明了在不对称信息下,若由风险厌恶的代理人来设计与供应商交易的治理合约,将扭曲对委托人来讲是最优的治理合约选择。由委托人的支付函数的结构可以看到,可以利用支付值、治理合约安排、交易费用、专用性租金及其分配、专用性投资、专用性等变量来间接识别可能存在的扭曲。根据已有经验,这些变量之中只有专用性的信息相对容易获取,因此,内生专用性成为最为便利的识别工具。
[1]D.Kreps,J.Milgrom Roberts &R.Wilson.R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nitely Repeated Prisoners Dilemma[J].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82,27(2):245-252.
[2]J.McMillan & C.Woodruff.Private Order under Dysfunctional Public Order[J].Michigan Law Review,2000,98(8):2421-2458.
[3]张凤超,付才辉.专用性的内生化——一个制度视角的解释[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7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