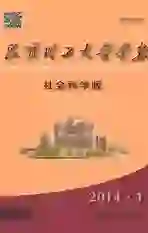论网络购物合同的成立及标价错误
2014-03-21雷秋玉苏倪
雷秋玉 苏倪
摘 要:网络购物合同的成立,取决于网络购物平台商品信息发布行为的法律定性,如将其认定为要约,消费者在网络购物平台上的下单行为即为承诺;如认定为要约引诱,订单确认信的法律性质就成了判断网络购物合同成立与否的关键,这两点亟待明确。网络购物合同成立后,网络购物平台上的经营者能否以标价错误为由撤销网络购物合同,取决于其是否存有过失及过失的认定标准。网络购物合同被撤销的,依现行缔约过失责任规则,消费者的信赖利益难以得到填补,信赖责任规则是一种理论上可行的替代办法,但德国民法传统上可变的缔约过失责任规则是一条更为可取的法律路径。
关键词:网络购物合同;合同成立;表示错误与撤销;信赖保护;可变的缔约过失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1-0043-13
一、问题的提出
(一)概念限定
网络购物问题所涉及到的相关概念众多,但是一些关键概念的外延均过于宽泛或者内涵不够确定。为了论述的方便及将本文论述的内容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需要对如下几个概念进行限定:
1.网络购物合同。本文拟探讨的网络购物合同为网络购物平台上的经营者与消费者,通过网络购物平台的相关网络技术设施而订立的,以实物商品和网络数字商品为标的之购物合同。其实现具有足够的自助性,即消费者以网络购物平台上购买按键设置,通过与电子设备的交流可以直接完成购买的意思表示。
2.商品信息发布。作为网络购物合同构成要素的商品信息发布的意思表示应当具备如下条件:①商品信息应当在网络购物平台上发布;②商品信息的发布应当具备图片及商品本身的详尽描述(包括商品名、规格、型号等)、价格、库存(现在有货还是无货,或者有具体的库存数量);③购买的按键设置完备,包括“加入购物车”“去购物车结算”“去结算”“提交订单”“支付”等按键技术设置,以便消费者在购买时,可以通过与电子设备的交流直接单方达成购买的意愿;④如果在线完成支付是消费者单方完成购买行为的必要条件,则完整的购买意思表示应包括支付行为的完成。
3.标价错误。标价错误,指网络购物平台上的经营者通过购物平台的网页所发布的与商品实际价格不符的标价,包括标价高于实际价格以及标价低于实际价格。本文拟论述的标价错误,仅限于标价远低于实际价格的标价错误,而将标价高于实际价格和标价一般性低于实际价格的情形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
4.因标价错误而撤销合同。本文所称的因标价错误而撤销合同,与前述网络购物平台标价错误的限定一致,仅指网络购物平台上的经营者因其标价错误而撤销合同,不包括消费者因标价错误而撤销合同的情形。
(二)问题的提出
2011年当当网发生书价标价错误,当当网要求以错误为由撤销订单,引发千名消费者维权参见李婧:《自取消订单,消费者一审告赢当当》,载《燕赵都市报》,http://bj.yzdsb.com.cn/system/2012/02/29/011620616. shtml.。该案曾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历一审与二审,最后法院判决当当网按活动价格,履行已确认的订单。2013年北京朝阳区法院就亚马逊单方面取消订单案,判决亚马逊向夏先生交付3块手表,夏先生同时支付价款396元。这两个案件均是在消费者收到订单确认信息后所发生网络购物平台标价错误案件,表明了我国法院对于网络购物平台标价错误处理的一般倾向。然而,法院在判决网络购物合同成立时,其依据是什么?为何不允许网络购物平台的经营者一方以错误为由撤销合同呢?这些问题令人疑惑。
网络购物平台标价错误是网络时代电子购物平台常见的意思表示错误。对于网络购物平台标价错误的法律处理,一般围绕下述三个问题进行:第一,网络购物合同应于何时成立?第二,如果网络购物合同成立生效,则网络购物平台的经营者是否以标价错误为由撤销购物合同?第三,在网络购物平台因标价错误撤销购物合同的情况下,是否存在消费者的信赖利益保护问题?在法院并未向公众公开已审决案件判决书的情况下,本文拟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对此展开一般性的探讨。
二、网络购物合同的成立
(一)电子形式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
网络购物,无疑涉及电子文件这一特殊意思表示形式的使用。由于电子文件不具备一般固定的有形外观,它是否具备与纸质文件或者纸质契约同等的法律效力?自1995年美国犹它州制定《数位签章法》(The Utah Digital Signature Act)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已经陆续制定专门的法律文件,规定两者之间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例如,澳大利亚《电子交易法》(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1999)第8条第1款规定:“基于联邦法律的目的,交易的效力不因其全部或者部分采用电子交流的形式而无效。”新加坡《电子交易法》(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2013)第6条规定,“不得仅因其采用了电子记载形式而否认信息的法律效力、有效性和可执行性”。两国相关法律文件均明确规定,采用电子形式的文件,不因不具有固定和有形的外观,而丧失其效力。采用类似规则的,还有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Uniform Electronic Transaction Act),欧盟电子商务指令(Direc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以及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Electronic Commerce)等。
我国2005年实施的“电子签名法”第3条规定,民事活动中的合同或者其他文件、单证等文书,当事人可以约定使用或者不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当事人约定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文书,不得仅因为其采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但是,身份行为、不动产交易行为以及公共事业等不得取用电子文件形式。由此可见,我国在较广泛的范围内承认电子文件形式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
(二)网络购物合同的成立
1.网络购物合同成立的基础。根据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定,一般情况下,合同于达成合意时开始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简单的合意乃合同成立的基础。在例外情况下,例如对于以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的情形,《合同法》第33条还规定,当事人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应至签订确认书时成立。然而,确认书似乎并无必要由双方签署,通常情况是:“双方达成协议以后,一方要求以其最后的确认为准,这样他所发出的确认书实际上是其对要约所作出的最终的、明确的承诺。”[1]
合同达成于合意,而合意建立在要约与承诺的基础之上。在网络购物的环境下,网络购物平台的商品信息发布是否要约?络购物平台发送给网购人的订单确认信是商家对合同的确认书,还是仅仅只是一种事实通知?这些事实的认定,对于判断网络购物合同订立于何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网络购物平台商品信息发布:要约抑或要约引诱。主要有下列两种见解:
(1)台湾地区的实务与理论见解。台湾地区对于网购业者将商品的图示、规格、功能、型号、售价等相关商品信息在网页上的展示行为是否应视为要约这一问题,晚近有三则判例可供参考。一是台北地方法院2004年度“消简字第18号案”。在该案中,网络购物平台的经营者主张,网络上相关商品的信息,是通过虚拟画面而不是以实际货物展示方式介绍商品,性质上仅类似于“价目表寄送”,故其仅属于要约引诱。然而法院认为,张贴于网络购物平台上的商品展示页面,标有实际图案、品牌、尺寸、商品功能描述及售价,足以认定为与传统买卖的陈列,具有同一效果,应视为“要约”台湾地区台北地方法院2004年度消简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二是2005年的一则判例。该判例认为,网络交易平台张贴的商品资料广告,属于对不特定消费者为出卖一定产品的“要约引诱”台湾地区台北地方法院2005年度消简上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其三是“戴尔案”的判决,认为戴尔公司约定“契约于戴尔接受客户订单后始为成立”,有不接受网站上商品信息发布的意思,故其商品信息发布仅为要约引诱台湾地区台北地方法院2001年度消简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台湾地区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货物标价陈列的行为性质,于其《民法典》第154条第2款规定:“货物标定卖价陈列者,视为要约。但价目表之寄送,不视为要约”。关于“货物标定卖价陈列者,视为要约”的含义,1945年永上字第531号判例判定,标价表示究竟是要约引诱还是要约,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应解释标卖人的意思确定[2]。王泽鉴先生也认为上述 “货物标定卖价陈列者,视为要约”的规定为“任意规定”,即其意究竟是要约还是要约引诱,应视标定卖价陈列者的意思定之。正是基于这一原理,王泽鉴先生对超级市场和自助商店里的商品陈列,似乎首肯为要约[3]。然而,王泽鉴先生的论述,仅限于现实生活世界。
在对网络购物平台中商品信息发布性质进行的探讨中,学者林丽真将此规则的阐释延伸至网络购物中。她认为,网络购物平台中的商品信息发布是否构成要约,应当仔细探究台湾地区民法第154条第2款与第1款之间的关系。按照第1款阐明第2款要约的含义,即“契约之要约人,因要约而受拘束。但要约当时,预先声明不受拘束或依其情形或事件之性质,可认当事人无受其拘束之意思者,不在此限。”[4]依其意思,网络平台的标价展示,是否构成要约,其关键条件在于,当事人是否有受约束的意思。郭戎晋将现实生活世界的商品信息发布与网络购物平台的商品信息发布予以比较,认为网络空间里的商品贩售网页与现实生活中开放式商品的货架陈列,事实仍存在若干差异,两者之间存在“消费者得否自助”的落差;后者可以认定为要约,但商品在网络购物平台中标价展示,似乎难以依台湾地区民法第154条第2款认定为要约。此外,现实生活中的商品陈列,除开放式货架陈列外,还有封架陈列的方式。在后种情况下,更难以认定为要约,网络购物环境中,不太可能存在这种类型的标价陈列。由此看来,在法律解释的意义射程之内,存在现行法律无法用来判断网络购物平台商品信息发布法律性质的缺憾[5]。黄茂荣先生将网络购物平台中的一般广告与“货物标定价格陈列”详加区分,认为“在网络中提供即时供货的服务,让购买人即可在网络上下载其订购之商品的情形(影视带或电脑软体)……与‘货物标定卖价陈列无异,应‘视为要约”。而其他情形下,则似乎不宜视为要约[6]。在解释上,可以将黄茂荣先生的观点与郭戎晋先生的观点等同,两人均倾向于以“消费者得否自助”作为网络购物平台商品信息发布作为要约的前提条件之一。
(2)比较法见解:以日本法为例。日本与网络购物有关的法律规范,除日本《民法典》与消费者契约法外,较为直接与网络购物有关的法律文件为“特殊交易法”。
“特殊交易法”规范访问买卖、电话劝诱买卖、邮购买卖、特定继续之劳务提供、连锁贩卖交易、业务提供引诱买卖等六种交易模式。其中,邮购买卖依特殊交易法第2条第2项规定,是指贩卖业者或劳务提供者,藉由邮件或者外务省令所定的方法,接受买卖契约或劳务提供契约的要约,进行商品或者指定权利或劳务的提供。其中,所谓外务省令所定的方法,依特殊交易法施行细则第2条,包括邮政、民间事业书信送达法第2条第6项所规定的一般业者或第2条第9项特定业者送达的方式,包括书信、电话、传真、通信机器或供情报处理用之机械、电报、对于存款户头缴纳之类型所谓对于存款户头缴纳之契约要约类型,如演唱会门票的邮购买卖,消费者事前不用通过电话、邮政为要约,而是在汇款单上填写姓名、信址、门票的种类及张数用来汇款的要约类型。。电子商务是藉由电脑、手机等“通信机器或供情报处理用之机械”进行的交易,因此属于邮购买卖。换言之,当网络购物当事人为企业经营者与消费者时,此时网络购物即属于邮政买卖。从邮政买卖的定义可知,在邮政买卖交易中,契约的要约人是消费者,企业经营者通过网络购物平台对商品进行标价展示的行为,为要约引诱[7]。
除上述规范性法律文件外,还有非作为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电子商务准则,它由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定期发布。依据2008年的电子商务准则,网络购物平台的商品信息发布,认定为要约引诱http:www.meti.go.jp/press/20080829004/03/t.pdf. 。
(3) 我国大陆地区的学术及实务观点。大陆有学者认为,判断电子交易信息属于要约还是要约邀请,可以参酌法律规定、当事人的意思,还可依据客观外在的情形。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实物商品网上销售的情形;一类为数字化商品网上销售的情形。就实物商品网上销售而言,先应考虑当事人明示的意图,如果商品信息发布人特别声明,不得就其提议作出承诺,或声明对此广告和信息的发布不承担合同责任,或提出该广告及信息仅供参考等,均应视为当事人所作意思表示仅为要约引诱。当然,如果商品信息的发布者明确表明其意思表示为要约的话,例如在商品信息中有“款到必发货”之类的明确表示,该商品信息如果还符合内容明确具体等条件,其发布应构成要约。在当事人没有为明确的表示时,此时即应根据当事人发布商品信息的客观情形来进行判断。例如,单纯的商品介绍推广信息、一般的商品广告或价目表等不宜认定为要约,但如果商家在网上既提供了商品的购买方法及购买的操作程序,标明的商品价格,还通过订单系统向顾客指明当前存货的数量。也就是说,顾客在网上订购商品之后,在该网站上显示的商品数量就相应地减少,或者指明了商品的具体存量的,此时该商品信息的内容已经明确具体,符合要约的条件,因此应视为要约[8]。在数字化商品网上销售的情况下,一般认为,其商品信息中商品本身的介绍、购买方法、商品价格等信息且可以“自落”的情况下,这种信息发布应认定为要约。对于实物商品的网上销售,例如淘宝网的“一口价”交易,有学者也表示了基本相同观点,其理由是淘宝网上相关商品的标价展示已经符合了我国《合同法》确定是否存在要约的两个实质性的条件,即内容具体确定,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当然,淘宝网上除了实物商品的“一口价”交易外,还存在虚拟商品的“一口价”交易,这种商品交易信息的发布为要约;闲置商品交易,由于存在“讨价还价”的空间,其发布行为宜为要约引诱;竞拍商品交易信息的发布,为要约邀请;代购合同信息的发布,应视具体情形是否符合《合同法》中要约的条件,确定为要约抑或要约邀请[9]。
从实务上看,上文已经提及的由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和朝阳区法院审理的当当网标价错误案和亚马逊单方取消订单案,均提示了网络购物交易中,经营者一方商品信息发布为要约引诱,而消费者下单结算为要约。实务与理论可能存在较大的反差。在我国欠缺关于此类交易的明确法律规定情况下,法院做出这种判决也在情理之中,这在法院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之内。从我国目前主要购物网站的情况看,没有哪个网站在其网页的显目位置标识“本站所有商品的标价展示均只为要约引诱”之类词语。在没有明示否定其为要约的情况下,我国主要购物网站的商品信息发布,不仅符合《合同法》所规定的要约的内容应明确具体的要求,而且只要具有一般常识的人均可以判断,它们也符合“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的条件。不过,好在上述法院均将消费者收到的网络购物平台自动发出的订单确认信,作为确证网络购物平台已经作为承诺的证据,不过在法理上仍存在较大的漏洞。我国《合同法》第21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根据该条规定,网络购物平台不难以言语技巧规避承诺的构成。以采自现实生活中的两份网络购物订单确认信为例。第一份是当当网的订单确认信。信件名称为“订单5514474244已收到,正在处理”。信的末尾是“重要声明”:“此封电子邮件仅确认我们已收到了您的订单,只有当我们向您发出商品出库的电子邮件通知您我们已将商品发出时,我们和您之间的订购合同才成立。如果您在一笔订单里订购了多种商品,而我们只给您发出了其中一部分商品出库的电子邮件,那么只有这部分商品的订购合同成立;直到我们向您发出其他商品出库的电子邮件,您关于其他商品的订购合同才成立。”第二份是亚马逊的订单确认人。信件名称为“您在亚马逊的订单”,内容包括致谢辞,“如何查看或修改您的订单”“购物信息”(主要罗列购物人的信息,包括邮箱地址、送货地址、订单金额),“订单汇总”(含订单号、送货方式、订单总计金额、预计送达日期、订购的商品信息)以及最后的特别说明:“此订单确认信仅确认我们已收到您的订单,只有当我们向您发出送货确认的电子邮件通知您我们已将产品发出时,我们和您之间的订购合同才成立”。这两份订单即是以明确语词表达,将订单确认信处理成了事实通知。而按照我国《合同法》的第21条,网络购物平台的经营者如此操作,并不违背法律的规定;且在网络购物平台发出如此的订单确认信之后,在法律适用的层面再将之解释为承诺,将与法律的明确规定存在明显抵牾。
3. 订单确认信:承诺抑或事实通知。如上所述,鉴于立法上对于网络购物平台的商品信息发布行为的法律性质,尚未有明确定性。根据网络购物交易一般运作模式,消费者在网络购物平台上按下确认购买的按键后,经营者通常会发送确认信,例如“我们已经收到您的订单……”等之类的用语。如果确认经营者在网络购物平台上所刊登的商品信息行为属要约,那么消费者点选订单并进行结算的行为即属于承诺,买卖合同已经成立,此时订单确认信的回复只应当具有事实通知的性质;但是,如果将经营者在网络购物平台上发布商品信息的行为认定为要约引诱,那么消费者在网络购物平台上下订单并结算的行为应为要约,此时买卖合同并未成立;经营者收到消费者的订单,通过电脑系统建立起来的自动回复性质的订单确认信,其性质或为承诺,或为事实通知。一般情况下,经营者往往会通过网页中定型化契约、服务说明或注意事项等形式表达所发送的自动回复订单确认信仅代表已方“收到”订单资料的通知而非承诺。例如,上述当当网和亚马逊网站的订单确认信中的“重要声明”和“特别说明”即是,须后续通过其他方式向消费者确认通知经营者已经“接受”订单之后,契约才算成立。然而,经营者通过对回复的订单确认信的效力加诸此等限制以规避其负担的责任风险,此种作法,是否的确能够对契约的成立加以限制?
台湾地区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曾针对这种情况发布新闻稿表示,不论这种交易的经营者在网络上所刊登的商品信息究属要约或要约引诱,只要消费者下单,之后存在确认信,买卖契约即已成立参见台湾地区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新闻稿:《购物标错价/购物金兑换:消费者的权益在哪里?》,http://www.cpc.gov.tw/detal.asp?id=444.访问日期:2013年11月9日。。然而,有学者认为这种规定过于草率,恐有损交易安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2005年7月通过国际契约使用电子通讯公约,亦认为委员会不宜提供指导准则使自动回复的电子系统确定契约成立,契约如何成立仍应由各国国内实体法加以规定。
有学者指出,网络购物平台上的经营者发出的订单确认信是否具有承诺的效力,应视其具备内容而定:(1)假若确认信中已经明确表示契约已经成立,纵然经营者在服务约款或定型化契约中已经加注保留最后出货的权利,契约仍应当确定无疑的成立;(2)假若确认信的语句明确表示契约尚未成立,契约尚未成立。但是,网络购物平台于其网站服务说明内标示消费者的订购及付款仅是经营者收到订单,并不表示契约已经成立之类的预约,是否具有效力,美国法院过去一直持否认态度;但是对于经营者通过网络的“点选同意契约”,要求消费者按下“我同意”之前必须详细阅读约款,一旦消费者按下同意,即表示消费者已经接受其约款的内容之类的预约,美国法院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否认其效力,但至1996年后,已经逐步接受同意其预约效力。(3)假如电脑自动回复的确认信内容语焉不详,则应视具体情况予以处理。例如,消费者下单并同时完成付款,应视为交易已经完成;消费者下单时未同时完成付款,应视为交易未完成[10]。
总体而言,订单确认信是否具有承诺的效力,首先取决于是否确认网络购物平台经营者的商品信息发布构成要约,如其构成要约,则消费者在网络购物平台上点击订单确认按钮或者在下单之后另行付款结算的行为构成承诺,之后的订单确认信只能认定为事实通知。但若将网络购物平台上经营者的商品信息发布认定为要约引诱,则经营者的订单确认信的性质认定,对于网络购物合同成立的时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刀切的标准显然并不科学,订单确认信的性质应依订单确认信的内容并结合消费者的具体情况而定。
三、得否以标价错误撤销网络购物合同
(一)《合同法》第54条内容的解释
我国《合同法》第54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关于该条中的重大误解,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的《民通意见》第71条。按照该条内容,“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数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且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错误。”在学说上,崔建远先生等忠实于上述规定,认为重大误解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误解合同性质,如将A类合同当作B类合同,较为典型的情形或许是误解买卖当赠与;其二,误解某人为相对人;其三,对标的物本身产生误解,包括误认A物为B物;其四,误认标的物的质量与数量;其五,对合同的履行重要内容产生误解,如数量、包装、履行方式、履行地点、履行期限等[11]。而张俊浩先生等对完全相同的规定,解释为重大错误与重大误解[12],其中重大误解的内容与合同法第54条的内容吻合,但“重大错误”不知从何而来,显得有些牵强。
可以说,在合同法第54条语义射程之内的司法或者学者的解释,均无法使合同法第54条涵盖表示错误的内容,包括网络购物平台的标价错误。
(二)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8条第1项的解释
根据郑玉波氏的介绍,错误在法律上的效力如何,各国的立法例不一致。有认为无效者,如日本民法日本民法采意思主义的立法例。例如,日本民法典第95条规定:“意思表示,于法律行为的要素有错误时,为无效。但是,表意人有重大过失时,不得自己主张其无效。”参见王书江:《日本民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及德国民法第一次草案,属于偏重于意思主义的结果,即从罗马法“错误者无意思”(errantis nulla voluntas est)的法谚中脱胎而来;有认为得撤销者,如德、奥民法,属于侧重于表示主义的缘故;也有认为无效兼得撤销的,如法国民法,属于折衷主义。台湾民法,采用的是源自于德、奥的表示主义[13]。
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8条第1项规定:“意思表示之内容有错误,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将其意思表示撤销之。但以其错误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过失为限。”这一规定,采用的就是有效,但得以有条件撤销的表示主义立法例。王泽鉴先生依法律教义主义,将台湾地区民法中所涉错误初步归纳为动机错误、内容错误、表示行为错误、关于当事人资格或物的性质的错误和传达错误,但由于动机错误不能一般地称为民法上的错误,故将动机错误从民法错误的类型中删去,但动机错误中的关于当事人资格或物的性质的错误,依台湾地区民法规范,被纳入内容错误。这样一来,最终民法上的错误,只有内容错误、表示行为错误和传达错误[14]。其中表示行为错误,即台湾地区民法“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为意思表示者”,如误言,误写,或者误取,在此情形下表意人可撤销其意思表示。网络购物平台的标价错误,可归于误写的表示错误类别,依传统民法理论,表意人可以有条件地行使撤销权。所谓“条件”,亦即台湾地区民法第88条第1项第2句所说的表意人对错误的发生无过失。
然而,对于何谓表示错误中的过失,学者见解不一。郑玉波主张具体轻过失,因为解为抽象轻过失,则表意人几乎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机会,对于表意人未免过酷;若解为重大过失,则表意人行使撤销权的机会过多,于交易安全有碍,故应调和于二者之间,取具体轻过失[13]349。也有主张抽象轻过失的[15]。在司法实务上,台湾地区台北地方法院2004年度消简字第18号民事判决认为应以“具体轻过失”为宜;而台湾地区2005年度消简上字第7号民事判决则表示应以抽象轻过失为宜。然而,上述2005年度消简上字第7号民事判决,同时判决网络经营业者可以撤销其意思表示,因为消费者并不存在可资保护的信赖,似有不当,消费者是否存在值得保护的信赖,仅影响消费者得否向网络购物的业者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似乎与业者得否撤销其错误的意思表示无关。
(三)比较法的见解
1.英美法中的表示错误。杨桢先生的《英美契约法论》将意思表示错误分为三类,即双方错误(mutual mistake)、共同错误(common mistake)与单方错误(unilateral mistake)[16]。如果表示错误要置于这一意思表示的错误体系中,即应置于双方错误或者单方错误之中。该论著认为,英美对意思表示错误的立法例为意思主义:“何种错误才能动摇契约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吾人以为,只有当该项错误引致双方之间根本没有真正之合意(real meeting of mind or mutual assent)时,才能使契约无效,即所谓有影响力之错误。契约一旦因错误发生无效,普通法上之救济乃当事人负有回复原状之责。”[16]202本文认为,杨桢先生对英美法的错误之效力可能存在判断失误。杨著主要参照的美国《契约法重述(第二次)》的相关条文对于意思表示错误效力的判断大量使用voidable表达。然而voidable并非无效的意思,而应是可撤销的意思。Voidable实际含义是“合同、契据、交易或其他行为,如果其在表面上是正常有效的,但因其在实际上含有瑕疵,从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有权将其撤销(rescind),则该合同、行为等属于可撤销的。”但是作为voidable词根的void则是无效之意参见薛波:《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在大陆法中,无效与可撤销存在较大差别,应明确分辨。
作为对照,英国法学者麦克雅克的《契约法》中,对于意思表示错误的效力,所使用的词汇为rescind[17]。这样或可省却不少误解。在上述《契约法》中,麦克雅克将表示错误界定为向对方当事人所做的有关事实或法律的模棱两可的、错误表述,具有实质性且导致契约的发生。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可撤销,即“撤销规则原则上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表示错误”。因此,英美法中的表示错误的处理规则,其立法例实际为表示主义。
2.德国法。如前所述,德国法对错误的立法例,系采表示主义。德国2004至2005年发生两宗有名的网络标价错误案。在第一宗案例中,卖家在其设置的网上商店的网页上销售电脑与配件,有一款笔记本电脑标价为799.24欧元,而其实际售价为1959.24欧元。买家以电子邮件向被告订购一台,卖家同日以自动回复系统的电子邮件,确认所订购的电脑与价格。但随后买家即收到了被告的第二封电子邮件,被告知标价错误,正确价格应是1959.24欧元。买家主张以799.24欧元出货,但卖家予以拒绝,并予数日后发函给被告,以错误为由撤销网购合同。买家于是主张赔偿差价,但亦遭卖家拒绝,遂诉于公堂。法院首先认定本案被告价格键入错误(Tippfehler),包括表意人事先将其价格键入错误的意思表示储存于电子设备中,而后于客户订购后自动发出的情形,属于德国民法第119条第1项的表示错误,依德国法的见解,得以错误为由撤销。 另一判例认定,资料利用软件自动传递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导致卖方将原本正确的标价,被错误地传输到网站的网页上,属于表示错误,得撤销之。
由上观之,德国民法中关于网络商品标价错误的处理规则极为清晰明了。事实上,网络上的标价错误,无论是由原始资料错误,还是由输入错误、电脑程式错误,抑或传递错误等导致,在德国民法上统合以表示错误予以归整,并统一赋予可撤销的法律效力。然而德国民法对于表示错误得否撤销,仍附有“如果可以认为,表意人若知悉情事并合理地考虑其情况后即不会作出此项意思表示时”可归责性条件,较之台湾地区民法的规定,似乎更倾向于客观过失。
(四)我国关于表示错误撤销规则之修正
1.关于表示错误撤销的一般考虑。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民法中的“重大误解”规则,系属表示主义的立法例,不因错误而使法律行为无效。
但是,也恰如上述,我国现行立法依合理的解释,无法涵盖表示错误,尤其是网络购物平台商品标价错误这种表示错误类型。较为合理的选择或许是回归传统民法,以错误规则修正现行法律中的“重大误解”规则。
在表示错误规则中,错误的表示能否撤销,可以吸取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中的表示错误规则,以过错作为错误表示的撤销主观条件。事实上,我国学者在论著中对此早有论及。例如,王家福指出:“如果重大误解是因误解者自己的故意或过失造成的,则不能赋予误解者变更权或撤销权,因为这种人本身就对其利益漠不关心,甚至有意丢弃,法律没有必要保护他”[18]。但这种论述仍显得不够细致。就表示错误而言,如故意而为,必然涉及欺诈,与表示错误的本意距离过远。在表示错误规则的语境之下,错误必非出于过失,亦即台湾地区民法典中“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为意思表示者”,或者德国民法典“如果他在知道事情的状况或合理地评情况时就不会做出该表示”的情形。关于此种过失的判决标准,仍需在司法实务中予以明确,即应将采用“具体轻过失”,还是“抽象轻过失”,抑或“重大过失”的选择权赋予司法实务机关,使其得以在实务上结合具体的社情、民情及时代要求进行自由裁量。在具体司法实务中,过失的证明是采用过失推定,还是一般的证明原则,考虑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及第三人证明的难度,或许采过失推定的立场会比较稳妥。当然,也可采用英美法中的客观过错规则。
2.商品标价错误的网络购物合同撤销。
网络购物平台上的商品信息发布之意思表示,如果存在错误,符合无过失等要件,错误的意思表示者可行使撤销权,使双方的法律关系恢复至网络购物合同之前的状态。但是在网络购物环境中,有下列两种情况需要特别考虑:
第一,网络购物平台的商品经营者故意标低价格。网络购物平台中存在故意标低价格的情形。例如,上海某照明设备有限公司在阿里巴巴上发布的强光狩猎灯标价仅为1元。消费者按照商家的数量标识,拍下10套后通过支付宝向卖家付款10元。可是联系卖家要求发货时该公司却说商品的实际价格是200多元,拒绝发货,要求买方以实际价格结算参见阿里巴巴:《卖家故意标低价格欺诈买家,怎么处理?》,http://baike.1688.com/doc/view-d3745135.html.。这样的交易实属欺诈。我国《价格法》第1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6条规定,经营者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一交易场所同时使用两种标签或者价目表,以低价招徕顾客并以高价进行结算属于价格欺诈行为。网络购物平台上的经营者在平台上发布的商品信息,标识的价格过低,而在消费者下单付款之后,要求消费者以实际的高价结算,本质上属于《价格法》第14条和《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6条所规定的欺诈行为。
对欺诈行为,因其欺诈而为意思表示的一方当事人可撤销其意思表示[19]。我国《合同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一方以欺诈、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做出欺诈意思表示的一方,无权撤销合同。因此,对于故意标低价格的情形,消费者一方如果对此不知情,而善意相信此标价为真实标价,即享有撤销权。如果消费者不撤销网络购物合同,实施价格欺诈的经营者即得按照所标明的商品或者服务价格履行合同。
第二,消费者恶意。在特殊情形下,网络购物平台过低的错误或者欺诈性标价,被消费者利用以达成其目的。在错误标低价格且错误标价一方当事人无过失,其可以意思表示错误为由主张撤销合同,此时不应考虑消费者恶者与否。较有疑问的是,如果错误标低价格意在欺诈,消费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存在错误标价,将错就错,利用这种错误与对方交易,意在获取不正当利益。这种情况明显与我国《合同法》第54条第2款所规定的适用范围不同,因为在此并不存在“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的情形,此时交易的法律效力如何?于此存在两难:一是故意标低价格的一方当事人因欺诈而无撤销其意思表示的可能性;二是恶意的消费者也不存在撤销网络购物合同的撤销权。因此,通过撤销权的行使而使合同归于无效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同时,在此情形下,也不存在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使合同无效的情形。然而,使这样的合同具有强制履行的法律效力,是否与我国《合同法》第6条所规定的“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意旨相违背呢?对此较佳的处理办法应是依诚实信用原则而使合同无效。
四、网购合同撤销后的处理路径
(一)现行缔约过失责任规则的缺憾
我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该条规则中,与网络购物合同因错误标价而撤销这一情形最为相关的是第2句。根据该句的规定,结合我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网络购物平台上经营者因标价错误撤销合同,仅在无过失的情形下,始有撤销权;经营者撤销网络购物合同之后,因其无过失,无须承担对方因此而导致的损害。第二,网络购物平台上经营者因标价错误撤销合同,仅在无过失的情形下,始有撤销权;有过失者,不得撤销网络购物合同,应继续履行合同。因此,依据我国现行《合同法》的规则,因错误而撤销合同的网络购物平台上的经营者,不会因其撤销网络购物合同而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即使消费者因其错误行为而遭受了损害。有损害而无救济,显然不符合民法的精神。
(二)信赖责任路径的可能性
1.信赖保护规则的体系与信赖责任。有学者提倡在我国民法中建立信赖责任保护规则[20-21]。信赖保护规则可依其保护的利益,分为信赖积极保护与信赖消极保护,前者保护合理信赖者得其所欲,后者使信赖补其所失[22]。信赖积极保护现今为各种表现规则所覆盖,如无权代理、善意取得等;信赖消极保护规则(下称信赖责任)是合同责任规则之外与合同紧密相连的规则,但它所依据的并非合同,即并非当事人之间基于意思自治的法律行为,而是依据一种社会性的利益,即信赖利益。
根据缔约过失责任的体系中的现有类型,可分为单方保护的依赖与双方保持的信赖。单方保持的信赖包括错误意思表示的撤销、无权代理、给付自始不能、恶磋商或欺诈等情形。双方保持的信赖包括合同成立、合同有效与缔约阶段的先合义务。单方保持的信赖中,错误意思表示的撤销、无权代理、给付自始不能归入信赖责任,而恶意磋商或欺诈等可以归入侵权责任。双方保护的信赖,事实均非真实地建立在信赖的基础上,而是法律基于诚实信用这一法律化的商业道德的要求;对当事人双方作出的要求,它们不适用信赖责任规则,而适用缔约过失责任规则[23]。即使承认存在相互的信赖,事后仍然会因责任的相互抵销而使得信赖责任规则变得毫无意义。
网络购物平台上的经营者将商品错误标价展示,之后因错误而撤销网络购物合同,由此所致损害,如上所述,无法在缔约过失责任规则中寻求救济。由于信赖责任并不以错误为意思表示者的个人性为标准,而又抽象错误意思表示的相对人是否存在合理信赖为标准,故网络购物因商品标价错误而撤销之后,或可由信赖责任规则中找到请求权的依据。
2.信赖责任的构成。我国学者亦提出了信赖责任的构成要件:第一,显然的意图或事实,即需要具备促使相对人或者第三人产生信赖的、显而易见的意思表示。例如,在英美法中,强调一方当事人须向另一方作出了肯定、明确的允诺、事实陈述等,因为非如此,不足使相对方产生信赖;第二,信赖行为,即相对人不仅由他人展现的事实产生了信赖,且基于此信赖而行动;第三,信赖人须为善意,即不得存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撤销原因的情形;第四,可归责性,即依理性人的标准,为错误意思表示者明知或应知其表示将唤起相对方的信赖行为,但这一条件并非必要[24]。
3. 信赖责任的适用现状。信赖责任在我国立法中尚无明确规定。国外立法中比较常见的导致信赖责任的具体行为类型,在我国均被纳入到了缔约过失责任范畴。因此,在网络购物环境中,无过失标错价格的经营者行使撤销权使网络购物合同之后,消费者即无从寻求《合同法》现行缔约过失责任规则的救济,也无法藉由学者们所频频讨论的信赖责任规则得到救济。在北大法宝及万方数据库中以“信赖责任”以及“信赖责任原则”等为关键词搜索的结果是,目前我国的信赖责任主要适用于行政法领域,在民法中付之阀如。由此可见,如果网络购物平台上的经营者享有法定的撤销权,消费者将处于尴尬的境地。
在实务中,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司法机关唯有关紧网络购物平台上的经营者行使撤销权的阀门,从严认定过失的存在,才有可能使消费者的利益借由合同的履行或者违约责任得到保护。从上文所举的当当网书价标价错误案以及亚马逊单方面取消订单案的处理看,法院均是判决网络购物平台上的经营者承担合同履行的责任,这或许是缔约过失责任规则逼出来的结果。
(三)可变的缔约过失责任:德国民法传统与旧民法的移植
在德国,虽然其立法中存在实质上的信赖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在德国民法理论中,受耶林的影响,大都被看作为缔约过失责任。其发展和演变,也是借由缔约过失责任的名义。所以,对德国法中信赖责任的历史梳理,必须以缔约过失责任的发展演化为线索。
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作为德国第一部统一民法典,受普通法学说的影响,对于缔约过失责任作了初步的规制。根据刘春堂教授的介绍,该法第一篇对于缔约过失责任作出如下规定[25]:第一,第三章第128条、第171条规定:“设本人于法定期间内对无权代理人行为拒绝承认者,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因契约无效所生之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又本人已撤销代理权之授予,代理人因未告知第三人(相对人)而与之缔结契约,代理人应赔偿该第三人因契约无效所生之损害。”第二,第四章第79条:“如表意人因自己过失而陷于错误,相对人对此不知而与之签订契约,表意人应对相对人因此所受之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第三,第五章第33条:“经过适当检查后未发现对方无行为能力,而因此与无行为能力人订约之相对人,因契约所生之损害,可请求以该无行为能力人之财产予以赔偿。”第四,第五章第53条:“给付义务人,明知其给付为自始不能而仍与他人订约者,因契约无效而使他人受损害时,应就他人因此所受损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五,第五章第105条:“要约人撤回要约时,怠于第104条所定之行为(及时通知),如对方已于相当期间内表示承诺者,撤回人对于相对人在未撤回期间内,因准备行为所受之损害,负赔偿责任。”
上述这些规定,部分被改造吸收到了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之中,主要包括:第一,意思表示错误的撤销。见于第118条、第119条和第120条,分别规定为“善意的戏谑”,基于错误认识而为的意思表示,以及误传;第二,标的自始客观不能,见于其第307条;第三,无权代理,规定于第179条第2款。1896年德国民法典没有继受《普鲁士普通邦法》中对于无行为能力主体订约的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则,其目的主要在于对无行为能力人的保护。同时,因1896年德国民法典已经明确要约具有约束力,不似普通法时期不承认要约的约束力。因此,要约撤回的缔约过失责任在该部民法典中未被采用依1896年德国民法典第145条,要约到达受要约人即具拘束力,即使要约人发出撤回其要约的通知也不产生法律效力,受要约人有权单方面决定是否作出承诺。。
1896年之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有关缔约过失责任的学说与判例均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在2002年债法改革之前,虽然个别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总的来说,缔约过失责任在德国民法体系中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换句话说,就是已经成为了固定的习惯法[26]。为呼应债法改革法,德国民法典的第二编“债务关系法”部分也作了相应的修订,即第241条增加一款,规定债务关系可以在内容上使任何一方负有顾及另外一方的权利、法益及利益的义务;另在第311条第2款作呼应性规定:“具有第241条第2款义务的债务关系,亦因下列行为而产生:第一,开始合同磋商;第二,开始接触缔约,但以一方当事人有可能的意定关系方面为另外一方当事人提供干预自己权利、法益及利益的可能性,或将其托付于另外一方当事人为限;第三,类此的交易接触。”这些规定表明着德国民法典在形成缔约过失责任一般性条款的努力。
然而,尽管如此,德国民法上并没有形成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统一归责原则,对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分散于各处的法律条款也无心归整于一处,而是有区分的对其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一类是因错误的撤销、无权代理所产生的信赖损害的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而另一类则是因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时所应担的损害赔偿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其中因错误而撤销的情形,现今规定于德国民法典的第122条:“(1)意思表示依第118条(欠缺真意)或依第119条(因错误而可撤销)、第120条(因误传而可撤销)而撤销的,如该意思表示须以他人为相对人而对出,则表意人必须向相对人,在其他情形下,向任何第三人,赔偿该相对人或第三人因信赖该意思表示有效而遭受的损害,但不超过该相对人或第三人就该意思表示之有效所拥有的利益的数额。(2)受害人知道或因过失而不知道(应当知道)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的,不发生损害赔偿义务。”参见陈卫佐:《德国民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对于上述第122条所规定的损害赔偿,我国有学者明确将之纳入到缔约过失责任中,并将之界定为“消极利益赔偿”[27]。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的第91条几乎全文移植了德国民法典第122条的规定:“第88条(意思表示错误)及第89条(传达错误)之规定,撤销意思表示时,表意人对于信其意思表示为有效而受损害之相对人或第三人,应负赔偿责任。但其撤销之原因,受害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对于台湾地区民法典的第91条,王泽鉴先生将其归入缔约过失责任[14]232-233。上述台湾地区台北地方法院2005年度消简上字第7号民事判决中,曾对第91条中受害人的“善意”作如下分析:上诉人在网上销售电视并非采用了超低价竞售的手法,被上诉人居于一般消费者的地位,以社会上相同经验智识之人,处于相同的状态下,应当可以知悉网页上所载的销售价格19499元(台币),有相当的可能系出于误载,被上诉人对系争电视售价表示错误,应有认识的可能。此外,被上诉人并未开始给付系争电视价金于上诉人,也没有在订购系争电视后为履行契约有所支出,可知被上诉人无足资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5]1-42。总体上,继受了德国民法传统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在缔约过失责任的归责上,基本维持了德国民法的可变的、分化的缔约责任归责原则。其基本体系如下:标的不能与契约无效,适用过失责任;错误意思表示,知用无过失责任,无权代理不生效力,适用无过失责任;违反说明义务、违反保密义务等,适用过失责任。
我国《合同法》在移植缔约过失责任的相关规则时,与台湾地区的民法典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错误而主张撤销合同的场合,主张撤销的一方如有过错,始应赔偿由此而使对方遭受的损失。按照朱广新的解读,我国《合同法》在此走向了与《瑞士债法典》第26条的“缔约上过失责任”相同的规则路径,而没有走向德国民法传统上的“信赖责任”[28]。根据孙鹏的表述,就是偏向了过失主义,而非偏向危险主义,偏向了静的安全,而非偏向动的安全[29]。这种立法思路使得交易第三人利益的保护被悬置起来。
五、结语及建议
网络购物合同的成立及标价错误问题,是网络时代出现的新问题。网络购物合同于何时成立,得否以标价错误为由撤销,以及撤销后的处理路径,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而不是将其悬置起来。
1.网络购物合同订立过程中与合同成立相关的规则需要尽快明确。网络购物平台上的经营者在平台进行商品信息发布的意思表示行为,其性质为要约,还是要约引诱?订单确认信的法律性质为承诺,还是事实通知?网络购物平台上的经营者对其发送的订单确认信的法律效力进行限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这些问题均需要尽快解决。如前所述,我国台湾地区无论学说还是判例,对于网络购物平台上的商品信息发布的法律性质,欠缺统一认识。日本的相关规则将其直接确定为要约引诱。我国大陆学者倾向于将其认定为要约,实务部门似乎更认同其为要约引诱。对于订单确认信,我国实务部门倾向于将其认定为承诺,且似乎更进一步地拒绝承认订单确认信中的效力限制性语句的限制性法律效力,但学者们更倾向于将其认定为事实通知。将来无论是通过法律修订,还是通过司法解释对网络购物平台上的经营者发布商品信息的行为及订单确认信进行法律定性,均应从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出发。
2.网络购物平台上的商品信息发布,出现标价错误,发布者如无过失,可以撤销网络购物合同。但是目前,我国亟需做的事情,是以错误规则全面取代“重大误解”规则,将标价错误归入到表示错误之中,为此类错误意思表示提供明晰的制度平台和一般性规则。
3. 无过失的网络购物平台上的经营者,可以标价错误为由撤销其与消费者订立的网络购物合同。但是,由于我国《合同法》第58条缔约过失责任规则的存在,此种情形下消费者的信赖利益难以得到保护。虽然学界提出了以信赖责任规则作为消费者权益救济的路径,但是信赖责任目前在我国并无制度基础;再者,即便在德国民法中,信赖责任也未成为一种制定法上的独立民事责任类型;大陆法系的其它国家或者地区,也鲜有提及以信赖责任取代缔约过失的。总而言之,依大陆法的固有传统,在不对缔约过失责任规则进行切割的前提下,基于德国民法传统的可变的缔约过失责任体系应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等. 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514.
[2]陈忠五.学林分科六法——民法[M]. 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1:121.
[3]王泽鉴.债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157.
[4]林丽真. 网路交易标价错误之契约法律问题探讨[J]. 东吴法律学报, 2012(4):1-26.
[5]郭戎晋.购物网站价格标示错误[J].台北大学法学论丛, 2010(76):1-42.
[6]黄茂荣.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65.
[7]杨其康.网路交易标价错误之分析——以我国与日本之法律见解为中心[D].台北:中原大学,2011:92.
[8]周洪政.网络时代电子要约和承诺的特殊法律问题研究[J].清华法学,2012(4):162-176.
[9]姚迪迪.对网络零售交易中意思表示的界定——以淘宝网为例[J].肇庆学院学报,2013(3).
[10]张瑞星.网路购物机制之徽调——从购物网站标价错误之数件判决谈起[J].台湾地区智慧财产评论,2011(1):1-41.
[11]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12-113.
[12]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83.
[13]郑玉波.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47.
[14]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71.
[15]林诚二.民法总则(下)[M].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86.
[16]杨桢.英美契约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03-204.
[17]Ewan McKendrick. Contrack Law:4th edition[M]. Palgrave Macmillan Ltd.,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80.
[18]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55.
[19]崔建远.民法总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52.
[20]朱广新.信赖责任研究——以契约之缔结为分析对象[M].北京:法律出版社版,2007:295-297.
[21]梅伟.合同因错误而撤销的信赖赔偿责任[J].现代法学,2006(3):74-82.
[22]丁南.信赖保护与法律行为的强制有效——兼论信赖利益赔偿与权利表见责任之比较[J].现代法学,2004(1) :70-74.
[23]涂咏松.信赖赔偿责任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9:113-114.
[24]朱广新.意思表示错误之撤销与相对人的信赖保护[J].法律科学,2006(4):114-120.
[25]刘春堂.缔约过失之研究[D].台北:台湾大学,1983:52.
[26]齐晓辊.德国新、旧债法比较研究——观念的转变和立法技术的提升[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43.
[27]杜景林.德国新债法总则新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8,65-66.
[28]朱广新.合同法总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96.
[29]孙鹏.民法上信赖保护制度及其法的构成——在静的安全与交易安全之间[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7):7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