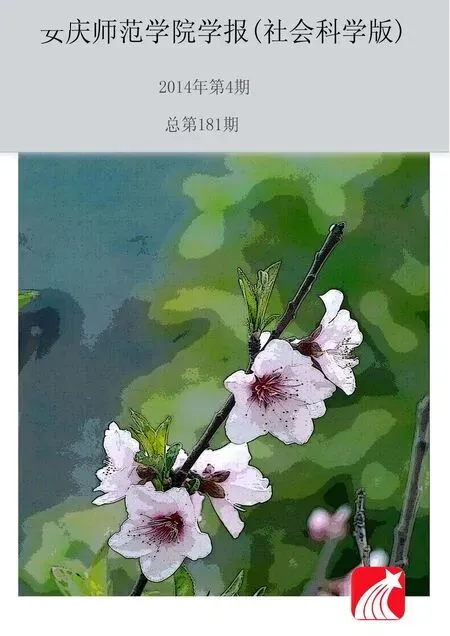启蒙文学思想的建构与影响
——重读《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
2014-03-21刘人梦
刘 人 梦
(安徽大学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启蒙文学思想的建构与影响
——重读《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
刘 人 梦
(安徽大学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中西文化碰撞的“五四”启蒙思想是现代文学思想的开端。“人的文学”和“为人生”是启蒙思想的两个要素。这两种现代文学观念的主要倡导者也是文学革命的先驱,他们将二者以文学史的方式确认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中。载于《大系》中的启蒙思想于当今文学仍有不可言弃的重要意义。
启蒙思想;中国新文学大系;人的文学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下简称《大系》)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该书是由茅盾、鲁迅、胡适、周作人等文学大家共同选编而成,按文体分为10卷。每集之前附有编者撰写的长篇《导言》。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蔡元培称其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1917-1927这十年间的许多作家作品都有着非凡的历史价值,“良友图书公司的‘新文学大系’的计划正是要替这个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做第一次的史料大结集”[1]。《大系》不仅是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成果进行史料性的编辑,而且也是先驱者自我审视性的总结。
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对文学的意义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人的文学”,即个人本位为核心的人的解放。表现在对人性的尊重,对健全人格的肯定,对个性自由的倡导。二是文学“为人生”观。这种观点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问题,提倡人性与社会性融合,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更加强调作家作品的时代性及社会责任感。王达敏先生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解释了这两种文学观:“‘人的文学’接受的是日本新村主义的人道主义,‘为人生’接受的主要是俄罗斯版本的人道主义,即博爱主义的人道主义。”[2]这两种文学观是五四时期文学启蒙的两面旗帜,也使新文学从思想内容上与传统文学区分开来。它们犹如两条奔腾呼啸的江水融入启蒙思想的汪洋。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启蒙思想有所中断,但其意义在今天仍被肯定,不少学者认为当今文学仍需启蒙。《大系》中的编者大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也是在中国最早建构这两种文学观的先驱者。他们在大系的编选过程中渗透了自身的意识观念。站在不同立场,持有不同观点的编者对于这两种文学观的阐述也各有侧重,这在大系及导言中也有所体现。
一
新文学运动也是文学革命,其意义在于对旧文学的破坏和建立新的文学理论。《建设理论集》的编者胡适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中心理论总结为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这两个概念包含了新文学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目标。胡适倡导语言革命即白话文写作,在文学内容的改革上他主张易卜生“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认为摧残个人的个性,钳制个人的自由发展,这是社会的最大罪恶。胡适主张个人要有自由意志,个人要有选择的权利,只有独立自由的人,才能铸造社会国家独立自由的人格,这也是国家的希望之所在。又如周作人《人的文学》中所提倡的人道主义,“我所说的人道主义没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后来将博爱主义与个人主义结合起来,更加完善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郁达夫在《散文二集》导言中表达了自己对“个人”发现的肯定。“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以着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五四是发现“人”的时代,“人的觉醒”、“人的发现”都是这一时代的呼声。茅盾曾这样概括“五四”时期:“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艺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向着这个目标。”[3]个人从传统的三纲五常中解放出来,开始关注人性的自由。
“人的文学”的文学思想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导思想之一,并且对国人的思想启蒙有着历史性的开拓意义。中国传统文学中人是被束缚的,妇女儿童不被看作是有健全人格的人,“君权”、“父权”、“夫权”将人的自然本性压抑,人的发展得不到重视,人存在的意义更多是为权力阶级服务。马尔库塞将此解释为现实原则,即在人的发展中(无论是在属的发展中—属系的发生史中—还是在个体的发展中—个体发生史中)快乐原则被现实原则替代,这是一个巨大的创伤事件[4]。新文学重视个人的独立自由,这受到了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人”的发现与诉求的影响,与西方宗教禁锢相似,人性的压抑在我国封建社会凸显,中西方都需要“人”的发现与解放,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人们经过对自然、自我和人类灵魂的探索,经过人类的自我觉醒和努力,可以战胜无知、迷信、狂热和专制,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正是人和人主体精神的展现。陈独秀“个人本位主义”、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周作人“人间本位主义”都是五四时期提倡个人解放的呼声。人是平等的,平等的享有权利,人们只有先爱自己,以个人本位为前提,才能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人。如果个人的个性得不到解放,人格被损害,那么也将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对个人本位的确认一时间成为五四新文学强有力的呼声。
《大系》分为文学运动、文学理论、文学作品三大板块,文学运动,文学理论影响着文学作品,并被文学作品所反映。这三个部分正是在影响与交错中形成了一种网状结构,而个人本位的文学观念在这个网状结构中不断被确认。《大系·诗集》中具有个人解放意识的诗歌不在少数,“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如郭沫若般大声疾呼,诗歌承载了作者鲜明的自我意识和飞扬的个性,“崇拜我”这样的诗句是诗人们高喊解放自我的口号。《大系·小说三集》选录了的郁达夫的《沉沦》。《沉沦》是一部自我剖析小说,大胆的表现了主人公内心的苦闷与压抑,是个人的反叛精神与苦闷岁月的碰撞。这部小说带有浓厚的抒情和自我表现的色彩,有人说在《沉沦》中,可以看到多层次的“我”的形象:追求肉欲的本我、矛盾的自我、道德的超我。大胆而深刻的自我揭示肯定自我的存在与内心的解放,这种自我解放是具有破坏性的,是爱欲与文明之间的深刻碰撞,是在传统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所没有的,个性解放的“人的文学”是新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重要特征。当然,也不能一味主张跳出社会专注于发展自己的个性,成为一种独善的个人主义,胡适也反对这种个人主义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是避世的,是避开社会的。这就是让步。这便是不奋斗。我们自然不应该提倡‘暴力’,但是非暴力的奋斗是不可少的”[5]。这也是鲁迅在《两地书》中曾提到过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有些启蒙者在后来呈现出衰老的状态,渐渐沉默成“三代以上的古人”,也有人退化成了阻碍新文学继续发展的反叛者,是因为他们局限于个人自由解放而与社会抽离,个人本位主义被混淆为自我的“利己主义”。
二
文学启蒙的另一面旗帜则是“为人生”的文学观。这是先驱们有关文学目的范畴的理解,是与旧文学相对立的。传统文学是封建统治者统治的工具,是儒家圣贤经典的载体,“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使得文学必须为圣贤立言。文学运动的启蒙者提倡文学应该真实的反映社会问题,探求人生的意义。“为人生”可以说是“人的文学”理念的进一步发展,从人的觉醒到自觉地承担社会赋予个人的责任,正如郁达夫所说:“统观新文学内容变革的历程,最初是沿旧文学传统而下,不过从一角新的角度而发见了自然,同时也就发见了个人;接着便是世界潮流的尽量的吸收,结果又发见了社会。”人为了更好的发展而屈从于现实原则,这是人性与社会性的结合,博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社会化。
“为人生”的文学观是《大系》启蒙理念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郑振铎是《文学论争集》的编选者,这集的理论思想明显受到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观影响。他们主张写实主义文学,文学应为反映社会的苦难而作,强调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应更较一般人深切感到国家社会的苦痛与灾难,批判重个人而不重社会的书写个人情感的作品。在序言中郑振铎又对创造社前期的浪漫主义唯美派思想进行反驳,创造社前期思想认为文学是纯艺术的应与功利主义保持距离,文学的意义在于带给创造者以及阅读者美的享受,这也是文学的为艺术派,这一主张与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消遣观在第一个十年的历史语境中是被驳斥的。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中依据文学的目的,将文学分为两派——为艺术派和为人生派。艺术派即注重文学的艺术价值,摒弃其功利价值,提倡作家独抒性灵、发展个性的创作态度,于世无益亦无损。他认为人的文学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是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6]。他所倡导人生的艺术派文学,文学既应注重其自身的艺术价值,但是亦不能脱离人生而孤立的存在。“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持有文学“为人生”观的《大系》编者们认为新文学之所以为新,就在于作家以反映社会现实,同情劳苦大众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茅盾在《小说一集》导言中也表达了对文学社会性的肯定,他也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说:“我们要在现代小说中指出何者是新何者是旧,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看作者对文学所报的态度;旧派把文学看做消遣品,看作游戏之事,看作载道之器,或者看作牟利的商品,新派一位文学是表现人生的,诉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扩大人们的同情的。”[7]茅盾与文学研究会的关系密切,他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问题,讨论与人生相关的主题。并且认为疏远农村和诚实劳动者的创作,是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小小一角,而这显然不是当时实际所需要。茅盾在《小说一集》中所选录的也大多是描写人生,反映问题的小说,如冰心《斯人独憔悴》、《超人》,庐隐的《海滨故人》。这也是由茅盾编选《一集》的范围限于文学研究会的各位小说作家所决定的,也在侧面反映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主张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的影响力。鲁迅也在《小说二集》序言中批评陈德征《编辑余谈》。鲁迅认为“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的‘翩跹回翔’,唱的‘婉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都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时代的呼声唤起了作家的历史沉重感,他们自觉地肩负起启蒙大众的责任,通过作品将五四精神传达。
“为人生”的文学理念是以博爱主义的人道主义为支撑的,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社会的人,社会的发展以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同时个人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的进步,这是人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也是“人的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是以人的发现为前提的。中国的五四时期是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从旧社会发展到新社会的历史时刻,知识分子大多希望借用西方的先进理论对中国国民进行启蒙教育,文学成为他们对付旧社会的投枪匕首。与少数偏安一隅的为艺术派享受着文学带来的精神美感相比,文学的“为人生”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格局。五四的历史语境否认了独抒性灵的抒情主义,没有为“为艺术派”的文学留有太多发展的空间,更多的先驱们投身于解救劳苦大众与探寻人生的意义,人道主义的爱与同情成为引领时代的潮流。梁实秋总结:“当时的现代中国文学‘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和‘人道主义’。”[8]
三
“人的文学”与“为人生”的文学思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思想的构成要素,《大系》被称为历史的参与者对历史的描述,先驱者对自己十年间的文学观进行的自我审视性评论。“人的文学”与“为人生”这两个重要的理论主张彰显了统一主旨下的分歧。毋庸置疑的是这两种文学观念已然成为后世文学的两面旗帜。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与海派文学替代了五四时期的文化思想革命成为两大强势主流。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部分中断了“人的文学”与“为人生”启蒙文学的发展,这也是时代赋予文学的新的使命。但是启蒙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启蒙思想对于作家的影响是融化在血液中的。20世纪30、40年代,胡风的文学理论是五四启蒙思想的回归。“真正艺术上的认识境界只有认识的主体(作者自己)用整个精神活动和对象物发生交涉时候才能达到。所谓交涉,就是主体发挥自己的全部的心理功能,对创作客体进行体验、渗透、选择,形成互相交融的类似化学的化合反应。”这种被命名为“心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对关注人物形象的文化心理现实的“为人生”文学观的传承。另一面胡风又从反封建的战略目标出发,再三强调“个性解放”,突出五四“人的发现”意义。他坚持用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观念去评价各种理论观点,然而这与当时的文化宣传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胡风的失败也代表了五四启蒙思想的再一次中断。五四启蒙思想培养出的作者们不得不舍弃个体命运和具体的生活现象,转而服务于政治,表现宏大题材。而失去了启蒙思想的文学,表现为人的主体思想弱化,不具备自由创作精神并且失去了对人生的独立思考,这样的文学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文革”结束之后启蒙思想迎来又一个春天,当代作家学者也越来越重视它。20世纪“底层”写作也受到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其中蕴含的人性关怀,对广大劳苦大众的同情是“为人生”与 “人的文学”的又一次复归,正如一些学者所说,若干年后我们才心情繁复地发现前进的足迹竟然是一个回归的圆!这是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们自觉承担起文学启蒙的重任。五四启蒙思想赋予作者鲜明的自我意识,即使今天知识分子们不再高呼激扬的口号,“人的文学”与“为人生”的思考已如甘泉般潺潺流入他们体内。
《大系》对第一个十年进行历史性的总结,在这十年间,“人的解放”以及“为人生”的启蒙思想对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并通过编者选择的作家作品以及撰写的序言反映出来。《大系》的影响力使得这两种文学理论观以文学史的方式确认下来。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后来的知识分子践行着“人的文学”与“为人生”的启蒙文学观,这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宗教情怀的缺失,肯定了人的价值,也是启蒙国人爱与同情的人道主义范式。它们如同普罗米修斯盗来的希望之火,是五四时期乃至于当代文学永恒的文学精神。
[1]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1917-1927)[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
[2]王达敏.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3.
[3]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98.
[4]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6.
[5]胡适.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67.
[6]徐鹏序,李广.《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53.
[7]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33.
[8]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李欧梵,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3.
责任编校:汪孔丰
ConstructionandInfluenceoftheEnlightenmentLiterature:ARereadingofGreatSeriesofChineseNewLiteraturefrom1917to1927
LIU Ren-meng
(College of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Anhui, China)
The May 4th enlightenment thought under the colli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mark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literary thought. “Human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for life” are two key elements. Their advocators were also the forerunners of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they confirmed these two concepts in the form of literary history inGreatSeriesofChineseNewLiteraturefrom1917to1927,and the enlightenment thought is significant 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nlightenment thought; great series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human literature
2013-11-28
刘人梦,女,回族,安徽亳州人,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时间:2014-8-28 15:45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40828.1545.026.html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4.026
I206.6
A
1003-4730(2014)04-01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