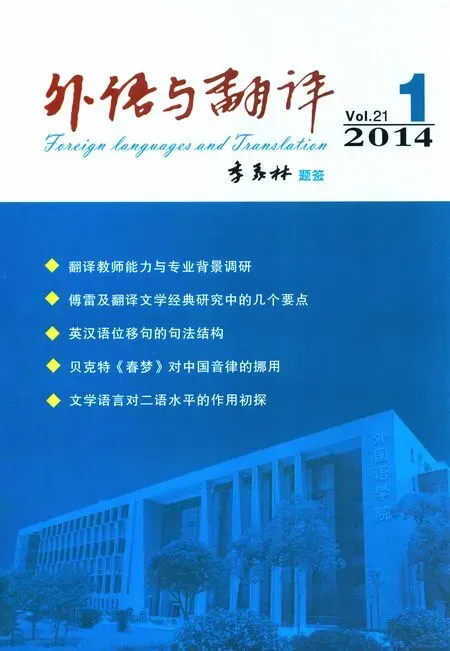论《细雪》中女性形象的病态美
2014-03-21王毓
王毓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225)
“病い”(病)是日本近代文豪谷崎润一郎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符号。谷崎“对疾病的关心,自创作初期至《疯癫老人日记》,从未停歇”。特别是在晚年的长篇巨著《细雪》中,频繁出现各种病名、药名,以及生病、注射和死亡等场景,据统计“与疾病有关的词语共出现了600多次”。《细雪》的英译本翻译家塞登斯蒂卡(Edward George Seidensticker, 1921-2007)更表示,在西欧The Makioka Sisters甚至被评论成“医学小说”。1978年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发表“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以后,出现了许多关于《细雪》中“病”的隐喻的研究成果,对比雪子和妙子在患病方面的差异来揭示她们与制度的关系、在作品中存在的意义等,借此探讨《细雪》中女性形象的问题。
然而,以上研究大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只关注“病”的隐喻的认知功能,而忽略了其审美功能。二是围绕“病”这一符号,妙子与雪子的对照关系往往被界定为“得病/不得病”,这一点也有待探讨。本文将从符号学美学的视角出发,围绕“疾病”与“病态”的隐喻展开论述,分析妙子与雪子的女性形象,探讨《细雪》中病态美的存在样式。
一、受疾病惩罚的妙子
妙子是“最有西洋趣味的”,“性子不偏不倚,适得其中”。“脸圆圆的,五官端正”,“常常是容光焕发”,“肌肉丰满结实”。素日里喜爱穿洋装,个人主张鲜明,通过学习制作布娃娃和裁缝来实现自己经济的独立。她尽管出身世家大族,却对莳冈家过去的繁华荣耀毫不在意,阶级观念也十分淡薄。不但在恋爱关系中经常表现出主动的姿态,甚至还发生过私奔见报的丑闻。作品中有三段妙子的恋爱经历,都伴随着死亡与疾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对妙子身体变化的描写,体现作者谷崎对妙子形象的态度,反映了谷崎在这一阶段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
妙子与板仓的恋爱始于一场大洪水。板仓从洪水中把处在濒死边缘的妙子抢救出来,赢得了妙子的爱恋。而在那之后,妙子的外貌、举止、体态就开始渐渐发生变化。在幸子看来,虽然妙子的言行一向具有现代风格,但“最近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不时表露出毫不检点的不好的言语举动”。她经常只穿一件浴衣在电风扇前吹风,似乎毫不在意在人前坦露自己的身体,有时还“敞着下身盘腿而坐”。洗澡时拉门开着五六寸,从门缝就可以看到她的上半身。幸子还回忆起以前父亲经常说“妙子这丫头最腌臜,一张脸漆黑成一团”。这些关于妙子的描写都让人联想到“性自由” “污秽”与堕落。最终,这个被莳冈家视为“最大问题”的板仓因中耳炎术后感染突然死亡。在其后的恋爱中,就连妙子自己也没能摆脱疾病与死亡的纠缠。
下卷第二十回,妙子感染赤痢卧病在奥畑家中:
病人长期不洗澡,全身腌臜固然不说,身上似乎另有一种不洁的气味。说起来这是一向品行不端的结果,往常可以靠巧妙的化妆掩饰过去,可是在这种身体病弱的时候,她的脸上、脖子上以及手腕上处处都勾画出一种阴暗的甚至可以说是淫猥的阴影来。(中略)她那张松弛的脸上阴沉暗淡的肤色有点像感染上花柳病毒的人的肤色,使人联想到那些下流女人的皮肤。另一方面,对比她身上盖的那条华丽的羽绒被,病人的复杂的不健康就更加显眼了。(下卷 二十)
这段描写虽然是从幸子的视角出发,但反映的却是作者谷崎的审美取向。初登文坛时的谷崎曾经在《刺青》(1910)、《麒麟》(1910)、《恶魔》(1912)、《饶太郎》(1914)、《金色之死》(1914)及《异端者的悲哀》(1917)中表达了对“美丽女人肉体”的渴望,对“性欲解放”的追求。他在《金色之死》中写到:“艺术就是性欲的发现,所谓艺术的快感就是生理官能的快感”,表现出明显的“女体至上”的思想。《痴人之爱》(1924)中的naomi与妙子类似,都是追求恋爱自由的新女性形象。而在《细雪》中,谷崎先后借鹤子、幸子、雪子之口表达了对妙子的厌弃,把妙子看成是莳冈家的“污点”,是“不洁”之物。审美取向的变化可见一斑。
下卷第三十七回,妙子与酒吧男三好的孩子足月,可在临产前妙子尽吐一些古怪黝黑的肮脏东西,分娩时由于院长失手,婴儿终于窒息而死了。妙子的恋爱以婴儿死产收场,似乎这一切都是她自己行为不检点的恶果,是她理应受到的惩罚。至此,一个因追求恋爱自由和经济独立而饱受家族厌弃与疾病折磨的渐失光彩的近代新女性——妙子形象跃然纸上。谷崎借妙子家人和世间非议之口透漏着对妙子的道德批判,借疾病和死亡之痛苦折磨着妙子的身体,把妙子刻画成一个“性自由”的象征,一个时常发病的污秽之物。
在谷崎1955年发表的《恋爱与色情》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这一时期谷崎抛弃妙子的原因。在受西方唯美主义影响创作了一系列妖女形象之后,谷崎逐渐意识到他的创作梦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很难一致的。其一,西方的男人会把女性思慕成“有如圣母玛利亚的形影”,仰之弥高,加以跪拜;而东方却没有这种思想。其二,西方式的姿态美、表情美、步态美在日本女人的身上是无法圆满完成的。在谷崎看来,西方女性达到女性美的极致往往要到三十一二岁,而日本女性只能维持到十八九岁。日本女性的美只能靠华丽的和服和化妆的技巧来装饰。这些都让谷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青年时代所塑造的那些“女神”形象根本就不符合日本女性的本来面貌,就像是做了一场“不着边际的梦”,到后来才发现“此梦难以成真”,唯有感到“无比的凄凉”而已。
二、雪子的病态美
姐妹中最富日本趣味的是雪子,她长着一张“长长的鹅蛋脸,身材苗条”,总是喜欢穿和服。性格上与幸子、妙子不同,雪子为人处事“考虑太多,过分因循守旧”,看上去“总是愁容满面、不胜凄楚的样子”,“怯生生的,怕羞害臊,谈锋又不健”,“沉默寡言是她的老毛病”。虽然雪子堪称莳冈家最健康的人,从不生病,就连照顾疾病中的家人也从不曾被传染,但她体质最弱,肩膀跟悦子差不多粗,“外表简直像个害了肺病的人”。小说一开始就交代莳冈家常备高效维生素注射剂,三姐妹连没什么毛病的时候也互相注射维生素B。雪子和幸子吃饭时筷子一遍又一遍地用开水消毒,掉在桌布上的东西坚决不吃。在贞之助看来,悦子“异常爱干净”的毛病、失眠症、神经衰弱就是幸子和雪子影响的结果。可见,雪子虽然看似与“疾病”绝缘,但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却都表现出明显的病态。
上卷第二十二回,有一段关于雪子身体的描写:
呆在不透气的屋子里,雪子身上难得穿了一件乔其纱的连衣裙。她知道自己这种弱不禁风的身体穿西服不适宜,所以普通的热天她都是穿和服,腰带系得端端正正的;…有时贞之助碰巧看到雪子穿了这身衣服,…看到她那藏青色乔其纱下面瘦削的肩胛和臂膀上寒气逼人的白皮肤,顿时觉得汗都收敛了。她自己当然不知道,可是在旁人眼里,她这种装束无异于一贴清凉剂。(中略)两条坦露的臂膀像剥光了衣服的日本布娃娃…(上卷 二十七)
这段描写突出了雪子身体的两个特点:瘦和白。瘦即柔弱的,白即无垢的。这两点正是雪子与母亲最相似的地方。四姐妹的母亲是明治时代的女子,身材娇小,手脚纤细可爱,“娇嫩优雅的手指活像精巧的工艺品”。无论是性情还是容貌,雪子都被公认是继承母亲优点最多的,在雪子的身上甚至能闻到一种母亲身上才会散发出的幽香。母亲在三十七岁时死于肺病,那时的幸子还只有十五岁。在她的眼里:
母亲生的尽管是肺病,可是直到她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失去某种妩媚。脸色没有变黑,只是白得像透明的一样;身体虽然消瘦,手和脚直到最后都是光润的。(中略)幸子她们看到母亲宁静安详的遗容,竟忘掉了恐惧,生出一种纯洁的感情。悲痛固然悲痛,不过那是超越个人关系、惋惜美好事物离开尘世的一种悲痛,是一种伴有音乐妙味的悲痛。(下卷 八)
莳冈家母亲所患的肺病,其实就是“结核病”。在西欧十八世纪中叶,结核就具有了“引起浪漫主义联想的性格”,是高雅、纤细、感性丰富的标志。《细雪》中几次提到雪子的外表看起来像是害了肺病的人;相亲时被怀疑得了肺病,还特意拍了X光给对方寄去确认;反复强调几姐妹中只有雪子跟母亲最像。这些都给雪子形象赋予了结核病的某种“意义”——柔弱的、敏感的、具有浪漫气质的人。而表现在雪子的身体上,象征着这种意义的符号正是她左眼梢的“シミ”(褐色斑)。这块阴影时隐时现,大多出现在雪子月经前后的那一个星期,医生觉得这是适龄未婚女子常见的生理现象,一结婚马上就会好,或者注射女性激素也能治愈。查阅医疗辞典就可以知道,“シミ”就是肝斑,是一种色素沉淀,多发于女性,起因是荷尔蒙紊乱。细谷博认为“雪子眉梢的シミ象征着她内心的阴翳和不如意,或是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对性的渴望”。这一点从雪子自身的言语举动中也可以窥见一二。时隔两年三个月,雪子迎来了与名古屋富豪泽崎的亲事。这一次,她虽然还是“嗯”“啊”着不明确表态,但幸子总觉得“这个一向自命清高的妹妹心理毕竟感到焦躁,不像过去那样对相亲挑剔得厉害,”而她眉梢的シミ深浅变得毫无规律,以前大致是月经前后颜色深,近来却变得没法预测什么时候深什么时候浅,在白粉的映衬下格外显眼,“就像体温计上的水银柱那样清楚”。(下卷 二)可见,雪子尽管表面上对相亲并非热心,但内心对婚姻却充满渴望。但就雪子而言,“シミ”和结婚似乎是一对矛盾的存在。尽管雪子自己对脸上的这块阴影从未在意,但每逢相亲这块阴影都是幸子心头的隐忧,“シミ”成了雪子结婚的障碍,而设置这个障碍的正是作者谷崎。他一边把雪子描绘成一个优雅美好的“理想女性”,一边又将其投入病态之中使其难以实现真正的幸福生活。シミ出现的原因是对婚姻生活的憧憬,是对性的热望。而另一方面,肺病患者一般的面容、因循守旧的性格、シミ的时隐时现,雪子的这些病态表现又都成为她达成婚姻生活的巨大障碍。可以说,谷崎成功地设置了一道又一道“障碍”(换个角度说是“保护”)把雪子牢牢地锁在一个无性的世界里,尽力地维持着一个纯洁无垢的雪子形象。
三、日本传统与女性病态美
可见,无论是妙子的“疾病”还是雪子的“病态”,都是一种呈现女性形象病态美的手段。女性形象的病态美历来是东方古典文学的传统。中国文学中素有“西施病心”、“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传说,更有“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文本。《西厢记》里的崔莺莺、《牡丹亭》里的杜丽娘、《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无不是典型的“病美人”形象。这一点,日本古典文学也不例外。川端康成把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比作“珍奇藤花”,正是因为它表现了“女性的优雅” “纤细柔弱,彬彬有礼,脉脉多情”,而这也正是“日本美的传统”。(《我在美丽的日本》 1968)《源氏物语》有一种激荡人心的“幽情”,流露出人生不如意的哀感,以及平安贵族行将就木的预感,具有浓厚的纤弱、艳美的官能性色彩。跟《源氏物语》齐名的《枕草子》优雅、绝艳,虽然使人产生一种“往昔徒然消逝”的失落感和淡淡的哀愁,但也“潜流着一股美感”。在日本几百年文学传统的淡淡哀愁中,洋溢着一种优雅、娴静的美,蕴含着深厚的民族古典的神韵。这种神韵在日本这个没有经历过重大质变变革的渐进型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传统的自然美。可以说,谷崎润一郎的《细雪》正是继承了日本的这种美学传统,展现了古典美的遗风。
[1]東郷克美.「細雪」試論——妙子の物語あるいは病気の意味[J].日本文学,34(2):115-118
[2]中村邦夫.谷崎潤一郎の漢字・漢語——『細雪』の用字・用語から[C]//佐藤喜代治.漢字講座9近代文学と漢字.日本东京:明治書院,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