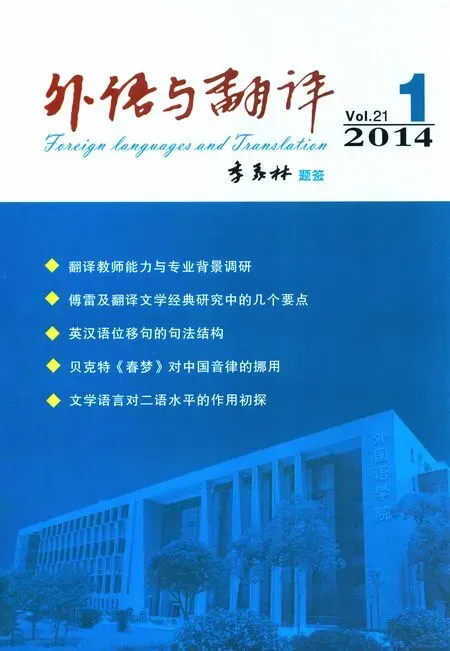从袁了凡事迹看经典注解对人的命运的影响
2014-03-21唐继华
唐继华
(苏州科技学院,江苏苏州,215200)
袁了凡(1533年-1606年),本名袁黄,字坤仪,江苏省吴江人。他的名著《了凡四训》,又名《命自我立》,是一部儒佛两家均非常推崇的经典。该书详细阐述了袁了凡自己的亲身经历,袁以其毕生学问与修养凝练成通俗而意味深长的事迹,其初始目的也许只是在于教戒他的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标准,要求子孙重视改过迁善、行善积德的效用。但是一经问世,即在民间广为流传,形成了独特的劝善效应。通过袁了凡对待命运态度前后的变化,可以看出对传统经典的不同解读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1]。
一、宋明儒学对传统经典的注解是袁了凡认命的理论
袁了凡对待命运前后的变化,以及他采取的更改命运的方法,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其中宋明理学对传统经典注解的影响不容忽视。我们知道,宋代朱熹朱夫子解释古代经典形而上学的“道”,发扬倡导了理学,认为天地之间自有天理流行,一切事物都有其一个理决定了它的存在和发展。按照朱熹的理学模式,很难产生摆脱命运束缚的巨大动力,因为所有学习、实践和修养的根本指向只是为了让人明白这个理而已,这个理既然先天就恒定了,人们对命运自然也就失去了超越的理由。而在人们的实际生存世界中,总是有很多的惊喜和未知等待着我们,吸引我们不断探索,在理先天已定、不可更改的基础上,理学家们以气作为理的对照,努力在现实层面构建一种生活和修养的能动理论。他们认为理虽无可动摇,但气却可以修养。气与理相依相存,理搭于气而动,气动,则理也动。宋儒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比喻来说明理与气之间的关系:理是不可能用眼睛看见的,但是它既然产生作用,就应该能够通过它的作用来认知。理就如同是一个人,气如同一匹马,人骑在马上,人虽然不动,但马走人也随着走,如此一动一静,人就可以推知理与气的奥妙[2]。
朱熹在《太极解义》中把理与气的关系更为清晰地作了表达,他认为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万物各具一太极,他通过这样的方式,阐述了天下虽然只有一个理,但每个人与物却可以得到不同的气,万物所得的气的禀赋不同,从而形成多姿多彩的世界。只是很可惜,朱熹认为每个人得到的仁义礼智信的气都有多寡,对普通人而言,非常直观的影响就是得到恶气的人就是天生恶人,得到善气的人就是天生善人。这也就是命由天定的消极思想,尽管朱熹设计了格物、穷理、积累、贯通等等的功夫操守,力图摒弃恶的人性,回归纯善,但个人修养如何拗得过天所赋予的气和早已命定的理,实在令人迷惘。袁了凡虽然是巧遇异人将其命运推演无遗而实实在在地笃信命运天定,但是不应忘记,有明一代,朱夫子的学术被列为国家考试的标准教材。袁了凡是隆庆四年(1570年)的举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进士,以“高考状元”之才华,对理学思想有深刻的认知,理论与实践相互印证,对袁了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才有了他与金陵云谷禅师对坐三日三夜而不闭眼的故事。
二、云谷禅师对传统经典的解读使袁了凡彻底转变
云谷禅师当时见袁了凡能够坐三天三夜不动,而且没见他生起妄念,觉得非常奇怪,于是便问:“凡人所以不得作圣者,只为妄念相缠耳。汝坐三日,不见起一妄念,何也?”袁了凡就坦言自己的命早已被算定,起不起念头都无所谓,也改不了。云谷禅师笑着对他说:“我还以为你是个豪杰,原来也只是个凡夫。”他引用儒家诗书经典对袁了凡讲:“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又用佛家教典中更为通俗的话来比照:“‘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既然一切能求,那命运就能够改变,诸佛菩萨岂会妄语骗人?”云谷禅师的话在袁了凡心中激起了波浪,他立即以孟子的话回应,他问道:“孟子曾说:‘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他说自己的修养是内在问题,可以自己把握,然而功名富贵都是外在的因素,这个怎么能够改变?从袁了凡引经据典的反应可以看出,他虽读理学对经典的诠释,但也早已对命由天定的理论心中存疑,只需稍作指点,可改天换地[3]。
云谷禅师的回答援引了佛家的理论,他指出正是袁了凡对经典解读错误导致了在人生观上的问题。他说:“孟子之言不错,汝自错解耳。汝不见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求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内外双得,是求有益于得也。若不反躬内省,而徒向外驰求,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内外双失,故无益。”意思非常明白,云谷禅师告诉袁了凡,孟子的话是告诉世人,能否得到外在的功名富贵确实有其偶然性,如果一味追求外在,又不得其道,那么就可能身败名裂。只有常常自省,提高修养,在自我修身的基础上去合理追求外在的名利,才有可能内外双收。一位出家人指点当朝进士(此时虽未高中,但学养自已不薄)儒家四书五经的章句义理,足可见解释的理路正确与否,对传统文化整体精神的把握就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作用。
云谷禅师与袁了凡的对话继续进行下去,渐入高潮。他问袁了凡那个异人如何给他算的命,袁据实相告,称算命的说自己没有高中科举的命,也没有生儿子的命。云谷禅师这才真正展示出禅门接引的大手笔,他反问袁了凡,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能够高中科举、命中得子的料?袁了凡被当头一棒,楞了许久,自己非常自觉地开始反省,怅然说到:“不应也。科第中人,类有福相,余福薄,又不能积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烦剧,不能容人;时或以才智盖人,直心直行,轻言妄谈。凡此皆薄福之相也,岂宜科第哉。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余好洁,宜无子者一;和气能育万物,余善怒,宜无子者二;爱为生生之本,忍为不育之根;余矜惜名节,常不能舍己救人,宜无子者三; 多言耗气,宜无子者四;喜饮铄精,宜无子者五; 好彻夜长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无子者六。其馀过恶尚多,不能悉数。”袁了凡剖析了自己种种缺点,一是自己没有福相,又不去做善事积累功德;二是做事情急躁不耐烦,不能容人;三是自诩聪明过人,常常对人对事妄加评论,这三个缺点就足以证明自己不能高中科举并去当官了。至于能否生子,袁也剖析了自己的毛病,一是眼里揉不进沙子,对人对事过于苛求;二是情绪容易暴躁;三是爱惜羽毛,不能舍己救人;再有就是不懂得保养自己的精气神等等。袁了凡对自己不能得到外在功名事业、无法生子的理由在我们现在看来自然是有些可笑,但云谷禅师并未跟他“讲科学”“摆真理”,而是随即应机施教,先顺其语意肯定了袁了凡这样的说法:“岂惟科第哉。世间享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应饿死者,定是饿死人物;天不过因材而笃,几曾加纤毫意思。”岂止是科举,享用亿万财富的定然是亿万富翁这样的人物,享用百万财富的自然是百万富翁这样的人物,穷得饿死,那也是只能饿死的人。总之是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天是不会给你增减半分的。“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其斩焉无后者,德至薄也。”生儿子也是一样,有什么样的德行,就有什么样的子孙,没有后代子孙的,说明德实在是太薄了。“汝今既知非。将向来不发科第,及不生子之相,尽情改刷;务要积德,务要包荒,务要和爱,务要惜精神。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数;义理之身,岂不能格天。”你现在既然知道了自己错在什么地方,那就针对自己的错误,把它们改正过来,反正是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命,天不会给你增减,那就只能靠自己改正缺点错误,这就能把命转换,如同再生了。云古禅师一下子把袁了凡被动接受天命的态度转化到主动应对自己缺点的现实修养上来。
云谷禅师继续引用儒家经典接引:“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犹可得而违;汝今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为君子谋,趋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趋,凶何可避?开章第一义,便说:汝信得及否?”他没有完全反对袁了凡固有的思想,却接着他的理念讲到天赋予人以性命,提出儒家的经典讲了“天作孽尤可活”,意思是说就算天给了人恶运,也还是有办法改变的,不能改变的反而是人自己作孽。如果能够力行善事,多积累功德,就是自己给自己造福,自己造的福,当然自己可以安心享用,天也抢不走。他还列举了《易经》证明这一观点,《易经》为君子谋划,可以趋利避害,如果天命是不变的,那趋利避害也就是句不可能实现的空话,《易经》就毫无道理可言了。他追问袁了凡,《易经·文言》讲积善之家,必有馀庆,此话你信得过吗?
云谷禅师所引用的都是袁了凡熟稔于胸的儒家经典语句,只是理念、解释一变,效果就完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以说对袁了凡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袁了凡不得不服:“余信其言,拜而受教。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云谷出功过格示余,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善则记数,恶则退除,且教持准提咒,以期必验。”从此袁了凡就走上了行善积德的道路,起心动念无不小心,将自己固有的恶习一一涤除,成功地转变了自己的命运,不仅高中科举、当官发财,而且也子孙满堂、益寿延年。纵使在其死后,他的德行事迹还感化了无数的百姓,令他享誉至今,成为吴地著名的历史人物。
三、从袁了凡的事迹可以看出对经典解读不可不慎
袁了凡读书不可谓不多,云谷禅师所引用的也全都是他从童子功练起、背得滚瓜烂熟的儒家经典,可他却在云谷禅师的三言两语下彻底转变了人生观,可见他接触到的经典注解有多么糟糕。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精髓和源头在先秦,对先秦经典的解读成为后世学者安身立命的学问基石。解读的正确与否,从历史上来看,也很难有定论,否则就不会有一代一代的学者不断地有新的理解。这是传统经典的魅力所在,同时也造成了许多困惑,有些困惑甚至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都造成了影响,从袁了凡身上,我们也可以得出很多信息。例如他与云谷禅师对坐三日三夜而不闭眼,显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受王阳明(1472~1528)心学流弊所影响,讲究静坐存养,追求豁然一悟,而且袁了凡的静坐功夫已然非比寻常。可惜功夫毕竟不是智慧,他自己也意识到枯坐的不利,“好彻夜长坐,而不知葆元毓神”,但此见地也仍旧局限在身体之上,其格局也为意识所囿,尚属小乘。也是云谷禅师慈悲,就其根器授其方法,令一个喜好夸夸其谈、脾气暴躁、又心灵枯萎的人走上了修身养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但大部分人没有袁了凡那样的因缘,清初颜习斋有鉴于明亡教训,痛惜地说:“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与朱熹的理学一样,心学也同样根基于先秦的学问,当代有学者指出,从根本上而言,理学与心学都认同一个道源,其不同处只是属于方法论上的区别。事实上远非如此简单,对道理不明白,当然方法会迷糊,方法迷糊,反过来也说明对道理不明白,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因此,对经典的注解是否有真见地,是否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始终是不变的主题。当代也面临着经典文化诠释的困境,如何真正接续上传统文化的脉络,使传统文化融汇古今东西的文明,特别是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使传统文化以新的面貌深深扎根,需要学者们共同的努力。但是在阐扬经典的同时,不能忘记佛家一字之差,即得五百年野狐身的故事,这还只是个人的因果的一面,自己的问题自己承担。通过袁了凡的故事,更应该明白经典阐释所造成的结果既可以使人活,也可以使人死。权威越大,影响就越深远,那生与死的就不只是某个人了。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袁了凡.了凡四训[M].凤凰出版社,2012.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