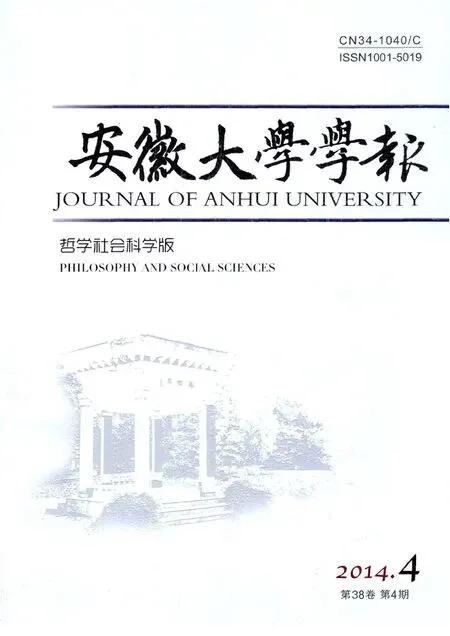徐璈《诗经广诂》考论
2014-03-20许结
许 结
清代嘉、道间《诗经》研究昌盛,皮锡瑞《经学历史》谓“雍、乾以后,古书渐出,经义大明”,称之“经学复兴时代”之中兴阶段①皮锡瑞:《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3页。。这其中包括对《诗经》的辑佚考证与阐发义理之成就。然此阶段不尽同于前贤之《诗》学贡献,要在分派考述而归义会通,并兼括“三家诗”与“毛诗”研究。就“三家诗”辑考而言,虽宋人王应麟《诗考》已肇端绪,然其成就则在清代,即肇始于乾隆间范家相之《三家诗拾遗》②范家相,字蘅洲,浙江会稽人,乾隆进士,官至柳州知府。《四库全书总目》评述范氏《三家诗拾遗》,以为较王应麟《诗考》“详赡远矣”,其与同时人所撰辑,如“严虞惇作《诗经质疑》,内有三家遗说一篇,又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于三家亦均有采掇,论其赅备,亦尚不及是编”。,至嘉、道间出现了诸如仪征阮元《三家诗补遗》,桐城徐璈《诗经广诂》,邵阳魏源《诗古微》,闽县陈寿祺、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以及高邮宋绵初《韩诗内传徵》,吴江迮鹤寿《齐诗翼氏学》等,其中以徐、魏、陈三书最著。而魏源认为“桐城徐璈之《诗经广诂》出,而三家遗文坠义,凡见《春秋》内外传及汉初诸儒所称引,无字句之不搜,而三家《诗》佚文几大备矣”,故自撰《诗古微》则在引申“三家大义微言”③魏源:《诗古微目录书后》,引自《魏源全集》第一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736页。,至晚清王先谦成《诗三家义集疏》,推重陈氏父子,徐氏之说则略有引录。而“毛诗”研究,虽属自汉毛郑以来传统之学,然嘉、道(延及咸丰)间出现的泾县胡承珙之《毛诗后笺》、桐城马瑞辰之《毛诗传笺通释》与长洲陈奂之《诗毛氏传疏》堪称三鼎足,尽管“论者多以陈称最”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北京:中国书店影印版,1985年,第184页。,然《四部备要》辑录清人经解,于《诗》仅取马书,亦可见推崇之意。清代东南学术,桐城名区,不尽在“古文”一途,前揭一时《诗》学之盛,于“三家”则有徐书,于“毛氏”则有马著,然马“显”而徐“微”,现代研马之作,层出不穷,而于徐书,偶或提及⑤例如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九章“清代《三家诗》学重要著作”对《诗经广诂》有简要介绍。另如房瑞丽《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论略》(《北方论丛》2008年第6期),于辑佚中阐发大义举例《诗经广诂》,有简短论述文字。,殊无专论。因献刍言,聊存补阙之义。
一、徐璈与《诗经广诂》
徐璈(1779—1841)字六骧(一作六襄),号樗亭,初号樗尹,室名敬跻堂,安徽桐城人。其先于元朝至正中由婺源迁桐城,十四世祖讳良佐,当元季以进士仕至陕西布政使。父讳之柱,少孤贫,育于外家,既长,辛勤治生,孝友刚介,耕读传家,善闻乡里。徐璈幼秉慧质,于嘉庆十九年(1814)中甲戌榜进士,授户部主事。以母老,改外补浙江寿昌知县,调知临海县。后转官山西阳城六年,有政声,人称“徐阳城”。历主亳州、徽州书院。自少至老,纂述不辍,人服其精博。曾师事姚鼐,受古文法,诗抒性情,尊温雅之旨。著《诗经广诂》三十卷、《牖景录》六卷、《河防类要》六卷、《黄山纪胜》四卷、《樗亭诗文集》若干卷①按: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著录《樗亭文集》四卷,方东树《仪卫轩文集》卷11著录《樗亭诗集》八卷。李灵年等编《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著录有《樗亭诗集》三卷本(原刻本)、四卷本(清刻本)、五卷本(约嘉庆间刻本)、八卷本(道光刻本)。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尚著录有《拾香录》、《七言古诗诵节》、《卧云书屋著录》、《五代史记补注》、《齐民要术注》、《槃园诗话》、《五律椎轮》、《七律讽音》、《词钞》等。。又选辑乡先辈诗成《桐旧集》四十二卷②据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载,《桐旧集》“刊未半而阳城卒”,后由马树华、苏惇元续成。,皆刊行。
《诗经广诂》是徐氏一生最重要的经学著述,也是其学术精粹之书,据书封署名“赐进士出身户部主事浙江临海县知县徐璈撰辑”(书内页署“辑录”)字样,是书当完成于徐氏官临海任上。《广诂》计三十卷,原刻于清道光十年(1830),即《贩书偶记》卷一载“道光十年刊,第二十三卷分上下”③孙殿起:《贩书偶记》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1页。,《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八《经籍考二》有著录,今《续修四库全书》据此本影印④徐璈:《诗经广诂》,《续修四库全书·经类》第69册,景武林任九思刻字本。。对此书治《诗》得失,魏源《诗古微目录书后》赞其搜罗“三家《诗》佚文几大备”,而批评其于三家义“案而不断”,最具代表性。晚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光绪丙子(1876)三月二十二日记:“阅《诗经广诂》……前有道光十年洪氏颐煊序,其书共八册,不分卷,先以序例、纲领及诗家源流,其后自《国风》至《商颂》,依次为说,皆搜辑古义,以为证左而不加论断。凡《春秋》内外传、周秦诸子以至宋明国朝人之说,无不甄录,间亦附注己见。曰《广诂》者,取诗无达诂之义也。”⑤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经部·诗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9页。按:李氏所见是不分卷本,当与道光十年刊本即《续修四库全书》所收非同一个版本。其说虽较详细,然大义仍承魏说。这也决定了当代学者对徐书的整体印象。
评价徐璈编撰《广诂》之本义,在有关徐氏生平著述之史料中,有几处信息值得关注。如《清史列传》将“徐璈”附《包世臣传》,仅寥寥数语,却重点记载了他在京师参与祭祀郑康成的活动:
璈邃于经术,官京师时,与诸名士相切劘。胡承珙公祭郑康成于万柳堂,时同会者朱珔、钱仪吉、魏源、胡培翚、张成孙、陈奂诸人,璈与焉。⑥《清史列传》卷73《文苑传四·包世臣(附徐璈)》,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015~6016页。
关于胡承珙(号墨庄)于京师万柳堂主祭郑北海事,详载胡培翚《汉北海郑公生日祀于万柳堂记》:
(墨庄)作启相与徵同志十余人祀之于万柳堂(堂为元廉希宪别墅,后舍为寺,国初鸿博诸君曾寓此)。是日也,宿雨初霁,天高景澄,而兹堂又僻处都城之东南隅,车辙罕至,尘嚣远隔。同人再拜礼成,登楼凝望,怀古思旧,酌蔬赋诗而退。属余记之,时嘉庆甲戌岁也。
这次参加祀游活动的有胡承珙、胡培翚、郝懿行、朱珔、马瑞辰、徐璈等十余人。而在此记文后胡培翚复作《又记》:
己卯岁七月初五日复祀于万柳堂,同祀者元和蒋香度廷恩、新城陈石士用光、嘉兴钱衎石仪吉、桐城光栗原聪谐、长洲陈硕甫奂、崇明陈辛伯兆熊、鹤山冯晋鱼启蓁、邵阳魏默深源、武进张彦惟成孙,暨朱兰坡、胡墨庄、徐樗亭与余。⑦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8,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泾川书院刻本。
据此可知万柳堂公祭郑北海活动主办两次,其间相隔五年,分别是甲戌(嘉庆十九年,1814)与己卯(嘉庆二十四年,1819)岁,《清史列传》所载当属己卯岁公祭事。观两次公祭活动,均参加者计四人,即胡承珙、胡培翚、朱珔与徐璈。第一次公祭正当徐氏中进士岁,第二次当于其户部主事任上,正因其两度参与胡承珙招邀之祀郑活动,近人《清儒学案》将徐氏归于胡承珙名下的《墨庄学案》⑧徐世昌等编《清儒学案》卷138《墨庄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472页。,这既是他在京师与《诗》学之结缘,也是其以《诗经广诂》为代表性成就之学术标识。
如果集合两次参加万柳堂祀郑活动的人员,就能发现嘉、道间东南(其时学术以东南为主)治《诗》卓然成就之大家多预其间,包括治《毛诗》三大家胡承珙、马瑞辰、陈奂,治“三家诗”相承而出成果的徐璈与魏源。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京师万柳堂祀郑活动,作为史实宜为嘉、道《诗》学研究之大事,其以文会友及志同道合的心志,为一时《诗》学研究的昌盛起了奠基或推波助澜之作用,徐氏两预其间,是有意义的。其二,尽管参与活动之人员治《诗》观点不同,其所存成果亦多批评或补正《毛传》与《郑笺》者,但其在郑玄生日举行“祀郑”礼仪,“致芹藻之敬”(胡培翚语),表达的是对治《诗》先贤之礼敬和对学术之崇敬,这也可见嘉、道间治《诗》不偏一隅之学风,徐氏治《诗》精神亦然。其三,后世学者研究嘉、道间《诗》学,为便于整理与考述,往往划分出“毛郑派”、“今文(三家)派”等等①例如陈国安《清代“诗经学”流派述略》即分有“毛郑派”、“朱传派”、“兼采派”、“小学派”、“史学派”、“文献派”、“文学派”、“今文派”等,文载《南阳师院学报》2005年第11期。,其方法与思路无可厚非,然回到历史语境,万柳堂祀游活动作为一学术标识,其参与人员及其所存著述,或主“毛郑”,或明“三家”,而相融相契,并无扞格,体现了当时会通学风,读徐氏《广诂》当作如是观。
另一则值得关注的史料是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记述徐璈官山西阳城时之政绩:
调山西阳城。蝗大起,民畏蝗以为神,因取食蝗示无畏,民乃敢捕蝗扑灭。修葺文庙,依古制笾豆、琴瑟之属,以乐章协宫商歌焉。居阳城六年,引疾归,民立祠祀之。行事率胸臆,不能伺应颜色。喜求民隐,与长官争是非。尝曰:“性不随时,才不周务,不堪世用也。”因自号“樗尹”云。②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10《姚总宪、光布政、徐阳城传第百七》,毛伯舟点注本,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385页。
这段文字,从关心民生、倡导礼义、为人真率三方面介绍了徐璈为官阳城时之政绩,其实这也是徐氏由京城到浙江再到山西为官的一贯作风,其中关键在经世致用思想。由为人看为学,徐璈学问与著述,无不有用而为,这一方针始终贯彻其《广诂》的编撰。《清史列传》称赞徐璈自为诗“惩卤莽、流易二弊,性情所抒,时有超诣。端木国瑚谓其有得于《葩经》温雅之旨”,是就其以《诗》学理论指导其创作而言;至于家居临海徐氏主政之地的洪颐煊《诗经广诂序》在称颂徐书“从千百年后收集散亡,凡古言古字,片言单辞,靡不穷源探委,以期有裨于兴观群怨之旨,厥功甚伟”后,笔锋一转而谓其为官“有惠政,记有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知其得力于经义者深矣”③徐璈《诗经广诂》卷首。按:洪序撰于道光十年,其序首开篇即谓“桐城徐樗亭先生宰临海之明年,一日出所撰《诗经广诂》一编以示颐煊,颐煊受而读之”,知其时徐氏正在临海任上,而书亦成于此时。。以“惠政”印证“诗教”,或谓“以经学润色吏治”④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8《经籍考二》转述洪序评《广诂》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029页。,这又是对徐氏经世致用《诗》学观的另一种解读。
在有关徐璈生平记述中,还有一突出现象,就是他为官时既“开山种地”以励农,亦“兴学院”以倡学,辞官归隐,又从教兴学,历主亳州、徽州书院教职。这既是徐氏人生兴致所在,也是其耕读传家之统绪。综观清代桐城学人,有为官与教学两途,然多终归教学之业,而教学者或主讲书院(如姚鼐),或设馆家塾(如方东树),淡泊官位利禄,诚其表征。徐璈师事姚鼐,其师曾愤辞“四库馆”,归返东南主讲众书院,徐氏为官亦“不能伺应颜色”,从容官场,这也是其辞官从教的一大原因。而从其为官兴办书院到辞官主讲书院来看,徐氏《广诂》之编纂当与教学有关,其资料性(广泛辑录大量文献)、系统性(先纲领、源流,后逐类逐篇辑考)与每有引述必明出处的方法,均可视为一《诗》学“教本”,这也与其经世致用思想潜孚默契。
二、从桐城诗经学看《诗经广诂》
倘将桐城学术囿于古文流派,则徐璈虽曾师事姚鼐习诗文,但因没有什么显著的古文成就以及相关之批评论点,似乎算不上“桐城派”中人;如果不局限于古文,而将桐城学术作为区域现象之存在加以审视,或视为东南学术(甚或“南学”)⑤王葆心《古文词通义》卷15论桐城派云:“论文于今日,南方居其极盛。自程鱼门、周书昌发为天下文章在桐城之言,世人类以桐城派称南方之文。然隘以桐城之称,不如竟称以南派为得其真。”,其中包括经史传统与诗文之学,则徐璈虽多年官历京师与地方,然其学术与桐城之关系,则不可断割,这也包括《广诂》之编。
前揭京师万柳堂公祭郑玄活动,为数不多的人中就有三位桐城人,即徐璈、马瑞辰与光聪谐⑥光聪谐,字律原,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选庶吉士。曾任职刑部主事,迁郎中,官福建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等。著《稼墨轩诗文集》十二卷、《笔记》十卷、《〈易〉图说》一卷等,尝搜集乡先辈撰著百数十种,成《龙眠丛书》,未刊行。按: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将其与徐璈合传。,而其参与者新城陈用光亦同为姚鼐弟子。假如说这仅是偶然现象或外在表现,那么通过徐氏《广诂》之引述,则可窥探其与桐城学术之内在关联。据徐氏书前洪颐煊题序所言,其主要选录唐前典籍,而“其有诗义未尽者,复引宋、元、明诸家之说以补之”。徐氏于书前《例言》“宋元至本朝”条,则列举有清中叶以前治诗学者如李樗、黄櫄、钱澄之、陈启源、姜炳章、惠栋等著述,以为资鉴,然却自谓“鲁目力有限,挂脱仍多”⑦洪序与徐氏《例言》均引自道光十年刻本《诗经广诂》卷首。。其实仅就清代而言,徐氏《例言》乃举要之说,书中引述广泛,绝非仅此。其中引述重要学者言说,除了前述数家,尚有如李光地、毛奇龄、范家相、阎若璩、全祖望、齐如南、惠周惕、惠士奇、戴震、毕沅、汪中、卢文弨、王念孙、王引之、孔广森、段玉裁、洪亮吉、郝懿行、程瑶田、汪师韩、赵翼、李兆洛、臧琳、江永、阮元、洪颐煊、魏源等。而在引述清人论述中,还有一突出现象,即书中考证,大量引述桐城前贤之论,除前列钱澄之,还多处引录方苞、姚范、姚鼐、叶酉等桐城名家的见解,以为己说佐证。
在桐城诸家中,徐氏引述钱澄之《田间诗学》内容最多,约有二十余处。考钱氏《诗》学,其自谓引毛、郑、孔“三家书”与“朱传”为多,且论诗依《小序》立说,属毛诗学派,与徐璈主引“三家诗”迥异,然后者引述前者文字至多,且取资接受,这一则说明徐氏广资博取,一则可见其于乡梓文献的关注。略举《诗经广诂》引“钱说”一例如次:
钱澄之曰:“卫人之妻能以礼谏其夫,是《卫风》当文公时。”(卷四《国风·鄘·相鼠》)
结按:此解《相鼠》三章引班固《白虎通》“此妻谏夫之诗”,复引王应麟《诗考》谓班氏“亦齐、鲁、韩之说”,故以钱氏言《卫风》旁证之。
上引钱说,主解诗义,自属《诗经学》范畴,而徐氏引述桐城诸家之说,或明诗义,或资考评,很大程度在表明作者对桐城学者文献之熟悉与利用。试举诸家之说数例:
方苞曰:“《采薇》、《出车》、《杕杜》三诗,所谓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帅殷之畔国以事纣,其明徵也。”(卷十六《小雅·鹿鸣之什》)①此文引自方苞《朱子诗义补正》卷4《小雅·鹿鸣之什》之《采薇》题下。按:方氏原文为:“《采薇》、《出车》、《杕杜》,序以为皆文王之诗……孔子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三诗及《春秋传》文王帅殷之畔国以事纣,乃其明徵也。”
结按:此解《出车》六章,徐氏先引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与班固《汉书·匈奴列传》引《诗》,征之范家相说,以为马、班皆“本于三家”,而复引杜预《左传·闵公元年注》参证史事,故引方苞说以明义。
此引方苞《朱子诗义补正》语,以明诗之本事,属直解《诗》例。他如诂解《诗·小雅·正月》十三章中“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句,徐氏引方苞语:“《传》引《诗》谓小人黩货无厌,以私厚其姻党,姻党必盛有所称述也。”(卷十九)则属解释书中所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文,乃引申诂训例。至于桐城二姚(范、鼐)一叶(酉)之说,如:
姚范曰:“《隋书·何妥传》:‘莫不用短,即便夸毗,选射名誉,厚相诬罔。’是夸大毗附之意,不与毛、郑同也。”(卷二十四《大雅·生民之什》)
结按:此解《大雅·板》之“天之方,无为夸毗”之“夸毗”词义,徐书引姚范说以辨明《隋书》所用与毛、郑传笺的不同。
姚鼐曰:“宣王建都,君子攸芊。其时民亦从而徙宅,百堵皆作。《鸿雁》咏焉。”(卷十八《小雅·鸿雁之什》)
结按:此解《小雅·鸿雁》“百堵皆作”句,徐书引“韩诗说”,以姚说证诗句本事。
叶酉曰:“卫宣尝与齐僖胥命于蒲,故黎人以方伯连帅之事望之。”(卷三《国风·邶·旄邱》)
结按:此解《邶风·旄邱》“裒如充耳”句,徐书引《释文》解“裒”字义,复引叶说兼明《诗》义。
略举三例,或解词义,或论本事,与《诗》之本义或诂解之意并无太大关联,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徐璈书中较多地引录桐城学者论述,当与其积学和偏嗜有关,当然这也可以说明他对桐城“《诗经》学”传统之认同。
清代桐城《诗经》之学,肇端于钱澄之《田间诗学》,其后桐城派中人无不以经史立学,其文集中对《诗》学研讨不乏精到论述,例如方苞的《读二南》、《读齐风》、《书周颂清庙后》、姚鼐《关雎说》、《斯干说》等。论其专书,继钱著则主要有方苞《朱子诗义补正》②方书由门人单作哲编次,计八卷,存《续修四库全书》经部“诗类”第62册。、叶酉《诗经拾遗》③叶书存《四库全书存目》经部“诗类”第79册,计十六卷。按:《清朝文献通考》著录十三卷。、马宗琏《毛郑诗训诂考证》④马书《桐城耆旧传》卷10《马鲁陈先生传第百三》有著录,并谓所著书“多散佚,鲜有传本”。、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徐璈《诗经广诂》、许畹《古邠诗义》⑤许书《贩书偶记》著录无卷数,有道光十二年(1832)刊本、同治六年(1867)重刊本。同治本署名“许宗寅撰”。、吴嘉宾《诗说》、吴德旋《诗经集注拾遗》、刘开《诗经补传》、侯桢《诗经笺雅》、方宗诚《诗传补义》、赵衡《毛诗考订》、马其昶《诗毛氏学》以及吴闿生的《诗义会通》⑥以上书目均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按:刘书署录吴闿生书名曰《诗经大义》。马其昶书三十卷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经部“诗类”第74册。等。在桐城诗学中,继钱澄之、方苞、叶酉三家之后,成就最突出的就是嘉、道间同时完成的马氏父子(宗琏、瑞辰)与徐璈的著述,并由此形成两大统绪:
一是由马宗琏父子到马其昶的《诗毛氏学》,形成颇有特色之桐城马氏“毛诗”学。对此,马其昶于《桐城耆旧传》记述马瑞辰学术传承时云:“先生少传父业,为训诂之学。尝谓《诗》自齐、鲁、韩,三家既亡,说《诗》者以毛、郑为最古。……于是撰《毛诗传笺通释》。”所谓“传父业”,指的就是马宗琏之《毛郑诗训诂考证》。也正因前述与马瑞辰书同出有胡承珙、陈奂的《毛诗》著述,且学者多以陈书为著,所以马其昶的《诗毛氏学》一则针对“陈氏奂《毛氏疏》始一廓清之,有功于毛诗矣。然所疏者类偏于训诂,大义未能全发也”,一则又“于诗笃信小序而主毛传”①马其昶《诗毛氏学》卷首姚永概《序》。,以承续乡先贤钱澄之、方苞的《诗》学观,试图完善其“毛诗学”体系。
另一统绪就是标著“三家”,以辑佚训诂为主,兼及义理,为桐城《诗》学中不拘守毛、郑之学开一新境,徐璈之书正为其代表。虽然,徐书以辑录众说为主,以致魏源在肯定其辑佚成就时,批评其于义理则“案而不断”,刘锦藻等编撰《清朝续文献通考》时也以马瑞辰书与徐著比较,表彰马氏“非若徐璈之《诗经广诂》案而不断”②刘锦藻等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8《经籍二》。。其实,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徐书中大量的“按”语或“璈按”③徐璈《诗经广诂》中的“按”语多叙述前说,以明源流与出处;“璈按”则综会众说,时出己见。,就会看到“案而不断”也是苛全之责,徐书隐含于大量文献辑佚中之评点,是不乏批评思想的。而徐氏以三家为主,兼采《毛诗》的补遗方法与广博视野,于某种意义也是上承叶酉《诗经拾遗》综会四家之说,而下启吴闿生之《诗义会通》撰述思想的。
刘师培在《经学教科书》中论“近儒《诗》学”,即首列《田间诗学》,于中对马瑞辰书之“精博”亦有褒词④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三十二课“近儒之诗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85页。,然此仅撮要而言,较为宽泛。若勘求一区域之学,如桐城《诗》学,就丰富多彩,其中如钱澄之重“小序”,方苞补“朱传”,马氏彰“毛传”,徐璈辑“三家”,吴闿生主“会通”等,各具特色,归纳其要,则又可分为前揭或论“毛诗”,或辑“三家”之两大统绪。但桐城《诗》学尤重会通,所以治“毛诗”者如马瑞辰也是“以三家辨其异同,以全经明其义例”(马其昶语),治“三家诗”者如徐璈更是多引“毛传”,甚至兼及四部以证义例。同时,桐城学术重义理,故其治《诗》最重经世致用之学;桐城学人尊古文“义法”,于《诗》亦重解释章句,这在徐璈《广诂》中均有所昭示。
三、《诗》主“三家”之辑考
自汉肇《诗经》之学,立博士学官,故而有今、古学之争⑤按:钱穆认为两汉今古文无争,争在今古学,缘自立博士学官之故,信然。参见氏著《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作为“三家”之今学,由兴盛而衰微,从后汉到唐、宋,《诗》之义理,尽归古学之《毛诗》,然由宋到清诸家发覆“三家”,于理无徵,学力尽归于辑考。缘此,近人刘师培平议清代《诗》学,大赞戴震、段玉裁、马瑞辰、胡承珙书“精博”,尤其赞美陈奂之作乃“集众学之大成”,却批评“三家”学者陈乔枞等“单词碎义,弗克成一家之言”,即如颇重义理的魏源《诗古微》,亦谓之“择说至淆”⑥前揭刘师培《经学教课书》第三十二课“近代之诗学”。。缘此,今人论述清代今文《诗》学成绩,则首在广辑佚文、考证家数、比较异同,钩稽遗说,然后方能阐申大义⑦洪湛侯:《诗经学史》第十章“清代今文《诗》学研究的方法与业绩”,第608~621页。,徐璈《广诂》主“三家”之辑考成绩,也最为明显。
据徐书《例言》自述,“三家诗”辑考首功是王应麟《诗考》⑧按:《四库全书总目》王应麟《诗考》“提要”称“三家诗”学“筚路蓝缕,终当以应麟为首庸”。,至清人范家相蔚然有成,而自为《广诂》,较前人则增益“十之六七”,其义理“或与毛、卫异趣,或与郑、孔殊途,或韩、鲁已有主名,或申齐未著明证”,皆为辨析,故被人称为辑考三家之“发挥型”著述⑨详前揭房瑞丽《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论略》,称徐书为“辑佚发挥型”。。其实所谓发挥,一在引述材料广博,一在书中“按语”之考述性质,而就徐氏自称“增益”情况来看,其发挥也是建立在对前人成果之增补与校注。虽然徐氏于《例言》中自谦“颜曰广诂,取诸昔人诗无达诂之义,庶以备解颐者之一隅”,然观其辑考成绩,则以其“广”而构建其宏整体系。概述其要,则有三端:
一曰“明源流”。在徐书中,《诗》主“三家”而不专于此,而以历史眼光观觇其《诗》学之流变与发展,表现了为“训诂”而不专于此的广博特征。认识《广诂》对《诗》学(尤其是三家)源流之考察,可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寻绎。就宏观言,徐书首列《诗诂纲领》,次列《诗家源流》,虽属材料的整理,然显然皆明源流之旨意。如其《纲领》,徐氏依时序共辑录自战国迄唐人论《诗》言说五十则,引述人物及典籍有荀子、庄子、《诗纬·含神雾》、陆贾、董仲舒、扬雄、刘向、《淮南子》、司马迁、刘歆、翼奉、龚遂、王褒、班固、郑兴、赵岐、王逸、魏文帝、杜预、袁宏、挚虞、左思、傅咸、苏子⑩徐氏自注:苏子曰引自《御览》六百二十九。并云:“苏子未详何时人,附著于此。”、杨泉、刘勰、萧子云、颜之推、王通、薛收、徐坚、刘知几、成伯玙、贾公彦、郑覃等,俨然而为一先唐《诗》论史料汇编。倘细察其义,从徐氏选辑诸家论述内容,亦可见他对《诗》学源流的几点态度:其一,首列《荀子·大略篇》“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之论,结合后引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篇》之“《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可知编者为《诗》学留有广大的解释空间,这也成为徐著主要特征之一。其二,辑录止于唐代而不收宋元以后论《诗》文献,要在徐氏认为自东汉“三家”衰微,至唐迨为“绝响”①《诗经广诂·例言》,《续修四库全书》本“经部”第69册,第365页。按:以下引述仅在文中注明页数。,而宋元以后诸家之说虽可补益,且多引证,然皆支离琐碎,其中也包含了自己重光“三家”的责任与抱负。其三,引述并重三家,不列《毛诗》及相关评论,此明徐书主“三家”之原则,然旁涉文史著作,亦有会通之义。其四,此中多引文学批评家及著述言论,如挚虞《文章流别》、左思《三都赋序》、刘勰《文心雕龙》之论,传承作为古学之《周礼》“六诗”之说②《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及《毛诗序》“六义”之论③《毛诗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既可见徐氏主“三家”而不固守,于《诗》持有共源会流的观点,又显示出他以文学解“经”之思想,这又与桐城文脉相关。
相对而言,徐书次列之《诗家源流》虽无新意,但却为“四家”《诗》传授特立之师承学谱,为书中具体引证文献起纲领作用。徐氏按鲁、齐、韩、毛“四家”序列,《鲁诗》自浮邱伯至蔡朗计五十家,《齐诗》自辕固生至陈纪计十八家,《韩诗》自韩婴至梁景计四十二家,《毛诗》自毛公至鲁世达计四十四家,皆援引史料为“注”,宏整可观。其后晚清人唐晏撰《两汉三国学案》,标列《诗》学传授谱系,较徐书似详④按: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5、卷6分列《鲁诗》五十九家,《齐诗》二十五家,《韩诗》五十五家,《毛诗》三十八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1~322页。,然其内容多同,梳理之功见于传承之间。观徐书所列《诗》家源流,以征引史料为主,却也不乏述义,例如关于刘向、歆父子归属《鲁诗》,出于《汉书·楚元王传》“少弟与申公俱受《诗》于浮邱伯,申公为《诗传》,元王亦次之”语,而向、歆为元王宗嫡,当无疑义,然徐氏仍有按语曰:“向、歆本传皆不言习鲁诗,然汉人皆世守其学,故后之称向、歆说者,俱以为鲁诗也。”(369页下)这也许就是魏源等人批评徐璈的“案而不断”类例,其实这正是徐氏引史述经的圆通之处。
就微观而言,其明源流的思想主要体现于《广诂》解《诗》之文本,这又根据徐书的体例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总类”解诂,如《国风》;二是“分类”解诂,如《周南》;三是“诗题”解诂,如《关雎》;四是“诗句”解诂(句解),如“关关雎鸠”等。以此为例,如解《国风》,徐氏引《乐记》、荀子、匡衡、何休、柳冕诸说,以明“风”义及因“风”观“志”之用,此则虽引述内容不多,却由战国至唐代,已提挈出“三家”论“风”之源流。又如解《周南》,徐氏引《孔丛子》、《吕氏春秋》、《韩诗叙》、匡衡、郑玄、郦道元、张晏、司马贞诸说,以明其地理方位、南音特征及讽诵之用等,又复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观于周乐,为之歌《周南》、《召南》”事,阐明观乐明教之义,引《魏书·儒林传》“梁武帝问于李业兴曰”一段,以资考证。虽然其间并无徐氏按语考辨,然史料之排列与出处之注明,已清晰地展示了解诂《周南》研究源流的要点。当然,引史料而参以“按语”,更能体现徐氏书中明“三家”源流的思想,这在“题解”、“句解”中尤多,并与博引证特点相契合。
二曰“博引证”。如前所揭,洪颐煊《诗经广诂序》称赞徐书“从千百年后收集散亡,凡古言古字,片语单辞,靡不穷源探委,以期有裨于兴观群怨之旨,厥功甚伟”,所言“厥功”,要在“穷源探委”,即广博征引以证其义。观徐书之博引证,较为突出地表现于解诂“诗题”与“诗句”方面。先看解诂“诗题”之引证。再以《关雎》为例,徐书首引“鲁诗曰”以明其题义:
鲁诗曰:“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璈注:《汉书》杜钦疏曰:佩玉晏鸣,《关雎》叹之。臣瓒曰:此鲁诗也。李奇注引鲁诗云云。《后汉书》注并同。(375页上)
继此徐氏复引《列女传》、“杨赐曰”两则以证其义,尤其是引袁崧《后汉灵帝纪》载杨赐解《关雎》说⑤袁崧《后汉灵帝纪》引杨赐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雎》之人,见几而作。”,以明鲁诗主“伤怨”的意义。次引“韩诗叙曰”,所言“刺时也”录自王应麟《诗考》,徐氏有按语云“后汉《章帝纪》‘应门失守,《关雎》刺世’注引《韩诗章句》以证,故王氏云然”,以点明《诗考》录“韩诗说”的来龙去脉。同时,徐书复引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及“张超曰”等文献,详证韩诗主“刺时”的意义。继后徐书引“张衡曰”、《诗纬推度灾》及《焦氏易林》有《关雎》诗题义的解读,不仅在广征博取,亦兼含“齐诗”之义⑥例如张衡赋中引诗,尝兼用“三家”义。往往从“鲁”,亦从“齐”,如张氏《东京赋》云“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考《汉书·翼奉传》载奉上元帝疏“臣奉窃学《齐诗》”,并针对“宫室苑囿,奢泰难供”谓“必有五年之余蓄,然后大行考室之礼”,师古注“《诗·小雅·斯干》之诗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按:奉用《齐诗》,张赋与之同。又按:“韩诗”义亦同。。尽管徐书宗旨在明“三家”,所以博征引的意义并不推重某家某说,以及优劣之争①钱穆《读〈诗经〉》云:“后儒论《关雎》,莫善于宋儒伊川程氏。其言曰:‘《关雎》,后妃之德,非指人言;周公作乐章以风化天下,自天子至庶人,正家之道当然。’”按:钱主优劣,故复引清儒戴震证程说,举魏源之言以辨其非,皆价值判断,属思想史研究。,但其于广泛引取时有辨析,体现的严谨态度,亦不乏“案断”之义。
解诂“诗句”,尤为徐书博引证义之用力处。如继《关雎》“题解”,徐氏转向“诗句”广诂,首句“关关雎鸠”一句,即博引如《孔子家语》、《列女传》、《文心雕龙》、《风土记》、《玉篇》以及张守节《史记正义》等文献以明“三家”义。又如同诗“钟鼓乐之”语,书中分别引录侯包、韩婴、孔安国、司马迁、匡衡等人解说,而于韩婴说后又复引《北史》中文献以佐证,于匡衡说后则引《天禄阁外史》以增义,均显示其博取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徐书征文考献,在于明辨“三家”诗义,然对征引文献本身,又不乏复征引文献以辨真伪之例。如《魏风·硕鼠》章,徐氏解“硕鼠硕鼠”、“适彼乐郊”句意时引述《吕氏春秋·举难篇》“宁戚欲干齐桓公……悲击牛角疾歌”一节,高诱注:“歌《硕鼠》也。”对此,徐书引王应麟《诗考》:“《三齐记》载宁戚歌,所谓‘南山矸,白石烂’者是也。今高以为歌《硕鼠》,未知何据?”再看针对王说之“璈按”一则:
乐府所载《南山歌》,殆汉人依托之词,不类周人之诗也。戚在齐位卑业污,有宦三年,不见知之意,故歌此诗(结按:指《硕鼠》)以闻于齐桓。此诗亦先戚百年而作,故戚得歌之也。(453页下)
为证其说,徐氏又引《后汉书·马融传》注引《说苑》“宁戚饭牛于康衢,击车辐而歌《硕鼠》”语,复引梁处素曰:“今《说苑·善说篇》作‘击车辐而歌顾见桓公得之’,‘顾见’字当是‘硕鼠’之讹。”如此梳理,文献自明,而征引取义,尤为要则。
三曰“重考述”。徐书辑佚之法,是于“诗题”、“诗句”后附以诸家文献,标明“三家”义,且多插入“按”或“璈按”语,尤其后者,多宣示己说。比如徐氏颇重钱澄之《田间诗学》,尝引以为证,却亦多有考辨补益,如《周南·甘棠》引钱说而示异云:“璈按:钱氏云周召分陕在武王得天下之后,而《甘棠》颂召伯当在康王之世。愚谓《外传》称述文王,其在武王以后明矣。”(388页下)而综观徐书考述“三家”《诗》之内容,要在四端:
一是“文字考”,例如:
璈按:“‘谓’,或作‘畏’,杜注‘惧多露之濡己’,似本作畏也。”(389页下)
结按:此考《召南·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之“谓”字。
璈按:“此与鄘风‘是絏袢也’皆改世从曳,缘避太宗讳而易其体也。”(401页下)
结按:此考《邶风·雄雉》“泄泄其羽”之“泄”字唐石经本作“洩”。
璈按:“‘止’,韩训‘节’,谓礼之品节无止,则汰侈逾制也。”(416页下)②按:《韩诗》说引见陆德明《经典释文》。
结按:此考《鄘风·相鼠》“人而无止”《韩诗》训“节”义。
璈按:“八成经邦,义最显著。此本三家笺,乃改依毛训也。”(518页上)
结按:此考《小雅·节南山》“谁秉国成”郑注“伤今无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训“国成”为“八成”。
略举四例,或考异文,或考“讳”字,或主“韩说”,或依“毛训”,均见徐氏锱铢必较的考述态度。二是“名物考”,例如:
璈按:“《易林》:‘蜲蛇九子,长尾不殆。’焦所述如蜥蜴、蝾螈之类,行步旋折宽舒,诗缘以取象。而委为蜲之省欤!”(390页上)
结按:此考《召南·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之“委蛇”,以《焦氏易林》诂解《韩诗》之说。
璈按:“《尔雅》‘水潦所止泥邱’,《释文》“泥亦作坭”。此所引即《韩诗》,泥,盖卫之泥中邑也。”(408页上)
结按:此考《邶风·泉水》“饮饯于祢”,引《韩诗》“引饯于坭,坭地名”及《初学记》、《白帖》均引作“饮饯于泥”。
仅举两例,一考述动物名,一考述地名,综会众说,辨其异同,在徐书比比皆是。三是“句意考”,例如:
璈按:“《淮南·说山》曰:‘桑叶落而长年悲。’盖感年华之盛衰者,多触寄于桑也。”(424页下)
结按:此考《卫风·氓》“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句,于引王肃、焦赣诸说后复借《淮南子》解诂其义。
璈按:“《左传》晋侯赐魏绛女乐二八房中者。女乐之所陈,以君子而执簧执翮于其间,所谓优杂子女,而不知其非古矣。又,《列女传》曰‘女乐俳优,纵横大笑’,即《诗》之‘阳阳陶陶,其乐只且’者耶!”(430页上)
结按:此考《王风·君子阳阳》“右招我由房”句,针对刘光伯“由房谓路寝下之燕寝”及顾栋高、王夫之、钱澄之诸说,复据《左传》、《列女传》解诂其义。
考述句意,为徐书最为详尽处,此举两则,一主于情感,一重在制度,解句析义,不乏己见。四是“篇章考”,徐氏于此或兼取“三家”,或专取“一家”,亦有舍“三家”而取“毛传”,如《周南·螽斯》篇义解即是,均可见其综会诸家而有所专取及发挥的特点。以《召南·草虫》为例,《广诂》卷二载:
《草虫》(三章)刘向曰:“《诗》之好善道之甚也。”
《说苑·君道篇》引“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范家相曰:“刘以思君子为好善道,则非大夫妻所作矣。”
璈按:“玩刘氏之说,与子展赋诗之意,则此篇与《杕杜》、《隰桑》同指。其陟山、采薇,既有仰高之慕;而草虫鸣,而阜螽从,是亦鹤鸣子和之象也。”(386页下)
此用《鲁诗》说,并据范家相《三家诗拾遗》解刘向解《诗》义,引申其“好善道”特色,得出《草虫》诗与《杕杜》、《隰桑》同指(旨),并有他诗“仰高之慕”与“鹤鸣子和之象”。
观上引诸例,可见徐书中“明源流”、“博引证”与“重考述”又浑然一体,使其对“三家”《诗》的解诂得以全面而立体地呈现。
四、引史明礼与章句义理
经学研究以《诗》、《书》最难解读,于《诗》训诂歧异尤多。对此,近人王国维释云:“《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是以知先儒亦不能解也。其难解之故有三:讹阙,一也;古语与今语不同,二也;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三也。”①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艺林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5页。有此“三难”,故拾遗补阙、辑考述义者多。徐璈为《广诂》,于前贤注《诗》亦多不满意,如《例言》云:“朱子序《读诗记》云:‘唐初诸儒作为疏义,因讹踵陋,百千万言,不出毛、郑二氏之区域。’愚谓疏家冗赜,诚如所讥,然自《集传》以后,元、明儒者专宗紫阳,依文衍义,取盈卷轴,说经铿铿,又类帖括矣。”(366页)②按:文中《读诗记》指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集传》即朱熹《诗集传》。这里除批评唐人义疏“因讹踵陋”,又提出宋、元后承朱说转而为科考经义“帖括”之弊。正因针对千百年来考试经义之敷衍凑泊,徐氏回归文献,转向实学,致力辑考,于《诗》义解读之困惑,则取“诗无达诂”说以为周旋。其实,任何一种整理与注疏,都具有重新解读的意义,徐书也是如此,通过考察其辑考成就,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论主旨。概括其要,徐书的《诗》论思想体现于引史实以明礼制与析章句而阐义理。
先说第一个问题,即以史明礼。以“史”解“诗”,是历史学家与解经学者共奉之原则,而“诗”、“礼”互释自郑玄《诗笺》多用《周礼》解《诗》已肇其端③关于清儒与近代学者对郑玄以“礼”笺“诗”的评论,详见梁锡锋《郑玄以礼笺诗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按:拙文《论东汉周礼学兴起的文化问题》亦有论述,文载《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一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所谓“以礼解诗,歌诗为礼”④前揭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二》。,似为通识。缘此,徐书多引史书,以阐发《诗》中礼制,并无创见,但考虑到他是针对历代经解之因陈守旧与帖括之敷演《诗》义,而落实于具体诗章、诗句之辑考,其解《诗》引史以明礼还是有实证意义的。例如《邶风·燕燕》(四章)本事,徐书引《左传·隐公四年》“卫庄公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蚤死;其弟戴妫生桓公,夫人庄姜以为己子”,又引郑玄《礼记注》“戴妫大归于陈,庄姜送之,作此诗”以证,其“璈按”云:
《史记·卫世家》:庄公娶齐女为夫人,好而无子;又娶陈女,生子,蚤死,其女弟生子完,完母死,庄公令夫人齐女子之,是为桓公。所云陈女,即厉妫;女弟,即戴妫。但云完母死然后庄姜以完为己子,则戴妫之卒在桓公未立以前,然则兹诗之所送者,岂即厉妫耶!(398页上)
此用《史记》所载史事驳正“郑玄注”,虽仅“二妫”之讹,然因史实之异,赠诗对象有别,其礼义精神之“见燕托兴”(徐书引顾梦麟语),自然也有所不同。此类引述史事“诗”、“礼”互释之例,在徐书中甚多,如《小雅·华黍》之与“乡饮酒礼”、《鸿雁》中“百堵皆作”之与都邑考工、《大雅·皇矣》“居岐之阳”之与史地考释皆是。
虽然,以“礼”注“诗”已是渊久传统,然徐书诂《诗》广泛引礼,当与乡先贤方苞有关。方氏治经,以《礼》最著,皮锡瑞谓其“兼通《三礼》,多信宋而疑汉”⑤皮锡瑞:《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306页。,故其为《朱子诗义补正》,尤多以《礼》释《诗》。例如《郑风·狡童》,方书卷三引《周礼·藁人》以补正“朱注”,反对其“淫诗”说;《小雅·鹿鸣》“皇皇者华”,方书卷四引《周礼·小行人》“使适四方”以解其义;《大雅·行苇》题义,方书卷六用周代礼制建言“朱子疑此为祭毕而燕之诗。然祭毕岂能复行射礼”,并引《礼记·文王世子》以证其说。他如《周颂·清庙》之与祀礼考述,《商颂·烈祖》所谓“观此诗则知祭祀之礼至周而后备”等①引见方苞《朱子诗义补正》,《续修四库全书》本“经部”第62册,第412、426、465、482、499页。,均可见方苞尊《礼》解《诗》的思想与方法。在此前提下,方氏对朱熹说《诗》的诸多补正,可知皮锡瑞所谓“信宋而疑汉”也仅是相对而言,殊非信谳。而方氏以《礼》解《诗》之法对徐氏《诗》、《礼》互证(包括对朱熹《诗》学的质疑)之影响,其中乡梓学术之传承,值得注意。
如果说徐书《诗》、《礼》互证或受方苞影响而与乡梓学术有关,那么第二个问题即通过章句的分析而阐发《诗》之义理,则师承姚鼐于《述庵文钞序》中倡导之“义理”、“考证”、“辞章”并重思想,并与清代初、中叶《诗》学研究风气相融契。马瑞辰撰《毛诗诂训传名义考》辨析解《诗》的“诂训”与“传”体之异云:“盖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②引自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倘与马氏《毛诗传笺通释》偏重“传”体相比,徐书显然属于“诂训”体解《诗》,是对围绕经文之“三家”说的辑考。然而这仅是论“体”而言,在实际操作中,学者往往破“体”为“文”,读徐璈《广诂》极重“章句”之学,不乏对《诗》义及“三家”说之引申与发挥,这在徐书《例言》中已有“夫子自道”,即“今所辑录,要自《正义》以前惟明引诗文,从而训释之,词虽单文只义,随在广取,咸可引伸”(366页上)。例如其解《周南·汉广》之“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诗句意,征引《韩诗内传》“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一段,旁引(用小字)《列仙传》、《文选·江赋注》等以佐证;又引《文选·琴赋注》“薛君章句”一段,复引焦赣《易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等以佐证,并为“璈按”:
游女之为汉神,犹《楚词》之有湘君、湘夫人也。《内传》述郑交甫事,未审系何时代,盖以证汉神之实有耳。《诗》以汉女之神不可犯与之子之归必备礼,非谓游女即之子也。观焦氏、陈氏之引述,不仅韩家为然矣。
继此“按语”,徐氏意犹未尽,又引刘向《列女传》、曹植《七启》、陈琳《神女赋》等有关“汉女”说法及描写以丰其义。而于刘向说后,复为“璈按”再解《诗》义云:
无宁,宁也;不显,显也。此诗两不可,犹言岂不可也。求者男,下女必备婚姻之礼乃云可耳。
次三章秣马秣驹,正谓其礼之备也(383页上)。
此由训“词”到释“义”,由句意解诂勘进于诗章解读,论者的引申与发挥,以及其因《礼》解《诗》以阐发其义理之方法,于中可见。又《齐风·鸡鸣》,徐书辑考诸家,先明章义,如引述《太平御览》引“韩诗曰”、《孔丛子·记义篇》、《易林·夬之屯》、“孙毓曰”、“李善曰”等以证,转而入章句之解,如“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之“璈按”云:
《韩诗》“谗人”之说,薛君注仅存片语,似谓蝇声可乱鸡鸣也。与《青蝇》诗指又异。岂视朝戒谗间之言,而远色为去谗之实。诗固曲寓深意欤!(444页上)
解诂诗之章句,明示义理,且寄发感慨,这也是徐书中常见的一种理解方式,给读者在实证意义上的遐想空间。
由于重视章句的分析,徐书虽以辑考方式诂训《诗》义,其中却不乏文学化解读诗章的意味。洪湛侯《诗经学史》论清代《诗》学,专辟一章列举“运用文学观点论《诗》”者有王夫之、金圣叹、方苞、袁枚、方玉润等③详前揭《诗经学史》第七章“清代运用文学观点论《诗》的学者与诗人”,第560页。,其中桐城学者方苞解《诗》的文学观点在于力主三百篇乃“以至诚感人心,以王政运天理”之作④前揭方苞《朱子诗义补正》卷1《国风》,第395页。,属于以《礼》(包括“情”)解《诗》的范畴。而徐书中之文学性当与方氏相近,只是因于体例,徐氏更多的是通过文献的辑引来表现的。换言之,《广诂》除了文学性解读如《秦风·黄鸟》“惴惴其栗”引刘勰《文心雕龙·哀吊》“哀者,依也。悲实依心”宣发其情(464页下),则大量引用“集部”文献以印证“三家”义以解《诗》。比如徐书中解《召南·甘棠》“勿翦勿拜”引《韩昌黎集注》,解《邶风·击鼓》“死生契阔”引高适文“契阔偕老”,解《王风·采葛》引庾信诗“避谗应采葛”等皆是⑤《诗经广诂》,分别见第388页、第400页、第431页。。而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引“赋”解“诗”。兹以解“风诗”为例:
《召南·殷其靁》引《韩诗》曰:“靁,雷也。”璈按:“《长门赋》:‘雷隐隐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此诗亦以南山殷殷之雷,拟君子归来之车声,赋同诗指也。”(391页上)
《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引《艺文类聚》录傅咸赋:“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何诗人之是兴,信进止之有序。秋背阴以龙潜,春晞阳而凤举……。”璈按:“傅氏述诗之意,以燕之秋去而春可复来,兴之子归国而不复返卫,诗人托物旨远而情深矣。”(398页下)
略举两例,已足见徐氏以“赋”解“诗”情与因“文”证“经”义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以文学作品引述《诗》义并具有阐释意味的,最初即是汉赋的创造,也正因为汉赋引《诗》有辑补之用,清代学者注《诗》亦尝取资赋文,以证经义。如胡承珙《毛诗后笺》考述《周南·关雎》,引汉赋以解证《诗》义:
扬雄《羽猎赋》云:“王雎关关,鸿雁嘤嘤。群娭乎其中,噍噍昆鸣。”张衡《思玄赋》云:“鸣鹤交颈,雎鸠相和。”又《归田赋》云:“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此所谓雌雄情意至者也。……张超《诮青衣赋》云:“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此即所谓有別者也。①胡承珙:《毛诗后箋》,郭全芝校点,合肥:黃山书社,1999年,第11页。
连引三条赋语印证《诗》义,也是汉赋引述与传播《诗》义的反证。他如段玉裁《诗经小学》解《诗》之“绿竹猗猗”、“螓首蛾眉”、“风雨潇潇”等,分別引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羽猎赋》、张衡《西京赋》中词语证其字义;焦循《毛诗补疏》与陈乔枞《毛诗郑笺改字说》解《诗》之“其虚其邪”均引班固《幽通赋》“承灵训其虚徐兮”证其字义②引见《清人说诗四种》,晏炎吾等点校,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130、132、140、273、380 页。。由此可见,徐璈《广诂》以“赋”证“诗”及融文学创作于《诗》义训诂,不仅彰显其注经特色,亦与当时治《诗》风习相关,是嘉、道间经学会通思想的表现。
五、树立经典的诗学传统
历代为《诗经》解诂义疏者,目的均在为其树立经典,所谓“四家”说以及围绕其说之研究皆是。这其间包括因承之说与创新之见,尤其是创新之见,在于对前说之“纠正”,而新的“经典”的树立,实质就是一种“纠正”。读徐璈《广诂》,其中通过对辑佚“三家”《诗》说文义之考述,且勘进于对《诗》本义之论析,均具有重新树立经典的意义。而论其成绩,据前人研究,又突出在两方面:
一是辑考成就,诚如前引魏源《诗古微序》所称颂的于“三家《诗》佚文几大备”;而作为清儒集“三家”说之成的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虽并不推重徐说,然亦不乏引赞之语。如王书卷一《周南·葛覃》解云:
“《葛覃》恐失其时”者,《古文苑》蔡邕《协和婚赋》云:“考遂初之原本,览阴阳之纲纪。乾坤和其刚柔,艮兑感其脢腓。《葛覃》恐其失时,《摽梅》求其庶士。唯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齿。婚姻协而莫违,播欣欣之繁祉。”徐璈云:“赋意盖以葛之长大而可为绤,如女之及时而当归于夫家。刈濩汙澣,且以见妇功之教成也,故与《摽梅》并称。是亦士大夫婚姻之诗,与何休谓‘归宁非诸侯夫人之礼’者义同,鲁家之训也。”愚案:徐说是也。③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17页。
此对徐氏有关《诗》意判断力之肯定,也是其辑考之功的体现。
二是经世致用,这在前引洪颐煊《诗经广诂序》所言徐氏撰此书时正值临海县丞职上,而“有惠政”,并称其“得力于经义者深”有所阐发,此乃典型的以经义缘饰吏治之论。如果我们对读徐书中对“三家”《诗》之“刺诗”说之引述,这种经世致用思想同样隐含着一种《诗》学传统。刘熙载《赋概》有云:“古人赋诗与后人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周语》‘瞍赋矇诵’是也;一以言志,《左传》赵孟曰‘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韩宣子曰‘二三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是也。”④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5页。就《诗》学而言,其中内涵了由周室王者观政、陈诗讽谏向春秋之世行人交往、赋诗言志的转变。而汉代归复王治,复兴“王言”,以经术饰吏治,无论“三家”学官治《诗》,或是“毛氏”言《诗》,要在美刺两端,所谓“《国风》、《小雅》为刺者多,《大雅》则美多而刺少……或于颂美之中,时寓规谏”⑤程廷祚:《青溪文集》卷1《诗论十三》,金陵丛书本。,甚或如《汉书·儒林传》载王式为昌邑王师“以三百五篇谏”的实用《诗》功。由此再看徐氏治《诗》与“吏治”的结合,正是其经世《诗》学观的传统。
除了前人已注意到的以上两点,我以为结合徐氏对乡梓文献的关怀,即晚年所编《桐旧集》之作为,他的《诗》学尚体现了“采诗”观风之传统,这也是其树立经典的要义所在。有关“采诗”之说,汉人说法甚多,如《汉书·艺文志》谓“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又《食货志》谓“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等。而徐氏《广诂》对此则在卷一《国风》后引述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之说: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374页下)
尽管何休之说具有很大的理想主义成分,但其中“饥者”、“劳者”之说则与徐氏《诗》学致用观契合,尤其是对“采诗”本事的信奉,则与徐氏晚年致仕归乡后编纂《桐旧集》思想有着逻辑的联系。
徐璈编《桐旧集》四十二卷,是今存最全的一部桐城诗歌总集,选录自明初迄清道光庚子(20年)近五百年桐城籍一千二百多名诗人七千七百余首诗作①关于《桐旧集》的编纂及原书,详见拙文《桐旧集与桐城诗学》,文载《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与前此潘江所编《龙眠风雅》比较②潘江:《龙眠风雅》,《四库禁毁书丛刊》景印康熙十七年(1678)石经斋刻本。,既为赓续之作,又更蔚然大观,以致民国初桐城后学光云锦认为“吾乡文献之存,惟此集是赖”③光云锦:《景印桐旧集识语》,民国十六年(1927)景印原刻本《桐旧集》卷末。。考察徐编《桐旧集》的编纂意图,诚如其《桐旧集引》自谓“采萃乡邑先辈诗章并言行之表见于他书者,寸累尺积,汇为若干卷,颜曰《桐旧集》,以蕲流示来兹,永言无也”。而此“采萃乡邑”诗章与《诗》三百“采诗侯邦”之成集的关系,则由徐氏外甥苏惇元道破:“古者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此列国风诗所由载之简策,孔子所由删定存三百篇者也。后世其制寝废,而郡邑各辑其诗为总集,亦犹古国风之遗意,其可阙乎?”④苏惇元:《校刊桐旧集后序》,《桐旧集》卷首。按:苏氏乃《桐旧集》之续成者。其实,宋代朱熹就说过“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的诗看”⑤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80《诗一·论读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083页。,即将当代诗与古《诗》连接,内涵“采诗”的当代性精神。由此再看徐氏在临海县丞任上撰《广诂》由存“三家”义到追述《诗》本义,致仕归乡采集乡邑先辈诗以成《桐旧集》,全面展示一邑之地方文献与诗风,其联系正在“古国风之遗意”,是“采风”诗学传统的承续,也是文学经典与地域传统之相资相生的发展。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这两本“诗集”编纂体例之一“同”一“异”观觇其意义。所谓一“同”,即辑考之方法:《广诂》每于诗篇、诗句后辑考“三家”说,或主一家,或并三家,并三家者亦先主一家历代之说,次二家诸说,再三家云云,文献翔实,而罗列有序;《桐旧集》每于作家名下撰“小传”,传文仅简介姓氏、职官、著述等,后则附以采辑诸家传记与评论,辑考之功,一同前者。所谓一“异”,即编排体例:《广诂》承续传统编《诗》方式,即“风”、“雅”(小、大)、“颂”(周、鲁、商),《国风》排序则依《毛诗》⑥按:《国风》排序,前五即“周、召、邶、鄘、卫”同,后十则《左传》、《毛诗》、《诗谱》排序不同,《毛诗》为: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桐旧集》则以家族为序,排列“方”、“姚”等八十五姓诗家作品成书,而“方姓”为桐邑第一大姓,故冠于首。考辨其异,《诗》之时代,乃宗法封建,“采诗侯邦”,献于天子,代表权力话语;而自秦汉一统,尤其是宋代以后,文化权力一则在中央集权的政治意志,一则在宗族共同体建立而体现的家族象征,地方文化的兴盛往往决定于望族大姓为支撑,《桐旧集》选目展示的家族特征,正标示了明清时代桐城诗学文化的权力话语。这也是徐璈依附权力话语而构建诗学经典的意义所在。
近代西方学者对“经典”形成的定义,内涵有王权话语、精英言说与“批评与教学工具”⑦[荷兰]D.福克马、E.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诗经》自孔子以后即成为“教本”且进入权力话语系统,历代的诂解注疏也标明了一种经典的复述;而对自汉代进入博士学官且渐趋消亡的“三家”《诗》说,徐氏《广诂》作为与书院有关的教本,并通过自己言说对其辑考叙述,既是对一“王言”传统丢失的追忆,也是对一“经典”传统的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