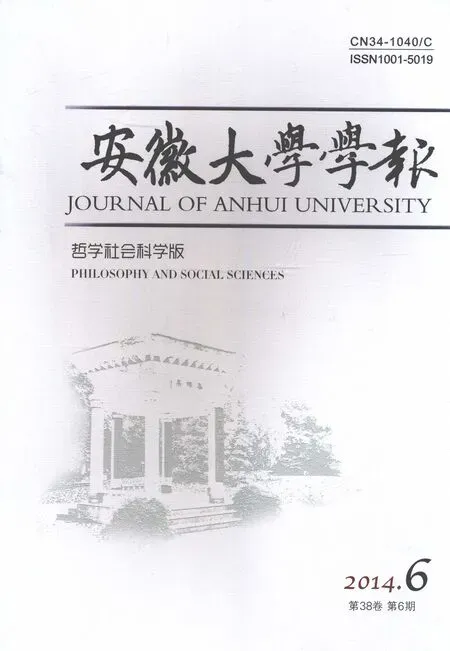清代徽州玉米经济新探
——以文书资料为中心
2014-03-20梁诸英
梁诸英
迄今为止,关于清代棚民在山区种植玉米的研究,涉及商品经济性质、地域分布、生态破坏作用以及地方社会的禁止性规定,也有文章探讨了玉米种植的传播过程①关于清代棚民种植玉米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冯尔康《试论清中叶皖南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刘敏《论清代棚民的户籍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4~155页;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4~85页;刘秀生《清代闽浙赣皖的棚民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1~112页;吕小鲜编《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实》,《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赵冈《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玉米传播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郭松义《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第7辑,1986年;曹树基《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不过,对山区外来棚民开垦作出禁止性规定并不等同于当地玉米种植被禁止。有鉴于此,对清代玉米经济的实态仍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笔者在检阅徽州契约文书资料时,发现有许多文书真实记录了清代徽州地区玉米垦殖的实际状况、对当地租佃形式的影响、收益分配以及对山林兴养的促进作用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此前都很少为学界所关注。存世徽州契约文书具有数量多、时间跨度长、系统性强等特点,能据以更好地复原徽州民众的农业生产及生活实态,极具史料价值。本文以徽州契约文书为主要资料,对徽州玉米经济实态进行考察,期望通过徽州地区这一生动案例,考察清代一些禁止性规定在基层的实际执行情况,进一步认识玉米种植在清代的影响,并丰富徽学研究的内涵。
一、清代徽州玉米垦殖概况
清代徽州地区的玉米垦殖情况,在地方史料中常有概括性的记载。道光《徽州府志》记录了苞芦种植充斥山场的情况,指出“昔间有而今充斥者,惟苞芦”①道光《徽州府志》卷5之2《食货志·物产》,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苞芦”是徽州对玉米的称呼。;俞正燮也指出徽州“苞芦已植到山巅”②同治《黟县三志》卷16《艺文志·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实际上,徽州契约文书中也多有此类玉米垦殖的具体实例。
乾隆、嘉庆年间徽州地方社会对棚民种植玉米多有禁令,但在禁令实行的同时,也出现了徽州本地农民效仿棚民垦殖玉米的状况,这是一种伴随人口流动而导致的农业技术的传播。史载徽州府“乾隆年间,安庆人携苞芦入境,租山垦种,而土著愚民间亦效尤而自垦者”③嘉庆《绩溪县志》卷3《食货志·土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关于这一点,诸多契约也可佐证。徽州地区较早明确记载种植玉米的契约,据笔者检阅,是乾隆三十五(1770)年二月祁门县潘有义所立的承佃山约。此约规定所租山场用于锄种苞芦,并以苞芦交租:“立承佃人潘有义,今承到程 名下山壹号六保江祥坑小土名外大弯,其山悉照老佃约,是身承去锄种苞芦,递年交纳苞芦壹佰陆十斤正,约至十月内付还,如过期加价行罚。”④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1辑第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4页。嘉庆年间,徽州也有垦殖玉米的契约,如嘉庆十八年(1813)三月张义所立承寄佃田坦约:“立承寄佃约人张义,今承到程开艮名下七保庙下车田墩土名界方位坦壹备,计租五十秤,凭中自愿是身承来耕种苞芦。”⑤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1辑第8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此时期明文载明玉米种植的契约绝非个例,据笔者对已出版徽州文书的检阅,还有11则之多⑥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1辑第7册,第199页、214页、230页、276页、318页、329页、373页、389页;第1辑第8册,第15页;第1辑第10册,第175页。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11,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道光年间及其后玉米种植仍然存在,道光、咸丰及光绪时期均有多则承佃山场的契约载明种植玉米事项。据咸丰三年(1853)十月初四日祁门县吴德侯等所立文约,在吴德侯等合伙承佃的汪慎德堂澄公祀名下的山地,并不禁种玉米:“倘有本山锄种苞芦,亦照六股均种,毋许倚强混种,所有山价酒水钱,亦照六股均出。”⑦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2辑第2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4页。这就说明,种植玉米在当时已是默认的群体性行为。除了可以将山场佃给多人合伙种植玉米外,还可以将某山场佃给个人种植玉米,如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二十日祁门吴德伏所立承山约:“立承约人吴德伏,今承到吴广宪族侄名下坐落本都六保土名树窟山壹号”,在此山四至之内“是身承去开挖兴种苞芦”⑧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2辑第2册,第157页。。《陶甓公牍》也记载了清末休宁县四都源、瑶碣源之棚民以烧炭或种植苞芦为生的状况,而其时绩溪县已出现把苞芦之粉“制成食品为正餐者”⑨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官箴书集成》第10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588页、第617页。。
由以上介绍可知,清乾隆以后各个时期均有关于玉米种植的契约。这说明虽然官方对棚民种植玉米多有禁令,但徽州民间对玉米的种植没有随之禁止,也不是偷偷摸摸地暗中进行,将玉米种植明确写进契约即是明证。赵冈认为,乾嘉道光年间政府禁止流民垦山种植玉米,“这些禁令虽非百分之百的生效,但在山区种植玉米的范围究竟大为减少”⑩赵冈:《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种植玉米范围大为减少的说法,若是针对棚民来论,是可信的;但若言山区玉米种植总体面积大为减少,则恐难以断定。
二、苞芦实物租:徽州民众对玉米的认可
清代徽州没有强行禁种玉米,这是清代徽州农业生产的真实形态。玉米种植对清代徽州的重要性有客观原因,即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粮食供应严重不足①吴媛媛:《明清徽州粮食问题研究》,《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吴媛媛:《从粮食事件看晚清徽州绅商的社会作用》,《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吴媛媛:《明清徽州的水旱灾害与粮食种植》,《古今农业》2007年第2期;李琳琦:《明清徽州粮商述论》,《江淮论坛》1993年第4期;柏家文、朱正业:《明清徽州社会救助体系浅论》,《江淮论坛》2012年第3期。,在此背景下玉米的功用更为突出:“煮粥炊饭,磨粉作饼,无所不宜,救荒疗饥必需物也,亦可炒食。”②嘉庆《黟县志》卷3《地理·物产》,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随着玉米种植的发展,苞芦实物租这一新的实物租形式得以实现。苞芦实物租成为徽州地区稻、麦、豆等实物租之外一种主要的实物租形式,这是清代徽州租佃制度的一种新情况,学界此前极少注意。徽州契约文书对苞芦实物租有大量记载,下面择要介绍。
乾隆、嘉庆年间,有不少承种、租佃山地及山坦的契约载明,交租的实物种类是苞芦,说明了玉米在当地的认可度及重要性。据笔者检阅,乾嘉年间徽州地区载明苞芦实物租的契约有20则之多③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1辑第7册,第156页、198页、210页、230页、305页、316页、318页、434页;第1辑第8册,第26页、29页、39页、42页、83页、87页、93页、149页、168页、183页、213页;第1辑第10册,第175页。。在承佃山场种植玉米的契约里,承佃人与山主绝大多数是异姓,我们推测,可能是伴随着清代人口流动的频繁,系外地人进入徽州垦种玉米的情况。也有少量契约载明了承种人是徽州附近府县的农民。比如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徐成花所立承佃坦约即是此种情况。徐成花是皖南石埭县人,程加灿是徽州祁门人,徐成花承佃“程加灿兄名下七保富村杨家巷口坦壹块,又占家坞坦壹块”,“迭年交纳租苞芦子贰十五斤,身不得短少”。照此看来,石埭县人徐成花到祁门开垦山坦种植玉米,属跨境垦种,当属棚民性质。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祁门程笄艮将田坦出佃给石埭县徐永成耕种收取苞芦实物租④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1辑第7册,第269页、333页。,也是这种情况。
此时期苞芦实物租交纳还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即明明是佃田契约,却规定需要交纳苞芦实物租。兹举一例: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朱相元承佃到程加灿名下之田,“计原租四秤”,“迭年硬交苞芦租子叁拾斤整”⑤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1辑第7册,第400页。。我们知道,根据玉米的作物特性和徽州山多田少的状况,清代徽州玉米是种在山地的,一般不种在田里。这种情况说明承佃人朱相元还有其他山地可种植玉米,以交纳苞芦租,或直接在此田块种植玉米。无论哪种情况,均说明玉米种植在当时的徽州不属罕见。
此时期不仅苞芦实物租绝非个例,而且和麦租等主要实物租种类类似,如果欠下苞芦实物租,也需要来年加利付还。据嘉庆元年十月祝天南所立欠山租字契约,祝天南“欠到程名下本苞芦蒲伍佰斤整”,要在来年秋收加利付还⑥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1辑第8册,第26页。。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苞芦实物租在当地被认可的情况。
道光、咸丰、光绪年间也均存在交纳苞芦实物租的诸多契约,这里不一一列举,仅举一则为例。道光二十四年(1844)祁门立承佃约人吴大柏,“今承到程彩记、端培、端埭等七保罗家岭下熟田七坵、熟坦壹备,土名大厂坞、小八坞等处熟田坦,是身承去入地耕种,无论丰歉,迭年硬交玉子贰佰壹拾斤,其玉子务要晒干挑送上门,毋得拖欠斤两。如违,听凭另召他人”⑦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1辑第8册,第438页。。此契约要求承佃人将苞芦租“挑送上门”,并且“毋得拖欠斤两”。
从现有交纳苞芦实物租的文书看,一般都规定苞芦需要“挑送上门”,并且“不得拖欠短少”,如果违反则“听凭另佃他人”。这些文书中,有些载明所租地块种植的是苞芦,有些是说开种杂粮或花利。此“杂粮、花利”很可能包括玉米,或者就是种植玉米。很难想象契约里的佃民、承租人会购买玉米来交租。自乾隆至清末,徽州各时期均有交纳苞芦租的实例,甚至在个别租佃“田”的契约中也显示交纳租谷的种类是“苞芦”。这些苞芦实物租的大量实证说明了玉米种植在清代徽州地区的发展以及民众对玉米的认可。
在清代徽州,玉米已出现在民间借贷或抵押关系中。徽州借贷米、麦并加利付还的契约不少,但借贷玉米的契约很难见到。所幸此类借贷文书仍有存世者,也足见其珍贵。据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祁门王之禄所立借字:“立借字:王之禄,今借到陈艮兄名下苞芦九拾斤正,其苞芦言定来年秋收加利付还,不得短少,付青[清]取字,其字执留,今恐无凭,立借约存照。”①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1辑第7册,第265页。在徽州人的买卖活动或集资活动中,还出现以玉米作价的情况。比如咸丰年间徽州水碓股份出卖时,即曾有以玉米作价而成交的情况,也可见玉米在徽州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咸丰八年十月吕邦闵所立卖碓契即是此类契约:“立卖契人吕邦闵,今因欠少使用,自身情愿将传字号内土名外坑下石桥里水碓一只,十大股合身分法四股之一,并堨脑、水圳,尽行出卖与堂伯清海、邦院名下经管,三面言定时值价钱苞芦一斗二升正,其苞芦当日收足,其水碓听凭随契经管,无得阻执。”②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3辑第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8页。将玉米作为借贷物及在市场交易中以玉米作价,也充分说明了玉米在清代徽州被广泛认可。
玉米在清代徽州社会中被认可,还可以从徽州地区与玉米有关的民俗及民间歌谣中得到反映。据珍稀史料《应酬便览》,清代徽州猴子尤其是猕猴对农作物玉米的破坏很严重,它们“逐队成群”来到玉米地“空劳大嚼”,“或残或拔”,使得“一山苗物尽空虚”,农民“半岁勤劳,不了郡凶残耗”。于是,有人作《祈神驱猴狲疏》,试图以祈神手段应对猴狲的破坏③王振忠:《清代徽州民间的灾害、信仰及相关习俗——以婺源县浙源乡孝悌里凰腾村文书〈应酬便览〉为中心》,《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希冀借助神灵驱赶猴狲以保护玉米生产,足见徽州百姓对玉米生产的重视。流传久远的歌谣也体现了传统时期徽州人民对玉米的喜爱。休宁县的歌谣《山里好》指出:“手捧苞芦馃,脚踏硬炭火,除开皇帝就是我”;绩溪县也有《手捏苞芦馃》歌谣:“手捏苞芦馃,脚踏树桩火;无忧又无虑,皇帝不抵我”④吴兆民:《从民间歌谣看徽州人的观念世界》,朱万曙、卞利主编:《戏曲·民俗·徽文化论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4页。。馃是一种油炸食品,符合徽州人饮食重油的特点,“苞芦馃”被当作美食,体现了徽州人对玉米的认可和喜爱。
三、清代徽州玉米垦殖的收益分配
关于徽州的租佃形式,叶显恩指出,“从涉猎到的材料看,当时徽州地区绝大部分取额租制,少量取分成制”⑤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75页。。徽州玉米种植中是否也存在这种定额租和分成租呢?据清代徽州地区的承山、佃山契约,答案是肯定的。
根据对相关契约的分析,分成租常常是山主、佃户之间二八分配的水准,如果违反约定则要受到“见壹罚拾”等类的经济处罚。在道光二十四年祁门吴士发等所立出佃山约中,吴士发等将山出佃给他人锄种苞芦,规定苞芦分配方式是“迭年秋收之日眼仝干分,言定贰八均分,佃得八,股得贰,无得私自采取,如违,见壹罚拾”⑥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2辑第2册,第66页。。晚清的承山契约对种植苞芦以及桐子也常常是二八分成。如光绪十六年祁门吴德伏所立承山约,吴德伏在所承之山四至之内“是身承去开挖兴种苞芦,主力贰八监分,务要眼仝登山采摘”⑦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2辑第2册,第157页。。也有少量契约是对半分配的情况,如嘉庆十八年三月张义承种程开艮的山场种植苞芦,“迭年秋收之日接坦主到坦干分对半”,并规定“佃人兴种苞芦,不得怠懈抛荒”⑧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1辑第8册,第168页。。
除分成租外,徽州地区还有交纳一定数量苞芦的形式,即定额租,规定佃户要将苞芦挑送上门,不得短少。如果违反,要受到经济处罚或夺佃处罚。乾隆四十年十一月祁门赵双声等承佃程元祯等的山场锄种苞芦,“言定迭年交纳苞芦子一百六十斤正,其租言定迭年十月内挑送上门,不得拖欠,如违,罚苞芦伍十斤”。佃户违约除了受到“罚苞芦”的实物惩罚外,还有金钱处罚的手段。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程天喜承到程元会、程加灿的山地种植苞芦,契约规定递年交纳玉米八十斤,不得短少,“如违,听山主另召。其租言定十月初十日上门交付,过期行罚。定后二各无悔,悔之者甘罚钱八百文公用”。第三种违约惩罚方式,是“另佃他人兴种”,这种夺佃的处罚方式在契约里也较常见。乾隆四十五年六月,祁门程延芳承佃程加灿山地锄种苞芦,交纳120斤的苞芦实物租,“如违拖欠,听自另佃他人兴种,无得言说”①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1辑第7册,第230页、276页、318页。。
据契约文书记载,承种山地进行玉米垦殖还有少量交纳货币租的,主要是外地棚民租佃山地种植苞芦的情况。如嘉庆五年九月初二日安庆潜山人许正明承租祁门县凌凤鸣名下的山地,“开挖锄种苞芦,三面言定,递年交纳租银壹佰文,其银递年至冬至日交付,不致短少”②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11,第331页。。这种交纳货币租的情况在清后期很少见,可能与嘉庆以后当地对外来棚民开垦的禁令有关。
在此背景下,一些山主靠出租山场获得大量玉米收益,这里举一个实例。程加灿是乾嘉年间当地的一个大地主,他除出租山场给人种植稻、麦外,还有部分山场租给他人种植玉米,收取玉米实物租。据对系列契约的统计,程加灿在乾嘉年间年获玉米收益达1500斤以上③据程加灿收取玉米实物租的18则契约统计,契约出自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1辑第7册、第8册。。
四、玉米种植对山地林木的兴养有一定促进作用
清代玉米种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学界有深入论述,此种研究主要是针对棚民的无序开垦来论述的。学者指出,“棚民对徽州山区的无序开垦和恶性开采,对徽州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④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8页。;在长期饱受生态环境恶化之苦的情况下,“徽州山区社会采取了驱禁棚民与封山育林,调整产业种植结构相结合的标本兼治的应对措施”⑤陈瑞:《清代中期徽州山区生态环境恶化状况研究——以棚民营山活动为中心》,《安徽史学》2003年第6期。。清代棚民玉米种植活动对山地生态的破坏是客观存在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徽州契约的内容还显示了玉米种植的另一方面,即通过玉米、桐子种植促进松杉等林木的种植,这也是清代徽州玉米种植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层原因,为学界所未注意。
山主为了使承租人对荒山进行开发以种植松杉,常常允诺或同意承租人种植玉米、桐子等以获得额外收益。这种将种植松杉与垦种玉米结合起来的模式在清代徽州契约文书中多有体现。大量玉米垦种方面的文书显示,承山人、租山人负有“补插苗木”等兴养山林的义务,并且不得抛荒丈土,如果违反则要受到罚款等经济处罚。以下择要予以介绍。
早在乾隆年间就有将锄种苞芦所获作为承山人、租山人补插苗木报酬的情况,合同还会规定承山人、租山人对于补插苗木、保养苗木所应承担的义务,即“通山养苗,不得懈怠”。兹举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祁门程发秀等所立兴山合约为例:
立兴山合文人程发秀、汪嘉谟、程开警、叶之桂、汪时道、张成福,今有八保山场壹备,土名黄兵坑、合坞等处,眼仝业主,内取逞坞空山壹号,出佃与汪时道名下前去砍拨,锄种苞芦,补插苗木,议定就台演戏壹台,加禁合坞松杉,以供国课。如有地方梗顽之徒入山盗砍,准许原佃投鸣山主,演戏加禁。如不遵者,众山主务要均照山分出费,鸣官理治。如果知情不举、得钞卖放饮食,留情不报者,与盗伐之人同论。其合坞山场苗木成材议作三股均分,主得二股、利得一股,其利分务要凑便山主。如违,不与利分。⑥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1辑第7册,第214页。
嘉庆年间,也有不少享有垦种苞芦权利同时负有兴养林木职责的山林契约,种植苞芦的权限常常为五年。据嘉庆三年六月汪光生所立承兴山佃约,汪光生承佃到山主程发秀、程嘉灿等人的山场,“锄种花利、栽扦苗木”。锄种花利要交纳苞芦租,“其山锄种五年为止”,同时负有兴山义务:“其山栽扦苗木,毋得抛荒”,“日后苗木长大成材作贰八均分,主得八,力得贰”。有些契约还对兴养苗木作出更为具体的要求,比如“要丛密成林”“壹丈三栽”等。据嘉庆九年正月鲍胜保、张成初立承兴山佃约,鲍胜保、张成初承到山主程加灿等四人山场,“准种五年”,交纳苞芦实物租,同时也负有“栽坌苗木”的义务,“其苗木务要丛密成林,壹丈三栽,毋得抛荒丈土”,如果违反,则罚银二两①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1辑第8册,第39页、83页。。
嘉庆以后,此类将垦种苞芦与兴养林木捆绑在一起的契约仍有不少,也是明确规定承山、佃山人可在该山四至之内种植苞芦及桐子作为收益,但同时负有扦插苗木、兴养山林的义务。如光绪十六年祁门吴德伏在所立承山约中,吴德伏承种了吴广宪族侄名下的一块山地,规定若“苗荒不齐”,则吴德伏要受到经济处罚②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2辑第2册,第78页。。
栽植松杉之前种植玉米,是传统时期徽州山林开发的特点,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如此。如休宁县花桥村:
地主经营林山的方法是这样的:凡林山在初期培植树苗时,必须经过开发荒山的过程,因此地主把占有的荒山首先租给农民开发种植苞谷,三年不收租(有的收租,但租额比田租为轻),但三年期满后要给地主培养好树苗,如杉、桐等,每亩山要栽三千棵左右。到期如数点缴给山主(地主)。这种方式看起来农民有三年苞谷收益,其实收益很小,而开发荒山、栽种树苗所耗的劳力很大,所以是极其严重的剥削,地主们不要花什么代价,而坐待收益。③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安徽省农村调查》,内部资料,1952年,第208页。
歙县长陔区南源村的情况类似:“杉苗由栽种到长成为周围三尺粗的杉木要三十年,最肥沃的山也需二十年方能长成。杉木砍伐之后,放火烧山作肥料,第二年即开垦种苞芦,连种二三年后,土质渐瘦薄时,即栽植杉苗,过二三十年再行砍伐。”④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安徽省农村调查》,第219页。
五、小 结
在清代徽州农村社会,虽然各种力量对棚民种植玉米制订了诸多禁止性措施,但棚民种植玉米并未绝迹。而且,棚民玉米种植对当地居民产生了一定的技术示范作用,即所谓的“土著愚民间亦效尤”。玉米种植对徽州民众生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除了能缓解徽州地区粮食紧张的状况外,还使得玉米实物租大量出现,这反映出徽州民众对玉米这一粮食种类的认可。从遗存的徽州地区契约还可以看出,清代徽州玉米垦殖收益的分配方式是多样化的,一些山主通过出租山场可获得大量玉米实物收益。清代徽州地区玉米种植的发展还与徽州区域性种植结构有关,即徽州地区荒山在栽植松杉前常种植玉米。山主允诺或同意承租人种植玉米以使承租人获得额外收益,同时也起到了促进徽州林木种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