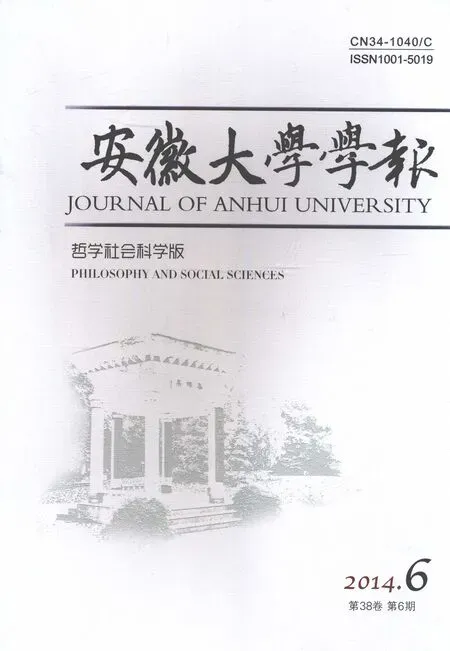明清徽州村社运作与宗族关系初探
2014-12-01张小坡
张小坡
在传统中国,社的崇拜与祭祀源远流长,直到民国时期也未曾中断,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走向。海内外学者对社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①可参阅杜正贞《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7~13页;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8页。。但学界对徽州社的研究尚不多见,日本学者牧野巽考察了明代徽州同族的社祭,认为明代徽州的社“虽然不是一族的祖先,而是庙的一种,宁可说是代表一个地方性的结合体更为适切”②[日]牧野巽:《明代同族的社祭记录之一例——关于〈休宁茗洲吴氏家记·社会记〉》,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第125~140页。。郑力民以歙南孝女会为例,对祠社关系、社庙结构等社屋的基本形态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从接菩萨、嬉菩萨、坐菩萨、送菩萨四个阶段解读了迎神赛会③郑力民:《徽州社屋的诸侧面——以歙南孝女会田野个案为例》,赵华富编:《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34~53页。。刘道胜对明清徽州会社关系文书进行了研究,认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宗族会社在徽州传统民间会社中占据重要地位,形形色色的会社使得徽州宗族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组织体系、社会主体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并在社会运行和演进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④刘道胜:《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5~201页。。陶明选考察了明清以来徽州会社所反映的信仰习俗,对会社兴盛的原因及其负面影响作了分析⑤陶明选:《明清以来徽州民间信仰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60~70页。。这些成果丰富了我们对传统时期徽州社的认识,但在揭示社的具体运行实态方面还有一定的发掘空间。
现存徽州各类文献中有关社的资料比较丰富,除了乾隆《橙阳散志》、民国《丰南志》等乡镇志的记述外,遗留下来的明清时期徽州族谱也保存了大量社的记载,其中既有立社的序文、社祭文,也有做社规约,还有社田的记载、社首轮值名单等。此外,可供披览的徽州文书中亦有不少社的文书,如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就收藏有《生活纪事文稿》《春秋社簿》等数份社祭文书。《生活纪事文稿》分年记载了从天启元年(1621)到弘光元年(1645)婺源朱氏春、秋二社祭祀的轮值、开支等情况;《春秋社簿》为万历刻本,但粗糙不堪,字迹多漫漶不清,记录了项氏举办春秋社祭的规约、利银收入、买房置地文契以及万历九年(1581)清丈户册等,内容颇为丰赡,亦有助于我们对社的理解。
本文即综合利用地方志、族谱、文书以及文集、笔记等文献资料,对明清徽州村社的运作实态及其与宗族的具体关系进行初步分析,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明清时期徽州社的概况
徽州设社的历史比较悠久,隋唐以前,社就开始零星出现,隆庆《续修新安歙北许村许氏东支世谱》载:“富昇社,在昇溪之右,本里之祖社也。肇建于南梁大同二年,迄宋景定甲子岁,幼学公同族许文伟等修葺,有石刻记文可考。东西二族春祈秋报,岁时崇祀焉。”①隆庆《续修新安歙北许村许氏东支世谱》卷2《墓道宫室桥梁考》。宋元时期,社在徽州普遍设立,明清达于极盛。如绩溪县,“祭赛社会之俗滥觞于北宋,而极盛于明清之间,兵燹以后此风顿戢”②民国《新安柯氏谱》卷26《杂记》。。康熙年间,程庭在返乡展墓日记中写下了家乡的风俗:“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支派有谱,源流难以混淆。”③程庭:《若庵集》卷5《春帆纪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8册,第114页。可见,社屋已成为徽州乡村不可或缺的一道景观,以致在歙县许村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话:“有女不嫁无祠无社之地。”④劳格文、王振忠主编,许骥著:《徽州传统村落社会——许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1页。意思是说许村的女子不能嫁到没有祠堂和社屋的村落,言外之意是将有无祠堂和社屋视为该地是否兴盛的标志,由此可见社屋之于村落的重要性。
明清时期徽州的社有两大系统,一是官方祀典体系下的社稷,徽州府及各县皆于城内设立社稷坛,于每年春秋仲月上戊日进行祭祀,本文略而不论。另一系统则是明初与里甲制度同时推行的里社。洪武八年(1375),诏天下乡民立社,规定:“凡各处乡村人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旸时若,五谷丰登。每岁一户轮当会首,常川洁净坛场,遇春秋二社,预期率办祭物,至日约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烛随用。祭毕,就行会饮。会中先令一人读抑强扶弱之誓,其词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力凌弱。违者先共制之,然后经官。或贫无可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并不许入会。’读誓词毕,长幼以次就坐,尽欢而退。务在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⑤申时行等修:《大明会典》卷94《群祀四·有司祀典下·里社》,《续修四库全书》本。可见,朱元璋力图将民间的社祭活动纳入官方的祭祀制度⑥郑振满指出:“明王朝推行里社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把各种宗教活动纳入官方的统一规范,以限制民间集会结社的自由。因此,明代的里社制度不仅是一种宗教制度,同时也是与里甲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郑振满:《明清福建里社组织的演变》,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6~337页。。但因经费所限,里社兴废无常,行之不久即多湮没无闻。嘉靖五年(1526),朝廷又重新明令地方立社。歙县知县孟镇为此将兴社“事理”刻石立碑,要求“永为遵守施行”:
直隶徽州府歙县孟为申明乡约以敦风化事。抄蒙巡差总理粮储兼巡按应天等处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陈案验备,仰县遵照。洪武礼制,每里建立里社坛场一所,就查本处淫祠寺观毁改为之,不必劳民伤财,仍行令各乡图遵行。嘉靖五年二月起,每遇春秋二社,出力办猪羊祭品,依式书写祭文,率领一里人户致祭,五行五献。设礼生冠带几人,务在诚敬丰洁,用虔祈报。祭毕就行会饮,并读抑强扶弱之词,成礼而退。仍于本里内推选年高矜式者一人为约正,有德行兼优者二人副之,照依乡约事宜置立簿二扇,或善或恶者各书一籍,每月一会,务在劝善惩恶,兴礼恤患,以厚风俗。乡社既定,然后立社学设教读以训童蒙,建社仓积粟谷以备凶荒,而古人教养之良法美意,率于此乎寓焉。果能行之,则雨旸时若,五谷丰登,而赋税自充;礼让兴行,风俗淳美,而词讼自简。何待于催科,何劳于听断,而水旱盗贼亦何足虑乎?此敦本尚实之政,良由此者,自当加意举行,不劳催督。各将领过乡约本数,建立过里社处所,选过约正、约副姓名,备造文册,各另径自申报,以凭查核。其兴之有迟速,行之有勤惰,而有司之贤否于此见焉。定于分别劝惩,决不虚示等因。奉此。除遵奉外,今将备蒙案验事理刻石立于本社,永为遵守施行。⑦《建立社坛示碑》,乾隆《橙阳散志》卷10《艺文志》。
可见,立社坛、设乡约、立社学、建社仓等举措已成为明朝治理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教化体系的重要环节。清康熙年间,徽州知府张叔珽以为明代之兴社,“其意大率本祈报之文,寓教养之法……一里之人咸聚焉。月有常会,会有常期,相与赏善罚恶,型仁讲义。立社学以训蒙,置社仓以贮谷,俾人自为教,家自为养”,故对江村重建慈化西社之举予以褒扬,并为之撰写碑记①《重建慈化西社记碑》,乾隆《橙阳散志》卷10《艺文志》。。在官方的鼓励下,社在徽州各地普遍设立。绩溪县里社,“城内及各乡群姓所置,在县东南者名德安社,在五根岭者名连城社,在翠眉麓者名西坛崇德社,并易坛以屋,易主以像”。婺源县“俗重社祭,里团结为会。社之日,击鼓迎神,祭而舞以乐之,祭毕颁肉群饮,语曰:‘社鼓鸣,春草生。’至秋而祭亦如之。闾里之欢,此为近古”②嘉庆《绩溪县志》卷7《祀典志·乡祀》;康熙《婺源县志》卷2《疆域志·风俗》。。徽州广大乡村以里为单位立社兴祀,以歙县西溪南为例,该地明清时期有社10处③民国《丰南志》卷2《舆地志·社宇》。,其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明清徽州歙县西溪南社之概况
歙县岩寺在明清时期也先后设立永兴义井社、长兴祖社、四义井社等15个里社组织④雍正《岩镇志草》元集《里社坛宇》。。江村立社的情况则为:“(新安)人心尚朴,事多近古,即乡社之举,至今独能行之,而江村则尤称最焉。其奉祀社稷,素有朝献之仪,每岁轮禋,无论家居恪遵先典,即远游千里外者亦莫不届期而至。其奉醴牵牲,诚敬丰洁,备极情文,可称盛举。”为顺利开展社祭活动,江村“里、外村介塘分二十四股,后并为十六股,轮司祀事,岁于正月上元前三日设祭演剧,陈列方物,广张灯彩,曰‘朝献’”⑤乾隆《橙阳散志》卷10《艺文志·重建慈化西社记碑》、卷6《礼仪志·祭祀》。。
古社制强调坛而不屋,多数地方设坛于山下,望山而祭。宋代,社坛开始立庙,庙中社主塑为人像,又配以夫妇,即广为所知的社公、社母。明清时期绩溪县境内的村社普遍易坛以屋,并“肖社神之像以祀之”,“(二月)戊日祀社,春祈秋报,岁凡二举,里自为域,献豜醉酒,尚遗古风。社神为男女二像,庞眉酷首,呼为社公、社母,社前有雨,谓之社公雨,言‘社神不能食宿水’”⑥康熙《绩溪县志》卷8《祀典志·坛壝》;嘉庆《绩溪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清同治年间黟县文人胡朝贺所著《知新录·提要录》亦云:“社翁社母,不饮宿水,故社日必雨,谓之社公雨。”⑦胡朝贺:《胡藤圃杂著·考·社稷考》,同治甲戌年镌刻,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藏。在明清徽州社会,社公、社母已逐渐成为社屋的代名词。笔者在绩溪县家朋乡幸福村竹里做田野调查时,曾根据康熙《周氏族谱正宗》中的村落图询问社屋遗址,村民周国发脱口而言“社公、社母在村西水口处”。虽然从宋代开始立社庙,但各地并没有完全步调一致,“乡里各自为之,非其国制然也”⑧胡朝贺:《胡藤圃杂著·考·社稷考》,同治甲戌年镌刻,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藏。。詹元相在《畏斋日记》中记录了清康熙年间婺源县庆源社无坛无庙的情况:“本村独无社坛,虽有社会,而祈报皆不得其所。惟各户轮流充首,迎至各家众屋中祭神、领胙而已。不知社无屋,于众屋中祭社,其事已非,又各户领胙而去,其有剩租,亦第春、秋二祭,其余祈雨祈晴,以及发风、驱耗等事并不之及。此而曰社何也?”①詹元相:《畏斋日记》,刘和惠标点,《清史资料》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9~200页。黟县直到清乾隆年间才因“坛场芜秽不洁”,开始建庙②胡朝贺:《胡藤圃杂著·考·社稷考》,同治甲戌年镌刻,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藏。。社屋一般为一间平房,偶尔也有两进的,规模大小不一。据今人许骥的调查,民国年间,歙县许村社屋为二进三开间,城东高阳社屋则为三进,社屋的内部格局是“下进有厢房两间,用于存放一些祭祀用品。上进是一个大厅,中间是一个神龛,神龛的上方悬挂着一字一匾的四个大字:‘土’、‘谷’、‘维’、‘修’。神龛前面摆放着供桌和香炉。供桌的左边安放有大钟,右边是大鼓。”③劳格文、王振忠主编,许骥著:《徽州传统村落社会——许村》,第393页。社屋的全称有一定的格式,一般写作“江南徽州府某县某乡某里某社”,但社屋门额均以末尾四字例题,如江村的“慈化西社”、呈坎的“长春大社”、岩寺的“长兴祖社”“义成祖社”等等。
二、明清徽州村社与宗族
据郑力民的研究,在宋明之间有社无祠的时期内,徽州各姓包括祭祖在内的种种族事活动即是在社中进行,或以社的名义举办,这时的社兼具后世祠堂的功能④郑力民:《徽州社屋的诸侧面——以歙南孝女会田野个案为例》,《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第34~53页。。常建华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证实了郑力民的观点,不过他强调明代中后期是徽州宗祠大规模兴起之时,而徽州宗祠的出现并且与社祭发生兼容可以追溯到宋元时代⑤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50页。。刘道胜亦指出,兴社成为宋元时期聚族而居的徽州地方村族祭祖祀神的重要形式⑥刘道胜:《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第177页。。
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与宗族的关系非常密切,众多的社屋由宗族所建。如休宁双溪毕良夫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号召族人重建河南敦睦大社,在交代立社原因时指出:“本族重兴祖社,乃先人所立,每岁依时致祭,以祈春种秋成,无失望也。爰自兵燹以后,人事出入,春秋祭祀,礼典缺焉。盖思先有其举,莫敢废也。兹今重兴社,薰莸同类,玉石混淆,于是族众会议,改立为河南敦睦大社。敦者,敦厚风俗;睦者,和睦姻族,是亦继志述事之一端也。”⑦正德《新安毕氏会通族谱》卷15《宫室志》。婺源上溪源程氏十九公自宋朝迁居溪源下村,六公迁居溪头上村,建坛于社屋溪。明成化八年(1472),程思隆等人以坛址弗利,重建于环拱坦,名曰崇兴上社。清雍正七年(1729)程暠辑录的《新安婺源上溪源程氏乡局记》中收录了此次重建的社庙钟文:“崇兴上社居民众信等,切缘社屋溪祖社坛少利,今众发诚心,议照丁粮出财卜地,于水口环拱坦填筑地基,创立社坛,重装圣像,铸造钟鼓,永充供养。上祝皇图巩固,下祈社界清平,壮观山川,匡扶人物,福音有攸归者。”⑧程暠:《成化社坛境神庙记(附社庙钟文)》,《新安婺源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抄本。徽州宗族甚至将立社视为聚族的一种手段,万历二十七年,方万山《柘源方氏族谱序》曰:“盖自予少时尝见时祭肇举,五派咸来……夫乡社亦聚族之一端也,昔也举同日、散同会,犹有家家扶醉之遗风焉。”⑨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2《各派谱序》。
徽州村社的建立存在多种形态,有的为一姓所建,并强调他姓不与,这类村社可称为祖社或族社,如万历休宁《茗洲吴氏家记》在《社会记》的前言中交代:“族社也,社名祈宁。”嘉靖《休宁县市吴氏本宗谱》在社款中明确提出:“吾吴氏恭立社神,惟本氏一族敬设,不紊外姓,名曰东岸节义社。计户三十有一,各备贮银若干,以为春秋祈报之需,年深月久,所积本利颇丰饶,递年出入银数另有收支簿以备存查。”⑩嘉靖《休宁县市吴氏本宗谱》附录卷10《社款》。歙县巨川毕氏设立的保厘祖社亦强调唯毕氏族人祀之:“保厘社庙,毕氏共建,春秋祭社稷之神。同治初适遭洪杨兵燹,至光绪壬午之末秋,族人重为建造。然古人何以命名曰保厘祖社邪?盖取毕公保厘东郊之意,保者,安也;厘者,理也。凡我巨川毕氏族人如遇水旱疾疫,皆赖神衹安而理之,所以惟我毕氏族人祀之,他姓不与焉。”⑪民国《巨川毕氏宗谱》卷5《宫室志》。
有的村社为多姓同建,如歙县潭渡黄氏的礼堂社,成化间社簿载社户不满三十,黄姓居大半,但仍有其他五姓,而朱姓居其一⑫《重订潭滨杂志·礼堂社》,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藏。。民国《新安柯氏谱》载:“嘉庆谱中又有麻田头社屋图,图中标明柯、程、王、董、李五姓同社,社额曰‘忠祈’,一切均与今同。此谱中又有三厅八社户之目,今族人亦传有是说,盖耕心堂派占一户,中和堂派占三户,敦伦堂派占四户,合其八户也。至八户之由来则无可考证,意者当日建社时,柯氏尚只八户,既各输建筑之费于前,复轮举祭赛之典于后,故遂因以得名欤。自咸同兵燹以后,中和堂派、敦伦堂派各有一户乏嗣,实际仅存六户。”①民国《新安柯氏谱》卷26《杂记》。由多姓同建的社有一部分在运作过程中逐渐归于单姓控制。据正德《新安毕氏会通族谱》载,歙县上北街毕氏于洪武十七年建河南福庆社稷行祠,“旧与杂姓淆混”,逮弘治癸丑(1493),毕元、毕永春、毕文玉等人“舍旧而新,惟与毕氏共祀之,而他姓不得与焉”,并创制立法,“甚得其宜,迄今礼乐衣冠容容如也”。毕文理还为之作序,颇可窥见毕氏何以单独立社的缘由:
今吾姓社原本与外姓相共,近数年来,老者希故,少者不知上古所立之风,不习规矩,希念至期饱食醉饮,甚则至于语言犯上,或相詈而散,无足观者。吾族众合议曰:“社本集义,今而如此,后必生祸。且吾族众不若另设,仍立祖社之名,春祈秋赛亦复如是。”今弘治十年春始立神牌,依姓郡氏,立河南福庆大社,稷之神是设。为因众姓混杂,无上古之风,弄酒乖张,难以为劝,一年一年,一代一代,尤恐后之子弟同流合污,仿效摧毁。吾之族氏古来良善,颇有文风,若不立成规矩,革故从新,亦复如是,是求荣反辱,求亲反疏也,徒哂于人,不如不设矣。今既族义立社,当以仁义处众,禀诸长少,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数事不可不察,齐家治国亦足为用是云。②正德《新安毕氏会通族谱》卷15《宫室志》。
歙县东门许氏宗族也是先与本关汪氏斋谕公等共为一社,宋季,荣甫公谋诸族人曰:“吾宗人繁衍,当自为一社,春秋祭祀,使子孙序昭穆、习礼义,或商或儒,各勤本业,谨守礼法,毋坠先志。”族人咸称善,于是该族自号为高阳和丰祖社③崇祯《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10《社序》。。明宣德二年(1427),许斯器在为该社营置义田所作序文中也同样强调单独祭社的重要性:“昔本族与异姓同奉社稷,后族内蕃衍,兼且异姓溷杂,意其不便,恐无以格神,是用改号高阳和丰祖社。凡遇春秋祭赛,皆吾宗枝子孙虔于祭奠,纯一不溷。逮至于今,咸仗神功,奕叶茂丽,以倍于前。”④乾隆《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10《本社营置义田序》。休宁茗洲吴氏的祈宁社亦经历了先与他姓共社,后将他姓逐出而单独祭社的过程:“先是,我社有非我族类溷其间者,凡四户,至正统丁卯社日尽绌之。增入我族户如其数,是社当称族社矣。长老曰:‘立社以来,故有纪事。今既称族社,则族属事尤载笔者所当记。’遂于是日具簿牒,书岁候,书牧长,及时事如故。”正统十二年(1447)春社之日,从本族内部增加四户以补前述去除的四户外姓,“是日,绌革吴宗成等非类者四户,新入德烜、德安、德皓、敏文四户”⑤万历《茗洲吴氏家记》卷10《社会记》。。从这个层面而言,由单姓祭祀的社也便具有族社的性质。
三、明清徽州村社的经费筹措与管理
社祭每年依例分为春社、秋社两次举办,由此需要一定的经费以维系社的正常运转。明清时期徽州各地村社的经费来源各有不同,但举其要者多集中在银和田两种形态上。有的社系社户出资襄助,如歙县虹梁村《程氏得卿公匣规条》规定:“支下轮值春秋两社,每户匣内贴纹银四钱。今议定发元丝银四钱一分二厘,社前十五日发。”⑥《歙县虹梁村程氏得卿公匣规条》,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资料室所藏复印本。歙县潭渡长至社规定,新入社者须出钞半锭,否则不许入分,并对旧社产立碑为记⑦雍正《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6《祠祀·元至正己丑长至社众公立礼堂旧社产土碑记》。。又如徽州项氏宗族,其族内旧例,新婚者每遇元宵,送花烛一对至祠堂,以求子嗣,按例设醴以酬答,后变其规,要求出银1钱5分入社,如此,项氏子孙便无需另外设置社田。经过多年积累,项氏春秋社的本利银已达124两余,除买田外,剩余银两放款生息。此外还规定,在64户社户中,新入者每户出5钱作为生息资本,违者以不义黜之。嘉靖十五年,社内资产清查情况如下:“今查众社内新旧银租二簿,置买山场田地,由成化丁未年在社子孙新娶者喜出花烛银一钱五分包利。至正德壬申始,买田起共存银一百二十四两二钱。后入社者出银五钱,又贡巧坑等处山场银放有利,田山有花,年积月累,共买民粮两硕,皆赖六十四户创。”从嘉靖十九年到三十年,项氏春秋社共有本银23两1钱8分,而利银达151两2钱,两者共计174两3钱6分⑧万历《春秋社簿·查簿遗》,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藏。。休宁县陪郭程氏在会约中规定,在会28户所出银两投积社内,每年由社首领去,加息3分,过春秋二戊,交与下次社首,社内各户添丁助银3分,亦同交付生息,不许隐匿侵欺,违者一罚倍十。另外,“在会人户每过二戊,亲赏缗币一付至当首,众取齐行礼,复以任时为约,有不至者罚银三分入众”。程氏族社还置有社田,订立合同,严禁社户盗卖:
我培[陪]郭程氏自宋元以来置立社田,具立规约,窃恐子孙众多,贤愚难保,原置文簿一扇或有损失,今立合同与诸房子孙收执,如有将社内田土盗卖及将存众钱本侵欺者,各执赴官陈告追给,仍将本人坐罪不孝,毋许入会者。
弘治十年八月十九日培[陪]郭程氏义社族众(以下28人名略)①弘治《休宁陪郭程氏本宗谱》附录《书锦坊陪郭义社首末》之《会约》、《社田合同》。
清嘉庆十一年(1806),歙县二十二图一都的郝、方、佘三姓公立社公神会,签订合同,对社内经费作出规定:
立议合同人郝、方、佘三姓人等,今因公议新起社公神会,名下议定每家喜取出银公放生息,其利言定会内支用,自议过之后无得退悔。公众退还银五钱,有本无利,倘有日后发大人圣,出银家家有份,如有无后,不得退还。其会二人合管,十二个月为满,将账算清以交下首,轮流交管。倘有上首不清,今首者倍赏。倘有人借去,须要硬保包付,方借用,不能自便取用。恐口无凭,立此合同一样二纸,各执一纸,永远存照。②《歙县二十二都一图方氏文书·清嘉庆十一年十月郝、方、佘三姓人等立议合同》,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3辑第3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
明清徽州村社的运作采取社首轮值制,当值社首负责该年春秋二祭的各事项,如办理不周,众议予以惩罚。休宁陪郭程氏订立了13年的社首当值顺序,每年春祈秋报各有一至二人轮值。流传于民间的《村社竹枝词》反映了社首操持忙碌的景象:“提灯社长唤邻家,今夜须教算莫差;某项某钱该某步,丝毫准折到棉纱。”③欧阳发、洪钢编著:《安徽竹枝词》,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60页。崇祯《生活纪事文稿》对每次社祭情况均记录在案,如崇祯六年(1633)八月十九日秋报,“头首弟子朱祉祚,酒肉羹饭俱好,鲞多一头,众议照前罚银三分整,家伙照旧不缺”。崇祯十年八月初三日秋报,“头首弟子朱立觉等,酒肉羹饭皆好,家伙照旧”。社首既承其责,也享有一定的权力。如绩溪县谷川柯氏的祖社名曰平安,向分六户。六户中推举一户轮流充当社首,每逢春社日为新旧社首换班之期,先行祀社,祀后新社首把米等物品颁给其余社户中有交谊者,并赠送给亲邻好友,旧社首亦如之,只是用蒸糕散发。每年元旦开门祭祀天地,须社首先举,届时合族数百家盥洗沐浴,执香以待,一闻社首鸣爆,则全村爆竹齐发;到除夕封门时,社首又居最后,如果社首已封门,而族众犹有未封者,则封门时不得鸣爆,违背此例者,族众共罚之。交年节也向无定期,例于腊八日由社首择定宣示大众④民国《新安柯氏谱》卷26《杂记》。。歙县潭渡春、秋二社皆设祭,虽然入社者有百户之多,“惟前后值年之二十户与祭,祭毕具饮福之礼,酒必老醇,肴必丰腆,炙鸡烹鱼,大胾肥脔,观者无不朵颐,稍有不善,则起訾之,盖循甲乙迭为宾主故也,然所费不赀,贫者每以为苦”⑤《重订潭滨杂志·社烛》,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藏。。
为保证社祭的顺利进行,明清徽州众多村社还制定了严格的社规。如《休宁县市吴氏本宗谱》收录的社款对立社的目的、如何办祭、社田的经管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社规是保证村社正常运行的章程,是社祭活动的准则,由社内全体成员共同制定,在经过成员同意之后开始生效,对全体成员产生约束力。一些村社还会对社规进行修改补充,如万历《春秋社簿》就先后收录了正德七年(1512)、嘉靖十五年(1536)、隆庆元年(1567)制定的社例条则,这为我们解读明代村社的管理运行实态提供了连续性的史料,有助于加深对明代徽州村社的认识。
正德七年订立了6条社例规则,主要是对社首所办酒馔及社银管理作出规定:
一、众社户尝牲,社首四人各己出肝、大肠五斤,好酒三杯,众用。
一、各社户出糯米半升,籼米一升,盐一两,纸十张,谷一秤。
一、赛社,各社首出好酒五杯及尝牲酒,如淡酸,倍罚之。
一、借银人户秋社之日领去,至次年秋社日齐要交纳,预期三日,社首同议各户催取,如期有误,每一日倍罚利一钱。
一、借社银照依前例供息,本利俱要白银,如有成色高低,凭众估补。
一、社之日以敬神为本,如在家而不亲莅者以亵渎论,罚白银一钱,如商游出外者不在此限,有子孙者许令替之。
嘉靖十五年秋,由众社户重新议订的社规比正德七年的社规要详细具体,有10条之多,从准备祭祀到祭祀礼仪的制定直至祭祀结束的分胙宴饮皆作了安排,涉及社祭的各个环节,其中有7条是对社首的规定,可看出社首在整个社祭过程中的重要性:
一、各社首每遇春秋二祭,先三日示谕各社户并执事者一十六人,务要斋戒沐浴,至是日清晨,各穿本色礼衣至祭坛行礼助祭,违者罚银五分入社公用。
一、各社首预集鼓乐,敬具祝版祭文,整备桌面各一张,奠食各三盏,羹饭各一碗,全猪各一口。五更,社首鸣锣一通,晓谕社户,亲临助祭,以敬为本,毋得懈怠喧哗,违者照前罚银公用。
一、例支社银一钱买香烛纸敬神。
一、未祭祀前十日,社首各出白糯米二斗,眼同上手社首造酒以备祭赛,众除干谷二秤抵还社首。如有造酒不如法者,俱是社首倍偿。
一、祭祀毕分胙外,其余猪首肝肺杂物烹熟,每户二株,好酒一壶,照依昭穆次序而饮。所言者皆寓道理之事,如有搀越次序,喧哗妄语,不依家规者,亦照前例罚银公用。
一、赛社毕,如不在家者,社首将所得酒肉送至大门之外,交与领去。如有不遵家规,闯至席内喧攘者,社首人户各照前例罚银。
一、社户名目务要照依房分,子承父名,排行次序,以便轮该社首。如有搀越者,亦照前例罚银公用。
一、每社首止许答牲首七斤、脚二只,余多不用。
一、社毕三日供,要将银两租谷结算明白交与下手社首,违者照前例罚。
一、社银,众举公道社首二人经管收支,如有不遵混收者照前例罚。
隆庆元年秋,又由九房尊长及公直者议立规约,该规约仅有4条,主要是对借社银逾期不还者社首如何催讨惩罚,以及对盗取社内器物者如何处理等作出规定,能够看出是对正德七年和嘉靖十五年所定规条的补充:
一、正借社银者至社日不还,众议停胙。
一、外借银者社日不还,照例除银一两,出社仍欠,照数加利扣算还社。如不还,众社户协同社首登门攻取,如社首不行催取以致拖欠,情甚不堪,仍要经手者催完,方许给胙,如不完,经手、社首一例停胙。
一、经收社内器皿等物乘盗匿不还者,将一家生日设誓,愿赔者听。
一、乘机盗社内器物赃证明白者坐赔,不准设誓,外人盗者,获赃报给赏告追。
四、余 论
传统徽州是中国境内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徽州地区的宗族制度堪称正统宗族制传承的典型。陈瑞指出,在中国宗族发展史上,徽州宗族已形成一种颇具自身鲜明个性特征的模式,或可称为宗族发展的“徽州模式”①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也正因为宗族在徽州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所以宗族与村社形成彼此难分的密切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明中叶以后,随着徽州宗族组织的不断完善,官方法定的里社祭祀制度因经费无常而趋于衰落的背景下,聚族而居的特征使得村社与宗族逐步融合,以族立社,社为宗族所有,各村的社庙有相当一部分成为家族的家庙。郑振满在研究明清福建里社组织的演变时曾指出:“清中叶以后,随着‘分社’、‘分祭’的日益盛行,里社组织逐渐趋于家族化、社区化或社团化。”②郑振满:《明清福建里社组织的演变》,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第351页。我们由此不难看出,徽州和福建两地在里社趋于家族化的时间上有先后之别。祭祀是徽州宗族的重要日常活动,宗族将社祭纳入岁时祭祀系统之中,既保证了村社的良性运行,同时也通过举办社祭,强化了宗族认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宗族整合。“社”作为一种地缘关系的象征机制,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共同构成地方社会的关系网络。围绕社祭及其所衍生出的迎神赛会,成为展示宗族实力,进行地域社会权力再分配的重要契机。探讨村社的运作,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考察明清徽州宗族及地方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