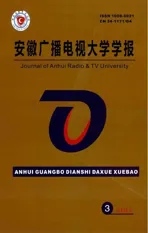自媒体时代极端维权的法社会学分析
——以冀中星案为例
2014-03-20谢昕欣
谢昕欣
(南京大学 法学院,南京 210093)
自媒体时代极端维权的法社会学分析
——以冀中星案为例
谢昕欣
(南京大学 法学院,南京 210093)
冀中星案是当下中国极端维权事件的缩影。极端维权反映出我国正规性传统维权渠道的失灵和制度缺陷,以及广大底层群体维权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而被迫选择其他非正规性维权渠道的现状。而在自媒体时代下,极端维权在网络和自媒体的广泛传播和影响下,显示明显的扩大效应和示范作用,对个体维权者的行动选择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极端维权在自媒体时代的负面社会效果凸显我国社会救济机制仍有很大不足。极端维权会降低正规维权渠道的公信力,因此,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
自媒体;极端维权;法社会学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7月20日,随着首都机场的一声巨响,全国上下的注意力聚集到一位名叫冀中星的山东籍残疾男子身上。冀中星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遂到机场发放传单,被阻拦后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到达大厅B出口外,引爆了自制的类似鞭炮的爆炸装置,造成本人胳膊受伤,一名警员也受轻伤。7.20首都机场爆炸案自发生后,成为互联网上又一热点话题,截至2013年7月25日,单从新浪微博平台统计来看,关于首都机场爆炸案的微博高达10万条,“首都机场”从案发之日起就持续位列热搜榜前三名之中。案发后,冀中星案在微博上引发了一场观点之战,一种观点认为冀中星爆炸了自己,点亮了他人,是义士之举,并对其八年艰辛的维权之举表示同情,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考虑,因其尚未造成严重伤亡,不应对其苛责;另一种观点认为冀中星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合引爆炸药还准备拉保安同归于尽危害很大,明显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更多的人将目光投向这个事件的起源,不断挖掘事情真相,并且开始反思当下的信访和司法制度以及社会救济和沟通问题。
冀中星案是近年来极端维权事件的一个缩影,一个突出特征是其社会影响力与自媒体的传播关系密切。我们不禁深思,如此小的个体维权案件为何社会反响如此之大,又是如何演变成一个社会热点案件?在自媒体时代下的中国,特别是在自媒体逐渐代替传统权威媒体的时代下,这种极端维权事件呈现怎样的新机制?又应当如何应对?
二、相关概念解析
(一)自媒体的概念及特征
美国新闻协会(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的媒体中心于2003年7月出版了一份有关博客传播模式的研究报告,将“自媒体”定义为“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事实、他们本身新闻的途径。”自媒体突破了传统传媒一贯的垄断地位,使每个普通人加入到社会话语权的行使中。微博、BBS、维基、podcasting等自媒体平台大量涌现,中国自媒体用户也迅猛增加。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即时通信网民规模达4.97亿,即时通信使用率为84.2%;博客和个人空间网民数量为4.01亿,使用率为68.0%;我国微博网民规模为3.31亿,网民中微博使用率达到了56.0%;我国社交网站网民规模为2.88亿,网民中社交网站使用比例为48.8%。[1]可以说,中国已经走入了自媒体时代,其时代特点也深深影响了当今言论格局。
第一,传播更加多样化、平民化与普泛化。在自媒体平台上,社会各个领域的事件都有可能进入大众的视野与讨论中,在官民关系、贫富分化、房价物价、城管执法、征地拆迁、司法公正、食品药品安全、教育政策等问题继续保持较高热度的同时,精神病鉴定收治、外地人引发群体冲突、环境污染事件、安全事故、公益慈善信任危机等新话题也呈明显上升趋势。另外,“分享”和“链接”使得“草根发行人”和事实传播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一方面人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博客、播客、网站等自媒体平台,另一方面社会公众人物不能在传统媒体发表的言论可以在自媒体的平台上自由发表,所以自媒体的“平民化”特别明显。也正是因为其多样性和平民化,自媒体的传播方式已经广泛进入每个人的生活,成了个人与外界重要的连接点,并随着连接点外延发展为蛛网似的社会言论网格。
第二,传播更加彰显个人色彩。和传统媒体相比较,自媒体时代的受众更加具有主观能动性和自主选择性,不仅成了内容消费者,还成了内容的生产者。浩如烟海的网络文化和互联网商业结构,给了网民更自由更全面的选择。传播个人主义意味着一种最小限度的国家或组织干预及最大限度的个人表达自由。这是一个开放社会所需要的个人主义。在自媒体时代,个体的优先价值才得以实现,普通公民、精英、政府机构可以在同一平台上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可以说,自媒体最大限度地凸显了平民的力量、个体的力量,促成传播的个人主义革命。
第三,易促成集体行动,产生群体效应。中国的信息流通长期内置于一个等级森严的科层体制内,各级官员垄断着绝大多数的信息流。从上至下的传播体系非常强大,机构与机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平行传播却几乎没有。自媒体大大改善了这种信息沟通状况,它带来了一种去中心化、去科层化的平行交流,有力地促成“共同意识”的形成与集体行动的生成。[2]在一个异质社会,平行分散的人们要组织起来面临着巨大的制度困境与组织成本,但在自媒体时代,这种组织变得容易。同样,在对某一事件的质问和声讨中,一个言论的提出与赞同在自媒体时代下,显得更加迅速,并且传染性和群体效应更强,“人肉搜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自媒体所具有的互动性,使网络“结社”变得简单而普遍。
(二)极端维权的概念及特征
“极端维权”顾名思义,即采用极端的手段,而非正常制度化和正规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以维护个人权益。比较常见的极端手段包括故意地通过伤害自己身体或生命的方式来维护个人权利,比如自焚、断指、开胸、割脉等,所以又称作“自残维权”或“身体维权”。维护的权益有住房、薪酬等财产权益,也有尊严、名誉等人身权益。[3]经过案例总结和分析,“极端维权”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极端维权者多为社会弱势群体,以农民工、无业者、社会底层人士为主。这些人群生活于社会平均经济水平以下,知识文化水平较低,为自身争取权利所拥有的自身能力有限。按照马斯洛需求定律,越贫穷的人,生存需求相比较其他需求更强烈,所以社会弱势群体更加重视基本生存权利,比如住房、求职、健康等权利,而这些权利被剥夺对于他们的生活影响相比其他阶层人群会更大,他们也对这些权利的变化更加敏感,而一旦被侵犯或剥夺,这些人群极易采取极端方式来维护个人权利。
第二,极端维权手段日趋暴力、残忍,反社会情绪较大,容易引起社会关注。近年来发生的极端维权案件越来越“惨不忍睹”,例如孙中界砍下手指向“钓鱼执法”说不;张海超为求真相开胸验肺揭穿谎言;唐福珍为抗拒拆迁最终点燃自己。
第三,极端维权事件中很大比例的事件是发生在个体与公权力之间,体现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和矛盾。长期以来,公权漠视私权,尤其对弱势群体的权益视而不见,加上一些政府官员官僚主义严重,服务意识缺乏,很难做到主动关注弱势群体的疾苦和心中的不满,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真诚地运用对话、协商机制解决问题,使得弱势群体与政府对话协商十分困难。如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长期得不到回应,或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长期得不到落实,或者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被任意践踏,就会使他们对政府产生仇视、对抗,进而促使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通过非理性的方式爆发。
三、自媒体时代极端维权的发生机制
(一)正规维权渠道堵塞
在我国,正规性维权渠道主要包括行政申诉、司法救济、信访制度等,这些渠道一般具有制度性的保障。现实中正规维权方式存在高昂的交易成本和制度固有的自身缺陷,使得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而维权者会因成本过高而绕开正规性维权渠道,而寻求其他路径。
在我国,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产生了救济不力、不及时、不公平的问题。“民权和法治已成为中国目前的时代话语”, 大量诉讼案件涌向法院,公民对于公平正义审判的需求巨大。而我国司法资源供给整体上存在不足,分配上也存在不均衡,当下的司法改革大力提倡的“司法能动主义”,赋予司法更多的社会任务,无论是从法官个人精力方面,还是从整个法院系统承受社会压力方面,都不堪重负。其次,司法脱离不了行政权力的影响,从而影响其公正裁判,特别在涉及公权力的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领域,“民告官”的难度仍然很大,起诉率很低,说明受到公权力侵犯的维权者对于通过司法途径而达到维护权利的目的信心不大,期望不高。最后,通过司法渠道维权成本较高,特别对于基层维权者而言,成本更加高昂,而期望收益却极不确定。
中国步入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和冲突增多,信访数量也急剧增加,随之出现“多次上访、越级上访、无理上访”等不合理信访行为。首先,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也存在供不应求问题,这也造成信访制度的低效,大大增加信访者的成本,降低其心理预期,从而降低信任度。其次,科层级的行政机关特征决定了信访制度的权力分配也呈现此特征。信访制度明显的科层级性质,促使民众产生对于高行政级别的信访机构权威的迷信,大量信访案件涌入省级或者国家级的信访机构,而这些机构并不了解具体情况,还是要将案件发送回原籍处理,这样一来一回所耗费的时间、人力、财力成本大大增加。最后,在信访过程中,耗费的财力、人力和精力巨大,普通人不堪重负。冀中星长达数年的上访并没有彻底解决纠纷,反而日积月累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使其对于社会的怨恨更深,信访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
(二)自媒体技术刺激维权极端化
自媒体作为非正规性渠道,虽然没有制度性的保障,但拥有独特的传播优势,日益被维权者所青睐。以微博为例,零门槛和平民化特征,使得社会每个群体都有平等的机会发泄不满情绪,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简洁和富有强烈生活气息的大众化文学表达形式以及图文并茂的综合效果,特别适合大众需求。在摆脱了那种类似下级向上级请示报告或民众向有关部门申诉上访、向裁判机关申请仲裁或起诉所需的正式、严肃、呆板的法律文书等公文式表达的羁绊与约束之后,近乎生活化、大众化的并常常伴随着图片与文字互动的文学式表达,可以将侵权事实和维权诉求表达得更加清楚明晰,且往往会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4]然而,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其对于维权的负面影响即在于容易将维权手段引向扩大化和极端化。
一方面,自媒体使个别事件影响扩大化,维权者为引起社会注意,而选择自媒体曝光。当个别维权事件发生后,自媒体通过全方位无死角的报道和强势道德批判,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从而达到向当局施加压力的效果,也间接形成了某种示范作用,使得维权者对于此渠道的价值评估较高,从而激励更多的维权者选择该渠道,而背离其他渠道。为寻求更多的关注,极端事件频发并愈演愈烈,这种事件的基数不断增加,从而使得维权者对此更加坚信不疑,因而被模仿的可能性增大。
另一方面,相比其他高成本低效率的渠道,自媒体这条维权渠道的风险小得多,“理性”的维权者会自动变更风险偏好,将更多的期望给予这种曝光渠道,越来越多的维权者选择这类渠道,甚至空置其他渠道。但发声之后如何获得更多的关注呢?正如高见泽磨所言,“逼迫他人自杀的人是会受到法律谴责的,在这种正义感情下,对于感到被逼入绝境的人来说,自杀成为最后的攻击性抵抗手段。扬言要自杀,并故意让他人看到为自杀而作的准备工作,仅此而已就可以成为进攻的手段,周围的人必须把这件事当作至关重要的事情来对待”[5]。事实上的确如此,“死亡能触动人们强烈的情感因素,并使除悲伤和同情之外没有多少其他共同点的人走到一起”[6]。为寻求尽可能高的曝光率和尽可能大的社会影响力,一个又一个极端维权案件爆发,社会影响一次比一次恶劣。“首都机场爆炸案”的当事人冀中星在经历起诉、上诉、上访等一系列正规性维权渠道后,均告失败,也求助过新闻记者,都没有得到合理处理,最后铤而走险采取这种引爆炸弹的方式来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其中一个细节是他特意选择机场的国际航班候车大厅,这里有更多的外国人,如果发生危险事件,不仅会造成国内恶劣影响,而且对我国的国际形象有很大程度的损害。
四、自媒体时代极端维权的社会效果
(一)促进维权矛盾的迅速解决
自媒体的特征之一是个人主义突出,此种特征表现在对于突发事件的反应中便是对事件的评论多样化,每当一个事件发生后,报道不再是光秃秃的纯叙事式的描述和单一立场的评论,而是生动多角度的直面报道和针锋相对的各种观点。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过程,原先小范围话题放大到更大领域甚至成为全国性热点关注的话题。发生极端事件后,媒体的报道总量在短时间内就能达到高峰,又加上极端事件本身关注度高,人际传播领域也异常活跃,使得信息的传递呈现“无影灯”效果。这样一来,这些极端事件总是比普通事件传播得更广。“冀中星案”发生后,现场群众在第一时间发布微博和现场图片,成为绝对的新闻发源地,并迅速发现冀中星的博客内容,将此事定性为维权事件。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冀中星案”已经成为最大的新闻。另外,不能忽视的是一个群体,即“意见领袖”,指在公众舆论中占有较高地位、拥有比普通人分量更重的话语权,拥有一定的言论权威的人或组织,比如大V、传统媒体、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等。这些人群特别具有名人串联效应,在这种扩大化影响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名人”比一般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们的关注与判断会在短时间内使事态升级,引起全社会关注。有关“冀中星案”的微博的转发群体构成主要有三类:媒体的官方认证微博,包括财经网、央视、财经、新浪航空、法制晚报、新华社,以及大批都市报和晚报的新浪认证微博;公共知识分子,如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崔向红、闾丘露薇、李开复,全媒体研究院秘书长张志安等大V第一时间转发;热心网友,如五月石、mild_luna、《大艺术》执行主编批评家陈默从现场第一时间发出微博和图片。[7]当个体事件扩大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热点事件时,个体维权的进展以及遇到的问题就不仅仅只关乎其个人,而是被放大为一个社会问题,全社会的人似乎都对该个体经历的遭遇“感同身受”,这就不得不加大政府等机关的压力。其导致的结果是,政府调集远超过处理个案的资源集中处理该个案,从而达到尽量短的时间内迅速处理,以回应愈演愈烈的“民愤”,在这个意义上相比正规性维权渠道更快更有效果。
(二)降低正规维权渠道的公信力
维权在自媒体时代走向极端的趋势,大大影响正规维权渠道的公信力,不仅影响干群关系,也会降低政府公信力和法律的权威。从当前来看,干群矛盾已经成了一种无法忽视的社会矛盾,而极端维权的蔓延正在使这种矛盾加剧。如果双方长期以暴力相加,用暴力来解决矛盾和冲突,最终只可能使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样,政府公信力建立在民众对其信任的基础上,保护其权利是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极端维权不断升级从侧面反映这种政府维权的方式已经出现巨大问题,在自媒体的渲染下,这种问题的严重性不仅被扩大化,而且深刻影响了当下人们对于政府的看法,在选择维权时也成为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自媒体时代极端维权对社会危害更大的是对于法律权威的损害。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在于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任和执行,而与其相反,极端维权倡导的并不是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社会关注度来迫使公权力机关来解决问题,这种模式本质上强调的不是规则意识,反而以破坏秩序为威胁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对于法律权威的公然挑衅。
此外,极端维权者的逻辑在于“闹大”就能维权,不再“小事化了”而是“小事闹大”,“制造出问题,给以戏剧性的夸大,引起人们的注意,给政府施加压力以解决此问题”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策略。[8]这种逻辑的本质是反规则的,甚至是无规则意识,这种以破坏规则为手段,用极其暴力和极端的方式来伸张权利的方式,在当下法治建设中却屡试不爽。极端维权降低的不仅是公民的规则意识和守法意识,也在整个维权领域制造了不好的先例,而现下政府在应对极端维权时的举措缺少远见,通过妥协而草草了事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自媒体时代。极端维权的社会影响力已经通过自媒体极易扩大到整个社会,而一旦处理不好,极易造成更加恶劣的结果,这对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机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五、自媒体时代极端维权的防范对策
前文已述,自媒体时代极端维权的发生原因之一是正规维权渠道堵塞。为此,首先应当健全原有的正规性维权渠道。与此同时,应加快建设社会预防机制,并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给予维权者足够的情感支持、行动协助和经济支持。此外,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在自媒体时代到来时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压力,自媒体影响下的网络传播在不适当的引导下极易走向歧途,有将暴力行为“合理化”甚至“英雄化”的倾向,赞扬“以暴抑暴”,用激进、暴戾手段解决矛盾冲突。这就需要政府引导媒体和网络,使其发挥积极作用。媒体和网络可以不遗余力赞扬公民理性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不要高标极端维权对于社会的意义,不应通过宣扬极端维权来吸引公众的视线。如果真正对社会对个体有益,应当提前介入事件。另外,塑造公民理性维权是一段长期工程,固然制度激励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对于公民理性维权的思维的教育应当是一项长期坚持的事业,[9]一方面需要公民教育系统工程的全面启动,多渠道、全方位进行理性思维的培养;另一方面,借助已经发生的事件,因势利导地予以引导锤炼公民理性思考的能力和品质。
[1] 〔美〕凯斯.R.桑斯坦.行为法律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43-470.
[2] 〔日〕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M].何勤华,李秀清,曲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96.
[3] 〔美〕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M].吴庆宏,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49.
[4] 〔英〕博温托·迪·苏伊.桑托斯.迈向新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M].刘坤轮,叶传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14.
[5] 汪大海,杨永娇,尹宗平.论身体维权的生成机制:基于社会安全阀的视角[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8(1):80-83.
[6] 潘祥辉.对自媒体革命的媒介社会学解读[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6):25-30.
[7] 杨建军,马治选.当代中国社会的维权行为:以维权类法治人物、案件和新闻为主要分析对象[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5):54-66.
[8] 徐祖澜.公民“闹大”维权的中国式解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4):29-37.
[9] 梅传强,贺宏波.通过微博维权预防群体性事件之研[J].法商研究,2013(2):17-23.
[10] 李立景.纠纷解决的舆论范式:传播学与法学科际交又视域中的级纷替代性解决分析[J].河北法学,2006(9):100-106.
[责任编辑 叶甲生]
TheAnalysisfromSociologyfromLawontheExtremeEventsinRightMaintaininginthe"We-Media"Era——Taking "Ji Zhong-xing Case" as an Example
XIE Xin-xin
(Law College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Ji Zhong-xing Case" is the miniature of Chinese extreme right maintaining events, which reflects the malfunctioning and defect of regular right-defending system. The social bottom class people's desire of rights protecting can't be satisfied and they have to seek for other irregular right-defending ways. In the era of "We-Media", these extreme events are widely spread by Internet and self-medias, taking obvious expansion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 and are deeply influencing people's right defending selecti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xtreme events in "We-Media" era are related with the deficient social remedy mechanisms of China. The extreme events in right maintaining will reduce the credibility of regular right maintaining channel, therefore, it should be prevented with effective measures.
"We-Media"; extreme right maintaining events; sociology of law
2014-04-28
谢昕欣(1990-),女,安徽芜湖人,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法经济学。
D920.5
:A
:1008-6021(2014)03-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