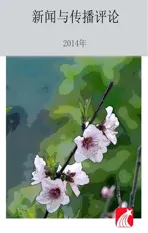大学形象研究的布尔迪厄立场
——《国家精英》的启示
2014-03-20王瀚东周中斌
□ 王瀚东 周中斌
大学形象研究的布尔迪厄立场
——《国家精英》的启示
□ 王瀚东*周中斌**
从批判的视角出发,大学形象的变迁所反映的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诸多关联,以及大学为代表的社会知识体系和社会权力体系之间的关联等问题,正在成为社会传播研究的关注重点。按照布尔迪厄对大学制度、知识系统和社会权力体系的讨论,大学形象作为“认识论秩序”的产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秩序,它的传播亦不可避免的成为象征性权力秩序的传播,一种以认可度为媒介标识的“服从”的传播。
大学形象 布尔迪厄 社会权力体系
大学形象,如同企业形象、政府形象、国家形象等,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和转型改革,已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媒介热衷的话题,并在近年来衍生出各类研究项目、课题、论文和专著。从行政的层面看,业已普及的中国高等教育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所滋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将不可避免给昔日的“象牙塔”带来腐蚀作用,影响大学整体的名誉,而大学形象、尤其是大学媒介形象的研究,当把关注焦点落在对危机事件的公关处理和舆论修复功能时,必然得到大学行政乃至政府管理部门的青睐。另一方面,从批判的视角出发,大学形象的变迁所反映的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诸多关联,以及大学为代表的社会知识体系和社会权力体系之间的关联,大学作为社会公平教育资源与大学等级排名、收费准入制度之间的矛盾,大学传播民主、科学、正义的社会义务与自身行政化、官僚化、神圣化的矛盾,正在成为社会研究、尤其是传播研究的关注重点。如布尔迪厄《国家精英》所给予的启示,以大学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作为研究对象,将不可避免地贯穿对大学制度、知识系统和社会权力体系的考量。
一、“认识论的秩序”与秩序的传播
在《国家精英》一书的序言中,布尔迪厄开门见山讨论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的对应关系,以确立其大学研究的基本哲学方法。在布尔迪厄看来,每个身处社会世界之中的行动者对其客观结构的探索本身也是对认知结构的探索。行动者在客观划分的社会结构中形成自己的心智结构,通过认知确立了划分社会世界的关注原则与划分原则。由此,行动者在社会空间或场域中具有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的双重身份。在大学体系中,学生、教师和教学机构的行动和表现依赖于各自的利益、观点和关注原则,而他们的利益、观点和原则等又是由社会客观结构中的位置所决定。另一方面,正是通过他们的行动和表现,大学的“行动者建构着社会现实,协调着他们赖以实施相互交流的条件”。(1页①)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研究者作为社会行动者,对大学形象建构与传播的结构性探索,实际上也是自身认知和心智结构的呈现。大学形象研究的分化差异,表面上看,是研究视点的不同,由于研究视点反映了研究者心智结构的差异和社会认知结构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是由研究者在社会结构中位置所确立,因此也是立场的问题。“而且,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借以认知、了解并改造世界的认识论范畴,其本身就是社会环境在主体身上的反映,那么,我们可以说,社会秩序在其本质上,就是一种认识论的秩序。”②因此,大学形象就不是一个教育学的命题,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社会学的命题。在布尔迪厄看来,教育社会学是“关于权力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通人类学”的基础,是知识社会学和权力社会学的一个篇章(8页)。
如果说,大学形象体现了社会秩序和认识论秩序的统一,那么传播作为认识论的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转换的中介性因素,根本上是秩序的传播。一篇来自国内某高校宣传部门的论文集中地反映了当下的大学形象研究通行命题和习惯话语:“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利用新闻传播的影响力构建地方高校的形象是事半功倍的选择。但是,传媒的‘新闻框架’影响着高校的预期新闻传播,媒体对高校负面信息报道的累积形成了社会公众的‘刻板成见’,要利用好这把‘双刃剑’,地方高校对内要利用媒体资源,建立高效的新闻传播体系、加强特色报道;对外要与大众媒体建立良好的新闻报道沟通合作机制,使二者的关系常态化,以提高公众对地方高校的认可度,使新闻传播成为地方高校良好形象构建的助推器和强化剂。”③在这一段论文摘要中,“利用资源”、“关系常态化”、“沟通合作”、“认可度”等语词的密集使用,无不指向“良好形象”所象征的大学既定的权力秩序,无不宣示以“新闻传播影响力”为标识的社会空间与大学之间的权力合作机制。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助推器”和“强化剂”的权力功能被赤裸裸地纳入大学形象建构的同谋诉求之中。正如布尔迪厄所言,“……倾向于这种同谋关系的习性也是一种效应,一种混合了霸权的效应。”这种同谋共构的大学“良好形象”具备了马克思意义上的“象征性暴力”:它是一群人心智结构的产物,又外化为制约他们的客观结构。“每当客观结构遇见了与之相适应的心智结构,人们所默认的这种制约必然得以实施。正是在客观结构与作为其产物的认知结构之间的原始同谋关系的基础上,绝对的、即时的服从才得以建立,这种服从就是人们出生所在的人群的教条经验中的服从——那个人群是一个毫不惊讶的社会④,在那里,一切都被当作不言而喻的事情来感知,因为现有秩序的内在倾向不断地同化某些本能地准备超越这些内在倾向的期待。”(7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归纳说,大学形象作为“认识论秩序”的产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秩序,它的传播亦不可避免的成为象征性权力秩序的传播,一种以认可度为媒介标识的“服从”的传播。
二、等级制仪式与“圣职授任礼”
如果说,《国家精英》等著作体现了布尔迪厄的“教育社会学”思想,那么这一思想的核心在于把教育的本质放在特定的权力场域中界定,将其视为一种着力于特定符号资本的分配、转换和再生产的过程,并在此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实现教育的中性化和神圣化。布尔迪厄认为,教育体系、尤其是大学具有“社会炼金术”的功能,通过对客观物质(资本)和主体认知能力的双重划分将社会分层神圣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的大学形象是社会等级制造者和时代秩序捍卫者的形象。
教育“炼金术”的主要程序之一是从全社会中“区隔”出一个大学生的特殊群体,“在社会鸿沟的形成和群体分离中,经过仔细选拔之后录取的学生被建构成了一个被分离的群体;当人们将这一过程当作合法化的选择来理解和认同的时候,它本身就会孕育出一种象征资本;如此建构起来的群体限制越严,排他性越强,其象征资本的意义就越大。垄断一旦得到认同,就会转化为精英。”(129页,黑体字为原译著所加。)大学生作为社会精英这一选择性、排他性或垄断的过程还将不断地经历时代发展、制度调整和政策“创新”。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有大学生身份的人群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大学录取率不断攀升,新开设的大学如新开张的楼盘一样层出不穷,导致垄断打破、精英遍野的世俗化危机。于是新的“区隔”举措出台:在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之间、在所谓的“一本”、“二本”和“三本”大学之间、在普通高校和重点高校之间、在“211”和“985”大学之间,体制划分出一系列的鸿沟和分层,以建立新的大学生选择机制和精英生产垄断的合法性。在全国性“中央级”、“主流”媒体的人事招聘公告中,堂而皇之的列出“211、985大学本科或研究生”这样的条件而不被视为歧视,可视为这种合法性强大效应的实例。“这种效应会越来越得到肯定和强化,原因在于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除了具有集体拥有的凝聚在称号里的象征资本之外,还在这种神奇的参股逻辑中具有了这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以个人名义拥有的象征资本。因此,这种异乎寻常的象征资本的集中便得以完成:聚集在一起的每一个年轻人都间接地借助于现有的象征资本和潜在的象征资本而使自己变得辉煌。”(129页)似乎是在验证布尔迪厄的上述论述,我们看到中国大学花样翻新、愈演愈烈的校庆活动每每挥发出上市公司挂牌仪式般深长而隆重的意味,以及校友会、杰出校友等名目在大学形象塑造中所营造的“股票”价值。
循着布尔迪厄的思路,划入不同层次的中国大学校庆仪式中校友的话语行动,将成为大学形象建构和传播研究的对象之一。校友会名单、杰出校友排名、以及一切与大学形象相关的排序,可能透露出大学形象建构那些最有用信息的一部分。在《国家精英》的正文中和每个部分的附录里都包含有大量的图表、数据及方法的详细阐述,为布尔迪厄的研究立场提供实证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在立场的关照下,枯燥乏味的数据变得生动鲜活起来。⑤“事实上,有用的信息常常都在行动者控制之外,存在于他们情不自禁地(有时候甚至是在他们的极力抵御中)流露出的信息与我们在别处收集到的(主要是关于其他机构的)信息之间的客观关系中。”(418页)当全国性媒体的招聘强调大学文凭的等级时,一个“一石二鸟”的策略或逻辑在起作用,即媒体排名分层的等级制和大学等级制的对应关系,媒介就业者文凭构成的等级制和他们进入大学杰出校友名单概率和顺序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通过不同场域中使用的分类原则的对应关系,以及在特殊情况下,学业场域使用的分类原则之间的对应关系,人们以最不易察觉的方式实现了最无懈可击的学业区分行为中所包含的社会歧视。”(469页)
按照布尔迪厄的理解,乍看起来,企业或社会的技能培训机构与大学之间、一般性大学与重点名牌大学之间的区别标准产生于教学活动,由教学的技术职能的普遍表现所决定,但实际的情况正相反,“从学校里获得的技术性能力在职业实践活动中运用得越少,或者说运用的时间越短,确保这些能力的称号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就越大。”(114页)换句话说,一个“985”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可能和一所地方院校的同专业学生掌握同样的或更少的采、写、编、评新闻技能,但是前者更可能在高级别的媒体就业,并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一来也就更能说明其文凭具有较高的“含金量”。因此,必须从教学活动的技术效应的对立面来提出问题:任何一项教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以造就特殊的神圣人群为目的的神话行动或制度化仪式?技术职能所产生的效应是不是掩饰大学履行礼仪性排他功能的合法表象?布尔迪厄认为,学业称号是得到公众认同的权力机关颁发的关于能力的证明,但是对于学业称号所证明的能力人们却永远也不可能分辨。从权力意义上说,学业称号赋予其拥有者的法定特性如“才智”、“技能”、“文化”等,独立于主观和局部的估计,混合了技术的和社会的因素,超越了个体自我而被赋予客观、普遍的效能。(673页)在封建社会中,教会机构的使命是将贵族阶层获得的(物质的)权力转换成神圣的权力,在以晚期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复杂社会中,学校接管了这种使社会分层神圣化的工作。“事实上,学业称号就是人们所说的国家魔法的最好体现”。(672页)布尔迪厄的结论是:所有以理性自诩的社会正是通过所谓的“圣职授任礼”来造就大学精英。(115页)而大学形象的研究可以从“圣职授任礼”现象出发建立起批判的视野。
三、双重的资本再生产与“国家魔法”
如同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把中世纪“授爵仪式的深层意义”看做“骑士的思想观念深刻转型的一个象征”,布尔迪厄认为,经由教育获得头衔的“圣职授任礼”,在其深层意义上则标志着一种新的统治形式的巩固,以及一种相应的社会策略的转变。通过这样一种策略,统治阶级迅速地并不断地自我转变,从而维持并控制了自己的统治。传统上,“在俗权与神权(或文化权)之间、士兵与教士之间,实业家(有时人们也称之为工业骑士)与知识分子之间,霸权的分工存在着根本的对立。或许在诸如此类错综复杂的历史年轮中权力场域的结构代表了某些不变的特征”。(460页)随着正式的理性国家的建立,这种二元性对立的双方被更换成更为复杂的、由多种场域交叉联系构成的网状系统,而诸种形式的社会权力便在这些场域中有效地流通并集中。这种互相依赖的网状链条把自己严密地缝合起来,形成一个特殊的整体,即“权力场域”。“权力场域”从经济场域的一端一直延伸到文化场域另一端。在经济和文化生产两个权力场域之间陈列着众多权力空间,或与经济资本相适应,或与文化资本相符合,分别占有不同的优势。但是,任何一种权力都不可能满足于仅仅作为一种权力而存在,不可能作为一种没有理由、没有依托的力量,它需要为自身的存在和存在形式寻找合理性和合法性,以掩盖自己专制的基础。因此,不同类别资本的拥有者发展出“维持或改善他们在社会空间中位置的再生产策略”。(459页)于是,一方面,掌握经济命脉的那部分人,“求助于学业上某种形式的神化,哪怕是最基本的神化,倾向于成为越来越广泛,越来越迫切的需要”。“以财产和财产所有者为基础的霸权模式演变成了另一种更理性、更民主,建立在‘技能’和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基础上的霸权模式。”(526页)另一方面,“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商”,掌握文化资本和象征符号的那一部分人则通过进入政府管理和工商企业管理领域,获的财富和经济掌控权,并强化了其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的霸权。这样的资本和权力双重、双向的再生产构成社会统治精英诞生的核心过程。正如布尔迪厄引用诗人波德莱尔的话:“一些人拥有智慧,另一些人拥有财产;当某一个辉煌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智者将成为有产者,而有产者将成为智者。这样,你们的力量将得以完善;面对这样的力量,谁都不会有半点异议。”(453页)
在布尔迪厄看来,大学的场域所形成的学业再生产方式比起企业、家族式权力传递的直接方式和简单程序更能够忍耐社会结构的骤变。因为教学体制的运作表面上像抽签一样具有公正性,而“这个充满系统性偏差的体制带着满脸的清白和无辜产生的效应”最终还是无限接近于通过直接继承进行权力传递所能达到的效应。(501页)由于大学通过学业完成的再生产过程和效应不是随机的、任意的,从而具有了社会公正论层面的合法性。这是“国家的魔法”。学业称号以国家的名义授予,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并作为国家建立和保证的象征性特权,作为行使某种职能和享受某类收益的独一无二的权力进入这种联系。“无论资本是以信用货币的形式出现,还是作为普遍有效的学业称号而存在,国家对每一资本类别所提供的保障或许就是国家作为国库而存在的最重要的效应之一,因为这个国库保证为私人占有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和象征资源。”(674页)
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形象归根到底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大学形象传播实质上是对国家精英生产神圣化的过程,因而也是权力资本再生产的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大众媒介的介入和推动的大学形象的传播进一步强化了“国家魔法”的表演。确实,“媒体对高校负面信息报道的累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表演和舞台的外在效果,将一部分的舞台“表演者”(大学机构、大学老师和大学生等)的神圣面貌打回原形。但是本质上传播媒介作为“国家魔法”整体呈现功能的一部分,它所起的作用如同戏剧批评一样,对于表演水准和观众品味提升至关重要,它对于不尽力、不称职、不“入戏”的大学形象表演者的揭露将有助于教育魔术表演的不断完善、演员水准的不断提高,并保证将那些“穿帮”者剔除在外。最低限度而言,即使如同批评家不能直接介入戏剧表演流程的改变,大众传媒对大学形象瑕疵的披露也不断提醒着社会对高等教育神圣理想的追求。如此,大学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纳入到布尔迪厄所描述的“合法化工作的基本经济法则”,从事于塑造良好大学形象、提高大学象征地位活动的大众传播或宣传机构,必然要在“信息含量最大化与赞美者(可见的)自主性的最大化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状态”,(689页)从而谋求大学形象传播的象征效能的最大化。
注释:
① 以下正文引用中只标明页码之处皆引自P.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图书馆,2005.
② 罗克·华康德、解读皮埃尔·布迪厄的“资本”——《国家精英》英译本引言、郭持华 赵志义译、引自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5/08/198.html。
③ 宋海霞.新闻传播对地方高校形象构建的影响及策略.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9/3。
④ 上引国内某高校宣传部门论文的表达方式,在另一种新闻语境或社会语境下读起来令人不可思议,而我们确实毫不惊讶,一切不言而喻。
⑤ 正如英译本引言所说,“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众多作品中,《国家精英》可能是最为费解,最具矛盾性的,无疑这些原因给国外读者带来了许多困惑。它的矛盾性体现在:第一,它引用的实证材料的性质与范围全部源自法国本土,然而其分析的意图与所达到的深度却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第二,这是一部深深烙上了布尔迪厄社会学风格的作品,所有的问题全部被具体材料实证化、数据化了,但是一种强有力的理论框架又赋予了它鲜活的生命力,并使它置于本世纪末有关权力、文化和理性讨论的漩涡之中。”同注2。
Bourdieu's Stand in His Critical Study of University Image
From critical view,the image of high education institute represents its relationship with politics,economics and society,as well as the social knowledge system and social power system.According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university,acknowledge and social power system by Pierre Bourdieu,the image of university as the symbol of social power communicates the order of society.
the image of university,Pierre Bourdieu,social power system
Zhongbin Zhou,Ph.D candidate,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Wuhan University.
* 王瀚东,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Handong Wang,Ph.D,Professor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Wuhan University.Mainly interested in interculture communication,broasting and television,media econology etc.
** 周中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