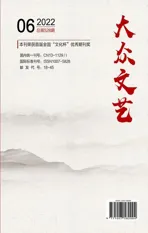论卞之琳前期诗歌创作中的时空关系
2014-03-13吕竹慧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7
吕竹慧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387)
论卞之琳前期诗歌创作中的时空关系
吕竹慧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387)
对时空关系的思考总是关乎人们认知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卞之琳前一个时期的诗作在组织时空距离时常常表现为交替、错位、跳跃、相对这几大特征。诗人把对时空关系的调度与组织化为种种的印象与经验,并从相对观念出发以智性的感悟去把握人生。时间长河里的世俗生态在相对性概念的暗示下给诗人带来一种全新的认知体验。相对观念在卞之琳这段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到了一种平衡作用。
卞之琳;时间意识;时空关系;相对
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回顾自己的诗歌创作历程时,把1937年抗日战争以前定为其诗创作的前一个时期。卞之琳前期的诗作中有绝大部分都蕴涵着深刻的时间意识,他对时空关系的调度与组织化为种种的印象与经验,其一瞬间的情感都沉淀为思辨的理趣,继而在相对概念的指引下去思考时空关系,并且从相对观念出发以智性的感悟去把握人生,时间长河里的世俗生态在相对性概念的暗示下给诗人带来一种全新的认知体验。时间流动、时空交替、时空错位、相对性的隐喻,本文将从这几个方面来讨论其诗歌作品。
人类社会需要时间和空间,于是人们把自然事物形态的变化特点认知为时间的作用,把自然事物的变化现象认知为空间的存在。对时空关系的思考总是关乎人们认知世界的角度和方式。诗人们总会强调一种属于时间动力学范围的相近观念,即一切“现在”都注定要变成种种的“过去”。时间把一切都分离成无穷的“之前”和“之后”系列,而这一切又必定在时间的销蚀中折射出它们的存在。
智者临水的喟叹是卞之琳早期诗作里一以贯之的“层叠的悲哀”,诗人从天光云影对世间万物的自然投射上观看时间形迹、省察光阴的流逝。“五点钟贴一角夕阳,/六点钟挂半轮灯火,/想有人把所有的日子/就过在做做梦,看看墙,/墙头草长了又黄了。”(《墙头草》)五点钟的夕阳、六点钟的灯火暗示着昼夜的交替,时间如此具体地向前迈步,而日子却仅是重复着过去,只有那墙头草长了又黄了,还带有变化的痕迹。在《寄流水》和《秋窗》中诗人怅惘的是红颜易逝和好景不长,喻示的是被发现的命运已今非昔比,而未被发现的命运则沉寂在时空里,“回头看过去的足迹”或是“对暮色苍茫的古镜梦想少年的红晕”都不免令人怅然。诗人又在《古镇的梦》中借助那不曾间断的“桥下流水的声音”暗示了“时间”的概念,同时以流水的永恒来对比人事的短暂,以时间的流动对照人的沉睡和无动于衷。随即,“檐溜滴穿的石阶,/绳子锯缺的井栏”使得时间的形迹更加具体,诗人缘此感叹:“时间磨透于忍耐!”(《白螺壳》)在普遍又严苛的时间法则面前,人无法直接对抗现代标准时间的冷漠无情,只能寄身在时间之流中“看夕阳在灰墙上”(《秋窗》),“听你的青春被蚕食”(《圆宝盒》),因此,当回过头去作往日之追寻时,不免感伤于这种时间的命定与悲哀。
时间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将销蚀任何一个极具忍耐心的人,所以总会出现人为控制地去截断时间之流的尝试。通过对时空关系的思考,卞之琳的诗作在组织时空距离时常常表现为交替、错位、跳跃、相对这几大特征。
在《雨同我》中,“‘天天下雨,自从你走了。’/‘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这一“走”一“来”形成了一段时空的交替。《水成岩》通过具体物象展现时序的更替:发黄的照片尘封在旧桌子抽屉里——那是被时间偷走的青春,一架的瑰艳藏在干瘪的扁豆荚里——那是被时间风干的美丽。《远行》则是在骆驼这一骑行工具的牵引下在时空中穿梭,先“涌上了沉睡的大漠”,又“穿进了黄昏的寂寞”。《西长安街》中时空的交错纠缠尤为突出,诗的第一段作于两年前的初冬,留此作为回忆,写的是老人和老人在长长的西长安街沉默地走着;在“影子”的衔接下,第二段向前进到两年以后,虽然时间前移了,但是人却感觉不到究竟在这条街上走了多少年,时间仿佛凝固一般地让人察觉不到变化;到第三段时,随着空间的变换——对古代长安的想象,时间又后移了并向着更远的历史延伸回去。《音尘》一诗常常将距离拉远,将时间移开,在超越具体环境之后模糊了时空的界限从而展现出时空跳跃的一帧帧画面,不管是“月夜”中“孤独的火车站”还是“夕阳里的咸阳古道”,仿佛是有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人能够随时消失并出现在另一个地方,这种不在规则内的空间传输带来了短暂的混乱和兴奋。《车站》也是由“潮来潮去”而引发的诗思,古人“逝者如斯”的慨叹,同“我”这个现代人静止地被贴在车站旁,形成了时空上大跨度的错位。
卞之琳的诗采取的是一种独特的时空感知和组织方式,诗人不愿对时光听之任之,他有时安排空间物的位移去完成不同时空间的置换,有时又让一维时间去和三维空间的不同弧线交织,为时间赋形。最终诗人豁然于找到一种解释宇宙人生的秘要,即相对。卞之琳在1934年翻译普鲁斯特的《往日之追寻》片段时作“按语”说:“这里的种种全是相对的,时间纠缠着空间,确乎成为了第四度(the forth dimension),看起来很玄,却正合爱因斯坦的学说。”“相对”是卞之琳完成时空思考的重要立足点,在他的作品里,时空关系大多是在意识流动中任意组合的,而只有在相对的观念中,才能突破现实时空关系的局限,突破日常逻辑的束缚,使自然外在与个体心灵达成自由跳跃和多重互换的默契。
“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报上。”《距离的组织》表达着一种国事的兴亡感和历史追思。罗马灭亡星与1935年的“现时”形成时空的相对,两千年漫长的历史也不过是宇宙的一瞬间,历史在这里借空间和距离传达着某种虚无感和茫然感。古罗马帝国覆灭时突然爆发的星球,其璀璨的光束竟到千年之后才投射到地球。正如诗人所说:“一刹那未尝不可以是千古。浅近而不恰切一点的说,忘记时间。具体一点呢,如纪德(Gide)所说,‘开花在时间以外’。”除了时空相对之外,这首诗中还体现出表象实体的相对、主客体相对、微观和宏观的相对以及存在与知觉的相对。
“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劫。”(李叔同译布莱克的《天真的预言》)《圆宝盒》里也充分体现出这种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相对的理趣。“一颗晶莹的水银/拥有全世界的色相”,说的是物质形体上的大小相对;“一颗金黄的灯火/笼罩有一场华宴”,暗含着空间上远与近的相对;“一颗新鲜的雨点/含有你昨夜的叹息”,雨点之短促、叹息之绵长又形成了时间上的短长相对。卞之琳自己曾在解释《圆宝盒》的创作思路时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我的‘圆宝盒’也可大可小,所以在人家看来也许会小到像一颗珍珠,或者一颗星。比较玄妙一点,在哲学上例有佛家的思想,在诗上例有白来客(W. Blake)的‘一砂一世界’。合乎科学一点,浅近一点,则我们知道我们所看见的天上的一颗小小的星,说不定要比地球大好几倍呢;我们在大厦里举行盛宴,灯烛辉煌,在相当的远处看来也不过‘金黄的一点’而已:故有此最后一语,‘好挂在耳边的珍珠——宝石?——星?”“虽然你们的握手/是桥——是桥——可是桥/也搭在我的圆宝盒里”,这句中“握手”是瞬时的,而“桥”却是衔接永恒情谊的象征,刹那的瞬间包含了千古的永恒。时间的相对随即又转向空间的相对,圆宝盒虽然只是天河中一件小小的装饰品,但在我看来它却可以容纳全世界的色相,可以放进一座结合情感的桥梁。
再看《航海》一诗中独特的时空观与相对意识。首句轮船的“直航”点出时间的流动和空间的延展,接下来以“说话的茶房”链接起不同时空间的切换和对照。现在的茶房虽然在骄傲地校对标准时间,但童年时依然有过想追赶时间的幼稚,“童心的失望”在于他想通过具体的空间运动来替换抽象的时间,却不能懂得时间的线性流动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茶房的经历引发了“多思者”的回忆:“想起在家乡认一夜的长途/于窗槛上一段蜗牛的银迹”,同样的时间里发生着不同的空间位移,时间在距离的变化中完成了种种变形,这种以空间距离为时间赋形的观照方式给人带来官感与内涵兼具的思辨美。废名论此诗时谈到:“蜗牛的一段银迹等于一只轮船的二百理的一夜,而茶房的差一刻钟又要对一对,时间与空间真是严格得很,荒唐得很,有趣得很。”此外,航海的形象通常是用来比喻人生旅行的,蜗牛的意象在佛经中也是俗世众生的代表,诗人通过“茶房”和“多思者”进行视角间的转换,以相对观念表达着他对人生的种种感悟。卞之琳在其散文《成长》中明确阐述了“相对”的内涵:“把一件东西,从这一面看看,又从那一面看看,相对相对,使得人聪明,进一步也使得人糊涂。因为相对相对,天地扩大了,可是弄到后来容易茫然自失。”
现实时间的不可逆转容易使人生出惘然与悲哀,“要知道,绝对呢,自然不可能;绝对的相对把一切都搅乱了:何妨平均一下,取一个中庸之道?何妨来一个立场,定一个标准?何妨来一个相对的绝对?”诗人因而借助“相对”观念的中和来使自己释然于“命定”的困惑,时空的形迹在诗中任他自由地组合和控制。相对观念在卞之琳这段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到了一种平衡作用,一方面被用来昭示空间的延展以开拓人的心境,另一方面被用来应对自然时间的直线型流动以抚慰诗人对人生轮回循环的怅惘与焦灼。
[1]卞之琳.江若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0.
[2]废名.朱英诞.陈均编订.新诗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
[3]张曼仪编著.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M].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