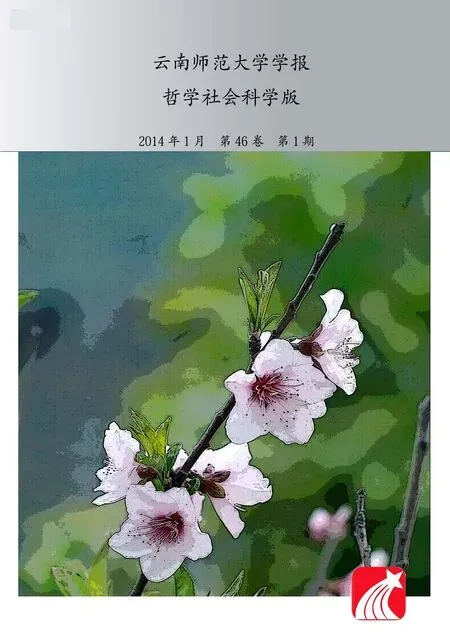共鸣:一个更需重视的悲剧生成审美机制
——从“中国无悲剧说”谈起*
2014-03-12寇鹏程
寇鹏程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近代以来,很多知名学者都纷纷指责“中国无悲剧”,*这些人中著名的有: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中国的戏曲小说都是乐天的,“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蔡元培《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中说:“西人重视悲剧,而我国则竟尚喜剧。”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曲改良》中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点。无论是小说,是戏剧,只是一个美满的团圆。”鲁迅先生也认为中国实在少真正悲剧:“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统统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等。当前也有很多学者依然继承了这种思想,致使这种观点广为传播,这使得近百年来我们关于悲剧的知识总量似乎并无多大增长。实际上“中国无悲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个伪命题,因为这是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悲剧的超越性而忽视了它的共鸣性结果。共鸣与超越本来是悲剧生成的两个机制,但是现在悲剧的“双轨”审美机制变成了“单轨制”,由此而单方面地将一大批悲剧排斥在所谓“真正的悲剧”之外,从而引发了无尽的争论。
一
在中国的知识语境中,我们流行的是“崇高悲剧”,只把具有“崇高精神”的悲剧当作真正的悲剧,强调悲剧里蕴含的伟大力量,主人公的抗争奋斗精神,主体尊严的“严肃”意义,其“英雄主义”的超越性成为“悲剧精神”的核心。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朱光潜先生的《悲剧心理学》就提出:“悲剧感是崇高感的一种形式……要给悲剧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崇高的一种,与其他各种崇高一样具有令人生畏而又使人振奋鼓舞的力量。”[1][p.301-302]朱先生认为观赏一部伟大的悲剧就好像观看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是感到面对某种压倒一切的力量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却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悲剧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生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朱先生完全是按照崇高美学的心理机制来阐释悲剧的美感,强调悲剧超越现实生活的那种强大“震撼”与“鼓舞”的“力量”。由此朱先生把中国的悲剧排斥在真正悲剧的行列之外,他说:“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2][p.428]由于朱光潜先生在中国美学、文艺理论界的深远影响,这种解释几乎成了我们解释悲剧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重视文学“大”的超越性的社会启蒙意义,而看轻其“小”的对于读者个人情感慰藉、共鸣的意义,这是我们对悲剧普遍的看法。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一代学者都是从“拯救国民性”与社会启蒙的角度出发而贬低中国悲剧的。而当代很多学者也都以此为标准继续贬低中国悲剧。前不久王富仁先生发表的长文《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就明显的是这种崇高悲剧理念的翻版。王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悲剧只具有一种“悲剧意识”,大多数只是一种“悲情悲剧”,并不是“真正的悲剧”。因为真正的悲剧具有一种永恒“反抗”的精神:“人将永远反抗宇宙的意志,反抗大自然的威胁,这种反抗永远没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天,这种反抗是无望的,是悲剧性的,但人却不能放弃这种反抗。人在这反抗中才表现着自己的独立性,表现着自己的独立意志,表现着自己主体性的力量。显而易见,这就是贯穿在悲剧中的悲剧精神。”[3]王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悲剧不具有这种宏大的“主体性力量”的反抗精神,表现不出“独立意志”,往往只具有“冤”、“怨”、“苦”的“悲情”,往往还只是“人生的叹息”,还只具有一种“悲剧意识”,还不够称为真正的悲剧。王富仁先生把“崇高”悲剧作为悲剧的标准,将“反抗”的多少与大小作为是否是真正悲剧的标准,认为我们只有“悲情悲剧”,“缺少崇高悲剧中那种理性精神和意志力量”,所以他呼唤崇高悲剧,并且认为中国人就是缺乏韧性战斗精神,而“崇高悲剧观念恰恰是医治这种国民性的良药”。王先生用崇高悲剧来医治国民性,让悲剧继续承担“启蒙”的重大社会使命,这样就仍然把中国传统的悲剧排除在“真正的悲剧”之外,这大概是继承了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良苦用心。
中国几代学者在悲剧问题上,实际上都秉承着大致相同的一种崇高悲剧观念,并进而重复着一个大致相似的“中国无真正悲剧”的结论。年轻一些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并没有更多的进展。黄克剑在《“悲”从何来?——就悲剧之“悲”对中西文学人文趣向的一个比较》中指出中国戏剧中常有一些演唱某一凄楚故事或若干惨烈情节的“苦戏”,还不能称为真正的悲剧,他认为像《窦娥冤》之类的悲剧最好还是称为“冤剧”:“冤是关汉卿的《窦娥冤》的主题辞,它的全部戏路纠结在主人公的那份令人凄绝、痛绝的‘冤’情上。悲苦由‘冤’而来,这剧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冤’剧。”[4]而一些更年轻的学者也在重复这样的悲剧观,孙秀昌在《两周时代“命”意识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悲”意识的影响》中说:“中国所谓的‘悲剧’事实上仍是一种‘冤剧’或‘怨剧’。”[5]于此我们已经能够证明近百年来在悲剧观念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进步并不大,知识扩充点并没有增加多少,并没有太多新的知识生长点,我们一直重复的是用崇高悲剧观念来证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学作品还没有过真正的悲剧而已。
二
我们很难跳出这样“宏大”悲剧观的价值阈限。悲剧不能是悲观的,必须是“乐观”的反抗与战斗,伤心、沮丧、不幸、忧郁等被看成了悲剧的“障碍”,当作了一种“消极”因素,这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只重视文学超越性的意义造成的。只重视“思想性”意义,而将文学寻求情感共鸣的“苦情”仅仅看做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消沉”,认为它“不积极向上”从而认为它“不健康”,再由此将其逐出真正的悲剧之列。在中国的语境中,我们过分注重文学重大的社会职责而忽视其对于个体性的情感共鸣作用,把文学个人的情感疏导、寄托作为次要的、不关紧要的东西,看轻其情感共鸣的价值。像这样对于文学“崇高”使命片面夸大的思想范式由来已久,在这方面甚至达到过偏执而令人胆战心惊的程度。在共鸣与超越,情感与思想的选择中,我们往往只选择“超越”与“思想”,而冷落共鸣与情感。在“高于生活”的口号中往往“远离”了生活,在崇高的追求中往往变成了“伪崇高”。这种不对称的“跛脚”审美机制,过度“崇高化”了文学,也将文学功能狭隘化、概念化,这也必然将人情僵硬化、冷漠化,这在中国是一种不容易摆脱的“文学惯性”,看一看我们的文学史,对悲剧长时间以来只看重其“崇高”、“乐观”的一面就不足为怪了。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中很多作品因为“调子低沉”、“阴暗”、“悲观”、“感伤”、“颓废”,不能给人“排山倒海”的革命豪情与乐观向上的奋斗精神,不能给人们指出“光明的出路”与“希望的未来”而受到指责。按照这种要指出“新出路”、描写“新光明”的标准,许多著名作家因为不够“光明”,没有指出“出路”而遭到批评。老舍《骆驼祥子》被批评“故事的结尾太低沉了,太阴惨了”,作品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气氛,没有给祥子指出“新生的道路”。[6][p.363]巴金的《寒夜》也是“没有高昂的理想主义的诗情和色调,没有勾画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没有为那些‘受生活压迫走进了可怕的绝路的人’明确指出一条正确的革命出路来。”[7]丁玲也被迫自我批评《莎菲女士的日记》、《梦珂》等作品的缺点就是没有找到“怎么去活的道路”,没有找到“去活的方向”。要求作家“乐观向上”、开出救世良方的期待成了压在作家头上的沉重负担,作家们背上了“救世家”的重担,承担起为读者指明“出路”,为社会寻找“光明”、“开药方”的重任了。在这样的文学取向中,我们自然就要从“乐观”、“出路”、“向上”等方面来解释悲剧了。悲剧的“哭”、“苦”、“怨”也因为没有“雄心壮志”的“豪情”而成了“阴暗”没有力量的代名词,成了“负面”情感。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甚至因为不乐观、不“鼓舞人”而被禁止在学校讲授,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甚至说社会主义已经不存在悲剧了。在这种环境下,认为悲情“不革命”而驱逐、看轻这种情感方式,在中国近百年来“革命文学”的阵营里是大有市场的。
我们一味盲目追求“昂扬”的格调,要求文学的是“正面”力量,集体性的“宏大”力量,对于个体性的、瞬间性的、情绪性的东西,我们觉得其意义不大,价值不高,“革命文学”、“斗争文学”盛行,讲个人情感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当时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就曾经说:“我们在作品中,每每写到感情时,就不敢写了,怕露出小资产阶级感情来。”[8][p.210]所以我们作品中的人物成了一种无情的空洞的符号,《人民的战士》中刘兴告诉小万的父亲小万受伤了,而小万的父亲不敢表示悲痛之情,个人情感似乎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专利。这种轻易否定情感性、个体性等“微小叙事”而过分张扬“革命”、“战斗”的宏大叙事的语境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文学的一个基本生存状况。正是在这样一种追求“战斗”、“昂扬”、“高亢”、“思想”、“政治”、“主体性”、“力量”的语境中,我们一直将“崇高”悲剧作为真正的悲剧,而其他低婉惆怅、缠绵悱恻的作品,往往被目为“调子低沉”的“悲情”而已,往往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消极颓废”。我们用“主体性尊严”、“抗争奋斗”、“英雄力量”等阐释悲剧精神,悲剧也被解释成“乐观”的了。我们一相情愿地认为悲剧反抗性越剧烈,战斗性越强,革命性就越强,悲剧性也就越强,情感倾诉性被淡化了,这里面就有着对于悲剧审美机制的狭隘化。
三
所以,我们要冲破这种单一“崇高悲剧”的价值观,把那种寻求情感共鸣的所谓“悲情悲剧”看成是与崇高悲剧并行的两种审美机制之一,而不是人为地抬高一方而贬低另一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年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9][p.63]悲剧功能本身就定位在“疏泄”情感上面。而我们国内现在的悲剧观主要是“恐惧”的悲剧,而忽略了“怜悯”的悲剧。我们强调悲剧中“大”到给人压抑的“恐怖”力量,而那种“怜悯”倾诉的悲剧,则有意无意之间被看成是次一等的。怜悯与恐惧,共鸣与超越的“双轨”审美机制也被移形换影变成了只有“恐惧”与“崇高”的“单轨制”悲剧机制,悲剧的“痛并快乐着”的“混合型”情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单纯化”了的“积极正面”的情感。
其实,文学除了给人高昂的“力量”,反映社会重大矛盾与历史进程的必然性而外,在人与人之间架起沟通、同情、共鸣的桥梁,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联系中玩味人生三昧,就像是烦闷时与一个朋友的倾诉,这种作为“苦闷的象征”式的共鸣性文学同样是文学神圣的使命,这个使命不应该被看成是低一等的。文学的使命应该是多元的,文学的共鸣性与超越性是同样有价值的,是文学的两种审美机制。托尔斯泰就曾经说:“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10][p.412]苏珊·朗格也认为文学就是情感的符号。在这里,寻求情感的共鸣本身成了艺术的本质,“情感传达”成了艺术不可忽视的最重要维度。文学这种不同品格的追求按道理来说并没有高下之分,正如王国维所说:“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11][p.2]只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细雨鱼儿出”的“闲适”优美往往和“帮闲”、“消闲”连在一起,和“庸俗”连在一起,和“视野狭窄”连在一起,和“价值不大”连在一起,在正统的文学价值谱系上明显让位于“落日照大旗”的崇高了,“趣味无争辩”变成了趣味的统一。
人与人之间寻求情感的共鸣,本来是最基本的生存要求,也是文学最基本的原始动力。中国传统文论历来有“言志缘情”的传统,“情动于中,故形于言”;“人禀七情,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根情、苗言、花声、实意”,情感共鸣性文学才是我们文学的正宗。但近代以来我们却慢慢淡忘、削弱了文学最基本的共鸣性存在,在所谓“救亡”与“启蒙”中把情感的感染、同情、寄托作为次要的内容,过分强调文学的“重大使命”与“思想力量”,将悲剧给我们的“眼泪的哭诉”,寻求同情的人生悲叹说成仅仅是“悲情”,说成还没有完成超越,没有真正的悲剧性。这是对文学的异化。像窦娥,她遭受那么大的冤屈痛苦,自然要向人申诉、哭诉,她那份“凄绝”哭诉的目的就是寻求同情与怜悯,渴望在另一个人的心里引起共鸣。这份“悲”是人之常情常理,渴望有人聆听、有人同情,这份“悲”本身就是这个悲剧的目的,这份“苦”,这份“哭”并不可耻,并不需要“转化”成坚强的战斗才有意义。像屈原,遭受那样的不公,自然要向人倾诉宣泄,他的目的就是要宣泄这种郁积的悲情,渴望有人共鸣,这是自然的、健康的,也是“积极的”。像这样情感的悲鸣,希望有人共鸣的诉求本身就是这类悲剧的目的,就是这类悲剧的价值,不必再“升华”成“主体精神的胜利”的“思想”上来。这自然应是悲剧的审美机制之一,但我们却因为这种倾诉“苦”、“冤”没有“战斗性”而否定它是“真正的悲剧”,这明显是因为我们先就主观地看轻了情感倾诉的共鸣性文学的价值。我们长期受“斗争哲学”的影响,“彻底革命”思想的影响,认为“反抗斗争”就比“改良”、“感化”、“情感”等优越。托尔斯泰式的“非暴力抵抗”、“同情心”、“温情主义”等就曾经是我们严厉批判的对象,被看做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幌子,这就将“情感文学”排除在外而将“斗争工具”的文学当作了文学的最高使命。
四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目的其实更多的是寻求共鸣的文学,而不是寻求超越的“战斗文学”。人们都说中国古代有“以悲为美”的文学传统,这种“悲美”之所以美,正是在一种悲情的共鸣基础上形成的。白居易在《序洛诗》中指出,历览古今歌诗,观其所自,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而起,这种愤忧怨伤之作,“通什古今,计八九焉”。这些忧愁幽思之作,更多的是一种人生在世的感受、体验、遭际的切身领悟,是一种情感倾诉的表达,是一种压抑寻求宣泄的方式,苦闷寻求共鸣的渴望。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则外有诗歌文章之表达,中国很多文艺作品注重的就是将自我内心的“郁积”表达出来,它是一种“发抒”,是一种“离骚”,是一种弗洛伊德所说的“释放”。它并没有刻意“昂扬”的调子,也不需要昂扬的调子,它寻求的是一种自我真实情感的疏通流露,并寻求与他人的共鸣,在这种情感的共鸣中释放自我、传达体验、寻找知音,获得身心的健康愉悦。它主要是一种朋友式的交流,情感的密会,这是中国文学的基本品格。而这种最“自然”之文学因为这种纯粹的表达性,少了藏之名山的宏图,少了艺术“关目”的人为性,其艺术性反倒是最高的。
人与人之间不管高亢还是低沉的情感共鸣,这本身都是有价值的。《牡丹亭》不是“无尽的抗争”的“力”的悲剧,但张生、崔莺莺真挚的情感却引起了我们无尽的共鸣。扬州姑娘小青,看了《牡丹亭》以后,写下“冷月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将作品喻为知己,反复阅读,不久郁郁而死。扬州金凤钿日夕把玩《牡丹亭》,而且“愿为才子妇”,想要嫁给作者,死后亦以《牡丹亭》放在棺材里。而林黛玉因为听了《牡丹亭》戏文而“心动神摇”、“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心痛神痴、眼中落泪。”能这样在一代人一代人之间共鸣的悲剧为什么还不是“真正的悲剧”呢?像《祝福》的祥林嫂,她确实没有那种无尽抗争的“悲剧精神”,一点也不“崇高”,但是她的命运却在我们心里激起了无尽的同情,我们的心被她的命运揪紧了,从而产生了对人生在世的无限思考,这种共鸣本身就是文学作品应有的价值。像张爱玲那样一种对人性的深切洞察的“苍凉”,川端康成的“雪国”、像卡夫卡那些“弱的天才”,像《孔乙己》《阿Q正传》、《沉沦》、《寒夜》等等作品中主人公,他们的“软弱”与“悲情”,我们感同身受似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与作品中人物同悲同喜,这样的作品的归宿就是这种共鸣,这样的情感作为悲剧的价值不应受到怀疑。
但是我们曾经把共鸣作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文学理论,把它看成是一种“谬论”,总想“加以摧毁”。当年王淑明在《论人情与人性》中认为归有光的《先妣事略》,袁枚《祭妹文》等作品,我们现代的读者在阅读它们时,仍然会为其艺术的力量所感动,这就因为人情的本质有其“共同相通”的地方存在而引起的共鸣。众所周知,这样的学说引来了大批判。柳鸣九在《批判人性论者的共鸣说》中认为:“共鸣一般是发生在同时代、同阶级的人们之间的。古典作品中的人物一般是不会引起现代人的共鸣的。因为,在他们与现代人之间有着阶级思想的藩篱和时代的隔膜。”[12]我们用“阶级立场”代替了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基本的情感交流,用“阶级斗争”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与共鸣,“共同美”成了一个问题。共鸣强调的那种对所有人普遍有效的基本情感、基本人性被认为是“反动言论”,共鸣曾经因为有“全民文艺”的嫌疑而被大加挞伐。20世纪50年代,巴人提出“当前文艺作品中缺乏人情味”,提倡“人情论”,认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愿望。但是大家知道,这一主张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而受到大批判,“人情人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领域一直是受批判的,我们强调只有在阶级斗争之下的人情,这样只重视斗争就形成了一种“斗争心理结构”。冰心的“母爱”、“童年”得到了读者强烈的共鸣,但是我们批判这是想以“爱的哲学”来缓和矛盾、安抚反抗,这“爱的哲学”是一种逆时代而动的哲学,没有任何“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意义”,“是与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相抵触的”。[13]冰心梦想的“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之类的“母爱”,得不到我们的共鸣,相反我们总批判这是“空想”,是“超阶级”的“抽象”人性论。像这样讴歌“母爱”、“童真”,寻求“爱”的共鸣的文字都一股脑儿受到无情的批判,这无异于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了一道隔离的高墙,人与人之间变得荒漠化、功利化、斗争化、无情化,也就是比较自然的结果了。现在我们慨叹当下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麻木、自私,一定程度上就在于我们长期重视“斗争”、“反抗”,而把“人类共同的爱”之类的共鸣思想盲目地完全说成是“反动言论”造成的。轻视共鸣,大讲斗争,导致现在的人情冷落、诚信缺失,这实在有着内在的某种深层次关系。其实不管是“抽象”的爱还是“具体”的爱,文学宣传爱总比宣传仇恨好,也可能比宣传以血还血、以暴易暴好。
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人情共鸣的空气稀薄不是偶然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文艺批评主要是一种政治批评、阶级斗争批评。毛泽东的“讲话”提出文学艺术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的标准,一个是艺术的标准,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使得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批评往往成了“政治鉴定”,政治具有“一票否决权”。从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开始,到《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巴人、钱谷融人情人性论批判,丁玲、冯雪峰批判以及邵荃麟“中间人物”批判等,特别是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学批评都演变成了对于作者的政治审判,文学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很多人因此没有工作、坐牢甚至被折磨致死。在政治高压下的文学尽是空洞的“革命”、“阶级”、“集体”、“光明”、“伟大”的宏大叙事,个人倾诉的共鸣式文学几乎消隐不见。红军转移中,因为担心婴儿的啼哭引来敌人,所以要把那些婴儿抛到山谷中,一些女红军心里有迟疑,这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描写。《艳阳天》中韩百安私藏了一点粮食,儿子要交出去,韩百安即使给儿子跪下,儿子还是“大义灭亲”,毫不犹豫地交出去,这种“精神”成为时代的“强音”。而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代里,一切都染上了阶级斗争的色彩,文学被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家也成了“阶级的耳目与喉舌”、“阶级的器官”。一部《红楼梦》也只是阶级斗争形象的历史,陈独秀让人们去“领略”《红楼梦》的“善写人情”,就被批判为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观点去欣赏《红楼梦》,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被斥为“谬论”、“肆意歪曲”,[14][p.196]这种阶级斗争论成为我们衡量文学作品的又一个基本尺度。在长期的这种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文学世界里,气氛紧张,充满了“血与火”的剑拔弩张,我们内心那种“温柔在诵”的情感需要已经被“时代”、“责任”、“社会”、“阶级”、“集体”、“国家”等异化掉了。我们那种看上去“软弱”的“私人”情感,文学的共鸣功能已经被压抑得奄奄一息了,我们对于共鸣有些生疏了,我们的内心变得坚硬了。在到处都洋溢着“阶级兄弟心连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公无私的海洋里,我们整人、斗人、打人的残酷冷漠自私,也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文革”中的很多血淋淋的历史事件足以证明我们的人心之硬。大讲阶级情、集体志,结果却成就了一群毫无人情的人,这不能不说与我们一直高举的“斗争哲学”是有关系的,与文学一边倒崇尚超越性价值而不注重人情共鸣有关。文学在美化人心、软化人情、撒播爱情方面没能起到应有作用,因此在中国的文学语境中,我们从来不缺乏高昂的“时代号角”,不缺乏超越性的作品,我们缺乏的是那些“家务事、儿女情”的“小文学”,那些没有“重大使命”的共鸣文学。
而当我们完成“拨乱反正”,开始重新回到“人”,开始重新注意小写的人的时候,我们又开始热衷于追寻西方各种光怪陆离的“现代主义”、“后现代”的试验,以“震惊”效果为目标,以“解构”为时髦,西方近百年来各种理论轮番登场,各种文学流派在短时间内一一亮相,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新批评、阐释学、解构主义、女权批评等等,不一而足,你方唱罢我登台。各种新名词自然也是满天飞,“陌生化”、“纯诗”、“聚焦”、“符号”、“零度”、“逻各斯”、“结构”、“解码”、“复调”、“透视”、“游戏”、“循环”、“原型”、“巫术”、“本我”等等,难以列举,我们来到了一个概念爆炸的时代。以至于我们有的学者惊呼我们得了“失语症”,除了西方的各种话语我们就不会说话了。文学价值取向在“多元共生”的喧闹中舒缓了政治焦虑,但是其价值核心的稳定性也随之丧失,文学又处于寻找核心价值的突围之中。在这一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共鸣”价值取向又因为太“传统”而被冷落,所以实际上至今我们文学领域里共鸣的空气还是很稀薄,我们最需要的还是共鸣性的文学。
按说,文学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在共鸣的基础上来实现超越的宏图,超越与共鸣共生共荣。但是,对于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来说,不可能任何时候都能把这两者完美融合在一起,往往各有所长。而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来说,往往也是各有侧重。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语境中,总的说来我们是过分重视超越性文学而忽略了共鸣性文学,因此现在共鸣文学对于我们来说就显得更加重要。史达尔夫人曾经说:“在外界,什么东西给人看过了,什么东西都给人鉴定过了;只有人的心,它的内部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引起惊讶的东西,唯一能激起强烈感觉的东西。”[15][p.305]我们的文学对于鉴定“外界”曾经太过重视,对于人内心细微情感的尊重显得过于粗暴,对于曾经斗争哲学笼罩的中国语境来说,那种内心温柔之爱,情感共鸣的文学显得尤其珍贵。因此当前刻不容缓的是恢复人情、人性本身的巨大价值,不妨将人情的共鸣本身就作为文学作品的最高价值之一,而不必一定要“升华”到“思想价值”上来。共鸣与超越,情感与思想,对于真正的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判定其中某一方就要更高级而另一方就要更低级。能共鸣、能情感,这对于人类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在悲剧中我们应该恢复其共鸣与超越的“双轨”审美机制,把情感共鸣本身就作为悲剧的目的之一,注重以此塑造人心、人情的“同构”场域,注重情感的倾诉、表达与疏导,而不是仅仅将“主体性尊严”的反抗与胜利作为“真正悲剧”的唯一标准,不是仅仅将其“思想性”的高大作为评价最高悲剧的唯一标准,这对于我们认识众多悲剧的价值是有益处的,对于我们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壁垒,共建美好的心灵世界是有好处的。悲剧能培育我们如此共鸣的能力、如此共鸣的情怀、如此共鸣的心性,这本身就是最美的悲剧了,当然也是“真正的悲剧”了。
重大使命的超越性文学让人心变得坚硬,让世界变得紧张。我们以鲁迅为师固然是历史的必然,他“一个也不饶恕”的战斗固然是可钦佩的,但有的人讲鲁迅的文字太“狠毒”,对于人的阳光心态,对于青少年并不是很有利,所谓“少不读鲁迅”,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情感倾诉的共鸣性文学让人心变得柔软,让世界变得温馨,缩短人与人的距离。冰心的文字虽没有重大的斗争,只是“茶杯里的风暴”,但她在美化人心方面却是无人能比。所以一个民族不能只有鲁迅,不能只有超越的文学,文学也不能只是“匕首”、“投枪”;也不能只有冰心,不能只有共鸣的文学,不能只是“爱的呢喃”。只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共鸣的文学显得尤其迫切。张爱玲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16][p.284]作为个人,我们尽可以只喜欢“力”或者只喜欢“美”,但是作为“美本身”,却是“力”与“美”同等并存的。如果“力”的悲剧是“积极悲剧”,那么柔美的悲剧则是“消极悲剧”。悲剧并非只有一种形态,这里的“消极”也不是“负面”意义上使用的。我们曾经只相信“力”的作品是美的,而“美”的作品则是不美的,张爱玲本人好长一段时间也进不了文学史,其作品价值长期处于埋没状态就是这个原因。而现在张爱玲“翻身”了,其“苍凉”的“美”的作品也在文学史上堂而皇之了,这实际上已经表明大众趣味对于那些“不革命”的“非超越性”的共鸣文学的肯定。但是我们的悲剧却还在重复“崇高悲剧”的理念,认为“悲情悲剧”还不是“真正的悲剧”,这种观念应该“终结”了,共鸣悲剧应该与崇高悲剧并驾齐驱了。这样看来,不是中国的悲剧出了问题,而是我们判断悲剧的价值标准出了问题。如果我们有了更健全的文学价值观,中国就会有很多“真正的悲剧”。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2]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
[3] 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J].江苏社会科学,2001,(1).
[4] 黄克剑.“悲”从何来?——就悲剧之“悲”对中西文学人文趣向的一个比较[J].文艺研究,2004,(3).
[5] 孙秀昌.两周时代“命”意识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悲”意识的影响[J].社会科学战线,2012,(4).
[6]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7] 宋曰家.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杰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论丛,1984,(4).
[8] 周扬.周扬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9] 亚里士多德.陈中梅译注.诗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10] 托尔斯泰.艺术论[M].伍蠡甫.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11] 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2] 柳鸣九.批判人性论者的共鸣说[J].文学评论,1960,(5).
[13] 范伯群,曾华鹏.论冰心的创作[J].文学评论,1964,(1).
[14] 洪广思.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15] 蒋孔阳.19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英法美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16] 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