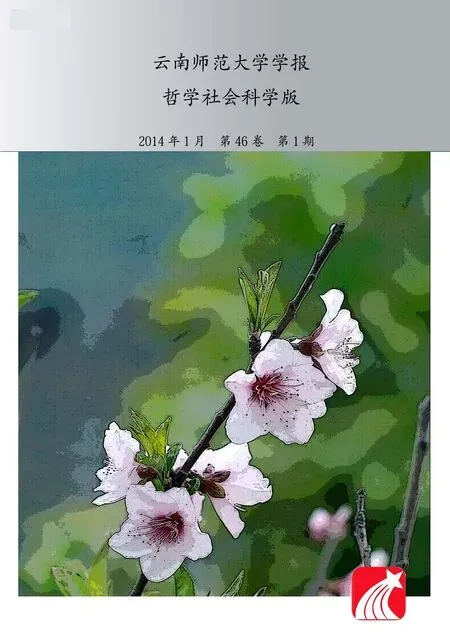董仲舒国家治理思想:历史观的创新与大一统思想的重构*
2014-03-12唐眉江
唐眉江
(西南交通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1)
大一统是董仲舒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董仲舒创立了三统论,为自己的大一统理想提供历史观的依据。从战国一直到他生活的时代,黄帝崇拜都是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为思想界和统治者普遍采用,以论证自身的合理性与权威性。董仲舒的三统论,依据的历史是夏、商、周三代,远没有黄帝古老。在一个崇古的时代,在人们普遍相信历史越久远,对现实越有说服力的时代,他为什么不利用黄帝崇拜这种盛行的历史观呢?
一、从秦王朝到汉武帝:历史观上的黄帝崇拜
作为一种历史观,黄帝崇拜表明,人们相信过去的历史能为现实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提供合理性的依据。从西周到战国,人们心目中古老的圣王从禹提前到了尧舜,又从尧舜提前到了黄帝,对历史的想象越来越久远,反映出人们普遍相信,历史越久远,则现实的合理性越强。
战国时代,黄帝崇拜的热潮已经兴起,并转化为政治意识形态,为政治实践提供着历史观的依据。产生于齐国稷下的黄老之学,将田氏齐国的统治者说成是黄帝苗裔,借助黄帝战胜炎帝的传说,为田氏取代姜氏(自认为炎帝之后)而有齐国制造了血统论上的理由;他们还利用黄帝一统天下的传说,为齐国统一天下的宏图大业制造着神圣的舆论环境。
秦统一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这种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迷信军事暴力、严刑峻法,可称为霸道暴政式的大一统。法家思想作为秦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历史观上,有着鲜明的黄帝崇拜色彩。早在先秦时代,法家就与黄老学关系密切,《管子》、《商君书》等法家著作大量称引黄帝,托名黄帝立论,把各种政治制度、包括“法”的制定,都归于黄帝名下*法家著作大量称引黄帝。如《管子·五行》:“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任法》:“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赵守正:《管子注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54页)《商君书·画策》肯定“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7页)综合这些资料,可以看到,黄帝被法家视为追求天下一统的先圣,是各种政治制度和“法”的制定者。。他们将黄帝与老子结合,援法入道,将老子的道论与托名黄帝的刑名法术结合,实现了道法合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1][p.2146]此外,秦统治者也以黄帝苗裔自居,希望以此来自高身价。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早在灵公时,秦国就开始作吴阳上畴,祭祀黄帝。[1][p.1364]当时的秦国,因僻居西方,相对落后,长期被东方诸国鄙视为蛮夷。祭祀黄帝的目的,正是要向天下昭示自己乃黄帝之后,以此获得心理上的自信,在文化上抗衡东方各国,为自己的统治披上神圣的外衣。可见,黄帝崇拜为秦王朝及其意识形态提供了合理性、权威性的历史观依据。
西汉建立,继续推行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鉴于秦朝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崇尚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可称为无为而治式的大一统。汉初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来自于黄老思想。但本阶段的黄老思想,与战国及秦王朝时相比,清静无为的因素被彰显出来,外显的法家、特别是严刑峻法色彩大大减弱。汉惠帝二年,曹参由齐相升任汉相,标志着汉王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明确推行无为之治。曹参的国家治理理念,“要用黄老术”,“贵清静而民自定”,其思想源头,正是“善治黄老言”的齐地胶西人盖公(《史记·曹相国世家》)。[1][p.2029]在汉初推行无为之治的数十年中,统治阶级普遍接受了黄老思想,在《史记》、《汉书》等史料中,有大量时人学习黄老思想、接受黄老思想的记载。如代曹参任汉相的陈平,“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史记·陈丞相世家》),[1][p.2062]而一直活到汉武帝时的窦太后,作为汉文帝的皇后,不仅自己“好黄帝、老子言”,而且在她的严厉要求下,“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1][p.1975]黄老思想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用黄帝的神话来神化自己的思想,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学思想基础,表明这种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在历史观上仍然坚持着黄帝崇拜。
汉武帝改制更化,“外事四夷、内兴功利”(《汉书·食货志上》),[2][p.1137]可称为多欲政治式的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意识形态领域废除了黄老思想的指导地位。但是,汉武帝虽然对老子不感兴趣,也抛弃了无为之治,但对黄帝却推崇备至,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史记·封禅书》[1][p.1393-1394]记载,申公向汉武帝描绘黄帝成仙的经过,专门提到“黄帝且战且学仙”,武帝听后,感叹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纵观汉武帝一生,正是在“且战且学仙”中度过的。他不断发动对周边民族的大规模战争,无休止地任用方士、封禅、巡游、求仙,至死都还幻想着能够升仙。此外,汉武帝还改造了汉王朝的神祇系统,他以太一作为唯一的天帝,以白、青、黄、赤、黑五帝作为人间的圣王。他使黄帝居于中央,其他四帝分居东、西、南、北四方。《韩非子·扬权》已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p.44]的中央集权论。黄帝的中央帝身份,使其地位高于其他四帝*战国时邹衍创立五德终始论,以黄帝为土德,为五德之始。《吕氏春秋·季夏纪》:“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1页)《淮南子·天文训》:“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第113页)《汉书·律历志》:“《易》曰:‘神农氏没,黄帝氏作。’火生土,故为土德。”([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12页。)《论衡·验符》:“黄为土色,位在中央,故轩辕德优,以黄为号。皇帝宽惠,德侔黄帝,故龙色黄,示德不异”([汉]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06页)。自战国至汉,这些广泛存在的观念表明,黄帝地位高于其他四帝。。汉武帝又改汉朝为土德,色尚黄,而黄帝正代表了土德,土色尚黄。汉武帝的改制,体现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治格局的要求,是在政治上对黄帝崇拜的肯定,确认了黄帝崇拜是汉王朝统治的合理性依据。可见,汉武帝否定黄老却推崇黄帝,其多欲政治式的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在历史观上同样坚持黄帝崇拜。
由此可见,从秦王朝到汉武帝的政治实践中,三种不同的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无一例外地都将黄帝崇拜作为自己历史观的重要内容,以论证自身的合理性与神圣性。不仅如此,整个思想界也呈现出“学者多称五帝”、“百家言黄帝”(《史记·五帝本纪》)[1][p.46]的空前盛况。当此之时,一个思想家却要在历史观上标新立异,无疑就十分值得关注了。这个思想家就是董仲舒,他的历史观就是三统论。
二、放弃黄帝崇拜,创立三统论:董仲舒历史观的创新
在董仲舒的著作中,根据笔者的统计,只有一处直接提到了黄帝的名字,他没有托黄帝立论,借黄帝之口去表达自己的思想,也没有对黄帝流露出崇拜、神往之情。在黄帝崇拜极度盛行的文化大背景下,董仲舒放弃黄帝崇拜,无疑是其历史观的一个鲜明特点。
董仲舒构建了以三统论为基本内容的历史观,来论证自己理论的合理性。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他提出:“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曰: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4][p.195-198]董仲舒虽也提到了五帝,但这些久远难稽的古帝,并不是他论述的重点。他的历史观真正依据的,还是离汉最近的夏、商、周三代。在董仲舒看来,孔子编写《春秋》的目的是“黜杞”、“新周”、“故宋”,为继三代而起的新王朝立根本大法。三统论认为夏、商、周三个王朝各代表一统,历史的发展就是根据三统的顺序不断地循环往复。每一个新王朝起来,都要根据自己的一统进行改制,即改正朔、易服色等。但是,夏、商、周三代政治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的典范,是努力追求以实现的目标,三统虽然不断循环,但承载于三统循环中的王道政治却是永恒不变的。因此,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2][p.2518-2519]新王朝改正朔、易服色等举措,仅仅是形式上的改变,以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天,而不是继承前朝而王。不管王朝如何更替,王道都是各个时代政治实践不变的内核,也就是“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4][p.19]每个时代政治实践的依据,就是体现于夏、商、周三代历史中的王道政治。三代历史是现实政治的范本,也是现实可以如此、应该如此的依据。
在人人竞相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历史依据,并把历史想象得越来越久远的时代,董仲舒却只将自己的历史依据追溯到三代,在思想竞争中显然不占优势。虽然黄帝崇拜不是先秦原始儒家的传统*顾颉刚先生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说:“儒家的孔、孟都不提黄帝,他们的经典《尚书》也没有叙述到尧之前,所以黄帝在儒家中是不占势力的。至于阴阳家、道家、神仙家、医家、历家……都常说起黄帝,而且把他看作教主……他们只是拉了一个当时认为最古老而且最有力的人作为自己学说的保护而已。……所以我们如果研究黄帝,切勿以为研究的是夏以前的史,而应当看作战国、秦、汉史,因为他的传说只是战国、秦、汉间的思想学术的反映,只是表现了战国、秦、汉间的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3页)他还指出,周人心中最古老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时才开始谈尧舜,黄帝神农的传说是战国时才产生的,到秦时则出现了三皇。(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9~60页。),但董仲舒不是固守传统、不知时变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在黄帝崇拜极度盛行的时代,他为什么要放弃黄帝崇拜这一有效的思想武器呢?如果将董仲舒与贾谊、司马迁、汉武帝做一比较,则其中原因更值得思考。汉文帝时期的贾谊,猛烈抨击汉初无为之治,屡屡在文帝面前“痛哭”、“长太息”,要求改正朔,易服色,其政治主张中的法家色彩非常鲜明,与稍后的晁错很相似。他的思想有着明显的黄老色彩,其著作经常称引黄帝,托黄帝立论。司马迁部分接受了董仲舒的历史观,也认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高祖本纪》)[1][p.393-394],但他对黄帝却推崇备至,皇皇巨著《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首先记载的就是黄帝,把黄帝作为整个文明史和历代圣王的源头,视黄帝为华夷共同的祖先。在他的笔下,不仅夏、商、周三代君王,而且包括秦、楚、越,甚至周边的民族如匈奴、朝鲜、南越、东越、西南夷等,都是黄帝的苗裔。司马迁的政治态度非常鲜明,他高度肯定汉初的无为而治,对武帝的多欲政治却多有批评。汉武帝改制更化,改汉朝为土德,色尚黄。他非常渴望象黄帝一样,在建立了人世间的辉煌功业后,乘龙升仙。汉武帝终其一生,始终在效法黄帝“且战且学仙”,为了能够升仙,他甚至愿意将妻儿像破鞋一样扔掉。他对黄帝的崇拜,已经痴迷到了近乎癫狂的地步。面对宣扬升仙之术的方士们,汉武帝虽然一次次发觉被骗,却仍然执迷不悟,希望总有一次能够遇到真人。
上述三人对于黄帝,有着程度不同的崇拜,他们的政治理念,与董仲舒也有程度不同的差别。历史观作为哲学基础,是为它背后的政治理念服务的,历史观的不同,正是政治理念不同的反映。特别是面对痴迷于黄帝的汉武帝,董仲舒不投其所好,反而在历史观上放弃了黄帝崇拜,是需要下很大决心的。董仲舒在历史观上无视时代潮流,不顾皇帝的感受,显然是因为政治理念的差别,使他不得不做出这样有风险的创造。大一统思想是董仲舒政治思想的核心,他在历史观上创立三统论,放弃黄帝崇拜,是与同时代其他政治思想展开竞争的需要,尤其是批判既有的三种大一统实践模式的需要。
三、董仲舒对大一统理想的批判重构
萌芽于先秦时代的大一统思想,最初是思想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主观想象。秦统一六国,使大一统由梦想变为了现实,但却二世而亡。汉初鉴于秦亡的教训,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取得了显著成效,也造成了严重问题。汉武帝改制更化,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取得了巨大成就,更造成了深重灾难。在董仲舒面前,已存在着三种大一统实践模式,即秦王朝所代表的霸道暴政式大一统、汉初所代表的无为而治式大一统、汉武帝所代表的多欲政治式大一统。董仲舒的大一统理想,与三种实践模式都有区别。他创立三统论的历史观,对黄帝崇拜的社会思潮,对汉武帝的个人喜好,不利用、不迎合,正是为了在实践批判基础上对大一统进行理想重构。已有的三种大一统实践模式都与黄帝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批判它们,就有必要放弃它们的历史观——黄帝崇拜。
(一)与秦王朝霸道暴政式的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相比,董仲舒的大一统理想,有很多显著的差别。概括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董仲舒吸收了法家的法、术思想,肯定刑法、军事暴力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但又坚持阳为德,阴为刑,根据阳尊阴卑的理论,提出了德主刑辅、教本狱末的为政原则。董仲舒认为,刑、法只是手段,只能从属于德、教。大一统理想的实质,是在统一的天下实行儒家的王道理想,首先发展社会经济,解决好民生问题,然后推行文德教化,实现思想文化层面的最高统一。这种庶之、富之、教之的路径,与孔子的思想一脉相承,与法家的思想大异其趣。法家主张赤裸裸的愚民政策,秦始皇更以焚书坑儒的实际举动,给文化以毁灭性的打击。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国,非常重视发展生产,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但却反对富民,害怕人民富裕了,不利君主的支配,不再勇于公战。显然,秦王朝的贫民、愚民政策,与儒家富民、教民的王道理想是针锋相对的。
其次,董仲舒与秦王朝一样,坚信大一统的前提是实现天下的政治统一,而政治统一的关键是实现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因此,必须强化君主权力,避免主弱臣强。但是,秦朝皇帝的权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既没有相应制度来稍微限制下君主的行为,君主自身又缺乏对天(神)足够的心理敬畏。秦始皇、秦二世都迷信自己无限膨胀的权力,为所欲为,最终耗尽民力。人民无法生存下去,只有铤而走险,让外表看似无比强大的秦王朝,只历二世,十五年就速朽了。为了既尊君集权,又使君主不能为所欲为,董仲舒专门设计了一套“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4][p.32]的理论,试图对君主行为加以神学上的限制。他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通过灾异、谴告等形式,企图借助天的至上权威,使君主感到恐惧,从而不敢为所欲为。同时,由于天道与人道本质上是相同的,天与人,又是相通的,这就为君主实行王道政治提供了天道的依据。
第三,秦王朝建立后,视天下为一家之私产,幻想其统治能够“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1][p.236]董仲舒的大一统,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始儒家公天下的传统。他的三统论,强调君主专制是万世不易的天道,但“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4][p.187]“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夺也……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4][p.220]天下不是天子的私产,天子只是代天来治理天下,如果不遵循天道,就要被取代。天命转移,不私一姓,王朝的更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
秦朝灭亡后,它所代表的霸道暴政式大一统遭到了汉朝人的全面批判,许多思想家甚至不承认秦是单独的一统。董仲舒放弃黄帝崇拜,从历史观的角度看,当然就否定了以黄帝崇拜为历史依据的秦式大一统的合理性。
(二)西汉前期实行无为而治式的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经过休养生息,西汉社会迅速从秦末战乱的巨大破坏中恢复起来,经济持续繁荣、社会相对安定,国家日益富强。但无为而治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分权,而大一统却建立在高度的集权专制基础之上,这就导致二者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政治上的放任导致汉初地方诸侯王势力逐渐壮大,直接威胁到中央的统治,破坏了大一统的政治基础;经济上的放任导致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在经济大繁荣的同时却产生了董仲舒所抨击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2][p.1137]的严重社会危机,破坏了大一统的社会经济基础。毕竟,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小农的大量破产,也意味着政治统治的深重危机。在政治实践中,声名狼藉的法家仍有很大影响,汉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汉书·刑法志》),[2][p.1099]汉景帝好刑名法术,任用的晁错,“学申商刑名”“为人陗直刻深”(《汉书·爰盎晁错传》),[2][p.2276、2277]具有鲜明的法家色彩。
董仲舒清楚地看到了无为而治与大一统基本原则的矛盾。他总结春秋历史经验,并根据汉景帝时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的当代教训,强调大一统理想必须建立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基础上。他依靠神学信仰、制度建设等举措,不断地强化君权,尊君卑臣,维护君主在臣下面前的绝对权威。无为而治主张君无为而臣有为,董仲舒却坚决反对君权任何形式的旁落。因为君无为而臣有为看似十分美妙,但长期执行必然导致君权旁落,臣下势力坐大。在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前,对汉中央政权威胁最大的就是那些诸侯王。董仲舒对他们充满了警惕。汉武帝时代,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已经基本消除,但在辽东高庙发生火灾后,他还是要借题发挥,建议武帝杀掉几个亲近的贵幸之人,防止他们死灰复燃。对于经济上的放任导致的土地兼并严重、人民生活艰难、社会矛盾尖锐等现实问题,董仲舒提出必须限民名田,限制土地兼并,避免社会矛盾过于尖锐。汉初无为而治所带来的弊病,董仲舒看得很清楚。这种大一统模式所依据的黄老思想,与秦政一样,都以黄帝崇拜作为自己历史观的依据。面对当时全社会浓厚的黄帝崇拜氛围,董仲舒抛弃这一现成的思想资源,新建三统论的历史观,来论证自己王道政治式大一统的合理性、权威性,显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三)汉武帝实行“更化”,改变了清静无为的统治策略。他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通过实行推恩令,制造淮南狱等举措,彻底消除了诸侯王势力对皇权的威胁。他按照儒生的建议,制礼作乐,改革博士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广泛推行学校教育,使“文学”成为重要的入仕之途,改变了汉初主要靠军功入仕、武人主政的局面,使西汉朝廷“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儒林列传》)。[1][p.3119-3120]他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2][p.212]初步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开始追求思想文化的统一。他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消除了周边民族的威胁,促进了民族交往与融合。这些举措,都符合董仲舒的政治理想,也得到了儒生们的普遍肯定。
但是,汉武帝的多欲政治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差点成了又一个秦始皇*《史记·孝武本纪》的《索隐述赞》有:“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奢丽,尤敬神明。坛开八道,接通五城。朝亲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乘卜征。登嵩勒岱,望景传声。迎年祀日,改历定正。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司马光评论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资治通鉴·武帝后元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47页)。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大兴土木,挥霍无度,把汉初几十年辛苦积累下来的财富几乎消耗殆尽,让社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穷兵黩武,无休止地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而有些战争,仅仅是为了满足他获取奇珍异宝的私欲,却造成了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为此,他加紧搜刮人民,实行盐铁专卖,不断增加税种,提高税赋并大量任用酷吏,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控制。对武帝之政的批评在两汉已经存在*宣帝时,夏侯胜反对为汉武帝立庙乐,理由是“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蓄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汉书·夏侯胜传》)班固虽然评价汉武帝“雄才大略”,也不得不承认“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莞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才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汉书·西域传下》)。董仲舒约卒于公元前107~104年间,亲历过汉武帝的许多作为,他对汉武帝的批评,是有现实根据的。
董仲舒认为大一统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人人各安其位的社会。包括天子在内,任何人都应该严格按照等级制度,获得他应得的东西,绝对不能逾制。汉代公羊学者反对天子的过度贪求,主张“王者无求,求金非礼也”(《春秋公羊传·文公九年》)。[5][p.292]董仲舒明确反对统治者利用权力,为了私欲,去额外掠取等级标准之外的东西。他提出:“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况人乎?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春秋繁露·度制》)[4][p.230]结合当时的横征暴敛,董仲舒的批评,对于不能富民、却与民争利、残民害民的汉武帝是完全适用的。
董仲舒的大一统理想是先富后教,先解决好民生问题,再推行文德教化,实现思想文化的统一。汉武帝没有搞好民生,反而弄得国贫民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正是对汉武帝的尖锐批评。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进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汉书·食货志》)[2][p.1137]这既是对汉武帝的不满,又是基于儒家理想的现实追求。
在“华夷之辨”上,董仲舒认为大一统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华、夷在思想文化层面的统一。华夷的本质差别是文化的高低,二者融合的基本途径是文化融合而不是军事征服。即使暂时无法实现文化融合,董仲舒也更倾向于采取和平的手段,“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汉书·匈奴传下》)。[2][p.3831]汉武帝则不然,他迷信军事暴力,无休止地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给汉朝、匈奴、朝鲜、西南夷等各族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董仲舒的大一统理想与汉武帝的大一统实践之间,存在着很多分歧。如果说董仲舒的大一统本质上体现的是儒家王道政治的理想追求的话,汉武帝的大一统,本质上更接近于秦的霸道暴政,只不过他很善于为自己的多欲政治披上一件温情脉脉的儒学外衣。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他真正喜欢任用的,还是那些儒表法里,能够“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汉书·公孙弘传》)[2][p.2618]的执法任刑之人。董仲舒是个真诚的儒家理想主义者,但终其一生,从未在政治上得到真正大用。
董仲舒对秦政的历史批判,更像是对汉武帝政治的现实批判。董仲舒与汉武帝,对大一统的理解存在差异,对历史观的选择存在分歧。三统论的历史观,是天道与人道的统一。王道理想是董仲舒所理解的永恒不变的天道,也是人道必须遵循的最高法则,天命不私一姓,如果不实行王道,天命就会转移,一个王朝的统治就会被取代。加上灾异、谴告说,这些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就其现实性而言,是对既幻想刘氏江山永固,又为所欲为的汉武帝的警示,是对他无限膨胀的权力和私欲的批判。汉武帝一生痴迷于黄帝,幻想像黄帝一样乘龙升仙,为此就是抛弃妻儿也在所不惜。董仲舒只将信仰的历史依据建立在三代,抛弃了黄帝崇拜,也就批判了以黄帝崇拜为历史依据的汉武帝的错误行径。在同一个时代,他们在历史观上的差异,支撑起了各自不同的大一统理念。
结 语
大一统是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核心理论。董仲舒赞成大一统,支持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并不是为了论证某一姓统治的千秋万世,而是要以此来实现儒家传统的王道政治理想。体现在三代政治中的王道理想是董仲舒大一统理想的内核,而已有的三种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都程度不同地违背了儒家的王道理想。他放弃黄帝崇拜,构建三统论,正是要从历史观的角度,批判三种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并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理想重构。董仲舒不是一个只会为统治者唱赞歌,只会为他们的统治进行合理性论证的御用文人,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儒家的理想主义者。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
[2]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
[3]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点校本.
[4] [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
[5] 李学勤.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