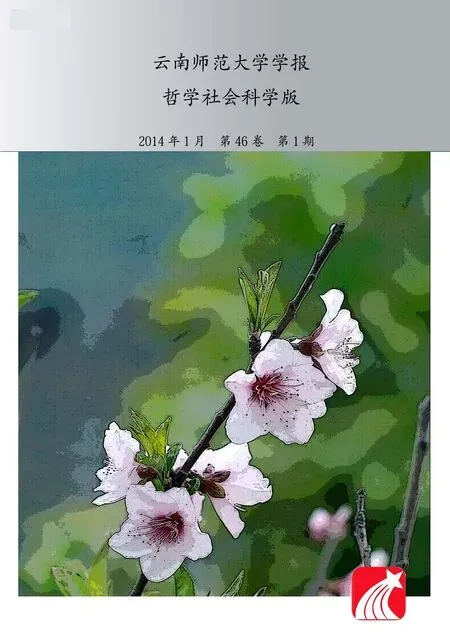场域与惯习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一夜情”*
2014-03-12张楠
张 楠
(重庆大学 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重庆 400044)
一、概念及其社会背景
“一夜情”是个舶来词,这个名称来自西方文化中的One Night Stand,解释为“两个陌生人在酒吧相遇,相互看中对方,继而发生性关系,一夜风流之后第二天各自离开,从此再不联系。”*Difference Between One Night Stands and Long Term Relationships. Articlewebshop.com (2010-07-16). Retrieved on 2011-04-28.中国人大多是通过大众媒介知晓这个名称。可是实际上,一夜情这种形式的性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有学者论述到:一夜情其实在我国古代叫做“露水夫妻”,就是天一亮,性关系也如同露水一样地消散。所以它不是一个新现象,只是一个新名词,是当今中国社会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话语建构。[1]
到目前为止,国内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对一夜情尚无统一的定义。有学者将中国的一夜情看成仅仅是一种性行为,认为One Night Stand应翻译为“一夜性”,因为“是一种偶发的性行为,通常仅只一次,也可能是有限的两三次,强调双方均基于性欲求的特点,拒绝感情与责任,常发生在并不熟悉的人之间。”[2]虽然这一观点忽略了“情”的存在,也就忽略了从关系的角度理解一夜情,但是这个概念与西方社会对一夜情的理解毕竟不同,提出了中国的一夜情有可能发生不止一次,可能是“多夜情”。同时这个概念也承认中国的一夜情还有可能发生在非陌生人之间。
近年来国内关注一夜情的学术研究十分稀少,目前只有潘绥铭在其完成的三次全国18-61岁的总人口调查数据:在男性中,曾经有过一夜情的在2000年占到2.0%,到2006年增加到4.3%,到2010年再次增加到8.7%;在女性中则分别是0.0%、1.4%和4.1%。潘绥铭对于一夜情及其迅速增加做出了自己的分析,[3]但由于他是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因此只作为本文的背景资料,不影响本文的论述。
二、理论出发点:从关系的角度理解一夜情
性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关系之一,考察一夜情的性关系,有助于理解人类性现象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作用和运行机制。对此,已有国外学者提出过“性的社会网络”的理论,认为性关系不仅仅是一对一的。如果出现任何形式的“多个性伴侣”的情况,那么人口总体中就可能存在“性的社会网络”。结果,“性行为”就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一种网络化的行为。[4]
进一步思考,这样的性行为是如何在关系网络中形成的呢?这与布迪厄关系主义方法论的视角不谋而合,即“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5]由此,在场域与惯习理论的指导下,把一夜情理解成是一种短暂的性关系,而非简单的一夜的性行为。有一夜情经历的人就是布迪厄理论中的行动者。
一夜情的场域可以看成是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一夜情性关系只是这样的关系网络中的一部分。这样的关系网络符合场域的基本特点:首先,这样的场域就像一个小世界,是可以相对独立存在的社会空间,表现为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工作关系等纵横交错的关系网。其次,场域中的每一个人作为行动者都有自己相应的客观位置,如工作岗位、社会地位等。人们依据其所在社会中占据的位置及其掌握的资源或资本,建立相互之间的联系。最后,在这样的场域中,人们通过日常社会交往,不断围绕社会资源的分布进行互动。一夜情也同样具有该场域的特性,并会受其所属场域的形塑影响。
有学者指出:布迪厄是一个方法论的“中观主义”者,他既不赞成方法论上的整体论(宏观主义),也不赞成个体主义(微观主义)。场域是联结宏观社会与微观个体的桥梁,应该通过研究它来理解社会与个人的关系。[6]这正是用场域理论来解释一夜情性关系的目的所在,可以既兼顾社会环境的影响,也考虑到个人的主观认识与行为特点。
在涉及一夜情性的日常交往关系网络中,人们会以这类关系为纽带开展一系列的社会交往活动。这样的活动称为性的社会交往的实践活动,即是一种惯习,简称为“性社会交往惯习”。其核心是以性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会活动,包括所有围绕性关系而开展的社会交往活动。这样理解的目的是为了把人的性行为放到社会关系中去理解。
有学者也提到了类似的概念,把“性的交往活动”分为“性的社会交往能力”和“性交往”两个概念。[7]其中的“性交往”和之前提到的性社会交往惯习的概念相近。但需要指出的是:依据场域与惯习的理论,性社会交往惯习具备“前理性”、“社会性”和“建构性”等特点。惯习是一种前理性的具体社会实践,既不像非理性主义者那样把实践解释为完全由本能支配的反逻辑过程,也不能像理性主义者黑格尔、马克思那样把实践看成完全合逻辑的过程。布迪厄提出了“实践的模糊逻辑”,认为真实存在的实践活动是受前理性支配的,这种前理性是社会性内化在人的体内的一种性情倾向。[5][p.20]在一夜情的场域中,行动者们围绕其性关系而展开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在一夜情事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虽然行动者能按照自身所在关系场域的规则采取行动,但都不是经过仔细的逻辑推论后才行动的,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在短时间内做出的反应,这种前逻辑的、非推论的特点就是“前理性”。惯习具有社会性,是因为惯习的形成会受到社会的限制,被社会制度、社会规定性所建构,并不断地内化到行动者的身体中。单从表现形式来看,惯习就是一种被社会化了的主观体现。[5][p.170]惯习具有能动的建构性,它能积极不断地把场域环境中的新因素、新条件纳入自身,在对实践对象不断更新认识、更新建构的同时不断对自身进行调整。这种建构的过程既不是理性的观念创新,也不是本能的即时冲动,而是社会外在影响因素在体内的沉淀。
在关系场域中还存在着资本和利益。资本是场域的动力,包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行动者因占有各类资本而掌握了权力,在场域中行动者们围绕资本展开斗争与博弈。如果说资本是指行动者已经占有了什么,那么利益就是指行动者想得到什么。利益不是抽象的,而是存在于特殊场域中的,它引导了行动者惯习的策略方向。[8]
总之,从关系的角度理解一夜情,就是以其行动者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为场域,以围绕性关系开展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为惯习,分析在特定社会关系场域的形塑下,行动者是如何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进行社会交往,并最终形成一夜情的事实。这是建构主义的研究视角,重点在于“何以”(how),而不是“为什么”(why)。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研究地点为中国南部的中等城市——木兰市*因为研究内容涉及被访者的个人故事,信息较敏感,故而隐去该城真名,笔者取名为木兰市,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之所以选择木兰市作为研究地点,主要原因是木兰市的“一夜情”发生率相对较高。早在2008年,该市的城市人口发生一夜情的比率就已经达到9.7%,而全国则是晚至2010年才达到这一水平。[3]正是这种明显的差异凸显了在该市开展一夜情研究的价值。
选择定性深入访谈的方法作为研究工具,有助于深入了解一夜情性关系场域的特点及性社会交往惯习的运作逻辑。依据质性研究的方法论,理想的样本量是通过访谈已经不能再发现新信息时,这时的样本量就足够了,并不刻意追求访谈了多少人。“唯一的价值在于最终发现了多少不同的情况。它们之间差异越多越好,越大越好。”[9]因此,在信息收集的开始阶段并没有设定具体的样本量。
由于收集信息的内容较为敏感,经过不断的经验总结和对木兰市当地环境的熟悉,最终采取了三种途径寻找被访者:其一,请当地具有“本地通”特点的朋友,帮助寻找他们身边有一夜情经历的朋友。通过这种方式共成功访谈了11人。其二,以往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与北卡大学的合作项目“促进艾滋病性病领域人文社会科学与公共卫生的合作:研究与培训”。发现,木兰市居民的夜生活非常普及与活跃,主要集中在休闲场所之内,这很可能与他们的多伴侣行为有密切关系。因此尝试在往来木兰市各类社交场所的普通人群中寻找被访者。通过这种方式共成功访谈了5人。其三,通过访谈可以结识一些积极参与并且愿意多谈的被访者,然后通过一起吃饭等形式加强沟通,请他们介绍身边符合被访条件的朋友。这种方式共成功访谈了10人。
信息收集工作从2011年7月到11月,历时4个月,共约访75人,因各种原因拒访或中途退出49人,实际访谈26人,15男,11女。年龄从19-56岁之间,职业包括摩的司机、工厂工人、公务员、政府官员、老板等。均为异性恋者。
主要的信息收集方法为半结构式深入访谈。因为一夜情话题敏感,一对一的深入访谈都是在相对独立的空间开展,以便更好地保护被访者的隐私。如在茶馆或咖啡馆开展,气氛比较轻松,被访者也较容易接受。半结构式访谈有访谈提纲的设计,还设计了前后逻辑关系的问题,以检测被访者答案的真实性。在访谈过程中,不断采用追问的方式以获取较多的信息。访谈结束后,尽快整理访谈信息,如发现还有信息需要补充的,则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被访者以补充信息,以免信息缺失。
为了能够清楚剖析行动者的这种短期多伴侣关系,将一夜情分为五个步骤来分析:
(1)发生一夜情之前,双方的多伴侣情况。由于行动者的多伴侣状况是基于自身社会交往关系网络(即所在的场域)而形成的,因此多伴侣关系的双方在所处场域中必然出现场域的交集才会相遇,这是多伴侣关系双方相遇的前提。(2)相识阶段。一夜情的双方在相互认识阶段所采用的渠道和方式、双方的动机、确定人选的主要原因。(3)实际性交之前的短暂阶段。很多被访者都提到:发生一夜情之前自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而是在经过一些短暂的交往活动,双方达成共识后,才有了一夜情。因此尝试论述这种短时间内双方所做出的性社会交往惯习的特点。(4)发生性交的阶段。主要包括时间、地点、性行为特点等。(5)一夜情过后,行动者如何建构自己的一夜情。他们为什么称这种性关系为一夜情。
四、一夜情的多样性及其分析
(一)互联网途径的一夜情
老蔡,男,汉族,个体老板,50岁,大学学历,离异,有过一夜情、找情人、被包养、买性等经历。
老蔡和他的一夜情伴侣之前并不认识,是通过在网络上QQ聊天认识的。直观上他们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并没有交集,但是老蔡知道很多要找多伴侣关系的人会在晚上12点之后QQ在线,已经成为规律。可见互联网的发展缩短了社会中网民之间的距离,增加了网民之间相互认识的可能性,科技手段把网民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扩宽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互联网虚拟的空间可以构成场域,因为老蔡在实际生活中所在的场域,还是他那个体老板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的场域,只不过场域作为关系的系统,一经形成就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5][p.145]因此,互联网对于老蔡只是寻求一夜情的工具。
1. 相识阶段
老蔡说:
她是木兰市本地人,我们在网上就聊了有两个小时吧。我们没有视频聊天,就是打字,对她知道个大概吧,可能比我小一、两岁吧,是有家的人。说一起出来见面,她也同意了,就只是没有说出来你跟我睡觉,没有这么直接说。我们说好第二天出来,就约在一个地方嘛,我当时还留了电话。
由此可见,老蔡非常清楚:性需求是自己利益所在。两个人都知道“同意见面”暗含着“要发生性关系”的意义,这就是一种默契。虽然老蔡对成与不成两种情况都有所预计,但还可能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所以不是所有的性社会交往惯习都能做得合情合理,人的惯习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同时,由于双方是通过网络认识的,没有社会交往过,而且一夜情后两个人很可能不再联系。由于不会太多地牵涉到双方的社会身份,因此两个人的社会位置及所在场域的构型作用对他们之间的一夜情影响不大。
2. 发生性关系之前的短暂阶段
老蔡虽然不满意伴侣的外表,但他也能接受,并给出了他的理由:“见面后发现她长得不怎么好,但我觉得一夜情不需要这种(外表),最主要是有需求,而且她也有需求。”可见在老蔡这次一夜情的经历中,利益需求主要是性需求。
3. 发生性行为阶段
一夜情的发生地点,老蔡运用了自己的社会资本:“刚好有个房子,我朋友的,他出去外面了,就上他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然而老蔡对这次的一夜情并不是十分满意,原因是没有满足他的性需求:“她不懂什么情调,跟木头似的,很快就结束了,感觉不爽。”但老蔡也提到这次性经历没有经济资本的卷入:“事后我没给钱,她也不要钱,反正大家聊得可以就出来耍(玩一夜情)的,这么远出来,不是为了钱,谈钱就低俗了。”老蔡言下之意一夜情是一种情调、一种品位,是跟付钱买性的低俗行为相区别的。
4. 对自己一夜情的建构
老蔡在事后是这样建构自己的一夜情的:
如果事后感觉好,还可以再联系,也可能变成情人关系。但这次不好,所以她对我来说一样不算,就是相互发泄一次就完了。以后不联系了,不爽嘛。这次只有一夜,而且没给钱,要给钱就成找小姐了,被警察发现要定罪的,哈哈,所以这次算是一夜情吧。
在老蔡的理解中,一夜情很可能过渡到情人关系,是一种铺垫。如果行动者双方经过一次一夜情后,相互表示满意,则很可能继续发展成为持续的情人关系。反之,就成了一夜情。每个人对这种概念的理解,主要跟个人具体一夜情经历有关。老蔡之所以把这次性经历定义为一夜情,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只发生了一夜性关系,二是他没付钱。这里也可以看出老蔡之所以认为买性不好,是因为他知道这就成了违法的“找小姐”行为,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低俗。
(二)路边邂逅的一夜情
1. 一夜情之前
燕姐,女,汉族,个体户,39岁,初中学历,离异,有一夜情、情人经历。在发生一夜情的时候,她还是个企业的临时工,其所在场域是临时工人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她的一夜情伴侣是个陌生的开车路人,两个陌生人处在不同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但由于相同时间、空间的交集,使两个人相遇。
2. 相识阶段
燕姐和她的一夜情伴侣是在路边偶然相遇的:
有一次我和我老公吵架,吵完之后心里很乱,我就离家出走了,……走到路边的草地上,在那里躺着睡着了,睡到大概晚上12点多吧。来了一个开小车的(男人),把我拍醒了问我:小妹,你干嘛呢?怎么不回家?我说:累了睡一会,他说:吵架了?他看出来我心情不好,说到我心里去了,后来他说:走,请你吃夜宵。我刚好肚子也饿了,就跟他去了。
在这一阶段中,燕姐的一夜情伴侣运用了自己的经济资本(开小车、请吃夜宵),而燕姐年轻的外表(小妹)也成了自己的资本(性),双方才得以一拍即合。
3. 发生性关系之前的短暂阶段
由于无处可去,燕姐同意开房去休息。两个人之间有了相互试探性的语言,这为发生性关系埋下伏笔。
吃完饭,他说:我开一个房间让你休息吧。我说:你有那么好心吗?他说:你怎么这样说呢,这一点还是可以做到的。然后他就真的带我去开房了。
单从前两个阶段来看,当时的社会情境对这种发生在“偶遇式陌生人之间”的一夜情发生着较大的作用。两个毫不相关的异性相遇之后,在短暂的时间内仿佛处在一个虚拟、宽松的场域中,在这里两个人暂时摆脱了自己原有场域的束缚(形塑),行为不受之前婚姻、家庭及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在这个短暂场域里行动者的性社会交往惯习跟平常的行为方式有着较大的区别。
4. 发生性行为阶段
燕姐的一夜情发生在宾馆里。
我去洗澡了,忘了锁门,现在回想起来就想笑。我在里面洗澡他也进来了,然后这样地在里面发生了。
燕姐从和丈夫吵架到和陌生的路人发生一夜情性关系,都不是她之前事先考虑好的,更不是精心计划的。但随着事情的发展,燕姐的一夜情却“合情合理地”发生了,这其实是燕姐在社会中通过不断地实践而得到的认识,并在惯习中体现出来的前理性。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时候不是因为信息缺失,也不是因为思维的局限而不能完全认识即时社会情境。这主要是由于人的思维受社会限制,是被社会组织和建构的。[5][p.170]
5. 对自己一夜情的建构
燕姐之所以在一夜情经历中有这样的性社会交往惯习,主要是受其经历和当时情境的影响。首先,她认为自己是结过婚、生过小孩的人,这样的经历过后,在这样的建构中,燕姐觉得她的一夜情的“性”经历较容易接受。那么,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燕姐结婚前,或许她并不会有一夜情。可见她的性社会交往惯习会受到生活中各种经历的影响,并与新发生的经历合并作用于自己的惯习,从而在这些经历的影响下进行不断的建构或者自我更新,逐步形成了如今的一夜情惯习,这是惯习的建构性。其次,当时燕姐刚跟老公吵过架,心情非常糟糕,又身无分文、无处可去。这时来了个虽然陌生但热心的路人,又是请吃饭,又是安排住处。这种即时的客观情境合并之前的经历共同作用在燕姐身上,发生了一夜情。这表面上看起来是燕姐的主观行动,而实际上是惯习社会性的体现。
很奇妙,因为我们不像少女,我们本身都是结过婚的,又生过小孩,在那种情况之下……可能心情不好最容易产生一夜情,这个是最关键的,如果是心情好就不容易这样了。大家去逛街、玩啊就不容易想这些事。找一夜情玩的50%都是处于空虚、心理失落,就像我。
但说到为什么没有继续保持这段性关系时,燕姐说:
我没有(继续)了,让老公知道了,我的家就不用要了。不管家怎么不好,毕竟是(夫妻)登记了的,不是同居在一起的。结婚也有结婚的好,要是同居,现在他买的房子就没有我的份了,你住院了(其他性伴侣)也不会帮你。
当行为的影响要超过短暂场域的界限时,行动者的惯习又会回到自己日常的场域中,行为特点要遵从日常场域的规则与逻辑。在燕姐的日常场域中,不仅婚姻关系对她的性社会交往惯习有较强的约束力,更重要的是婚姻背后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如金钱资助、房子分享和生活的照顾等。
当问到“什么是一夜情”时,燕姐说:“只发生了一次,然后再没(相互)联系,就是一夜情。”可见燕姐对一夜情的理解重点在“一次”上。
(三)熟人之间的一夜情
治国,男,汉族,公务员,31岁,大学学历,已婚,有一夜情、买性经历,所在的场域是公务员社会交往关系网络。他有一个两岁多的小孩,生活在木兰市属于一般水平,不富裕但也不贫困。平时他空闲时喜欢和一帮摄影爱好者出去采风。他的一夜情伴侣是风景点一家小旅馆老板的女儿,她帮着打理旅馆生意,熟悉风景点环境,经常和采风爱好者打交道,可见她的场域是风景点旅馆经营者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
1. 相识阶段
在相识阶段中,治国在风景点的旅馆里,偶然遇到“长得不漂亮,但是看起来很青春,很活泼”的店老板女儿,相互看上了对方。这是“性风采”在这个阶段发挥的作用。性风采就是“一切足以给主体带来性方面的自豪感或满足感的自我形象呈现的总和。”[3][p.83-89]第二天两个人在一起游玩的时候,有了更亲密的行为。从此两个人建立了长期的联系,但一直没有发展成性关系。
2. 发生性关系之前的短暂阶段
双方逐渐成为相互熟悉的人。但直到最近一次两个人一起去开房,才有了发生性关系的可能。在治国对自己一夜情惯习的建构中,“开房”是两个人对性关系心领神会的信号。
最近一次是一个月前,她来进货,我们一起吃饭,我说这次不要走了,她想了想就同意了,我开了个房告诉她下午忙完了,就去那里等我,我下午也要上班。其实开房时她就明白我的意思了,都是成年人,谁不懂啊。
3. 发生性行为阶段
治国对这次性关系并不是十分满意,因为性伴侣在脱了衣服后的外表让他觉得“没有想象中的好”,在这一点上没有完全满足治国对“性”的利益需求。虽然最终他们还是发生了性关系,但是同时也成了没有下一次的原因。另外,治国强调自己那天发生过性关系后,晚上10点就回家了,原因是怕一夜情性关系传出去被老婆知道,可见他所在的场域对性社会交往惯习的形塑力,在婚姻关系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治国不敢在外过夜,怕被发现。
4. 对自己一夜情的建构
治国把它建构成一夜情,原因就是他觉得不会再和旅馆老板的女儿发生性关系了:“只发生了一次,我觉得这是一夜情吧。因为上次发生关系感觉不好,我想应该不会有第二次了。”但治国提到他们还保持着联系,因为治国觉得他们是朋友关系,“如果她还联系我,我想我们还会保持朋友关系的。”可见发生在熟人之间的一夜情,或许“性”可以只发生一次,但社会交往联系未必能断,这一点和西方的一夜情有着较大的区别。
(四)隶属关系中的一夜情
1. 一夜情之前双方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系
文博,男,汉族,企业白领,26岁,大专学历,未婚,有一夜情经历。他在还是学生的时候发生过一次一夜情。当时他21岁,社会位置是在校的大专生,场域是在校学生有限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他的一夜情伴侣是他的女外语老师,约26岁,已婚。从社会交往关系网络来看,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他俩的场域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交集。
2. 相识阶段
文博和外语老师相识有两三年了。这位老师年轻、漂亮,很受文博和同学们的喜欢,私下里还曾经有些男生向这位外语老师表白过。这位老师独对文博学习和生活很照顾,文博也很喜欢这位老师,但双方这种相互爱慕一直没有捅破。在这一阶段双方产生好感是来自“外表”与“温情”的吸引,也为之后的性交往惯习注入了社会化[5][p.26]的内容。
3. 发生性关系之前的短暂阶段
毕业前这位外语老师来参加文博班级的聚餐,他们两个聊了很久,直到聚会结束只剩下两个人。文博描述了当时引发一夜情的情境:酒精的作用、愉快的聊天、暧昧的眼神、双方都有发生性关系的需求、聚会最后只剩独处的两个人等,这种情境充当了文博性社会交往惯习的催化剂。
喝完酒,我说今晚不回去了,她犹豫一下,我连拉带拽就把她拉去开房了。我敢拉她去开房是因为我感觉她当时也很想玩一夜情,反正她也没有抗拒嘛,有的话那肯定做不了。
4. 发生性行为阶段
开房的费用是外语老师付的,可是文博对那次一夜情性经历很满意。
5. 对自己一夜情的建构
虽然文博对外语老师有好感,但那次一夜情并不是文博事先计划好的,只是在当时的情境下,临时做出的决定。再加上之前两个人相处的经历,社会化体现在文博主观的性社会交往惯习中,这体现了惯习的前理性与社会性。“我没想到会和她发生一夜情,哪敢想啊,那件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在谈到为什么把这次性关系称为一夜情时,文博说:
就一次而已,就算是和老师一起发生的,也是一夜情吧。那一夜过去之后就再没有和她联系了,我毕业了,来木兰市工作了,如果我们以后再有同学聚会,应该还会见到她吧,听说她现在都有小孩了。
在文博的建构中,“一次性关系”和“不再联系”就是一夜情的主要概念构成因素。
五、类型对比与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依据事件发展的五个阶段,主要对陌生人之间一夜情和熟人之间一夜情的特点进行如下的理论对比与总结。
(一)一夜情之前双方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系
相同点:无论是陌生人之间还是熟人之间的一夜情,双方行动者的场域都需要出现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集,这是发生一夜情的必要条件之一。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夜情双方才能建立联系,行动者占有的位置、资源在一夜情关系中才有意义。
不同点: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陌生人之间的一夜情中,两个行动者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虽然没有明显紧密联系,但在空间上两个人都处在可相见的区域内,再加上现代化科技沟通手段的辅助作用,使原本陌生的两个人有了相遇的机会。熟人之间的一夜情则不然,两个行动者不仅已经相遇,而且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社会交往后已经相互熟悉的人。在他们的一夜情形成之前,他们处在相对紧密联系的社会场域中,而且即使一夜情之后再也没有性关系的发生,双方似乎也不能离开共同的社会关系场域。
(二)相识阶段
相同点:在这个阶段表面上看,性需求和情感需求在各类资本的运作下,对一夜情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行动者评估自己“有什么”和对方“能提供什么”是否匹配的阶段,这跟行动者心中建构的一夜情或对一夜情的期待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不同点: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一夜情,不管是通过什么渠道结识的,都需要有一个相互认识与评估的阶段,一夜情能否形成跟短时间内双方的利益需求、资本运作和当时的社会情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陌生人之间一夜情更能体现惯习中“不是出于有根有据的意图和盘算,却也是合情合理的实践”。[5][p.163]而发生在熟人之间的一夜情经过了长期社会交往的铺垫,双方对相互情况有一定了解,一般比“陌生人”更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因此他们之间更多体现的是惯习的建构性和社会性特点。
(三)发生性关系之前的短暂阶段
相同点:这个阶段看似短暂,但在一夜情形成过程中却起着关键的作用。从案例中总结,至少有三方面的因素在这个阶段发挥作用。首先是当时社会情境的作用,很多被访者(行动者)提到当时由于“太晚了”、“打不到车了(没出租车)”、“喝多了”、“心情不好”、“性暗示”等情境因素的发生,催化了他们一夜情的形成。其次是之前在相识阶段相互评估结果的铺垫作用,因为对之前铺垫的良好评估,所以当时的情境成为了一种“借口”。最后是行动者各自利益需求的作用,这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直接影响着行动者的意愿,利益需求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是几种需求合并发挥作用,如“性需求”、“情感需求”,甚至是“工作需求”、“社会从众需求”等。但“性需求”是其中最根本的利益需求。各种各样的利益需求是最终导致一夜情发生的内在驱动力。
不同点:单从这个阶段看,两种一夜情中惯习的区别并不大,但惯习背后隐藏的社会性、建构性都有着实际的区别。如在熟人之间“文博与外语老师的故事”中,其实他们之前有很多相处的机会,但相互爱慕一直没有捅破,这种以往经验历史性的积累在最后一次毕业聚餐时才爆发出来,这是惯习历史性、社会性的特点。由于陌生人的一夜情发生在一个短暂的、宽松的临时场域中,他们之间一夜情惯习的社会性、建构性具有相对的间接性,因为缺乏以直接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历史基础,也就缺乏直接的“相互了解”及“经过评估后的信任与情感”等因素的支持。
(四)发生性行为阶段
相同点:两种一夜情都发生在木兰市相同的社会大环境下,因此行动者的性社会交往惯习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大场域中法律、社会道德和婚姻的形塑约束,这是场域能动性的作用。一夜情现象虽然发生率在增长,但这类性关系毕竟不被主流社会认同,一夜情行动者在发生性行为阶段,或多或少都要考虑到自己所在场域的影响。如已婚的治国会选择“不过夜”,因为担心被老婆知道。已婚的燕姐也提到一夜情如果“让老公知道了,我的家就不用要了”。案例中离异的个体户老蔡虽然不用担心一夜情对婚姻的影响,但他也提到自己的一夜情没有给钱,否则就成了“找小姐”了,万一被发现会被警察定罪,可见老蔡也会考虑社会场域中法律的约束力。另,不得不指出的是,特定一夜情关系场域与特定的性社会交往惯习相应,不能把一种性社会交往惯习“生搬硬套”地放到另一种一夜情场域中去理解。如在个体老板老蔡的场域中,由于他们受社会组织的约束力较小,体现在他们性社会交往惯习中的自由度就较大,而公务员治国所在场域的形塑力则严格得多。所以,一种场域照应一种性社会交往惯习,将个体户关系场域的性社会交往惯习简单地搬到公务员场域中分析,则会导致“水土不服”。
不同点:在这一阶段两种一夜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性健康的评估上。在其他一夜情研究中发现,[10]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一夜情,由于对之间关系缺乏足够的信任,觉得不安全或可能会感染性传播疾病,这部分人较倾向于使用安全套。而熟人之间的一夜情由于行动者之间的认识,建立在较为熟悉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上,这种社会关系会影响其对性安全意识的判断,这些人更倾向于少用或不用安全套。
(五)对自己一夜情的建构
两种行动者在建构一夜情概念时,并没有明显的差别。有些行动者甚至一开始并不知道这次性关系会是一夜情,他们都是在事后才把这次性经历归类为一夜情的。因此,对于行动者建构下“什么是一夜情”的问题,把所有26个案例归纳总结如下:a.只和伴侣发生过一次性关系,然后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过第二次。这和之前其他一夜情研究提出的“通常仅只一次,也可能是有限的两三次”的概念内容有所不同。[2]一夜情强调一次性关系,明显把性和持续的“爱”分离开来。b.不以金钱为前提发生性关系,就算有给或送金钱和礼物的情况发生,也是以相互表示友好为目的而赠送的,并不是“性”的价格。行动者们之所以这么解释自己的一夜情,一是为了区别于“卖淫嫖娼”这种违法的性关系,二是为了突出其中的“情”而非单一的“性”,尤其是熟人之间的一夜情更加明显。c.一夜情也可以不过夜,甚至可以发生在白天。这是由于社会场域对性关系的形塑作用,在法律、法规、婚姻家庭、社会道德规范等约束力的影响下,行动者用不过夜的方式躲避别人的察觉,中国的一夜情也可以是“白天情”。d.木兰市一夜情的伴侣选择范围已经超出了西方一夜情的常规,不仅可以是在路边、酒吧等地方认识的陌生人,或者通过互联网认识的网友,也可以是自己生活圈子中的熟人,可以是通过生活圈子认识的朋友,即“朋友的朋友”。这一点在定量调查中得到了证实,2010年中国地级市里40%左右的一夜情都是在熟人之间发生的,其中男性有2/5、女性有1/2的一夜情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3][p.316]而且在26个访谈中,很多被访者提到,这种发生在熟人间的一夜情往往只是停止性关系,但由于很多人还在一个社会交往关系网络中,所以还会拥有持续的社会关系。
可见,中国的一夜情和西方的并不完全一样,舶来的性关系名称在中国人的建构下,有了本土的含义。其最大特点就是把“持续的社会关系”与“不持续的性关系”统一在这种快餐式的性关系里,同时,一夜情性关系又把“持续的情爱关系”和“一次的性关系”清晰分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统一”与“分离”,其背后的社会根源是什么?这为后续的研究提出了思考。
六、结 语
从场域理论的视角看中国社会中的一夜情,这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人际交往过程中宏观社会与微观个体之间的关系,开启了一种“中层理论”,[6]给研究社会对人的关系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场域把社会看成是客观关系的网络,惯习指行动者社会化的主观行为。客观决定着主观,也就是场域决定着惯习。但一夜情关系场域与性社会交往惯习之间不是单纯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通过“实践”来“生成”或“建构”的关系。[6]一夜情性关系行动者既不是单纯受外在社会因素决定的纯客观个体,也不是只受内在理性引导的纯主观个体。行动者在自己所处的复杂关系场域中通过实践,不断认识场域,不断被场域形塑,而又不断依据这样的形塑建构自己的性情倾向。[5][p.165]场域介于宏观社会与微观个体之间,内部行动者的惯习在经过场域的形塑后,反馈给宏观社会,而社会对个体的作用也得先经过场域的构型作用后,才能作用到个体身上。可见场域理论既考虑到了社会的整体客观作用,也兼顾到了社会中个体的主观能动反馈。
场域与惯习理论从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一夜情,这为理解社会空间中人的互动活动与实践逻辑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一夜情场域是关系的场域。一夜情并不是单纯的性行为,而是在复杂社会关系网络中形成的一种短暂的性关系,这种性关系形成于客观社会关系交织的空间中。从关系的角度来考虑一夜情,才能准确把握行动者的位置、掌握的资本及所需的利益等,才有助于理解一夜情场域中的特定逻辑及性社会交往惯习的互动活动。性社会交往惯习是关系的惯习。一夜情行动者将对社会的不断认识内化到自己的生理行为中,体现了惯习与身体的关系。用关系论的思维分析一夜情社会现象,是认识社会本质的一种方法。
[参考文献]
[1] 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M].台湾:万有出版社,2006.
[2] 毛燕凌.一夜情研究[EB/OL].http://www.sex-study.org/news.php?isweb=2&sort=168&id=1662&classid=2013-2-2.
[3] 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 Laumann,E.O.&J.H.Gagnon,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Sexual Action[A].Richard G.Parker & john H. Gagnon(eds.),Conceiving Sexuality,Approaches to Sex Research in a Postmodern World[C].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5.
[5]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6] 毕天云.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J].学术与探索,2004,(1).
[7] 潘绥铭,黄盈盈.性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 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9] 潘绥铭,姚星亮,黄盈盈.论定性调查的人数问题:是“代表性”还是“代表什么”的问题——“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及其方法论意义[J].社会科学研究,2010,(4).
[10] Zhang Nan,Abler Laurie,Bao Yu,Pan Suiming,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short-term,Yiyeqing relationships and how they are formed:Implications for condom use in Liuzhou, China[J].Journal of AIDS and Behavior,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