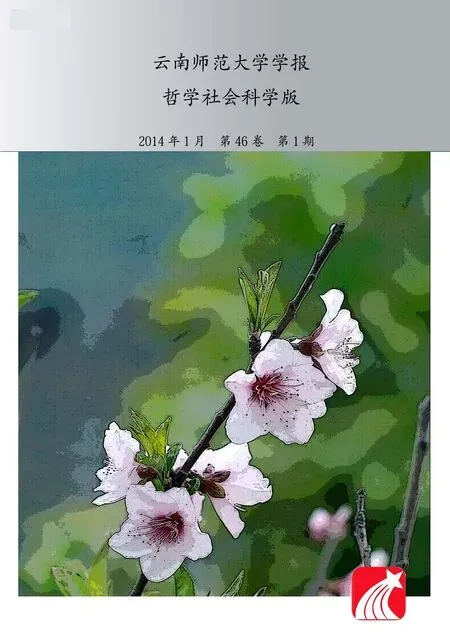中国外语规划与外语政策的基本问题*
2014-03-12赵蓉晖
赵蓉晖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上海 200083)
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6000多种语言的世界,由语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众多,为交际、管理、认同等目的,人们开始从事语言选择、语言规范、语言教育、语言传播等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语言规划活动。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是人类有意识地影响和干预、调整、管理语言发展的活动,是对语言多样性的一种人工调节,是一种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活动(刘海涛 2006)。[1]
语言规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迅速发展,与政治学、社会学关系密切。Ricento(2000)[2]将其划分为3个主要阶段:(1)早期工作(1950-1960年代晚期),脱离殖民统治后的新兴国家为追求国家统一和现代化,纷纷用法律形式确立国家语言或官方语言;(2)第二阶段(1970年代早期—1980年代晚期),语言规划开始从单一的以语言代码为中心的理论过渡到综合考虑语言应用和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的关联问题;(3)第三阶段(1980年代中期以后),语言规划进入后现代主义时代,开始重视语言多样性,提倡语言生态观,维护语言人权、濒危语言保护成为语言规划的基本目标。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迅速变化,虚拟世界迅速发展,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较量带来了国际范围内的语言竞争和传播。笔者认为应对Ricento的划分加以补充,区分语言规划的第4个阶段(1990年代初至今),即语言规划的国际化发展阶段。
在前3个阶段,语言规划基本上由主权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开展,规划的对象以本国的民族语言为主。但进入第4个阶段之后,由于经济发展的国际化、人口的国际流动、虚拟世界交流增加,影响语言规划的因素增多,外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外语规划和外语政策制定问题于是成为当代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
关于语言规划的类型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区分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和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是最普遍的做法,还有人提出了习得规划(acquisition planning)(Copper 1989)[3]和功能规划(function planning)(李宇明 2004)[4]。由于外语不是我国固有的语言,其本体规划应由其来源国承担。我们将具体讨论外语规划与外语政策的4个具体层面。
一、外语的地位规划与政策问题
(一)外语的内涵与外语的地位
外国语言文字在我国通常被简称为“外语”,顾名思义,这是指非本国固有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是以政治文化因素定义语言的典型例子。人们常用“母语”指称自幼习得、使用最熟练、最能代表个人身份认同和民族情感的语言;而以一种语言被习得的顺序称呼“第一语言”、“第二语言”等。而“外语”则完全建立在国家认知的基础上,一种语言如果不是一个国家固有民族的母语,通常就被认为是外语。在个人认同中,“外语”是异邦的语言,即使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公民生活在英语国家讲着英语,他通常也会认为英语对他而言只是外语而已。可见,外语的概念和国家认同、公民意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一个和政治文化因素紧密相连的概念,外语与使用者身份、国家认同高度相关,在各国的语言政策体系中都是特殊的、边缘化的部分。一个国家在制定语言政策时,首先要考虑本国语言,而对外语不予提及或少有提及,体现了语言的国家主体意识。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有3处提到语言,所说的都是中国民族语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部中国语言政策的最高法典中,虽有4个条款涉及外语,但都规定,外语在中国的使用必须以首先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前提;在我国各级政府颁布的近500个涉及外语使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外语的从属地位同样十分明确(赵蓉晖、郭家堂 2010)。[5]可见,作为中国语言规划对象的外语规划,其法理依据和现实基础与中国民族语言完全不同,外语政策的目标、显现方式、作用范围、对象、实现途径等也必然和国内语言政策有很大差别,这是我们开展外语规划、制定和理解中国外语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近年来有不少对外语的质疑,大都涉及外语在中国的地位问题。从上述内容可见,中国各民族语言是中国语言资源体系中不可动摇的主体,外语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在我国语言资源体系中的“配角”地位。至于有人担心外语危害中国语言的地位或“纯洁性”而导致“汉语危机”,影响汉语发展或国际传播等(潘文国 2011,[6]傅连连 2012,[7]李君、马庆株、黄彩玉 2012,[8]陈春雷 2013[9]),是因为对语言传承、语言演变、语言系统自我调节规律了解不够,或者是因为缺乏对社会语言生活的全局性关照所导致的。
(二)语言的价值与语种规划
尽管当今世界已进入后工业时代,全球化、信息化、媒体化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很多人甚至认为全球一体化时代已经到来。但在语言学家看来,“这个世界没有变成一个村,相反地,它是由村庄、城市、社区、居民点通过物质的和象征的纽带以难以预料的方式组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Blommaert 2010),[10][p.1]语言往往成为划分人群的标准。“不过,尽管语言四分五裂,人类还是联系在一起,因为有人能说不止一种语言,不同集团因此可以相互交际。……语言集团(language group)之间由兼通多语之人建立的这种联系,非但不是没有一定之规,还构成了一个超强高效的网络,……这种神奇的联系方式构成了全球语言系统。”(Swaan 2001)[11][p.1]在全球语言系统中,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的价值,这些价值就是语言规划者确定语言地位的基本标准。由于外语的特殊地位和传承方式,它的发展更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应以满足输入国实际应用需求为基本宗旨,国内语言规划中需要特别关照的认同、人权等因素,在主权国家的外语规划中是次要、甚至被忽略的问题。
国际上开展语种规划时,不同国家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而推出了不同的政策。例如,荷兰、澳大利亚、英国以满足公民国际化生存为目标的外语规划,把国际经济活动中需要使用的语言作为主要的外语语种发展;美国致力于开展维护国家安全的外语规划,其语种选择以对美国国家安全有现实或潜在威胁的国家与地区语言(包括方言变体)为主;以融入国际社会为主要目标的韩国和日本,国际通用度最高的英语是其重点发展的外语语种。但对语言价值的判断和度量至今仍然是语言规划中的难题之一。
尽管可以明确,“中国的外语发展应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服务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提供语言支撑。”(赵蓉晖 2010)[12]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做好语种规划并非易事。尽管我国的外语语种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语种数量和语种结构难以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问题依然存在。赵蓉晖(2010)[12]从国家安全需求和现有语种结构出发,认为当前应重视欧盟、拉美、非洲、南亚、南海国家的语言;张治国(2011)[13]结合政治、经济、综合国力与教育等因素,提出了一份包括24个语种的中国“关键语言”清单;赵蓉晖(2011)[14]针对上海世博会的需求与城市国际化发展目标,综合语言流行度、人口覆盖面、经济外向度等因素,提出了上海市应发展的外语语种;胡文仲(2009)[15]、文秋芳(2011)[16]等学者指出了我国在这一方面的问题与不足。尽管学者们试图解决我国外语语种规划面临的现实问题,但由于我国外语政策的价值导向还不甚清晰、外语的需求和人才分布不均,使得我国很难用统一的标准做出一以贯之的语种规划,开展多层面的语种规划十分迫切。
荷兰学者Swaan以“Q值”表示语言的交际价值,它由语言的流行度和中心度决定。其中,流行度标示着使用该语言能与语群中其他人直接交际的机会,中心度标示着与其他语言的联系程度。Q值越大,语言的交际价值越大,被个人学习和传播的可能性就越大(Swaan 2001)。[11][p.39-46]我们认为,Q值计算方法可以用于在外语规划中衡量语种价值,尽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语言Q值的因素及其作用方式要复杂得多。此外,语言活力评估法、复杂网络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等,也有可能为语言价值评估带来新的实现途径,这是值得我国的语言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
二、外语的功能规划与应用政策
语言功能规划是在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的。李宇明(2008)[17]指出,功能规划的任务是“规划各功能层次的语言作用,或者说是规划各语言现象在各功能层次的价值与作用”,是对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的延伸。社会生活可按照职业、行业管理部门设置等标准划分成不同的领域,语言的功能则相应地划分为国语、官方工作语言、教育、大众传媒、公共服务、公众交际、文化、日常交际等8个层次。在我国,外国语文的应用体现在教育、大众传媒、公共服务、文化活动、日常交际中,体现了国际化浪潮给我国社会语言生活带来的直接影响。
(一)公共场所的外语应用与政策
在外语功能规划和政策层面,当前突出的问题体现在公共生活领域中的外语使用管理方面,具体表现在大众传媒、公共服务、文化活动等3个层面。一方面,城市国际化发展的不断推进使公共生活领域中的外语需求不断增加,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西安、南京等城市规划者纷纷把城市外语能力和外语使用程度列入城市国际化评估指标,城市语言生活中的外语成分在持续增加(赵蓉晖 2009[18],2012[19]);另一方面,由此带来的管理问题也逐渐显露,引发了社会上对“外语过度使用”、“外语滥用”的质疑,进而上升到担心汉语空间被挤占、国家形象受损、国家认同减弱等文化安全层面,甚至连续多年成为全国和众多地方两会上被提议改进的问题(《外语战略动态》 2009-2013)。
其实,我国的政策法规中已经包含了不少涉及外语使用的内容。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截至2010年,我国省部级以上政府部门正式颁布的针对国内事务的相关管理法规已接近500个,涉及行政活动、安全监督、保险业、银行业、财务、公安、工商、边防海关、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40多个行业领域,涵盖公文、地名、社会用语用字、城市语言环境建设、灾害警示、人事资格等多种内容。其中,绝大部分都明确规定,在我国境内或由我国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中,必须首先使用中国语言文字,外语只能处于补充、说明的从属地位,最多只允许中外文并用的情况出现,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我们也确实发现,在个别政策法规中有特别强调外语使用的情况(赵蓉晖、郭家堂 2010)。[5]参照几次外语使用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到,当今外语使用中的乱象,主要是由法规知晓度低和执法不严造成的。这方面的政策研究和执法改进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二)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政策及争议
将外语作为教学语言曾局限在外语教学课堂内。随着外语教育的深入发展和教育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外语(主要是英语)逐渐成为非语言学科的教学语言,这在国内被称为“双语教学”*小学和幼儿园中的双语教学大多指外语教学,与大学用外语讲授非语言课程的做法不同,因此这里只讨论大学的情况。。与加拿大、美国、中国民族地区开展旨在维护民族和谐的民族双语教育不同,我国的“中—外双语教育”最直接的目标是提高外语水平、培养掌握外语的专业人才(王斌华 2003)。[20]后来,随着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需要,用英语开设专业课程成为吸引海外留学生的重要手段,也得到了政策的大力扶持。
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我国外语教育的全面普及开始于2001年,用外语作为非语言课程教学语言的尝试也始于同一年。教育部在2001年发文明确提出,要在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其中“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还特别强调“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我国入世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更要先行一步,力争三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要达到所开课程的5%至10%”(新浪网 2004)。2007-2010年,教育部与财政部联合评选了一批高校中的双语教学示范课程,资助的课程数量分别为100门(2007年)、100门(2008年)、158门(2009年)、434门(2010年),每门课程资助10万元。地方政府和学校的相应扶持政策也不断出台,例如上海市就出资建设了一批全英语课程,很多高校也对双语课程给予了政策上的大力扶持。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外语(主要是英语)迅速进入高校课堂成为教学语言,在教育中的功能得到扩大。但由于推进速度较快、师生外语水平参差不齐和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等原因,双语教学受到了不少质疑和批评(李慧仙 2005,[21]马庆株 2007[22]),被指违反法律、费时低效、危害国家文化安全、影响母语能力和生存空间等,成为社会热议话题。因此,对双语教学政策的评估与调整,也是我国外语规划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外语的习得规划与教育政策问题
语言习得规划属于教育范畴,是通过教育手段使被教育者获得特定语言能力的行为,是国家语言规划总目标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和落实,我国学界习惯上称之为“语言教育规划(或语言教育政策)”。由于外语缺乏国内语言所具备的自然传承条件和应用环境,其发展尤其需要依靠人为的语言教育,外语教育规划因此成为外语规划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中华民族同外部世界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有据可查的中国外语教育最早开始于元朝,此后历经多个朝代曲折发展。1949年以后,我国的外语教育规划经历过几次重大政策调整,对我国的外语发展影响深远。胡文仲(2009)[15]把新中国教育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1)1949-1965年:我国外语教育形成新的格局;(2)1966-1977年:外语教育遭受严重破坏;(3)1978-2009年:外语教育恢复和发展,改革全面展开。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外语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各个层面都开展了广泛的外语教育,学习过外语的人数已接近4亿*根据《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提供的数据推算而来。,外语教育的规模居世界前列,教育体系、教育质量、语种规模等都大为改观,为我国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外语人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Kaplan和Baldauf(1997)[23]认为,语言习得规划应包括6个目标:(1)决定教授何种语言;(2)决定教师的数量与资质;(3)融入地方社区;(4)决定在教学大纲中使用什么材料以及如何使用;(5)建立国家与地方的评估体系;(6)决定财政投入。参照这些目标和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现实,应该看到,我们还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主要包括:(1)缺少外语教育规划机构,各阶段外语教育缺少衔接,直接影响外语教育效率和效果;(2)缺少中长期发展规划,整体规划缺失;(3)缺少权威的语言能力标准和认证机构,评估体系不健全;(4)缺少外语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师资质量良莠不齐;(5)语种数量与先进国家差距较大,对一些语言的重要方言、社会变体认识不够,教学和研究都很缺乏;(6)外语学科布局缺乏科学性,造成学科布局失衡、学科水平下降、教育质量堪忧。(戴炜栋 2010[24],赵蓉晖 2010[12];文秋芳 2011[25];束定芳 2012[26])
与此同时,社会上对外语教育的“声讨”不断,先是批评外语教育“费时低效”,然后批评外语考试在人才评价中的“一票否决”作用影响了人才多样性,再接着批评“全民学外语”导致的社会资源浪费,开始有人怀疑外语教育影响民族认同和母语的发展,有人甚至认为当前的外语教育是“摧毁中国素质教育的一把利剑”(《文摘报》2004-08-22)。《外语战略动态》(2009-2013)连续几年报道的全国两会代表对外语政策的质疑中,有不少是直接针对外语教育的。可见,外语教育规划中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外语教育改革已成为外语规划和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四、翻译规划与翻译政策
翻译是为满足不同语言群体的交际需要而进行的语言转换活动,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翻译跨越中西、沟通古今、穿越时空,是连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与文化的最主要的桥梁。翻译不仅丰富了各民族的语言,促进了各民族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还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谢天振等 2009)[27][p.1]我国历史上的4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元化翻译),无不与社会文化的重大发展联系在一起。翻译并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替换,实质上是一种改写。翻译过程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政府所颁布的翻译政策、设置的翻译管理机构对翻译活动具有最强大的规约作用,直接决定了译者译什么和如何译。很多国家或政权通过制定政策,利用翻译活动作为实现其政治或经济等目的的工具。因此,翻译规划应是语言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特殊的语言功能规划,外语规划应特别关注这一内容。
在中国历史上,翻译规划和翻译政策在翻译活动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唐朝政府对佛经翻译的支持,明末清初允许外国传教士与中国译者合作翻译科技著作,到清朝末年洋务派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设立同文馆与江南制造局,这些翻译行为无一不从属于政府在当时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翻译活动也体现出了为政治、经济、文化服务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引发了苏俄作品的翻译高潮,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也决定了英美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汉译的相对低迷。随着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破裂,我国对苏联作品的翻译也几乎完全停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迎来了新一次翻译高潮,西方国家的作品通过翻译大量涌入,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思想发展。
翻译政策可以是“有形的”(tangible),也可以是“无形的”(intangible),有时可能没有明确的关于某项翻译政策的官方文献或声明,但是可以在政府领导人的讲话或官方报纸杂志的头版文章或编者按中找到其踪迹。另外,翻译作为文化活动经常受到政治、经济、出版等因素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往往体现在基于外交政策、文化政策、出版政策或因经济原因而采取的政策手段上,并且不同的文本类型,采取的政策手段也不相同。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增加,作为联系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手段,翻译活动更加活跃,但同时也逐渐暴露出很多问题。例如,翻译市场混乱,缺乏有力的监管措施,导致无序竞争、鱼龙混杂;源文本的选择中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导向突出,对学术、文化价值较高但受众面较小的作品重视不够;翻译标准缺失,译者资质良莠不齐,直接影响翻译质量。此外,中国文化与思想如何通过翻译进入世界主流话语体系的问题,也已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需要尽快提出对策。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制定《翻译服务规范》(2003)、《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2003),推出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CATTI),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在“走出去”战略框架下推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建立多个翻译研究基地,研制公共场所外文译写标准,等等。
我们认为,翻译规划与政策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可以结合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理论开展多方面的深入探讨,为我国的翻译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和对策建议。
小 结
中国人学习和使用外语,绝不是由单纯的经济或文化因素决定的,而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带来的深刻认识,也是国家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外语规划是我国语言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外语特殊的地位和存在方式,外语规划和政策制定、实施的原则与路径和国内语言有很大区别。由于对外语规划的认识和研究不足,相关政策制定和执行不力,使外语成为当代社会语言生活中备受批评的话题,不仅影响了语言生活的和谐,也可能影响外语的健康发展。本文结合语言规划理论和我国语言生活实际,探讨了外语地位规划、外语功能规划、外语习得规划和翻译规划等4个层面的内容,展示了外语规划的体系,提出了每个层面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希望以此引发社会与学界对此类问题的关注,促进相关研究的开展。
[参考文献]
[1] 刘海涛.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从定义变迁看学科发展[A]. 陈章太.语言规划的理论和实践[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
[2] Ricento, Thomas.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0,(2).
[3] Copper, Robert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4] 李宇明.强国的语言和语言的强国[N].光明日报,2004-07-28.
[5] 赵蓉晖,郭家堂.外文管理政策法规汇编[R].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2010.
[6] 潘文国.“语文歧视”会引发汉语危机吗[N].解放日报,2011-02-07.
[7] 傅连连.浅谈汉语在外语学习中的渗透与中国汉语危机[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12).
[8] 李君,马庆株,黄彩玉.我国英语教育状况及对汉语国际化的影响[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2,(4).
[9] 陈春雷.汉语危机并非耸人听闻——与汉语危机否定论者商榷[J].学术界,2013,(4).
[10] Blommaert,Jan.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1] Swaan,Abram D.Words of the World:The Global Language System[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2] 赵蓉晖.国家安全视域的中国外语规划[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13] 张治国.中国的关键外语探讨[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1).
[14] 赵蓉晖.世博会外语环境建设研究[R].上海市“十一五”语言文字工作科研规划项目综合报告,2011.
[15] 胡文仲.新中国六十年外语教育的成就与缺失[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3).
[16] 文秋芳.美国国防部新外语战略评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5).
[17] 李宇明.语言功能规划刍议[J].语言文字应用,2008,(1).
[18] 赵蓉晖,罗雪梅,韩耀军,郭家堂.全国外文使用情况调查报告[R].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2009.
[19] 赵蓉晖.上海市公共场所外文使用情况调研报告[R].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2012.
[20] 王斌华.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1] 李慧仙.高校双语教学的多学科批判[J].高等农业教育,2005,(9).
[22] 马庆株.反思“全民学英语”和“双语教学”[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434d1010009b4.html,2007.
[23] Kaplan,Robert & Baldauf Richard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M].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7.
[24] 戴炜栋,吴菲.我国外语学科发展的约束与对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3).
[25] 文秋芳,苏静,监艳红.国家外语能力的理论构建与应用尝试[J].中国外语,2011,(3).
[26] 束定芳.中国外语战略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27] 谢天振等.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