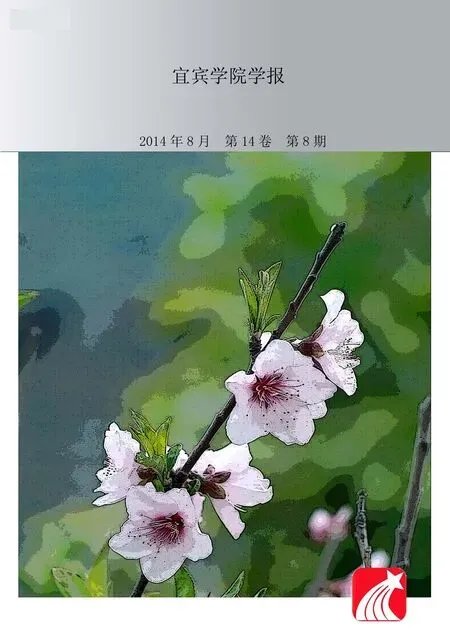王安石《洪范传》的思想架构
2014-03-12胡金旺
胡金旺
(宜宾学院 历史与哲学研究所,四川 宜宾 644007)
《尚书·洪范》以九畴为论述的中心,作为对该文进行注解的王安石的《洪范传》当然也是围绕此中心而展开的。王安石对九畴的论述在宋代“洪范”学的研究中是较为出色的[1],而对其中“五行”一畴的发挥由于思想新颖尤为引人注目。从宇宙论上看,五行是道形成万物的五种共同属性,因而通过五行就可以认识万物之道;从本体论上来看,道也正是借此万物之道使自己呈现出来。因而认识到万物之道就认识了本体之道。所以,五行是连接道与万物之道的纽带。具体之道得其序,则五行也得其序,道本体因而也得以体现出来。王安石认为九畴中除去五行和验证具体之道是否得其序的五福、六级两畴外,其他七畴就是具体之道的实际例证。因此,七畴得其序就是具体之道得其序,则五行也就能得其序。他正是以此构思来处理九畴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全文的思想架构。
一 对天地之数与五行及五神关系的整合
王安石在《洪范传》中论到五行时说道:“‘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变化而行鬼神,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是故谓之行。天一生水,其于物为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于物为神,神者,有精而后从之者也。天三生木,其于物为魂,魂从神者也。地四生金,其于物为魄,魄者,有魂而后从之者也。天五生土,其于物为意,精神魂魄具而后有意。自天一至于天五,五行之生数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数之中也,盖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于两,成于三,变于五,而天地之数具。”[2]993
王安石认为“自天一至于天五,五行之生数也”,亦即天地之数产生了五行。之所以是五行而不是六行或者其他,根本的原因在于五行之数要与天地之数五相一致。既然五是天地之数,则形成万物之五行之数当然也应是五,因为天地是万物产生的根源。这解释了五行的由来以及五行何以在产生万物的过程中具有本源的作用。这种思想主要还是对已有思想成果的继承,而在五行中最能体现王安石思想创新性的是将天地之数与五行及五神整合在一起。
王安石将天地之数、五行与五神联系起来,是吸收了《尚书大传》《素问》《八十一难经》等书中的相关思想,再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提炼与创造。
王安石将天地生数与五行结合起来的思想直接来自《尚书大传》,其原文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天五生土。”[3]卷二而五行与精神魂魄意五神的结合则来自《素问》和《难经》。《素问》中有这样一些有关五脏与五行关系的说法:“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秋脉者,肺也,西方金也”“冬脉者,肾也。北方水也”“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同时也有关于五脏与五神关系的看法:“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脏所藏。”[4]卷六很显然,王安石在《洪范传》中将五行与五神直接对应是去掉了二者之间的中介五脏,同时也对五神的顺序与“志”这个名称进行了调整与修改。而对“志”这一名称的修改也是有根据的,其根据来自《八十一难经》中所谈的五脏与七神之间的关系,其原文是:“五脏有七神,各何所藏耶?然。脏者,人之神气所舍藏也。故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与智,肾藏精与志也。”[5]133原来,肾不仅藏“志”,也藏“精”,自然王安石将《素问》中的“志”说成“精”就不是空穴来风。王安石通过舍弃《素问》中的中介五脏而直接将五行与五神关联起来,从而将五行与五神的关系推广到万物,而不只是局限于从五脏的角度来谈五神与五行的关系,即是说万物之五行与五神都是有关系的。但这又不是一般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将五行之物质与五神之精神联系起来,因为五行并不仅仅是就物质而言。从万物都具有精神魂魄意来说,王安石对物的看法具有泛神论的色彩。
概言之,王安石在五行一畴中其创新精神体现在:不仅将天地之数与五行及五神直接联系起来,也对五神的顺序和名称进行了调整和取舍,表明其思想来自前人而又能超迈前人,体现了其思想的创新品质。根据以上的分析,正确评价王安石在五行一畴中匠心独运地将天地之数与五行及五神整合在一起的思想,应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之上的一种创新,而不完全是他的一己之见,也不是对前人成果的直接蹈袭。
二 认识事物之道的不同进路
由于道生五行①,五行变化而为万物,万物的产生都与五行这个本源有关。因此万物之道都可以通过五行分析出来。这是从宇宙论的角度来把握形下的具体之道,与根本之道相一致,因为根本之道要通过五行生成的万物方可体现出来。
从五行赅括万物总的特点,从而可以通过五行分析万物之道来看,这无疑是认识具体之道的一种方法,这种认识具体之道的方式就是所谓的术数的认识方式②。从《洪范传》中对五行相生相克关系及其他篇章对五行与利害关系的论述来看,王安石对这种认识方式也是认可的。在《原性》中,王安石说道:“夫太极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而太极不可利害言也。”[6]316可见,王安石对五行与利害吉凶的关系是认可的。但从王安石的学术实践来看,他主要还是以分析义理的方式来认识万物之道,而这种方式的途径又是多种多样的。就王安石的学术思想来看主要有字学的认识途径和经典的认识途径,这两种途径的共同之处就是要经过我们的心之思才能认识事物之道。经典与字学的认识途径是因为圣人将对大道的认识表达在文字与经典之中,而圣人又是悟道的,所以可以通过这些圣人思想的表达形式而认识到圣人之道。
那么,阴阳五行术数的认识方法与义理的认识方法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术数认识方式是根据万物产生的宇宙论的途径来认识万物之道,而义理认识方式不经过万物产生的宇宙论的线索来认识万物之道,是直接从义理来探索万物之道。因为万物之道与本体之道是一致的,而道本体可以通过心来体悟到,则形下的万物之道也就可以通过心来领悟到。当然,术数也必然要用到心之思,但是术数的认识方式不是直捣义理,而是先通过认识事物的阴阳、五行、术数之间的关系,再从中分析出道理来。很显然,义理的认识方式省略掉了术数这个中间环节。所以,术数的认识方式的根据就是万物生成的宇宙论的生成进路,而义理认识方式的根据就是道本体可以用心体证到,则万物之道也可以用心领悟到。
心可以体证到道本体,为什么就意味着心就可以领悟到具体的形下之道?从性命之理出于人心来说③,心与道是同一的,所以养心致精明之至就可以悟道④。如果我们能用心至诚,则也一定能把握到道之体所生之用。就是说既然道之体可以用心体悟到,则道之用也可以用心领悟到。所以,用心可以把握到具体之道的根源在于悟道也是用心至诚的结果。从形上的角度看,心与道是同一的,那么从形下的角度看,心与具体之道也是同一的,因为形下之心与具体之道分别是形上之心与大道之用,这就从根源上保证了我们可以用心之思领悟到七畴等具体之道。
从对七畴的具体阐述来看,王安石认为心之思还必须有其他方法的检验和辅助,他说:“虽不专用己而参之于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诚不善,则明不足以尽人物,幽不足以尽鬼神,则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2]991就是要参诸人物与鬼神,但是根本的办法依然是心之思。这是因为:第一,参诸人物鬼神也是我们心之思的结果,认为应当这样做;第二,如果参诸人物鬼神有问题,我们就得反思,即“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所以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仍然要求助于心,心之思是认识形下之道的根本途径。
总之,无论是通过阴阳五行术数还是义理的方式,我们都可以掌握到形下的万物之道。通过对一个个具体之道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达到一种有思后无思的状态,即达到了一种豁然贯通顿悟的程度。
在《洪范传》中,王安石所阐述悟道的途径是:“志致一之谓精,唯天下之至精,为能合天下之至神。”[2]994“思者,事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圣也。既圣矣,则虽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2]999后一种途径可以明显地确定为是从领悟到形下的具体之道以后顿悟到道本体,即到圣人的境界。而将“志致一之谓精”和《致一论》中的“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则可以入神矣”[2]1043合看,也可以确定王安石这里的悟道仍然是通过精天下之理的方式,即通过对形下具体之道的领悟到一定程度而悟到大道。很显然,王安石也注意到了另外一种悟道的途径,即通过养气的修养途径直接顿悟大道,即不须作穷理的工夫,而是通过修养的途径顿悟大道。这一点在《周礼新义》中表达得很清楚。可见,王安石与理学家一样认识到对大道的顿悟也有两种途径⑤。在《礼乐论》中,王安石也说道:“不听而聪,不视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尽心尽诚者之所至也。”[2]1031只要尽心尽诚,就能将人所固有的本性显露出来,也就是达到了道与入神的境界。而尽心尽诚主要是一种修养工夫,王安石以为通过此修养工夫就能够入神,即顿悟大道。
顿悟大道以后,对具体之道就可以不思而得。因而,与前文讲到的两种从形下的层面掌握具体之道的认识方式(术数与义理)不同,另一种掌握具体之道的方式是从体证到形上之道来达到掌握形下具体之道的顿悟方式。它们是认识事物之道的不同进路。而这两种方式的悟道为王安石的政治变法提供了理论根据。王安石将自己的政治变法看作是探索大道的一种方式,即通过对形下具体之道的探索到达一定的程度以后就能豁然顿悟,而领会到大道。而一旦悟道,就能“不思而得”,对形下之道做到完全正确的把握。因而,对于一个得道之人,其所作所为就必然是正确的。同样,如果王安石自以为得道,则他必然会自信地认为其变法措施就必然是正确的。这种看法无疑是将大道看作一种一成不变的存在,以为一旦悟得,就一劳永逸地掌握了道。因而极易导致一种教条主义的作风,固执己见,就不会因应现实情况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改变。虽然王安石也主张要采取权变措施[7],但是他一旦自以为得道,就极有可能听不见他人的意见。因此,王安石在实际政治中有时听不见他人的意见,不仅有其性格因素使然,而且还有其学理上的根源。
三 具体事物之序得以实现,五行之序就得以实现
王安石认为在《洪范传》中五行之序是道之序,他说道:“其相生也,所以相继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语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语时也以相继,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范》语道与命,故其序与语器与时者异也。”[2]993-994在万物产生的过程中出现了相生相克的现象,相克为器,相生为时,它们的顺序与道之序不同。王安石在此强调了道之序与器与时之序不同的依据在于五行排列的顺序不同。道之序是水、火、木、金、土,而器之序是水、火、金、木、土(《尚书·大禹谟》),时之序是木(春)、火(夏)、金(秋)、水(冬)(《礼记·月令》)。
从五神之序与五行之序相对应来看,五神之序也是道之序。这种道之序,我们将其与《老子注》中谈到的非道之序作一对比也可以反映出来。在《老子注》中,王安石说道:“一者,精也。魂魄既具而精生,精生则神从之。”[8]17精神之所以能从魂魄中产生,是因为魂魄的产生是由于精气作用的结果,即“精气为物”[8]18。魂魄中潜存着精神,因而魂魄一旦产生,精神也就应运而生。这种魂魄具而精神生的顺序是后天的万物再到先天精神的顺序,因此与道之序不同。这种后天万物返回先天精神的顺序从反面印证了精神魂魄意是道之序,也表明了我们后天的努力就是要遵循天道,回到天道。所以,后天物之序与先天道之序不同,前文所说到的器与时之序与道之序的不同也应如是视之。
这种顺序上的差异表明,第一,事物的展开是有先后顺序之分的。这种看待问题的方法,王安石不只应用于《洪范传》中,在《周官新义》中也经常使用到,它往往能准确地揭示出事物的实质特性。但是二程却对王安石这种重视事物发展顺序的方法不以为然,说道:“五行在天地之间,有则具有,无生出先后之次也。或水火金木土之五者为有序不可也,然则精神魂魄意之五者为序亦不可也。”[9]1272第二,既然事物有先后顺序的差异,则事物之间就是有差异的。这一点也为程颐所不容,说道:“介甫自不识‘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9]282程颐批判王安石将天人之道分开,但是这句话中程颐实际上也将道区分为天道、地道与人道,看不出程颐与王安石所论之道的实质差异。实际上,要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别考察程颐与王安石在道本体上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已经溢出了本文的论旨,不能作详细的讨论。但是不妨在此处作一个概要的阐述。概括地说,程颐形上意义上的天理(即道)是从万事万物都要遵循一定的规范乃至规律这个意义上来说的,都是由天理所决定的。从都要遵循天理而不能肆意妄为来说,则万物是一。既然天理是一,天道与人道等形而下之道就没有根本的区分。但是王安石的天道与人道是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说的,就它们是具体之道来说,它们是有差异的。王安石正是通过精此天下之具体之道之理而悟道,强调了万物具体之道的不同,主要是从形下的角度而言,而不是像程颐从形下之道就其形而上的根源是相同而言。显然,王安石重视从事物的差异性来认识它们,与程颐从事物都要受到天理的制约从而获得我们在修养上要保持一种“敬”的启发侧重点不同。而王安石从万物之道的差异性上,表明了要对万物有等而视之的态度。因此,王安石既重视性理,也重视事物之理,而这一点是为其事功提供内在的根据的,这也与程颐轻视事功的态度不同。
王安石将道之序与器与时之序不同的思想用到了对九畴关系的阐述之中。在阐述九畴之间的关系时,安石说道:“九畴以五行为初,而水之于五行,貌之于五事,食之于八政,岁之于五纪,正直之于三德,寿、凶短折之于五福、六极,不可以为初故也……人君之于五行,以五事修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纪协其数,以皇极建其常,以三德治其变,以稽疑考其难知,以庶证证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征,各得其序,则五行固已得其序矣。”[2]1019
王安石阐明九畴之间的关系的思想,只要将其与《老子》联系起来探究就一清二楚。王安石在《老子》一文中说道:“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2]1083将《老子》与《洪范传》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五行生成万物相当于无为,从五事到庶征七畴相当于有为。无为与有为的相辅相成才能成就万物之用,这时它们才各自得其序。因此,无为产生万物还不能得其序,还必须有人道的有为在无为的基础上成就万物,无为才得其序。所以,无为得其序是从成就万物而言,不只是从产生万物而言。因此,无为得其序是有赖于人道的有为。只有有为得其序,无为才得其序。当然,有为得其序也是在无为的基础之上得其序的,所以有为与无为得其序是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的。
同样如此,在《洪范传》中,王安石也是用此种思想看待五行与七畴之间的关系。他说:“九畴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纪、三德、五福、六极,特以一二数之,何也?九畴以五行为初,而水之于五行,貌之于五事,食之于八政,岁之于五纪,正直之于三德,寿、凶短折之于五福、六极,不可以为初故也。”[2]1019可见,从成就万物来说,五行与七畴是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的;从先后次序上来说,是先有五行,后有七畴,五行包括七畴等所有人道的基础。所以,王安石说只有七畴得其序,五行才得其序。他说:“或曰:‘箕子之所次,自五行至于庶证,而今独曰自五事至于庶证,各得其序,则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于庶证,各爽其序,则六极之所集,何也?’曰:人君之于五行也,以五事修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纪协其数,以皇极建其常,以三德治其变,以稽疑考其难知,以庶证证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证,各得其序,则五行固已得其序矣。”[2]1019
从宇宙论的角度讲,七畴得其序则成就了万物,因而五行也得其序。而从本体论的角度上讲,七畴得其序,是形下之道得其序,那么形下之道得以实现,因而形上之道也就体现了出来。
结语
由于受到《洪范传》主要是讲治国大法内容的限制,王安石在此也只能阐述治国方面的形下之道。但是在道之体与用的关系上,王安石很显然又不局限于此,而是认为道之体与形下的所有道之用都是一致的。形下具体之道得其序,则五行也就得其序。而如果顿悟道之体以后自然就能认识到道之用,就自然能无思而得。于是,本体之道与具体之道就成了一种互相通达的关系,王安石正是以此思想作为指导而形成了《洪范传》的思想架构。这种架构不仅重视了七畴等人道的有为,也强调了遵循天道五行的无为和本体论意义上的道本体。具体之道与道本体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因而就从根源上保证了对七畴等具体之道把握的正确性。
注释:
①在《洪范传》中,王安石对“五行”一畴的阐述实际上包含了阴阳与五行,因万物的产生不仅与五行有关,也与阴阳有关,即“道立于两,成于三,变于五”。本文为了论述的简洁,有的地方只是提到了五行。
②《四库全书总目·术数类》中说道:“术数之兴, 多在秦汉以后, 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 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物生有数,象生有数,乘除推阐, 务究造化之源兴, 是为数学。星土云物, 见于经典, 流传妖妄, 寝失其真, 然不可谓古无其说, 是为占候, 自是以外, 末流猬杂, 不可殚名, 《史》《志》总概以五行。”
③安石说道:“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参见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2页。
④王安石认为顿悟(悟道)是通过养气进而养心来达到的。他在《洪范传》中认为养心可以达到顿悟的程度。王安石说道:“孔子斋必变食,致养其气体,所以致精明之至也;夫然后可以交神明矣。”(参见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三)——周礼(上)》,国立编译馆1987年版,第85页。)在《礼乐论》中,他也说道:“心生于气。”(参见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3页。)
⑤王安石针对《周礼·天官》“王齐日三举”,写道:“孔子斋必变食者,致养其体气也,王斋日三举则与变食同意……盖不以哀乐欲恶贰其心,又可以去物之昏愦其意志者,而致养其气体焉;则所以致精明之至也,夫然后可以交神明矣。然此特祭祀之斋,尚未及夫心斋也,所谓心斋则圣人以神明其德者是也,故其哀乐欲恶,将简之弗得,尚何物之能累哉?虽然,知致一于祭祀之斋,则其于心斋也,亦庶几焉。”(参见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三)——周礼(上)》,国立编译馆1987年版,第85页)我们可以以“不以哀乐欲恶贰其心”以至可以致精明之至,然后交神明之德的方法而直接顿悟大道。而心斋的修养方法之区别是可以不用进行祭祀之斋的养气而能直接神明其德,通达大道。在此处,王安石祭祀之斋的修养方法是采用一种与外界暂时隔绝的方法,即使在饮食上也有特别的限制,以此来养气,而养气就可以交神明而悟道。总而言之,是通过养气来悟道。在《礼乐论》中,王安石也是以此种方法来悟道。而从心斋来看,神对应于道,而圣人对应于德,圣人可以在道上是神,而能明其德,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意思,这在《大人论》中说得很清楚。心斋通常是圣人采用的方法,就是说已经悟道之圣人就能采用心斋的修养方法,而我们普通的人只能采用祭祀之斋,但从能最终悟道来看,与心斋亦庶几可近矣。祭祀之斋的修养方法对于悟道来说是一种直接体悟大道的方法,这也可以尽性,可见我们只要有一般的领悟形下之道的经验,然后通过心斋的修养方法就可以直接顿悟大道,这可以说是直接悟道了,而不是通过形下的无数的具体之道的积累而悟道。
参考文献:
[1] 郑涵.北宋《洪范》学简论[J].中州学刊,1981(2).
[2] 李之亮.王荆公文集笺注[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
[3] (清)孙之騄辑.尚书大传[M].四库全书本.
[4] (唐)王冰次注.黄帝内经素问[M].四库全书本.
[5] (战国)扁鹊.黄帝八十一难经[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6] (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7] 胡金旺.论王安石与苏轼孟学思想之差异[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12(3).
[8] (宋)王安石著.容肇祖辑.王安石老子注辑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