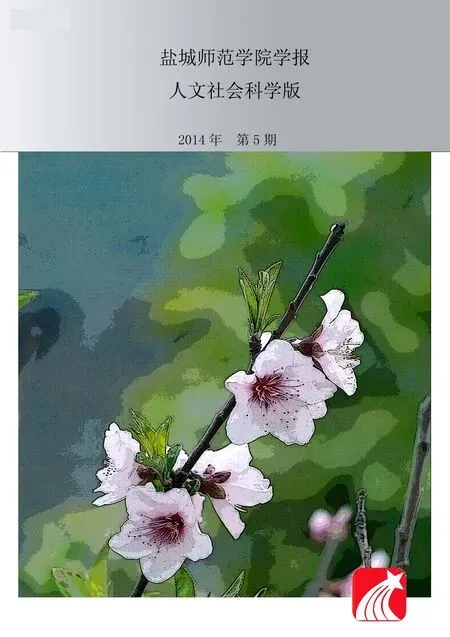坚守 多元 超越:新世纪江苏文学创作形态论
——以“紫金山文学奖”为考察中心*
2014-03-12孙晓东
孙晓东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支流,江苏作家群凭借对现实敏锐而大胆的把握,对人的精神深处透彻的挖掘,对当代复杂而又多彩的生活的展现,成为了当今文坛公认的一支文学劲旅。据江苏省作家协会不完全统计,新世纪其共创作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翻译等5600余部(集),创作或改编电视剧、电影50多部,不少作品发表后产生较大反响。在亚洲文学奖及国内诸多期刊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排行榜等许多有影响并被广泛认可的奖项和排行榜中,赵本夫、苏童、毕飞宇、范小青、储福金、鲁敏等江苏作家都是榜上有名,他们以斐然的成绩跻身于文学前沿。
1999年,为全面展示江苏文学各门类创作成果,彰显文学价值,明确文学标准,推介优秀作品,引导文学消费和参与文学经典化,江苏省作家协会适时设立紫金山文学奖,并于2000年举办首届评奖活动。这是江苏省最具权威的文学大奖,也是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省级文学奖之一,迄今已连续举办了四届评奖活动,设有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等多个奖项,其中文学创作奖共评出长篇小说22部、中篇小说20部、短篇小说26部、散文20部、诗歌16部、儿童文学18部、报告文学20部,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江苏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尽管在大陆,文学评奖问题一直饱受争议,甚至有学者将之称为是“文学奖是组织者、评委和获奖者的一次‘自助餐’”[1]。但就目前大陆地区而言,文学评奖正以“一种肯定的、鼓励的积极性方式代替了以往的否定的、惩罚的消极方式”,“实现着文化领导权从个别人手中开始转向对大众的民主化诉求,从而在政治意识形态退隐时刻在民主化的维度中确立自身的合法性,以及在大众和专家双重评价视野下的科学性追求中重新建构自身权威性”[2]。作为连续性的区域综合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对于江苏作家创作的激励,得到了国内文学界的认可,成了江苏文学事业繁荣的见证,被称之为江苏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因而,我们这里试图以紫金山文学奖为考察中心,以紫金山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依据,窥斑见豹,对江苏新世纪文学创作形态作一粗浅勾勒与描述,也就显得可能而且恰当。
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坚守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一个异彩纷呈的时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等文学思潮及“底层写作”、“欲望写作”等各种流派写作是“你方登罢我登场”,喧嚣一时,而与之相随的却是文学经典的远离。在传统媒介及网络等多种媒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一方面使得个人化写作得到了极大的张扬,文学作品得到极大丰富,另一方面却又使得写作者和读者对文学经典认识陷入到一种现代性的焦虑之中。进入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在抛出一个个热点问题炒作吸引读者眼球的同时,依然难以摆脱日益边缘化的尴尬境地。2007年新浪读书频道携手贝塔斯曼书友会评选出的“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中,当代通俗文学作家就占了三成多,其中包括10多名网络作家。而那些能带来心灵感动或思想感召力,关注民生,反映社会变革时代的历史镜像意义,具有深厚涵盖力与包容性以及丰富的审美表现力的文学作品,逐步远离了现代社会的“阅读中心”。
反观新世纪江苏文学,从苏童、毕飞宇、周梅森、赵本夫、范小青、叶兆言、黄蓓佳、赵恺、储福金、朱苏进,到韩东、罗望子、荆歌、朱辉、夏坚勇、朱文颖、叶弥,及更年轻的鲁敏、庞余亮、庞培等,虽然他们之中存在着个性差异和文学理想的不同,但他们始终能沉潜于生活,努力把笔触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触摸历史和现实的前进步伐,感受改革浪潮的新鲜讯息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变迁,以真实感人的艺术描写、富于时代特征的典型性格和人物形象,创造出新时代的史诗,体现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可贵坚守。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的背景下,以高中毕业回乡的“愣头青”端方充满梦想与幻灭、挣扎与奋斗的独特心路历程为主线,辅之以端方、地主女儿三丫、知青支书吴蔓玲的爱情纠葛,写出了现实与历史的荒谬,刻划了人性与欲望的惨烈:高中毕业回王家庄的端方以他的勇猛和智慧,树立了他在王家庄的地位,赢得了地主女儿三丫的爱情,但闲言碎语很快压垮了这个脆弱的爱情之火,三丫最后选择了死亡。而此时大队女支书吴蔓玲却不可抑制地爱上了端方,端方身上独特的男人气息,重新激活了她这个几乎没有性别意识的政治动物身上的女性情愫,但是,端方只想利用吴蔓玲的权力去参军以离开王家庄。作家以一种近乎放肆狂欢的笔调,书写上世纪七十年代苏北农村的经验与记忆及时代的大喜大悲,带着洞悉历史的力量和高度,对历史肌体中隐藏的创痛进行了带血的切割。如果说毕飞宇是以一种回溯的笔法重现逝去现实的话,徐风的《浮沉之路》则是一部当代版的准官场小说。主人公田萌生本是草根一族,好不容易混成个芝麻小吏,可他偏偏又想往上爬一爬。殊不知他面对的是一张权势和良知、利欲和尊严、农村和城市交织起来的错综复杂的网,他纵然在里面左冲右突,终究难逃悲剧命运。作者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今中国官场及社会之种种怪现象的同时,将人性这一永恒母题贯穿于作品的始终,“以犀利的笔锋和激烈的冲突,揭示了人性本端的压抑和沉重,和西西弗一样,遍体都是苦苦寻觅的身不由己和欲罢不能,奔跑的伤口分明流淌着力不从心的悲哀”[3]。冯亦同的第三届紫金山文学奖获奖诗集《紫金花》的题名诗作《紫金花》,取材于1937年底日军的南京大屠杀,真实地还原出炮火肆虐的场景,抒写了劫波度尽之后对于这场深重灾难的追忆、铭记和痛定思痛的振发。诗人以花为媒,通过一种不知名的小花在焦土废墟间怒放,并因此表现而震撼和教育了一位日本军医,使之成为反战人士。在诗中,诗人始终无法忘怀于对社会现实的吟诵和讽喻,凝重又激昂的感叹使诗歌对于世道人心的风化作用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吟唱相得益彰,充分表现了一个投身社会正义的诗人公民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和生活热忱。
二、审美品格的多元化
江苏文学一向注重艺术上的创新和探索,这或许得益于江苏文人对“形式”方面追求的迷恋和江南文人的“形式主义”特长,因为我们考察“20世纪以来的江苏文学,尽管江苏在文化区上不能定于统一,但文学的南倾是很明显的”[4]。人们对与江苏文学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江南的文化记忆,精致、唯美、忧伤,灯红酒绿、笙歌处处”[5],而正是这种文化间细微的分歧和异质,甚或是文化间细微的差异,影响和形成了多元化的江苏文学审美内涵的叙事风貌。
新世纪以来,江苏作家在承继上世纪老一辈作家文学传统的同时,力求用现代的审美意识去打量过往的历史和现实的生活。在多维的时空架构中,融入自己对动态的矛盾过程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把握以,以对生活的多向度、多侧面的思考,创造出具有艺术审美经验和创作风格的作品。第二届紫金山文学奖获奖作品庞瑞垠的长篇小说《秦淮世家》,凭借新历史主义创作态度,以三部曲的形式和一种史诗般追求的气度,通过对谢、尹、邹三个家庭命运的描摹,以逾百万字的篇幅,写出了中国的百年沧桑,展示了广阔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我”眼中的历史,突破了一般历史小说对历史史实“形”似的拘泥而转入到一种“神”似巨大的空间。苏童以对自己时代记忆的整合,写作的长篇小说《河岸》充满了神秘与伤感,困苦与无奈。主人公库文轩是烈士之子,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动荡年代里,有人揭露其烈属身份的虚假,有人揭发他作风不正,甚至有人还怀疑其身上的鱼形胎记。为了能让离开河岸的父亲与奶奶的纪念碑永远在一起,库文轩的儿子库东亮把奶奶——烈士邓少香——的碑背到了船上,引来了岸上人们声势浩大的讨伐,最后库文轩背起母亲的纪念碑投河自尽。小说所展示的“童年的视角,成长的主题,残酷的青春,历史的浮沉,河与岸的象征,意象包裹的语言”,构成了苏童小说诗性元素的一次完美组合[5]。黄蓓佳的小说《所有的》一反传统家族小说“差序格局”的叙述框架,抛却第一人称带来的叙述便利,借双胞胎姐妹中艾晚的叙述口吻,以姐妹俩成长经历和爱恨情仇为主线,穿行于回忆与现实之间,书写了两个年轻女孩彼此间的争执与伤害、温暖与友爱,以细腻的笔触去探究人性的丰富与深厚,写出了“人性的不同侧面的偏至”[6],道出了人世间“所有的的秘密,所有的哀伤,所有的背叛,所有的救赎,所有的无奈,所有无法掌控的变异,当然,也包括所有的来自生命本源的快乐”[7]。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以日常性的叙事风格,隐去政治的背景,不写文革,不写粉碎四人帮等,不写知青,不写下放干部,只写“在万泉和眼睛里看到的事情和他听到的事情(少数)”[8],进而对人、社会与疾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生存状况与制度文化进行了反思。赵本夫的长篇小说《无土时代》以带有点悬疑小说色彩的笔触,描写了一群生活在城市里却怀念乡村,与城市格格不入的怪人,他们变着法儿与城市对抗,上演了一出出人间悲喜剧,形象地讲述了现代性的两面性。袁杰的诗集《夜曲》钟情于文本艺术技巧与思想深度的打造以及多种艺术可能性的寻找,充溢着一种风格集大成后的创新自信,洋溢着浓厚的中西文化元素。其中的诗剧《J和上帝》直接取材于《圣经·旧约》,通过对古希伯莱史的诗性重写,表达诗人对于“J和上帝”及其使者的崇仰之情。徐风的紫砂文化散文《一壶乾坤》中的历史、文化和智性使它不同于其他散文,也有别于一般传记的史传文学。作者以人及史,从文化历史的画卷中展示文化人格的深度,是一部紫砂艺术家的系列传记和一部中国紫砂艺术史的完美结合。
三、乡土文学的新超越
江苏文学有着天然的对江南文化的自恋和倚重,这种自恋和倚重影响并形成了江苏乡土作家特有的创作思维和地域化美学风貌,并“实指性”地呈现于他们笔下的文学世界中,构筑起他们一个个独特的审美地域空间。“乡土性”成了“不同地域文化和文学形态对话的根本性前提和基石”[9],其特有的地域文化因子和审美艺术风貌也因此成了一些作家的显著性的标识。陆文夫“苏州情结”下的一幅幅苏州地域风情画,艾煊笔下最具江苏地域特色的水、船,范小青作品中的古城苏州的风貌及至后来朱文颖《浮生》《水姻缘》等作品中呈现出来的苏州“水乡之气”等都显示地域风物在地域文学中的一种“实指性”存在。
随着文学多元化时代的到来,这种江南文化一元主导的的乡土文学结构变得不再稳固,“地域这一概念应该是不再重要或必须超越的了,我们即使选择一个发生在特定地域里的故事来描述,或者直接告诉我们作为现在人的复杂而骚乱的内心,这一切后面也应该有一双打量整个人类的眼睛,有一种面临世界文化趣同的状态,在各种纷至踏来的文化潮流中稳舵前行的勇气”[10]。而这种打破和超越首先来自于赵本夫这个从徐州起家的作家,他以一个外乡人身份闯入江苏乡土文学世界,他不满于江南文化的过分精致和纯净,渴望一种野性和苍茫,在他构筑的文学世界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与北方文化亲和的一面,他笔下人物谱系大多具有一种豪侠之气,包括女人,如他的长篇小说《刀客和女人》。地域风情不再仅仅是一个实指性存在,而是成了小说叙事语境和结构性情节的一个虚拟的符号。而在新世纪一些新进作家那里,这样的超越变得更为直接,他们一方面承继着江苏乡土文学书写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在他们的文学世界里对地域风物进行“移位”,使之成为营造作品艺术格调的一种外在表征,将其作为虚构的叙事背景和服务于叙事表达功能的意象而存在,地域性的审美内涵因此也被演绎成了一种文学精神和气质。苏童的小说《河岸》中充斥着的水乡意象的叙述,不仅带有一种水乡阴郁的意境和质感,而且这些草、树、鸟、人等都在苏童笔下转化为叙事的功能具象,成为苏童小说诗性气质元素的美学符号。一如莫言的“高密乡”、贾平凹的“清风街”、阎连科的“耙耧山”、李锐的“吕梁山”、韩少功的“马桥”,“东坝”是江苏70后作家鲁敏为自己找的文学“故乡”。在这个文学原乡的小镇上,苏北平原上的半实半虚的小镇已经幻化为作者自身成长记忆与故土经验。在获第三届紫金山文学奖的“东坝”系列小说之一《逝者的恩泽》中,这个苏北小镇东坝的冬季景象不再是纯粹的地域标识,而是成了故事发生叙事背景和情节展开的铺垫,在“路边铺着枯黄的小草,树枝杂乱地伸向天空,街面的店铺们覆盖着一整年的厚厚灰尘”的冬季,一个从新疆来的女子古丽,带着孩子到了东坝并在这“呈现出黯淡的色调,触目所见,了无生趣”的苏北沿海小镇而开始了“两女一夫”世俗生活:去西北打工的陈寅冬,将妻女俩留在了家乡东坝小镇。但他在西北又找了一个女人过日子,当他因意外逝去以后,女人古丽带着儿子来到东坝找到他的遗孀红嫂。这里的“东坝”是沉默寡言的,飘渺又切实,虚幻又真切,在那片土地上,不仅“有着狡黠、认命亦不乏趣味的人们,有着静海深流的情感与故事”,同时也有着“小谎言,小伤感,小爱情以及小小而珍贵的‘善’”[11]。作家无意于描摹其地域风物和世俗风情,而更多地以情感、经验、感性的注入来实现其对历史、现实的认知,让善与美在这个小镇上交相辉映,和谐共生。
四、结语
如今,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一个个断裂的年代而进了新的时代。新世纪的文学虽已走出了20世纪那种启蒙的精神现代性和革命的政治现代性挂帅的时代,但文学面临市场经济以及文学边缘化的压力依然严峻,网络的盛行,传媒的介入,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推动着非精英化的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的出现,挤压着文学发展的空间。在此情境之下,江苏文学所显示出来的“文学苏军”精神品貌显得难能可贵,江苏作家也因其阵容强大,成绩斐然而为文坛所瞩目,这或许是江苏作家的勤奋精进的禀赋使然,但同时也与江苏近年来营造的良好文学创作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在文化强省的方针下,江苏省实施了文学创作与评论工程,实行面向省内外青年业余作家签约制,增加对优秀作品扶持及宣传研讨力度,举办多种形式的作家讲习班,加深了作家之间、作家协会和基层作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深入的交流。作家的个性化、多样化得到了极好的尊重,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梯队良好的作家队伍。我们通过对紫金山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检视,不难发现江苏作家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坚守和乡土文学学创作的超越及审美风格的多样化追求,使之成为了当今文坛上一支不可小觑的文学力量。紫金山文学奖设立的举措可谓是适逢其时,但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充分尊重自己的心灵自由,重建人的现代生活感性,拒绝为获奖而写作,或许才是文学生命的所在。
【参考文献】
[1] 王彬彬.文学奖与“自助餐”[N].文学报,2004-11-25.
[2] 张丽军.文学评机制改革与新时期文学[J].小说评论,2011(6):4-8.
[3] 张田田.读徐风《浮沉之路》[N].新民晚报,2004-09-28.
[4] 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5.
[5] 汪政,晓华.江苏文学风格散论[J].山花,2008(12):136-148.
[6] 朱晓进.细节所蕴含的文化况味——黄蓓佳小说《所有的》和《家人们》的艺术境界[J].当代作家评论,2012(6):100-104.
[7] 黄蓓佳.所有的[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封底.
[8] 范小青,汪政.灯火阑珊处——与《赤脚医生万泉和》有关与无关的对话[J].西部,2007(5):93-111.
[9] 端传妹,金春平.论新时期江苏地域小说的审美生成[J].当代文坛,2011(4):48-51.
[10] 董小玉,娄吉海.家园的篱笆:从地域分区看文坛的“四个作家群”[J].文艺评论,1998(4):35-41.
[11] 鲁敏.我是东坝的孩子[N].文艺报,2007-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