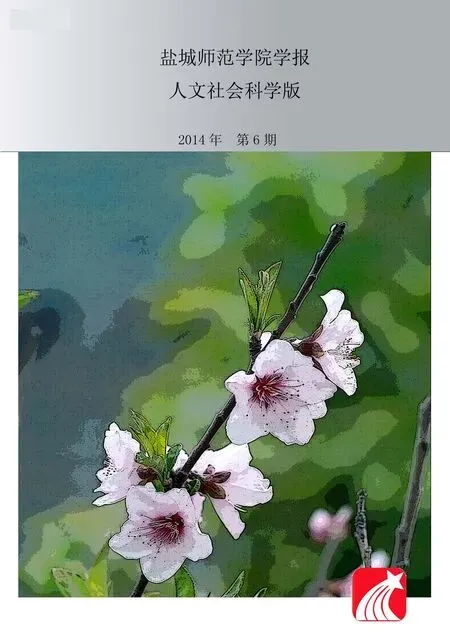论淮剧文化品格的缺失*
2014-03-12孙晓东
孙晓东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淮剧是散落在江淮平原上一颗璀璨夺目的珍珠,具有鲜明的苏北盐淮、盐阜地区特色,并在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了朴实醇厚、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1]。淮剧从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一跃成为江苏省代表剧种之一,活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的淮剧艺人也纷纷走出国门,登上世界的舞台[2]。但随着时光的推移,淮剧历经了昔日的辉煌之后也和我国其他地方戏曲一样面临困境,被纳入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淮剧专业团体从鼎盛时期的30多个,缩减到现在的13个。近年来,为了保护淮剧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和有关部门以及许多热爱淮剧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淮剧依然难以摆脱日渐式微的窘境。究其原因,人们常常将此归咎于市场经济等外部原因的冲击。事实上,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形态的载体,淮剧在二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努力形成自身特色的同时,文化品格的某些缺失也是其发展掣肘的不容忽视的原因。
一、淮剧审美内驱力不足
农耕文化是孕育淮剧的摇篮。淮剧从简陋原始表演粗糙的“三可子”“江北戏”,一直发展到体制成熟的淮剧,其起源与发展一直与农耕文化关系密切,不仅其内部的概念,其外部表现也是努力满足农民、农村和农业的需求。
首先淮剧的基本曲调是由苏北里下河一带农村中的民谣小调、劳动号子发展起来的,随后受到具有宗教戏剧活动性质的“香火戏”及徽班东进的影响,在门叹词的基础上形成初具规模的原始戏剧状态——“三可子”戏,后来在清同治年间,大批里下河徽班的艺人投靠到淮剧阵营,“三可子”艺人全面引进徽剧艺术,淮剧于是过渡到“徽夹可”时期的“江北小戏”阶段。清末民初,苏北水灾不断,“江北小戏”艺人随难民一起逃难到上海,他们在广泛吸收其他姐妹剧种的艺术营养,特别是南派京剧,淮剧遂又过渡到“京夹淮”时期的“江淮小戏”阶段。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成为戏剧品格比较完善的剧种。其次,淮剧的早期艺人大多都是做“僮子”、唱“香火戏”出身,他们在农闲时唱“香火会”,农忙时务农,具有半农半艺的性质。“门叹词”艺人随后也加入了淮剧行业,但是“门叹词”最初只是一种为了方便乞讨、博取同情发展而来的卖唱艺术。后来著名的“徽夹可”“京夹淮”时期淮剧艺人们也大都处于个体状态,社会地位很低,生活没有保障。再次,苏北盐阜两淮一带古称“淮夷”,从事农耕和煮海烧盐是这里先民们主要的生产活动方式,因此盐淮地区的城镇化步伐非常缓慢,商业文明低下,市民阶层无法产生,淮剧最初面对的观众只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
从起源上看,淮剧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深受农耕文化的浸染,与底层大众血肉相连,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具有质朴自然、不矫揉造作的表演风格,但农耕文化中的安土重迁,自给自足,自我满足,封闭保守等带来文化创新动力不足也显而易见,早期淮剧艺人们从艺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一种精神追求和审美创造,而是将它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观众也仅将其作为辛苦劳作之后愉悦感官的工具,而并非是以艺术欣赏者的身份去品味,这样一种对淮剧低标准的要求也使得淮剧形制与其他戏曲相比略显粗糙,更接近生活的原生态,缺乏一种文化生长发育的内部驱动力,致使淮剧剧目缺乏创新,唱腔拖沓,长期以来“九莲”“十三英”“七十二记”等传统剧目始终占据主角,艺术形式相对粗放陈旧,难以争取到青少年观众。
二、悲剧品格的缺失与淮剧审美震撼力的不足
与其他地方戏种相比,淮剧尤其擅长演悲剧,创设以“淮悲调”“大悲调”等为代表的擅长表演悲苦情怀,传达哀怨情结的曲调,创立了在“九莲”“十三英”“七十二记”等传统剧目中占主流的悲苦戏。这一方面由于早期淮剧艺人多是贫苦出生,对人世间种种的不公与悲苦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从而将自己的悲苦之情寄予淮剧;另一方面还与历史上淮剧发源地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从自然环境来看,日光充足,四季分明的江淮地区本来应该是农业发达的鱼米之乡。但历史上却经常受到自然灾害的侵扰,主要的自然灾害有洪涝、旱、台风等。每当淮河泛滥,海水倒灌之后,当地农民辛苦劳作一年的庄稼颗粒无收,煮海烧盐的劳动成果付之东流。灾害过后,大片农田因盐碱化而无法耕作,饥荒,瘟疫接踵而来。从社会环境来看,盐淮地处南北要道,每当战乱,这里必定首当其冲,百姓多受荼毒。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了淮剧忧郁型的艺术气质,表现了民众内心深处的伤痛,悲愤与无奈。
淮剧的很多苦情戏多表现为伦理冲突,即善与恶、忠与奸等两种对立的伦理道德力量的冲突,虽然在冲突中也表现为具体的实体,但冲突的双方实际上各自体现了两种对立的伦理道德观念,冲突的起因缘于恶对善的欺凌,冲突的结果是善最终战胜恶,从而使人们得到是非善恶的伦理道德教育[3]。而其中造成冲突的道德伦理力量有时候并不是悲剧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例如像“孝”“忠”之类的义务和责任,这就造成悲剧冲突个人化色彩减弱,社会化色彩变浓,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冲突的悲剧性。他们同时也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表现恶对善的压迫,以伦理否定的方式表现善对恶的反抗,这种冲突的构成和进行方式也大大弱化了冲突的悲剧性和尖锐程度。最后在情节结局上,无论之前的剧情多么凄苦曲折,最终都要尽力达到完满。有的即使在现实的世界里无法改变其悲剧的结局了,也要像《长生殿》里面的唐明皇和杨贵妃一样在超现实的世界里使其得以圆满的结局。
因此,淮剧所擅长的悲情大部分还停留在苦情戏的层面,没有上升到美学意义的审美层面,缺乏一种西方悲剧的崇高,缺乏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美。悲剧的主要美学风格是崇高,悲剧能够唤起人们心中的崇高感,使人们震惊、激动,感叹人的伟大、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本质。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及崇敬,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有震撼力的悲剧往往悲剧性成分较多,并以个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对抗作为悲剧性冲突的主题,而且这种冲突带有浓烈色彩的个人性并且不可避免,不容退避,冲突非常尖锐、激烈,后果直接导致悲剧主体的不幸与困难。在情节结构上,它们也往往是一悲到底的直线型,悲剧情感贯穿全剧的始终,绝对不允许诙谐等喜剧因素的混杂和穿插。它们的结局也往往是主人公遭受巨大的不幸和灾难,这使得它们始终笼罩在浓重的痛苦和死亡的阴影中,是“人生中可怕的事物”[4]。而淮剧的很多苦情戏缺乏这种悲剧震撼力,虽然诉说的是遭遇的不幸,表达一种悲苦的感情,但并未能让大多数观众在对这种悲苦一撒同情泪水的同时对人物的悲剧命运和剧中的悲苦情节做深层次的探讨,而仅仅将他们局限在生活表象的层面和宿命论的框架之中,戏中抒情性特征也使它侧重于在戏剧冲突中表现人物的内在情感,而不注重表现冲突的外在的现实行为,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冲突的尖锐激烈程度。这样的审美层次已经不适合现代人的娱乐心理并且缺乏当下消费市场中洋溢的游戏精神和娱乐意识,不能满足现代观众越来越挑剔的审美情趣要求,只会让他们陷入了一种审美疲劳状态,从而削弱了淮剧的悲剧审美震撼力。
三、民间生存与淮剧的文化传播力局限
淮剧是“草根艺术”,一直以来都扎根在民间土壤并且在人民大众的呵护下不断发展,民间活动一直贯穿于淮剧的发展历程中。上文提到淮剧产生于盐淮地区,而这片区域商业经济落后,一直没有产生真正的市民阶级,很少有文人雅士直接参与戏曲的创作,更没有出现有影响的文人群体和人文精神。淮剧早期的许多专业演员大都是农民、小生产者和城市贫民,他们走上淮剧的艺术道路大都是生活所迫,业余的爱好加上自身的天赋。不光许多专业演员来自民间,许多江淮民众出于对淮剧的热爱自发组织了广泛的民间业余班社,据1945年春统计,盐阜地区就有500多个农村剧团,团员达9000余人。可见淮剧业余艺术队伍有着深厚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淮剧民间色彩浓烈的特点。淮剧一直以来都表现了苏北地区特有的乡情乡音,展现江淮地区的地方面貌和风土人情,所选取的题材也是和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如和淮剧有着极深渊源的“门叹词”讲的大都是唱者自身的不幸遭遇和坎坷经历,在发展中形成的淮剧剧目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源于江淮地区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例如《关公辞曹》、《孝灯记》等;二是表现百姓实际生活,表达农民情感的现代戏,例如《种大麦》《鸡毛蒜皮》等。总之无论是传统剧目还是现代新编作品,淮剧的题材都承载着盐淮地区百姓生活不同层面的面貌、民众精神、历史文化信息及社会心理。淮剧的唱词和念白也都体现江淮地区的特色,首先是采用本地口语,例如在剧中常见“爬上头”“死纠活缠”等江淮口语,十分具有乡土风味。二是在唱词中使用当地的民歌,例如在《刘贵成私访》中“叮叮当,开古道,得得得,不招摇,小毛驴,满街跑,驮着我,刘保朝”。民歌素来多是劳动人民的创造,因此淮剧向民歌汲取营养更加重了淮剧的地方特色。三是唱词通俗易懂。淮剧所表现出来的口语语言,方言俚语等无一不体现其浓浓的草根味。这种民间性生存特征固然造就了淮剧的独特性,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发达,常态的人口流动使得空间不再封闭,同一个城市、同一个社区甚至同一个居民小区都会存在各种不同的方言。如果淮剧仍然以江淮方言为其演出语言,那么,即使是在江淮地区内部它也会被很多人放弃,难以扩大观众群体,影响淮剧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更不利于淮剧走出江淮,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
淮剧与我国其它地方性剧种一样,面临着传承、发展与保护的考量和问题,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努力营造适合淮剧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还需正视淮剧自身文化品格的缺失,增强其文化创新的活力,摆脱苍白的说教和道德伦理感化,用现代的眼光去探索人物命运背后的奥秘与哲理,提升其悲剧审美文化内涵与品性。与此同时,借用影视,魔幻等现代艺术品种的元素与淮剧固有的艺术手法相融合,在舞台灯光、戏曲音乐、人物服装、舞台道具等方面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借助新的媒体力量来进行淮剧的推送,拓展其传播空间,使其真正成为大众的文化盛宴,唯其如此,振兴淮剧才不致于沦为空话。
【参考文献】
[1] 孙晓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淮剧文化[J].中华文化论坛,2013(1):138-142.
[2] 梁伟平.淮剧在美国[J].上海戏剧,2009(6):14-16.
[3] 李秀敏.论中国古代戏曲的反悲剧倾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5):64-69.
[4]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