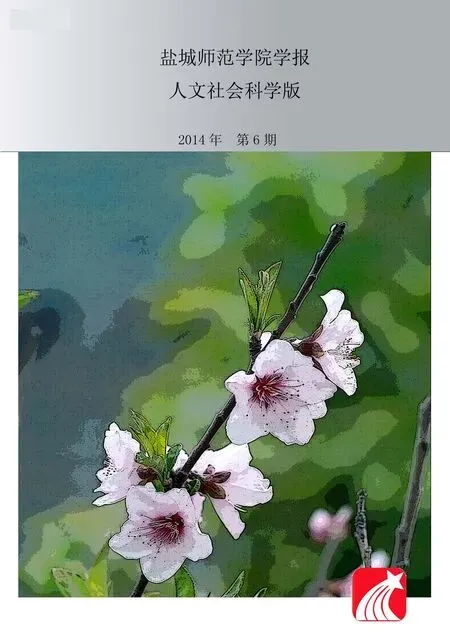福建家族书院论考*
2014-03-12牛丽彦金银珍
牛丽彦,金银珍
(武夷学院 艺术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最早的闽北书院,当属建阳的鳌峰书院。鳌峰书院“在县西崇泰里熊坉,唐兵部尚书熊秘建”[1]。当时,熊秘之所以建此书院,其目的乃“为子孙肄业之所”,也就是为其儿孙弄一处求学之地,实属私塾性质。熊秘的初衷,也正是我们的先贤们创办大大小小书院的目的之一。从这样的私塾性质逐步发展成为有规模的书院,是名正言顺的“家族书院”,是本文考察之对象。始初并非是私塾性质,或是讲学之所、或是读书之处,而后靠其后裔发展成为书院的,也是本文所论及之对象。
像熊秘的这些先贤,都非常明白治国要先齐家,齐家要先修身的道理。所谓五伦,其出发点正是家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分析五伦的逻辑关系,是从家庭关系外延于国家、社会,而家庭作为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单位牢牢地占据其五项关系之首位。进而言之,“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正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修身齐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为中国家族书院蓬勃兴起和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广阔的土壤。这一点上,闽北的书院也不例外。邵武的和平书院是典型一例。
后唐工部侍郎黄峭弃官归隐,创办书院,主要是为了训诫子弟,修身齐家,黄峭的二十一个儿子,应该是在此书院接受各种教育。现今海内外黄峭后裔众多,又是名家辈出,应与当年黄峭的这种伦理观念有着直接关系。
闽北最早的书院——鳌峰书院的始末,建阳市政府网站是这样介绍:
“鳌峰书院”坐落于建阳市莒口镇焦岚村樟埠,唐兵部尚书熊秘建。熊秘于唐末乾符间任右散骑常侍,领兵入闽守温陵(今泉州),不久就卜居建阳的莒口义宁,后人遂称其居处为熊墩。熊秘定居此处后即兴办家塾,以教子弟。宋初,熊秘后裔熊知至,自号鳌峰先生,隐居此处,遂名家塾为鳌峰书院。北宋熙宁、元丰间,由于家学兴旺,子弟苦读成风,熊墩常出人才,进士及弟,至南宋仍久盛不衰。熊氏子孙在此书院攻读而登进士者,先后共有十三人。宋亡后,熊秘后裔熊禾主持书院并予重修……熊禾逝世后,后人即以此地建祠奉祀之,故又称勿轩先生祠。明永乐初年书院寝废,院址被权势侵占。正统十二年,熊禾六世孙为此申诉上司高某与董某,书院才得以收回修复……鳌峰书院毁于中华民国后期,留下五大圆门与残垣断壁,1976年将遗址改为良田。
鳌峰书院自创办到败落,办办停停、停停办办,前后经历了千余年的时间,大体上具备了如下几个特征:其一,本地士人所设;其二,家族的共同努力;其三,祠祀功能的凸显;其四,官府的介入,而这些特征或多或少也是福建其余书院创办乃至延续其命脉的重要原因所在。
一、福建书院的创办主体——士人
福建家族书院的创办主体,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本地本乡的士人。论其本地本乡,光泽的西山书院,则是光泽县乌洲李氏家族的李郁于宋绍兴年间创办;浦城的叶安节书院则是浦城人叶安节于宋治平四年创办;宋嘉定十四年的西山精舍乃是浦城人真德秀创办;建瓯市的环溪精舍则是朱熹童年随父寓居读书之所;武夷山的叔圭精舍,则是北宋政和五年,武夷山乡贤江贽创办;武夷山的洪源书堂则是建阳人熊禾创办;建阳的廌山书院则是建阳人游酢于北宋绍圣三年所建。再论其士,士者,旧时指读书人也。家族书院的这些创设主体,无论是从官、从民,都是当时当地很有名望的士子无疑。比如,熊秘乃当朝兵部尚书;李郁则是光泽乌洲李氏家族领军人物;叶安节则是宋治平四年进士、后又任县令;真德秀则官至户部尚书、是被称为“小朱子”的南宋著名的朱子学者;江贽乃是以易学著名的隐逸人士;熊禾则是朱熹三传弟子;游酢则是北宋著名理学家;而朱老夫子更不在话下。对这些士者而言,书院是他们传播和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显现其超强文化适应力的一种渠道。
二、家族的共同努力
家族书院之所以能够延续其命脉,主要靠的是该家族祖孙几代、甚至数十代人的共同努力。如鳌峰书院,熊秘所设,只是书院的雏形,是家塾,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院,始无名。“鳌峰书院”之名,实与熊知至的“鳌峰先生”这一雅号有关,并非创设主体——熊秘所为。它通过熊秘、熊知至、熊禾,乃至其世孙们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延续和发展。我们不妨再以“九峰书院”的发展史为例予以说明。九峰书院真正意义上的前身应该是蔡元定之父蔡发的堂舍——“牧堂”。蔡发自号“牧堂”,中年归隐武夷山,买田置地,构筑屋宇,始建“牧堂”。这样“牧堂”成为了其子蔡元定启蒙之所、藏修之处。蔡元定,字季通,建阳人。史载,当他慕朱熹大名归依求教时,“熹叩其学,大惊曰:‘此吾老友,不当在弟子列。’遂与对榻讲论诸经奥义”[1]。蔡元定三子蔡沈,自号“九峰”,在其父去世之后,将这一祖上堂舍加以修缮扩建,名之曰“南山书堂”。其后,蔡沈次子蔡沆又在“南山书堂”的基础上,扩充舍宇、构筑书院,名之曰“咏归精舍”。因内祀其父九峰先生遗像,故又称“九峰书院”。到了明代,蔡沈十世孙蔡珙又将破落不堪的九峰书院复兴。入清后,九峰书院移至崇安,原址废弃。综观九峰书院的整体发展过程,正如清人董天工所言,“斯道在天下,必有托而后传,所谓尧传舜、舜传之禹”[2]。
的确如此,“书院即家塾也,古无是名,至宋始盛”[3],这种“家塾”性质的家族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真正意义上的书院,得力于以士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的持之以恒的支持和投入,而这种支持和投入的支撑点,正是深厚的儒家文化积淀。儒家文化是中国自本自根的文化,其核心内容就是“做君子、讲道德”,而到达“做君子、讲道德”这一最高境界的唯一途径就是读书治学。尤其是在官学不够发达,或是出于种种原因无暇顾及基层社会的年代,像家族书院这样的家族为主力的民间办学机构,是支撑和推动基层社会教育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加上,中国历史上主要是“士”者政府从事社会管理,官吏主要是通过推选,或者是从科举考试中接受了儒家教育的士者中产生。这些家族书院中的一代接一代的士者,不仅是各地家族书院中的“传道、授业、解惑”者,更是担当着维系一方人心、协调基层安定的重任,同时也主持着当地的道义与公正。这些士者其实靠的并不是规矩和说教,靠的是身体力行的示范、是早已制度化了的儒家文化。家族书院始建者们的初衷,尽管是“为子孙肄业之所”,但并不仅限于“为子孙肄业之所”,往往负有行教与祠祀双重使命,并且越是往后,后来居上的祭祀功能越发凸显,甚至“往往被称为祠学”[4]的程度。
三、祠祀功能的凸显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礼记·祭义》)子孙后代祭祀早已作古的先祖,这种“反古复始”的行为,是为了向后人表明宗族的血脉之源。通过对先祖的祭祀,让后人从内心深处产生对本家族的荣誉感和归附感,由此起到强化家族意识的作用。这样,祀贤功能比起传道愈加凸显,一跃而成这些家族书院的第一要义,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家族在书院祭祀先祖的目的,既然是强化家族化意识,具有为本家族的后裔树立精神榜样和行为准则的意味,那么祭祀对象应该既和书院有直接关联,又是值得做这一家族精神和道德上的楷模之人,而后者的比重远比前者大。
位于武夷山的叔圭精舍是崇安学者江贽于宋政和年间创建。其后,江贽之侄江德修扩为淮阳书院。再其后,江贽裔孙江睿在书院旧址建“奉先祠”,祀江贽等先祖。江贽既是以《易》学著名的学者,又是“三聘不起”的高尚的隐士,而江德修乃是恪守父辈遗训,嗜学苦读,官至朝议大夫的江贽之侄。江贽后裔在书院旧址建祠祭拜这两位先祖,真正起到了家族意识的强化作用。江贽无论是学问,还是人品,作为其后人之楷模,是毫不逊色。而江德修尽管没有其叔父有名,但是作为恪守父辈遗训,成名成才之典型也是值得被后人称颂的。加上江贽的书院始建者的身份,成为叔圭精舍的祭祀对象,可谓名正言顺。单纯家族化的叔圭精舍的祭祀对象不同,鳌峰书院的祭祀对象,则富有层次,尊卑有序。
中为传衷堂,以祀熊禾,后为道原堂,祀先圣,而以颜、曾、思、孟四子配。先圣五十一代孙孔元敬书额。左为晦庵师友道义之祠,五夫刘珙书额。右为南昌熊氏忠孝之祠,南昌族子朋来书额。前为三门,匾曰“鳌峰书院”。成化十五年,知县海澄重建二坊于门外,左曰“道学”,右曰“忠孝”。[1]
可见,鳌峰书院供奉的是两种人,一是先祖,二是先圣。我们先看这些被祭祀的先圣们。这里的先圣包括儒家圣祖和理学大师,如孔孟和朱熹等,可谓圣人贤者之尊。祭祀孔子,这是中国古代各类性质学校的传统做法,加上书院的学术性质,也决定了其祭祀对象的性质。书院的祭祀对象应该是立功、立德、立言的大贤大德。书院之所以要祭祀他们,是了尊崇报答他们的功德:是他们恢弘了大道,兴盛了教化,改易了风俗;是他们著述立说,承前前贤,启迪后学。祭祀的目的,正是为了表达后者的思慕之情和敬仰之意,树立真正意义上的行为榜样。鳌峰书院的祭祀空间,有后面的道原堂和中间的传衷堂。我们先看“后”面的“道原堂”。这是供奉先圣之处,鳌峰书院采取以孔子为主,颜、曾、思、孟四子为辅的方式,设置好书院祭祀的中心,然后再把朱熹和家族,各自安排到左右两边。在朱熹和家族的次序安排上,遵从的是左尊右卑的传统观念,左为朱熹、右为家族。再说中间的传衷堂,这里供奉的是熊氏家族先祖——熊禾。这一点上,鳌峰书院不同于叔圭精舍。
叔圭精舍的祭祀对象——江贽,既是著名的学者,又是高尚的隐士,更是该书院的始建者。而鳌峰书院放弃该书院的始建者——熊秘不祀,偏偏单独祭祀熊禾,原因何在?熊秘乃右散骑常侍、兵部尚书,世居洪都南昌樟埠。之后,在鳌峰南麓建私塾以教授子弟,这私塾就是鳌峰书院。至其后裔熊知至,鳌峰书院已有一定规模,传至熊禾,“四方学者云集”,鳌峰书院盛极一时,名传海内。熊氏家学兴旺,子弟苦学成风,历代都有杰出人物脱颖而出。熊秘官至兵部尚书,是鳌峰书院始建者,又是熊氏家族入闽第一人,为熊氏在闽地繁衍生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比起熊禾却少一份资质,那就是理学家的资质。熊禾为宋咸淳十年进士,曾任汀州司户参军。南宋亡后,愤而不仕,隐居武夷山从事讲学和著述,是元代朱子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如前所述,书院的学术性质,决定了其祭祀对象的学者性质。这是各时期理学家成为各级各类书院祭祀的灵魂和核心缘由所在。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朱熹是当代的孔子,是儒家道统在现时代的代表者,那么祭祀朱熹为首的这些理学家,也就是对孔子的礼敬,对儒家道统的尊崇。舍弃熊秘、选择熊禾,可谓有理有节。这样,后面的道原堂和中间的传衷堂,组成祭祀先圣先祖的完整祭祀构图,再与前面的讲堂共同构成秩序井然的书院精神环境,做到既可以强化家族意识,又可以加强学术氛围,不可不是明智之举。
四、官府的介入
福建的家族书院和其他地方的家族书院一样,尽管不是官办学院,但是纵观其整体的发展过程,少不了官府的介入。书院的初始阶段,家族书院是书院的主要源头,相比而言,官府则处于次要的地位,但不可小觑官府在书院发展中的存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皇帝、中央政府、地方官员等,都实质性地影响着家族书院的命运。
在福建的家族书院的发展中,官府的介入,主要是通过这么几种方式去完成的。
(一)赐匾撰记
建阳的西山书院,真德秀于南宋嘉定十四年创建,元延佑初,真德秀裔孙真渊,把城区的故居改为书院,江浙行中书省呈报朝廷,延佑四年四月,朝廷题名为“西山书院”。同样位于建阳的瑞樟书院,宋绍兴间,刘中将先祖卜居之地改建为书院,与其兄刘子翚在书院讲学。嘉熙三年,朝廷颁赐“瑞樟书院”匾,因以为名。建阳的廌山书院,乃游酢于北宋绍圣三年十月创办,南宋嘉熙二年,敕赐“廌山书院”匾。
这种“赐匾”,集中表现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封建社会,对那些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政治规范政绩显著者,政府常常赏匾额加以表彰,称“扁表”。这种匾额,有恩赐、嘉奖、表彰、礼仪、祝贺、命名等多种用途,被历代帝王将相、士大夫乃至民间广泛使用。把它悬挂在显要的位置,有荣宗耀祖的作用。因此,闽北的这些家族书院,有些是获匾得名,有些是获匾显名,充分体现了官府对这些民众的求学之所、官府的养士之场的重视程度。
再说“撰记”。武夷山的留云书屋是武夷山学者董茂勋构筑,乾隆初,董茂勋之子董天工在书屋后增建“望仙楼”,在楼内研读学问,并撰《武夷山志》24卷。清《武夷山志》载,康熙五十四年冬,李光地为此撰写《留云书屋记》。李光地,福建安溪人,当朝文渊阁大学士,是有名的理学家。李光地在《留云书屋记》开篇之处写到:
余以康熙乙未请假南归,道出武夷,有朱子讲学之堂在焉。余意其中必水秀山明,跨越四方名胜,非是则不能聚一时之人豪,着千秋之大业也。[5]
据《留云书屋记》记载,该文是在书院建院第二年,74岁高龄的李光地请假回乡途经武夷山时,应主人之请而为,而李光地也在这次回乡省亲返京后的第二年去世。如今随着岁月的流逝,包括各种书院在内的多少古迹、古人都杳无踪迹,而《留云书屋记》则向后人娓娓道来一曲古人之幽,这也正是撰记人希望所在。
(二)重修改建
光泽县的云岩书院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李方子读书和讲学之所,其遭毁后,被当时县令侯逵复建,这是元天历二年的事。而到至正二年又毁于兵,明宏志时,由其子裔孙李茂继造茅屋奉香火。正德十二年县令钟华改创书院于上云岩。至清顺治五年又毁,康熙十一年县令王吉又捐资重建;乾隆三年又重修一新。
如果说上述的赐匾题名和赠联撰记都是一种精神上的褒奖和鼓励的话,那么这种重修改建则是物质上的支持和关照,尽管这些物质上的支持并不是有计划的,但如果没有这种反反复复的、断断续续的支持,单靠家族的力量来维持,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加上修葺也好、重建也罢,上至皇帝,下至县令,都是显示自己政绩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国泰民安、其乐融融,何乐而不为呢?
(三)赠田发银
与南宋理学家蔡元定有直接关系的九峰书院,自明中叶之后日益颓败破落,遂被荒草淹没。后由蔡元定之子蔡沈和之孙蔡抗先后两次复建。至明代,蔡沈的十世孙蔡珙,又在原址上将其复兴,并拨官田若干,以佐岁时祭祀之需,故先祖之学、圣贤之学得以再传。而这位蔡沈的十世孙蔡珙则是一名训导,训导乃一官名,明清在府、州、县学均置训导,辅助教授、学正、学谕教诲生员。
上述九峰书院的前身——庐峰书院,元初就已经毁损,但由其后裔极力经营;到了明代,被永乐十四年的洪水,冲得堂宇推荡无存,仅余基址。正统十三年,奉礼部令谕,重建庐峰书院。成化十一年,巡按御史尹仁捐俸银一百两重建书院,增建头门、中厅、大殿、左右两厢共五栋,外建庐峰书院砖坊。
从官府介入这一视角而言,这些家族书院既满足了中国士人自身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又整合了传统的官学、私学,可谓系于一个家族、甚至是系一方民心,就官府而论,它们早已成为了不可忽略的文化基地。加上这些家族书院的日益社会化,和日益彰显的不重门户、自由会讲的学术风格,不能不使官府对它们有一个明确的认同,即这些家族书院也是当时讲学精神的滥觞之一。
【参考文献】
[1] 黄仲昭.八闽通志:下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1-16.
[2] 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七[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3]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73.
[4] 徐梓.书院祭祀的意义[J].寻根,2006(2):22-25.
[5] 王瑞兴.李光地题记武夷山“留云书屋”[J].福建档案,2003(2):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