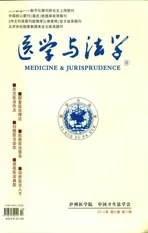生命决定权:安乐死立法不可逾越的法理之“坎”
2014-03-11姚军
姚军
◆理论前沿
生命决定权:安乐死立法不可逾越的法理之“坎”
姚军
在法理上,生命权作为最基本的人权不得代理,立法机关无权对安乐死立法;在我国采用全民公决方式进行安乐死立法也缺乏可行性和正当性。可见,采用正面立法方式设定安乐死制度不可行。
生命决定权;安乐死;立法;正当性
“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作为当今世界所公认的基本人权,在18世纪就从思想家们的理念“步入”了法律文件;它们不仅“与生俱来”“不可剥夺”,[1]而且对之保障和使之实现,是公权力机关(即政权当局)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责。当然,“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三项权利的地位并不相同。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逻辑上,其中的生命权无疑是最基本的权利,是其他两项基本权利的基础与前提:若一个自然人的生命权受到侵害,其其他权利(部分著作人身权除外)安在?!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但丁在其《论世界帝国》一书中认为,(自然人)主体的基本权利,对公、包括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在内的公权力,具有防御性。[2]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则在1958年的“吕特案”判决中宣称:“基本权利主要在于确保个人的自由领域免于遭受公权力的干预;基本权利是人民对抗国家的防御权。”防御权(或防御性)原则,现已被法治(或宣誓“依法治国”的)国家普遍认同,成为“法治”内涵的重要要义。因此,在已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的我国,“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三项权利自然也应具有防御权(或防御性)。
基于上述两个命题(即生命权系基本权利、基本权利具有防御性)的成立,笔者认为,在我国采用正面立法方式设定安乐死制度不可行。
一、安乐死立法属于法律绝对保留的领域
在一个所有自然人都是权利主体(而非权利客体)的现代共和国,任何自然人的生命权均受到国家(公权力)消极或积极的保护。前者是指国家通过立法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利,严格限制或禁止剥夺公民生命权利的行为(在此问题上,外国人因享有国民待遇而被覆盖);除具有合法豁免依据(亦即阻却违法事由),任何侵害公民生命权利的行为都系犯罪。后者则指公权力机关(尤其是政府部门)动用物质性的公共资源去挽救公民生命的行为,如公共机构实施的治疗、防疫和干预自杀等行为。
在当今的中国,任何人都是其生命权的主体,任何人的生命权利都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换言之,侵害任何人生命权的行为均将受到法律的追究。经笔者梳理,在我国,(除对外战争行为以外)损(侵)害他人生命权而又有合法(或称“不违法”)豁免依据(亦即阻却违法事由)的情形仅包括:其一,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判处并执行死刑;其二,基于法定情形而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而致不法侵害者死亡;其三,基于法定情形而实施的紧急避险行为而导致致险人或相关者死亡;其四,自杀行为。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第二、三种情形须完全符合法定情形且未超过必要限度,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第三、四种情形一般不能免除民事责任①。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除第四种情形外,上述其他三种情形均只能法定,而这里的法定的“法”仅指法律。这是因为,涉及公民生命权的褫夺问题如同我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款规定②一样,在法治国家中属于法律(绝对)保留的范畴,我国的其他法源不能、也不应涉及或覆盖该领域,否则违法。
可见,一方面,在制度设计和安排(即立法创制)层面,涉及生死(生命决定权)问题,当属法律绝对保留的领域;且根据(行政)职权法定、越权违反的原则,在我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甚至国务院也压根儿无权进行安乐死“立法”,唯有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来解决此问题才具有形式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在事实操作层面,则不能排除上述第四种自我处分生命权的情形,虽然此种行为不可取。[3]
二、我国立法机关无权对安乐死立法
安乐死立法,旨在将医护人员③通过“安乐”方法提前终结临床上“适格”④的终末期病人生命的行为合法化。问题在于:制定和认可我国法律的国家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否有权对提前终结患者生命的安乐死问题进行立法?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保留死刑的国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刑法》规定,在坚持“少杀慎杀”的前提下,仅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判处并执行死刑;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以外者(即使是临床上“适格”的终末期病人)的生命,立法机关是否有权决定提前终结?
如前所述,作为基本人权之一的生命权对公权力机关具有防御性(即所谓“免于遭受公权力的干预”)。同时,根据法治国家的另一要义——“有限的政府”——的要求:不仅政府要有限,立法机关(及其立法权)也是有限的,不是什么事项均可立法。可见,无辜者的生命权这一具有防御性的基本人权领域,不属于立法机关可自行立法的权限范围。
更为关键的是:作为行使立法职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是否有权代表全国公民(含前文所称的“当事人”)行使其生命决定权呢?换言之,生命权能不能“被代表”呢?假若可以“被代表”,安乐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基本法律,那么,总数不超过3000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就可代表近13.4亿的全国公民⑤并在特定情形下决定其生死(基本人权);安乐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一般法律,那么,100多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就可代表13.4亿的全国公民并决定其生死。这样的结论让人难以想象和无法接受,这种将人的生命权“被代表”而制定的安乐死立法显然是不具有正当性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荷兰、比利时等国的安乐死立法同样存在法理上的瑕疵,缺乏正当性。特别是荷兰已通过的儿童安乐死法案⑥及其实践,有悖于国际所普遍认同的儿童福利原则。不过根据传统国际法尊重他国主权的原则,安乐死立法属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别国不便过多非议和干预。
由此可见,我国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具有对安乐死进行立法的职权。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5年3月-2016年6月烟台市妇幼保健院1 900例孕产妇,其中自愿参与孕产妇保健系统的983例产妇作为观察组,末完全实施孕期保健的孕产妇917例作为对照组,两组孕产妇均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史及神经精神类疾病史和家族史。观察组孕产妇平均年龄(29 .3±3.7)岁,孕次为(1.75±0.53)次,初产妇占65.41%,经产妇占34.59%。对照组孕产妇平均年龄(28.9±4.3)岁,孕次为(1.89±0.59)次,初产妇占62.8%,经产妇占37.2%。
三、在我国采用全民公决方式进行安乐死立法缺乏可行性和正当性
既然生命权不可“被代表”,否则有悖于正义原则的基础性要义;既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进行安乐死立法行不通,那么是否可以采用全民公决的方式进行安乐死立法呢?笔者认为,在我国,采用全民公决方式进行安乐死立法缺乏可行性和正当性。
一方面,采用全民公决方式立法在我国不具有可行性。其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未举行过全民公决,没有进行全民公决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实践经验。其二,我国(大陆地区)人口众多,人口总数达1339724852人⑦,若以总基数60%的人为具有意思能力的成年人计,我国(大陆地区)则有8亿多人具有公决投票资格。如果进行全民公决,无疑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超级举动;而为其专门设立一个全国公决组委会、确定一个统一的公决时间段或收集和统计投票等,都将是困难重重,其成功率实难保证(估计这也是我国难以开展普选的原因;事实上,全国性公决的难度较普选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三,无论是公决还是普选,保障选民的独立和真实意愿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但我国现在尚有大量的不知选票价值何在和缺乏知情能力的投票人。从具有相同原理的我国现有的地方选举和文艺界“海选”的实践来看,不论是采用纸面选票、电视观众短信投票、现场投票,还是采取现代通信方式(如微信、网络等)投票,均无法消除贿选、“被代表”、被强迫以及同一人重复投票(尤其是在采取现代通信技术投票的情况下)等违背独立、真实原则的舞弊现象。值得我们警觉的是,在我国已出现一些专门(通过忽悠、收买、威胁等手段)操纵此类投票的商业性项目承揽公司。在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下,最终可能使公决“走向”采取公决初衷的背面。因此,在我国采用全民公决的方式进行安乐死立法不可行,也不可取。
另一方面,采取全民公决方式进行安乐死立法在法理上也不具有正当性。在参与公决投票的人中有各种年龄段的人,父子、母女、甚至祖孙可能一同投票,这里的选民代际难以划分。即使暂且忽略代际因素,因采用全民公决方式创制且全国适用的“安乐死法”不属于仅适用于特定时间段的狭义特别法(即专适用于特定的主体、特定的区域或特定时间段的法律),其一旦施行不可仅适用于公决的这一代人,对于那些(未参加公决投票)成年变老而适用该“法”的人来说,其神圣的、不容“被代表”的生命权则被其前辈们完完全全地“代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种立法方式产生的安乐死“法”的正当性何在?!
四、反证:安乐死没有立法建制的价值
法的施行极为重要:制定法律的目的是通过施行来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主体行为;良法往往不是一步到位,需要在施行后不断地修正才能成就,故有“法之价值在于施行”之说;[4]且依照哲学原理,施行(实践)还是法(正面或负面)价值体现的重要手段与方式。故在此,我们首先作一个前提假设,假设安乐死“法”被通过并施行;通过看其被“施行”后是否出现负面问题来确定其有无通过立法存在的必要和价值。
基于正义原则,笔者认为“非自愿安乐死”不是安乐死。这种类型的“安乐死”根本无法防止和排除基于为财及其他动机的谋杀,⑧而尽可能地管住、防止和杜绝任何危害因素是立法的“天然职责”,[5]因此不将其“入围”进行讨论。这里欲探讨的类型仅以签署“living will”(即“生前自愿选择安乐死”)者为限。
“living will”被医学界或卫生法学界称为“生前遗嘱”。然依笔者之见,此处的“living”应当有两次“生存”的含义,第一次为某人处于生存状态,第二次为某人决定其自身是否继续生存下去。因此,该词组的完整含义应为“(某人)生前所做的关于其届时(经临床确诊处于不可逆的终末期,下同)终止生存的遗嘱”,简称“生前终止生存遗嘱”。既为遗嘱,则应具有遗嘱的特性(法律特征),但“living will”某些方面并不符合遗嘱的共同特性。其一,遗嘱应是生前处分或安排、死后生效,而“living will”的生效肯定还处于遗嘱人生存的状态,否则无须实施安乐死。其二,在现代的共和制社会,遗嘱所能处分的只能是财产权益,不包含人身权利,当然更不包括生命权客体(生命),但“living will”所处理的正是人的生命。其三,遗嘱执行人在遗嘱所生效时,应依照遗嘱人的遗愿将遗嘱所涉标的交付该遗嘱所指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而“living will”的执行人则须是具有法定执业证书的医护人员,且未必是该will所指定的人。如某人在上海的某医院签署了“living will”,后到峨眉山旅游时遇险且处于“届时”状态,让其回上海由该院医护人员执行“living living”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完全可能在颠簸的途中去世)。
另一个问题是,签署“living will”后,在“届时”前,遗嘱人能否后悔与撤销?从法律性质上说,“living will”是民事法律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非契约型的双方法律行为)。在我国,即使是契约型的双方法律行为成立甚至生效后尚可以基于特定情形被撤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甚至规定消费者可以无理由退货;按理,作为单方面法律行为的遗嘱,在成立后、生效前无疑也是可以被撤销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历经25年举国的辩论和酝酿、世界上第一个以国会立法方式通过安乐死法且有多年相关实践的荷兰,依然出现3万余签署了“living will”的老人为躲避“被安乐死”而逃往德国等邻国的现象,[6]这只能被理解为老人们在签署“living will”后难以行使撤销权(即后悔渠道不畅)。试想,在国民对实施安乐死持支持态度的荷兰尚且如此,要是在人口众多、相当比例的民众压根儿不知道“安乐死”真实含义的我国立法施行安乐死制度的话,那后果真是令人不敢想象……
从施行的结果上看,安乐死立法这种决策实不足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采用立法方式正面设立安乐死制度无论在法理、医学理论和社会管理的论证上都存在悖论。因此,长期为我国安乐死立法不懈努力的人们不妨换个思路,采用形而下之个案剔除方式,即从相关个案研究中找出各个刑法之阻却违法事由成立的共同特性(即哲学中的共性因素)加以归纳、提炼,由此上升至法理(哲)学、伦理学高度,岂不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只不过,遗憾的是笔者至今对此尚未深入思考,实无发言权。
注释
①在我国,自杀死亡者依《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五款之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并不意味着可被免除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②我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
③这里仅指依照《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护士条例》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经依法注册取得相应执业证书的医护人员。
④即符合临床上特定条件,又被称为“在临床上具有实施安乐死的指征”。限于篇幅,本文只研讨相关的法律(理)问题,不涉及具体的医学技术问题,故在此不作展开。
⑤⑦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4月29日发布的最近一次(即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大陆)人口总数为1339724852人。
⑥据《新民晚报》2005年12月15日(转引新华社)报道,荷兰于2005年12月14日通过法案,允许在“特定情况下”,经患儿父母的许可(无须征得患儿本人的意愿),对“适格”病患儿童实施安乐死。
⑧连以签署“living will”为前提的荷兰也不能幸免,已发生多起此类的谋杀事件。资料来源:中华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网2007年6月12日老龄新闻栏下之国际老龄。
[1][美]林·亨特.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
[2][意]但丁.论世界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7.
[3][美]德沃金.认真对待人权[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8.
[4]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34.
[5][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206.
[6]姚立.荷兰老人出国躲避安乐死[N].环球时报,2004-02-11(06).
(责任编辑:王海容)
Life Decisions:an Insurmountable Legal Barrier for Euthanasia Legislation
Yao Ju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theory,the right to life,the most basic human rights,shall not be agented,and the legislature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the euthanasia legislation;and it lacks the feasibility and validity of euthanasia legislation by a referendum in our country.Therefore,it is infeasible to set a system of euthanasia by adopting positive legislation.
life decisions;euthanasia;legislation;validity
姚军,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