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道
2014-03-08丁真
丁真
味道
丁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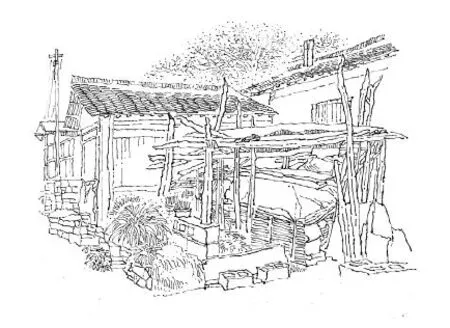
味道,水果的味道。我说我能闻出每一个城市的味道,我说每一个城市都有一种水果的味道。许多人都不相信,他们说怎么可能,城市怎么会有水果的味道。我说不仅城市如此,男人也是如此,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一种水果的味道,遇到我喜欢的水果,我就有了欲望。他们笑得就更厉害了,他们说要说男人身上有烟酒味我们倒是相信,要说有水果味我们是万不相信的。
我没有反驳,因为我确信我是有某一种超感觉的,就像我可以闻出某一种水果味一样。另外一点要说明的是,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就要上飞机了,他们听完后便争先恐后地挤来挤去,只有我一个人,慵慵懒懒地,握着登机牌,走在最后。
有什么可高兴的呢?不过是一个同学的婚礼、一个老姑娘的婚礼。我今天穿得光鲜艳丽、打扮得清透娇嫩,长途跋涉,为的是什么?难道就只是在昔日同窗好友的婚宴上吸引已婚的未婚的所有男人的眼球?
15排B座。我还是没有得到A座的机会,我永远都得不到靠近窗口的那个位置。机上还有人在窃窃私语,刚才那个女的是不是有点毛病,什么叫水果的味道?
我笑,表面上看上去笑得很温柔,其实很讽刺。在我笑的间隙有一个男人已悄然坐在我身边的位置上,他看了看我——或者又不是在看我,是在看靠窗口的位置——那里已经有人坐了。也许靠窗的位置是他的,但现在已被别人占了去——这些人的素质大抵如此。
正在我想着他是否会因此上前理论一番的时候,他却一声不吭地坐了下来。
他很高,很壮实。这是我唯一能感觉到的。我并没有去看他,我认为我这样去看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是不礼貌的,但是我感觉到了,一片水果湖。对,我脑海里唯一冒出的就是这个词。
水果湖,这是一个孩子在文章中曾经提到的,今天我在这里用上它了。有时我在想,水果湖,那是怎么一种香味呢?香,就只有一个香字能够表述,没有体味、没有风尘味,只有一种成熟水果发出的果香味,非常纯净。
这是我喜欢的味道。我深呼吸了一口,闭上了眼睛,飞机起飞得并不好,可能是因为气流的原因也可能是驾驶技术不好,总之在收起落架的瞬间机身颠簸了一下,这让我的耳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耳膜发胀的那一刹,我听到邻座的他对空姐说:机内的空气非常不好,太浑浊了。而空姐回答他说:您也知道,国内的环境就是这样,人的素质不高,自然什么味道都有。
味道。这是我非常敏感的词。我抬头看了一眼边上的男人,正好他也在看我,在长长的粗绒围巾包裹下,一张白净的脸,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有些孩子气。
不知道是哪本书上看到的,书上说要想嫁入豪门或者是钓到金龟婿就必须得先投资,也就是说你必须先挤到头等舱或者是高级的鸡尾酒会中去,才能在那里遇到那些上等人。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到这句话。或许不合适。
SPA。看杂志的时候我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去放松过了。推背?水疗?也许只有在放松的时候才能够清醒的面对自己。还有人生。
我和他是因为什么才聊起来的?我不记得了,大概是因为一杯水的缘故?或者是他在偶尔的一个细节的小动作上帮了我的忙,然后我说“谢谢”或说“不客气”接着就有了对白?
我把手机掏了出来——在下飞机通往出口的路上,他也是,我们都把手机颠来倒去地看,但是没有说一句话——我想他大概是想问我要电话号码,其实我也想问,但是谁都没有开这个口。然后就上了大巴、然后大巴开了、然后、然后……我们不紧不慢地聊天,聊一些空洞的、没有实际内容实际意义的话题,双方都没有听清楚对方在讲什么——至少我没有听清楚或者是没有认真去听他在讲什么。我们都在看手机,希望用语言能把话题带到“号码”这个词上来。
窗外飞过去一片片红的土地绿的树木白的房屋。他说,你来过这里么?我摇头,瞬间又点头。他糊涂了,我也糊涂了。他说,那你们那儿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比较喜欢旅游。我点头,没有你们城市美,但下次你若来,我给你当导游。
好啊,那我先得留一个你的电话。
我突然抬头。准确地说,是我们俩都突然抬头。也许我们都在等这个机会这句话,一直。像一级可以下台的台阶像一根可以救命的稻草,在大巴车,快驶到下车点的一刹那,铺垫了许久的那句话,终于出现。而接下来的动作几乎可以说一气呵成。
我感到周身充满了虚而爽的气息,当我踏上这块土地。就好像幼年时偷偷地在浴缸里撒了泡尿那般。这样一个邂逅事件虽然情节老套但却总能让人心潮澎湃。
汽车到站。到站广播声不合时宜地响起,他到了,我还得继续坐在位置上。
他没有继续话题,关于我和他的,也许因为是公共场合,又也许因为只是初次相见。
他只是扯了扯大衣,把长长的粗绒围巾拉过了嘴,伸出手向我示意一下。
再见。我嚅嗫着嘴,嘴角微微扯动,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
我永远会比对方多一点矜持。
酒宴就永远是那个场面。不管是谁,在这种场合喝醉的,就是傻逼。
新娘很美,谁都看不到那张厚厚的粉底涂抹下的真正的脸是怎么样的,也许会有几分沧桑几分怠倦甚至会是几分嫌恶,唯一不变的,是脸上凝固的笑容。
只有和现实中反差太大才会觉得妆后的脸是如此美丽。我对邻座的女伴说这句话的时候男生们正在拼酒,我们班的班长正在哄他第二任当教师的娇小玲珑的女友开心,而我的女伴正在喂他儿子吃饭。
我并不觉得这句话有多恶毒。然而可惜的是邻座的女伴没听到。
你的牙真好。班长的第二任女朋友对我说。
我看着她。就这么看着她。她穿着白底绿格子的衣服,白嫩的脸上有着一对小酒窝——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纯的女孩子了。
她提到了我的牙。让我想起近十几年来对牙科的无数次造访,那里白的墙绿的格子间黄的地板,还有无影灯。所有器皿上的味道,和医生身上的味道一样,那是一种叫来苏儿的消毒药水的味道。医生修长白皙冰凉的手,配合冰冷的器械,有力地撞击着我的每个牙齿、触动着我每条神经。那是一种可怕的呻吟,是开满鲜花的坟墓。
我向她凑过去,像狗一样地耸了耸鼻尖,使劲在她身上闻了闻,想闻出点什么花草的淡淡清香的体味来。
她惊了一下。
我感到失望,并不是因为我的行为让她受到了惊吓,而是因为我在她身上,只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水味,也许价格很昂贵,但明显地掺和有人工合成的成分,这种香味覆盖了她的体味,这种香味传染到我身上,让我毫不犹豫地打起了冷战。
这种情况下,我用了一个糟糕透顶的词,我说,你很风尘。
我确实是不明白她是如何理解“风尘”这两个字的,但我可以保证用了这个词绝对不是出于她讽刺我牙齿的一种报复。虽然在说了这个词以后我多少感到一阵轻微快感袭来但是我仍然坚持这个词在我的词语世界里面顶多属于中性词,之所以说这个词用得糟糕透顶是因为正是由于这个词的运用才使得后来的局势发展变得难以控制。
当时这个年轻气盛的女教师站了起来,注意,她是对着正在猜拳的男朋友也就是我们的班长站起来的,她用尖得像针尖一样的细长的声音调到最大音量说,我要回去!
班长下意识地甩掉了她搭过来的手——他肯定不是故意的,那时他正出三根手指头嘴里喊着六六顺之类的猜拳“术语”。他面红耳赤、神情激动,压根没顾上身边偶发的那些细节。
情况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她扳过班长的身子——要知道,要想扳动一个一米八五的壮汉的身子,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见当时她的愤怒,一定是到达了极点的。
我原以为她是会打他一个耳光的,也许我心里正在期待着这个结局,但是我没等到。这个娇小的女人用她涂抹了淡淡的唇彩的樱桃小口,狠狠地在班长的手上咬出了一个劳力士的形状。
班长发出一声沉闷的低吼声,拖着他特有长长的后鼻音。
喧闹中,唯有我们这一桌停了下来。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错,应该说是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在等待后面的故事。
我们的寂静没能坚持多久就被周围一浪高过一浪的叫喊声给吞没,男人们继续着他们的猜拳敬酒,女人们继续着她们的贪婪蚕食,孩子们,则不断地跑来跑去,对着台上高高叠起的香槟杯子发呆,对着台上摆放着的三层的大蛋糕,淌下了口水。有几个胆大的,上去用手指,狠狠地抠了一指头的奶油,放在嘴里使劲地吮吸,这才感受到了满足。
只有班长和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而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腕上的牙印——那不是劳力士,那只是无数个密密麻麻的小出血点,或者说,这是他本次恋爱的
终结通牒。而我,则在看着台上那顺着香槟杯外壁不断流淌下来的香槟汁,想象着那该是怎样香味的液体?竟然晶莹剔透竟然泛着金黄色的光芒?也许,我心里想着的,却是拆散一对是一对?
我不去看班长的脸也能体味到当那双高跟鞋“笃笃笃”的声音消失了以后的他的心情,一定比苦瓜好不了多少,也许消失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关键是那双高跟鞋是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消失的,这远比咬他一口更让他觉得郁闷。
他不能哭也不会哭。不管他心情怎样坏他也舍不得破坏自己那么长时间以来在我们心中建立起的这张酷酷的脸。
我有预感,这个,肯定又要黄了。也许,不久的将来会见到他的第三任女友了。我吐了一口气,朝着流淌下来的香槟的方向。是的,一定是好事。
什么叫把盏言欢?
我只看到他们在不停地推杯问盏。言欢?仿佛是的。然而我不是。
没有人对我感到惊叹,即使是这一身名贵又花心思准备的衣服,即使是这精心描拭过的清透的裸妆,也即使是手指上灯光下熠熠发光的钻石,再即使,就是这么近的路程,居然还是乘飞机来。他们和她们,什么惊讶都没有。
有时候,无人问津比丑陋更可怕。那种平淡的寂寞,让人无处可逃,让人歇斯底里的疯狂。
骡子喝醉了。不,也许是所有的男人都喝醉了。
骡子叫我出来的时候,我刚换上了睡衣在回答同屋也是刚才邻座女伴的有关于护肤用品的问题,我认为我身上还是具有让男人感到相当惊奇和迷惑的力量的,于是我走了出去。
电梯停在了一楼。骡子正在和酒店大厅总台的女服务员们调情,也许他只愿意做不花钱就可以享受一次精神上做爱的旅程,或者更加坦白地说,他兜里穷到只会叮当响的物质力量只支持他精神上的快感。
我径直走了过去,在靠近他的时候顺手从总台拿了份报纸,或许是体育板块,又或许是广告,总之一长着两颗兔子门牙的光溜溜的脑袋正咧着嘴朝我笑。我说,玩够了么?还不去睡?
我说这话的口气像是一个在教训不听话孩子的严厉母亲而不是一个操着吴侬软语的情人。
他乖乖地跟我进了电梯,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电梯门合上。在这个时间段几乎没有人进出这台电梯。
我用食指,轻轻地在“4”这个数字上摁下。骡子突然把我压在电梯壁上,用他的胳膊,紧紧地环住了我。
报纸,掉到了地上。
4楼到。骡子不顾我的挣扎,摁亮了“1”的数字键。
骡子的身上有一股浓烈的烟味和酒味,这是许多男人身上的体味,但却不是我想要的。我把头扭到一边,他贴上来的嘴亲到了我的脸颊,很难想象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见面礼。
电梯又回到了1楼。
夏天真不是个好季节,在衣衫单薄下我感受到了他下体膨胀到发硬。骡子说,求求你,就一次,一次好么?我心虚了,突然间宁愿自己身上所有令男人惊奇和迷惑的力量全部消失。我和骡子在看上去有些搞笑的相互挣扎场面中交换着摁下“4”和“1”这两个数字键。
电梯上上下下的运行,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它一定承受不了这样的折腾。我想。我也是,于是在最后一次电梯上到了4楼的时候,我使出吃奶的劲来,抽了骡子一个耳光。
骡子蹲了下去,呜呜地哭了起来,像个被冤枉的孩子。
我笑,笑得有些勉强、有些惨。目前这个状况比无人问津更难以想象。我捡起落在地上的报纸,终于看清楚了,那张脸是罗纳尔多,很清晰的轮廓。
一路狂奔,回了房间。
同屋的女伴正在哄儿子入睡,小宝宝响亮清醒的哭喊声一声一声地挑战着我的耳膜。女伴烦躁地说,今晚到现在我们家宝贝已经都尿了三次了,什么枕巾、浴巾,我都用上了,他妈的烦死了,早知道就不带这鬼东西出来了。
在这个房间里我闻到的是风尘味,一种初始悲哀的风尘味。女伴的皮肤从此将开始粗糙,她
将不再会花时间在着装打扮上而是把全部经历放在应付儿子上,她将失去一张花容月貌的脸和一副婀娜多姿的身段,换来的是由于长期抱孩子做家务而不断粗壮的四肢和长期在超级市场或农贸市场里因为一块钱青菜两块钱白菜双方可以形成口水大战而不断粗俗的话语。
女伴腾出空档,微笑着说,最近你在研究什么?
我附和地笑了两声,干巴巴。我说,体味。
女伴很好奇地说,那我是什么体味?
可能,水果味吧。
撒谎。我绝对撒谎了。
有些心虚。跟着她笑,也不知道自己在念叨什么,就只知道呆呆地坐在床沿上。女伴铺好了床,忽抬头问了一句:骡子找你干吗?
干吗干吗?我在思考着,没有回她的话,干吗?
我看着她,一眨不眨。她大概觉得问得有些失态,于是就慌张地补了一句:我也就这么随口一说。
我还是就这么看着她,盯着她,还有她怀里的她的宝贝儿子。然后就笑了起来,大声地笑,一口气从腹部直冲喉咙自嗓门而出,蔓延在这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旮旯。笑得自己都有些落魄笑到把她儿子都给怔住了。
末了,我重复了一句,是啊,骡子找我干吗呢?
我眯起眼,我知道她装作不在意其实在听我的下文,于是我说,我下去的时候,你猜怎么的?
她果然有了兴趣,怎么?
我装作很可笑地说,他呀,喝醉了,居然在酒店大厅总台和女服务员们在聊天,我下去拉他,他说,一块聊吧。我没说什么就回来了,他可能要和这些女人们聊一晚上了,醉了!
她的眼神里尽是失望的神情。
这个故事一点也不好笑。
但是我笑了,我笑了是因为她的失望,我让她失望了。我不像她们,不会因为一次长途跋涉就纵容自己去发生一夜故事,更何况,我已经不是如今街上十八九的大姑娘了,遇上帅哥就会立马发花痴。
她兴趣缺缺地说,我去叫我老公把骡子给拉回来,这个样子像什么话,太丢人了。
在她甩门而去的刹那,我轻轻地吐着字眼。
你越来越像是个成熟的女人——如此八卦。
这一次,我没说谎。
第二天早上的阳光,温暖的,如想象中妈妈的手,轻轻地拂着每个人的脸庞。我的脑袋发晕,我想我是病了,一种莫名的病因,以至于都想不起来,自己昨天晚上有没有做梦、做了什么梦。
对面男生的房间里,他们还在洗漱。骡子一个人坐在床上整理行李,看着电视里T型台上高挑婀娜的模特们一个个在他面前飘过,见我和女伴进来,只是淡淡一笑,他说,我要早些走,最近生意比较忙。然后就像那些个在他面前飘过的模特一样,在我们面前,陌生地飘过。
骡子的背影,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的背影,和大部分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的背影,没有什么区别。
陌生地飘过。他怎么能陌生飘过。就这么陌生飘过?过了一个不到五小时的夜,就好像陌生人一样,从我的面前飘过,拎着,他的行李。
我原本想从他的眼神里看到那种我原谅了他而使他感激的神情,但是,没有,眼里没有,脸上也没有。
我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记忆起来。
难道昨天晚上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难道我想不起的昨晚做的那个梦就是梦到了骡子?还是我真的喝醉了,醉得一塌糊涂?
我望着女伴,她怀里抱着的是她的宝贝儿子,这边拼命地往孩子嘴里塞奶嘴这边大声地对丈夫呵斥道:怎么还没有好啊,磨蹭什么!
只有阳光晒过干净的气味,停留在这个房间里。什么烈烟、什么烈酒的味道,都不复存在。而这,仅仅只是过了一夜。
于是,我们就像谁也不认识谁了一样。
可能,我们本就谁也不认识谁,这原本就是一次普通的旅行。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股味道,一种水果的味道。我在候机大厅里对一同候机的人说。再一
次。
哄笑。再一次。
异样的眼光。也再一次。
我视若无睹地拎起了包,从兜里掏出了机票,依旧是走在最后一个。
味道。水果湖的味道。那种仿佛陌生模糊于远古而又清晰在身边的味道,没有风尘、没有体味——成熟的果味。
抬头。一张孩子气的脸。小眼睛,鼻梁上架着一副斯文的眼镜,大格子的围巾,灰色混呢的大衣。
他熟练地扣上安全带,看都没看我,就说,我注意你很久了。
俗套的开场白让我笑了起来,于是我也不免俗地说:还是那个号码?
他点头,回了一句:你也是?
我们都笑了。
我说,你见到我不吃惊么?我们竟然这么……有缘。
是,我吃惊到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好,只好用最俗套的开场白了。
机舱内闷热的温度里混杂着乘客们的体味——各式各样的体味,而水果湖却能在这混沌的体味中依然清新。他说,这几天里你为什么没打电话给我呢?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只是点着头,小心翼翼地说,我忙,有点忙。后来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你为什么也从没打给过我?
他脸上竟然泛了一些红。他很不自然地说,我……也忙。
我们都相互理解地笑笑。在起落架放下的瞬间,他说,回去后,有空联系我,我的号码不变。
手心,微微地,微微地,出了些汗。我开启手机,找到他的号码,向他扬了扬,说,我的,也不变。
我们坐同一架飞机去了相同的城市又回来,难道还不算是所谓的千丝万缕的缘分?我手里握着手机,上面显示有他的号码,紧紧握着,然而,也就是这样握着了么?
我也曾经在那一个氤氲瞬间凭超六感以为会发生点什么。
然而,握着的,也仅仅是这样握着的。
在那匆匆一别以后,我再也没有打电话给他过,而他,也没有打过给我。看上去好像会发生点什么的都市浪漫情缘故事,仅有个开头,却没有人们想要的结尾。
感冒有些加重了,全身发软、没有胃口,只能不断地用纸巾擦拭去流出来的眼泪和鼻涕,眼睛也好像变得迷糊了,不知道应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接下来又该干什么。窗外的天气突然变得冷起来了,医院里输液大厅里挂针的大人们孩子们从里面一直,排队到了外面。房间里残余着暖气,耳塞里花儿乐团嘈杂欢乐的合唱声,面对着电脑屏幕,飞快地敲击着键盘。
在面前那杯热水腾腾上升热气的瞬间,我心里冒出一张模糊的脸。
味道。
对,味道。水果湖的味道。没有体味、没有风尘味,只有一种成熟水果发出的果香味,非常纯净。
